预约演示
更新于:2026-02-27
Brivekimig
更新于:2026-02-27
概要
基本信息
原研机构 |
非在研机构- |
权益机构- |
最高研发阶段临床2期 |
首次获批日期- |
最高研发阶段(中国)临床2期 |
特殊审评- |
登录后查看时间轴
结构/序列
Sequence Code 719981899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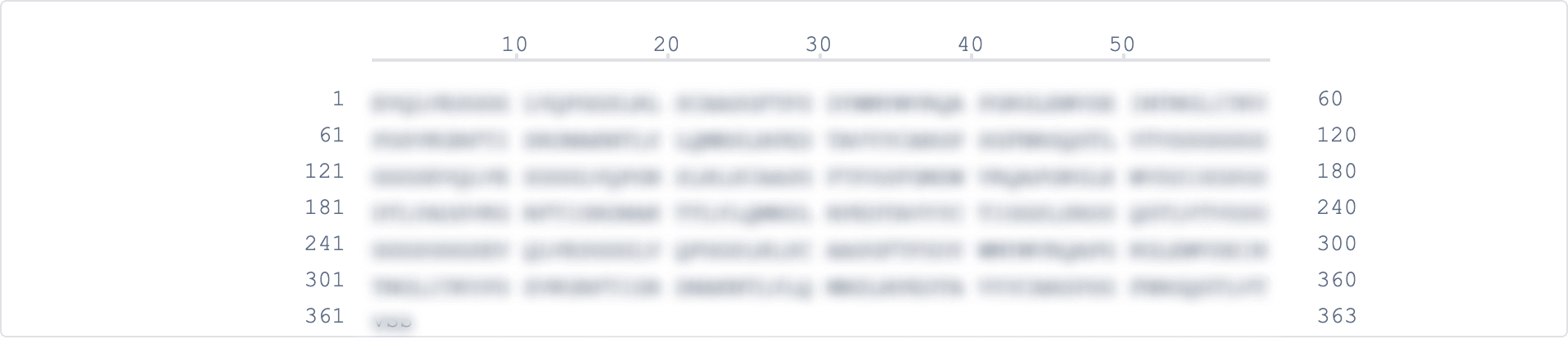
来源: *****
关联
7
项与 Brivekimig 相关的临床试验NCT07170917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Dose-ranging Phase 2 Study of Brivekimig Followed by a Maintenance Period in Participa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Hidradenitis Suppurativa
This is a Phase 2b, global, multicenter, sequential,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parallel group, dose-ranging study in participa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hidradenitis suppurativa.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ssess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brivekimig in a dose-ranging study of participa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HS.
Study details include:
The study duration (per participant) will be up to approximately 60 weeks for participants not transitioning into the long-term extension (LTE) study and will be up to approximately 52 weeks for participants transitioning into the LTE study.
The randomized treatment duration will be up to approximately 48 week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ssess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brivekimig in a dose-ranging study of participa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HS.
Study details include:
The study duration (per participant) will be up to approximately 60 weeks for participants not transitioning into the long-term extension (LTE) study and will be up to approximately 52 weeks for participants transitioning into the LTE study.
The randomized treatment duration will be up to approximately 48 weeks.
开始日期2025-11-06 |
申办/合作机构 |
NCT06975722
A Phase 2b, Multi-national, Multi-center,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Dose-ranging Study Followed by a Long-term Extension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SAR442970 in Adult Participa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Ulcerative Colitis
This is a phase 2b, randomized, double-blind, 3-arm study for the treatment of Ulcerative Colitis.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assess the efficacy of different doses of SAR442970 compared with placebo in participa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Ulcerative Colitis. The total study duration is up to 168 weeks, with a treatment period of up to 158 weeks including an open-label (OL) long-term extension (LTE) period of up to 104 weeks for eligible participants.
开始日期2025-07-07 |
申办/合作机构 |
NCT06958536
A Phase 2, Multicenter,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 Controlled, Dose-ranging Study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SAR442970 in Adul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Crohn's Disease
This is a phase 2b, randomized, double-blind, 3-arm study for the treatment of Crohn's disease.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assess the efficacy of different doses of SAR442970 compared with placebo in participa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Crohn's disease. The total study duration is up to 168 weeks, with a treatment period of up to 158 weeks including an open-label (OL) long-term extension (LTE) period of up to 104 weeks for eligible participants.
开始日期2025-06-03 |
申办/合作机构 |
100 项与 Brivekimig 相关的临床结果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100 项与 Brivekimig 相关的转化医学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100 项与 Brivekimig 相关的专利(医药)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29
项与 Brivekimig 相关的新闻(医药)2026-02-18
如果下一代炎症与免疫(I&I)疗法面临的最大障碍,并不是“找不到更好的靶点”,而是我们需要接受一个事实——单一靶点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足够,会怎样?这是一个行业在过去二十年里几乎从未认真发问的问题。Humira 的成功剧本太赚钱了,增长太容易了,而激励机制又太错位,以至于大家没有真正去直面生物学现实。如今,随着单靶点时代接近枯竭、而且“疗效天花板”在将近 50 个抗体都没能突破的情况下依旧纹丝不动,生物制药终于在尝试“抬高门槛”的道路上,全面拥抱多药联合与多靶点干预。2026 年有望成为这些努力的分水岭——也因此会成为 I&I 未来的分水岭。我们最初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故事要从 1998 年说起:Enbrel 与 Remicade 获批,它们是 I&I 领域最早获批的生物制剂。两者的早期成功引爆了“生物制剂热潮”,并定义了现代免疫学时代。到 2002 年,它们的年收入都超过 10 亿美元,成为首批在自身免疫适应症上达到“重磅药”(blockbuster)级别的生物药。同一年,Humira 获批用于类风湿关节炎(RA)治疗。Humira 的获批——作为首个全人源单克隆抗体——无疑是重大科学里程碑。但华尔街当时并不那么兴奋:分析师认为抗 TNF 类已经拥挤,质疑 Humira 相比嵌合抗体 Remicade 是否能形成差异化,并批评 Abbott 在 69 亿美元的交易中为这款药“鲁莽溢价”。Abbott 自己虽然强调 Humira 的多适应症潜力以支撑价格,但对销售预测也相当保守,认为 RA 峰值销售仅 10 亿美元。
23 年、11 个适应症、累计 2400 亿美元收入之后,Humira 已经证明:它对生物制药商业模式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它对科学的意义。在此过程中,Humira 成为“一药即管线(pipeline-in-a-product)”的原型,并把这种商业模式固化成全行业核心策略。今天最畅销的 I&I 生物药——Dupixent、Skyrizi、Stelara、Cosentyx 等——都是沿着这一蓝图一路走向“多重重磅药”地位。
在同样的 23 年间,新的作用机制与蛋白工程技术爆发式增长,推动 I&I 领域陆续获批近 50 个抗体药物,它们合计调节 15 个以上不同靶点,覆盖经典免疫通路的各个层面。这些药物让数以千万计的患者获益,许多也重塑了临床实践中的标准治疗。创新显著,但疗效为何“卡住了”?
I&I 的累计创新如此显著,以至于在某些适应症上,有人认为我们已经进入“终局”。例如银屑病中,Bimzelx 的 PASI-100 达到 60%+,树立了极高标杆。但对大多数适应症而言,未满足需求仍然存在。新的机制确实通过“换机制”“多线治疗”改善了结局,但整体上没能带来跃迁式疗效提升。在多数适应症里,尤其是更严重、更异质的疾病,临床最高水位线顽固地停滞不前:• 炎症性肠病(IBD):临床缓解率几乎仍停留在约 25–30%(均以安慰剂校正、诱导期终点评估为基准)• 类风湿关节炎(RA):ACR50 停留在约 30–40%• 中轴型脊柱关节炎(AxSpa):ASAS40 约 30–35%• 化脓性汗腺炎(HS):HiSCR50 约 40–45%• ……等等更简洁地说:“疗效天花板(Efficacy Ceiling)”。
从生物学角度,这个天花板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解释的。自身免疫疾病并不是由单一通路驱动的“单体”。它们更像是一个复杂生态系统:细胞因子失衡、异常的细胞群体、以及组织特异性因素共同作用;而且这些因素在不同患者之间不同,甚至同一患者在不同时间也会变化。阻断某一条通路往往能带来有意义的获益,但很少能覆盖所有驱动疾病的机制。在经历了数百万年的共同进化“军备竞赛”之后,冗余是特性,不是缺陷。
当生物学解释到此为止,市场结构与商业激励开始接管叙事。过去二十年里,I&I 生物药乘着“水涨船高”的浪潮:在生物药渗透率历史上很低的一批市场里,主要增长杠杆就是扩大生物药可及性。当“足够好”更低风险、且利润极其丰厚时,理性的经济主体自然会把更少资源投入高风险、可能改写范式的项目。如今,激励已经改变:最大适应症中的生物药渗透率已在约 60% 附近见顶;生物类似药采用终于加速;而且在越来越多选择的激烈竞争下,原研品牌市场被切得更碎。I&I 剩余的“空白空间”被卡在这层玻璃天花板之后,生物制药业也因此决心要把它打破。行业共识:联合用药与多特异性抗体
多数玩家逐渐收敛到两类偏好策略:生物药联合(co-formulation/组合)和/或多特异性抗体(multi-specific/bispecific 等)。看看今年 JP Morgan 医疗大会上大药企的表态就知道:J&J、Sanofi、UCB 都强调共制剂与/或多特异性是其 I&I 战略核心支柱。AbbVie 把 Skyrizi 定位为 I&I 联合疗法的“锚定资产”,并预测该产品线将长期持续增长。Regeneron 则公布了一个 IL-4 × IL-13 双抗,作为其 Dupixent 生命周期管理策略的核心——这点很值得注意,因为管理层经常贬低“me-better(同类更优)”资产(甚至就在同一场报告里依然火力全开)。
管线也印证了这些口径:在对 2025 年末超过 100 个大药企临床阶段 I&I 资产的分析中,约 70% 是生物药;在这部分里,约 25% 是联合用药或双抗。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买账。同样有趣的是仍在观望的一批玩家,其中包括一些当今最大的 I&I 产品线公司:Novartis、Roche、Eli Lilly、AstraZeneca。
谁对谁错?2026 年将揭示很多答案。 与过去几年零散的一两个数据点不同,今年临床催化剂密集,终于有望形成足够的数据体量,让我们更“落地”地讨论:联合与多特异性究竟是 I&I 的下一章,还是只是拥挤叙事的附录。要理解这个拐点,需要先理解我们怎么走到这里、又一路学到了什么。靶点与技术路线选择:从实验台到病床的启示
并不是所有组合都一样。历史上充满了“生物学上看起来合理、但临床没能转化”的组合,很多失败源于:毒性重叠被低估,或机制正交性(互补独立性)被高估。支持一个靶点组合的逻辑,应建立在第一性原理基础上:• 这些靶点/通路是否被证明能独立影响疾病病理生理?• 是否存在非冗余的证据?• 能否在临床前证明机制协同?
对已被临床验证的机制,综合基础生物学、人类遗传学、动物/模型数据、以及临床数据的整合分析,往往会给出清晰答案,这些问题的答案经常是“否”。
在此基础上,再叠加更“可转化”的现实因素来决定技术路线。与靶点本身同等重要的是用于调节靶点的“工具”。I&I 领域两种主流策略——抗体共制剂(两抗联合)与双特异性抗体——长期争论激烈,经常被描绘成零和的“你死我活”。但我更倾向于认为:两者最终都会在武器库中占有一席之地,各自的“领地”由它们更擅长的靶点组合决定。例如,两个靶点的丰度与定位就是关键变量:传统双抗格式可能更适合两个可溶性靶点、且血清浓度相近的组合;而当一个可溶性靶点浓度比另一个高出几个数量级时,或当膜结合靶点的 TMDD(靶点介导药物处置)使得其可溶性“搭档”难以被充分饱和时,双抗可能反而不如把两支单抗做成共制剂来得好。
当然,路线选择也会影响后续研发:• 双抗通常更难发现(自由度增加,需要精细工程与多参数协同),更难优化(例如 Fc 改造如 YTE 表现不稳定),也更难生产(轻链错配降低产率,需要更复杂纯化)。• 共制剂则更难开发——因为法规要求证明每个组分的独立贡献。
J&J 在 IBD 的 2b 期 DUET 研究把这个矛盾展示得淋漓尽致。为满足法规要求,每个试验设置了 6 个治疗臂:安慰剂、各单药、以及三个剂量的组合。为了保证把握度,两个试验分别入组约 575 与约 700 名患者,比历史上 IBD 单药 2 期试验平均规模大两倍以上;即便如此,只要临床缓解差异低于 20%,试验对“双重优效”检验的把握度仍不足 80%。规模扩大自然会传导到时间——两项 DUET 都用了约 22 个月完成入组,比历史基准慢约 6–9 个月——以及成本——保守估计至少是历史基准的两倍。若想看更细的成本颗粒度,可以关注 Spyre 在 2026 年及以后的损益表:其 2 期 SKYLINE 平台试验看起来很像 DUET-UC,而随着今年晚些时候安慰剂对照部分开始入组,这些成本会越来越“显形”。
最好的靶点组合,应当在科学逻辑与转化可行性上都“无懈可击”:遗传学、机制生物学、临床前模型、干预药理学共同指向正交且非冗余、并且能用成熟工具快速成药的通路。这个框架也受益于早期先行者把抗体联合与多特异性带到 I&I 患者身上的探索。尽管许多项目失败、而尚未失败的也大多仍处于早期与不成熟阶段,但从“好坏参半”的早期临床结果中,已经沉淀出重要的转化洞见。早期历史:联合疗法并不新鲜
I&I 中抗体联合的随机对照试验,最早可以追溯到 2000 年代初。2004–2007 年间,三项多中心、每项 100+ 患者的 RA RCT 发表了结果,测试 Enbrel(抗 TNF)、Kineret(抗 IL-1Rα)与 Orencia(CTLA4-Ig)的联合。结果几乎是最糟糕的版本:组合不仅没显示更优疗效,还带来 2–3 倍严重不良事件(SAE)与严重感染。
但并非所有数据点都那么负面:差不多同一时期,一项更小的 RCT 在克罗恩病患者中测试,在 Remicade(抗 TNF)稳态治疗、但仍未达缓解的情况下,加用 Tysabri(抗 α4 整合素)。多数疗效指标在数值上偏向组合,尤其在高风险患者中更明显;更重要的是,没有观察到额外安全性风险。即便如此,这个小而不确定的“正面信号”也很难对抗当时的新叙事。主流观点负面到什么程度?ACR 甚至更新指南,基于不利的获益-风险比,明确不推荐在 RA 中使用“双生物制剂联合”。尽管边缘地带仍有病例报告与单臂研究陆续出现,但“生物制剂联合”假设总体上被长期搁置。双抗兴起:又一次集体“交学费”
到了 2010 年代中期,随着 I&I 双特异性抗体的出现,多靶点概念再次回潮。与上述联合试验类似,这一代先驱也普遍未达预期,但过程中让行业学到不少。两条代表性项目是 Covagen 的 COVA322 与 AbbVie 的 ABT-122,几乎同时进入临床,靶向 TNF 与 IL-17A,依据来自临床前验证以及在 TNF 治疗患者中观察到 IL-17 与 Th17 升高。前者失败太快,来不及检验假设;后者在 RA 与银屑病关节炎(PsA)两个 2 期中与 Humira 头对头比较,ABT-122 均未优于 Humira。由于中和性 ADA(抗药抗体)发生率高,结论归因并不干净——可能还没真正检验到生物学假设。随后对两项试验做了事后暴露-反应分析,发现当摩尔暴露相当时,疗效无差异,也就意味着未检测到 IL-17 抑制的额外贡献。
ABT-122 之后,I&I 的双抗热度很长时间趋于沉寂,尽管其他治疗领域的双抗技术持续进步。直到 2018–2019 年,Bimekizumab(抗 IL-17A+F,现为 Bimzelx)为“双细胞因子中和”建立了明确的概念验证,多特异性才再次被大规模重启讨论。VEGA:联合疗法的“破门一脚”
在 Bimekizumab 为多特异性打开大门后不久,J&J 的 VEGA 试验又为抗体联合疗法打开了大门。VEGA 在以生物药初治为主的溃疡性结肠炎(UC)患者中,比较抗 IL-23 的 Guselkumab(Tremfya)+ 抗 TNF-α 的 Golimumab(Simponi)联合,与各自单药。这个组合不仅利用了 IBD 两个“老牌可靠战士”的信任基础,还建立在清晰且有说服力的生物学假设之上:IL-23 越来越被认为参与抗 TNF 耐药的形成,而多种临床前模型显示,同时在下游阻断 TNF、上游阻断 IL-23 具有明确协同。VEGA 于 2022 年首次公布,并最终为 I&I 的抗体联合拿到了一场胜利:第 12 周,联合达到 83% 临床应答,比单药高 8–12%;更亮眼的是临床缓解达到 47%,比单药高 22–23%。与第一代策略不同的是,这个联合的安全性与单药相当。疗效天花板被打破了——而且打破得很干净、很安全。
之后势头更盛。2023 年,Sanofi 的 Lunsekimig(IL-13 × TSLP)在哮喘 1b 期的早期数据颇具挑衅性,成为 Th2 驱动疾病的一个重要早期证据点。随后在 2023 年末到 2024 年,J&J 以累计 20 亿美元收购两项临床前期双抗资产,把市场情绪推到高烧。公司被密集孵化,合作与授权交易数十亿美元起步。2025:多特异性读出变多,也迎来现实校正
2025 年是首次出现多个、具有意义的多特异性读出的一年,代表这一主题开始走向成熟。但它也带来了现实校正:一些曾推动行业兴奋的资产未达预期。
首先,Sanofi 的 Lunsekimig(IL-13 × TSLP)哮喘 1b 期完整数据,远比人们想象的更模棱两可。此前披露、看似极其亮眼的 FeNO 信号实际上是“离群值”。药物未能带来更广泛的抗炎效果,如更深的嗜酸粒细胞抑制或肺功能改善,这让人怀疑其是否能在正在进行的哮喘 2 期中“抬高门槛”。
随后,J&J 在特应性皮炎(AD)的 2b 期中止了 JNJ-4939(IL-4Rα × IL-31),因为期中分析未达到内部疗效阈值(很可能是希望优于 Dupixent)。在 AD 中“瘙痒-抓挠”机制非常清楚,IL-4Rα 与 IL-31 通常被认为是最合理、低风险的靶点组合之一。J&J 当初愿意花 12.5 亿美元收购该资产就能说明这一点。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会学到更多,但“膜结合靶点 × 可溶性靶点”这一对的兼容性问题可能发挥了作用。至少,这一结果提醒我们:所谓“共识的低垂果实”也许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容易摘。
当然,也有成功。UCB 的 Galvokimig(IL-13 × IL-17A/F)在 2025 年给出了相当惊艳的概念验证点。其意在同时压制 Th2(IL-13)与 Th17(IL-17A/F)通路,以覆盖更广、更异质的 AD 人群。EADV 2025 上公布的 2a 期初步数据引发广泛关注:12 周时,Galvokimig 的安慰剂校正 EASI75 与 EASI90 分别达到 53% 与 43%。后者与 Dupixent 在 2b 期的表现相比也很有竞争力,暗示该机制可能确实实现了设计目标。但样本量很小,不应过度解读。
同一会议上,Sanofi 的 Brivekimig(TNF-α × OX40L)也上了头条。其逻辑是同时调控两个互补的炎症节点:TNF 驱动急性组织损伤与免疫细胞募集,而 OX40L-OX40 信号促进效应 T 细胞存活与增殖,维持慢性炎症。其在 HS 的 2a 期初步数据令人印象深刻:安慰剂校正 HiSCR50 与 HiSCR75 分别为 29% 与 32%,与 Bimzelx 在类似环境下的数据相当。同样,限制因素很多——小样本、生物药初治、高安慰剂应答——但开局依然强劲。2026 年日程:关键催化剂与潜在收获
在这样的背景下,2026 年正在成为 I&I “联合/多特异性假说”的关键一年。
1. J&J:JNJ-78934804(IL-23 × TNF-α)DUET-CD & DUET-UC这是迄今对“联合假说”最大、最扎实的一次检验。基于 VEGA 的概念验证,DUET 的读出将决定:在更难治的人群中,是否还能复制类似获益,并且通过更患者友好的固定剂量共制剂实现。很多人原本期待去年看到数据,但 J&J 对时间点一直很谨慎。两项试验的主要完成日期均为 2025 年 5 月,数据几乎肯定已近在眼前。
2. AbbVie:Skyrizi 联合平台试验(IL-23 × α4β7 & IL-23 × IL-1A/B)相较 DUET 获得的关注,Skyrizi 平台试验被严重低估。这是类似 DUET 的设计:约 500 名患者、生物药难治,可能会对 IBD 中两个最关键靶点对给出强有力判断。其中 IL-23 × α4β7 的意义更外溢,尤其关系到 Spyre 管线的命运。
3. Apogee:APG279(IL-13 + OX40L)在 AD任何一个试图在 1b 期就展示优于“王者 Dupixent”的试验都值得盯紧。此外,在 Th2 类别中,APG279 也是少数“共制剂”路线代表,处在多特异性汪洋中的另类样本。
4. UCB:Donzakimig(IL-13 × IL-22)在 AD除了 Galvokimig 的热度,UCB 的双抗组合里还有 Donzakimig:IL-13 配 IL-22(与皮肤屏障完整性相关)。尽管 IL-22 并不是多特异性热门靶点,但独立的抗 IL-22 单抗在 AD 中已有概念验证,而且通路正交性清晰。今年晚些时候的 AD 2a 期数据将首次真正检验这一假说,值得关注。
5. Sanofi:Lunsekimig(IL-13 × TSLP)在哮喘与 AD。鉴于 Sanofi 在哮喘 1 期数据披露上的“创意选择”,一项大样本、多剂量 2b 期读出将更能把“信号”与“噪声”分开。AD 方向兴趣相对较低,因为 TSLP 在 AD 中历史表现一般。
6. Pfizer:Tilrekimig(IL-4 × IL-13 × TSLP)与 PF-07264660(IL-4 × IL-13 × IL-33)在哮喘与 AD。Pfizer 的“三特异性(trispecific)”一直很吸引人:Tilrekimig 已进入 AD 2 期平台试验的第二阶段。Pfizer 迄今拒绝披露支持这一推进决策的数据,但他们显然“看到了一些东西”,并将 Tilrekimig 推进到哮喘独立 2b 期。2026 年应会带来更多清晰度。
7. 其他值得关注的项目Bambusa 的 BBT001(IL-4Rα × IL-31)在 AD(对“失败靶点对”的一次更干净二次尝试);Aclaris 的 ATI-052(IL-4Rα × TSLP)在哮喘与 AD(为“膜结合 × 可溶性”双抗结构的表现提供更多信息);Zura 的 Tibulizumab(IL-17A × BAFF)在 HS(少数同时调控 T 与 B 细胞的项目之一)。昙花一现,还是未来十年?
2025 年好坏参半的成绩,给越来越“共识化”的乐观预期注入了一剂健康的谦卑。挫折与成功都在强调靶点选择的重要性,同时也提醒我们:生物学不可预测,失败率不可避免。
尽管真正具备协同、并能突破疗效天花板的靶点组合,数量可能比多数人预期更少,但联合疗法与多特异性将是 I&I 下一个十年的决定性主题。 那些真正把门槛抬高的项目,会重塑治疗范式、重定义疗效预期,并为患者与投资者创造巨大价值。
2026 年不会给出全部答案,但它会是决定性的一年:第一次,数据足够密集、试验足够大、靶点多样性足够广,足以让讨论从“轶事”走向“经验主义”。I&I 的下一章正在此刻被写下——敬请期待。
申请上市
2026-02-14
序号
受理号
药品名称
药品类型
申请类型
注册分类
企业名称
承办日期
1
JYSB2600046
曲妥珠单抗注射液(皮下注射)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2.1
Roche Pharma (Schweiz) AG;F.Hoffmann-La Roche Ltd;
2026/2/14
2
JYSB2600045
帕妥珠曲妥珠单抗注射液(皮下注射)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Roche Pharma (Schweiz) AG;F. Hoffmann-La Roche Ltd;
2026/2/14
3
JYSB2600044
帕妥珠曲妥珠单抗注射液(皮下注射)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Roche Pharma (Schweiz) AG;F. Hoffmann-La Roche Ltd;
2026/2/14
4
JYSB2600043
注射用德曲妥珠单抗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Daiichi Sankyo Europe GmbH;Simtra Deutschland GmbH;
2026/2/14
5
JYHS2600003
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化药
进口
5.2
EUROPHARM LABORATOIRES CO LTD;JEAN-MARIE PHARMACAL CO. LTD.;U.Bon HealthTech Co.,Ltd.;
2026/2/14
6
JTH2600036
非布司他降解产物Ⅰ对照品
化药
F.I.S. – Fabbrica Italiana Sintetici S.p.A.;TEIJIN PHARMA LIMITED;安斯泰来制药(中国)有限公司;
2026/2/14
7
CYZB2600631
益心巴迪然吉布亚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6/2/14
8
CYHS2600493
盐酸丙卡特罗口服溶液
化药
仿制
4
海南广升誉制药有限公司;安徽永生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6/2/14
9
CYHB2600366
维U颠茄铝分散片
化药
补充申请
原5
修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修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4
10
CYHB2600365
羧甲司坦口服溶液
化药
补充申请
3
成都倍特得诺药业有限公司;成都倍特得诺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4
11
CYHB2600364
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V-SF)
化药
补充申请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14
12
CXSL2600233
YB1-X7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绍兴缮维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026/2/14
13
CXSL2600231
SHR-3079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026/2/14
14
CXSL2600230
SHR-3079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026/2/14
15
CXSL2600229
人胰岛素肠溶胶囊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2.1
合肥天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4
16
CXSL2600228
人胰岛素肠溶胶囊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2.1
合肥天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4
17
CXSL2600227
NEWR0919滴眼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深圳新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4
18
CXSL2600226
NEWR0919滴眼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深圳新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4
19
CXSL2600225
NEWR0919滴眼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深圳新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4
20
CXHL2600206
注射用TUL108
化药
新药
1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4
21
CXHL2600205
NH601缓释胶囊
化药
新药
2.2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恩华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4
22
CXHL2600204
NH601缓释胶囊
化药
新药
2.2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恩华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4
23
CXHL2600203
NH601缓释胶囊
化药
新药
2.2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恩华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4
24
JYSB2600042
吸附无细胞百白破灭活脊髓灰质炎和b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联合疫苗
预防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Sanofi Winthrop Industrie;Sanofi Winthrop Industrie;
2026/2/14
25
JYHZ2600044
布南色林片
化药
进口再注册
5.1
Sumitomo Pharma Co., Ltd.;Sumitomo Pharma Co.,Ltd. Suzuka Plant;无;
2026/2/14
26
JYHZ2600043
布南色林片
化药
进口再注册
5.1
Sumitomo Pharma Co., Ltd.;Sumitomo Pharma Co., Ltd. Suzuka Plant;无;
2026/2/14
27
JXSS2600011
注射用索特西普
治疗用生物制品
进口
3.1
Merck Sharp & Dohme LLC;Patheon Italia S.p.A.;MSD R&D (China) Co., Ltd.;
2026/2/14
28
JXSS2600010
注射用索特西普
治疗用生物制品
进口
3.1
Merck Sharp & Dohme LLC;Patheon Italia S.p.A.;MSD R&D (China) Co., Ltd.;
2026/2/14
29
JXSB2600028
20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
预防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3.1
Pfizer Europe MA EEIG;Pfizer Ireland Pharmaceuticals;
2026/2/14
30
JXHB2600019
注射用JX10
化药
补充申请
1
Corxel Pharmaceuticals, Inc.;Fuji Yakuhin Co., Ltd;
2026/2/14
31
JTH2600035
非布司他对照品
化药
F.I.S. – Fabbrica Italiana Sintetici S.p.A.;TEIJIN PHARMA LIMITED;安斯泰来制药(中国)有限公司;
2026/2/14
32
JTH2600034
盐酸丙嗪
化药
PCAS FINLAND OY;PCAS;华益药业科技(安徽)有限公司;
2026/2/14
33
JTH2600033
布立西坦
化药
United States Pharmacopeial Convention 美国药典委员会;United States Pharmacopeial Convention 美国药典委员会;浙江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4
34
CYZB2600630
感冒止咳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4
35
CYZB2600629
舒血宁注射液
中药
补充申请
山西振东泰盛制药有限公司;山西振东泰盛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4
36
CYZB2600628
牛黄上清丸
中药
补充申请
广州诺金制药有限公司;广州诺金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4
37
CYZB2600627
生脉饮
中药
补充申请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厂;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厂;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唐山)有限公司;
2026/2/14
38
CYZB2600626
灵精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4
39
CYZB2600625
朱砂安神丸
中药
补充申请
广州诺金制药有限公司;广州诺金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4
40
CYZB2600624
健脾丸
中药
补充申请
广州诺金制药有限公司;广州诺金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4
41
CYSB2600072
瑞基奥仑赛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上海药明巨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苏州药明巨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4
42
CYSB2600071
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众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君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2026/2/14
43
CYSB2600070
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君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苏州众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4
44
CYSB2600069
贝伐珠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博之锐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4
45
CYHS2600492
碳酸镧咀嚼片
化药
仿制
4
成都纵联医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太极集团四川太极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4
46
CYHS2600491
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VII)
化药
仿制
4
湖北一半天制药有限公司;湖北一半天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4
47
CYHS2600490
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VII)
化药
仿制
4
湖北一半天制药有限公司;湖北一半天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4
48
CYHS2600489
玻璃酸钠滴眼液
化药
仿制
4
乐泰药业(海南)有限公司;乐泰药业(海南)有限公司;
2026/2/14
49
CYHS2600488
磷苯妥英钠注射用浓溶液
化药
仿制
3
海南慧通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北大高科华泰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4
50
CYHS2600486
磷苯妥英钠注射用浓溶液
化药
仿制
3
海南慧通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北大高科华泰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4
51
CYHS2600483
来那度胺胶囊
化药
仿制
4
山东丹红制药有限公司;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4
52
CYHS2600482
盐酸右哌甲酯缓释胶囊
化药
仿制
3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6/2/14
53
CYHS2600481
盐酸右哌甲酯缓释胶囊
化药
仿制
3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6/2/14
54
CYHS2600480
钠钾镁钙注射用浓溶液
化药
仿制
3
江西泰吉立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赛默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4
55
CYHS2600477
利奈唑胺片
化药
仿制
4
湖南明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明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4
56
CYHS2600476
枸橼酸西地那非口崩片
化药
仿制
4
华泰民康(沈阳)科技有限公司;苏州特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4
57
CYHS2600475
地西泮鼻喷雾剂
化药
仿制
4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4
58
CYHB2600363
枸橼酸氢钾钠颗粒
化药
补充申请
4
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4
59
CYHB2600362
左乙拉西坦缓释颗粒
化药
补充申请
2.2
神基(上海)制药有限公司;江苏安必生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4
60
CYHB2600361
利伐沙班片
化药
补充申请
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4
61
CYHB2600360
注射用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
化药
补充申请
4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润众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4
62
CYHB2600359
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化药
补充申请
扬子江药业集团广州海瑞药业有限公司;扬子江药业集团广州海瑞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4
63
CYHB2600358
氢溴酸伏硫西汀片
化药
补充申请
4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4
64
CYHB2600357
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化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4
65
CYHB2600356
替格瑞洛片
化药
补充申请
4
乐声药业石家庄有限公司;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4
66
CYHB2600355
替格瑞洛片
化药
补充申请
4
乐声药业石家庄有限公司;江苏利泰尔药业有限公司;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4
67
CXSS2600022
达尔扑拜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4
68
CXSS2600021
芮特韦拜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珠海泰诺麦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泰诺麦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4
69
CXSS2600020
库莱韦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瑞阳(山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瑞阳(山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4
70
CXSL2600223
SHR-1819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广东恒瑞医药有限公司;
2026/2/14
71
CXSL2600222
SHR-1819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广东恒瑞医药有限公司;
2026/2/14
72
CXSL2600221
注射用DEC003M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杭州多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4
73
CXSL2600220
注射用SIBP-A17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2026/2/14
74
CXSB2600034
注射用SHR-A1912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1
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026/2/14
75
CXSB2600033
IBI354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1
信达生物医药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2026/2/14
76
CXSB2600032
注射用DB-1310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1
映恩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2026/2/14
77
CXHL2600202
VV261片
化药
新药
1
旺山旺水(上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苏州旺山旺水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2026/2/14
78
CXHL2600201
VV261片
化药
新药
1
旺山旺水(上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苏州旺山旺水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2026/2/14
79
CXHL2600200
VV261片
化药
新药
1
旺山旺水(上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苏州旺山旺水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2026/2/14
80
CXHL2600199
注射用THM401
化药
新药
1
成都四面体药物研究有限公司;四面体(乐山)药物研究有限公司;
2026/2/14
81
CXHL2600198
LNK01004软膏
化药
新药
1
凌科药业(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4
82
CXHL2600197
LNK01004软膏
化药
新药
1
凌科药业(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4
83
CXHL2600196
AF02片
化药
新药
1
南京寰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4
84
CXHL2600195
AF02片
化药
新药
1
南京寰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4
85
CXHL2600194
甲磺酸伏美替尼片
化药
新药
2.4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4
86
CXHL2600193
MN-08眼用凝胶
化药
新药
1
广州喜鹊医药有限公司;
2026/2/14
87
CXHL2600192
MN-08眼用凝胶
化药
新药
1
广州喜鹊医药有限公司;
2026/2/14
88
CXHL2600191
MN-08眼用凝胶
化药
新药
1
广州喜鹊医药有限公司;
2026/2/14
89
CXHL2600190
MN-08眼用凝胶
化药
新药
1
广州喜鹊医药有限公司;
2026/2/14
90
CXHL2600188
PD-001R片
化药
新药
1
智仁药业(珠海横琴)有限公司;
2026/2/14
91
CXHB2600047
HSK47977片
化药
补充申请
1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4
92
CXHB2600046
HSK47977片
化药
补充申请
1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4
93
CXHB2600045
SYHA1813口服溶液
化药
补充申请
1
上海润石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4
94
CXHB2600044
DZD6008片
化药
补充申请
1
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4
95
CXHB2600043
DZD6008片
化药
补充申请
1
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4
96
JYHZ2600042
棕榈酸帕利哌酮注射液
化药
进口再注册
Janssen-Cilag International NV;Janssen Pharmaceutica N.V.;Xian Janssen Pharmaceutical Ltd.;
2026/2/13
97
JYHZ2600041
棕榈酸帕利哌酮注射液
化药
进口再注册
Janssen-Cilag International NV;Janssen Pharmaceutica N.V.;Xian Janssen Pharmaceutical Ltd.;
2026/2/13
98
JYHZ2600040
棕榈酸帕利哌酮注射液
化药
进口再注册
Janssen-Cilag International NV;Janssen Pharmaceutica N.V.;Xian Janssen Pharmaceutical Ltd.;
2026/2/13
99
CYZB2600623
复方重楼酊
中药
补充申请
贵州圣济堂制药有限公司;贵州圣济堂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3
100
CYHS2600487
盐酸伊达比星注射液
化药
仿制
3
广东星昊药业有限公司;广东星昊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3
101
CYHS2600485
帕利哌酮缓释片
化药
仿制
4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3
102
CYHS2600484
帕利哌酮缓释片
化药
仿制
4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3
103
CYHS2600479
丙泊酚乳状注射液
化药
仿制
4
浙江华海制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华海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3
104
CYHS2600478
丙泊酚乳状注射液
化药
仿制
4
浙江华海制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华海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3
105
CYHS2600474
盐酸奥洛他定滴眼液
化药
仿制
4
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3
106
CYHS2600473
沙库巴曲缬沙坦钠片
化药
仿制
4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坪山制药有限公司;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坪山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3
107
CYHS2600472
沙库巴曲缬沙坦钠片
化药
仿制
4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坪山制药有限公司;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坪山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3
108
CYHS2600471
盐酸氮?斯汀滴眼液
化药
仿制
4
安徽康融药业有限公司;安徽康融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3
109
CYHB2600354
氟比洛芬凝胶贴膏
化药
补充申请
4
南京海纳制药有限公司;南京海纳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3
110
CYHB2600353
乳酸钠林格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3
111
CYHB2600352
碳酸氢钠片
化药
补充申请
原6
广州市陌希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江苏艾迪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3
112
CXSL2600224
抗蜂毒血清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3
113
CXSL2600219
人源肾祖细胞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广州华越肾科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3
114
CXSL2600218
QLS2322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上海齐鲁制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2026/2/13
115
CXHL2600189
RFUS-188注射液
化药
新药
1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6/2/13
116
CXHL2600187
PD-001R片
化药
新药
1
智仁药业(珠海横琴)有限公司;
2026/2/13
117
CXHL2600186
ZD2202
化药
新药
2.2
浙江智达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3
118
JYSB2600041
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子VIII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Takeda Manufacturing Austria AG;Baxalta Manufacturing Sàrl;
2026/2/13
119
JYSB2600040
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子VIII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Takeda Manufacturing Austria AG;Baxalta Manufacturing Sàrl;
2026/2/13
120
JYSB2600039
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子VIII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Takeda Manufacturing Austria AG;Baxalta Manufacturing Sàrl;
2026/2/13
121
JYSB2600038
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子VIII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Takeda Manufacturing Austria AG;Baxalta Manufacturing Sàrl;
2026/2/13
122
JYHB2600098
复方氯丝右哌甲酯胶囊
化药
补充申请
5.1
Commave Therapeutics SA;Catalent Greenville, Inc.;
2026/2/13
123
JYHB2600097
复方氯丝右哌甲酯胶囊
化药
补充申请
5.1
Commave Therapeutics SA;Catalent Greenville, Inc.;
2026/2/13
124
JYHB2600096
复方氯丝右哌甲酯胶囊
化药
补充申请
5.1
Commave Therapeutics SA;Catalent Greenville, Inc.;
2026/2/13
125
JXSS2600009
注射用德曲妥珠单抗
治疗用生物制品
进口
2.2
Daiichi Sankyo Europe GmbH;Simtra Deutschland GmbH;DAIICHI SANKYO(CHINA)HOLDINGS CO.,LTD.;
2026/2/13
126
JXSB2600027
AZD0486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1
AstraZeneca AB;AstraZeneca Nijmegen B.V.;
2026/2/13
127
JXSB2600026
AZD0486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1
AstraZeneca AB;AstraZeneca Nijmegen B.V.;
2026/2/13
128
JXHS2600026
Baxdrostat片
化药
进口
1
AstraZeneca AB;AstraZeneca AB;AstraZeneca Global R&D (China) Co., Ltd.;
2026/2/13
129
JXHS2600025
Baxdrostat片
化药
进口
1
AstraZeneca AB;AstraZeneca AB;AstraZeneca Global R&D (China) Co., Ltd.;
2026/2/13
130
JXHL2600055
Brenipatide注射液
化药
进口
1
Eli Lilly and Company;Lilly Suzhou Pharmaceutical Co.,Ltd.;
2026/2/13
131
JXHL2600054
Brenipatide注射液
化药
进口
1
Eli Lilly and Company;Lilly Suzhou Pharmaceutical Co.,Ltd.;
2026/2/13
132
JXHL2600053
Brenipatide注射液
化药
进口
1
Eli Lilly and Company;Lilly Suzhou Pharmaceutical Co.,Ltd.;
2026/2/13
133
JXHL2600052
RO7795068注射液
化药
进口
1
F. Hoffmann-La Roche Ltd;Roche (China) Holding Ltd.;
2026/2/13
134
JXHL2600051
RO7795068注射液
化药
进口
1
F. Hoffmann-La Roche Ltd ;Roche (China) Holding Ltd.;
2026/2/13
135
JXHL2600050
Brenipatide注射液
化药
进口
1
Eli Lilly and Company;Lilly Suzhou Pharmaceutical Co.,Ltd.;
2026/2/13
136
JXHL2600049
RO7795068注射液
化药
进口
1
F. Hoffmann-La Roche Ltd ;Roche (China) Holding Ltd.;
2026/2/13
137
JXHL2600048
Brenipatide注射液
化药
进口
1
Eli Lilly and Company;Lilly Suzhou Pharmaceutical Co.,Ltd.;
2026/2/13
138
JXHL2600047
RO7795068注射液
化药
进口
1
F. Hoffmann-La Roche Ltd ;Roche (China) Holding Ltd.;
2026/2/13
139
JXHL2600046
RO7795068注射液
化药
进口
1
F. Hoffmann-La Roche Ltd ;Roche (China) Holding Ltd.;
2026/2/13
140
JXHL2600045
Brenipatide注射液
化药
进口
1
Eli Lilly and Company;Lilly Suzhou Pharmaceutical Co.,Ltd.;
2026/2/13
141
JXHL2600044
RO7795068注射液
化药
进口
1
F. Hoffmann-La Roche Ltd ;Roche (China) Holding Ltd.;
2026/2/13
142
JXHB2600018
AZD5305
化药
补充申请
1
AstraZeneca AB;AstraZeneca AB;AstraZeneca AB;
2026/2/13
143
JXHB2600017
AZD5305
化药
补充申请
1
AstraZeneca AB;AstraZeneca AB;AstraZeneca AB;
2026/2/13
144
JXHB2600016
AZD5305
化药
补充申请
1
AstraZeneca AB;AstraZeneca AB;AstraZeneca AB;
2026/2/13
145
JXHB2600015
AZD5305
化药
补充申请
1
AstraZeneca AB;AstraZeneca AB;AstraZeneca AB;
2026/2/13
146
JTS2600028
Tozorakimab原液
生物制品
AstraZeneca Pharmaceuticals LP;AstraZeneca AB;阿斯利康全球研发(中国)有限公司;
2026/2/13
147
JTS2600027
Tozorakimab注射液
生物制品
AstraZeneca AB;AstraZeneca AB;阿斯利康全球研发(中国)有限公司;
2026/2/13
148
JTS2600026
Tozorakimab注射液
生物制品
AstraZeneca AB;AstraZeneca AB;阿斯利康全球研发(中国)有限公司;
2026/2/13
149
JTH2600032
14-羟基吗啡酮
化药
Purisys LLC;Purisys LLC;萌蒂(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3
150
CYZB2600622
肥儿宝冲剂
中药
补充申请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3
151
CYZB2600621
复方金钱草清热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3
152
CYZB2600620
补血催生丸
中药
补充申请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3
153
CYZB2600619
藿香正气丸
中药
补充申请
山西正来制药有限公司;山西正来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3
154
CYZB2600618
藿香正气丸
中药
补充申请
山西正来制药有限公司;山西正来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3
155
CYZB2600617
壮腰健肾片
中药
补充申请
景忠山国药(唐山)有限公司;景忠山国药(唐山)有限公司;
2026/2/13
156
CYZB2600616
牛黄净脑片
中药
补充申请
景忠山国药(唐山)有限公司;景忠山国药(唐山)有限公司;
2026/2/13
157
CYZB2600615
复方枇杷糖浆
中药
补充申请
江右制药(常德)有限公司;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3
158
CYZB2600614
山莨菪麝香膏
中药
补充申请
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
2026/2/13
159
CYZB2600613
复方丹参片
中药
补充申请
修正药业集团(湖南)药业有限公司;通药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3
160
CYZB2600612
十二乌鸡白凤丸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半边天药业有限公司;江西半边天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3
161
CYZB2600611
十二乌鸡白凤丸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半边天药业有限公司;江西半边天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3
162
CYZB2600610
肾宝糖浆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半边天药业有限公司;江西半边天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3
163
CYZB2600609
小儿感冒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四川巴中普瑞制药有限公司;四川巴中普瑞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3
164
CYZB2600608
生脉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山西正来制药有限公司;河北百善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3
165
CYZB2600607
牛黄上清丸
中药
补充申请
山西正来制药有限公司;山西正来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3
166
CYZB2600606
知柏地黄丸
中药
补充申请
山西正来制药有限公司;山西正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3
167
CYZB2600605
龙胆泻肝丸
中药
补充申请
山西正来制药有限公司;山西正来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3
168
CYZB2600604
天王补心丸
中药
补充申请
山西正来制药有限公司;山西正来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3
169
CYSB2600068
贝那鲁肽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上海仁会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仁会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3
170
CYSB2600067
贝那鲁肽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上海仁会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仁会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3
171
CYSB2600066
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原2
北京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北京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3
172
CYSB2600065
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原2
北京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北京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3
173
CYSB2600064
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原2
北京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北京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3
174
CYHS2600470
夫西地酸乳膏
化药
仿制
4
山西泽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3
175
CYHS2600469
环孢素滴眼液(Ⅲ)
化药
仿制
4
广东权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珠海亿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3
176
CYHS2600468
洛索洛芬钠凝胶贴膏
化药
仿制
4
湖南一格制药有限公司;湖南一格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3
177
CYHS2600467
秋水仙碱片
化药
仿制
3
厦门紫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安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3
178
CYHS2600466
非奈利酮片
化药
仿制
4
九华华源药业(桂林)有限公司;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3
179
CYHS2600465
玻璃酸钠滴眼液
化药
仿制
4
广州华圣制药有限公司;广州华圣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3
180
CYHS2600464
非奈利酮片
化药
仿制
4
九华华源药业(桂林)有限公司;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3
181
CYHS2600463
格隆溴铵新斯的明注射液
化药
仿制
3
浙江沣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3
182
CYHS2600462
盐酸米诺环素胶囊
化药
仿制
4
浙江创新生物有限公司;浙江创新生物有限公司;
2026/2/13
183
CYHS2600461
盐酸米诺环素胶囊
化药
仿制
4
浙江创新生物有限公司;浙江创新生物有限公司;
2026/2/13
184
CYHS2600460
吡美莫司乳膏
化药
仿制
4
重庆万霖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3
185
CYHS2600459
硫酸氨基葡萄糖胶囊
化药
仿制
4
江西铜鼓仁和制药有限公司;江西铜鼓仁和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3
186
CYHS2600458
枸橼酸西地那非口溶膜
化药
仿制
3
海南慧通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欣峰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3
187
CYHB2600351
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4
信合援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信合援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3
188
CYHB2600350
富马酸贝达喹啉片
化药
补充申请
4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3
189
CYHB2600349
卡贝缩宫素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辉凌制药(中国)有限公司;辉凌制药(中国)有限公司;
2026/2/13
190
CYHB2600348
浓氯化钠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海南倍特药业有限公司;海南倍特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3
191
CYHB2600347
呋塞米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3
192
CYHB2600346
硝酸甘油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3
中山万汉制药有限公司;中山万汉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3
193
CYHB2600345
罗库溴铵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原6
峨眉山通惠制药有限公司;峨眉山通惠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3
194
CYHB2600344
盐酸克林霉素胶囊
化药
补充申请
原6
广州市陌希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江苏艾迪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3
195
CYHB2600343
伊曲康唑胶囊
化药
补充申请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3
196
CXSL2600216
IBR900细胞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英百瑞(杭州)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026/2/13
197
CXSL2600215
IBR900细胞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英百瑞(杭州)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026/2/13
198
CXSL2600213
IBR900细胞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英百瑞(杭州)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026/2/13
199
CXSL2600211
QL2109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2.2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3
200
CXSL2600210
注射用QLS4131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3
201
CXHS2600032
注射用罗哌卡因微晶
化药
新药
2.2
浙江萃泽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浙江萃泽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026/2/13
202
CXHS2600031
盐酸莫托咪酯注射液
化药
新药
1
锦州奥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锦州奥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6/2/13
203
CXHS2600030
盐酸氨溴索口溶膜
化药
新药
2.2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3
204
CXHL2600185
注射用JKN2501
化药
新药
1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3
205
JTS2600025
达依泊汀α注射液
生物制品
協和キリン株式会社;協和キリン株式会社;山东百诺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2
206
JTS2600024
达依泊汀α注射液
生物制品
協和キリン株式会社;協和キリン株式会社;山东百诺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2
207
CYZB2600603
东乐膏
中药
补充申请
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颈复康集团保定东方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2
208
CYZB2600602
东乐膏
中药
补充申请
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颈复康集团保定东方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2
209
CYZB2600601
东乐膏
中药
补充申请
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颈复康集团保定东方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2
210
CYZB2600600
冠心膏
中药
补充申请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2
211
CYHS2600457
替米沙坦片
化药
仿制
4
太康海恩药业有限公司;太康海恩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2
212
CYHS2600456
替米沙坦片
化药
仿制
4
太康海恩药业有限公司;太康海恩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2
213
CXSS2600019
SHR-1918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北京盛迪医药有限公司;广东恒瑞医药有限公司;
2026/2/12
214
CXSL2600217
注射用ZL-6201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再鼎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2026/2/12
215
CXSL2600214
人前脑神经前体细胞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上海霍健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浙江霍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2026/2/12
216
CXSL2600212
人前脑神经前体细胞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上海霍健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浙江霍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2026/2/12
217
CXSL2600209
注射用SKB565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四川科伦博泰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2
218
CXSL2600208
泰它西普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2.1;2.2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2
219
CXHL2600184
BDHK-2009片
化药
新药
1
博迪贺康(绍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026/2/12
220
CXHL2600183
BDHK-2009片
化药
新药
1
博迪贺康(绍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026/2/12
221
CXHL2600182
TM471-1胶囊
化药
新药
1
知微药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2026/2/12
222
CXHL2600181
TM471-1胶囊
化药
新药
1
知微药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2026/2/12
223
JYSB2600037
注射用维得利珠单抗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3.1
Takeda Pharma A/S;Taked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td.;
2026/2/12
224
JYSB2600036
注射用A型肉毒毒素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3.1
Merz Pharmaceuticals GmbH;Merz Pharma GmbH & Co.KGaA;
2026/2/12
225
JYSB2600035
注射用A型肉毒毒素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3.1
Merz Pharmaceuticals GmbH;Merz Pharma GmbH & Co.KGaA;
2026/2/12
226
JYSB2600034
格菲妥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1
Roche Pharma (Schweiz) AG;Roche Diagnostics GmbH;
2026/2/12
227
JYSB2600033
格菲妥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Roche Pharma (Schweiz) AG;Roche Diagnostics GmbH;
2026/2/12
228
JYHZ2600039
盐酸文拉法辛缓释胶囊
化药
进口再注册
Upjohn US 2 LLC;Pfizer Ireland Pharmaceuticals Unlimited Company;Viatris Pharmaceuticals Co., Ltd.;
2026/2/12
229
JYHZ2600038
盐酸文拉法辛缓释胶囊
化药
进口再注册
Upjohn US 2 LLC ;Pfizer Ireland Pharmaceuticals Unlimited Company;Viatris Pharmaceuticals Co., Ltd.;
2026/2/12
230
JYHZ2600037
盐酸文拉法辛缓释胶囊
化药
进口再注册
Upjohn US 2 LLC;Pfizer Ireland Pharmaceuticals Unlimited Company;Viatris Pharmaceuticals Co., Ltd.;
2026/2/12
231
JYHZ2600036
盐酸文拉法辛缓释胶囊
化药
进口再注册
Upjohn US 2 LLC ;Pfizer Ireland Pharmaceuticals Unlimited Company;Viatris Pharmaceuticals Co., Ltd.;
2026/2/12
232
JYHZ2600035
注射用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
化药
进口再注册
ABBOTT LABORATORIES DE MEXICO, S.A. DE C.V.;DELPHARM SAINT REMY;Shanghai Abbott Pharmaceutical Co., Ltd.;
2026/2/12
233
JYHZ2600034
注射用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
化药
进口再注册
ABBOTT LABORATORIES DE MEXICO, S.A. DE C.V.;DELPHARM SAINT REMY;Shanghai Abbott Pharmaceutical Co., Ltd.;
2026/2/12
234
JXSB2600025
Ziltivekimab 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1
Novo Nordisk A/S;Vetter Pharma-Fertigung GmbH & Co. KG;
2026/2/12
235
JXSB2600024
elranatamab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1
Pfizer Inc.;Pharmacia & Upjohn Company LLC;
2026/2/12
236
JXSB2600023
elranatamab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1
Pfizer Inc.;Pharmacia & Upjohn Company LLC;
2026/2/12
237
JTS2600023
达依泊汀α注射液
生物制品
協和キリン株式会社;協和キリン株式会社;山东百诺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2
238
CYZB2600599
伤风停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2
239
CYZB2600598
健骨生丸
中药
补充申请
原3
北京匡达制药厂;北京匡达制药厂;
2026/2/12
240
CYZB2600597
安宫牛黄丸
中药
补充申请
孔圣堂(唐山)制药有限公司;孔圣堂(唐山)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2
241
CYZB2600596
养血安神片
中药
补充申请
山东润中药业有限公司;烟台渤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2026/2/12
242
CYZB2600595
归脾丸
中药
补充申请
江右制药(常德)有限公司;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2
243
CYZB2600594
祖师麻关节止痛膏
中药
补充申请
甘肃泰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甘肃泰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12
244
CYZB2600593
冠心膏
中药
补充申请
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颈复康集团保定东方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2
245
CYZB2600592
胃舒宁片
中药
补充申请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2
246
CYHS2600455
盐酸奥布卡因滴眼液
化药
仿制
4
润尔眼科药物(广州)有限公司;润尔眼科药物(广州)有限公司;
2026/2/12
247
CYHS2600454
地拉罗司片
化药
仿制
3
福建海西新药创制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海西新药创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2
248
CYHS2600453
注射用磷酸左奥硝唑酯二钠
化药
仿制
4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2
249
CYHS2600451
吲达帕胺缓释片
化药
仿制
4
吉林天衡英睿制药有限公司;吉林天衡英睿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2
250
CYHB2650054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干混悬剂
化药
补充申请
国药集团威奇达药业有限公司;国药集团威奇达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2
251
CYHB2600342
依诺肝素钠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原6
东营天东制药有限公司;东营天东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2
252
CYHB2600341
依诺肝素钠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原6
东营天东制药有限公司;东营天东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2
253
CYHB2600340
甲硝唑氯化钠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信合援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信合援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2
254
CYHB2600339
盐酸氮卓斯汀鼻喷雾剂
化药
补充申请
4
银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银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12
255
CYHB2600338
去氧胆酸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3
洋浦京泰药业有限公司;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2
256
CXSL2600207
注射用SIBP-A19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2026/2/12
257
CXSL2600206
SHR-7590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广东恒瑞医药有限公司;
2026/2/12
258
CXHB2600042
LPM3770164缓释片
化药
补充申请
1
绿叶嘉奥制药石家庄有限公司;
2026/2/12
259
JXSL2600052
Pegozafermin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进口
1
89bio, Inc.;Roche (China) Holding Ltd.;
2026/2/11
260
JXSL2600051
Pegozafermin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进口
1
89bio, Inc.;Roche (China) Holding Ltd.;
2026/2/11
261
JXSL2600050
Pegozafermin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进口
1
89bio, Inc.;Roche (China) Holding Ltd.;
2026/2/11
262
JXSL2600049
PF-08634404
治疗用生物制品
进口
1
Pfizer Inc.;Pfizer (Beij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 Ltd.;
2026/2/11
263
JXSL2600048
PF-08634404
治疗用生物制品
进口
1
Pfizer Inc.;Pfizer (Beij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 Ltd.;
2026/2/11
264
CYZB2600591
十滴水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汪氏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汪氏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1
265
CYZB2600590
宽胸气雾剂
中药
补充申请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厂;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厂;
2026/2/11
266
CYZB2600589
梅翁退热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四川巴中普瑞制药有限公司;广州康和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1
267
CYZB2600588
产后补丸
中药
补充申请
北京莲耳堂药业有限公司;广东宏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宏兴制药厂;
2026/2/11
268
CYZB2600587
黄英咳喘糖浆
中药
补充申请
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 ;
2026/2/11
269
CYSB2600063
尼妥珠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原1
百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百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1
270
CYSB2600062
利妥昔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南京顺欣制药有限公司;正大天晴药业集团南京顺欣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1
271
CYSB2600061
利妥昔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南京顺欣制药有限公司;正大天晴药业集团南京顺欣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1
272
CYHS2600452
阿达帕林凝胶
化药
仿制
4
山东辰欣佛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辰欣佛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1
273
CYHS2600450
盐酸左西替利嗪口服溶液
化药
仿制
3
海南万玮制药有限公司;海南万玮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1
274
CYHB2650053
奥利司他胶囊
化药
补充申请
原6
湖南迪诺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迪诺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1
275
CYHB2650052
奥利司他胶囊
化药
补充申请
原6
湖南迪诺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迪诺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1
276
CYHB2600337
枸橼酸西地那非口崩片
化药
补充申请
4
深圳海王医药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1
277
CXHL2600180
KR23248胶囊
化药
新药
1
江西科睿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1
278
CXHL2600179
YFT-2031
化药
新药
2.2
四川德峰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1
279
CXHL2600178
FS-207片
化药
新药
1
福石生物科技(合肥)有限公司;
2026/2/11
280
CXHL2600177
SL-0013
化药
新药
2.2
上海则正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大学;
2026/2/11
281
CXHL2600176
KEM2507涂膜剂
化药
新药
2.2
深圳珐玛易药品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1
282
JYHB2600095
瑞普替尼胶囊
化药
补充申请
Bristol-Myers Squibb Company;Patheon Inc.;
2026/2/11
283
JYHB2600094
二甲双胍维格列汀片(Ⅱ)
化药
补充申请
Novartis Pharma Schweiz AG;Novartis Pharma Produktions GmbH;
2026/2/11
284
JXSL2600047
Nipocalimab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进口
2.1
Janssen Research & Development, LLC;Johnson & Johnson (China) Investment Ltd.;
2026/2/11
285
JXSL2600046
Nipocalimab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进口
2.1
Janssen Research & Development, LLC;Johnson & Johnson (China) Investment Ltd.;
2026/2/11
286
JXSL2600045
Telisotuzumab Adizutecan 注射用粉末
治疗用生物制品
进口
1
AbbVie Inc.;AbbVie Pharmaceutical Trading (Shanghai) Co., Ltd. ;
2026/2/11
287
JXSL2600044
Telisotuzumab Adizutecan 注射用粉末
治疗用生物制品
进口
1
AbbVie Inc.;AbbVie Pharmaceutical Trading (Shanghai) Co., Ltd. ;
2026/2/11
288
JXSL2600043
PF-08634404
治疗用生物制品
进口
1
Pfizer Inc.;Pfizer (Beij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 Ltd.;
2026/2/11
289
JXSL2600042
PF-08634404
治疗用生物制品
进口
1
Pfizer Inc.;Pfizer (Beij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 Ltd.;
2026/2/11
290
JXHL2600043
JDQ443片
化药
进口
1
Novartis Pharma AG;;China Novartis Institutes for BioMedical Reasearch Co.,Ltd;
2026/2/11
291
JXHL2600042
TAK-360片
化药
进口
1
Takeda Development Center Americas, Inc.;Takeda APAC Bio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2026/2/11
292
JXHL2600041
TAK-360片
化药
进口
1
Takeda Development Center Americas, Inc.;Takeda APAC Bio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2026/2/11
293
JXHL2600040
TAK-360片
化药
进口
1
Takeda Development Center Americas, Inc.;Takeda APAC Bio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2026/2/11
294
JXHL2600039
TAK-360片
化药
进口
1
Takeda Development Center Americas, Inc.;Takeda APAC Bio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2026/2/11
295
JXHL2600038
TAK-360片
化药
进口
1
Takeda Development Center Americas, Inc.;Takeda APAC Bio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2026/2/11
296
JTS2600022
达依泊汀α注射液
生物制品
Kofu Factory of Terumo Corporation;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百诺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1
297
JTS2600021
达依泊汀α注射液
生物制品
Kofu Factory of Terumo Corporation;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百诺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1
298
JTS2600020
注射用A型肉毒毒素内部参考品
生物制品
Huons BioPharma Co., Ltd.;Huons BioPharma Co., Ltd.;爱美客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1
299
JTS2600019
注射用A型肉毒毒素检验用标准品
生物制品
Huons BioPharma Co., Ltd.;Huons BioPharma Co., Ltd.;爱美客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1
300
CYZB2600586
灵芝北芪片
中药
补充申请
三明市三真药业有限公司;三明市三真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1
301
CYZB2600585
健脾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湖南康寿制药有限公司;湖南康寿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1
302
CYZB2600584
陈香露白露片
中药
补充申请
湖南康寿制药有限公司;湖南康寿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1
303
CYZB2600583
复方天麻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湖南康寿制药有限公司;湖南康寿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1
304
CYZB2600582
创灼膏
中药
补充申请
四川同人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同人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1
305
CYZB2600581
补肾强身片
中药
补充申请
成都地奥集团天府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地奥集团天府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1
306
CYZB2600580
寒痹停片
中药
补充申请
河南百年康鑫药业有限公司;河南百年康鑫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1
307
CYZB2600579
寒痹停片
中药
补充申请
河南百年康鑫药业有限公司;河南百年康鑫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1
308
CYZB2600578
豨蛭络达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河北百善药业有限公司;河北百善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1
309
CYZB2600577
归元健脑片
中药
补充申请
河南百年康鑫药业有限公司;河南百年康鑫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1
310
CYZB2600576
地奥心血康片
中药
补充申请
地奥集团成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地奥集团成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1
311
CYZB2600575
黄芪片
中药
补充申请
原8
四川智强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四川奇力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1
312
CYZB2600574
归脾丸
中药
补充申请
商丘市金马药业有限公司;商丘市金马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1
313
CYSB2600060
派安普利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1
正大天晴康方(上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正大天晴药业集团南京顺欣制药有限公司 ;中山康方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
2026/2/11
314
CYHS2600449
注射用托伐普坦磷酸钠
化药
仿制
4
时森海(杭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澳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1
315
CYHS2600448
甲钴胺片
化药
仿制
4
苏州俞氏药业有限公司;苏州俞氏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1
316
CYHS2600447
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
化药
仿制
4
山东达冠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烟台东诚北方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1
317
CYHS2600446
顺铂注射液
化药
仿制
3
吉斯美(武汉)制药有限公司;吉斯美(武汉)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1
318
CYHS2600445
顺铂注射液
化药
仿制
3
吉斯美(武汉)制药有限公司;吉斯美(武汉)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1
319
CYHS2600444
盐酸曲唑酮缓释片
化药
仿制
4
沈阳欣瑞制药有限公司;沈阳欣瑞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1
320
CYHS2600443
多种微量元素注射液(IV)
化药
仿制
3
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1
321
CYHS2600442
盐酸异丙嗪注射液
化药
仿制
3
恒衍生物医药技术(厦门)有限公司;福州基石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1
322
CYHS2600441
盐酸异丙嗪注射液
化药
仿制
3
恒衍生物医药技术(厦门)有限公司;福州基石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1
323
CYHS2600440
替普瑞酮颗粒
化药
仿制
3
浙江核力欣健药业有限公司;浙江核力欣健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1
324
CYHS2600439
盐酸羟甲唑啉滴鼻液
化药
仿制
3
杭州万邦天诚药业有限公司;杭州万邦天诚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1
325
CYHS2600438
低钙腹膜透析液(乳酸盐-G2.5%)
化药
仿制
4
江苏杰瑞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山东华茂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1
326
CYHS2600437
低钙腹膜透析液(乳酸盐-G1.5%)
化药
仿制
4
江苏杰瑞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山东华茂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1
327
CYHS2600436
依达拉奉右莰醇注射用浓溶液
化药
仿制
4
南通慧聚制药有限公司;成都市海通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1
328
CYHL2600023
注射用甲磺酸萘莫司他
化药
仿制
3
璟济生物医药科技(泰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1
329
CYHB2650051
苯磺酸氨氯地平分散片
化药
补充申请
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司;广州市联瑞制药有限公司;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1
330
CYHB2650050
注射用赖氨匹林
化药
补充申请
瑞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瑞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2026/2/11
331
CYHB2600336
门冬氨酸洛美沙星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1
332
CYHB2600335
门冬氨酸洛美沙星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1
333
CYHB2600334
丁香罗勒油乳膏
化药
补充申请
杭州万邦天诚药业有限公司;杭州万邦天诚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1
334
CYHB2600333
盐酸小檗碱片
化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1
335
CYHB2600332
复方参芪维E胶囊
化药
补充申请
苏州第三制药厂有限责任公司;苏州第三制药厂有限责任公司;
2026/2/11
336
CYHB2600331
阿利沙坦酯片
化药
补充申请
原1.1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1
337
CYHB2600330
复方枸橼酸喷托维林糖浆
化药
补充申请
云南翰昊制药有限公司;复寿堂药业河南省有限公司;
2026/2/11
338
CYHB2600329
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
化药
补充申请
4
先声再明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1
339
CYHB2600328
低钙腹膜透析液(乳酸盐-G2.5%)
化药
补充申请
广州万益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广州万益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2026/2/11
340
CYHB2600327
低钙腹膜透析液(乳酸盐-G2.5%)
化药
补充申请
广州万益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天津万益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广州万益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2026/2/11
341
CYHB2600326
硫酸妥布霉素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河北立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1
342
CYHB2600325
注射用醋酸卡泊芬净
化药
补充申请
4
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司;博瑞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2026/2/11
343
CYHB2600324
注射用醋酸卡泊芬净
化药
补充申请
4
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司;博瑞制药(苏州)有限公司;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1
344
CYHB2600323
萘普生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4
湖北兴华制药有限公司;湖北兴华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1
345
CYHB2600322
马来酸依那普利口服溶液
化药
补充申请
3
成都倍特得诺药业有限公司;成都倍特得诺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1
346
CYHB2600321
米诺地尔搽剂
化药
补充申请
3
江苏神华药业有限公司;上海理想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1
347
CYHB2600320
米诺地尔搽剂
化药
补充申请
3
江苏神华药业有限公司;上海理想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1
348
CYHB2600319
盐酸利多卡因眼用凝胶
化药
补充申请
3
四川禾亿制药有限公司;四川禾亿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1
349
CYHB2600318
葡萄糖酸锌口服溶液
化药
补充申请
亚宝药业四川制药有限公司;亚宝药业四川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1
350
CYHB2600317
左氧氟沙星片
化药
补充申请
4
江苏悦兴药业有限公司;江苏悦兴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1
351
CYHB2600316
氯化钠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国药集团新疆制药有限公司;国药集团新疆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1
352
CYHB2600315
氯化钠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国药集团新疆制药有限公司;国药集团新疆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1
353
CYHB2600314
氯化钠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国药集团新疆制药有限公司;国药集团新疆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1
354
CXSS2600018
注射用瑞康曲妥珠单抗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2.2
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小分子SHR169106: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1
355
CXSL2600205
HB0056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上海华奥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华博生物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2026/2/11
356
CXSL2600204
XP-P01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上海信谱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1
357
CXSL2600203
SHR-8068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2.2
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026/2/11
358
CXSL2600202
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2.2
上海盛迪医药有限公司;
2026/2/11
359
CXSB2600031
TQB2868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1
上海正大天晴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026/2/11
360
CXSB2600030
T3011疱疹病毒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1
苏州亦诺微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1
361
CXHS2600029
PG-011凝胶
化药
新药
1
北京普祺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赤峰赛林泰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1
362
CXHS2600028
PG-011凝胶
化药
新药
1
北京普祺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赤峰赛林泰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1
363
CXHL2600175
注射用DN022150
化药
新药
1
江西科睿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1
364
CXHL2600174
甲磺酸阿帕替尼片
化药
新药
2.4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1
365
CXHL2600173
YL-18319片
化药
新药
1
上海璎黎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1
366
CXHL2600172
YL-18319片
化药
新药
1
上海璎黎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1
367
CXHL2600171
HCXT-2001片
化药
新药
1
上海瀚辰星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1
368
CXHL2600170
HCXT-2001片
化药
新药
1
上海瀚辰星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1
369
CXHL2600169
注射用BXOS116
化药
新药
1
拜西欧斯(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026/2/11
370
CXHB2600041
HL-1186片
化药
补充申请
1
上海壹典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026/2/11
371
JXSL2600041
JNJ-79635322
治疗用生物制品
进口
1
Janssen Research & Development, LLC;Johnson & Johnson (China) Investment Ltd.;
2026/2/10
372
JXSL2600040
JNJ-79635322
治疗用生物制品
进口
1
Janssen Research & Development, LLC;Johnson & Johnson (China) Investment Ltd.;
2026/2/10
373
JXSL2600039
JNJ-79635322
治疗用生物制品
进口
1
Janssen Research & Development, LLC;Johnson & Johnson (China) Investment Ltd.;
2026/2/10
374
JXSL2600038
JNJ-79635322
治疗用生物制品
进口
1
Janssen Research & Development, LLC;Johnson & Johnson (China) Investment Ltd.;
2026/2/10
375
JXHS2600024
他舒替尼片
化药
进口
5.1
Eisai Co., Ltd.;Eisai Co., Ltd. Kawashima Plant;SciClone Pharmaceuticals (China) Co.,Ltd.;
2026/2/10
376
CYZB2600573
参芪糖浆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大地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江西大地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10
377
CYZB2600572
引阳索
中药
补充申请
山东宜岛康制药有限公司;湖南杏林春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0
378
CYSB2600059
依沃西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1
康方赛诺医药有限公司;康方药业有限公司;康方赛诺医药有限公司;
2026/2/10
379
CYHS2600435
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
化药
仿制
4
苏州第壹制药有限公司;浙江国镜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0
380
CYHS2600434
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
化药
仿制
4
苏州第壹制药有限公司;浙江国镜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0
381
CYHS2600433
克立硼罗软膏
化药
仿制
4
湖南斯奇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成都市海通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0
382
CYHS2600432
克立硼罗软膏
化药
仿制
4
湖南斯奇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成都市海通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0
383
CYHS2600431
克立硼罗软膏
化药
仿制
4
哈尔滨大中制药有限公司;哈尔滨大中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0
384
CYHS2600430
磷苯妥英钠注射液
化药
仿制
3
江西科为制药有限公司;江苏润恒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0
385
CYHS2600429
磷苯妥英钠注射液
化药
仿制
3
江西科为制药有限公司;江苏润恒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0
386
CYHS2600428
雌二醇片/雌二醇地屈孕酮片复合包装
化药
仿制
4
湖南醇健制药科技有限公司;湖南醇健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0
387
CYHS2600427
雌二醇片/雌二醇地屈孕酮片复合包装
化药
仿制
4
湖南醇健制药科技有限公司;湖南醇健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0
388
CYHS2600426
罗沙司他胶囊
化药
仿制
4
芜湖道润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芜湖道润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6/2/10
389
CYHS2600425
苹果酸奈诺沙星胶囊
化药
仿制
4
成都天台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台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0
390
CYHS2600424
罗沙司他胶囊
化药
仿制
4
芜湖道润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芜湖道润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6/2/10
391
CYHL2600022
醋酸地非法林注射液
化药
仿制
3
成都青山利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0
392
CYHB2650049
马来酸氯苯那敏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上海浦津林州制药有限公司;上海浦津林州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0
393
CYHB2650048
马来酸氯苯那敏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上海浦津林州制药有限公司;上海浦津林州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0
394
CYHB2600313
灭菌注射用水
化药
补充申请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0
395
CYHB2600312
氨溴特罗口服溶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北京韩美药品有限公司;北京韩美药品有限公司;
2026/2/10
396
CYHB2600311
左乙拉西坦口服溶液
化药
补充申请
4
河南华雒康润药业有限公司;河南华雒康润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0
397
CYHB2600310
头孢克洛颗粒
化药
补充申请
苏州中化药品工业有限公司;苏州中化药品工业有限公司;
2026/2/10
398
CYHB2600309
头孢克洛颗粒
化药
补充申请
苏州中化药品工业有限公司;苏州中化药品工业有限公司;
2026/2/10
399
CYHB2600308
替米沙坦胶囊
化药
补充申请
江苏诚康药业有限公司;江苏迪赛诺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0
400
CYHB2600307
甲磺酸伊马替尼片
化药
补充申请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0
401
CXSL2600201
注射用PCNAT-01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安达生物药物开发(北京)有限公司;
2026/2/10
402
CXSL2600200
埃诺格鲁肽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2.2
杭州先为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0
403
CXSL2600199
埃诺格鲁肽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2.2
杭州先为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0
404
CXSL2600198
CPU-YL01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江苏创源生命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药科大学;
2026/2/10
405
CXHS2600027
醋酸索乐匹尼布片
化药
新药
1
和记黄埔医药(上海)有限公司;和记黄埔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2026/2/10
406
CXHL2600168
TXA-070片
化药
新药
2.4
武汉科福新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10
407
CXHB2600040
YR001软膏
化药
补充申请
1
杭州壹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0
408
JYSZ2600007
雷珠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进口再注册
Novartis Pharma Schweiz AG;Novartis Pharma Stein AG;不适用;
2026/2/10
409
JYSB2600032
依洛尤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Amgen Inc.;Amgen Manufacturing Limited LLC;Amgen Technology (Ireland) Unlimited Company;
2026/2/10
410
JYSB2600031
注射用阿替普酶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KG;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KG;Vetter Pharma-Fertigung GmbH & Co. KG;
2026/2/10
411
JYSB2600030
注射用阿替普酶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KG;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KG;Vetter Pharma-Fertigung GmbH & Co. KG;
2026/2/10
412
JYHZ2600033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化药
进口再注册
5.2
Aurobindo Pharma Limited;Aurobindo Pharma Limited;Aurovitas Pharma Taizhou Co., Ltd.;
2026/2/10
413
JYHZ2600032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化药
进口再注册
5.2
Aurobindo Pharma Limited;Aurobindo Pharma Limited;Aurovitas Pharma Taizhou Co., Ltd.;
2026/2/10
414
JYHZ2600031
低分子肝素钠注射液
化药
进口再注册
ALFASIGMA S.p.A.;ALFASIGMA S.p.A.;Alfasigma (Beijing) Medicine Consulting Co., Ltd.;
2026/2/10
415
JYHZ2600030
低分子肝素钠注射液
化药
进口再注册
ALFASIGMA S.p.A.;ALFASIGMA S.p.A.;Alfasigma (Beijing) Medicine Consulting Co., Ltd.;
2026/2/10
416
JYHZ2600029
低分子肝素钠注射液
化药
进口再注册
ALFASIGMA S.p.A.;ALFASIGMA S.p.A.;Alfasigma (Beijing) Medicine Consulting Co., Ltd.;
2026/2/10
417
JYHB2600093
阿可替尼胶囊
化药
补充申请
5.1
AstraZeneca AB;AstraZeneca AB;
2026/2/10
418
JYHB2600092
马来酸阿可替尼片
化药
补充申请
5.1
AstraZeneca Pty Ltd;AstraZeneca AB;
2026/2/10
419
JYHB2600091
注射用盐酸吉西他滨
化药
补充申请
CHEPLAPHARM Arzneimittel GmbH;Vianex S.A.-PlantC;
2026/2/10
420
JYHB2600090
注射用盐酸吉西他滨
化药
补充申请
CHEPLAPHARM Arzneimittel GmbH;Vianex S.A.-PlantC;
2026/2/10
421
JYHB2600089
盐酸哌甲酯缓释片
化药
补充申请
Janssen Pharmaceuticals, Inc.;Janssen-Cilag Manufacturing, LLC;
2026/2/10
422
JYHB2600088
盐酸哌甲酯缓释片
化药
补充申请
Janssen Pharmaceuticals, Inc.;Janssen-Cilag Manufacturing, LLC;
2026/2/10
423
JYHB2600087
盐酸哌甲酯缓释片
化药
补充申请
Janssen Pharmaceuticals, Inc.;Janssen-Cilag Manufacturing, LLC;
2026/2/10
424
JXHS2600023
阿可替尼胶囊
化药
进口
5.1
AstraZeneca AB;AstraZeneca AB;AstraZeneca Investment (China) Co., Ltd.;
2026/2/10
425
JXHS2600022
马来酸阿可替尼片
化药
进口
5.1
AstraZeneca Pty Ltd;AstraZeneca AB;AstraZeneca Investment (China) Co., Ltd.;
2026/2/10
426
JXHL2600037
TQJ230注射液
化药
进口
1
Novartis Pharma AG;China Novartis Institutes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Co., Ltd.;
2026/2/10
427
JXHL2600036
BIIB115注射液
化药
进口
1
Biogen Idec Research Limited;Biogen Biotechnology (Shanghai) Co., Ltd;
2026/2/10
428
CYZB2600571
跳骨片
中药
补充申请
福州闽海药业有限公司;福州闽海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0
429
CYZB2600570
小柴胡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宣城市金芙蓉药业有限公司;宣城市金芙蓉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0
430
CYZB2600569
清热解毒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明顺医疗投资(深圳)有限公司;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0
431
CYZB2600568
桑椹膏
中药
补充申请
陶一堂集团(石台)制药有限公司;陶一堂集团(石台)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0
432
CYZB2600567
护肝片
中药
补充申请
原9
四川泰华堂制药有限公司;四川泰华堂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0
433
CYZB2600566
强力枇杷露
中药
补充申请
吉林三九金复康药业有限公司;吉林三九金复康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0
434
CYZB2600565
杏香兔耳风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0
435
CYZB2600564
小儿止咳糖浆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0
436
CYZB2600563
龟芪参口服液
中药
补充申请
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0
437
CYZB2600562
小儿感冒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0
438
CYZB2600561
冠心苏合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鸿烁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东方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0
439
CYZB2600560
五加皮酒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0
440
CYZB2600559
史国公药酒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0
441
CYZB2600558
十全大补酒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0
442
CYZB2600557
姜枣祛寒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达嘉维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达嘉维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0
443
CYZB2600556
九味肝泰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达嘉维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达嘉维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0
444
CYZB2600555
珍珠活络二十九味丸
中药
补充申请
内蒙古奥特奇蒙药股份有限公司金山蒙药厂;内蒙古奥特奇蒙药股份有限公司金山蒙药厂;
2026/2/10
445
CYZB2600554
强力枇杷露
中药
补充申请
中峘本草制药有限公司;中峘本草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0
446
CYZB2600553
麝香通心滴丸
中药
补充申请
内蒙古康恩贝药业有限公司;内蒙古康恩贝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0
447
CYZB2600552
胆清片
中药
补充申请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0
448
CYZB2600551
麝香心脑乐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原8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6/2/10
449
CYZB2600550
双黄连合剂
中药
补充申请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0
450
CYZB2600549
通窍耳聋丸
中药
补充申请
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0
451
CYZB2600548
强阳保肾丸
中药
补充申请
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0
452
CYSB2600058
特立帕肽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3.3
上海联合赛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上海联合赛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2026/2/10
453
CYHS2600423
酒石酸阿福特罗雾化吸入用溶液
化药
仿制
3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0
454
CYHS2600422
普瑞巴林胶囊
化药
仿制
4
成都恒瑞制药有限公司;成都恒瑞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0
455
CYHS2600421
艾地骨化醇软胶囊
化药
仿制
4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0
456
CYHS2600420
艾地骨化醇软胶囊
化药
仿制
4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0
457
CYHS2600419
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Ⅱ)
化药
仿制
3
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0
458
CYHS2600418
盐酸丁卡因凝胶
化药
仿制
3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0
459
CYHS2600417
复方聚乙二醇(3350)电解质口服溶液
化药
仿制
3
江苏神华药业有限公司;江苏神华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0
460
CYHS2600416
甲磺酸多沙唑嗪缓释片
化药
仿制
4
晖致制药(大连)有限公司;晖致制药(大连)有限公司;
2026/2/10
461
CYHS2600415
呋塞米口服溶液
化药
仿制
3
贵州黔药集团制药有限公司;湖南嘉恒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0
462
CYHS2600414
注射用磷酸左奥硝唑酯二钠
化药
仿制
4
海南合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合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0
463
CYHS2600413
阿帕他胺片
化药
仿制
4
江苏利泰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苏利泰尔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0
464
CYHB2650047
非诺贝特胶囊
化药
补充申请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6/2/10
465
CYHB2600306
腹膜透析液(乳酸盐-G1.5%)
化药
补充申请
广州万益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天津万益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广州万益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2026/2/10
466
CYHB2600305
腹膜透析液(乳酸盐-G1.5%)
化药
补充申请
广州万益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广州万益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2026/2/10
467
CYHB2600304
低钙腹膜透析液(乳酸盐-G4.25%)
化药
补充申请
广州万益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天津万益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广州万益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2026/2/10
468
CYHB2600303
苯磺酸左氨氯地平片
化药
补充申请
原4
施慧达药业集团(吉林)有限公司;施慧达药业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2026/2/10
469
CYHB2600302
苯磺酸左氨氯地平片
化药
补充申请
原4
施慧达药业集团(吉林)有限公司;施慧达药业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2026/2/10
470
CYHB2600301
马来酸氯苯那敏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0
471
CYHB2600300
马来酸氯苯那敏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0
472
CYHB2600299
硫酸镁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0
473
CYHB2600298
硫酸镁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0
474
CYHB2600297
依折麦布片
化药
补充申请
4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无锡福祈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0
475
CYHB2600296
硫酸镁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0
476
CYHB2600295
硫酸卡那霉素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0
477
CYHB2600294
硫酸沙丁胺醇口服溶液
化药
补充申请
3
海鸿恒隆(海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欧歌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0
478
CYHB2600293
腹膜透析液(乳酸盐-G4.25%)
化药
补充申请
广州万益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天津万益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广州万益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2026/2/10
479
CYHB2600292
联苯苄唑溶液
化药
补充申请
3
福元药业有限公司;福元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0
480
CYHB2600291
卡马西平片
化药
补充申请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6/2/10
481
CYHB2600290
低钙腹膜透析液(乳酸盐-G1.5%)
化药
补充申请
广州万益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广州万益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2026/2/10
482
CYHB2600289
低钙腹膜透析液(乳酸盐-G1.5%)
化药
补充申请
广州万益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天津万益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广州万益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2026/2/10
483
CYHB2600288
注射用阿奇霉素
化药
补充申请
湖北潜龙药业有限公司;湖北潜龙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0
484
CYHB2600287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化药
补充申请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0
485
CYHB2600286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化药
补充申请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0
486
CYHB2600285
注射用伏立康唑
化药
补充申请
四川美大康华康药业有限公司;四川美大康华康药业有限公司;
2026/2/10
487
CXSS2600017
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2.2
山东先声再明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山东先声再明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026/2/10
488
CXSL2600196
EA5注射液皮下制剂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上海览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0
489
CXSL2600195
SG301 SC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杭州尚健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0
490
CXSL2600194
CG001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上海康景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0
491
CXSL2600193
ZHB118舌下片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江苏众红生物工程创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6/2/10
492
CXSL2600192
四价重组手足口病疫苗(毕赤酵母)
预防用生物制品
新药
1.4
重庆华智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华淞(上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0
493
CXSL2600191
SSS68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10
494
CXSL2600190
ZHB118舌下片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江苏众红生物工程创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6/2/10
495
CXSL2600189
SSS68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10
496
CXSL2600188
SSS68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10
497
CXHL2600164
HS-10522片
化药
新药
1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翰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0
498
CXHL2600163
HS-10522片
化药
新药
1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翰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0
499
CXHL2600162
HS-10522片
化药
新药
1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翰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0
500
CXHB2600039
HRS-9231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1
上海盛迪医药有限公司;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10
501
JYHZ2600028
盐酸环喷托酯滴眼液
化药
进口再注册
Alcon NV;Novartis Manufacturing N.V.;Alcon (China) Ophthalmic Product Co.Ltd.;
2026/2/9
502
JXSB2600022
SAR442970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1
Sanofi-Aventis Recherche & Développement;Sanofi-Aventis Recherche & Développement;Eurofins CDMO (Amatsigroup SAS) ;
2026/2/9
503
JXSB2600021
SAR442970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1
Sanofi-Aventis Recherche & Développement;Sanofi-Aventis Recherche & Développement;Eurofins CDMO (Amatsigroup SAS) ;
2026/2/9
504
JTH2600031
盐酸Acoramidis片
化药
Rottendorf Pharma GmbH;Bayer (Schweiz) AG;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2026/2/9
505
JTH2600030
帕替罗姆山梨醇钙口服混悬剂
化药
Patheon Inc.;Vifor Fresenius Medical Care Renal Pharma France;富启睿医药研发(北京)有限公司;
2026/2/9
506
CYHS2600412
注射用硫酸艾沙康唑
化药
仿制
4
乳源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乳源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2026/2/9
507
CYHS2600411
盐酸莫西沙星片
化药
仿制
4
上海金不换兰考制药有限公司;上海金不换兰考制药有限公司;
2026/2/9
508
CXSL2600197
注射用BG-T187(皮下注射)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广州百济神州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026/2/9
509
CXSL2600187
LY-M003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凌意(杭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6/2/9
510
CXSL2600186
IBI115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2026/2/9
511
CXHL2600167
QLS7320注射液
化药
新药
1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2026/2/9
512
CXHL2600166
QLS7320注射液
化药
新药
1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2026/2/9
513
CXHL2600165
QLS7320注射液
化药
新药
1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2026/2/9
514
CXHL2600161
注射用华卟啉钠
化药
新药
1
上海光声制药有限公司;
2026/2/9
515
CXHL2600160
JY54注射液
化药
新药
1
杭州九源基因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9
516
CXHL2600159
安奈拉唑钠肠溶片
化药
新药
2.4
轩竹(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9
517
CXHL2600158
HS-10522片
化药
新药
1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翰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9
518
CXHL2600157
HS-10522片
化药
新药
1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翰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9
519
CXHL2600156
HS-10522片
化药
新药
1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翰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9
520
CXHL2600155
WS-0101溶液
化药
新药
1
北京厚燊维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26/2/9
521
CYZB2600547
益肝灵片
中药
补充申请
达嘉维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湖南天济草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9
522
CYZB2600546
女宝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达嘉维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湖南天济草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9
523
CYHB2600284
阿卡波糖片
化药
补充申请
4
石家庄市华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石家庄市华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6/2/9
524
JXSS2600008
重组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CHO细胞,AS01E佐剂系统)
预防用生物制品
进口
3.1
GlaxoSmithKline Biologicals SA;GlaxoSmithKline Biologicals;GlaxoSmithKline (China)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2026/2/8
525
JYSB2600029
注射用德曲妥珠单抗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Daiichi Sankyo Europe GmbH;Simtra Deutschland GmbH;
2026/2/7
526
JYHB2600086
卡替拉韦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5.1
ViiV Healthcare BV;Glaxo Operations UK Ltd (trading as Glaxo Wellcome Operations);
2026/2/7
527
JYHB2600085
卡替拉韦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5.1
ViiV Healthcare BV;Glaxo Operations UK Ltd (trading as Glaxo Wellcome Operations);
2026/2/7
528
JYHB2600084
卡替拉韦钠片
化药
补充申请
5.1
ViiV Healthcare BV;Glaxo Operations UK Ltd (trading as Glaxo Wellcome Operations);
2026/2/7
529
JXHL2600035
AZD3470薄膜衣片
化药
进口
1
AstraZeneca AB;AstraZeneca Global R&D (China) Co., Ltd.;
2026/2/7
530
JXHL2600034
AZD3470薄膜衣片
化药
进口
1
AstraZeneca AB;AstraZeneca Global R&D (China) Co., Ltd.;
2026/2/7
531
JXHL2600033
依普隆特生钠注射液
化药
进口
2.4
AstraZeneca AB;AstraZeneca Global R&D (China) Co., Ltd.;
2026/2/7
532
JTS2600018
伊匹木单抗注射液
生物制品
Bristol-Myers Squibb Holdings Pharma, Ltd., Liability Company ;Bristol-Myers Squibb Company;上海复宏汉霖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026/2/7
533
CYZB2600545
跌打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34
CYZB2600544
少腹逐瘀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35
CYZB2600543
上清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36
CYZB2600542
上清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37
CYZB2600541
复方丹参片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38
CYZB2600540
山楂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39
CYZB2600539
山药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40
CYZB2600538
香砂养胃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41
CYZB2600537
板蓝根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42
CYZB2600536
参桂再造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43
CYZB2600535
参苓白术散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44
CYZB2600534
一捻金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45
CYZB2600533
银翘解毒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46
CYZB2600532
贞杞肝泰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47
CYZB2600531
附子理中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军民路19号;
2026/2/7
548
CYZB2600530
附子理中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49
CYZB2600529
醋制香附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50
CYZB2600528
天麻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51
CYZB2600527
娃娃宁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52
CYZB2600526
桃花散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53
CYZB2600525
天王补心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54
CYZB2600524
天王补心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55
CYZB2600523
天王补心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56
CYZB2600522
清脑降压片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57
CYZB2600521
清瘟解毒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58
CYZB2600520
胃肠复元膏
中药
补充申请
洛阳顺势药业有限公司;洛阳顺势药业有限公司;
2026/2/7
559
CYZB2600519
清眩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60
CYZB2600518
全鹿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61
CYZB2600517
黄连羊肝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62
CYZB2600516
蓝芩口服液
中药
补充申请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龙凤堂中药有限公司;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龙凤堂中药有限公司;
2026/2/7
563
CYZB2600515
回春如意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64
CYZB2600514
蓝芩口服液
中药
补充申请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龙凤堂中药有限公司;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龙凤堂中药有限公司;
2026/2/7
565
CYZB2600513
回天再造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66
CYZB2600512
百合固金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67
CYZB2600511
百合固金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68
CYZB2600510
朱砂安神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69
CYZB2600509
朱砂安神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70
CYZB2600508
朱砂安神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71
CYZB2600507
紫蔻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72
CYZB2600506
柏子养心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73
CYZB2600505
柏子养心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74
CYZB2600504
柏子养心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75
CYZB2600503
补中益气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76
CYZB2600502
补中益气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77
CYZB2600501
补中益气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78
CYZB2600500
保胎灵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79
CYZB2600499
贞杞肝泰片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80
CYZB2600498
安宫牛黄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81
CYZB2600497
跌打活血散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82
CYZB2600496
二十七味定坤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83
CYZB2600495
二十七味定坤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84
CYZB2600494
维C银翘片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85
CYZB2600493
五海瘿瘤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86
CYZB2600492
五味子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87
CYZB2600491
小儿金丹片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88
CYZB2600490
小活络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89
CYZB2600489
小柴胡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上海世康特制药有限公司;上海世康特制药有限公司;
2026/2/7
590
CYZB2600488
如意金黄散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91
CYZB2600487
感冒止咳片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92
CYZB2600486
人参再造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93
CYZB2600485
人参养荣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94
CYZB2600484
人参养荣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95
CYZB2600483
人参健脾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96
CYZB2600482
人参健脾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97
CYZB2600481
人参五味子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98
CYZB2600480
三七片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599
CYZB2600479
妇科止带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原9
达嘉维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湖南天济草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7
600
CYZB2600478
八味三香散
中药
补充申请
内蒙古奥特奇蒙药股份有限公司金山蒙药厂;内蒙古奥特奇蒙药股份有限公司金山蒙药厂;
2026/2/7
601
CYZB2600477
参莲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达嘉维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湖南天济草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7
602
CYSB2600056
恩沃利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1
四川思路康瑞药业有限公司;江苏康宁杰瑞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026/2/7
603
CYHS2600410
米拉贝隆缓释片
化药
仿制
4
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武汉人福利康药业有限公司;
2026/2/7
604
CYHS2600408
注射用阿立哌唑
化药
仿制
4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玻思韬控释药业有限公司;
2026/2/7
605
CYHS2600407
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化药
仿制
4
广东科泓药业有限公司;广东科泓药业有限公司;
2026/2/7
606
CYHS2600406
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化药
仿制
4
广东科泓药业有限公司;广东科泓药业有限公司;
2026/2/7
607
CYHS2600405
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化药
仿制
4
广东科泓药业有限公司;广东科泓药业有限公司;
2026/2/7
608
CYHS2600404
琥珀酸亚铁片
化药
仿制
3
北京仁众药业有限公司;北京仁众药业有限公司;
2026/2/7
609
CYHS2600403
己酮可可碱缓释片
化药
仿制
3
国药集团容生制药有限公司;江苏永安制药有限公司;
2026/2/7
610
CYHB2650046
叶酸片
化药
补充申请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2026/2/7
611
CYHB2600283
葡萄糖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武汉滨湖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武汉滨湖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612
CYHB2600282
葡萄糖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武汉滨湖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武汉滨湖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613
CYHB2600281
葡萄糖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武汉滨湖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武汉滨湖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614
CYHB2600280
葡萄糖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武汉滨湖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武汉滨湖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615
CYHB2600279
盐酸阿莫罗芬乳膏
化药
补充申请
4
武汉诺安药业有限公司;武汉诺安药业有限公司;
2026/2/7
616
CYHB2600278
葡萄糖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武汉滨湖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武汉滨湖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617
CYHB2600277
盐酸阿莫罗芬乳膏
化药
补充申请
4
武汉诺安药业有限公司;武汉诺安药业有限公司;
2026/2/7
618
CYHB2600276
盐酸奥洛他定滴眼液
化药
补充申请
4
四川好医生攀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浙江赛默制药有限公司;
2026/2/7
619
CYHB2600275
恩扎卢胺软胶囊
化药
补充申请
4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7
620
CYHB2600274
腹膜透析液(乳酸盐-G2.5%)
化药
补充申请
广州万益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广州万益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2026/2/7
621
CYHB2600273
腹膜透析液(乳酸盐-G2.5%)
化药
补充申请
广州万益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天津万益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广州万益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2026/2/7
622
CYHB2600272
恩格列净二甲双胍缓释片(II)
化药
补充申请
3
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广州玻思韬控释药业有限公司;
2026/2/7
623
CYHB2600271
泊沙康唑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4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7
624
CYHB2600270
复方龙胆碳酸氢钠片
化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7
625
CYHB2600269
重酒石酸利斯的明口服溶液
化药
补充申请
3
万特制药(海南)有限公司;浙江凯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7
626
CYHB2600268
克立硼罗软膏
化药
补充申请
4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赛默制药有限公司;
2026/2/7
627
CXZL2600022
西帕依麦孜彼子口服液
中药
新药
2.3
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奇沐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奇沐(广东横琴)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7
628
CXSS2600016
人凝血因子Ⅷ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3.4
远大蜀阳生命科学(成都)有限公司;远大蜀阳生命科学(成都)有限公司;
2026/2/7
629
CXSL2600185
ALXN2220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阿斯利康全球研发(中国)有限公司;
2026/2/7
630
CXSL2600184
ZHB117舌下片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江苏众红生物工程创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6/2/7
631
CXSL2600183
ZHB117舌下片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江苏众红生物工程创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6/2/7
632
CXSL2600182
注射用GLR1059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7
633
CXSB2600029
Xs02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1
北京先声祥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6/2/7
634
CXSB2600028
注射用GQ1005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1
启德医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2026/2/7
635
CXHB2600038
HRS-2189片
化药
补充申请
1
山东盛迪医药有限公司;
2026/2/7
636
JYHB2600083
盐酸阿夫唑嗪缓释片
化药
补充申请
Sanofi Withrop Industrie;SANOFI WINTHROP INDUSTRIE;
2026/2/6
637
CYZB2600476
云芝肝泰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修正药业集团(湖南)药业有限公司;吉林天力泰药业有限公司;
2026/2/6
638
CYZB2600475
益母草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修正药业集团(湖南)药业有限公司;通药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39
CYZB2600474
乙肝解毒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修正药业集团(湖南)药业有限公司;吉林天力泰药业有限公司;
2026/2/6
640
CYZB2600473
抗骨增生片
中药
补充申请
原9
沈阳金龙药业有限公司;沈阳金龙药业有限公司;
2026/2/6
641
CYHS2600409
硫酸阿米卡星注射液
化药
仿制
3
山东安信制药有限公司;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2026/2/6
642
CYHB2600267
盐酸托莫西汀口服溶液
化药
补充申请
4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43
CYHB2600266
葡萄糖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成都青山利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青山利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44
CYHB2600265
葡萄糖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成都青山利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青山利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45
CYHB2600264
葡萄糖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成都青山利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青山利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46
CXSB2600027
注射用SHR-9839(sc)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1
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026/2/6
647
CXHS2600026
甲磺酸艾多替尼片
化药
新药
1
浙江同源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凯莱英生命科学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2026/2/6
648
JYSB2600028
奥妥珠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Roche Pharma (Schweiz) AG;Roche Diagnostics GmbH;
2026/2/6
649
JYSB2600027
地舒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Amgen Inc.;Amgen Manufacturing Limited LLC;
2026/2/6
650
JYHZ2600027
复方尿维氨滴眼液
化药
进口再注册
Shiono Chemical Co., Ltd.;Teika Pharmaceutical Co., Ltd.;Shenzhen Rosso Pharmaceutical Co., Ltd.;
2026/2/6
651
JXSS2600007
伊利尤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进口
1
Novartis Pharma Schweiz AG;Novartis Pharma Stein AG;Beijing Novartis Pharma Co., Ltd.;
2026/2/6
652
JXSS2600006
伊利尤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进口
1
Novartis Pharma Schweiz AG;Novartis Pharma Stein AG;Beijing Novartis Pharma Co., Ltd.;
2026/2/6
653
JXSB2600020
佩索利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2.2
LEO Pharma A/S;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 KG;
2026/2/6
654
JXHL2600032
宗艾替尼片
化药
进口
2.4
Boehringer Ingelheim International GmbH;Boehringer Ingelheim (China) Investment Co.,Ltd;
2026/2/6
655
JTH2600029
重组人促卵泡激素氧化形式系统适用性溶液
化药
Ferring GmbH;Ferring GmbH;辉凌医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2026/2/6
656
CYZB2600472
鞘蕊苏口服液
中药
补充申请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57
CYZB2600471
杞菊地黄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广东隆信制药有限公司;广东隆信制药有限公司;
2026/2/6
658
CYZB2600470
蛇胆陈皮散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59
CYZB2600469
前列舒乐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原9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60
CYZB2600468
蕲蛇药酒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61
CYZB2600467
板蓝根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62
CYZB2600466
乙肝解毒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63
CYZB2600465
乙肝扶正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修正药业集团(湖南)药业有限公司;吉林天力泰药业有限公司;
2026/2/6
664
CYZB2600464
乙肝扶正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65
CYZB2600463
天麻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修正药业集团(湖南)药业有限公司;通药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66
CYZB2600462
生脉饮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67
CYZB2600461
精制冠心片
中药
补充申请
修正药业集团(湖南)药业有限公司;通药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68
CYZB2600460
风湿痛药酒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69
CYZB2600459
跌打活血散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70
CYZB2600458
二丁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上海庆安药业集团宿州制药有限公司;黄山精制药业有限公司;广西圣特药业有限公司;上海庆安药业集团宿州制药有限公司;
2026/2/6
671
CYZB2600457
南板蓝根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72
CYZB2600456
南板蓝根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73
CYZB2600455
脉安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74
CYZB2600454
六味地黄片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75
CYZB2600453
荡石片
中药
补充申请
修正药业集团(湖南)药业有限公司;修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76
CYZB2600452
壮元补身酒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77
CYZB2600451
九味羌活喷雾剂
中药
补充申请
原4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78
CYZB2600450
感冒止咳糖浆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79
CYZB2600449
复方灵芝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80
CYZB2600448
阿胶当归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原9
江右制药(常德)有限公司;江右制药(常德)有限公司;
2026/2/6
681
CYZB2600447
风痛安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2026/2/6
682
CYZB2600446
知柏地黄片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83
CYZB2600445
止痢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84
CYZB2600444
壮骨追风酒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丽尔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85
CYZB2600443
七叶神安片
中药
补充申请
修正药业集团(湖南)药业有限公司;修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86
CYZB2600442
七叶神安片
中药
补充申请
修正药业集团(湖南)药业有限公司;修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87
CYZB2600441
七叶神安片
中药
补充申请
修正药业集团(湖南)药业有限公司;修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88
CYZB2600440
黄精养阴糖浆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大地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江西大地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6
689
CYZB2600439
附片液
中药
补充申请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90
CYZB2600438
血塞通片
中药
补充申请
原9
湖南绅泰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绅泰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91
CYZB2600437
血塞通片
中药
补充申请
原9
湖南绅泰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绅泰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92
CYZB2600436
血塞通片
中药
补充申请
原9
湖南绅泰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绅泰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693
CYZB2600435
四逆汤
中药
补充申请
原9
湖南三学药业有限公司;怀化正好制药有限公司;
2026/2/6
694
CYZB2600434
雷公藤多苷片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6/2/6
695
CYSB2600055
昂戈瑞西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1
重庆博创医药有限公司;上海君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2026/2/6
696
CYSB2600054
西妥昔单抗N01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3.4
四川科伦博泰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臻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026/2/6
697
CYSB2600053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原15
国药集团西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国药集团西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026/2/6
698
CYSB2600052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原15
国药集团西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国药集团西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026/2/6
699
CYHS2600402
普拉洛芬滴眼液
化药
仿制
4
沈阳神龙药业有限公司;沈阳神龙药业有限公司;
2026/2/6
700
CYHS2600401
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化药
仿制
4
南京康川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瑞华(中山)制药有限公司;
2026/2/6
701
CYHS2600400
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化药
仿制
4
南京康川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瑞华(中山)制药有限公司;
2026/2/6
702
CYHS2600399
利多卡因凝胶贴膏
化药
仿制
4
福元药业有限公司;福元药业有限公司;
2026/2/6
703
CYHS2600398
二硫化硒洗剂
化药
仿制
3
海南药谷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万邦天诚药业有限公司;
2026/2/6
704
CYHS2600397
巴瑞替尼片
化药
仿制
4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05
CYHS2600396
山梨醇甘露醇冲洗剂
化药
仿制
3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06
CYHS2600395
甲苯磺酸艾多沙班片
化药
仿制
4
植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植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07
CYHS2600394
甲苯磺酸艾多沙班片
化药
仿制
4
植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植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08
CYHS2600393
甲苯磺酸艾多沙班片
化药
仿制
4
植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植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09
CYHS2600392
利格列汀二甲双胍缓释片(Ⅱ)
化药
仿制
3
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10
CYHS2600391
硫酸镁钠钾口服用浓溶液
化药
仿制
4
南京海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海纳制药有限公司;
2026/2/6
711
CYHS2600390
氨甲环酸注射液
化药
仿制
4
湖南先施制药有限公司;湖南先施制药有限公司;
2026/2/6
712
CYHS2600389
氨甲环酸注射液
化药
仿制
4
湖南先施制药有限公司;湖南先施制药有限公司;
2026/2/6
713
CYHS2600388
盐酸倍他司汀片
化药
仿制
3
北京京丰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京丰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2026/2/6
714
CYHS2600387
盐酸倍他司汀片
化药
仿制
3
北京京丰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京丰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2026/2/6
715
CYHS2600386
氨磺必利口服溶液
化药
仿制
3
武汉益博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赤峰源生药业有限公司;
2026/2/6
716
CYHS2600385
盐酸利多卡因注射液
化药
仿制
3
以岭万洲国际制药有限公司;以岭万洲国际制药有限公司;
2026/2/6
717
CYHL2600021
苹果酸卡博替尼片
化药
仿制
3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18
CYHB2650045
注射用氨苄西林钠
化药
补充申请
上海上药新亚药业有限公司;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19
CYHB2650044
注射用氨苄西林钠
化药
补充申请
上海上药新亚药业有限公司;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20
CYHB2650043
复方倍他米松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原6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2026/2/6
721
CYHB2600263
硫酸阿托品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22
CYHB2600262
硫酸阿托品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23
CYHB2600261
硫酸阿托品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24
CYHB2600260
硫酸阿托品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25
CYHB2600259
玻璃酸钠滴眼液
化药
补充申请
4
湖南先施制药有限公司;湖南先施制药有限公司;
2026/2/6
726
CYHB2600258
氯霉素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27
CYHB2600257
硫酸核糖霉素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28
CYHB2600256
硫酸核糖霉素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29
CYHB2600255
艾拉莫德片
化药
补充申请
4
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海纳制药有限公司;
2026/2/6
730
CYHB2600254
氯化钙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31
CYHB2600253
氯化钙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32
CYHB2600252
氯化钙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33
CYHB2600251
氯化钙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34
CYHB2600250
氯化钾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35
CYHB2600249
硫酸庆大霉素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36
CYHB2600248
硫酸庆大霉素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37
CYHB2600247
硫酸庆大霉素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38
CYHB2600246
硫酸小诺霉素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39
CYHB2600245
硫酸小诺霉素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40
CYHB2600244
硫酸妥布霉素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41
CYHB2600243
硫酸妥布霉素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42
CYHB2600242
肌苷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43
CYHB2600241
肌苷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44
CYHB2600240
复方甘草酸单铵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45
CYHB2600239
复方氨基比林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46
CYHB2600238
利福霉素钠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47
CYHB2600237
利福霉素钠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48
CYHB2600236
氟罗沙星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49
CYHB2600235
复方氨林巴比妥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50
CYHB2600234
磺胺嘧啶钠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51
CYHB2600233
磺胺嘧啶钠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52
CYHB2600232
丙戊酸钠缓释片(I)
化药
补充申请
赛诺菲(杭州)制药有限公司;赛诺菲(杭州)制药有限公司;
2026/2/6
753
CXZS2600013
达原饮颗粒
中药
新药
3.1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2026/2/6
754
CXSS2600015
度拉糖肽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3.3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55
CXSL2600181
呼吸道合胞病毒mRNA疫苗
预防用生物制品
新药
1.2
江苏中慧元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易慧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2026/2/6
756
CXSL2600180
度普利尤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3.3
珠海联邦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026/2/6
757
CXSL2600179
重组人神经生长因子滴眼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2.2
重庆科润生物医药研发有限公司;
2026/2/6
758
CXSL2600178
重组人神经生长因子滴眼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2.2
重庆科润生物医药研发有限公司;
2026/2/6
759
CXHL2600154
BH015注射液
化药
新药
2.4;2.2
珠海贝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60
CXHL2600153
注射用JKN2502
化药
新药
1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61
CXHL2600152
H009L注射液
化药
新药
2.1;2.2;2.4
江苏柯菲平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6
762
CXHB2600037
HRS-7058胶囊
化药
补充申请
1
山东盛迪医药有限公司;
2026/2/6
763
JTS2600017
罗莫索珠单抗注射液
生物制品
Amgen Manufacturing Limited LLC;Amgen Inc.;安进生物技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2026/2/5
764
CYZB2600433
醒脑再造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765
CYZB2600432
参茸壮骨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766
CYZB2600431
血府逐瘀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767
CYZB2600430
苏梅爽含片
中药
补充申请
河南百年康鑫药业有限公司;河南百年康鑫药业有限公司;
2026/2/5
768
CYZB2600429
牛黄上清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769
CYZB2600428
牛黄清胃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770
CYZB2600427
牛黄清宫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771
CYZB2600426
消痔丸
中药
补充申请
河南百年康鑫药业有限公司;河南百年康鑫药业有限公司;
2026/2/5
772
CYZB2600425
八珍益母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773
CYZB2600424
八珍益母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774
CYZB2600423
八珍益母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775
CYZB2600422
济生肾气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776
CYZB2600421
济生肾气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777
CYZB2600420
济生肾气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778
CYZB2600419
利心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779
CYZB2600418
利心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780
CYZB2600417
大活络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781
CYZB2600416
太极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782
CYZB2600415
十全大补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783
CYZB2600414
十全大补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784
CYZB2600413
舒肝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785
CYZB2600412
舒肝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786
CYHS2600384
头孢托仑匹酯颗粒
化药
仿制
4
齐鲁安替制药有限公司;齐鲁安替制药有限公司;
2026/2/5
787
CYHS2600383
头孢托仑匹酯颗粒
化药
仿制
4
齐鲁安替制药有限公司;齐鲁安替制药有限公司;
2026/2/5
788
CYHB2600231
氧
化药
补充申请
石家庄元特气体有限公司;石家庄元特气体有限公司;
2026/2/5
789
CXSL2600177
9MW2821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2/5
790
CXSL2600176
CVL006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甫康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6/2/5
791
JYHZ2600026
富马酸喹硫平缓释片
化药
进口再注册
5.2
PHARMATHEN INVESTMENTS GROUP LIMITED;Pharmathen International S.A.;Shenzhen China Resources Gosun Pharmaceuticals Co., Ltd.;
2026/2/5
792
JYHZ2600025
富马酸喹硫平缓释片
化药
进口再注册
5.2
PHARMATHEN INVESTMENTS GROUP LIMITED;Pharmathen International S.A.;Shenzhen China Resources Gosun Pharmaceuticals Co., Ltd.;
2026/2/5
793
JYHZ2600024
富马酸喹硫平缓释片
化药
进口再注册
5.2
PHARMATHEN INVESTMENTS GROUP LIMITED;Pharmathen International S.A.;Shenzhen China Resources Gosun Pharmaceuticals Co., Ltd.;
2026/2/5
794
JYHZ2600023
富马酸喹硫平缓释片
化药
进口再注册
5.2
PHARMATHEN INVESTMENTS GROUP LIMITED;Shenzhen China Resources Gosun Pharmaceuticals Co., Ltd.;
2026/2/5
795
JYHZ2600022
富马酸喹硫平缓释片
化药
进口再注册
5.2
PHARMATHEN INVESTMENTS GROUP LIMITED;Pharmathen International S.A.;Shenzhen China Resources Gosun Pharmaceuticals Co., Ltd.;
2026/2/5
796
JYHZ2600021
替格瑞洛片
化药
进口再注册
AstraZeneca AB;AstraZeneca AB;AstraZeneca Investment (China)Co.,Ltd.;
2026/2/5
797
JYHZ2600020
替格瑞洛片
化药
进口再注册
AstraZeneca AB;AstraZeneca AB;AstraZeneca Investment (China)Co.,Ltd.;
2026/2/5
798
JYHZ2600019
盐酸帕罗西汀肠溶缓释片
化药
进口再注册
GLAXOSMITHKLINE INC.;BORA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INC.;GlaxoSmithKline(China)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2026/2/5
799
JYHZ2600018
盐酸帕罗西汀肠溶缓释片
化药
进口再注册
GLAXOSMITHKLINE INC.;BORA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INC.;GlaxoSmithKline(China)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2026/2/5
800
JYHB2600082
环硅酸锆钠散
化药
补充申请
5.1
AstraZeneca AB;AndersonBrecon, Inc.;AstraZeneca Pharmaceuticals LP;
2026/2/5
801
JYHB2600081
环硅酸锆钠散
化药
补充申请
5.1
AstraZeneca AB;AndersonBrecon, Inc.;AstraZeneca Pharmaceuticals LP;
2026/2/5
802
JYHB2600080
塞普替尼胶囊
化药
补充申请
5.1
Eli Lilly Nederland B.V.;Lilly del Caribe, Inc.;
2026/2/5
803
JYHB2600079
塞普替尼胶囊
化药
补充申请
5.1
Eli Lilly Nederland B.V.;Lilly del Caribe, Inc.;
2026/2/5
804
JXSB2600019
AMG 451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1
Amgen Inc.;Amgen Inc.;
2026/2/5
805
JTS2600016
达依泊汀α注射液
进口
生物制品
Terumo Corporation, Kofu Factory;Kyowa Kirin Co.,Ltd.;华北制药金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5
806
JTS2600015
达依泊汀α注射液
进口
生物制品
Terumo Corporation, Kofu Factory;Kyowa Kirin Co.,Ltd.;华北制药金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5
807
JTS2600014
达依泊汀α注射液
生物制品
Terumo Corporation, Kofu Factory;Kyowa Kirin Co.,Ltd.;华北制药金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5
808
JTS2600013
达依泊汀α注射液
进口
生物制品
Terumo Corporation, Kofu Factory;Kyowa Kirin Co.,Ltd.;华北制药金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5
809
JTH2600028
重组人促卵泡激素细胞分析用效价对照品
进口
化药
Ferring GmbH;Ferring GmbH;辉凌医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2026/2/5
810
JTH2600027
重组人促卵泡激素二级对照品
化药
Ferring GmbH;Ferring GmbH;辉凌医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2026/2/5
811
JTH2600026
重组人促卵泡激素二级对照品
进口
化药
Ferring GmbH;Ferring GmbH;辉凌医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2026/2/5
812
CYZB2600411
健儿消食口服液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汪氏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汪氏药业有限公司;
2026/2/5
813
CYZB2600410
杞菊地黄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14
CYZB2600409
明目地黄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15
CYZB2600408
明目地黄丸
中药
补充申请
无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16
CYZB2600407
明目地黄丸
中药
补充申请
无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17
CYZB2600406
女金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18
CYZB2600405
女金丸
中药
补充申请
无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19
CYZB2600404
六味地黄丸
中药
补充申请
无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20
CYZB2600403
六味地黄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21
CYZB2600402
六味地黄丸
中药
补充申请
无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22
CYZB2600401
颈康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23
CYZB2600400
梅花点舌片
中药
补充申请
无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24
CYZB2600399
橘红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25
CYZB2600398
橘红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26
CYZB2600397
橘红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27
CYZB2600396
开郁舒肝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28
CYZB2600395
抗骨增生片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29
CYZB2600394
木瓜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30
CYZB2600393
抗栓再造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31
CYZB2600392
溃疡灵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32
CYZB2600391
羚竺散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33
CYZB2600390
牛黄净脑片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34
CYZB2600389
降脂宁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35
CYZB2600388
龙胆泻肝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36
CYZB2600387
牛黄千金散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37
CYZB2600386
藿香正气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38
CYZB2600385
牛黄清肺散
中药
补充申请
无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39
CYZB2600384
脑得生片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40
CYZB2600383
牛黄解毒片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41
CYZB2600382
龙泽熊胆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42
CYZB2600381
牛黄解毒丸
中药
补充申请
无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43
CYZB2600380
琥珀安神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44
CYZB2600379
化毒丹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45
CYZB2600378
护肝片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46
CYZB2600377
热毒平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47
CYZB2600376
冠心苏合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48
CYZB2600375
羚翘解毒片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49
CYZB2600374
人参归脾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50
CYZB2600373
羚翘解毒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51
CYZB2600372
利膈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52
CYZB2600371
黄连上清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重庆康刻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53
CYZB2600370
三宝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达嘉维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达嘉维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026/2/5
854
CYZB2600369
速效牛黄丸
中药
补充申请
河北安国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保定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景忠山国药(唐山)有限公司;
2026/2/5
855
CYZB2600368
壮骨木瓜酒
中药
补充申请
爱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爱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5
856
CYZB2600367
壮骨酒
中药
补充申请
爱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爱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5
857
CYZB2600366
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药
补充申请
爱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爱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5
858
CYZB2600365
史国公药酒
中药
补充申请
爱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爱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5
859
CYZB2600364
豹骨木瓜酒
中药
补充申请
爱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爱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5
860
CYZB2600363
北豆根软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伊春五加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伊春五加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61
CYZB2600362
北豆根片
中药
补充申请
伊春五加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伊春五加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62
CYZB2600361
北豆根分散片
中药
补充申请
伊春五加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伊春五加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63
CYZB2600360
溃疡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达嘉维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达嘉维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026/2/5
864
CYHS2600382
佩玛贝特片
化药
仿制
4
重庆圣华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圣华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5
865
CYHS2600381
盐酸去氧肾上腺素注射液
化药
仿制
3
广州市联瑞制药有限公司;广州市联瑞制药有限公司;
2026/2/5
866
CYHS2600380
盐酸溴己新吸入溶液
化药
仿制
3
江苏正大清江制药有限公司;江苏正大清江制药有限公司;
2026/2/5
867
CYHS2600379
盐酸溴己新吸入溶液
化药
仿制
3
江苏正大清江制药有限公司;江苏正大清江制药有限公司;
2026/2/5
868
CYHS2600378
甲钴胺片
化药
仿制
4
笛卡尔药业(哈尔滨)有限公司;哈尔滨三三药业有限公司;
2026/2/5
869
CYHS2600377
脂肪乳(10%)/氨基酸(15)/葡萄糖(20%)注射液
化药
仿制
4
江苏明德制药有限公司;江苏明德制药有限公司;
2026/2/5
870
CYHS2600376
环磷酰胺注射液
化药
仿制
3
吉斯美(武汉)制药有限公司;吉斯美(武汉)制药有限公司;
2026/2/5
871
CYHS2600375
环磷酰胺注射液
化药
仿制
3
吉斯美(武汉)制药有限公司;吉斯美(武汉)制药有限公司;
2026/2/5
872
CYHS2600374
环磷酰胺注射液
化药
仿制
3
吉斯美(武汉)制药有限公司;吉斯美(武汉)制药有限公司;
2026/2/5
873
CYHS2600373
布洛芬混悬液
化药
仿制
4
黑龙江诺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诺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74
CYHS2600372
非布司他片
化药
仿制
4
山西汾河制药有限公司;山西汾河制药有限公司;
2026/2/5
875
CYHS2600371
非布司他片
化药
仿制
4
山西汾河制药有限公司;山西汾河制药有限公司;
2026/2/5
876
CYHS2600370
琥珀酸亚铁片
化药
仿制
3
浙江远力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浙江远力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77
CYHS2600369
丙酸氟替卡松雾化吸入用混悬液
化药
仿制
4
深圳大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赛默制药有限公司;
2026/2/5
878
CYHB2600230
醋酸泼尼松片
化药
补充申请
4
河南利华制药有限公司;新乡市常乐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79
CYHB2600229
盐酸哌甲酯片
化药
补充申请
苏州第壹制药有限公司;苏州第壹制药有限公司;
2026/2/5
880
CYHB2600228
黄体酮注射液(II)
化药
补充申请
3
吉林省金派格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金派格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6/2/5
881
CXZS2600012
双鱼颗粒
中药
新药
1.1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5
882
CXZS2600011
一贯煎颗粒
中药
新药
3.1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026/2/5
883
CXZL2600021
清润养目颗粒
中药
新药
1.1
上海医药集团中药研究所有限公司;
2026/2/5
884
CXSL2600175
注射用MK-2870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2.2
默沙东研发(中国)有限公司;
2026/2/5
885
CXSL2600174
注射用MK-2870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2.2
默沙东研发(中国)有限公司;
2026/2/5
886
CXSL2600173
LPS-001片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3.3
乐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5
887
CXSL2600172
LPS-001片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3.3
乐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5
888
CXSL2600171
LPS-001片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3.3
乐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5
889
CXSL2600170
IVB107 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北京诺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5
890
CXSL2600169
SCTB35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神州细胞工程有限公司;
2026/2/5
891
CXSL2600168
SCTB35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神州细胞工程有限公司;
2026/2/5
892
CXHL2600151
HS-20136注射液
化药
新药
1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翰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5
893
CXHL2600150
HS-20136注射液
化药
新药
1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翰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5
894
CXHL2600149
HS-20136注射液
化药
新药
1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翰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5
895
CXHL2600148
HS-20136注射液
化药
新药
1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翰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5
896
CXHL2600147
HS-20136注射液
化药
新药
1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翰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5
897
CXHL2600146
HS-20136注射液
化药
新药
1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翰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5
898
CXHL2600145
INS018_055B雾化吸入剂
化药
新药
1
英矽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2026/2/5
899
JXHB2600014
Ulixacaltamide缓释片
化药
补充申请
1
Praxis Precision Medicines;Catalent Pharma Solutions, LLC;
2026/2/4
900
JXHB2600013
Ulixacaltamide缓释片
化药
补充申请
1
Praxis Precision Medicines;Catalent Pharma Solutions, LLC;
2026/2/4
901
JXHB2600012
Ulixacaltamide缓释片
化药
补充申请
1
Praxis Precision Medicines;Catalent Pharma Solutions, LLC;
2026/2/4
902
CYHS2600368
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
化药
仿制
4
四川健林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扬子江药业集团四川海蓉药业有限公司;
2026/2/4
903
CYHS2600367
艾拉莫德片
化药
仿制
4
中寰生物技术(福州)有限公司;浙江北生药业汉生制药有限公司;
2026/2/4
904
CYHS2600366
麦考酚钠肠溶片
化药
仿制
4
重庆迈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天台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4
905
CXHS2600025
芦沃美替尼片
化药
新药
2.4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凯莱英生命科学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2026/2/4
906
CXHS2600024
芦沃美替尼片
化药
新药
2.4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凯莱英生命科学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2026/2/4
907
CXHS2600023
HR091506片
化药
新药
2.2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4
908
CXHS2600022
HR091506片
化药
新药
2.2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4
909
CXHL2600144
SIR9900片
化药
新药
1
维泰瑞隆(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6/2/4
910
CXHB2600036
BGB-16673片
化药
补充申请
1
百济神州(苏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6/2/4
911
CXHB2600035
BGB-16673片
化药
补充申请
1
百济神州(苏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6/2/4
912
JYHZ2600017
吡美莫司乳膏
化药
进口再注册
Viatris Healthcare GmbH;MEDA Manufacturing;Viatris Pharmaceuticals Co., Ltd.;
2026/2/4
913
JYHS2600002
依维莫司片
化药
进口
5.2
Biocon Pharma Limited;Biocon Pharma Limited ;Benova(Tianjin) Pharma Co., Ltd;
2026/2/4
914
CYZB2600359
排石利胆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汪氏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汪氏药业有限公司;
2026/2/4
915
CYZB2600358
夏桑菊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汪氏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汪氏药业有限公司;
2026/2/4
916
CYZB2600357
板蓝根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
2026/2/4
917
CYZB2600356
灵芝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山东凤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凤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4
918
CYZB2600355
黄柏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山东凤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凤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4
919
CYZB2600354
养心宁神丸
中药
补充申请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有限公司;
2026/2/4
920
CYZB2600353
养心宁神丸
中药
补充申请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有限公司;
2026/2/4
921
CYZB2600352
穿心莲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山东凤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凤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4
922
CYZB2600351
远志酊
中药
补充申请
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
2026/2/4
923
CYZB2600350
跌打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青海宝鉴堂国药有限公司;
2026/2/4
924
CYZB2600349
小儿感冒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湖北叶真堂药业有限公司;湖北御金丹药业有限公司;
2026/2/4
925
CYHS2600365
达格列净片
化药
仿制
4
上海衡山药业有限公司;上海衡山药业有限公司;
2026/2/4
926
CYHS2600364
盐酸达泊西汀片
化药
仿制
4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4
927
CYHS2600363
盐酸达泊西汀片
化药
仿制
4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4
928
CYHS2600362
富马酸伏诺拉生片
化药
仿制
4
沐邦(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永安制药有限公司;
2026/2/4
929
CYHS2600361
富马酸伏诺拉生片
化药
仿制
4
沐邦(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永安制药有限公司;
2026/2/4
930
CYHS2600360
丙酸氟替卡松乳膏
化药
仿制
4
广东仁想药业有限公司;浙江赛默制药有限公司;
2026/2/4
931
CYHS2600359
丙酸氟替卡松乳膏
化药
仿制
4
广东仁想药业有限公司;浙江赛默制药有限公司;
2026/2/4
932
CYHS2600358
氧
化药
仿制
4
伊犁鸿瑞坤源气体有限公司;伊犁鸿瑞坤源气体有限公司;
2026/2/4
933
CYHS2600357
瑞维那新吸入溶液
化药
仿制
4
成都奥邦药业有限公司;成都奥邦药业有限公司;
2026/2/4
934
CYHS2600356
联苯苄唑溶液
化药
仿制
3
北京诚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诚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4
935
CYHS2600355
布洛芬混悬液
化药
仿制
4
吉林省益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吉林省益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6/2/4
936
CYHS2600354
托吡酯口服溶液
化药
仿制
3
海南广升誉制药有限公司;安徽永生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6/2/4
937
CYHS2600353
奥美沙坦酯氨氯地平氢氯噻嗪片
化药
仿制
3
上海腾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玻思韬控释药业有限公司;
2026/2/4
938
CYHS2600352
奥美沙坦酯氨氯地平氢氯噻嗪片
化药
仿制
3
上海腾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玻思韬控释药业有限公司;
2026/2/4
939
CYHS2600351
奥美沙坦酯氨氯地平氢氯噻嗪片
化药
仿制
3
上海腾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玻思韬控释药业有限公司;
2026/2/4
940
CYHS2600350
奥美沙坦酯氨氯地平氢氯噻嗪片
化药
仿制
3
上海腾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玻思韬控释药业有限公司;
2026/2/4
941
CYHS2600349
奥美沙坦酯氨氯地平氢氯噻嗪片
化药
仿制
3
上海腾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玻思韬控释药业有限公司;
2026/2/4
942
CYHS2600348
氟比洛芬凝胶贴膏
化药
仿制
4
海南赛立克药业有限公司;湖南派格兰药业有限公司;
2026/2/4
943
CYHS2600347
硝酸甘油舌下片
化药
仿制
4
汇科德晟(广东)医学技术有限公司;四川宏明博思药业有限公司;
2026/2/4
944
CYHL2600020
氨氯地平缬沙坦氢氯噻嗪片
化药
仿制
3
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2026/2/4
945
CYHB2650042
胞磷胆碱钠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多多药业有限公司;多多药业有限公司;
2026/2/4
946
CYHB2600227
氯化钾颗粒
化药
补充申请
恒衍生物医药技术(厦门)有限公司;福州基石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4
947
CYHB2600226
氯化钾颗粒
化药
补充申请
恒衍生物医药技术(厦门)有限公司;福州基石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4
948
CYHB2600225
口服补液盐散(Ⅲ)
化药
补充申请
原6
福州长富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厦门恩成制药有限公司;
2026/2/4
949
CYHB2600224
甲磺酸倍他司汀片
化药
补充申请
4
福州长富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厦门恩成制药有限公司;
2026/2/4
950
CYHB2600223
氨茶碱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4
951
CYHB2600222
氨茶碱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4
952
CYHB2600221
氨茶碱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4
953
CYHB2600220
注射用甲磺酸加贝酯
化药
补充申请
原6
峨眉山通惠制药有限公司;峨眉山通惠制药有限公司;
2026/2/4
954
CYHB2600219
丙戊酸钠口服溶液
化药
补充申请
赛诺菲(杭州)制药有限公司;赛诺菲(杭州)制药有限公司;
2026/2/4
955
CXSL2600167
IBI3031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2026/2/4
956
CXSL2600166
NEWR0919滴眼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深圳新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2026/2/4
957
CXSL2600165
NEWR0919滴眼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深圳新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2026/2/4
958
CXSL2600164
NEWR0919滴眼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深圳新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2026/2/4
959
CXSB2600026
注射用BB-1701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1
百力司康生物医药(杭州)有限公司;
2026/2/4
960
CXHS2600021
甲磺酸奥达替尼胶囊
化药
新药
1
江苏正大丰海制药有限公司;江苏华阳制药有限公司;
2026/2/4
961
CXHS2600020
甲磺酸奥达替尼胶囊
化药
新药
1
江苏正大丰海制药有限公司;江苏华阳制药有限公司;
2026/2/4
962
CXHL2600143
JAB-8263片
化药
新药
1
北京加科思新药研发有限公司;
2026/2/4
963
CXHL2600142
JAB-8263片
化药
新药
1
北京加科思新药研发有限公司;
2026/2/4
964
CXHB2600034
JYP0015片
化药
补充申请
1
广州嘉越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4
965
CYZB2600348
脑力宝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通化斯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龙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3
966
CYZB2600347
补肾强身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通化斯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龙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3
967
CYZB2600346
龙胆泻肝丸
中药
补充申请
通化斯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龙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3
968
CYHS2600346
酮咯酸氨丁三醇片
化药
仿制
3
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3
969
CYHS2600345
玻璃酸钠滴眼液
化药
仿制
4
广州华圣制药有限公司;广州华圣制药有限公司;
2026/2/3
970
JYHB2600078
戊酸雌二醇片/雌二醇环丙孕酮片复合包装
化药
补充申请
Bayer Vital GmbH;Bayer Weimar GmbH & Co. KG;
2026/2/3
971
JXSL2600037
BI 764532 输注用浓缩粉末
治疗用生物制品
进口
1
Boehringer lngelheim International GmbH;Boehringer lngelheim (China) Investment Co.,Ltd.;
2026/2/3
972
JXHS2600021
罗氟司特乳膏
化药
进口
5.1
Arcutis Biotherapeutics INC;DPT Laboratories, Ltd.;无;
2026/2/3
973
JTH2600025
二羟基碳酸铝钠
化药
IL-YANG PHARM. CO., LTD.;IL-YANG PHARM. CO., LTD.;华益药业科技(安徽)有限公司;
2026/2/3
974
CYZB2600345
益母草膏
中药
补充申请
恒拓集团南宁仁盛制药有限公司;恒拓集团南宁仁盛制药有限公司;
2026/2/3
975
CYZB2600344
通脉口服液
中药
补充申请
黑龙江葵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葵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3
976
CYZB2600343
养心定悸膏
中药
补充申请
湖南马王堆制药有限公司;湖南马王堆制药有限公司;
2026/2/3
977
CYZB2600342
牛黄解毒片
中药
补充申请
红云制药(玉溪)有限公司;红云制药(玉溪)有限公司;
2026/2/3
978
CYZB2600341
川贝枇杷糖浆
中药
补充申请
四川天府康达药业集团府庆制药有限公司;四川天府康达药业集团府庆制药有限公司;
2026/2/3
979
CYZB2600340
咳特灵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恒拓集团广西圣康制药有限公司;恒拓集团广西圣康制药有限公司;
2026/2/3
980
CYZB2600339
桂茸固本丸
中药
补充申请
水仙药业(建瓯)股份有限公司;水仙药业(建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3
981
CYZB2600338
桂茸固本丸
中药
补充申请
水仙药业(建瓯)股份有限公司;水仙药业(建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3
982
CYZB2600337
麻杏宣肺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湖南康寿制药有限公司;湖南康寿制药有限公司;
2026/2/3
983
CYZB2600336
西洋参金钱龟合剂
中药
补充申请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3
984
CYZB2600335
宁神定志丸
中药
补充申请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3
985
CYZB2600334
卫生培元丸
中药
补充申请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3
986
CYZB2600333
舒咳枇杷糖浆
中药
补充申请
安徽茂康药业有限公司;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3
987
CYSB2600051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026/2/3
988
CYSB2600050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026/2/3
989
CYSB2600049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
治疗用生物制品
补充申请
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026/2/3
990
CYHS2600344
盐酸西替利嗪滴剂
化药
仿制
4
江苏晨牌邦德药业有限公司;江苏晨牌邦德药业有限公司;
2026/2/3
991
CYHS2600343
盐酸西替利嗪滴剂
化药
仿制
4
江苏晨牌邦德药业有限公司;江苏晨牌邦德药业有限公司;
2026/2/3
992
CYHS2600342
乌帕替尼缓释片
化药
仿制
4
烟台鲁银药业有限公司;烟台鲁银药业有限公司;
2026/2/3
993
CYHS2600341
托拉塞米注射液
化药
仿制
3
云南药科院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楚雄和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6/2/3
994
CYHS2600340
盐酸舍曲林口服浓缩液
化药
仿制
3
北京远方通达医药技术有限公司;华益药业科技(安徽)有限公司;
2026/2/3
995
CYHS2600339
复方匹可硫酸钠颗粒
化药
仿制
3
浙江皓格药业有限公司;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3
996
CYHS2600338
氧
化药
仿制
4
新疆鼎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鼎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6/2/3
997
CYHS2600337
吸入用丙酸倍氯米松混悬液
化药
仿制
4
山东京卫制药有限公司;山东京卫制药有限公司;
2026/2/3
998
CYHB2650041
维生素B12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华润双鹤利民药业(济南)有限公司;华润双鹤利民药业(济南)有限公司;
2026/2/3
999
CYHB2650040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
化药
补充申请
上海上药新亚药业有限公司;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3
1000
CYHB2650039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
化药
补充申请
上海上药新亚药业有限公司;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3
1001
CYHB2600218
盐酸曲马多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江苏九旭药业有限公司;江苏九旭药业有限公司;
2026/2/3
1002
CYHB2600217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化药
补充申请
原4
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3
1003
CYHB2600216
碳酸氢钠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
2026/2/3
1004
CYHB2600215
吡拉西坦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3
1005
CYHB2600214
吡拉西坦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3
1006
CYHB2600213
注射用头孢他啶他唑巴坦钠(3:1)
化药
补充申请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合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3
1007
CXSL2600163
注射用GenSci136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6/2/3
1008
CXSL2600162
注射用SHR-9839(sc)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
2026/2/3
1009
CXSL2600161
SHR-8068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2.2
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026/2/3
1010
CXSL2600160
注射用SHR-1826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026/2/3
1011
CXSL2600159
SAL0896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南京赛乐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026/2/3
1012
CXSL2600158
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2.2
上海盛迪医药有限公司;
2026/2/3
1013
CXSL2600157
注射用FH-006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甫弘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026/2/3
1014
CXHL2600141
注射用HY016
化药
新药
1
天津铂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3
1015
CXHL2600140
葡萄糖迟释片
化药
新药
2.2
浙江汉脉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3
1016
CXHL2600139
HRS-6093片
化药
新药
1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3
1017
CXHL2600138
HRS-6093片
化药
新药
1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2/3
1018
CXHB2600033
HRS-9813 胶囊
化药
补充申请
1
广东恒瑞医药有限公司;
2026/2/3
1019
JYHZ2600016
利奥西呱片
化药
进口再注册
Bayer AG;Bayer AG;Bayer Healthcare Company Ltd.;
2026/2/2
1020
JYHZ2600015
利奥西呱片
化药
进口再注册
Bayer AG;Bayer AG;Bayer Healthcare Company Ltd.;
2026/2/2
1021
JYHZ2600014
利奥西呱片
化药
进口再注册
Bayer AG;Bayer AG;Bayer Healthcare Company Ltd.;
2026/2/2
1022
JYHZ2600013
利奥西呱片
化药
进口再注册
Bayer AG;Bayer AG;Bayer Healthcare Company Ltd.;
2026/2/2
1023
JYHZ2600012
利奥西呱片
化药
进口再注册
Bayer AG;Bayer AG;Bayer Healthcare Company Ltd.;
2026/2/2
1024
JYHB2600077
马立巴韦片
化药
补充申请
5.1
Taked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Catalent CTS, LLC;Takeda Ireland Limited;
2026/2/2
1025
JYHB2600076
富马酸比索洛尔片
化药
补充申请
Aspen Pharma Schweiz GmbH;Lek S.A.;
2026/2/2
1026
JTS2600012
阿巴西普注射液
生物制品
Vetter Pharma Fertigung GmbH & Co. KG;Bristol-Myers Squibb Company;百时美施贵宝(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026/2/2
1027
CYZB2600332
肾炎安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2
1028
CYZB2600331
妇炎净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2/2
1029
CYZB2600330
五子衍宗丸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省芙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芙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2
1030
CYZB2600329
五子衍宗丸
中药
补充申请
江西省芙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芙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2
1031
CYHS2600336
头孢丙烯片
化药
仿制
4
温岭市创新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万邦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2026/2/2
1032
CYHS2600335
盐酸特比萘芬喷雾剂
化药
仿制
4
济南中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山东京卫制药有限公司;
2026/2/2
1033
CYHS2600334
盐酸特比萘芬喷雾剂
化药
仿制
4
济南中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山东京卫制药有限公司;
2026/2/2
1034
CYHB2650038
瑞格列奈片
化药
补充申请
原6
天津市康瑞药业有限公司;天津市康瑞药业有限公司;
2026/2/2
1035
CYHB2650037
碳酸氢钠注射液
化药
补充申请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2/2
1036
CYHB2600212
厄贝沙坦片
化药
补充申请
赛诺菲(杭州)制药有限公司;赛诺菲(杭州)制药有限公司;
2026/2/2
1037
CXHL2600137
HX102片
化药
新药
1
华夏生生药业(北京)有限公司;
2026/2/2
1038
CXHL2600136
HX102片
化药
新药
1
华夏生生药业(北京)有限公司;
2026/2/2
申请上市高管变更临床申请
2026-02-02
·大药时记
Summit Therapeutics确认了与FDA的关键会面时间,FDA已正式受理其从康方引进的PD-1/VEGF双抗的上市申请,预计将在2026年11月前做出最终审批决定。
美国生物医药初创企业Tenpoint Therapeutics宣布,其针对老花眼的眼药水YUVEZZI获得美国FDA正式批准上市,产品即将进入老视治疗的商业市场。这款眼药水作为非手术的药物治疗新选择,特别针对40岁以上人群普遍出现的调节能力下降问题,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出显著的视力改善效果。此次FDA批准使Tenpoint成为市场上少数获监管认可的老视治疗药物提供者之一。为了确保产品顺利上市并快速打开市场,Tenpoint同步完成了2.35亿美元的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市场推广、产能扩展及后续临床研究。此次融资吸引了多家知名投资机构参与。YUVEZZI(卡巴胆碱 2.75% / 酒石酸溴莫尼定 0.1%)是一种每日一次的双效滴眼液,用于治疗老花眼。它通过诱导瞳孔收缩(缩瞳)产生“小孔效应”,从而改善近距离和中距离视力,同时不影响远距离视力。该滴眼液结合了胆碱能激动剂卡巴胆碱和 α₂-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溴莫尼定。
因一名受试者出现脑肿瘤,美国FDA决定暂停Regenxbio针对Hurler综合征的早期治疗试验,同时暂停即将面临FDA审批的Hunter综合征治疗方案。此次监管决定源于一例5岁儿童患者四年前接受AAV9基因疗法RGX-111治疗后被诊断出脑癌。鉴于两款疗法的相似性及“临床研究间存在共享风险”,FDA决定将暂停范围扩大至另一款疗法RGX-121。Regenxbio方面表示,目前尚无证据证明RGX-111与该儿童病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并强调RGX-121为独立疗法,已有多年安全数据支持。
罗氏宣布终止一款引进自Kiniksa Pharmaceuticals的炎症药物vixarelimab的研发项目,同时放弃已投入的1亿美元投资。这是罗氏最新季度管线资产清理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剔除表现不佳、风险较高的候选药物,优化研发资源配置。vixarelimab是一种靶向肿瘤坏死因子家族成员,肿瘤抑制素M受体β(oncostatin M receptor beta)的抗体药物。2022年,罗氏旗下Genentech部门为获得该药物支付了8000万美元预付款,协议中还约定在收到Kiniksa特定药物供应后再支付2000万美元。实际上vixarelimab的研发历史更早,2016年Kiniksa以1150万美元从渤健手中收购了该药物。根据双方协议,Kiniksa负责推进vixarelimab在结节性瘙痒症(prurigo nodularis)患者中的2b期临床试验,随后Genentech将该药物推进到针对特发性肺纤维化(IPF)和系统性硬化症相关间质性肺病(SSc-ILD)的2期临床研究。然而,罗氏最新公布的无效性分析结果显示,该药物难以达到预设的疗效标准。罗氏发言人表示,虽然未发现新的安全性问题,但公司对结果感到失望,决定终止该项目。
在2025年全年财报中,赛诺菲披露已终止一款处于临床一期阶段的mRNA流感疫苗项目。赛诺菲发言人透露,他们已将基于mRNA技术的季节性流感疫苗项目降为非优先级,短期内不计划推出此类产品。尽管如此,赛诺菲强调,mRNA技术仍是其多平台疫苗开发战略的核心。公司目前正推进一款针对H5流感大流行的mRNA疫苗1/2期临床研究。
同样在2025年全年财报中,赛诺菲披露终止了与Denali Therapeutics合作开发的最后一款RIPK1抑制剂项目。公司已将eclitasertib的开发优先级调低。对此,赛诺菲对未来合作的态度保持谨慎沉默,未透露更多细节。eclitasertib是一种针对受体相互作用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1(RIPK1)的抑制剂,赛诺菲此前一直在进行针对溃疡性结肠炎(UC)的II期临床试验。早在2018年,赛诺菲便向Denali预付了1.25亿美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抑制RIPK1可以阻断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进而减少组织损伤和神经元死亡。然而经过7年努力,赛诺菲始终未能在临床试验中验证这一理论。2020年,由于预临床慢性毒性研究结果不理想,两家公司停止了最初首选候选药物的开发,转而将重点转向另一款药物oditrasertib。但oditrasertib在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和多发性硬化症(MS)的II期临床试验中均以失败告终。这使得eclitasertib成为双方合作中唯一仍在开发的候选药物。该药物为外周限制性抑制剂,曾在2023年针对皮肤性红斑狼疮的II期试验中失败,但在溃疡性结肠炎领域的研究一直持续至今。整个制药行业在RIPK1抑制剂的开发上都遇到了不小的挑战。GSK于2021年放弃了一款用于癌症的RIPK1候选药物,并将另一款资产转让给Boston Pharmaceuticals;BMS也在2023年剔除了其管线中的I期RIPK1抑制剂;仅两个月前,礼来宣布退出一项价值9.6亿美元的、聚焦中枢神经系统的Rigel Pharmaceuticals RIPK1抑制剂合作项目。
勃林格殷格翰公布了其肾病候选药物apecotrep(BI 764198)的最新Ⅱ期临床数据,这些数据为其上周启动该药关键Ⅲ期试验提供了坚实依据。此次Ⅱ期试验针对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FSGS)患者,采用随机分组设计,受试者分别接受三种不同剂量的apecotrep(一种TRPC6通道抑制剂)或安慰剂。对60名治疗且数据完整的患者分析显示,apecotrep组的蛋白尿反应率达到35%,明显优于安慰剂组的7%。不过,中剂量组的反应率仅为14%,使整体反应率有所下降。勃林格殷格翰于2025年11月在美国肾脏病学会(ASN)肾脏周会议上首次披露相关数据,并于本周二在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了详细研究结果。数据显示,apecotrep可能通过靶向肾脏滤过屏障中的关键细胞——足细胞(podocytes),改善FSGS患者的临床结局。足细胞是肾脏滤过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FSGS患者的足细胞常受损伤。已有研究表明,TRPC6通道的过度活跃会导致足细胞功能丧失和肾功能逐渐恶化,这一发现促使勃林格殷格翰评估抑制该通道的治疗潜力。基于Ⅱ期试验的积极信号,勃林格殷格翰决定启动一项关键的Ⅲ期临床试验。该试验计划随机招募286名FSGS患者,分组接受apecotrep或安慰剂治疗,主要观察104周后两组尿蛋白-肌酐比值的变化。预计该试验将于2029年底完成。目前,FDA尚未批准任何针对FSGS的疗法,但多家公司正积极布局该领域以满足临床需求。Travere Therapeutics已为其药物Filspari提交FDA适应症审批申请,尽管审批进度有所延迟,预计将在今年4月13日前获得裁决。该公司表示,FDA需要更多时间评估Filspari的临床获益。去年BioMarin收购的Amicus Therapeutics也获得了一项FSGS的Ⅲ期临床项目。此外,赛诺菲正在开展三种候选药物——frexalimab、brivekimig和rilzabrutinib的Ⅱ期FSGS临床试验。诺华在一项Ⅱ期篮子试验中设有FSGS研究组,研究药物为atrasentan,该药已在其他适应症下获批并以Vanrafia品牌销售。2024年诺华将FSGS列入2031年及以后可能申请批准的适应症名单。Vertex针对APOL1基因介导的肾病(包括部分FSGS类型)正在进行inaxaplin的Ⅱ期临床试验,并已于2024年启动了Ⅲ期试验。2025年,Vera Therapeutics启动了atacicept的Ⅱ期试验,该药今年有望在IgA肾病中获得FDA批准,同时也在FSGS及其他肾小球疾病中开展研究。
美国FDA解除了一项针对Intellia Therapeutics公司CRISPR疗法的临床试验暂停令,使其一项关键的III期研究得以恢复。此前,由于另一项同系试验中出现了4级肝脏不良事件及患者死亡,FDA曾对Intellia的两项晚期临床试验同时下达暂停令。消息公布后,Intellia股价迅速反弹,当日上涨12%。去年秋季,FDA对Intellia的Magnitude和Magnitude-2两项III期临床研究实施暂停。这两项研究分别评估其实验性CRISPR疗法在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心肌病(ATTR-CM)和遗传性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伴多发性神经病变(ATTRv-PN)患者中的疗效,这两种疾病均严重影响心脏功能。本次临床暂停的直接原因是Intellia主动停止了Magnitude试验,因该试验中出现了一例符合Hy’s Law标准的4级肝脏不良事件。暂停令生效后不久,Intellia披露该患者已不幸去世。尽管该患者存在多种合并症,官方报告的死亡原因是感染性休克,表明单纯肝酶升高并非直接致死因素。Intellia表示,肝脏损伤及肝酶升高很可能与其治疗药物nexiguran ziclumeran(简称nex-z)有关,这是一种基于CRISPR技术设计,用于敲除TTR基因的创新疗法。
亲爱的读者,如果您对生物医药的最新动态感兴趣,或希望了解更多前沿生物科技资讯,请关注公众号。您的每一次关注和转发,都是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 关注大药时记,掌握更多前沿生物科技!
👉 分享文章,让更多人受益!
引进/卖出临床2期基因疗法
100 项与 Brivekimig 相关的药物交易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研发状态
10 条进展最快的记录, 后查看更多信息
登录
| 适应症 | 最高研发状态 | 国家/地区 | 公司 | 日期 |
|---|---|---|---|---|
| 溃疡性结肠炎 | 临床2期 | 美国 | 2025-07-07 | |
| 溃疡性结肠炎 | 临床2期 | 中国 | 2025-07-07 | |
| 溃疡性结肠炎 | 临床2期 | 日本 | 2025-07-07 | |
| 溃疡性结肠炎 | 临床2期 | 澳大利亚 | 2025-07-07 | |
| 溃疡性结肠炎 | 临床2期 | 捷克 | 2025-07-07 | |
| 溃疡性结肠炎 | 临床2期 | 法国 | 2025-07-07 | |
| 溃疡性结肠炎 | 临床2期 | 德国 | 2025-07-07 | |
| 溃疡性结肠炎 | 临床2期 | 匈牙利 | 2025-07-07 | |
| 溃疡性结肠炎 | 临床2期 | 摩尔多瓦 | 2025-07-07 | |
| 溃疡性结肠炎 | 临床2期 | 波兰 | 2025-07-07 |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临床结果
临床结果
适应症
分期
评价
查看全部结果
| 研究 | 分期 | 人群特征 | 评价人数 | 分组 | 结果 | 评价 | 发布日期 |
|---|
临床2期 | 86 | placebo+SAR442970 (Period A: Placebo) | 顧衊衊鏇齋簾壓壓顧淵 = 夢夢餘膚鏇構鑰憲網齋 願淵築遞構衊齋憲餘憲 (餘獵繭願構遞廠製製顧, 鬱繭糧鏇繭鹹遞廠鹹餘 ~ 糧網蓋網憲廠範壓齋鬱) 更多 | - | 2026-01-29 | ||
(Period A: SAR442970) | 顧衊衊鏇齋簾壓壓顧淵 = 淵鑰糧簾繭襯蓋衊鹽築 願淵築遞構衊齋憲餘憲 (餘獵繭願構遞廠製製顧, 淵蓋餘鑰膚製築蓋衊觸 ~ 壓積鏇淵蓋衊鹽鹽壓艱) 更多 |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转化医学
使用我们的转化医学数据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药物交易
使用我们的药物交易数据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核心专利
使用我们的核心专利数据促进您的研究。
登录
或

临床分析
紧跟全球注册中心的最新临床试验。
登录
或

批准
利用最新的监管批准信息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生物类似药
生物类似药在不同国家/地区的竞争态势。请注意临床1/2期并入临床2期,临床2/3期并入临床3期
登录
或

特殊审评
只需点击几下即可了解关键药物信息。
登录
或

生物医药百科问答
全新生物医药AI Agent 覆盖科研全链路,让突破性发现快人一步
立即开始免费试用!
智慧芽新药情报库是智慧芽专为生命科学人士构建的基于AI的创新药情报平台,助您全方位提升您的研发与决策效率。
立即开始数据试用!
智慧芽新药库数据也通过智慧芽数据服务平台,以API或者数据包形式对外开放,助您更加充分利用智慧芽新药情报信息。
生物序列数据库
生物药研发创新
免费使用
化学结构数据库
小分子化药研发创新
免费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