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约演示
更新于:2025-1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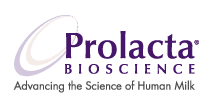
Prolacta Bioscience, Inc.
更新于:2025-12-05
概览
关联
17
项与 Prolacta Bioscience, Inc. 相关的临床试验NCT06102213
A Randomized, Open-Label, Multicenter, Phase 2a Study To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PBCLN-010 In Combination With PBCLN-014 in Participants Receiving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ation (Allo-HCT)
This is a Phase 2a, open-label, multicenter study to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HMO (PBCLN-010) and B. infantis (PBCLN-014) on the gut microbiome and GI domination by pathobionts in participants receiving allo-HCT.
Approximately 60 participants will b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nd all participants will undergo screening assessments up to 28 days before the first study drug dose (D 7). Participants meeting all the eligibility criteria based on the screening assessments will be enrolled and randomly assigned to 1 of the 3 cohorts:
* Cohort A (HMO 9.0 g and B. infantis) BID
* Cohort B (HMO 4.5 g and B. infantis) BID
* Cohort C (Control Cohort): Participants in this cohort will not receive any study drug.
Approximately 60 participants will b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nd all participants will undergo screening assessments up to 28 days before the first study drug dose (D 7). Participants meeting all the eligibility criteria based on the screening assessments will be enrolled and randomly assigned to 1 of the 3 cohorts:
* Cohort A (HMO 9.0 g and B. infantis) BID
* Cohort B (HMO 4.5 g and B. infantis) BID
* Cohort C (Control Cohort): Participants in this cohort will not receive any study drug.
开始日期2023-09-18 |
申办/合作机构 |
NCT05141903
Dietary Study of a Complex Oligosaccharide With and Without a Probiotic Following Antibiotic Treatment in Healthy Volunteers
Complex oligosaccharides can alter the gut microbiome by aiding in the growth of certain organisms, and possibly, inhibiting others. The synergy with a probiotic may enhance gastrointestinal colonization.
开始日期2021-09-21 |
申办/合作机构 |
NCT04413994
Effects of an Exclusive Human-milk Diet in Preterm NEOnates on Early VASCular Aging Risk Factors (NEOVASC)
Early vascular aging has its origins in fetal and neonatal life. The NEOVASC clinical trial aim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an exclusive human milk diet in extremely preterm infants on long-term cardiovascular health.
开始日期2020-10-09 |
申办/合作机构 |
100 项与 Prolacta Bioscience, Inc. 相关的临床结果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0 项与 Prolacta Bioscience, Inc. 相关的专利(医药)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3
项与 Prolacta Bioscience, Inc. 相关的文献(医药)2013-12-01·The Journal of pediatrics2区 · 医学
Randomized Trial of Exclusive Human Milk versus Preterm Formula Diets in Extremely Premature Infants
2区 · 医学
Article
作者: Cynthia L. Blanco ; Ursula Kiechl-Kohlendorfer ; Steven Abrams ; Elizabeth A. Cristofalo ; Sandra Sullivan ; Martin L. Lee ; Golde Dudell ; Alan Lucas ; Richard J. Schanler ; David J. Rechtman ; Rudolf Trawoeger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duration of parenteral nutrition, growth, and morbidity in extremely premature infants fed exclusive diets of either bovine milk-based preterm formula (BOV) or donor human milk and human milk-based human milk fortifier (HUM), in a randomized trial of formula vs human milk.
STUDY DESIGN:
Multicen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The authors studied extremely preterm infants whose mothers did not provide their milk. Infants were fed either BOV or an exclusive human milk diet of pasteurized donor human milk and HUM. The major outcome was duration of parenteral nutrition. Secondary outcomes were growth, respiratory support, and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NEC).
RESULTS:
Birth weight (983 vs 996 g) and gestational age (27.5 vs 27.7 wk), in BOV and HUM, respectively, were similar.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edian parenteral nutrition days: 36 vs 27, in BOV vs HUM, respectively (P = .04). The incidence of NEC in BOV was 21% (5 cases) vs 3% in HUM (1 case), P = .08; surgical NEC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BOV (4 cases) than HUM (0 cases), P = .04.
CONCLUSIONS:
In extremely preterm infants given exclusive diets of preterm formula vs human milk, there was a significantly greater duration of parenteral nutrition and higher rate of surgical NEC in infants receiving preterm formula. This trial supports the use of an exclusive human milk diet to nourish extremely preterm infants in the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2007-03-01·Breastfeeding medicine :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Breastfeeding Medicine4区 · 医学
Antimicrobial and Antiviral Effect of High-Temperature Short-Time (HTST) Pasteurization Applied to Human Milk
4区 · 医学
Article
作者: Lee, Martin L. ; Rechtman, David J. ; Engelenberg, Frank A.C. Van ; Terpstra, Fokke G. ; Berg, Hijlkeline ; Hoeij, Klaske Van ; Wout, Angelica B. Va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cerns over the transmiss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have led to donor human milk generally being subjected to pasteurization prior to distribution and use. The standard method used by North American milk banks is Holder pasteurization (63 degrees C for 30 minutes). The authors undertook an experiment to validate the effects of a high-temperature short-time (HTST) pasteurization process (72 degrees C for 16 seconds) on the bioburden of human milk. It was concluded that HTST is effective in the elimination of bacteria as well as of certain important pathogenic viruses.
2006-03-01·Breastfeeding medicine :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Breastfeeding Medicine4区 · 医学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n Unpasteurized Donor Human Milk
4区 · 医学
Article
作者: Berg, H. ; Lee, Martin L. ; Rechtman, David J.
As a result of concerns over the transmiss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by donor milk, as well as the possible loss of nutritional value of donor milk through exposure to a variety of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e prac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to discard unpasteurized donor milk that has thawed or sat for several hours at room temperature or in the refrigerator rather than (re)freezing it. We undertook an experiment to measure the effects of ambient temperature conditions and refreezing on the bioburden and nutritional content of human milk. We conclude that unpasteurized human milk is robust and can be used after storage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27
项与 Prolacta Bioscience, Inc. 相关的新闻(医药)2025-11-18
Prolacta Offers the Only Nutritional Products Free From Cow Milk and Added Synthetic Ingredients Like Corn Syrup for Extremely Premature Infants in the U.S.
DUARTE, Calif., Nov. 18, 2025 /PRNewswire/ -- Prolacta Bioscience® is celebrating Prematurity Awareness Month with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in neonatal care: In 2025, the majority of Level III and IV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s (NICUs) in the U.S. (55%) used Prolacta's 100% breastmilk-based fortifiers and formulas, free from cow milk.1 This shift in feeding practices is reducing serious complications and supporting better short- and long-term health outcomes for the tiniest babies.2-8
Each year in the U.S., about 36,000 babies are born weighing 1,250 grams (2.75 lbs) or less9 and face the highest risk of serious complications, including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NEC), a life-threatening intestinal disease.6-8,10
Compared to cow milk-based products, an Exclusive Human Milk Diet (EHMD) with Prolacta's 100% breastmilk-based nutritional fortifiers and formulas is shown to increase survival11 and reduce the most common complications of prematurity,4-8 enabling infants born as early as 22 weeks gestation to not just survive, but to thrive.
Prolacta's nutritional products have also been shown to impact developmental milestones years later.2,3 Most recently, an independent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despite being born earlier and weighing less, premature infants fed Prolacta's EHMD had lower motor skill disability risk by age 3 compared to preemies fed a non-EHMD.12
"Two decades of research have shown the benefits of breastmilk-based nutrition, free from cow milk, for the most fragile premature infants," said Scott Elster, CEO of Prolacta. "Across the country, clinicians and parents are seeing fewer complications, shorter hospital stays, and better developmental outcomes."
Since 2006, Prolacta has continuously supplied breastmilk-based fortifiers for the most vulnerable infants in the NICU, adding breastmilk-based formulas in 2013. With production capacity that has always been able to scale to meet demand and a robust waiting list of donors ready to contribute, Prolacta continues to provide lifesaving nutrition for every preemie born weighing 2.75 lbs or less as more hospitals adopt breastmilk-based feeding as the standard of care.
Understanding the Unique Nutritional Needs of Preemies
Premature babies need 20% to 40% more calories and protein than full-term babies to make up for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ey missed during the third trimester.13,14 As a result, hospitals add a nutritional "fortifier" to mom's own milk or donor milk to provide the extra nutrition needed for healthy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ere are two types of fortifiers available: cow milk-based and breastmilk-based. In the U.S., both are labeled "human milk fortifiers," but only those from Prolacta are made from 100% donor breastmilk instead of cow milk. The difference can be life-changing for critically ill and premature infants. As awareness has grown regarding the two nutrition options, so too have parental requests for nutrition free from cow milk and added synthetic ingredients for their fragile preemies in the NICU.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breastmilk-based nutrition, visit parents.prolacta.com.
About Prolacta Bioscience
Prolacta Bioscience® is a global life sciences company dedicated to Advancing the Science of Human Milk® to improve health outcomes for critically ill and premature infants. More than 125,000 extremely premature infants worldwide15 have benefited from Prolacta's human milk-based products, which have been evaluated in more than 30 peer-reviewed clinical studies. In a significant advancement, Prolacta has developed Surgifort®, the first and only FDA-approved human milk-based fortifier designed for term infants recovering from corrective surgery for gastroschisis. Operating the world's first pharmaceutical-grade human milk processing facilities, Prolacta maintains the industry's strictest quality and safety standards, with over 20 validated tests for screening and testing human milk. Prolacta's manufacturing process uses vat pasteurization to ensure pathogen inactivation while protecting nutritional composition and bioactivity. Learn more online, or on X, Instagram, Facebook, and LinkedIn.
Media Contact:
Loren Kosmont
[email protected]
310-721-9444
References
Data on file; number of U.S. hospitals that used Prolacta's fortifiers and formulas in 2025.
Hair AB, Patel AL, Kiechl-Kohlendorfer U, et al. Neurodevelopmental outcomes of extremely preterm infants fed an exclusive human milk-based diet versus a mixed human milk + bovine milk-based diet: a multi-center study. J Perinatol. 2022;42(11):1485-1488.
Bergner EM, Shypailo R, Visuthranukul C, et al. Growth, body composition, and neurodevelopmental outcomes at 2 years among preterm infants fed an exclusive human milk diet in the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a pilot study. Breastfeed Med. 2020;15(5):304-311.
Huston R, Lee M, Rider E, et al. Early fortification of enteral feedings for infants <1250 grams birth weight receiving a human milk diet including human milk-based fortifier. J Neonatal Perinatal Med. 2020;13(2):215-221.
Delaney Manthe E, Perks PH, Swanson JR. Team-based implementation of an exclusive human milk diet. Adv Neonatal Care. 2019;19(6):460-467.
Assad M, Elliott MJ, Abraham JH. Decreased cost and improved feeding tolerance in VLBW infants fed an exclusive human milk diet. J Perinatol. 2016;36(3):216-220.
Hair AB, Peluso AM, Hawthorne KM, et al. Beyond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prevention: improving outcomes with an exclusive human milk-based diet [published correction appears in Breastfeed Med. 2017;12(10):663]. Breastfeed Med. 2016;11(2):70-74.
Sullivan S, Schanler RJ, Kim JH, et al. An exclusively human milk-based diet is associated with a lower rate of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than a diet of human milk and bovine milk-based products. J Pediatr. 2010;156(4):562-567.e1.
Osterman MJK, Hamilton BE, Martin JA, Driscoll AK, Valenzuela CP. Births: Final data for 2022. 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s; vol 73, no 2. Hyattsville, MD: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2024. doi:
Harris L, Lewis S, Vardaman S. Exclusive human milk diets and the reduction of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Adv Neonatal Care. 2024;24(5):400-407.
Abrams SA, Schanler RJ, Lee ML, Rechtman DJ. Greater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in extremely preterm infants fed a diet containing cow milk protein products. Breastfeed Med. 2014;9(6):281-285.
Chou FS, Zhang J, Villosis MFB, et al. Exclusive human milk diet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 risk of motor function impairment at three years of corrected age. J Perinatol. 2025.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Policy statement: breastfeeding and the use of human milk. Section on Breastfeeding. Pediatrics. 2022;150(1):e2022057988.
Hair AB, Bergner EM, Lee ML, et al. Premature infants 750-1,250 g birth weight supplemented with a novel human milk-derived cream are discharged sooner. Breastfeed Med. 2016;11(3):133-137.
Data on file; estimated number of premature infants fed Prolacta's products from January 2007 to May 2025.
SOURCE Prolacta Bioscience
21%
more press release views with
Request a Demo
2025-11-12
Totality of Evidence Demonstrates Meaningful Reductions in Both Medical and Surgical NEC for Ver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s
DUARTE, Calif., Nov. 12, 2025 /PRNewswire/ -- A landmark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Nutrients has found that an Exclusive Human Milk Diet (EHMD) with Prolacta Bioscience's human milk-based fortifiers is associated with 35% reduced risk of medical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NEC) and 49% reduced risk of surgical NEC in premature infants, compared to diets containing cow milk-based products.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represents the most ext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evidence to date, examining 20 studies encompassing 6,794 very low birth weight (VLBW) premature babies.
NEC is a devastating intestinal disease that is a leading cause of death and disability in premature infants. The new findings provide crucial clarity for clinicians and families navigating nutrition decisions for the most vulnerable babies.
"This is the largest and most comprehensive analysis to date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an Exclusive Human Milk Diet on NEC outcomes," said co-author Jenelle Ferry, MD. "As both a neonatologist and researcher, these findings confirm the protective benefits I've consistently observed in my own clinical practice with premature infants."
The meta-analysis included f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and 15 observational cohort studies conduc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Canada, Austria, and Sweden. Researchers used rigorous statistical methods to account for differences in study design, fortification protocols, and baseline patient characteristics. The trials were analyzed both by study type and collectively, and the observed reduction was consistent across both the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 and the observational studies.
"While individual randomized trials have often failed to reac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hey were also underpowered to detect differences in rare outcomes like NEC," said co-author Sarah M. Reyes, Ph.D. "Our synthesis demonstrated a consistent direction and magnitude of benefit across all study types. This suggests that for ver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s, particularly those weighing 1,250 grams or less, an EHMD with human milk-based fortifiers is associated with meaningful reductions in both medical and surgical NEC."
NEC can vary in severity. Medical NEC requires intervention such as stopping feeds and administering antibiotics. Surgical NEC, the most severe and often life-threatening form, occurs when the intestine perforates or tissue dies, requiring surgery that often involves removing damaged sections of the intestine.
Key findings:
In direct comparisons of fortifier type with a base diet of human milk, Prolacta's human milk-based fortifiers were associated with 35% lower odds of medical NEC and 49% lower odds of surgical NEC compared to cow milk-based fortifiers.1
The protective association was consistent across both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and real-world observational studies, with pooled analyses achieving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1
The majority of infants studied weighed ≤1,250 grams (2.75 lbs) at birth, representing the smallest and most vulnerable babies at highest risk for NEC.1
The inclusion of real-world observational data provides essential evidence of effectiveness across diverse clinical settings. The authors note that existing randomized trials enrolled relatively small numbers of infants (53-228 total) at a time when NEC incidence was already declining due to improved practices in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s (NICUs). Detecting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uch rare outcomes would have required enrollment of approximately 5,000-9,000 infants — a number that renders traditional randomized trials impractical.
The authors call for standardization of fortification protocols and reporting metrics, pragmatic registry-based trials, and continued documentation of both feeding practices and outcomes to strengthen the evidence base for optimal nutrition strategies in VLBW infant care.
About Prolacta Bioscience
Prolacta Bioscience® is a global life sciences company dedicated to Advancing the Science of Human Milk® to improve health outcomes for critically ill and premature infants. More than 125,000 extremely premature infants worldwide2 have benefited from Prolacta's human milk-based products, which have been evaluated in more than 30 peer-reviewed clinical studies. In a significant advancement, Prolacta has developed Surgifort®, the first and only FDA-approved human milk-based fortifier designed for term infants recovering from corrective surgery for gastroschisis. Operating the world's first pharmaceutical-grade human milk processing facilities, Prolacta maintains the industry's strictest quality and safety standards, with over 20 validated tests for screening and testing human milk. Prolacta's manufacturing process uses vat pasteurization to ensure pathogen inactivation while protecting nutritional composition and bioactivity. Learn more online or at X, Instagram, Facebook, TikTok, and LinkedIn.
Media Contact:
Loren Kosmont
[email protected]
310-721-9444
References
Reyes SM, Paul TL, Ferry J. Human milk fortification and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in very low birthweight infants: state of evidence and systematic review with meta-analysis. Nutrients. 2025;17:3384.
Data on file; estimated number of premature infants fed Prolacta's products from January 2007 to May 2025.
SOURCE Prolacta Bioscience
21%
more press release views with
Request a Demo
临床结果临床研究
2025-10-14
Company Introduced Fortifiers Free From Cow Milk in 2006 to Improve Long-Term Outcomes
DUARTE, Calif., Oct. 14, 2025 /PRNewswire/ -- Prolacta Bioscience®, the world's leading hospital provider of 100% human milk-based nutritional products for critically ill and premature infants, approaches two decades of providing the only alternative to cow milk-based fortifiers in the U.S. for the most fragile preemies born weighing < 1,250 grams (2.75 pounds).
Multiple studies conducted over the past 15 years show that cow milk-based fortifiers increase the risk of the life-threatening intestinal disease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NEC) in extremely premature infants. These studies compared infants fed cow milk-based fortifiers to those fed 100% human milk-based fortifiers as part of an exclusive human milk diet (EHMD).1-3 For each 10% increase in cow milk-based protein in an infant's diet, there is a 11.8% increase in the risk of NEC, 20.6% increase in the risk of surgical NEC, and 17.9% increase in the risk of sepsis.4
Additionally, a recent independent study evalu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n EHMD and motor function impairment at 3 years of corrected age. Read more about the published findings here.5
Since introducing Prolact+ H2MF®, the world's first and only 100% human milk-based fortifier, in 2006, Prolacta has contributed to changing the standard of care for critically ill and premature infants in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s (NICU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company's nutritional products are made from 100% breast milk and are free from cow milk and other added fats and sugars, including corn syrup solids. The products have been studied extensively throughout the company's nearly 20-year history, showing reduced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d outcomes for vulnerable infants.1-3,6-9
"Our company's history and commitment to advancing neonatal nutrition is supported by extensive clinical data and two decades of real-world use of our products," said Scott Elster, CEO of Prolacta. "Our legacy and continued mission reflect the vital role of human milk nutrition in helping extremely premature infants not just survive their earliest days but also grow and develop so they can thrive throughout their lives."
Prolacta's advancements in neonatal nutrition have been marked by several key milestones:
2006: Prolacta introduces Prolact+ H2MF® – the first and only 100% human milk-based fortifier as an alternative to cow milk-based products for extremely premature infants
2007: Prolacta introduces Prolact HM® – the industry's first protein- and calorie-standardized pasteurized donor human milk for use alone or with Prolact+ H2MF human milk fortifier when mother's own milk is unavailable
2007: Prolacta enters the European market with first international sale
2010: First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published demonstrating the benefits of Prolacta's human milk-based fortifiers3
2013: Prolacta introduces Prolact RTF™ – the first and only 100% human milk-based "ready to feed" (RTF) premature infant formula indicated for when a mother's own milk is unavailable and fortification is needed
2014: Prolacta introduces Prolact CR® – the world's first and only 100% human milk caloric fortifier made from pasteurized human milk cream to help preemies increase weight and length
2017: Prolacta develops world's first test to directly detect bacteria and viruses in donor breast milk, setting the highest safety standard in the human milk industry
2017: Prolacta begins directly testing donor milk for traces of drugs, including opiates, nicotine, and marijuana, as well as adulterants
2020: Prolacta introduces products in the Middle East
2023: Australia approves use of Prolacta's nutritional products
2024: More than 50% of Level III and IV NICUs in the U.S. used Prolacta's 100% human milk-based fortifiers and formulas for the tiniest preemies weighing less than 1,250 g (2.75 lbs.)
2025: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pproves Prolacta's Surgifort® fortifier – the first and only 100% human milk-based fortifier designed for term infants recovering from corrective surgery for gastroschisis
A growing body of clinical evidence demonstrates the short- and long-term health benefits of human milk-based nutrition for critically ill and premature infants. Compared to cow milk-based products, an EHMD with Prolacta's 100% human milk-based nutritional fortifiers has been clinically proven in numerous studies to:
Lower mortality and morbidity4,10
Reduce risk of NEC1-3
Reduce incidence of feeding intolerance1
Achieve adequate growth8,11,12
Reduce incidence of 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 (BPD)1,2,8,9
Reduce incidence of retinopathy of prematurity (ROP)1,2,9,13
Reduce late-onset sepsis incidence2,13 and evaluations9
Improve long-term outcomes such as neurodevelopment6,7
Shorten stays in the NICU1
Reduce hospital costs1,14
About Prolacta Bioscience
Prolacta Bioscience® is a global life sciences company dedicated to Advancing the Science of Human Milk® to improve health outcomes for critically ill and premature infants. More than 125,000 extremely premature infants worldwide15 have benefited from Prolacta's human milk-based products, which have been evaluated in more than 30 peer-reviewed clinical studies. In a significant advancement, Prolacta has developed Surgifort®, the first and only FDA-approved human milk-based fortifier designed for term infants recovering from corrective surgery for gastroschisis. Operating the world's first pharmaceutical-grade human milk processing facilities, Prolacta maintains the industry's strictest quality and safety standards, with over 20 validated tests for screening and testing human milk. Prolacta's manufacturing process uses vat pasteurization to ensure pathogen inactivation while protecting nutritional composition and bioactivity. Learn more online, or on X, Instagram, Facebook, TikTok, and LinkedIn.
Media Contact:
Loren Kosmont
[email protected]
310-721-9444
References
Assad M, Elliott MJ, Abraham JH. Decreased cost and improved feeding tolerance in VLBW infants fed an exclusive human milk diet. J Perinatol. 2016;36(3):216-220. doi:10.1038/jp.2015.168
Hair AB, Peluso AM, Hawthorne KM, et al. Beyond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prevention: improving outcomes with an exclusive human milk-based diet [published correction appears in Breastfeed Med. 2017 Dec;12 (10):663]. Breastfeed Med. 2016;11(2):70-74. doi:10.1089/bfm.2015.0134
Sullivan S, Schanler RJ, Kim JH, et al. An exclusively human milk-based diet is associated with a lower rate of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than a diet of human milk and bovine milk-based products. J Pediatr. 2010;156(4):562-567.e1. doi:10.1016/j.jpeds.2009.10.040
Abrams SA, Schanler RJ, Lee ML, Rechtman DJ. Greater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in extremely preterm infants fed a diet containing cow milk protein products. Breastfeed Med. 2014;9(6):281-285. doi:10.1089/bfm.2014.0024
Chou FS, Zhang J, Villosis MFB, et al. Exclusive human milk diet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 risk of motor function impairment at three years of corrected age. J Perinatol. 2025;45:1274–1280. doi:10.1038/s41372-025-02296-z
Hair AB, Patel AL, Kiechl-Kohlendorfer U, et al. Neurodevelopmental outcomes of extremely preterm infants fed an exclusive human milk-based diet versus a mixed human milk + bovine milk-based diet: a multi-center study. J Perinatol. 2022;42(11):1485-1488. doi: 10.1038/s41372-022-01513-3
Bergner EM, Shypailo R, Visuthranukul C, et al. Growth, body composition, and neurodevelopmental outcomes at 2 years among preterm infants fed an exclusive human milk diet in the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a pilot study. Breastfeed Med. 2020. 15(5):304-311. doi:10.1089/bfm.2019.0210
Huston R, Lee M, Rider E, et al. Early fortification of enteral feedings for infants <1250 grams birth weight receiving a human milk diet including human milk-based fortifier. J Neonatal Perinatal Med. 2020;13(2):215-221. doi:10.3233/NPM-190300
Delaney Manthe E, Perks PH, Swanson JR. Team-based implementation of an exclusive human milk diet. Adv Neonatal Care. 2019;19(6):460-467. doi:10.1097/ANC.0000000000000676
Lucas A, Boscardin J, Abrams SA. Preterm infants fed cow's milk-derived fortifier had adverse outcomes despite a base diet of only mother's own milk. Breastfeed Med. 2020;15(5):297-303. doi:10.1089/bfm.2019.0133
Huston RK, Markell AM, McCulley EA, Gardiner SK, Sweeney SL. Improving growth for infants ≤1250 grams receiving an exclusive human milk diet. Nutr Clin Pract. 2018;33(5):671-678. doi:10.1002/ncp.10054
Hair AB, Hawthorne KM, Chetta KE, Abrams SA. Human milk feeding supports adequate growth in infants ≤1250 grams birth weight. BMC Res Notes. 2013;6:459. doi:10.1186/1756-0500-6-459
O'Connor DL, Kiss A, Tomlinson C, et al. Nutrient enrichment of human milk with human and bovine milk-based fortifiers for infants born weighing <1250 g: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published correction appears in Am J Clin Nutr. 2019 Aug 1;110(2):529] [published correction appears in Am J Clin Nutr. 2020 May 1;111(5):1112]. Am J Clin Nutr. 2018;108(1):108-116. doi:10.1093/ajcn/nqy067
Ganapathy V, Hay JW, Kim JH. Costs of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and cost-effectiveness of exclusively human milk-based products in feeding extremely premature infants. Breastfeed Med. 2012;7(1):29-37. doi:10.1089/bfm.2011.0002
Data on file; estimated number of premature infants fed Prolacta's products from January 2007 to May 2025.
SOURCE Prolacta Bioscience
WANT YOUR COMPANY'S NEWS FEATURED ON PRNEWSWIRE.COM?
440k+
Newsrooms &
Influencers
9k+
Digital Media
Outlets
270k+
Journalists
Opted In
GET STARTED
上市批准临床结果
100 项与 Prolacta Bioscience, Inc. 相关的药物交易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100 项与 Prolacta Bioscience, Inc. 相关的转化医学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组织架构
使用我们的机构树数据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管线布局
2026年02月07日管线快照
管线布局中药物为当前组织机构及其子机构作为药物机构进行统计,早期临床1期并入临床1期,临床1/2期并入临床2期,临床2/3期并入临床3期
其他
3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药物交易
使用我们的药物交易数据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转化医学
使用我们的转化医学数据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营收
使用 Synapse 探索超过 36 万个组织的财务状况。
登录
或

科研基金(NIH)
访问超过 200 万项资助和基金信息,以提升您的研究之旅。
登录
或

投资
深入了解从初创企业到成熟企业的最新公司投资动态。
登录
或

融资
发掘融资趋势以验证和推进您的投资机会。
登录
或

生物医药百科问答
全新生物医药AI Agent 覆盖科研全链路,让突破性发现快人一步
立即开始免费试用!
智慧芽新药情报库是智慧芽专为生命科学人士构建的基于AI的创新药情报平台,助您全方位提升您的研发与决策效率。
立即开始数据试用!
智慧芽新药库数据也通过智慧芽数据服务平台,以API或者数据包形式对外开放,助您更加充分利用智慧芽新药情报信息。
生物序列数据库
生物药研发创新
免费使用
化学结构数据库
小分子化药研发创新
免费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