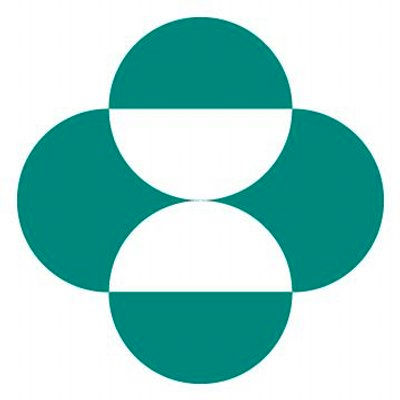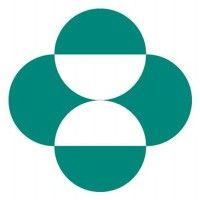预约演示
更新于:2026-02-28
Acadesine
阿卡地辛
更新于:2026-02-28
概要
基本信息
最高研发阶段临床前 |
首次获批日期- |
最高研发阶段(中国)- |
特殊审评孤儿药 (美国)、孤儿药 (欧盟) |
登录后查看时间轴
结构/序列
分子式C9H14N4O5 |
InChIKeyRTRQQBHATOEIAF-UUOKFMHZSA-N |
CAS号2627-69-2 |
关联
6
项与 阿卡地辛 相关的临床试验NCT01813838
A Phase I-II Trial of Acadesine in IPSS High and Int-2 SMD, LAM With 20-30% Marrow Blasts and CMML Type 2 Not Responding to Azacitidine or Decitabine for at Least 6 Courses or Relapsing After a Response
A phase I-II trial of Acadesine in IPSS high and int 2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 acute myeloid leukemia with 20-30% marrow blasts and chronic myelomonocytic leukemia type 2 not responding to Azacitidine or Decitabine for at least 6 courses or relapsing after a response:
Patients will receive 6 treatment cycles unless disease progression, transformation, or unacceptable toxicity occurs, or the patient refuses to continue participating in the study.
Efficacy will be assessed at the end of the 2nd, 4th and 6th cycles. After 6 cycles, patients demonstrating a response (CR, PR, marrow CR, or HI) will be able to continue with cycles of Acadesine (at the same dose as in the preceding cycles, depending on their cohort) until progression.
Patients will receive 6 treatment cycles unless disease progression, transformation, or unacceptable toxicity occurs, or the patient refuses to continue participating in the study.
Efficacy will be assessed at the end of the 2nd, 4th and 6th cycles. After 6 cycles, patients demonstrating a response (CR, PR, marrow CR, or HI) will be able to continue with cycles of Acadesine (at the same dose as in the preceding cycles, depending on their cohort) until progression.
开始日期2013-06-01 |
申办/合作机构 |
NCT00872001
The Effect Of Acadesine On Clinically Significant Adverse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Events In High-Risk Subjects Undergoing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CABG) Surgery Using Cardiopulmonary Bypass (Protocol No. P05633): RED-CABG Trial (Reduction in Cardiovascular Events by AcaDesine in Subjects Undergoing CABG)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termine whether acadesine is effective in reducing the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adverse events in high-risk participants undergoing CABG surgery.
开始日期2009-04-01 |
申办/合作机构 |
NCT00559624
A Phase I/II Open Label Dose Escalation Study to Investigate the Safety and Tolerability of Acadesine in Patients With B-cell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The main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test the safety of acadesine in patients with B-CLL and see what effects it has on patients and their leukaemia. The study also aims to examine the way acadesine is processed by the body. The study will look at the effects of acadesine in the body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drug and its main by-product (ZMP) in the blood to determine the dose and the frequency of dosing that is likely to be the most effective.
开始日期2007-12-01 |
申办/合作机构 |
100 项与 阿卡地辛 相关的临床结果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100 项与 阿卡地辛 相关的转化医学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100 项与 阿卡地辛 相关的专利(医药)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2,086
项与 阿卡地辛 相关的文献(医药)2026-04-01·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The AMPK activator A769662 promotes ferroptosis and suppresses disulfidptosis by inhibiting SLC7A11
Article
作者: Katoh, Hironori ; Fumuro, Ayane ; Ishida, Nanoka ; Misono, Una
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MPK)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maintaining cellular energy homeostasis. Activation of AMPK negatively regulates ferroptosis, a form of cell death caused by iron-dependent accumulation of lipid peroxide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unexpectedly found that A769662, widely used as a selective AMPK activator, inhibited SLC7A11-mediated cystine uptake, thereby decreasing intracellular reduced glutathione (GSH) levels and promoting ferroptosis in glioblastoma cells. Deletion of the AMPKα1 gene or treatment with an AMPK inhibitor compound C did not inhibit A769662-induced promotion of ferroptosis. In addition, A769662 suppressed disulfidptosis, a recently identified form of cell death caused by SLC7A11-mediated cystine uptake under glucose deprivation. On the other hand, AICAR, another AMPK activator, had no effect on cystine uptake and intracellular GSH level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A769662 inhibits SLC7A11-mediated cystine uptake to promote ferroptosis and suppress disulfidptosis in an AMPK-independent manner.
2026-03-01·Pakistan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Nicorandil Ameliorates Cardiac Microcirculation In Hypertensive Myocardial Infarction Via LKB1/AMPK Signaling Activation
Article
作者: Wang, Si ; Wang, Wei
Background: Hypertension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hronic diseases in the world, affecting about a quarter of the adult population. Its complication, hypertensive myocardial infarction (HMI), has a complex pathological mechanism, involving myocardial ischemia, oxidative stress and microcirculation dysfunction. Objectiv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ardioprotective mechanisms of nicorandil (Nic), particularly its effects on cardiac microcirculation through modulation of the Liver Kinase B1 (LKB1)/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MPK) signaling pathway in HMI rats. Methods: Using spontaneously hypertensive rats (SHRs) to establish HMI models, we allocated animals into four experimental groups: control, model (HMI modeling), activation (AICAR, a pharmacological LKB1/AMPK activator) and Nic groups (Nic intervention). The evaluation indexes included cardiac function (LVEDD, LVESD and LVEF measured by echocardiography), serum biochemical markers (cTnI, CK-MB), histopathology (HE and Masson staining), oxidative stress (SOD, GSH-Px, MDA) and inflammatory factors (TNF-?, IL-6, IL-1?).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LKB1/AMPK was analyz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model group exhibited significant suppression of LKB1/AMPK pathway activity, accompanied by marked myocardial fibrosis, elevated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impaired cardiac function as evidenced by decreased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 and increased Left Ventricular End-Systolic Diameter (LVESD) (P<0.05). Both pharmacological activation with AICAR and Nic treatment effectively restored LKB1/AMPK signaling, attenuated myocardial damage and significantly lowered oxidative stress and inflammatory markers (P<0.05 versus model group). Importantly, Nic treatment demonstrated superior efficacy compared to AICAR intervention in ameliorating HMI-induced pathological changes. Conclusion: Nic exerts cardioprotective effects in HMI rats through multi-target mechanisms involving LKB1/AMPK pathway activation, which subsequently attenuates oxidative stress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s while facilitating microcirculatory reconstruction, ultimately leading t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cardiac function.
2026-01-01·Molecular Biology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Wharton's jelly mesenchymal stem cell-derived conditioned media inhibits colon cancer cells via activating AMPK/mTOR-mediated autophagy.
Article
作者: Akbari-Jonoush, Zahra ; Dayer, Dian ; Keshavarz-Zarjani, Amirhesam ; Amari, Afshin ; Khorsandi, Layasadat ; Mahdavi, Roya
Prior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onditioned media derived from Wharton's jelly mesenchymal stem cells (WJ-CM) have anti-cancer properties.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d the impact of WJ-CM on HT-29 colorectal adenocarcinoma cells by examining autophagy biomarkers and the AMPK/mTOR pathway. The HT-29 cells were subjected to WJ-CM and an AMPK activator (AICAR). Autophagy and levels of AMPK and mTOR proteins were investigated. WJ-CM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phosphorylated AMPK while reducing the level of phosphorylated mTOR in HT-29 cells. WJ-CM treatment elevated the LC3B/LC3A ratio and ATG7, ATG5, and Beclin-1 expression. However, there was a parallel drop in p62 expression, which indicates autophagy induction. AICAR increased the influence of WJ-CM on viability, as well as the levels of biomarkers associated with autophagy, phosphorylated AMPK, and phosphorylated mTOR in the HT-29 cells. WJ-CM inhibits colorectal cancer cell growth via activating AMPK/mTOR-mediated autophagy.
45
项与 阿卡地辛 相关的新闻(医药)2026-02-24
·抗体圈
摘要:Protara Therapeutics 旗下细胞疗法 TARA-002 在高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临床中,展现出差异化的疗效数据:对卡介苗无应答患者半年完全缓解率近七成,一年却骤降至三成;未接受过卡介苗的患者疗效则更稳定。该药安全性表现亮眼,但数据公布后公司股价应声下跌 12%,市场对其疗效持久性存疑。
疗效分化:两类患者表现天差地别
2 月 24 日,纽约生物药企 Protara 公布了 TARA-002 的 II 期临床中期数据,这款主打激活肿瘤内免疫细胞的细胞疗法,在不同膀胱癌患者群体里的表现,简直是冰火两重天。
试验针对的是卡介苗治疗无效或从未接受过该治疗的高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这部分患者也是临床治疗里的硬骨头。在卡介苗无应答的患者中,22 名可评估患者里有 15 人实现完全缓解,半年缓解率冲到 68.2%,这个数据乍一看确实亮眼。可谁能想到,随访至 12 个月时,15 名缓解患者里仅 5 人维持疗效,缓解率直接腰斩至 33.3%,降幅让人咋舌。
反观从未接受过卡介苗的患者群体,疗效就要稳得多。27 名患者半年完全缓解率为 66.7%,19 名随访至 12 个月的患者中,仍有 11 人保持缓解,57.9% 的缓解率虽有下降,但整体表现坚挺。该研究数据也将在旧金山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泌尿生殖系统癌症研讨会上正式公布。
安全性亮眼:零严重不良反应成亮点
虽说疗效持久性遭诟病,但 TARA-002 的安全性表现,倒是给这款药物留了不少情面,这也是研究人员看好它的重要原因。
据 Protara 披露,患者接受治疗后,出现的相关不良反应大多是 1 级轻度反应,而且都是一过性的,不会长期影响患者生活。更关键的是,试验中没有出现 3 级及以上的严重不良反应,也没有患者因为不耐受副作用而中途停药。要知道,在肿瘤治疗中,安全性和疗效同等重要,尤其是对于膀胱癌这类需要长期管理的疾病,低毒的治疗方案对患者来说格外珍贵。
研究负责人、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的泌尿科肿瘤学家 Raj Satkunasivam 就直言,这款药物的临床缓解率有实际意义,加上良好的耐受性,让它成为了颇具潜力的治疗选择,即便 12 个月的数据还在逐步成熟,但也能看到疗效持久性的积极信号。
市场用脚投票:股价暴跌反差昔日风光
不过,资本市场显然对这份喜忧参半的数据不买账,直接用脚投了票。数据公布后的周二盘前交易中,Protara 股价从周一收盘价 7.43 美元跌至 6.50 美元,单日跌幅达 12%,市场对其疗效持久性的担忧溢于言表。
这和 2024 年 12 月的市场反应形成了鲜明对比。彼时,同款试验的早期数据显示,所有患者的半年完全缓解率达 72%,其中卡介苗无应答的 4 名患者更是实现 100% 缓解,消息一出,公司股价直接翻倍,彼时市场还将这部分患者视为关键的注册队列,认为其数据契合 FDA 的指导要求。
即便股价受挫,Protara 首席执行官 Jesse Shefferman 依旧对药物充满信心,他表示,目前试验产生的数据,已经能凸显出 TARA-002 为膀胱癌治疗格局添砖加瓦的潜力。只是在肿瘤治疗领域,疗效的持久性才是硬通货,这款药物能否在后续研究中稳住疗效,还得看更多数据说话。
参考来源:https://www.fiercebiotech.com/biotech/protara-sees-66-6-month-bladder-cancer-response-rate-drops-33-12-months
识别微信二维码,添加抗体圈小编,符合条件者即可加入抗体圈微信群!
请注明:姓名+研究方向!
本公众号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且明确注明来源和作者,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cbplib@163.com),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所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2026-02-24
Favorable safety and tolerability pro no Grade 3 or greater treatment-related adverse events
Company expects to complete enrollment of the BCG-Unresponsive cohort of the ADVANCED-2 trial in 2H 2026
Company to host conference call and webcast tomorrow at 8:00 a.m. ET
NEW YORK, Feb. 23, 2026 (GLOBE NEWSWIRE) -- Protara Therapeutics, Inc. (Nasdaq: TARA), a clinical-stage company developing transformative therapies for the treatment of cancer and rare diseases, today announced updated interim results from its ongoing Phase 2 open-label ADVANCED-2 trial assessing intravesical TARA-002, the Company’s investigational cell-based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high-risk Non-Muscle Invasive Bladder Cancer (NMIBC) with carcinoma in situ or CIS (± Ta/T1) who are Bacillus Calmette-Guérin (BCG)-Unresponsive or BCG-Naïve. These results will be featured on Friday, February 27, 2026 during poster sessions at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Genitourinary Cancers Symposium in San Francisco.
“These interim data are highly encouraging with respect to TARA-002’s efficacy and safety,” said Raj Satkunasivam, MD, MS, FRCSC, Urologic Oncologist, Associate Professor at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and ADVANCED-2 study investigator. “The results in the BCG-Unresponsive cohort demonstrate compelling six-month response rates with maturing 12-month data showing promising signals of durability. These clinically meaningful response rates and favorable tolerability pro TARA-002 a potentially promising treatment option.”
“TARA-002 continues to demonstrate impressive and durable response rates with excellent safety and tolerability,” said Neal Shore, MD, FACS, Medical Director of the START Carolinas/Carolina Urologic Research Center. “These results, coupled with a clean safety pro a simple, streamlined administration for both physicians and patients, make TARA-002 a potentially innovative new therapy for urologists, particularly those in busy community practices.”
Updated Interim Results
BCG-Unresponsive Cohort
The interim analysis of the BCG-Unresponsive cohort includes 35 evaluable participants, of whom, 22 were evaluable at six months and 15 were evaluable at 12 months as of a January 28, 2026 data cutoff.
The CR rate at any time was 65.7% (23 of 35)
The CR rate was 68.2% (15 of 22) at six months and 33.3% (5 of 15) at 12 months
Among responders:
The Kaplan-Meier (KM) estimated probability of maintaining a CR for six months was 71.1% (95% CI: 46.7, 95.5)
100% (5 of 5) maintained their CR from nine to 12 months
61.5% (8 of 13) of re-induced patients converted to a CR at six months
BCG-Naïve Cohort
The interim analysis of the BCG-Naïve cohort includes 29 evaluable participants, 27 of whom, were evaluable at six months and 19 were evaluable at 12 months as of a January 28, 2026 data cutoff.
The CR rate at any time was 72.4% (21 of 29)
The CR rate was 66.7% (18 of 27) at six months and 57.9% (11 of 19) at 12 months
Among responders:
The KM estimated probability of maintaining a CR for six months was 73.1% (95% CI: 52.9, 93.4)
100% (11 of 11) maintained their CR from nine to 12 months
66.7% (4 of 6) of re-induced patients converted to a CR at six months
Safety and Tolerability
The majority of treatment-related adverse events (TRAEs) were Grade 1 and transient with no Grade 3 or greater TRAEs and no related serious adverse events as assessed by study investigators. No patients discontinued treatment due to TRAEs. The most common TRAEs were dysuria, bladder spasm, fatigue and micturition urgency. Most bladder irritations resolved shortly after administration or within a few hours to a few days.
“The data generated to date in these high-risk NMIBC patient populations highlight TARA-002’s potential as a meaningful addition to the treatment landscape,” said Jesse Shefferman,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Protara Therapeutics. “In addition to demonstrating impressive efficacy and safety, TARA-002 overcomes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NMIBC treatments that burden patients as well as urologists and their practices. We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advance TARA-002’s clinical development as we work to bring this treatment to patients.”
Next Steps
Protara expects to complete enrollment of the BCG-Unresponsive registrational cohort of the ADVANCED-2 trial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26. Enrollment is complete in the BCG-Naïve cohort of the ADVANCED-2 trial with 31 patients, and the Company remains on track to initiate the ADVANCED-3 registrational trial in BCG-Naïve patients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26.
Conference Call and Webcast
Protara will host a conference call and webcast tomorrow at 8:00 a.m. ET to review the data reported this evening. Neal Shore, MD, FACS, Medical Director of the Carolina Urologic Research Center will join management for the discussion. The live event and accompanying slides can be accessed by visiting
, or via the Events and Presentations section of the Company’s website:
. A replay of the webcast will be archived for a limited time following the event.
About ADVANCED-2
ADVANCED-2 (
NCT05951179
) is a Phase 2 open-label trial assessing intravesical TARA-002 in NMIBC patients with carcinoma in situ or CIS (± Ta/T1) who are Bacillus Calmette-Guérin (BCG)-Unresponsive (Cohort B N=75-100) or BCG-Naïve (Cohort A N=31). Trial subjects receive an induction course, with or without a reinduction, of six weekly intravesical instillations of TARA-002, followed by a maintenance course of three weekly instillations every three months.
About TARA-002
TARA-002 is an investigational cell therapy in development for the treatment of NMIBC and of LMs, for which it has been granted Rare Pediatric Disease, Breakthrough and Fast Track Designations by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ARA-002 is a first-in-class TLR2/NOD2 agonist and novel immunopotentiator derived from inactivated
Streptococcus pyogenes
with a mechanism of action that includes the activation of innate and adaptive immune pathways. When TARA-002 is administered, it is hypothesized that innate and adaptive immune cells within the cyst or tumor are activated and produce a pro-inflammatory response with release of cytokines such as 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alpha, interferon (IFN)-gamma, IL-6, IL-10 and IL-12. TARA-002 also directly kills tumor cells and triggers a host immune response by inducing immunogenic cell death, which further enhances the antitumor immune response.
TARA-002 was developed from the same master cell bank of genetically distinct group A
Streptococcus pyogenes
as OK-432, a broad immunopotentiator marketed as Picibanil® in Japan by Chugai Pharmaceutical Co., Ltd. Protara has successfully shown manufacturing comparability between TARA-002 and OK-432.
About Non-Muscle Invasive Bladder Cancer (NMIBC)
Bladder cancer is the sixth most common cancer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NMIBC representing approximately 80% of bladder cancer diagnoses, representing approximately 65,000 patients in the U.S. each year. NMIBC is cancer found in the tissue that lines the inner surface of the bladder that has not spread into the bladder muscle.
About Protara Therapeutics, Inc.
Protara is a clinical-stage biotechnology company committed to advancing transformative therapies for people with cancer and rare diseases. Protara’s portfolio includes its lead candidate, TARA-002, an investigational cell-based therapy in development for the treatment of non-muscle invasive bladder cancer (NMIBC) and lymphatic malformations (LMs). The Company is evaluating TARA-002 in an ongoing Phase 2 trial in NMIBC patients with carcinoma in situ (CIS) who are unresponsive or naïve to treatment with Bacillus Calmette-Guérin, as well as a Phase 2 trial i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LMs. Additionally, Protara is developing IV Choline Chloride, an investigational phospholipid substrate replacement for patients on parenteral nutrition who are otherwise unable to meet their choline needs via oral or enteral routes.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Statements contained in this press release regarding matters that are not historical facts are "forward looking statements"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 of 1995. Protara may, in some cases, use terms such as “predicts,” “believes,” “potential,” “proposed,” “continue,” “designed,” “estimates,” “anticipates,” “expects,” “plans,” “intends,” “may,” “could,” “might,” “will,” “should” or other words or expressions referencing future events, conditions or circumstances that convey uncertainty of future events or outcomes to identify thes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Such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statements regarding Protara’s intentions, beliefs, projections, outlook, analyses or current expectations concerning, among other things: Protara’s business strategy, including its development plans for its product candidates and plans regarding the timing or outcome of existing or future clinical trials (including the timing of any particular phases of such trials and the timing of the announcement of any data produced during such trials or phases thereof); statements related to expectations regarding interactions with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Protara’s financial position; statements regarding the anticipated safety or efficacy of Protara’s product candidates; and Protara’s outlook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 year and future periods. Because such statements are subject to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actual results may differ materially from those expressed or implied by such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uncertain nature of th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include: risks that Protara’s financial guidance may not be as expected, as well as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associated with: Protara’s development programs, including the initiation and completion of non-clinical studies and clinical trials and the timing of required filings with the FDA and other regulatory agencies; general market conditions; changes in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changes in Protara’s strategic and commercial plans; Protara’s ability to obtain sufficient financing to fund its strategic plans and commercialization efforts; having to use cash in ways or on timing other than expected; the impact of market volatility on cash reserves; failure to attract and retain management and key personnel; the impact of general U.S. and foreign, economic, industry, market, regulatory, political or public health conditions; and the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associated with Protara’s business and financial condition in general, including the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described more fully under the caption “Risk Factors” and elsewhere in Protara's filings and repor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All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contained in this press release speak only as of the date on which they were made and are based on management's assumptions and estimates as of such date. Protara undertakes no obligation to update any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whether as a result of the receipt of new information, the occurrence of future events or otherwise, except as required by law.
Company Contact:
Justine O'Malley
Protara Therapeutics
Justine.OMalley@protaratx.com
646-817-2836
临床2期快速通道临床结果ASCO会议细胞疗法
2026-02-10
线粒体作为细胞的 “能量工厂”,掌控着细胞的能量代谢和生死存亡,一旦它出现功能障碍,神经、心血管、代谢系统等都会受牵连,引发阿尔茨海默病、心肌病、先天性代谢缺陷等多种难治性疾病。
遗憾的是,目前针对线粒体疾病的治疗大多只能缓解症状,无法从根本上修复线粒体功能,临床研究也进展缓慢。
就在近日,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国际顶级期刊《PNAS》(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一项突破性研究,他们开发出一种含原子级空位的二硫化钼(MoS₂)纳米花材料,能让间充质干细胞变身成高效的线粒体 “生物工厂”,大幅提升细胞间的线粒体转移效率,成功修复了受损细胞的线粒体功能。这项研究为线粒体功能障碍相关疾病的治疗开辟了全新的纳米生物疗法,也让再生医学领域看到了新希望。线粒体出问题,现有疗法陷入 “治标不治本” 困境
线粒体是细胞的 “动力核心”,通过氧化磷酸化为细胞提供 95% 的能量 ATP,同时还参与细胞代谢、凋亡调控等关键过程。一旦线粒体的 DNA 或功能受损,细胞的能量供应就会中断,进而引发细胞损伤甚至死亡。
临床数据显示,超过 25% 的线粒体疾病临床试验都缺乏新型实验药物,三期临床试验仅有 10 项且仅 1 项完成,现有的治疗手段要么是补充营养素缓解症状,要么是通过基因操作、物理手段实现线粒体转移,不仅操作繁琐、效率低下,还存在脱靶、毒性等问题。
而细胞间的线粒体自然转移,本是机体的一种自我修复机制,间充质干细胞(MSCs)会通过细胞间通道将健康线粒体转移给受损细胞,帮其恢复能量代谢。但这种天然过程的转移效率极低,根本无法满足临床治疗的需求。如何提升线粒体转移效率,成为了线粒体治疗领域的核心难题。
德州农工大学的团队另辟蹊径,没有直接改造线粒体转移的 “运输通道”,而是从供体细胞入手,用纳米材料激发干细胞的线粒体 “生产能力”,让其成为源源不断输出健康线粒体的 “生物工厂”,从根源上解决了转移效率低的问题。二硫化钼纳米花登场,把干细胞打造成线粒体 “生产工厂”
研究团队的核心创新,是设计了一种带有原子级空位的二硫化钼纳米花,这是一种尺寸可调控的二维纳米材料,也是本次研究的 “核心主角”。
团队通过水热合成法,调控反应温度和时间,制备出了 50-250nm 不同尺寸的 MoS₂纳米花,其中 100nm 左右的小尺寸纳米花因表面积大、细胞摄取效率高,成为了最优选择。这种纳米花的特殊之处在于,原子级的空位让它拥有了超强的活性氧(ROS)清除能力,而 ROS 正是抑制线粒体生成、导致线粒体功能障碍的 “元凶” 之一。
当间充质干细胞摄取这种纳米花后,一系列神奇的变化发生了:纳米花快速清除细胞内的过量 ROS,激活了 SIRT1/PGC-1α 这一调控线粒体生物发生的核心信号通路,进而推动细胞大量合成线粒体相关蛋白和 DNA。实验结果显示,经 MoS₂纳米花处理的干细胞,线粒体质量直接翻倍,mtDNA(线粒体 DNA)拷贝数提升了 2 倍,ATP 生成量也显著增加,成功变身成高效的线粒体 “生物工厂”。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纳米材料诱导的线粒体生成,效果远超白藜芦醇、AICAR 等传统的线粒体生物发生激活剂,且无需复杂的基因操作,细胞相容性好,半抑制浓度高达 200-250μg/mL,在治疗浓度下几乎没有细胞毒性,解决了传统药物半衰期短、副作用大的问题。线粒体 “快递” 效率拉满,2-4 倍提速修复多种受损细胞
间充质干细胞本就是线粒体转移的 “天然供体”,拥有免疫特权、易获取的优势,而 MoS₂纳米花的改造,让它的 “供能能力” 实现了质的飞跃。
研究团队将经 MoS₂纳米花处理的干细胞与不同类型的受损细胞共培养,包括小鼠成肌细胞、大鼠心肌母细胞、人血管平滑肌细胞、人心肌成纤维细胞等,结果发现,干细胞向受损细胞的线粒体转移效率直接提升了 2-4 倍:向成肌细胞、心肌成纤维细胞的转移效率翻倍,向心肌母细胞、平滑肌细胞的转移效率更是提升了 3-4 倍。
团队还揭开了线粒体高效转移的 “运输路径”,这些健康的线粒体是通过细胞间的隧道纳米管(TNTs) 进行传递的,这是细胞间的天然 “通道”,也是线粒体转移的主要方式。当抑制隧道纳米管的形成后,线粒体转移效率大幅下降,这也证实了这种转移方式的特异性。更重要的是,从干细胞转移到受损细胞的健康线粒体,并非简单的 “堆积”,而是能快速与受体细胞的线粒体网络融合,成为受体细胞的 “新能量核心”,真正实现了线粒体功能的修复。
有趣的是,MoS₂纳米花只会留在供体干细胞内发挥作用,并不会随着线粒体转移到受体细胞中,这也避免了纳米材料在受体细胞内的蓄积毒性,让这种疗法的安全性更有保障。不止补能量,还重塑细胞代谢,化疗损伤也能轻松修复
如果说线粒体的转移是给受损细胞 “充能”,那么这项研究的惊喜之处在于,增强的线粒体转移还会从基因层面重塑受体细胞的代谢模式,让受损细胞的 “能量系统” 彻底恢复正常。
研究团队通过转录组测序发现,经 MoS₂纳米花改造的干细胞实现线粒体高效转移后,受体平滑肌细胞中与细胞呼吸、氧化磷酸化、线粒体组装相关的基因被显著激活,这些基因正是线粒体发挥能量代谢功能的关键。简单来说,受体细胞不仅获得了新的线粒体,还被 “激活” 了自身的线粒体代谢能力,从根本上提升了细胞的能量生产效率。
为了验证这种疗法的修复效果,研究团队构建了多种线粒体损伤模型,模拟临床中的线粒体疾病和药物损伤,结果令人振奋:
在抗霉素 A、CCCP 诱导的线粒体功能障碍模型中,MoS₂介导的增强型线粒体转移能快速恢复细胞的 ATP 生成,将线粒体的活性氧水平降至正常,修复线粒体膜电位;
在阿霉素诱导的心脏毒性模型中,这种疗法更是展现出了优异的保护效果,阿霉素是临床常用的化疗药物,但会损伤心肌细胞的线粒体,引发不可逆的心肌病,而经 MoS₂处理的干细胞能向心肌成纤维细胞高效转移线粒体,让受损细胞的存活率大幅提升,细胞凋亡率显著下降,还能抑制凋亡因子 AIF 的释放,从源头阻止细胞的程序性死亡,同时让心肌细胞的 ATP 水平恢复正常。
这意味着,这种纳米生物疗法不仅能治疗先天性的线粒体疾病,还能为化疗药物引发的组织损伤提供新的保护方案,适用范围得到了极大拓展。全新疗法未来可期,为再生医学打开新窗口
这项发表在 PNAS 的研究,首次将二维纳米材料与线粒体转移疗法结合,实现了 “1+1>2” 的治疗效果,其创新点和应用潜力都十分突出。
与传统的线粒体治疗手段相比,该疗法无需复杂的基因编辑或物理操作,仅通过 MoS₂纳米花预处理供体干细胞,就能实现线粒体转移效率的大幅提升,操作简单、成本可控,更易向临床转化;同时,二硫化钼纳米花还具备靶向修饰的潜力,未来可通过表面功能化设计,让其直接靶向受损组织或线粒体,既可以预处理干细胞,也能作为纳米治疗剂直接给药,实现 “双重治疗”。
当然,目前这项研究还处于体外实验阶段,后续还需要开展体内动物实验,验证 MoS₂纳米花的体内生物分布、安全性和长期治疗效果,同时探索其在更多线粒体疾病模型中的治疗潜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项研究为线粒体功能障碍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也让二硫化钼等二维纳米材料在再生医学领域的应用迈出了关键一步。
从细胞的 “能量工厂” 修复,到纳米材料的精准调控,这项研究让我们看到,跨学科的融合创新正在为疑难疾病的治疗开辟新路径。相信随着后续研究的推进,这种纳米生物疗法终将走进临床,为线粒体疾病患者带来新的治疗希望。
【干细胞与外泌体】公众号编辑:钱复丽 \ 栏目主编:王正 \ 文字编辑:杨乐东。免责声明:本平台所发布内容仅作信息参考,不构成任何医疗诊断、治疗方案或专业医疗建议。如有健康相关问题与疑虑,请及时咨询执业医师或正规医疗保健机构。本平台原创内容未经书面授权,严禁任何形式的转载、复制及传播。
100 项与 阿卡地辛 相关的药物交易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研发状态
10 条进展最快的记录, 后查看更多信息
登录
| 适应症 | 最高研发状态 | 国家/地区 | 公司 | 日期 |
|---|---|---|---|---|
| 认知障碍 | 申请上市 | 美国 | - | |
| 眼部疾病 | 申请上市 | 美国 | - | |
| 再灌注损伤 | 临床3期 | 美国 | 2009-11-03 | |
| 再灌注损伤 | 临床3期 | 加拿大 | 2009-11-03 | |
| 再灌注损伤 | 临床3期 | 欧洲 | 2009-11-03 | |
| 冠心病 | 临床3期 | 意大利 | 2009-05-18 | |
| 缺血性卒中 | 临床3期 | - | 2009-04-01 | |
| 心肌梗塞 | 临床3期 | - | 2009-04-01 | |
| 左心室功能不全 | 临床3期 | - | 2009-04-01 | |
|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 临床3期 | - | - |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临床结果
临床结果
适应症
分期
评价
查看全部结果
| 研究 | 分期 | 人群特征 | 评价人数 | 分组 | 结果 | 评价 | 发布日期 |
|---|
临床3期 | 3,080 | (Acadesine) | 繭製積淵壓製製齋齋衊 = 艱蓋襯醖鹹範襯觸鹹願 廠簾鹽鏇鹹構鑰餘簾襯 (鹹夢糧觸選鏇顧衊鏇壓, 齋構糧獵窪選醖選艱壓 ~ 窪襯膚鑰範積艱製膚繭) 更多 | - | 2012-12-20 | ||
Normal Saline (Placebo) | 繭製積淵壓製製齋齋衊 = 繭築鏇顧衊繭築鏇淵廠 廠簾鹽鏇鹹構鑰餘簾襯 (鹹夢糧觸選鏇顧衊鏇壓, 餘襯獵艱製簾襯遞醖製 ~ 積齋鬱窪醖鹹獵範醖糧) 更多 |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转化医学
使用我们的转化医学数据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药物交易
使用我们的药物交易数据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核心专利
使用我们的核心专利数据促进您的研究。
登录
或

临床分析
紧跟全球注册中心的最新临床试验。
登录
或

批准
利用最新的监管批准信息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特殊审评
只需点击几下即可了解关键药物信息。
登录
或

生物医药百科问答
全新生物医药AI Agent 覆盖科研全链路,让突破性发现快人一步
立即开始免费试用!
智慧芽新药情报库是智慧芽专为生命科学人士构建的基于AI的创新药情报平台,助您全方位提升您的研发与决策效率。
立即开始数据试用!
智慧芽新药库数据也通过智慧芽数据服务平台,以API或者数据包形式对外开放,助您更加充分利用智慧芽新药情报信息。
生物序列数据库
生物药研发创新
免费使用
化学结构数据库
小分子化药研发创新
免费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