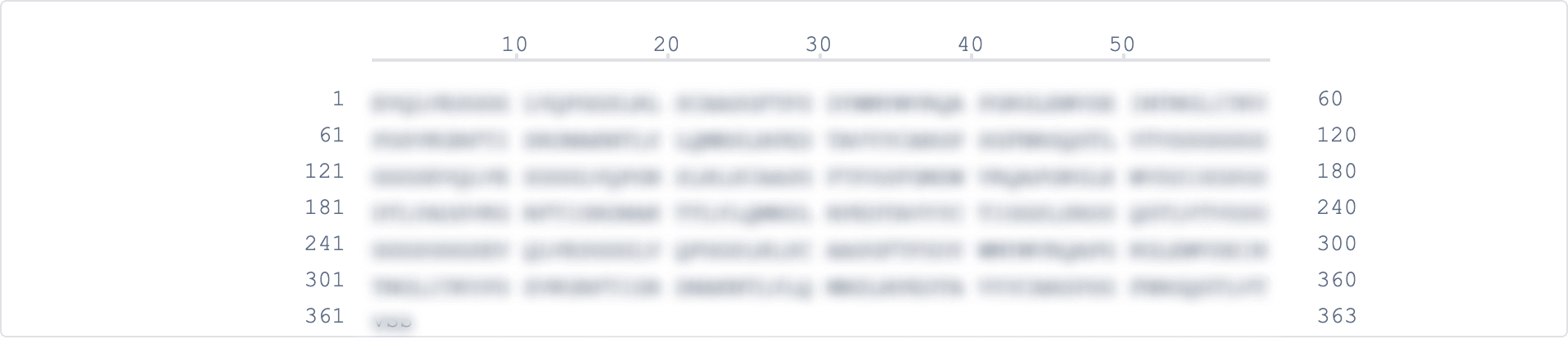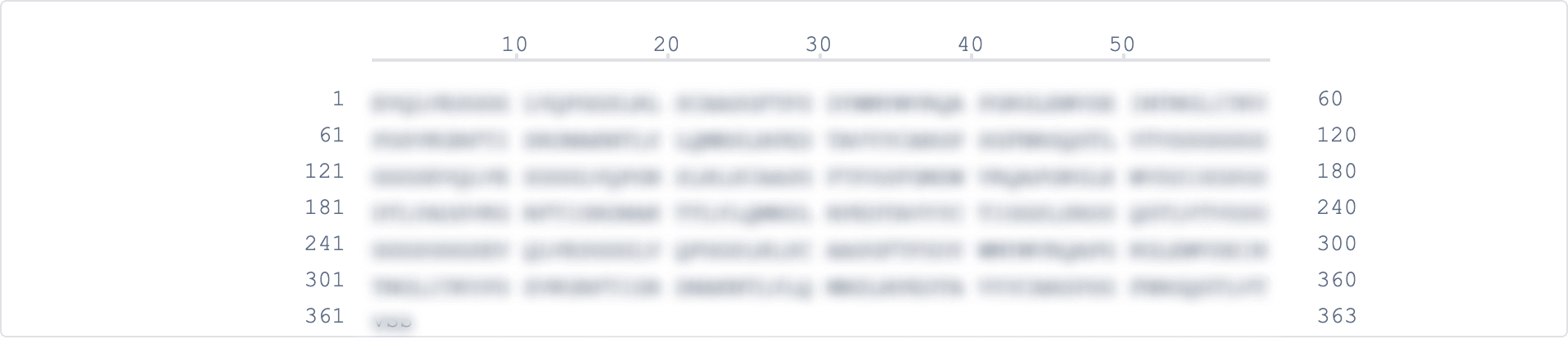5
项与 Rinatabart Sesutecan 相关的临床试验A Randomized, Open-Label, Phase 3 Study of Rinatabart Sesutecan (Rina-S) Plus Standard of Care Versus Standard of Care as Maintenance Treatment After 2L Platinum-Based Doublet Chemotherapy in Participants With Recurrent Platinum-Sensitive Ovarian Cancer (PSOC)
This Phase 3 study will be conducte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ith up to about 528 participant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how well Rina-S works against ovarian cancer in combination with available standard of care therapy that is already approved and used for ovarian cancer.
Participants will receive either Rina-S monotherapy (by itself), Rina-S plus bevacizumab, bevacizumab (standard of care) by itself, or no treatment (only monitoring, also standard of care). No participants will be given placebo. Participants will participate in 1 of 2 arms.
The treatment duration will be different for every participant. If a participant's cancer stays the same or gets better, and there are not any serious problems, participants can keep getting study treatment for as long as the study is open.
Participants will be asked to attend 1 to 3 visits at the study clinic for each cycle (duration of cycle is 3 weeks). During visits, there will be various tests (such as blood draws) and procedures (such as recording of heart activity and imaging) to monitor whether the study treatment is safe and effective. The overall study duration (including screening, treatment, and follow-up) for each participant will be different for every participant.
A Phase 2, Open-label, Multicohort Study of Rinatabart Sesutecan (Rina-S) in Participa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This Phase 2 study will be conducte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ith up to about 240 participant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how well Rina-S works against lung cancer.
The treatment in this study is Rina-S monotherapy (by itself). All participants will receive active drug; no one will be given placebo.
The treatment duration will be different for every participant, but an average of 12 months is expected. Participants will be asked to attend 1 to 5 visits at the study clinic for each cycle (duration of cycle is 3 weeks). If a participant's cancer stays the same or gets better, and there are not any serious problems, participants can keep getting study treatment for as long as the study is open.
Participation in the study will require visits to the study site(s). During site visits, there will be various tests (such as blood draws) and procedures (such as recording of heart activity, imaging/X-rays) to monitor whether the study treatment is safe and effective.
A Phase 3 Randomized, Open-label Study of Rinatabart Sesutecan (Rina-S) Versus Treatment of Investigator's Choice (IC) in Patients With Endometrial Cancer After Platinum-Based Chemotherapy and PD(L)-1 Therap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mpare how well Rina-S (GEN1184) works compared to treatment of physician's choice (paclitaxel or doxorubicin) that are considered standard medical care for the treatment of recurrent or progressive endometrial cancer (EC) following prior therapy. There is an equal (50:50) chance of getting either Rina-S or a chemotherapy agent as treatment in this study.
The study duration will be approximately 3 years. The treatment duration will be different for every participant, but an average of 4 to 6 months is expected.
All participants will receive active drug; no one will be given placebo. Participation in the study will require visits to the study site(s).
100 项与 Rinatabart Sesutecan 相关的临床结果
100 项与 Rinatabart Sesutecan 相关的转化医学
100 项与 Rinatabart Sesutecan 相关的专利(医药)
212
项与 Rinatabart Sesutecan 相关的新闻(医药)2026年2月23日,Genmab在clinicaltrail登记了GEN1106的FIH临床(NCT07416123)研究。
🙅♀️本研究预计招募103人,包括Part1 剂量爬坡,Part2 剂量优化,Part3 剂量拓展。适应症包括尿路上皮癌和其他实体瘤。
㊙️目前Genmab尚未公开产品相关信息。不过根据Genmab对收购普方生物后管线的命名规则,GEN1106很可能为之前公开的PRO1106:靶向SLITRK6的ADC。
🛡️根据其2025年公开的专利(WO2025149661A1 PRO1106.pdf)和AACR2024 abstract,候选抗体可能为新筛选的不同表位抗体hu1H2-03-LALA,Drug-liner 为LD038 (sesutecan),与Rina-S相同。在多个临床前模型中展示了良好的药效。
SLITRK6(SLIT and NTRK-like family member 6)是一种跨膜蛋白,属于SLITRK家族成员,在神经发育和肿瘤生物学中具有重要功能。
SLITRK6在尿路上皮癌、肺癌、乳腺癌、胶质母细胞瘤等上皮肿瘤中高表达,正常组织中表达受限,使其成为潜在治疗靶点。
尿路上皮癌表达
膀胱癌表达
正常组织表达
安斯泰来/Seagen开发了首款靶向SLITRK6的ADC Sirtratumab vedotin(AGS-15E),并完成mUC患者的初步临床I期剂量探索。
相关结果发表于2016 ASCO:
在分析的肿瘤组织中,85%(n=46)为SLITRK6 阳性(其中 56% 的 H 评分≥150)。
🙅♀️截至 2016 年 1 月 21 日,共入组 43 例患者。在 ≥0.5 mg/kg剂量水平下观察到抗肿瘤活性(本次报告 n=37)。中位年龄 64 岁;100% 患者 ECOG 体力状态评分≤1;22 例患者(56%)接受过≥2 线既往治疗。
👍有效性:1 例患者达到确认的CR,10 例患者达到PR,ORR为 30%,其中肝转移患者 3/10 例(30%)获得缓解。中位研究治疗时间为 14 周。
👻安全性:37 例患者(95%)出现不良事件(AE),最常见不良事件为疲乏(56%)。20 例患者(51%)出现 3/4 级不良事件,其中 35% 与试验药物相关。9 例患者(23%)出现眼部异常(1 例 3 级)。4 例患者(11%)出现方案定义的剂量限制性毒性(DLT)。共 2 例死亡,与试验药物无关。
📝ASG-15ME 血清浓度呈多指数下降,药物暴露量与剂量呈正相关。ASG-15ME 半衰期为 2.3 天。中位PFS为 16 周(非预设探索性分析)。
从目前临床结果来看,SLITRK6 ADC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期待GEN1106临床结果。
关注小编不迷路
参考文献:
AGS-15E临床I期结果:
https://ascopubs.org/doi/10.1200/JCO.2016.34.15_suppl.4532
PRO1106 AACR2024 abstract:
https://www.abstractsonline.com/pp8/#!/20272/presentation/6890
WO2025149661A1 PRO1106.pdf
AGS-15E MCTAACR 文章.pdf
关注并星标CPHI制药在线
摘要:在生物医药的黄金时代,肿瘤药物研发曾被视作一条通往财富与荣耀的快车道。无数资本涌入,管线层出不穷,仿佛每一个新靶点的发现都能改写癌症治疗的格局。然而,随着2024年至2025年一系列重磅临床数据的披露以及跨国药企的管线调整,行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祛魅」过程。从Genmab放弃进度领先的PD-L1/4-1BB双抗Acasunlimab,到百济神州、吉利德在TIGIT赛道上的巨资折戟;从强生、Zymeworks在MSLN靶点TCE(T细胞连接器)上的黯然退场,到拜耳忍痛终止斥巨资收购而来的STAT3抑制剂。这些案例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构成了当前肿瘤药物研发生态的真实写照。「肿瘤药物管线终止是行业常态,背后涉及临床数据、战略调整、市场竞争等多重因素。」这句断言如今已成为业界的共识。本期,我们将结合近期发生的数个典型案例,深入剖析药物管线终止背后的科学逻辑与商业考量,探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与复杂的生物学机制面前,药企如何做减法,以及行业正走向何方。
1. 临床数据的硬伤:疗效与安全性无法逾越的鸿沟
药物研发的本质是科学,而临床数据是检验科学假设的唯一标准。在众多管线终止案例中,最直接、最残酷的原因莫过于II期或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药物无法在预期人群中展示出具有临床意义的获益,或者其安全性风险超出了可接受的范围。
1.1 TIGIT靶点的连环溃败:机制验证的全面挫折
TIGIT曾被视为继PD-1之后的下一个免疫检查点「明日之星」。然而,现实却给了行业一记重锤。2025年4月,百济神州宣布终止其TIGIT抗体Ociperlimab(欧司珀利单抗)针对肺癌的III期AdvanTIG-302试验。独立数据监查委员会(IDMC)基于无效性分析建议终止,理由是难以达到总生存期(OS)主要终点。这一决定导致百济神州累计投入的20.9亿元研发资金付诸东流。紧接着在2025年12月,吉利德与Arcus Biosciences联合宣布,其PD-1+TIGIT+化疗一线治疗胃癌的III期临床STAR-221也宣告失败。
这一连串的失败揭示了深层的生物学问题:在胃癌、非小细胞肺癌等实体瘤中,TIGIT介导的免疫抑制可能并非肿瘤逃逸的主导机制。肿瘤微环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免疫抑制网络,仅仅阻断TIGIT这一条通路,难以撬动整个免疫系统的激活。此外,临床前模型与人体实际环境的巨大差异,导致了早期过度乐观的预期未能转化为临床终点上的成功。
图1. STAR-221宣布终止
1.2 强生MSLN TCE的退场:毒性控制与疗效的平衡难题
靶向间皮素(MSLN)的T细胞连接器(TCE)曾是实体瘤免疫治疗的热门方向。然而,2025年9月,强生悄无声息地终止了其MSLN TCE药物JNJ-79032421的开发。几乎同一时间,Zymeworks也宣布终止同类药物ZW171的临床开发。
ZW171的终止源于I期临床中的毒性问题。尽管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得到了控制,但观察到了明显的剂量限制性毒性,且与MSLN相关的「on-target off-tumor」(脱靶)毒性一致。这意味着药物在攻击表达MSLN的肿瘤细胞的同时,也误伤了表达该抗原的正常组织。更为关键的是,在疗效方面,根据Zymeworks公布的平行比较数据,JNJ-79032421虽然对T细胞的亲和力最高,但其肿瘤细胞杀伤活性反而是最弱的。这说明单纯调整亲和力策略并不足以解决TCE在实体瘤中面临的渗透难题和毒性风险。当风险-获益特征不符合预期时,及时止损是药企的必然选择。
图2. ZW171宣布终止
2. 战略调整与资源配置:从「大而全」到「少而精」
药物研发不仅是科学实验,更是商业投资。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药企需要不断评估现有管线的潜力,将资金集中于成功率最高、市场价值最大的项目。战略调整往往是管线终止的幕后推手。
2.1 Genmab的断舍离:聚焦优势平台,淘汰非核心资产
2025年12月,Genmab宣布终止PD-L1×4-1BB双特异性抗体Acasunlimab的开发。这距离该药启动非小细胞肺癌(NSCLC)III期试验仅过去了一年多。作为该赛道的领头羊,Acasunlimab的终止令业界唏嘘。
Genmab给出的理由非常明确:「基于对整体竞争格局变化的考虑」。虽然Acasunlimab解决了4-1BB单抗严重的肝毒性问题,但其疗效数据难言惊艳。在II期临床中,Acasunlimab单药治疗经治NSCLC的客观缓解率(ORR)仅为13%,即使联合K药,ORR也仅为31%,且肝毒性(转氨酶升高)问题依然存在。
图3. Acasunlimab开发终止
在PD-1/PD-L1抑制剂价格下降、竞品层出的背景下,一款疗效没有压倒性优势的双抗很难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因此,Genmab选择将资源集中到更具潜力的后期管线上,包括已获批的CD3/CD20双抗Epkinly、EGFR/LGR5双抗petosemtamab以及ADC药物Rina-S。这种「做减法」的战略,保证了Genmab能将资源集中在其最有把握的领域,体现了跨国药企成熟的投资组合管理能力。
2.2 拜耳的管线大清洗:并购后的理性再评估
2025年11月,德国制药巨头拜耳宣布终止四个癌症候选药物的开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从Vividion Therapeutics获得的STAT3抑制剂VVD-130850(BAY 3630914)。2021年,拜耳以15亿美元的高溢价收购了Vividion,看重其化学蛋白质组学技术平台。
然而,在I期临床试验启动后不久,拜耳便决定终止该项目。据悉,这主要是基于包括安全性、PK/PD(药代动力学/药效学)和活性在内的全部数据做出的战略决定。除了STAT3抑制剂,拜耳还清理了两个DGK抑制剂和一个CCR8抗体。
这一系列动作表明,拜耳正在对其此前通过并购获得的资产进行严格的「去伪存真」。尽管STAT3是一个经典的致癌靶点,但开发口服小分子抑制剂面临极大的成药性挑战。当早期临床数据未能展现出突破性优势时,果断终止项目,转向泌尿生殖系统、胃肠道和肺癌等具有最高潜力的领域,是拜耳在面临业绩压力下做出的理性选择。
3. 市场竞争与格局演变:内卷下的生存法则
在肿瘤药物研发领域,速度往往决定了一切。当同一赛道变得过度拥挤,或者后来者展现出更具竞争力的机制时,早期的跟随者往往会失去市场价值,从而导致管线终止。
3.1 PD-L1/4-1BB赛道的格局重塑
Acasunlimab的终止不仅关乎数据和战略,也反映了市场竞争的白热化。虽然它是全球首个进入III期的PD-L1/4-1BB双抗,但国内药企如维立志博、齐鲁制药等也在快速推进同类项目至II期临床。
随着Genmab的退出,这一赛道的重心正在向中国转移。然而,对于后来者而言,Genmab的失败是一个巨大的警示:如果不能在疗效或安全性上超越现有的PD-1单抗及其联合疗法,双抗仅凭机制创新很难获得市场认可。竞争格局的变化迫使企业必须不断更新其产品特征,否则只能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3.2 治疗格局的迭代
在胃癌、肺癌等领域,标准治疗方案正在不断更新。从化疗到靶向治疗,再到免疫治疗及其联合方案,新药的门槛越来越高。例如,在TIGIT抗体的临床试验中,由于PD-1联合化疗已成为一线标准,TIGIT抗体必须在此基础上显示出显著的OS获益。然而,随着后续治疗手段(如ADC、新型免疫疗法)的丰富,OS终点变得越来越难以达到。这种治疗格局的快速迭代,使得许多处于研发后期的药物在还没上市前就已经「过时」,这也是导致管线终止的重要外部因素。
4. 失败后的突围:行业的新方向探索
管线的终止并不意味着研发的终结,往往是新探索的开始。面对挫折,各大药企正在积极寻求转型的路径,试图突破困境。
4.1 双抗与新分子的迭代
尽管TIGIT单抗屡战屡败,但阿斯利康等企业并未放弃该靶点,而是转向了PD-1/TIGIT双特异性抗体(如Rilvegostomig)的开发。双抗的设计理念在于通过同时阻断两条免疫逃逸通路,产生协同效应,并可能改善药代动力学特性。此外,针对TCE亲和力调整的探索也在继续,希望通过精细的分子设计解决「on-target off-tumor」毒性。
4.2 联合方案的优化与Biomarker的探索
针对胃癌等复杂适应症,研究者开始反思联合方案的合理性。除了与化疗联合,TIGIT抗体与ADC、抗血管生成药物的联合也在探索中。更重要的是,Biomarker(生物标志物)的精准筛选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仅仅依靠PD-L1表达进行分层已显不足,未来需要基于基因突变谱、免疫微环境特征等多维度数据,寻找真正能从免疫治疗中获益的「超级响应者」。
4.3 新靶点的开辟
Arcus Biosciences在STAR-221失败后,迅速将重心转向HIF-2α抑制剂Casdatifan。这一靶点在肾细胞癌中显示出独特机制,且早期临床数据显示了良好的疾病控制率和安全性。这种在新靶点上的快速布局,体现了药企在面对单一靶点失败时的灵活应变能力和对肿瘤生物学机制的深入理解。
5. 结语
综上所述,Genmab放弃Acasunlimab、百济神州终止Ociperlimab、强生清理MSLN TCE、拜耳砍掉STAT3抑制剂……这些名字和案例,共同构成了2025年生物医药行业的悲壮注脚。然而,这并非行业的衰退,而是成熟的标志。
肿瘤药物研发本质上是一个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的过程。管线终止不仅是研发过程中的「过滤器」,更是资源配置的「调节器」。它通过残酷的市场机制,淘汰了科学机制不成立、临床数据不佳、商业竞争力不强的项目,将有限的资金、人才和患者资源导向更有希望的领域。
从狂热追逐热门靶点,到理性评估临床价值;从盲目铺开管线,到聚焦核心优势。总之,失败并非终结,而是迭代的开始。当下的行业正在经历一场从「Me-too」向「First-in-class」或「Best-in-class」的深刻转型。
参考文献:
1. https://secure.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251212586271/en/Arcus-Provides-Update-on-Phase-3-STAR-221-Study-and-Concentrates-Its-RD-Investment-on-Casdatifan-and-Emerging-Inflammation-and-Immunology-Portfolio
2. https://ir.zymeworks.com/news-releases/news-release-details/zymeworks-announces-decision-discontinue-clinical-development
3. https://www.fiercebiotech.com/biotech/biontech-ends-work-genmab-partnered-bispecific-antibody-acasunlimab
作者简介:凯文,从事药物临床评价与合理用药、药事管理相关研究。
END
扫码领取CPHI China2026展会门票
智药研习社近期直播
来源:CPHI制药在线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并不代表制药在线立场。本网站内容仅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如需转载,请务必注明文章来源和作者。
投稿邮箱:Kelly.Xiao@imsinoexpo.com
▼更多制药资讯关注CPHI制药在线▼
点击阅读原文,进入智药研习社~
2026年1月19日,艾迪药业宣布其抗艾滋病2.3类改良型新药——多替拉韦/拉米夫定/替诺福韦单片复方制剂ADC205片,获准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将三种经典抗艾药物整合为每日一次、每次一片的给药方案,旨在简化HIV-1感染者的长期治疗,提升服药依从性,为中国艾滋病防治提供更便捷、更优化的治疗选择。
2026年1月23日,英矽智能宣布其潜在同类最佳口服NLRP3抑制剂ISM8969获美国FDA临床试验批准,将开展针对帕金森病的I期临床研究。
2026年1月23日,勤浩医药宣布其1类新药ERK1/2抑制剂GH55联合SHP2抑制剂GH21的临床试验申请获中国国家药监局批准。该联合疗法旨在通过上下游协同阻断MAPK信号通路,为RAS、RAF等基因突变导致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实体瘤患者提供全新治疗选择,标志着我国在靶向耐药机制和联合用药策略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默沙东的注射用索特西普获CDE拟纳入优先审评
2026年1月22日,南京维立志博宣布其核心产品维利信®(LBL-024)获欧盟委员会授予孤儿药资格认定,用于治疗肺外神经内分泌癌。这是该药物继获中国CDE突破性疗法认定、美国FDA孤儿药与快速通道资格后,又一重要国际监管进展。
2026年1月21日,BioNTech宣布其研发中的mRNA癌症免疫疗法BNT113获得美国FDA快速通道认定,用于治疗表达PD-L1的HPV16阳性头颈鳞状细胞癌患者。 这是全球首款进入关键临床阶段的靶向HPV16的mRNA癌症疫苗,有望为这一缺乏靶向治疗选择的患者群体提供全新的免疫治疗策略。
2026年1月22日,瑞博生物宣布其自主研发的靶向ApoC3的小干扰RNA药物RBD5044,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监局II期临床试验默示许可。 该药物为全球第二款进入临床阶段的靶向ApoC3的siRNA疗法,凭借其“单次给药、长效降脂”的潜力,有望为高甘油三酯血症患者提供更精准、便捷的治疗新选择。
2026年1月22日,拜耳旗下全资子公司BlueRock Therapeutics宣布,其在研细胞疗法OpCT-001获得美国FDA孤儿药认定,用于治疗视网膜色素变性。 该疗法基于诱导多能干细胞技术,旨在通过替换视网膜中丧失的感光细胞,为遗传性视网膜疾病患者提供一种潜在的全新治疗路径,标志着细胞治疗在眼科领域的又一重要进展。
2026年1月22日,亚虹医药宣布其自主研发的高选择性FGFR2/3双靶点抑制剂APL-2401在澳大利亚获批开展Ⅰ期临床试验,此前该药已在中国快速获批并完成首例患者给药。 该药物针对FGFR2/3基因异常的晚期实体瘤患者,有望为尿路上皮癌、胆管癌、子宫内膜癌等多种难治性肿瘤提供新的靶向治疗选择,标志着中国创新药国际化进程再进一步。
2026年1月22日,Corcept Therapeutics宣布其在研新药relacorilant联合白蛋白紫杉醇治疗铂类耐药卵巢癌的关键III期临床研究ROSELLA达到总生存期(OS)主要终点。 研究显示,联合治疗组较单用化疗组死亡风险降低35%,中位OS延长4.1个月。此前该研究已达到无进展生存期(PFS)主要终点,意味着OS与PFS双重获益已获证实,为这一难治性患者群体带来全新的治疗希望。
2026年1月23日,赛诺菲公布其新型OX40配体靶向抗体药物amlitelimab在两项全球III期临床研究——SHORE与COAST 2中的积极结果。
2026年1月26日,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阿斯利康的PD-L1抑制剂英飞凡®(度伐利尤单抗)联合化疗,用于错配修复缺陷(dMMR)的原发晚期或复发性子宫内膜癌的一线治疗。 这是中国首个获批用于该人群的免疫治疗方案,标志着子宫内膜癌治疗正式进入“免疫联合”新时代,为约占患者总数20%-30%的dMMR人群带来了显著的生存希望。
2026年1月26日,在刚刚落幕的第44届摩根大通医疗健康年会上,来自中国的创新企业莱芒生物向全球展示了其极具颠覆性的CAR-T疗法临床成果:仅用常规剂量千分之一的细胞数量,成功让多位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实现完全缓解出院,并在复发难治性白血病/淋巴瘤治疗中达到100%完全缓解率。
外周动脉疾病(也称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一种易被忽视的血管疾病挑战
2025年1月24日,中国呼吸疾病治疗领域迎来一项重要进展:葛兰素史克(GSK)旗下药物全再乐®(氟替美维吸入粉雾剂)获中国国家药监局批准,新增用于成人哮喘患者的维持治疗。
国家药监局关于暂停进口、销售和使用Sun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Limited重酒石酸卡巴拉汀胶囊的公告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多糖结合疫苗核磁共振研究的技术考虑(试行)》的通告(2026年第8号)
2026年1月21日,深圳康源久远宣布其自主研发的PEG化T细胞接合剂JY108获得美国FDA临床试验批准,用于治疗CD19阳性复发性/难治性非霍奇金淋巴瘤。 作为全球首款基于PEG技术的TCE类双特异性抗体,JY108旨在克服传统T细胞接合剂常见的细胞因子风暴与组织渗透性局限,展现出独特的临床开发潜力。
2026年1月22日,拜耳集团及其子公司BlueRock Therapeutics宣布,其在研细胞疗法OpCT-001获得美国FDA孤儿药资格认定,用于治疗视网膜色素变性。该疗法是一种基于诱导多能干细胞的再生医学产品,旨在通过替换患者视网膜中丧失的光感受细胞,恢复视力功能,为这一目前缺乏有效治疗手段的遗传性眼病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维昇药业隆培促生长素在华获批上市
2026年1月26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舒立瑞®(依库珠单抗注射液)适应症扩展至6岁及以上抗AChR抗体阳性的难治性全身型重症肌无力儿童患者。这是目前中国首个且唯一获批用于该疾病儿童患者的靶向治疗,填补了长期存在的临床空白,为患儿及其家庭带来新的治疗希望。
2026年1月23日,Bausch Health Companies Inc.公布其全球III期RED-C临床研究计划的最新结果:评估无定型利福昔明固态分散体在肝硬化患者中用于预防肝性脑病的两项临床试验,尽管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但均未达到主要终点。这一结果表明,肝性脑病的一级预防领域仍存在显著未满足的临床需求,相关药物开发面临挑战。
2026年1月26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附条件批准华辉安健(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立贝韦塔单抗注射液(商品名:华优诺)上市,用于治疗伴有或不伴有代偿期肝硬化的慢性丁型肝炎病毒感染成年患者。这是中国首个获批用于治疗慢性丁型肝炎的药物,标志着这一长期缺乏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领域迎来重要突破。
2026年1月27日,德曲妥珠单抗(T-DXd)用于HER2表达子宫内膜癌辅助治疗的全球III期临床研究DESTINY-Endometrial02在中国完成首例患者给药。 该研究旨在比较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放疗与标准化疗在HER2阳性患者术后的疗效与安全性,标志着这一已在晚期癌症中验证疗效的ADC疗法,正式向早期治疗领域拓展。
2026年1月27日,信达生物宣布其自主研发的抗GPRC5D/BCMA/CD3三特异性抗体IBI3003获得美国FDA快速通道资格认定,拟用于治疗既往接受过多线治疗的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
普方生物的注射用PRO1184获CDE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
诺和诺德的德谷胰岛素利拉鲁肽注射液获CDE拟纳入优先审评
卫材的仑卡奈单抗注射液(皮下注射)获CDE拟纳入优先审评
瑞阳(山东)生物的库莱韦单抗注射液获CDE拟纳入优先审评
2026年1月27日,葛兰素史克宣布其佐剂重组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Arexvy获欧盟委员会批准,适用范围扩展至18岁及以上的所有成年人。此前该疫苗已在欧盟获批用于60岁以上及50-59岁高风险人群。此次批准意味着欧洲所有成年人均可接种该疫苗,为预防RSV引起的下呼吸道疾病提供了更广泛的人群防护策略。
2026年1月27日,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正大天晴宣布,其自主研发的口服乙肝核心蛋白变构调节剂TQA3605在Ⅱ期临床研究中达到主要终点。 结果显示,该药联合现有核苷(酸)类药物治疗低病毒血症慢性乙肝患者24周后,近90%患者实现HBV DNA低于检测下限,为长期面临“病毒低水平复制”困扰的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国家药监局关于暂停进口、销售和使用Supriya Lifescience Ltd.马来酸氯苯那敏原料药的公告(2026年第14号)
2026年1月27日,尧唐生物自主研发的新型CRISPR基因编辑系统Cas12HF蛋白核心专利正式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 该系统通过公司自建超高通量分子进化平台挖掘优化,兼具高编辑活性与极佳特异性,且分子尺寸更小、更适配体内递送,已应用于其临床阶段体内基因编辑药物,标志着我国在下一代基因编辑核心技术领域实现重要自主突破。
盛迪亚生物的注射用瑞康曲妥珠单抗获CDE拟纳入优先审评
2026年1月28日,强生宣布其基于DARZALEX FASPRO®(达雷妥尤单抗/透明质酸酶)的四联疗法D-VRd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用于治疗不适合自体干细胞移植(ASCT)的新诊断多发性骨髓瘤(NDMM)成人患者。这是DARZALEX FASPRO®在全球获批的第12个适应症,也是其在新诊断患者中的第5个适应症,标志着该药物在多发性骨髓瘤治疗中的基石地位进一步巩固。
2026年1月28日,勃林格殷格翰公布其口服TRPC6抑制剂apecotrep(BI 764198)用于治疗原发性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症(FSGS)的II期临床试验结果。 数据显示,20mg剂量组治疗12周后,患者蛋白尿(尿蛋白肌酐比)较安慰剂组显著降低40%。该结果已发表于《柳叶刀》,并为这款潜在“同类首创”的非免疫抑制靶向疗法进入III期临床奠定基础。
2026年1月26日,中国生物制药旗下北京泰德制药宣布,其国产首仿妥洛特罗贴剂(德瑞妥®)0.5mg/贴儿童规格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用人群拓展至最小6个月的婴幼儿。 这是继成人规格获批后,该产品在儿童精细化用药领域的重要进展,为支气管哮喘、喘息性支气管炎等儿童常见呼吸疾病提供了更便捷、依从性更高的透皮给药选择。
2026年1月28日,诺华公司宣布其全球首创小干扰RNA降胆固醇药物乐可为®(英克司兰钠注射液)获中国国家药监局批准,新增单药治疗成人原发性高胆固醇血症或混合型血脂异常适应症。这意味着该药在原有联合治疗方案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适用人群,为患者提供了一种“一年两针”的长效降脂选择,有望显著提升治疗依从性与血脂达标率。
2026年1月28日,微芯生物宣布其自主研发的多靶点小分子抗肿瘤药西奥罗尼在胰腺导管腺癌治疗中展现出突破性潜力。 II期临床数据显示,西奥罗尼联合AG化疗一线治疗患者客观缓解率达50%,中位无进展生存期达9.1个月。同时,临床前研究表明西奥罗尼与泛RAS抑制剂具有协同抗肿瘤效应,为攻克“癌王”胰腺癌提供了新的联合治疗思路。
2026年1月28日,恒瑞医药子公司山东盛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批准,同意其自主研发的1类创新口服小分子GLP-1受体激动剂HRS-7535片,开展用于高血压合并超重或肥胖适应症的Ⅲ期临床研究。
2026年1月27日,先为达生物研发的埃诺格鲁肽注射液单药治疗2型糖尿病的Ⅲ期临床研究(EECOH-1)成果在国际知名期刊《自然·通讯》正式发表。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一百零一批)的通告(2026年第3号)
国家药监局关于适用《M14:使用真实世界证据进行药品安全性评估的非干预性研究:规划、设计、分析和报告的一般原则》(2026年第16号)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用于术后镇痛的长效局部麻醉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的通告(2026年第2号)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化学药品创新药晶型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的通告(2026年第10号)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预防用mRNA疫苗药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的通告(2026年第12号)
2026年1月27日,Arrowhead Pharmaceuticals宣布,其创新双靶点RNA干扰(RNAi)疗法ARO-DIMER-PA的1/2a期临床试验(ARO-DIMER-PA-1001)已正式启动。该疗法是全球首个进入临床阶段的、可同时沉默PCSK9和APOC3两个关键基因的单分子RNAi药物,旨在为混合性高脂血症患者提供全新的治疗选择。
2026年1月28日,复宏汉霖宣布,其创新PD-L1抗体偶联药物(ADC)HLX43联合H药汉斯状(斯鲁利单抗)及重组抗EGFR单抗HLX07,用于晚期实体瘤治疗的临床试验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这一三药联用方案,是继HLX43分别与斯鲁利单抗、HLX07两药联合探索后的进一步升级,有望通过“免疫检查点阻断+ADC细胞毒性+EGFR靶向抑制”三重机制协同增效,为晚期实体瘤患者提供全新的治疗可能性。
新《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2026版全文
宜联生物的注射用YL201获CDE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
康方生物的AK112注射液获CDE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
恒瑞医药的HRS-4642注射液获CDE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
盛迪医药的SHR-1918注射液获CDE拟纳入优先审评
2026年1月29日,AI制药先锋企业英矽智能宣布,提名其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ISM0676为临床前候选化合物(PCC),这是一款靶向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受体(GIPR)的新型拮抗剂,旨在治疗肥胖、2型糖尿病及相关心血管疾病。从项目启动到PCC提名仅耗时14个月,合成测试分子数不足200个,充分展现了AI驱动的药物研发效率。值得注意的是,在临床前模型中,ISM0676与司美格鲁肽联用可实现31.3%的显著减重效果,同时更好地保留肌肉量,为下一代体重管理疗法带来突破性潜力。
2026年1月29日,盟科药业宣布,其自主研发的新型苯并噻唑类抗菌药MRX-5片的新药研究申请(IND)已获美国FDA批准,将在美国开展针对脓肿分枝杆菌复合群感染引起的非空洞性肺病成人患者的IIa期临床研究。这标志着盟科药业在抗耐药菌感染这一全球公共卫生挑战领域,实现了重要的海外研发突破。此前,MRX-5已在澳大利亚完成I期临床,并于2024年获得FDA孤儿药资格认定。
2026年1月29日,环码生物宣布,其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创环形RNA药物HM2002注射液获得美国FDA授予的“快速通道”资格(Fast Track Designation)。这是该药物继在中美两国共获4项临床试验批件后,在国际化开发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HM2002聚焦于缺血性心脏病,特别是慢性冠脉综合征这一临床治疗空白领域,旨在通过促进治疗性血管新生,从根本上改善心肌微循环功能。
2026年1月29日,天泽云泰宣布,其自主研发的基因治疗产品VGN-R09b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孤儿药资格认定(ODD),用于治疗芳香族L-氨基酸脱羧酶缺乏症(AADCD)。这是继2025年11月获FDA罕见儿科疾病资格认定(RPDD)后,VGN-R09b在短期内获得的第二项FDA资格认定,标志着其在全球罕见病治疗开发进程中迈出关键一步。
100 项与 Rinatabart Sesutecan 相关的药物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