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约演示
更新于:2025-05-07
Trop-2 x TLR7 x TLR8
更新于:2025-05-07
关联
2
项与 Trop-2 x TLR7 x TLR8 相关的药物作用机制 TLR7激动剂 [+2] |
在研机构 |
原研机构 |
在研适应症 |
非在研适应症- |
最高研发阶段临床申请批准 |
首次获批国家/地区- |
首次获批日期1800-01-20 |
作用机制 EGFR拮抗剂 [+3] |
非在研适应症- |
最高研发阶段临床申请 |
首次获批国家/地区- |
首次获批日期1800-01-20 |
100 项与 Trop-2 x TLR7 x TLR8 相关的临床结果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100 项与 Trop-2 x TLR7 x TLR8 相关的转化医学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0 项与 Trop-2 x TLR7 x TLR8 相关的专利(医药)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13
项与 Trop-2 x TLR7 x TLR8 相关的新闻(医药)2025-03-29
·医药笔记
▎Armstrong2025年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年会(AACR)即将于4月25-30日在美国芝加哥举行,最近会议摘要已经公开,中国创新密集亮相。以ADC领域为例,绝大部分的报告来自中国药企,创新ADC接近100款,覆盖各种技术路线和靶点上的创新,真正开始引领ADC的创新前沿。双靶点ADC为ADC领域当前最热门的方向之一,百力司康、百奥赛图、博锐生物、橙帆医药、多禧生物、恒瑞医药、基石药业、金赛药业、康宁杰瑞、康源博创、联进生物、启德医药、石药集团、拓济生物、先声药业、信达生物、映恩生物、亲和力生物等多家企业布局。双毒素ADC也开始走到台前,康弘药业、亲和力生物系统布局双毒素ADC,康弘药业的KH815为全球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双毒素ADC新药。两种payload分别为TOP1i和RAN POL2i,同时抑制RNA合成并诱导DNA双链断裂。康宁杰瑞进一步开发了双靶点双毒素ADC,即EGFR/HER3双毒素ADC新药JSKN021。传统ADC的理念是毒素经抗体结合受体介导内吞后释放,DXd-ADC则证明了旁观者效应的重要作用,宜联生物则进一步开发了非内吞ADC,靶向游离靶标VEGF,通过肿瘤微环境特异性酶来释放毒素,进一步打开了ADC药物的应用空间。维立志博开发了首款TCE的ADC,即DLL3/CD3 ADC新药LBL-058,由DLL3/CD3双抗偶联TOP1i而成,T细胞杀伤与payload细胞毒杀伤效应协同。虽然TCE在少数靶点已经开始突破实体瘤,但TCE-ADC的设计无疑为突破实体瘤提供了一种全新强化设计的思路。总结从此次AACR会议来看,中国ADC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差异化设计上,毫无疑问都在真正引领ADC的创新前沿,新靶点ADC、新靶点组合双靶点ADC、双毒素ADC、PDC、TCE-ADC、非内吞ADC等等,以及AACR会议不涉及的自免ADC(映恩生物已经进入临床阶段)等。未来几年,国产ADC的临床突破和出海交易仍然是值得期待的行业焦点所在。Armstrong技术全梳理系列GPRC5D靶点全梳理;CD40靶点全梳理;CD47靶点全梳理;补体靶向药物技术全梳理;补体药物:眼科治疗的重要方向;Claudin 6靶点全梳理;Claudin 18.2靶点全梳理;靶点冷暖,行业自知;中国大分子新药研发格局;被炮轰的“me too”;佐剂百年史;胰岛素百年传奇;CUSBEA:风雨四十载;中国新药研发的焦虑;中国生物医药企业的研发竞争;中国双抗竞争格局;中国ADC竞争格局;中国双抗技术全梳理;中国ADC技术全梳理;Ambrx技术全梳理;Vir Biotech技术全梳理;Immune-Onc技术全梳理;亘喜生物技术全梳理;康哲药业技术全梳理;科济药业技术全梳理;恺佧生物技术全梳理;同宜医药技术全梳理;百奥赛图技术全梳理;腾盛博药技术全梳理;创胜集团技术全梳理;永泰生物技术全梳理;中国抗体技术全梳理;德琪医药技术全梳理;德琪医药技术全梳理2.0;和铂医药技术全梳理;荣昌生物技术全梳理;再鼎医药技术全梳理;药明生物技术全梳理;恒瑞医药技术全梳理;豪森药业技术全梳理;正大天晴技术全梳理;吉凯基因技术全梳理;基石药业技术全梳理;百济神州技术全梳理;百济神州技术全梳理第2版;信达生物技术全梳理;信达生物技术全梳理第2版;中山康方技术全梳理;复宏汉霖技术全梳理;先声药业技术全梳理;君实生物技术全梳理;嘉和生物技术全梳理;志道生物技术全梳理;道尔生物技术全梳理;尚健生物技术全梳理;康宁杰瑞技术全梳理;科望医药技术全梳理;科望医药技术全梳理2.0;岸迈生物技术全梳理;礼进生物技术全梳理;康桥资本技术全梳理;余国良的抗体药布局;荃信生物技术全梳理;安源医药技术全梳理;三生国健技术全梳理;仁会生物技术全梳理;乐普生物技术全梳理;同润生物技术全梳理;宜明昂科技术全梳理;派格生物技术全梳理;迈威生物技术全梳理;Momenta技术全梳理;NGM技术全梳理;普米斯生物技术全梳理;普米斯生物技术全梳理2.0;三叶草生物技术全梳理;贝达药业抗体药全梳理;泽璟制药抗体药全梳理;恒瑞医药抗体药全梳理;齐鲁制药抗体药全梳理;石药集团抗体药全梳理;豪森药业抗体药全梳理;华海药业抗体药全梳理;科伦药业抗体药全梳理;百奥泰技术全梳理;凡恩世技术全梳理。
抗体药物偶联物AACR会议
2024-10-05
摘要:抗体药物偶联物(ADC)通常由单克隆抗体(mAbs)通过化学连接臂共价连接到细胞毒素药物。它结合了高度特异性靶向能力和高效杀伤效果的优势,实现对癌细胞的精准和高效清除,已成为抗癌药物研发的热点之一。自第一个ADC药物Mylotarg®(吉妥珠单抗奥佐加霉素)在2000年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以来,全球迄今已有14种ADC药物获得市场批准。此外,目前有100多个ADC候选药物正在临床阶段进行研究。这种被称为“生物导弹”的新型抗癌药物,正在引领靶向癌症治疗的新时代。在这里,我们对ADC的历史和作用机制进行了回顾,并简要讨论了ADC关键组成部分的分子方面以及这些关键因素如何影响ADCs的活性。此外,我们还回顾了已批准的ADCs和在III期临床试验中其他有前景的候选药物,并讨论了下一代开发当前的挑战和未来的展望,为使用ADCs研发新型癌症治疗方法提供了见解。
1. 引言
癌症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健康威胁,2020年约有1000万人死于癌症。几十年来,基于细胞毒素剂的化疗一直是治疗广泛癌症的主要方法。这些细胞毒素剂包括DNA碱基类似物(5-氟尿嘧啶和8-氮鸟嘌呤)、DNA作用剂(顺铂和放线菌素D)、抗代谢物(氨基蝶呤和甲氨蝶呤)和微管抑制剂(紫杉醇和长春新碱衍生物)等。然而,这些化疗药物大多表现出较低的治疗指数,严重的副作用通常归因于非特异性药物暴露于非靶组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家一直在开发具有更高靶向能力的新型癌症治疗方法。
早在20世纪初,保罗·埃尔利希首次提出了“魔法子弹”的概念,并假设某些化合物可以直接作用于细胞中的某些期望靶标以治疗疾病。理论上,这些化合物应该能有效杀死癌细胞,但对正常细胞无害。一种可行的方法是识别一些在癌细胞上特异性高表达的抗原,以区分癌细胞和健康细胞,如乳腺癌上的HER2(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和B细胞淋巴瘤上的CD20(分化簇20)。这些抗原的特异性表达为通过单克隆抗体(mAbs)精确靶向肿瘤提供了可能性,自1975年杂交瘤技术发展以来,这一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mAbs,如阿瓦斯汀、曲妥珠单抗、利妥昔单抗和小细胞肺癌,已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批准,用于治疗各种实体瘤和血液癌症。
mAbs的出现通过精确靶向肿瘤表面抗原改变了癌症治疗的范式,然而,单独使用mAbs治疗通常是不够的,可能由于与化疗相比对癌细胞的致死性不够满意。因此,提出了一种新概念,即抗体-药物偶联物(ADC),以弥合mAb和细胞毒素药物之间的差距,提高治疗窗口。ADC由肿瘤靶向mAbs通过精心设计的化学连接臂与细胞毒素有效载荷共轭,实现了精确靶向和强大效果的双重能力。此外,由于连接到一个大的亲水性抗体,细胞毒素有效载荷在抗原阴性细胞中的非特异性摄取受到限制,有助于扩大治疗指数。
2000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首次批准了ADC药物Mylotarg®(吉妥珠单抗奥佐加霉素),用于治疗成人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AML),这标志着癌症靶向治疗ADC时代的开始。截至2021年12月,全球已有14种ADC药物获得批准,用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和实体瘤。此外,目前有100多个ADC候选药物处于不同的临床试验阶段。ADC药物从其起步阶段到成熟发展阶段在过去一百年中的里程碑事件如图1所示。随着靶标和适应症的不断扩大,ADC正在引领靶向癌症治疗的新时代,预计未来将取代传统的化疗。在这篇综述文章中,我们讨论了ADC的关键组成部分的分子方面和作用机制,并简要总结了ADC发展的进展。我们还回顾了已批准的ADCs和III期临床试验中的其他有前景的候选药物,并讨论了下一代ADC开发的当前挑战和未来展望。
图1 展示了自1910年Paul Ehrlich提出“魔法子弹”概念以来,过去一个世纪ADC药物开发和批准的重要事件时间线。ADC代表抗体药物偶联物;CEA代表癌胚抗原;ALL代表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BR96是一种结合Lewis Y的抗体;DOX代表多柔比星;FDA代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 ADC的关键组成部分
如图2所示,ADC由抗体、细胞毒素有效载荷和化学连接臂组成。一个理想的ADC药物在血液循环中保持稳定,准确到达治疗目标,并最终在目标附近(例如癌细胞)释放细胞毒素有效载荷。每个元素都可能影响ADC的最终疗效和安全性,通常ADC开发需要考虑所有这些关键组成部分,包括选择目标抗原、抗体、细胞毒素有效载荷、连接臂以及偶联方法。
图2 展示了ADC药物的结构和特点。核心组成部分包括目标抗原、抗体、连接体、细胞毒素药物以及它们的关键功能。
2.1. 目标抗原选择
肿瘤细胞上表达的目标抗原是ADC药物识别肿瘤细胞的导航方向,它还决定了将细胞毒素有效载荷输送到癌细胞的机制(例如内吞作用)。因此,适当的选择目标抗原是ADC设计的首要考虑因素。为了减少非靶组织的毒性,目标抗原首先应该在肿瘤细胞中特异性表达或占主导地位,在正常组织中很少或很低表达。理想情况下,抗原是表面(或细胞外)抗原,而不是细胞内抗原,以便被循环中的ADC识别。例如,某些肿瘤中HER2受体的表达量比正常细胞大约100倍,这为阿多珠单抗艾美曲辛、法姆珠单抗德鲁替康和迪司他珠单抗的发展成为坚实的基础。其次,目标抗原应该是非分泌性的,因为循环中的分泌性抗原会导致不希望的ADC在肿瘤外部位点的结合,导致肿瘤靶向性降低和安全性问题增加。第三,目标抗原理想情况下在与相应抗体结合后能够被内吞,以便ADC-抗原复合物进入癌细胞,随后通过适当的细胞内运输途径和有效释放细胞毒素有效载荷。
目前,如图3所示,已批准的ADC药物的目标抗原通常是癌细胞中特异性高表达的特定蛋白质,包括实体瘤中的HER2、Trop2、Nectin4和EGFR,以及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的CD19、CD22、CD33、CD30、BCMA和CD79b。在肿瘤学和免疫学基础研究的推动下,ADC目标抗原的选择已逐渐从传统的肿瘤细胞抗原扩展到肿瘤微环境中的目标,例如基质和血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血管系统的组成部分、亚内皮细胞外基质和肿瘤基质可能是ADC药物开发中有价值的目标抗原。例如,基质靶向ADC药物有潜力通过降低基质细胞产生的生长因子浓度来引起癌细胞死亡。由于癌细胞的生存依赖于血管生成和基质因子,ADCs可能通过靶向这些组织具有更广泛的疗效。此外,这些细胞的基因组比癌细胞更稳定,这可能为降低突变诱导的药物抗性提供了有希望的手段。
图3 展示了用于开发ADC的重要肿瘤细胞靶点抗原(过度表达和驱动基因)以及肿瘤微环境(血管和基质)。这些图像是使用BioRender.com创建的。
2.2. 抗体质点
肿瘤靶向抗体对于ADC与目标抗原之间的特异性结合至关重要。理想的抗体质点除了对目标抗原具有高亲和力外,还应促进有效的内吞作用,展示低免疫原性,并保持长的血浆半衰期。在ADC药物开发的早期阶段,主要使用小鼠来源的抗体,但由于严重的免疫原性相关的副作用,导致高失败率。随着重组技术的出现,小鼠抗体大多被嵌合抗体和人源化抗体所取代。目前,ADC越来越采用完全人源化的抗体,显著降低了免疫原性。在14种批准的ADC药物中,只有brentuximab vedotin使用嵌合抗体。
作为血清中免疫球蛋白的主要组成部分,目前ADC药物中使用的抗体大多是免疫球蛋白G(IgG)抗体,包括IgG1、IgG2、IgG3和IgG4四个亚型。IgG1是ADC常用的亚型,因为IgG1在血清中含量最丰富,并且能够通过与Fc受体的高亲和力诱导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ADCC)、抗体依赖性吞噬作用(ADCP)和补体依赖性细胞毒性(CDC)等强效应器功能。这些Fc介导的效应功能在抗体药物的抗癌活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IgG3很少用于ADC,因为其清除速率很快。与其他三种亚型的半衰期大约21天不同,IgG3在血清中的半衰期仅为大约7天。IgG2在体内通常倾向于形成二聚体和聚集体,导致ADC药物的浓度降低。IgG4可以诱导ADCP,然而,IgG4是一种具有Fab臂交换的异常动态抗体,导致效力降低和靶向效果不佳。
关于抗体-抗原复合物的内吞作用,效率主要取决于抗体与肿瘤细胞表面抗原之间的结合亲和力,其中更高的亲和力通常导致更快的内吞作用。然而,具有高抗原亲和力的抗体可能会减少进入实体瘤的渗透。实体瘤的治疗比血液瘤更复杂,因为实体瘤存在“结合位点屏障(BSB)”,极其强烈的抗体与抗原结合导致ADCs在从血管渗出后被困在血管附近,而较少渗透到远离血管的肿瘤细胞。因此,抗原与抗体之间的合理亲和力应该被优化,以平衡在目标细胞中的快速吸收和抗癌效力。除了结合亲和力外,影响肿瘤渗透的另一个因素是抗体的大小。IgG抗体(约150 kDa)的分子量大通常对通过血浆毛细血管和肿瘤基质的渗透构成挑战。因此,早期ADC主要针对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为了使ADC更好地适用于实体瘤治疗,研究人员尝试通过去除FC段来缩小抗体的大小。缩小的抗体不仅保持了高亲和力和特异性,而且还更容易通过血管渗透到实体瘤中,从而大大提高了对实体瘤的杀伤效果。然而,这样的变化也被发现会导致体内半衰期的减少。因此,在设计使用缩小抗体的ADC时,应考虑多种因素。
2.3. 连接臂
ADC中的连接臂连接抗体与细胞毒素药物。它是与ADC稳定性和有效载荷释放特性相关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对ADC的最终治疗指数至关重要。理想的连接臂不应引起ADC聚集,预期限制血浆中有效载荷的过早释放,并促进在期望的目标部位释放活性药物。根据细胞内的代谢命运,可裂解和不可裂解连接臂在大多数ADC药物中得到应用。
可裂解连接臂利用系统循环和肿瘤细胞之间的环境差异来准确释放游离细胞毒素药物,它们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化学裂解连接臂(腙键和二硫键)和酶裂解连接臂(葡萄糖苷酸键和肽键)。腙是一种典型的酸敏感(pH敏感)连接臂。腙连接的ADC通常在血液循环中稳定,但在内吞进入目标癌细胞后,在溶酶体(pH 4.8)和内质体(pH5.5–6.2)中水解,释放细胞毒素有效载荷。然而,腙键的水解并不完全局限于溶酶体,偶尔也会在血浆中发生,导致靶向效率降低和非靶向效应。迄今为止,含腙连接臂的ADC主要用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例如,gemtuzumab ozogamicin和inotuzumab ozogamicin分别使用腙连接卡利奇霉素与mAbs治疗AML和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ALL)。基于二硫键的连接臂是另一种化学敏感的可裂解连接臂,对还原性谷胱甘肽(GSH)敏感。GSH在维持细胞存活、增殖和分化以及维持细胞内氧化还原平衡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血液中的GSH浓度远低于癌细胞内的浓度。因此,这种类型的连接臂可以保持在血液系统中稳定,同时在GSH水平升高的癌细胞中特异性释放活性有效载荷。
在酶敏感连接臂方面,基于肽的连接臂对溶酶体蛋白酶敏感,已在许多ADC中得到应用。溶酶体蛋白酶,如卡他蛋白B,在癌细胞中通常过度表达,使药物能够在肿瘤附近准确释放。此外,由于血液中存在蛋白酶抑制剂,连接臂通常在系统循环中稳定,降低了副作用的风险。在批准的ADC药物中,有9种使用基于肽的连接臂。例如,brentuximab vedotin使用缬氨酸-瓜氨酸连接臂。此外,β-葡萄糖苷酸连接臂是ADC中常用的另一种酶敏感连接臂。它可以通过β-葡萄糖苷酸酶在细胞内裂解,释放有效载荷,该酶在肿瘤区域的水平通常较高。
相比之下,不可裂解连接臂(例如硫醚或马来酰亚胺己酰基团)对体内的常见化学和酶环境无反应。不可裂解连接臂的最大优势是其低非靶向毒性,得益于血浆稳定性的提高。不可裂解连接臂依赖于ADC的抗体部分的酶促水解,最终释放与抗体降解产物中的氨基酸残基连接的“复合体”有效载荷。只有能够耐受化学修饰的小分子(例如,药效团远离偶联位点时)才适合基于硫醚的连接臂。ado-trastuzumab emtansine(T-DM1)展示了硫醚连接臂的成功应用。该偶联物是抗HER2单克隆抗体与DM1(美登木素)通过琥珀酰亚胺-4-(N-马来酰亚胺甲基)环己烷-1-羧酸盐(SMCC)连接臂链接的产物。连接臂使偶联物在血液中更稳定,并在癌细胞内经蛋白酶消化抗体部分后释放活性代谢物赖氨酸-MCC-DM1。
2.4. 细胞毒素有效载荷
细胞毒素有效载荷是ADC进入癌细胞后发挥细胞毒性的弹头。由于静脉注射后只有大约2%的ADC能够到达目标肿瘤部位,因此作为ADC中的有效载荷,化合物需要具有很高的效力(IC50在纳摩尔和皮摩尔范围内)。此外,这些化合物应在生理条件下保持稳定,并具有可用于与抗体偶联的官能团。目前,ADC中使用的主要细胞毒素有效载荷包括强效的微管抑制剂、DNA损伤剂和免疫调节剂(表1)。
微管是细胞骨架的主要成分,在细胞分裂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肿瘤细胞的快速增殖中。微管抑制剂包括促进微管聚合和抑制微管聚合的药物,它们已成为抗癌药物研发的热点之一。微管聚合促进剂靶向微管二聚体的β亚基,干扰微管依赖的有丝分裂,其代表药物有auristatin衍生物单甲基auristatin E(MMAE)和单甲基auristatin F(MMAF)。在14种批准的ADC药物中,有5种使用MMAE/MMAF作为有效载荷。相比之下,微管聚合抑制剂阻断微管二聚体形成成熟的微管。典型的抑制剂包括maytansinoid衍生物DM1和DM4(ravtansine)。Ado-trastuzumab emtansine是2013年获得FDA批准的首个使用maytansinoid衍生物的ADC药物。此外,tubulysins(从粘细菌中分离出的四肽)是另一类微管聚合抑制剂,显示出有希望的抗癌活性。例如,EC1169是一种针对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SMA)的tubulysin B hydrazide偶联物,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NCT02202447)。
与微管抑制剂的纳摩尔级 IC50(半最大抑制浓度)相比,DNA损伤剂的IC50值能够达到皮摩尔级别,因此与DNA损伤剂结合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DCs)有时更有效,并且可能独立于细胞周期工作(与主要在有丝分裂阶段工作的微管蛋白抑制剂相比),它们甚至可能对那些抗原表达较低的细胞也有效。DNA损伤剂所涉及的详细机制主要包括:(i)DNA双链断裂,如卡利切阿米辛;(ii)DNA烷基化,如二卡霉素;(iii)DNA插入,如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iv)DNA交联,如吡咯并苯并二氮卓(PBD)。卡利切阿米辛是一种天然烯二炔抗生素,对DNA损伤极为有效。与DNA的小沟结合后,卡利切阿米辛产生自由基并引起链断裂,从而诱导细胞死亡。在卡利切阿米辛衍生物中,卡利切阿米辛γ1是最显著的,用于吉妥珠单抗奥佐加米辛和伊诺珠单抗奥佐加米辛。二卡霉素是另一类极为有效的抗肿瘤抗生素,它与DNA的小沟结合并烷基化核苷酸腺嘌呤。SN-38(7-乙基-10-羟基喜树碱)和DXd(exatecan衍生物)是两种主要的喜树碱衍生物,作为ADC药物的有效载荷,通过抑制DNA拓扑异构酶I。例如,萨西图珠单抗戈维特坎是一种针对Trop-2的首创ADC,将SN-38与萨西图珠单抗偶联,而泛曲妥珠单抗德鲁斯特坎由一个针对HER2的抗体与DXd通过肽链偶联组成。PBD是在1960年代早期发现的一类抗肿瘤抗生素。PBD作为二聚体与DNA的小沟结合。结合后,二聚体促进与DNA上的鸟嘌呤在N2位置的氨基交联,从而阻止DNA与转录因子的结合,导致细胞增殖停滞,最终导致细胞死亡。这种机制不依赖于特定的细胞复制周期,DNA损伤难以修复,导致强大的细胞毒性。隆卡替珠单抗特西林是目前唯一在临床上使用,采用PBD作为有效载荷的ADC。除了传统的细胞毒素,越来越多的具有新机制的有效载荷被纳入ADC设计。例如,最近开始应用于新型ADC药物开发的小分子免疫调节剂,也被称为免疫刺激抗体偶联物(ISACs)。ISACs结合了抗体导航靶向的精确性和基于小分子的先天和适应性免疫系统调节的力量。在多种肿瘤模型中记录了有希望的肿瘤退缩和长期抗肿瘤免疫。目前,新型有效载荷主要包括Toll样受体(TLR)激动剂和干扰素基因刺激剂(STING)激动剂。TLRs是先天免疫中一组关键的模式识别受体,在免疫-肿瘤界面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TLR7和/或TLR8的激活可以诱导依赖于MyD88的信号通路,激活NF-κB以分泌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允许抗肿瘤淋巴细胞的渗透。BDC-1001是一种Boltbody ISAC,目前正在临床开发中(第1/2阶段,NCT04278144)。它由一个针对HER2的抗体与TLR7/8激动剂链接,用于治疗HER2阳性实体瘤患者。Silverback Therapeutics还开发了ImmunoTAC平台,并设计了几种使用TLR8激动剂作为有效载荷的ISACs,如SBT6050、SBT6290和SBT8230。至于STING,它也是一个研究充分的先天免疫途径,STING激动剂能够诱导抗肿瘤免疫活性。武田的CRD5500和Mersana的XMT-2056是两个正在进行临床开发的领先的STING激动剂ADC项目。ISACs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但一些候选药物已经相继进入临床开发,其后续进展值得期待。
2.5. 偶联方法
除了选择抗体、连接体和有效载荷外,小分子部分(即连接体加有效载荷)与抗体连接的方法对于成功构建ADC也很重要。通常,抗体上的赖氨酸和半胱氨酸残基提供了可接近的反应位点用于偶联,早期的ADC药物通常利用预先存在的赖氨酸或半胱氨酸残基上的随机偶联通过适当的偶联反应。酰胺偶联可以说是最常用的方法,其中活性羧酸酯(当连接体中存在时)用于将有效载荷连接到抗体上的赖氨酸残基,如在吉妥珠单抗奥佐加米辛、T-DM1和伊诺珠单抗奥佐加米辛中所见。然而,一个抗体通常包含大约80-90个赖氨酸残基,其中40个赖氨酸残基通常是可修饰的。通过与赖氨酸残基的随机偶联,可能将不同数量(0-8)的小分子毒素附加到一个抗体上,导致广泛的药物-抗体比(DAR)分布。此外,由于赖氨酸残基分布在抗体的轻链和重链上,靠近抗体-抗原识别位点的偶联反应可能会降低ADC与目标的结合。基于半胱氨酸的反应提供了另一种偶联方式。还原后,二硫键可以转化为可接近偶联反应的半胱氨酸残基。通常,IgG1抗体既有链间二硫键也有链内二硫键。链间二硫键暴露在抗体的外部,容易被还原以暴露自由的半胱氨酸残基,为连接体-有效载荷与抗体的偶联提供了可用的位点。由于结合位点数量有限以及巯基团的独特反应性,使用半胱氨酸作为连接位点有助于减少ADC的异质性。根据还原比例,可以生成DAR为2、4、6和8的产品,与赖氨酸残基偶联的产品相比具有更好的均匀性。这是迄今为止商业产品中最常用的偶联方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打开链间二硫键可能会破坏抗体的完整性。通常与基于赖氨酸和半胱氨酸残基的随机偶联相关的一些缺点。这种偶联的稳定性有时不足,导致过早的有效载荷释放,从而产生非靶向毒性。此外,很难保证有效载荷连接到抗体上的一致位点,也很难实现质量控制和临床使用所青睐的均匀DAR。为了减少ADCs的异质性,已经在新的ADCs中开发了几种位点特异性偶联策略(表2)。首先,引入工程化反应性半胱氨酸残基已成为位点特异性偶联的常用方法。由Genentech开发的ThioMab技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在曲妥珠单抗的轻链V110A和重链A114C的特定位置插入半胱氨酸残基,然后与半胱氨酸上的硫醇基团偶联MMAE,合成位点特异性抗MUC16 ADC。产生的ADC中DAR为2的比例高达92.1%。此外,ThioMab技术没有影响免疫球蛋白的折叠和组装或抗体与抗原的结合。另一方面,ThioMab技术的一个主要限制是硫醇基团引入步骤可能会导致两个Fab之间的错误二硫键形成,这仍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挑战。此外,尽管偶联效率低和链内错误桥接,二硫键重新桥接偶联也引起了关注。与传统的半胱氨酸偶联类似,偶联位点也是通过还原链间二硫键获得的。而不是随机偶联,二硫键重新桥接涉及与半胱氨酸选择性交联试剂的反应,如双磺酰基试剂,下一代马来酰亚胺(NGMs),和吡啶嗪二酮(PDs)。双反应试剂使抗体的多肽链重新连接以及在抗体上的有效载荷偶联成为可能。根据每个连接体上附加的有效载荷数量,可以产生DAR为4、8或16的ADCs。
位点特异性偶联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引入非天然氨基酸,包括N-乙酰-L苯丙氨酸、叠氮甲基-L苯丙氨酸和叠氮赖氨酸。这些非天然氨基酸中的特殊功能基团使位点特异性偶联成为可能。此外,偶联是可控的和定量的,以产生具有均匀DAR、高效率、良好稳定性和高安全性的ADCs。然而,有时很难生产修饰过的抗体,含有非天然氨基酸的抗体可能会引起免疫原性。
非天然氨基酸的疏水性也增加了抗体聚集的风险。酶辅助连接也是一种有效的位点特异性偶联策略。通过基因工程,人工诱导特定的氨基酸序列在抗体中表达,这些序列可以被某些酶识别,随后特定的氨基酸残基被酶修饰,从而实现位点特异性偶联。目前,常用的有甲酰甘氨酸生成酶(FGE)和转谷氨酰胺酶(TG)。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氨基酸序列的修饰可能会诱导免疫原性。位点特异性ADCs也可以通过糖链重塑和糖基偶联来生成。在抗体的Fc片段中,每个重链CH2域的N297位置的N-糖链存在,使得通过糖基化与有效载荷偶联的反应位点成为可能。多糖与Fab区域之间的远距离定位可以最小化对抗原结合亲和力的损害。这可能是通过赖氨酸基础化学偶联构建ADC的一个缺陷。此外,最近开发了一种名为pClick技术的位点特异性偶联技术用于ADC。通过引入一种近距离激活的交联剂,带有叠氮基团的肽可以自发地与抗体上最近的赖氨酸残基反应。而叠氮基团为带有生物正交手柄修饰的有效载荷提供了点击化学的可用位点。由于不需要抗体工程和后反应处理,产量和抗体稳定性因此显著提高。pClick技术为ADC开发提供了一种更便捷、更有效的方式进行位点特异性偶联。
3. ADC的作用机制
ADC协同发挥“特异性”靶向作用和对癌细胞的“高效”杀伤效果。这些药物就像是一个精确制导的“生物导弹”,能够准确摧毁癌细胞,提高治疗窗口,减少非靶向的副作用。ADC的主要作用机制如图4右上角所示。一旦ADC的mAb与癌细胞特异性表达的目标抗原结合,ADC就被细胞内吞/内化形成早期内体,随后成熟为晚期内体,并最终与溶酶体融合。细胞毒性有效载荷最终通过化学或酶介导在溶酶体中释放,导致细胞通过靶向DNA或微管凋亡或死亡。当释放的有效载荷是可渗透或跨膜的,它也可能诱导旁观者效应以增强ADC的疗效。此外,这些药物的旁观者效应还可能改变肿瘤微环境,进而进一步增强ADCs的杀伤效果。此外,ADC的抗癌活性还涉及ADCC、ADCP和CDC效应。一些ADC的Fab片段可以与病毒感染细胞或肿瘤细胞的抗原表位结合,而FC片段与杀伤细胞(NK细胞、巨噬细胞等)表面的FCR结合,从而介导直接杀伤效果(图4左下角)。此外,ADC的抗体部分可以特异性地结合到癌细胞的表位抗原,并抑制抗原受体的下游信号转导(图4右下角)。例如,T-DM1的曲妥珠单抗可以与癌细胞的HER2受体结合,阻断HER2与HER1、HER3或HER4形成异二聚体,抑制细胞存活和增殖的信号转导途径(如PI3K或MAPK),诱导细胞凋亡。
图4 概述了ADC通过不同途径杀死癌细胞的机制。右上角:ADC的主要核心作用机制;左下角:ADC的抗体部分与免疫效应细胞结合,引发包括CDC、ADCC和ADCP效应在内的抗肿瘤免疫;右下角:ADC的抗体部分保持其活性特征,因此可以干扰目标功能,减弱下游信号以抑制肿瘤生长。使用BioRender.com创建。
4. ADC开发的进展
从药物组成和技术特点的角度来看,ADC药物的开发通常可以细分为三代(表3)。
4.1. 第一代ADCs
在早期,如BR96-doxorubincin等ADC,主要由常规化疗药物通过不可切割的连接体与小鼠来源的抗体偶联而成。这些ADC的效力并不优于游离的细胞毒素药物,而且免疫原性经常是一个问题。后来,使用更有效的细胞毒素药物与人类化mAbs结合,大大提高了疗效和安全性,从而获得了第一代ADCs的市场批准,包括吉妥珠单抗奥佐加米辛和伊诺珠单抗奥佐加米辛。在这两种产品中,使用了IgG4亚型的人类化mAbs,并通过酸敏感的连接体与强效的卡利切阿米辛偶联。然而,这个系统并不完美。例如,酸性条件可能在身体的其他部位出现,第一代ADC中的连接体也可以在系统循环中缓慢水解(pH 7.4,37°C),导致无法控制的有毒有效载荷释放和意外的非靶向毒性。其次,卡利切阿米辛是疏水性的,容易引发抗体聚集,这解释了一些缺陷的出现,如半衰期短、清除速度快和免疫原性。此外,第一代ADC的偶联是基于赖氨酸和半胱氨酸残基的随机偶联,导致高度异质的混合物,具有可变的DARs。DAR对ADC的效力至关重要。不一致的DAR影响ADC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PK/PD)参数和治疗指数。因此,第一代ADC展示了次优的治疗窗口,需要进一步改进。
4.2. 第二代ADCs
以brentuximab vedotin和ado-trastuzumab emtansine为代表的第二代ADC随后推出,对mAbs亚型、细胞毒素有效载荷以及连接体进行了优化。这两种ADC都基于IgG1亚型mAbs,与IgG4相比,更适合与小分子有效载荷进行生物偶联,并且具有更高的癌细胞靶向能力。第二代ADC的另一个重大突破是使用更有效的细胞毒素药物,如auristatins和mytansinoids,提高了水溶性和偶联效率。因此,可以在每个mAb上装载更多的有效载荷分子,而不会引起抗体聚集。除了与抗体载体和细胞毒素有效载荷相关的改进外,第二代ADC中的连接体也得到了改进,以实现更好的血浆稳定性和均匀的DAR分布。总的来说,这三个要素的改进使第二代ADC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得到了提高。然而,仍存在一些未满足的需求,例如由于非靶向毒性导致的治疗窗口不足,以及在高DAR的ADC中聚集或快速清除。当DAR超过6时,ADC表现出高疏水性,并且由于体内更快的分布和清除,倾向于降低ADC的效力。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位点特异性偶联优化DAR,以及持续优化mAbs、连接体和有效载荷,成为第三代ADC成功开发的关键。
4.3. 第三代ADCs
以polatuzumab vedotin、enfortumab vedotin、fam-trastuzumab deruxtecan和后来批准的ADC为代表的第三代ADC。得益于位点特异性偶联技术的引入,生产出了具有良好特征DARs(2或4)和期望的细胞毒性的均匀ADCs。
具有一致DAR的ADCs表现出较少的非靶向毒性和更好的药代动力学效率。此外,第三代中使用完全人源化抗体而非嵌合抗体以减少免疫原性。此外,正在开发抗原结合片段(Fabs)以取代一些ADC候选中的完整mAbs,因为Fabs在系统循环中更稳定,可能更容易被癌细胞内化。此外,还开发了更有效的载荷,如PBD、tubulysin和具有新颖机制的免疫调节剂,与抗体偶联。尽管第三代中的连接体类型没有显示任何更新,但已经开发并使用了像Fleximer平台这样的一些新实体来偶联不同的载荷。为了避免干扰免疫系统并提高在血液循环中的保留时间,第三代ADC中采用了更多亲水性连接体调节,如PEGylation。亲水性连接体也在平衡某些细胞毒性载荷(如PBD)的高疏水性方面提供效用,考虑到含疏水性载荷的ADCs通常容易聚集。总的来说,第三代ADC具有更低的毒性、更高的抗癌活性以及更高的稳定性,允许患者接受更好的抗癌治疗。
5. ADCs的临床开发
5.1. 获批的ADC药物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优化关键组成部分,目前有超过100个ADCs处于临床开发中,截至2021年12月,共有14种ADC药物在全球不同国家获得了市场批准。巧合的是,获批的ADC药物中有一半主要用于血液恶性肿瘤,其余的主要用于实体瘤。这些ADCs的概述,包括它们的分子设计、初步批准年份、市场公司、批准国家和批准适应症,如表4所示。
5.2. 血液恶性肿瘤
吉妥珠单抗奥佐加米辛(Mylotarg®,辉瑞):吉妥珠单抗奥佐加米辛是世界上第一种获批用于临床的ADC治疗药物。它由一个工程化的人源化单克隆IgG4抗体组成,靶向CD33,并通过一个可切割的腙连接体连接一个细胞毒性的N-乙酰-γ-卡利切阿米辛。吉妥珠单抗奥佐加米辛的平均DAR为2-3。以26%的响应率,它最初被FDA批准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r/r)CD33阳性AML患者,这些患者年龄超过60岁,不适合其他常规化疗。成人和儿童AML中大约85-90%为CD33阳性。在与CD33抗原结合并被癌细胞内化后,随后腙键水解释放卡利切阿米辛。卡利切阿米辛还可以扩散到附近的其他癌细胞,诱导那些抗原阴性癌细胞的旁观者杀伤效应。然而,吉妥珠单抗奥佐加米辛中的腙基连接体并不完全稳定,导致卡利切阿米辛在血浆中提前释放,增加非靶向毒性。来自SWOG S0106A研究的结果显示,与单独接受化疗(多柔比星和阿糖胞苷)的患者相比,接受联合治疗(吉妥珠单抗奥佐加米辛与标准多柔比星和阿糖胞苷化疗)的患者观察到更高的严重致命毒性发生率,但没有显著的临床益处反应。因此,辉瑞公司在2010年10月自愿将该产品撤出市场。之后,使用比2000年批准的(9 mg/m2)更低的推荐剂量(3 mg/m2)重新评估了吉妥珠单抗奥佐加米辛的疗效和安全性。吉妥珠单抗奥佐加米辛联合化疗在临床试验ALFA-0701中进行了研究,这是一项多中心、随机、开放标签的3期研究。共有271名(50-70岁)新诊断的AML患者随机分配接受包含(n = 135)或不包含(n = 136)吉妥珠单抗奥佐加米辛的诱导治疗,包括多柔比星(60 mg/m2)和阿糖胞苷(200 mg/m2)。无事件生存期(EFS)被用作主要终点,接受吉妥珠单抗奥佐加米辛联合化疗的患者比仅接受化疗的患者显示出更长的EFS,中位EFS分别为17.3个月和9.5个月(HR = 0.56 [95% CI:0.42–0.76])。两组中发生的3级及以上不良事件(AEs)包括感染(47% vs 39%)、出血(18% vs 9%)和肝静脉闭塞性疾病(2% vs 0%)。此外,吉妥珠单抗奥佐加米辛作为单药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AML-19和MyloFrance-1研究中进行了评估。在AML-19中,总生存期(OS)被用作评估疗效的指标。结果表明,接受吉妥珠单抗奥佐加米辛治疗的患者的中位OS为4.9个月,而接受最佳支持治疗的患者为3.6个月(HR = 0.69 [95% CI:0.53–0.90])。3级以上不良事件在超过5%的患者中包括感染(35%)、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18%)、出血(13%)、疲劳(12%)、肝脏(7%)和心脏(6%)。在MyloFrance-1中,观察到26%的完全缓解(CR)率。超过5%的患者中发生的3级及以上不良事件包括败血症(32%)、发热(16%)、皮疹(11%)、肺炎(7%)、出血(7%)。基于以上三项研究者主导的临床试验中取得的整体积极结果,Mylotarg®于2017年被FDA重新批准。最近,吉妥珠单抗奥佐加米辛获得了FDA的新适应症批准,用于治疗新诊断的CD33阳性AML,包括1个月及以上的儿童患者。从吉妥珠单抗奥佐加米辛的撤回和重新批准中获得的罕见上市经验为ADCs的开发和临床试验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布伦图珠单抗维多汀(Adcetris®,Seagen):布伦图珠单抗维多汀也称为SGN-35,是FDA于2011年批准的第二种ADC药物,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r/r)CD30阳性霍奇金淋巴瘤(HL)和系统性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sALCL)。它由一个针对CD30的嵌合IgG1单克隆抗体brentuximab组成,一个马来酰亚胺连接基团,一个可切割的二肽连接体(马来酰亚胺-缬氨酸-瓜氨酸-对氨基苯甲酰氧羰基或mc-VC-PABC),以及抗有丝分裂剂MMAE。布伦图珠单抗维多汀的平均DAR为4。通过选择性靶向HL和ALCL的特征性抗原CD30,布伦图珠单抗维多汀通过依赖于clathrin的机制内化,并转移到内体和溶酶体中,其中连接体被半胱氨酸蛋白酶(如B)水解。释放出的游离MMAE随后靶向微管蛋白,以抑制其聚合,导致细胞周期停滞和细胞凋亡。由于旁观者效应,布伦图珠单抗维多汀对那些抗原阴性的癌细胞也有效。与吉妥珠单抗奥佐加米辛中的肼连接体相比,布伦图珠单抗维多汀中的基于二肽的连接体在生理条件下显示出更好的稳定性,因此血浆中细胞毒性载荷的过早释放最小。此外,连接体对半胱氨酸蛋白酶敏感,可以促进有效载荷在癌细胞内的高效释放,以确保杀伤效果。布伦图珠单抗维多汀的另一个改进是使用了更强效的细胞毒性载荷,MMAE。它是天然产物Dolastatin 10的合成衍生物,作为一种超有效的抗有丝分裂剂,通过阻断微管蛋白聚合来诱导细胞周期停滞。155 它被广泛用作几种ADCs的有效载荷,如polatuzumab vedotin、enfortumab vedotin和disitamab vedotin。布伦图珠单抗维多汀对HL和sALCL的疗效在两项单臂2期试验中进行了研究,分别有73%和86%的患者实现了客观反应,因此FDA在2013年加速批准了Adcetris®用于r/r HL和sALCL。在一项关键的2期、单臂、多中心研究中,对102名接受过自体干细胞移植(SCT)的r/r HL患者进行了布伦图珠单抗维多汀对HL的疗效评估。
目标反应率(ORR)被用作主要终点。结果表明,在接受了brentuximab vedotin(1.8 mg/kg)治疗的患者中,有73%出现了完全反应(CR)或部分反应(PR),患者对治疗的平均反应时间为6.7个月。在至少5%的患者中出现的3级及以上不良事件(AEs)包括中性粒细胞减少症(20%)、周围感觉神经病变(8%)、血小板减少症(8%)和贫血(6%)。对于sALCL,它在58名复发或难治性sALCL(r/r sALCL)患者的2期、单臂、多中心研究中进行了评估。在接受brentuximab vedotin(1.8 mg/kg)治疗的患者中,有86%经历了完全或部分反应,并且平均反应时间为12.6个月。在sALCL患者中观察到的严重不良事件与接受干细胞治疗(SCT)的患者相似。2017年11月,基于3期研究(ALCANZA)的积极数据,brentuximab vedotin获得了额外的批准,用于治疗先前接受过系统治疗的原发性皮肤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pcALCL)或表达CD30的蕈状真菌病(MF)。在该研究中,brentuximab vedotin显示出至少持续四个月的ORR。此外,在2018年,brentuximab vedotin获得了另外两个临床适应症的批准,与化疗联合使用,包括治疗某些类型的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和先前未经治疗的III期或IV期经典霍奇金淋巴瘤(cHL)。伊诺珠单抗奥佐加米辛(Besponsa®,辉瑞):伊诺珠单抗奥佐加米辛,也称CMC-544,由一个针对CD22的人源化mAb组成,连接到细胞毒性的N-乙酰-γ-卡利切阿米辛,平均DAR为5-7。CD22是大多数(60-90%)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B-ALL)中发现的细胞表面抗原。与CD22结合激活了ADC的一系列下游过程,包括内化、连接体水解和有效载荷释放,类似于吉妥珠单抗奥佐加米辛中所见。通过一项开放标签、随机、国际多中心3期研究(INO-VATE 1022),评估了伊诺珠单抗奥佐加米辛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与研究者选择的化疗方案进行了比较,研究对象为326名接受过一种或两种先前治疗的成人r/r B-ALL患者。所有入选的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伊诺珠单抗奥佐加米辛治疗或替代化疗方案,包括FLAG(氟达拉滨、阿糖胞苷和G-CSF)、HIDAC(高剂量阿糖胞苷)、阿糖胞苷和米托蒽醌的混合物。该研究中使用的主要指标是治疗后无疾病证据和血细胞计数完全恢复的患者百分比。结果显示,35.8%接受伊诺珠单抗奥佐加米辛治疗的患者实现了CR,而替代化疗组观察到17.4%。伊诺珠单抗奥佐加米辛组中出现的3级及以上不良事件包括中性粒细胞减少症(47%)、血小板减少症(41%)、白细胞减少症(27%)和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27%)。基于这些积极结果,2017年8月,FDA批准Besponsa®上市,这是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针对CD22的ADC,用于治疗成人r/r B细胞前体ALL。
毛细胞白血病(HCL)是一种罕见的血液恶性肿瘤,其特征是脾肿大、出血和异常B淋巴细胞的积累。除了B-ALL,CD22也在HCL的B细胞中表达,因此被用作治疗靶点。moxetumomab pasudotox不是使用小分子有效载荷,而是由针对CD22的moxetumomab与假单胞菌外毒素A(PE38)的38kD片段偶联而成。171 CD22在成熟B细胞上表达,在100%的毛细胞上表达更为强烈,为HCL治疗提供了理想的治疗靶点。与CD22结合后,moxetumomab pasudotox被内化,裂解并释放外毒素的催化域进入癌细胞内,抑制蛋白质的翻译导致凋亡。moxetumomab pasudotox的3期临床研究(Study 1053)招募了80名组织学证实的HCL或HCL变异型患者,这些患者需要治疗,基于存在细胞减少症或脾肿大,并且之前接受过至少两种系统疗法(包括一种嘌呤核苷类似物)。患者接受moxetumomab pasudotox治疗(0.04 mg/kg),直到观察到CR、疾病进展或不可接受的毒性。在研究中,moxetumomab pasudotox单药治疗的ORR和CR率分别为75%(95% CI,64-84)和41%(95% CI,30-53)。此外,持久的CR率为30%(95% CI,20-41)。最常见的3-4级事件包括淋巴细胞减少(20%)、贫血(10%)和无症状低磷血症(10%)。2018年9月,FDA批准了AstraZeneca的Lumoxiti®用于治疗先前至少接受过两种系统疗法(包括嘌呤核苷类似物)失败的成人r/r HCL患者。这使得moxetumomab pasudotox成为过去20年来首个获批用于治疗HCL的新药,是HCL临床治疗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Polatuzumab vedotin(Polivy®,罗氏):Polatuzumab vedotin,也称DCDS4501,包含一个针对CD79b的人源化抗体,通过可被蛋白酶切割的二肽连接体(mc-VC-PABC)连接到微管破坏剂MMAE,平均DAR为3.5。CD79b是B细胞受体(BCR)的一个组成部分,超过90%的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nHL)恶性肿瘤表达,并被视为一个有前景的抗体靶点。与brentuximab vedotin类似,给药后,polatuzumab vedotin选择性地结合到CD79b,随后内吞和蛋白水解裂解,释放MMAE,诱导细胞周期停滞和细胞死亡。2019年7月,Polivy®获得FDA批准,与苯达莫司汀加利妥昔单抗联合用于治疗至少接受过两种先前治疗的复发或难治性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这是首个获批用于治疗DLBCL的ADC,DLBCL是最常见的nHL类型。批准基于全球、随机的2期GO29365研究的积极结果,该研究包括80名至少接受过一种先前方案治疗的r/r DLBCL患者。入选的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polatuzumab vedotin(Pola,1.8 mg/kg,静脉注射)与苯达莫司汀(B,90 mg/m2静脉注射)和利妥昔单抗(R,375 mg/m2静脉注射)联合治疗,或单独BR,共6个21天周期。CR率和反应持续时间被确定为研究终点。结果显示,接受Pola+BR治疗的患者中有40%观察到CR,而单独接受BR治疗的患者中有18%。在接受Pola+BR治疗并有PR或CR的患者中,反应持续时间超过6个月和12个月的比例分别为64%和48%。Pola+BR组中出现的3-4级不良事件包括中性粒细胞减少症(46%)、血小板减少症(41%)、贫血(28%)、淋巴细胞减少症(12.8%)和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10.3%)。
Belantamab mafodotin(Blenrep®,GSK):Belantamab mafodotin,也称GSK2857916,是一种新型ADC,由一个针对BCMA的人源化FC修饰抗BCMA mAb组成,通过不可切割的马来酰亚胺缬氨酸(mc)连接体与细胞毒素MMAF偶联。Belantamab mafodotin的平均DAR为4。BCMA是一种跨膜糖蛋白,在多发性骨髓瘤(MM)细胞表面特异性过度表达。
与BCMA结合后,belantamab mafodotin被迅速内化,在溶酶体内降解,释放不渗透的MMAF进入多发性骨髓瘤(MM)细胞内。MMAF与MMAE类似,也是一种有丝分裂抑制剂。它可以通过阻断微管蛋白的聚合来抑制细胞分裂,导致细胞周期停滞并诱导依赖于caspase-3的凋亡。总的来说,belantamab mafodotin能够有效地引起过度表达BCMA的癌细胞死亡。2020年8月,FDA批准了Blenrep®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r/r MM)。这是首个基于DREAMM-2临床试验结果获批的BCMA靶向治疗药物,DREAMM-2是一项双臂、开放标签、多中心的2期研究。
在这项研究中,共有221名(年龄≥18岁)接受过三线或以上治疗并且对免疫调节药物和蛋白酶抑制剂耐药,以及对CD38单抗抗药性或不耐受(或两者都有)的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且其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的表现状态为0-2,被纳入并随机分配(1:1)接受两种不同剂量的belantamab mafodotin(分别为2.5 mg/kg和3.4 mg/kg)治疗,直至疾病进展或不可接受的毒性。有效性基于ORR和反应持续时间。结果显示,单独使用belantamab mafodotin治疗,2.5 mg/kg组和3.4 mg/kg组的ORR分别为32%和35%。在2.5 mg/kg组和3.4 mg/kg组中,分别有58%和66%的患者观察到有希望的部分反应(VGPR)。最常见的3-4级不良事件包括角膜炎(2.5 mg/kg组为27%,3.4 mg/kg组为21%)、血小板减少症(分别为20%和33%)和贫血(分别为20%和25%)。
Loncastuximab tesirine(Zynlonta®,ADC Therapeutics):Loncastuximab tesirine,也称ADCT-402,由一个针对CD19的人源化mAb组成,通过可切割的(缬氨酸-丙氨酸二肽)马来酰亚胺型连接体与PBD二聚体偶联。Loncastuximab tesirine的平均DAR约为2.3。PBD二聚体是ADC开发中新一代的细胞毒性有效载荷。它与DNA不可逆地结合并引起强烈的链间交联,阻止DNA链分离,从而破坏必要的DNA代谢过程,最终导致细胞死亡。它不依赖于细胞分裂周期,损伤不易恢复,显示出更好的细胞毒性。2021年4月,Zynlonta®获得FDA加速批准,用于治疗接受过两线或以上系统治疗的成人复发或难治性大B细胞淋巴瘤,包括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未另行指明(NOS)、由低级别淋巴瘤发展而来的DLBCL和高级别B细胞淋巴瘤。Loncastuximab tesirine是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获批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DLBCL的CD19靶向ADC,作为单一药物。
Zynlonta®的批准基于LOTIS-2研究的数据,LOTIS-2是一项多中心、开放标签、单臂、2期试验。共有145名接受过至少两线系统治疗方案的成人复发或难治性DLBCL或高级别B细胞淋巴瘤患者被纳入并接受loncastuximab tesirine(0.15 mg/kg)治疗。总的ORR被用来评估loncastuximab tesirine的主要疗效。结果显示,接受loncastuximab tesirine治疗的患者,ORR达到了48.3%(95% CI:39.9–56.7),CR为24.1%(95% CI:17.4–31.9)。在平均7.3个月的随访后,中位反应持续时间为10.3个月(95% CI:6.9,NE)。在70名实现客观反应的患者中,36%在3个月前就被审查了反应持续时间。最常见的3级及以上不良事件包括中性粒细胞减少症(26%)、血小板减少症(18%)和γ-谷氨酰转移酶增加(17%)。
5.3. 实体瘤
Ado-trastuzumab emtansine(Kadcyla®,罗氏):约15%-20%的乳腺癌患者表现出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过度表达,具有更高的侵袭性。Ado-trastuzumab emtansine,也称T-DM1,是一种靶向HER2的ADC药物,也是首个获准用于实体瘤的ADC。它由一个针对HER2的人源化mAb组成,通过一个不可切割的连接体(丁二酰亚胺-4-(N-马来酰亚甲基)环己烷-1-羧酸酯,SMCC)连接到DM1,平均DAR为3.5。该连接体可以使偶联物在血浆循环中更稳定,但在HER2阳性癌细胞内吞后释放有效载荷。曲妥珠单抗在溶酶体中被蛋白酶完全消化,允许释放含有DM1的代谢产物,赖氨酸-MCC-DM1,其显示出与游离DM1相似的细胞毒性。此外,赖氨酸-MCC-DM1在生理pH下带电,不适用于发挥旁观者效应。因此,T-DM1只针对并导致抗原阳性癌细胞死亡。此外,T-DM1显示出与曲妥珠单抗类似的机制,它可以抑制HER2信号通路,诱导ADCC和CDC效应。
2013年,Kadcyla®获得FDA市场批准,作为单一药物用于治疗先前接受过Herceptin®(曲妥珠单抗)和紫杉醇化疗的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批准基于3期研究(EMILIA)的积极结果。共有991名接受过曲妥珠单抗和紫杉醇治疗的HER2阳性不可切除、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成人患者被纳入并随机分配接受T-DM1(3.6 mg/kg)或拉帕替尼加卡培他滨。PFS和OS被用作主要终点。在最终描述性分析中,T-DM1组的中位PFS为9.6个月,而拉帕替尼加卡培他滨组为6.4个月(p < 0001)。T-DM1组和拉帕替尼加卡培他滨组的中位OS分别为30.9个月和25.1个月。T-DM1组中最常见的3级及以上不良事件包括:血小板减少症(12.9%)、AST增加(4.3%)和ALT增加(2.9%)。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观察到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降低,T-DM1有心脏毒性的警告标签。
此外,基于3期研究(KATHERINE)的积极结果,FDA在2019年5月扩大了Kadcyla®的批准,用于治疗接受过新辅助紫杉醇和基于曲妥珠单抗治疗后仍有残留浸润性疾病的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EBC)患者的辅助治疗。共有1486名符合标准的患者被纳入研究,并随机分配接受T-DM1或曲妥珠单抗治疗。作为该研究的主要终点,接受T-DM1治疗的组与接受曲妥珠单抗治疗的组相比,无浸润性疾病生存期(IDFS)显著提高了50%。在三年时,接受T-DM1治疗的患者中有88.3%没有复发,而接受曲妥珠单抗治疗的患者中有77.0%。
恩福妥昔单抗(Padcev®,Seagen):恩福妥昔单抗也被称为ASG-22ME,已获FDA批准用于治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的成年患者。它由一个全人源抗nectin-4 IgG1 kappa单克隆抗体(AGS-22C3)组成,通过可被蛋白酶切割的连接体(MC-VC-PABC)与MMAE相连,平均DAR约为3.8。Nectin-4是一种跨膜蛋白,属于nectin家族,对细胞增殖、迁移和粘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已发现它在多种恶性肿瘤中高度表达,尤其是在尿路上皮癌中。通过免疫组化分析,60%的膀胱肿瘤标本观察到强烈的染色,而正常组织中染色有限。因此,它已成为ADC新分子设计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靶点。恩福妥昔单抗是目前唯一获得FDA批准的靶向nectin-4的ADC。2019年12月,FDA首次授予加速批准,随后在2021年9月基于一项开放标签、随机、多中心3期研究(EV-301)的结果进一步授予常规批准。在EV-301研究中,共有608名接受过PD-1或PD-L1抑制剂和基于铂的化疗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被纳入并随机平均分配,接受恩福妥昔单抗(1.25 mg/kg)或替代化疗(多西他赛、紫杉醇或长春瑞滨)治疗。OS和PFS分别用作评估疗效的主要终点和次要终点。与替代化疗相比,恩福妥昔单抗取得了显著的疗效,中位OS(12.9个月对9.0个月)和中位PFS(5.6个月对3.7个月)均显著延长。199,204 至少5%的患者中发生的3级及以上不良事件包括斑丘疹(7.4%)、疲劳(6.4%)和中性粒细胞计数下降(6.1%)。
Fam-trastuzumab deruxtecan(Enhertu®,第一三共):Enhertu,也称DS-8201或T-DXd,是针对不可切除或转移性HER2阳性乳腺癌成年患者的HER2靶向ADC,这些患者在接受转移性治疗时已接受过两种或以上的抗HER2方案。它由一个人源化HER2抗体(曲妥珠单抗)组成,通过一种酶可切割的四肽连接体与一种新型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DXd)作为有效载荷偶联,平均DAR为7-8。DXd被报道比SN-38(伊立替康的活性形式)更强效,DXd的更高效力确保了其在ADC中作为有效载荷时的疗效。DS-8201的另一个改进是采用了新型四肽连接体技术,该连接体在血浆中更稳定,降低了系统毒性的风险。2019年12月,基于单臂、多中心、2期DESTINY-Breast01研究的积极结果,FDA批准了Enhertu®。共有184名接受过两种或以上抗HER2治疗的HER2阳性、不可切除和/或转移性乳腺癌(mBC)女性患者被纳入研究。主要终点是ORR和反应持续时间。结果显示,接受DS-8201(5.4 mg/kg)治疗的患者ORR为60.3%(95% CI:52.9, 67.4),CR率为4.3%,PR率为56%。中位反应持续时间为14.8个月,中位PFS持续时间为16.4个月。至少5%的患者中发生的3级及以上不良事件包括中性粒细胞计数下降(20.7%)、贫血(8.7%)、恶心(7.6%)、白细胞计数下降(6.5%)、淋巴细胞计数下降(6.5%)和疲劳(6.0%)。此外,DESTINY-Breast03的最新数据,这是一项全球性、头对头、随机、开放标签、关键3期试验,证明了DS-8201相比T-DM1具有显著优势。具体来说,共有524名接受过曲妥珠单抗和紫杉醇治疗的HER2+ mBC患者被纳入并随机分配(1:1)。主要终点是PFS,包括OS、ORR和反应持续时间的次要终点也被使用。结果显示,DS-8201的中位PFS未达到,而T-DM1为6.8个月。而且,接受DS-8201治疗的患者的中位反应持续时间为14.3个月,而接受T-DM1治疗的患者为6.9个月。此外,另一项头对头研究(DESTINY-Breast09)正在进行,比较DS-8201和曲妥珠单抗。DESTINY-Lung01研究还评估了DS-8201在携带HER2突变的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在91名入选患者中,55%在平均随访时间为13.1个月时确认有客观反应。中位PFS持续时间为8.2个月,中位OS持续时间为17.8个月。观察到46%的患者出现3级及以上不良事件,包括中性粒细胞减少症(19%)和贫血(10%)。该临床观察也对DS-8201潜在的肺部毒性提出了关注。值得注意的是,间质性肺病(ILD)在26%(91名患者中有23名)的患者中观察到,两名患者死于治疗相关的ILD。ILD是一组影响肺部间质的呼吸系统疾病,这将破坏我们身体的修复损伤过程,并阻止氧气参与血液循环。因此,在后续的临床试验中,需要更加谨慎地关注ILD,并适当培训临床医生识别和管理这种毒性效应。自从DS-8201推出以来,其临床潜力仍在不断扩大和深化。DS-8201用于胃癌的新适应症也已获得批准。乳腺癌的治疗线也在向前推进,不断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选择。
Sacituzumab govitecan(Trodelvy®,Immnomedics):Sacituzumab govitecan,也称IMMU-132,是一种ADC,由一个针对Trop-2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组成,通过一个可水解的连接体(CL2A)与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SN-38)偶联,平均DAR约为7.6。Trop-2是一种40-kDa糖蛋白,作为细胞内钙信号传导的转导体。在大多数实体瘤中观察到Trop-2的过度表达,包括三阴性乳腺癌(TNBC)。从理论上讲,Trop-2蛋白的过度表达与强烈的侵袭性和不良预后有关,这使得Trop-2成为一个理想的广谱治疗靶点。在sacituzumab govitecan中,SN-38是伊立替康的活性形式,通过抑制DNA拓扑异构酶I引起频繁的DNA单链断裂,最终导致细胞死亡。73 就CL2A而言,它连接SN-38和Trop-2抗体,是sacituzumab govitecan作为第三代ADC的最突破性设计。这个设计良好的连接器提高了Trop-2抗体与SN-38的结合比率,在肿瘤中具有更高的毒性浓度,但在非靶标中的浓度更低,半衰期更短。通过优化连接体的稳定性,它不仅可以在目标肿瘤细胞中释放SN-38,而且还能实现旁观者效应,杀死难以靶向的邻近癌细胞。2020年4月,sacituzumab govitecan获得FDA加速批准,用于治疗接受过两种或以上系统治疗的不可切除局部晚期或转移性TNBC患者,至少一种用于转移性疾病。这是FDA批准用于转移性TNBC的第一个抗Trop-2 ADC。sacituzumab govitecan的临床益处在随后的多中心、开放标签、随机试验(ASCENT)中得到进一步确认,该试验促进了FDA的常规批准。ASCENT研究在529名接受过至少两种化疗后复发的不可切除局部晚期或mTNBC患者中进行,其中一种可能是在新辅助或辅助环境中,如果进展发生在12个月内。入选的患者被随机分为两组,分别接受sacituzumab govitecan(n = 267,10 mg/kg)和单一药物化疗(n = 262,卡培他滨、艾瑞布林、长春瑞滨或吉西他滨)。主要疗效终点是无脑转移患者的PFS。结果显示,接受sacituzumab govitecan治疗的患者的中位PFS为4.8个月,而接受化疗的患者为1.7个月。而且,中位OS分别为11.8个月(sacituzumab govitecan)和6.9个月(化疗)。
sacituzumab govitecan的3级及以上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包括中性粒细胞减少症(51%)、白细胞减少症(10%)、腹泻(10%)、贫血(8%)和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6%)。
Cetuximab sarotalocan(Akalux®,Rakuten Medical):Cetuximab sarotalocan也被称为RM-1929,是一种新型ADC,由一个抗EGFR嵌合单克隆抗体cetuximab与近红外光敏染料IRDye® 700DX偶联而成。cetuximab sarotalocan的平均DAR在1.3-3.8范围内。EGFR在多种实体瘤表面高度表达,包括头颈鳞状细胞癌(HNSCC)、食管癌、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和其他实体瘤。Cetuximab sarotalocan能够靶向EGFR,并在与癌细胞结合后由光纤释放的红激光局部激活,导致细胞死亡。它不仅利用抗体介导的靶向输送实现高肿瘤特异性,还采用激光激活的生物物理机制精确诱导癌细胞的快速死亡,而不损伤周围正常组织。
2019年9月,cetuximab sarotalocan获得日本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局(PMDA)批准,用于治疗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或复发性头颈鳞状细胞癌。批准是基于一项多中心、开放标签2a期试验的积极数据。共有30名无法通过手术、放疗或含铂化疗满意治疗的局部区域性头颈鳞状细胞癌患者被纳入研究。在给予RM1929 24小时后,使用非热红光照射肿瘤区域。结果显示,cetuximab sarotalocan治疗的ORR为28%,其中包括14%的CR,中位PFS和中位OS分别为5.7个月和9.1个月。最常见的3级及以上不良事件包括皮肤反应(18%)、甲沟炎(12%)和过敏反应(3.5%)。迄今为止,cetuximab sarotalocan尚未在日本以外获得批准,目前正在进行全球3期试验。
Disitamab vedotin(Aidixi®,RemeGen):Disitamab vedotin也被称为RC48,是第三种上市的HER2靶向ADC,由一种新型人源化HER2抗体、可被组织蛋白酶切割的连接体(mc-VC-PABC)和细胞毒素MMAE组成。RC48的平均DAR约为4。Disitamab vedotin中使用的抗体对HER2具有更高的亲和力,在动物模型中显示出更强的抗肿瘤活性。2021年6月15日,disitamab vedotin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的有条件批准,用于治疗至少接受过2种系统化疗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胃癌(包括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患者。这是中国开发的首个获批上市的ADC药物。批准是基于RC48-C008研究的结果,该研究表明接受RC48治疗的患者具有临床意义的反应和生存益处。
RC48-C008研究是一项单臂、多中心、开放标签、2期临床试验,共有127名组织学证实的胃或胃食管结合部癌、HER2过度表达、接受过至少2种系统治疗的患者被纳入。在试验中,参与的患者接受disitamab vedotin(2.5 mg/kg)治疗,直到研究者评估的临床获益丧失或不可接受的毒性。ORR被用作主要结果,PFS和OS作为次要结果。数据显示,所有患者的ORR为18.1%(95% CI:11.8–25.9%)。亚组ORR分别为接受2线和≥3线治疗的患者的19.4%和16.9%。总体而言,接受至少2个周期治疗的111名患者的ORR为20.7%。对于所有127名患者,中位PFS为3.8个月,中位OS为7.6个月。3级或更高不良事件在40名患者(32.0%)中观察到,其中最常见的是中性粒细胞计数下降(14.4%)、WBC计数下降(14.4%)和贫血(5.6%)。
此外,disitamab vedotin还于2021年12月获得NMPA的有条件批准,用于接受过含铂化疗治疗失败的HER2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的二线治疗。这得益于RC48-C005研究的结果,这是一项开放标签、多中心、单臂、非随机2期研究。64名HER2过度表达和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在接受顺铂、吉西他滨和紫杉醇治疗失败后被纳入并接受RC48(2 mg/kg)治疗。ORR被用作主要终点。截至2020年11月30日,接受1线、2线和≥3线治疗的患者的ORR分别为55.6%(5/9)、50.0%(21/20)和30.8%(4/13)。
Tisotumab vedotin(Tivdak®,Genmab/Seagen):Tisotumab vedotin是最近获批的ADC药物,平均DAR为4,包含一个完全人源化的mAb,结合组织因子(TF),一个可切割的mc-VC-PABC连接体,和一个抗有丝分裂剂MMAE。TF在肿瘤生长、血管生成和转移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且在几种实体瘤中特异性过度表达。Tisotumab vedotin旨在靶向癌细胞上的TF抗原,并将细胞毒素MMAE直接输送到癌细胞内。此外,旁观者效应、ADCC和ADCP也被证明参与了tisotumab vedotin的作用机制。2021年9月,Tivdak®获得FDA批准,用于治疗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的成年患者,这些患者在化疗后或化疗期间疾病进展,这是首个且唯一获批的TF靶向ADC治疗。
批准是基于innovaTV 204研究的发现,这是一项多中心、开放标签、单臂、2期试验。共有101名符合标准(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患者,之前接受过不超过两种系统治疗方案,包括至少一种复发或转移性环境中的基于顺铂的化疗方案)的患者被纳入研究,接受每21天2 mg/kg的tisotumab vedotin治疗,直至疾病进展或不可接受的毒性发生。确认的ORR被用作主要疗效结果。结果显示,ORR为24%(95% CI:15.9%-33.3%),中位反应持续时间为8.3个月(95% CI:4.2,未达到)。3级或更高不良事件在28%的患者中观察到,包括中性粒细胞减少症(3%)、疲劳(2%)、溃疡性角膜炎(2%)和周围神经病变(2%)。
5.4. 晚期ADC候选药物
除了上述14种获批的ADC药物外,目前还有数百种采用更新技术和新颖靶点的ADC正在进行临床试验。本综述中讨论了三个代表的3期ADC候选药物,以提供概念性的快照。
Mirvetuximab soravtansine(ImmunoGen)。Mirvetuximab soravtansine(IMGN853)由一个针对叶酸受体α(FRα)的人源化mAb组成,通过一个可切割的连接体(sulfo-SPDB)与强效细胞毒素DM4偶联。它已获得FDA授予治疗卵巢癌的孤儿药指定。通过在二硫键的α位引入两个甲基基团以及一个磺酰基,提高了连接体的亲水性,克服了药物在血浆循环中过早释放的缺点。2015年12月,进行了一项开放标签、随机3期试验(NCT02631876),以研究IMGN853与选定的单一药物化疗在治疗对铂类药物耐药的FRα阳性晚期上皮性卵巢癌、原发性腹膜癌和/或输卵管癌的女性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是首个进入人体临床试验的FRα靶向ADC候选药物。共有366名患者随机(2:1)接受IMGN853(6 mg/kg)或单一药物化疗(聚乙二醇化脂质体多柔比星、拓扑替康或紫杉醇)。本研究的主要终点是PFS。
2019年初公布的结果显示,在主要终点PFS方面没有显著差异[HR, 0.98; 95% CI, 0.73–1.31; p = 0.897],IMGN853组和化疗组的中位PFS分别为4.1个月和4.4个月。240 尽管没有达到主要终点,但在次要终点中观察到IMGN853在FRα过度表达的患者中表现更好,包括更好的ORR(24%对10%)和CA-125反应(53%对25%)。因此,FDA推荐进行额外的3期试验。2019年12月,Immunogen宣布了一项3期单臂试验,包括两项研究:SORAYA研究(NCT04296890)和MIRASOL研究(NCT04209855)。此外,另一项1b/2期临床试验(NCT02606305)调查了IMGN853(6 mg/kg)联合贝伐珠单抗(15 mg/kg)在对铂类药物耐药的晚期上皮性卵巢癌、原发性腹膜癌或输卵管癌患者中的应用。Immunogen在2021年ASCO年会上最近宣布了结果。在接受联合治疗的60名患者中,有28名观察到客观反应,确认的ORR为47%(95% CI, 34–60),在高FRα表达的患者中(n = 33),确认的ORR为64%(95% CI 45–80),这表明IMGN853与贝伐珠单抗联合治疗对高FRα复发性卵巢癌患者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最常见的不良事件包括腹泻、视力模糊、疲劳和恶心。
Datopotamab deruxtecan(DS-1062, Daiichi Sankyo/AstraZeneca)。DS-1062或Dato-DXd是第二种靶向Trop2的ADC,由一个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DXd)通过一个可切割的四肽连接体与人源化抗Trop2 IgG1 mAb偶联。平均DAR为4。目前,DS-1062正在进行临床试验,以单独或联合治疗的方式评估对乳腺癌和NSCLC等实体瘤的疗效。TROPION-PanTumor01的更新结果,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1期研究,研究对象为晚期/转移性NSCLC患者(NCT03401385),显示DS-1062(6 mg/kg)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显示出有希望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125名可评估反应的患者中,1%(1/125)有确认的CR,26%(32/125)有PR,并且有4个PR正在等待确认。在6个月时持续反应的概率超过80%,疾病控制率(CR + PR + SD)为79%。它目前也在一项随机、开放标签的3期研究(TROPION-Lung01)中进行研究,比较DS-1062与多西他赛治疗晚期/转移性NSCLC患者的效果,这些患者没有EGFR、ALK或其他可操作的基因变异。设计计划是将590名患者随机1:1分配接受DS-1062(6 mg/kg)或多西他赛(75 mg/m2)。双重主要终点PFS和OS被用作双重主要终点。
Tusamitamab ravtansine(SAR-408701, Sanofi)。SAR-408701是一种新型抗CEACAM5 ADC。它由一个人源化抗体组成,靶向CEACAM5,通过一个可切割的连接体N-succinimidyl 4-(2-pyridyldithio) butyrate (SPDB)与细胞毒素maytansinoid DM4偶联。CEACAM5是一种在正常成人组织中很少表达,但在包括NSCLC在内的多种实体瘤中过度表达的糖蛋白。SAR-408701的前临床活性被研究,结果显示其为CEACAM5阳性癌症的有前途的治疗候选药物。SAR-408701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一项开放标签、剂量递增、剂量扩展的1期研究(NCT02187848)中进行了检查。在研究中,92名患者(28名CEACAM5中等表达者和64名高表达者)接受了SAR-408701(100 mg/m2),截至2020年1月,在接受SAR-408701治疗的中等表达者队列中观察到2个确认的PR(ORR 7.1%),而在接受治疗的高表达者队列中有13名患者确认PRs(ORR 20.3%)。27名(42.2%)患者病情稳定;在接受过抗PD1/PD-L1治疗的患者中观察到17.8%的ORR。目前,有几项SAR-408701的2期或3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采用单一药物或联合治疗NSCLC和其他实体瘤适应症(NCT04154956, NCT04659603, NCT04394624, NCT05071053, NCT04524689)。
6. ADCs的当前挑战和下一代
从前面部分列出的获批药物和在研候选药物中可以看出,与早期代相比,新一代ADCs正在展现出越来越优化的特异性和细胞毒性特征。然而,在开发和使用抗癌ADCs方面仍然存在许多挑战,包括药代动力学的复杂性、不足的肿瘤靶向和有效载荷释放,以及药物抗性。本节提供了这些挑战的概述,随后讨论了在新兴一代ADCs中可能的解决方案。
6.1. 主要挑战
复杂的药代动力学特征。在ADC(大多数通过静脉注射)给药后,系统循环中可能存在三种主要形式,即完整的ADC、裸抗体和游离的细胞毒素。由于目标结合、消除和解偶联,这三种形式的比例将动态变化。在ADC的典型药代动力学特征中,随着ADC的内吞作用和抗体清除,结合的ADC和裸抗体的浓度持续下降。影响抗体清除的因素包括单核吞噬细胞系统和新生儿Fc受体(FcRn)介导的循环。通过与内吞体空泡中的ADC结合,FcRn将ADC导出到细胞外部分进行循环。因此,包括结合的ADC和裸抗体在内的抗体通常比传统的小分子药物具有更长的半衰期。关于游离的细胞毒素,它主要在肝脏代谢,并通过肾脏(尿液)或粪便从体内排泄,这可能受到药物-药物相互作用和肝肾功能损害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再加上患者间变异性高,使得建立PK和PD模型来描述ADC的临床特征并协助设计新的ADCs变得具有挑战性。
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在获批的14种ADCs中,最常见的严重副作用(3级或更高)是血液毒性,包括中性粒细胞减少症、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和贫血。血液毒性以及肝毒性和胃肠道反应可能与细胞毒素过早释放到血液循环中有关。这与主要影响快速增殖的健康细胞的传统化疗药物一致。此外,ADC的抗体部分引起的免疫反应可能导致二次损伤,导致肾毒性。根据最近的临床观察,ADC治疗期间潜在的肺部毒性效应,如间质性肺病(ILD),应引起注意,特别是在抗HER2 ADCs中。T-DM1和DS-8201的临床试验中报告了几例与ILD相关的死亡案例。然而,ILD的作用机制的详细情况仍不清楚。有猜测可能的原因之一可能与ADC在健康肺细胞中的不希望摄取和从ADC释放的游离有效载荷有关。由于血液流动最丰富且在肺部保留时间最长,不希望的ADC摄取和血液中的游离有效载荷最常发生的是在肺部,从而诱发ILD。因此,需要对下一代ADC进行相应的优化,以最小化副作用。在用药期间,应密切监测、预防或给予不良反应的支持性治疗。
肿瘤靶向和有效载荷释放。与传统的细胞毒素药物相比,ADC的分子量要大得多,药物穿透肿瘤的效率受到限制。当前研究表明,只有一小部分输入患者体内的ADC能够到达肿瘤细胞,因此在设计ADC时需要考虑有效载荷的效力。对于ADC药物,有效载荷的传递依赖于通过抗原依赖性内吞作用或抗原非依赖性胞饮作用内吞形成的ADC-抗原复合物。内吞后,ADC抗原复合物将被运输到内体或溶酶体释放有效载荷。当有效载荷通过酸可切割的连接体连接时,对于需要特定蛋白酶的ADCs,有效载荷可能在早期内体中释放。对于需要特定蛋白酶的ADCs,有效载荷的释放将发生在晚期内体或溶酶体中。无论有效载荷释放途径如何,一些ADCs具有“旁观者效应”,可以影响不表达目标抗原的周围癌细胞。对于内吞的ADC,它被认为是具有高异质性目标抗原表达的肿瘤活性ADC的一个重要因素。旁观者效应需要有效载荷穿过细胞膜,因此,通过可切割连接体释放的非极性有效载荷是首选,因为极性分子更有可能留在细胞内。
药物抗性。ADC开发的另一个挑战是药物抗性。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的药物抗性通常涉及药物靶标的逃逸突变。然而,ADCs的药物抗性机制尚未得到充分阐明。由于ADCs的基本作用机制,它们可能更加复杂和多样化。目前的证据表明,肿瘤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逃避ADC的活性,例如减少抗原表达水平、改变细胞内运输途径、对有效载荷的药物抗性。这些潜在机制已在体外和动物模型的临床前研究中得到验证,而确认这些机制的临床证据仍然有限。例如,长期暴露于靶向HER2的ADC,乳腺癌细胞系将减少HER2受体的表达,并减少溶酶体酸化以减慢蛋白质降解和代谢。一些ATP结合盒(ABC)转运蛋白被发现在抗癌药物的出口中很重要,使肿瘤产生抗性。在ADC中常用的有效载荷,如MMAE、MMAF和卡利奇霉素,可以被ABC转运蛋白从癌细胞中输出,这使得这些ADCs表现出药物抗性。
6.2. 未来一代ADCs
ADC由单克隆抗体、连接体和有效载荷组成,因此替换这三个组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影响ADC的效果。针对同一抗原的不同抗体可能具有不同的结合能力,并对受体二聚体化和抗原内吞作用产生不同的影响。当前研究表明,ADC的内吞作用和细胞内运输途径对ADC的细胞毒性活性有关键影响。与野生型蛋白相比,突变蛋白通常具有更高的泛素化水平,更容易被内吞和降解。这意味着,如果ADC用于靶向突变蛋白,它可能会带来显著的临床反应。可以想象,靶向携带致癌突变蛋白的ADCs(如某些EGFR突变体)可能最大化治疗的肿瘤特异性,并达到选择性TKI的水平。此外,双特异性抗体技术的进步为ADC创新带来了更多可能性。这些ADC设计可能提高抗体内吞作用并改善肿瘤特异性。目前正在开发的治疗方法一直在探索这些可能性。例如,靶向同一抗原上不同位点的双特异性ADC可以改善受体聚集并导致目标的快速内吞作用。此外,在临床前实验中,一种双靶向HER2和LAMP-3的双特异性ADC显示出更好的溶酶体聚集和载荷传递。类似地,可以开发使用两种不同细胞毒素药物作为有效载荷的双载荷ADC,以减少药物抗性。通过准确控制两种药物的比例,可以通过将两种协同有效载荷传递到癌细胞中来实现更强的疗效。并且随着两种具有不同机制的有效载荷的应用,药物抗性的发生率将显著降低。例如,一种含有MMAE和MMAF的均匀抗HER2 ADC被设计出来,在异种移植小鼠模型中比相应的单载荷ADCs的联合给药表现出更显著的抗肿瘤活性。
ADC开发的另一种策略是放弃传统mAb的结构,选择将有效载荷与分子量较小的多肽片段或单链可变区片段偶联。这些策略的主要目的是减少ADCs的分子量,从而提高穿透效率和有效载荷传递到肿瘤组织。例如,PEN-221是一种由DM-1与靶向生长抑素受体2的多肽链偶联而成的ADC。它的分子量仅为2 kDa,远低于传统ADC中150 kDa的IgG分子。这种ADCs的当前技术挑战是它们可能在血浆中被迅速清除。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这个障碍,它可能在治疗难以接触的肿瘤方面具有潜力,包括血管化不良和中枢神经系统肿瘤。传统上,需要高内吞能力的mAb来将有效载荷传递到癌细胞中。然而,由于抗原屏障,mAb通常很难扩散到实体肿瘤块中。因此,可以为ADC开发非内吞性抗体。它基于这样一个原理:有效载荷直接在肿瘤微环境中的还原条件下在细胞外释放,然后扩散到癌细胞内导致细胞死亡。
最后,在有效载荷选择方面仍然存在许多创新机会。目前,载荷的选择不再局限于标准细胞毒素药物,而是开始发现更多针对性药物和免疫药物。例如,mirzotamab clezutoclax是一种靶向B7-H3的ADC,它采用促进细胞凋亡的新型BCL-XL抑制剂作为有效载荷。目前正在早期临床试验中进行评估。
7. 结论
来自学术界和工业界的数十年努力已经成功地开发了多种ADC疗法,使成千上万的癌症患者受益。14种ADC药物的推出和其他ADC候选药物的激动人心的临床表现也吸引了更多人关注这个领域,这对于这个相对年轻但高度复杂的领域非常重要。幸运的是,大量研究为决定ADC最终行为的关键要素提供了见解。建立适当的方法对ADC的每个组分进行体外和体内评估至关重要。识别和验证新的抗原/抗体、开发具有最佳毒性的新有效载荷,以及设计新的连接体以平衡稳定性和有效载荷释放,对下一代ADCs至关重要。随着这些领域的研究人员的持续努力,不难想象未来的ADCs将在癌症的靶向治疗中带来更多惊喜。
抗体药物偶联物临床3期
2024-10-02
摘要:抗体-药物偶联物(ADCs)是一种快速发展的靶向生物治疗药物类别,目前结合了单克隆抗体的选择性和由细胞毒素组成的有效载荷的效力。多年来,微管靶向和DNA嵌入剂一直是ADC开发的核心。最近,两种基于拓扑异构酶1抑制剂的ADC——曲妥珠单抗德鲁替康(Enhertu®)和萨奎图珠单抗戈维替康(Trodelvy®)的批准和临床成功,展示了将非传统有效载荷与差异化作用机制结合的潜力。在未来ADC领域的发展中,有效载荷多样化预计将发挥关键作用,这一点从越来越多的临床前和临床阶段非传统有效载荷偶联ADC的数量中可以看出。本综述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概述,涵盖了不同作用机制的经过验证的、被遗忘的和新开发的载荷。
1.引言
使用单克隆抗体作为治疗载体是Paul Ehrlich在“神奇子弹”概念中提出的假设。生物学和化学方面的显著进步导致了抗体-药物偶联物(ADCs)的开发,这是新一代的生物治疗药物,结合了抗体的高度特异性和小分子细胞毒素的效力,目的是在目标细胞内传递高度有效的有效载荷。这些武装化的抗体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显著提高细胞毒素分子的治疗指数,并减少它们的非靶向毒性,这是传统细胞毒素化疗的主要问题。
抗癌ADCs由三部分组成:一种特异性识别目标细胞上抗原的单克隆抗体(mAb)、一种在释放时触发细胞死亡的有效小分子,以及连接这两个元素的链接器。
这些药物的复杂性解释了它们艰难的开发过程,最好的例子是gemtuzumab ozogamicin的混乱历史,它最初在2000年获得批准,在2010年从大多数市场撤出,然后在2017年被FDA重新批准。在mAb设计、目标选择、偶联技术、有效载荷选择和质量控制标准化方面的主要进步,使这个家族演变成了抗癌药物的成熟组成部分,目前有13种药物获得批准用于治疗癌症,其中7种是在过去三年中获得批准的。
鉴于有效载荷的效力,抗体必须对其目标高度选择性,并在偶联后保持其半衰期和生物学特性。抗体工程,如Fc(可结晶片段)沉默或Fc容量增强,是一种强大的工具,分别用于平衡由T细胞靶向引起的抗体非靶向毒性或增加抗体功能,如ADCC和ADCP,两种方法都已在治疗性mAbs的背景下证明其临床益处。在ADCs的背景下,假设Fc沉默将显著减少非靶向毒性。血小板减少症和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是接受ADCs治疗的患者常见的不良反应,可能与血小板表面FcγRIIa受体的表达有关。MEDI4276,一种减少了FcγR结合的曲妥珠单抗艾美坦辛(T-DM1,Kadcyla®)的类似物,已在临床试验中进行了研究,旨在减少与T-DM1观察到的血小板减少症(NCT02576548)。令人惊讶的是,这种ADC在首次人体试验中显示出显著的毒性。相比之下,Fc容量增强已通过brentuximab vedotin(Blenrep®)的批准证明了其益处,其mAb是岩藻糖基化的。最近mAb衍生物的开发扩大了载体的可能性,同时旨在改善ADC载体的基本特性。较小的格式,如mAb片段(scFv、单链可变片段和Fabs、抗原结合片段),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了探索(小格式药物偶联物),目的是增强实体肿瘤的穿透和细胞内化。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候选药物没有进入临床试验,因为它们被发现面临快速消除,可能因此无法提供比传统mAb格式的好处。相比之下,另一类基于自行车肽的小格式药物偶联物似乎满足了与mAb格式偶联物竞争的挑战,具有竞争性的摄取效率,正如目前正在进行的三个自行车肽偶联物的临床试验所说明的(NCT04561362、NCT04180371和NCT03486730)。
除了大小之外,其他重要参数影响这些大分子的药代动力学(PK)和循环半衰期,包括化学修饰,影响它们通过肾小管上皮细胞的保留,以及它们通过新生儿Fc受体(FcRn)的回收率。小格式偶联物可能受益于这些参数的调节。多价结合实体,如二价抗体或双特异性抗体,正在开发中,以提高抗原亲和力、选择性或内化,并可能构成有前途的载体。
最广泛应用的生物偶联方法使用赖氨酸侧链胺和半胱氨酸链间硫醇。然而,所得混合物的异质性一直是ADC失败的主要问题。其他偶联策略已经开发出来,包括通过特定或工程化氨基酸的位点特异性偶联,但迄今为止未能在临床试验中证明改善结果。Iladatuzumab vedotin(DCDS0780A),一种FDA批准的polatuzumab vedotin(Polivy®)的THIOMAB™版本,在临床试验中进行了探索,但由于在测试剂量下的过度眼部毒性而未能进入II期。这种THIOMAB™药物偶联技术展示了巨大的潜力,但两个mAbs之间的区别和/或在临床设计上,包括选定的剂量、适应症和患者群体,可能导致一个获得批准而另一个没有。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要强调不仅技术很重要。正在探索新的偶联策略,如糖链和短肽标签(酶辅助连接)或最近通过ADP-核糖环化酶,目的是生成均匀且物理稳定的ADCs。
连接子在抗体药物偶联物(ADC)设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它强烈影响着ADC的安全性、效力和活性。最重要的是,连接子需要在循环中保持稳定,以避免药物过早脱落,同时允许其在目标细胞内释放。根据其可切割性,已经开发并区分出两类连接子。可切割连接子要么对pH敏感,如腙连接子,要么对谷胱甘肽或二硫化物异构酶敏感,如二硫键连接子,要么对蛋白酶敏感,如二肽键对卡他普辛B。不可切割连接子依赖于抗体部分的溶酶体降解,从而至少保留一个氨基酸,通常是赖氨酸或半胱氨酸,连接到载荷-连接子复合物。这种方法提高了连接的稳定性,因为需要抗体消化才能释放载荷。虽然强调连接子越稳定,引起的非靶向毒性就越少,但这些技术通常发现过于严格,无法支持抗肿瘤活性。ADC的安全性仍然是其设计中的主要挑战,靶向和非靶向毒性不仅由连接子-载荷的不稳定性驱动。实际上,靶向毒性总是由单抗及其对目标的亲和力/亲和力驱动,以及载荷的作用机制,这再次说明了肿瘤类型、目标抗原和ADC结构匹配的重要性。最近对连接子设计改进的兴趣导致了亲水性连接子的开发,以平衡载荷的疏水性。硫酸盐、聚乙二醇(PEG)、多唾液酸(PSAR)或最近基于DNA的连接子显著提高了ADC的稳定性和药代动力学,导致毒性更低、活性更高的ADC。
药物-抗体比率(DAR)直到现在一直保持在四个以下,以避免单抗聚集并限制ADC的整体疏水性,这与毒性、缩短的半衰期和狭窄的治疗指数相关。因此,增加DAR更适合于疏水性较低或得到良好补偿的疏水载荷,如新型连接子技术所示,包括掩蔽实体或连接子亲水插入物,其效率直接决定了DAR增加的能力。恢复亲水性和裸mAb药代动力学特性以及高DAR显著增加了载荷对肿瘤的暴露。这些新的连接子技术使得开发比DNA插入或微管干扰剂更少效力的载荷成为可能,如两个基于拓扑异构酶1的ADC在DAR8处的结合所示,曲妥珠单抗deruxtecan(Enhertu®)和sacituzumab govitecan(Trodelvy®)。这些高度装载的ADC与非传统载荷也可能潜在地扩大ADC的治疗适应症,通过解决高或低目标表达水平的肿瘤,如基于DESTINY-Breast04结果最近批准的Enhertu®在HER2低表达肿瘤中所示。相反,在高效力载荷的背景下,到目前为止,较低的DAR更受欢迎,如最近批准的loncastuximab tesirine(Zynlonta®),一个DAR2的极强吡咯苯并二氮杂卓(PBDs)载荷。值得注意的是,与在临床试验中评估的曲妥珠单抗deruxtecan和类似物在DAR8处结合不同,datopotamab deruxtecan的DAR降低到4,以减少其目标驱动的毒性,这表明了ADC设计的多维性。
载荷(也称为弹头)发挥了ADC的细胞内细胞毒性活性。通过连接子部分共价结合到抗体的细胞毒素的性质非常重要,因为它的作用机制将决定ADC作为抗癌化合物的效力及其可能的适应症。第一代ADC结合了传统化疗药物(紫杉醇、蒽环类),因为载荷不够有效,只有一小部分总偶联物成功地在目标细胞内传递了它们的载荷。肿瘤穿透、细胞表面的靶标拷贝数以及ADC的内化和降解强烈影响细胞内游离载荷的浓度。因此,载荷必须在低浓度下具有高度效力,其50%抑制浓度(IC50s)在低至亚纳摩尔范围内。其他因素,如分子在血浆中的稳定性和在酸性条件下的稳定性、结合位点的可及性或溶解度至关重要。多年来,载荷基本上由两类组成:微管抑制剂,包括美登素和auristatins,以及DNA烷基化剂,如calicheamicins。这些载荷导致了八个ADC的批准(图1)。
图1 FDA对抗癌ADCs的批准。根据其有效载荷的性质对ADCs进行识别:微管破坏剂;DNA靶向剂:卡利奇霉素,吡咯并苯并二氮杂环(PBD),拓扑异构酶1(TOPO 1)抑制剂。
新型且更有效的DNA烷基化剂,如PBD单体和二聚体、indolino-benzodiazepines(IGNs)或cyclopropabenzindolone(CBI)单体和二聚体,IC50值在皮摩尔范围内,一直处于ADC设计的前沿。这些分子是有史以来合成的最强大的抗肿瘤化学物质之一,它们通过ADC结构特异性靶向肿瘤细胞以产生高度有效的“魔法子弹”进行了研究。然而,强烈的剂量限制毒性限制了它们的临床发展,目前只有loncastuximab tesirine在2021年获得了FDA批准(图1)。已经做出了努力,使载荷家族多样化,以获得具有原始作用机制的分子,包括几个不直接针对DNA或微管的分子。效力较低的分子从ADC结构的重大突破中受益,通过改进的连接子设计允许更高的DAR值、更稳定的载荷附着或增强的旁观者杀伤活性。最近和引人注目的成功是拓扑异构酶1(topo-1)抑制剂的开发,这代表了载荷选择的转折点,自2019年以来批准了两个基于topo-1抑制剂的ADC(图1),曲妥珠单抗deruxtecan(Enhertu®,DS-8201a)和sacituzumab govitecan(Trodelvy®)。最近的综述已经描述了ADC的验证和探索性治疗靶标的格局。这篇综述旨在描述ADC背景下验证的、被遗忘的和新开发的载荷的格局,具有多种作用机制,不包括微管抑制剂和DNA烷基化剂。
2.成功的载荷家族:拓扑异构酶1抑制剂
拓扑异构酶1抑制剂是FDA最近批准的抗体-药物偶联物载荷家族,最初由曲妥珠单抗deruxtecan推动,随后是sacituzumab govitecan(表1,图2A)。这些基于中等效力载荷的偶联物的最近发展得益于生产了DAR值为8的高负载ADC。
图2 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基础的ADCs结构图。A FDA批准的ADCs和有效载荷(紫色)以及正在临床评估中的ADCs和有效载荷(蓝色)。B 用于临床前开发的拓扑异构酶1抑制剂(绿色)。C 作为ADCs潜在有效载荷的下一代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图中注释:[ADC名称],抗体,有效载荷。
拓扑异构酶酶位于细胞核内。它们的作用是控制和修复在DNA开放、上游转录和复制过程中发生的DNA超螺旋和纠缠。这些催化酶切割、修复超螺旋并重新连接DNA链。拓扑异构酶根据它们的切割活性分为两个家族:拓扑异构酶I切割单链DNA,而拓扑异构酶II切割双链DNA。拓扑异构酶抑制剂特异性结合到DNA-拓扑异构酶复合物的界面,从而抑制拓扑异构酶修复机制,导致DNA损伤和随后的细胞凋亡。然而,最有效的拓扑异构酶抑制剂的效力比美登素或calicheamicin低100到1000倍,这解释了在最初的ADC设计中对这种载荷类别最初缺乏兴趣。
这种载荷类别包括基于喜树碱和非喜树碱的化合物。喜树碱(CPT)是一种由五个化学环组成的天然植物生物碱,其水溶性差(图2B)。几种衍生物已经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具有改善的生物利用度,即拓扑替康、伊立替康和贝洛替康。这些药物已获得批准用于多种适应症,包括卵巢癌、肺癌、宫颈癌和结直肠癌。伊立替康的脂质体制剂也已获得批准用于治疗晚期胰腺癌。还合成了几种其他CPT衍生物,如gimatecan,目前正在II期评估中,用于治疗卵巢癌、输卵管癌或腹膜癌(NCT04846842)。基于CPT的分子最严重的不良事件(SAEs)包括严重水样腹泻、中性粒细胞减少和血小板减少。
由于其中等细胞毒性效力,CPT衍生物最近被用作ADC载荷,其IC50值在低纳摩尔范围内。它们的效力介于非常有效的(皮摩尔IC50s)抗微管/DNA靶向剂和最初用于最初的ADC项目的传统(微摩尔IC50s)化疗药物之间,后者因缺乏效力而失败(甲氨蝶呤和多柔比星)。到目前为止,有两种CPT衍生物已成功结合到抗体上并获得批准:DXd和伊立替康的活性代谢物SN-38(表1)。
2.1.Exatecan及其衍生物
DXd是exatecan(也称为DX8951f)的衍生物,与CPT相比,该化合物具有增强的活性和改善的溶解性,并且被描述为不是ABCC2或ABCG1的底物。未偶联的exatecan在几项临床试验中进行了评估,但由于其狭窄的治疗窗口,剂量限制性中性粒细胞减少和血小板减少以及强烈的胃肠道毒性,没有提高生存率。最初尝试将exatecan生物偶联到抗体上取得了部分成功,但偶联物出现显著聚集。这个问题通过第一三共制药科学家使用稍微修改的exatecan衍生物,名为DXd,得到了解决。发现这种新化合物保留了exatecan的效力,同时能够成功生物偶联多达8个DXd分子每个抗体,而没有显著的聚集。这种deruxtecan药物连接子在几个专有ADC项目中使用,例如DS-8201a(Enhertu®)、U3-1402和DS-6157a,以DAR8偶联,DS-1062a和DS-7300a以较低的DAR(4)偶联以限制它们的毒性[39],它们要么已经获得FDA批准(DS-8201a),要么目前正在临床评估中(表1,图2A)。尽管DXd载荷展示了比exatecan甲磺酸盐更低的被动膜渗透性,但发现它较少骨髓毒性,因此也被选择用于其改善的安全概况。
曲妥珠单抗deruxtecan(DS-8201a或Enhertu®)由已获批准的靶向HER2的抗体曲妥珠单抗组成,通过一个基于马来酰亚胺的mc-GGFG-am蛋白酶可切割连接子连接到8个DXd载荷(图2A)。这种创新的DAR8 ADC在优化的连接子和载荷方面,与第一代ADC相比,在临床前展现了改善的治疗窗口。在两项大型3期研究(DESTINY-Breast03, NCT03529110, DESTINY-Gastric01, NCT03329690)之后,曲妥珠单抗deruxtecan已于2019年获得FDA批准用于治疗不可切除或转移性HER2+乳腺癌(BC),并于2021年获得批准用于治疗晚期或转移性HER2+胃癌或胃食管癌,2022年稍后用于治疗不可切除或转移性HER2+非小细胞肺癌(DESTINY-Lung02)。值得注意的是,曲妥珠单抗deruxtecan在曲妥珠单抗emtansine治疗后复发的乳腺癌患者中展现了强大的抗肿瘤活性,并在胃癌患者中显示出比伊立替康更强的活性,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和结直肠癌中显示出持久的抗癌活性。另一个ADC批准的突破是由其在DESTINY-Breast04试验中的临床评估所展示,该试验导致其在2022年获得批准用于治疗不可切除或转移性HER2低表达乳腺癌。目前还有几项其他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包括DESTINY-breast05和DESTINY-breast09,分别评估Enhertu在新辅助疗法后残留疾病HER2+BC患者中的使用或与当前一线标准护理方案在HER2+BC中的对比,再次展示了其成功。其他四个含有这种有前景的连接子-载荷的ADC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评估,用于治疗实体瘤,分别靶向NSCLC中的HER3、转移性结直肠癌和乳腺癌、TROP2在NSCLC和三阴性乳腺癌(TNBC)、B7-H3在晚期实体瘤或GPR20在胃肠道间质瘤(GIST)中(表1)。
最近,由于开发了能够绕过化合物的疏水性和促聚集特性的亲水性可切割连接子结构,exatecan(图2B)已经在临床前作为潜在的ADC载荷进行了探索。这允许在不干扰ADC药代动力学特性的情况下以高DAR值偶联exatecan(表1)。这些ADC在肿瘤异种移植物中展现了强大的抗肿瘤活性,并由于与DXd相比exatecan改善的被动细胞渗透性,与基于deruxtecan的ADC相比显示出更强的旁观者杀伤效应。目前正在开发两种使用这种药物连接子策略的ADC:PRO1184和PRO1160,分别含有亲水性exatecan基连接子,以DAR8偶联到抗FRa和抗CD70抗体,并预计将于2023年进入临床试验。最近的体内研究还表明,exatecan不需要呋喃环功能就能发挥其抗肿瘤活性,从而扩大了该分子的功能化可能性,以生成可连接的衍生物(表1)。使用这种策略开发的最有前途的ADC(mAbE-21a,衍生物11,DAR7.5)在EGFR+模型中以0.25 mg/kg剂量展现了显著的抗肿瘤活性,完全缓解。
今年披露了一种新型专有exatecan衍生物AZ’0132,正在作为ADC AZD8205的载荷进行研究,靶向B7-H4(表1,图2A)。AZD8205目前正在进行I/II期研究,用于治疗乳腺癌、卵巢癌和子宫内膜癌以及胆管癌(NCT05123482)。
2.2.伊立替康
伊立替康已获得FDA批准用于治疗各种实体瘤,如胃肠道恶性肿瘤、胶质母细胞瘤和宫颈癌,是拓扑异构酶1抑制剂SN-38的前药。SN-38水溶性差,会引起严重的毒性,包括强烈的骨髓抑制和高级别腹泻。因此,开发了伊立替康以改善生物利用度并获得可接受的治疗指数。IMMU-132(Trodelvy®)是一种抗TROP2抗体,与基于SN-38的药物连接子偶联(表1,图2A)。这种ADC已于2020年获得FDA批准用于治疗三阴性转移性乳腺癌和转移性尿路上皮癌,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用于治疗HR+/HER2-、前列腺和子宫内膜癌(NCT03725761和NCT04251416)。其他ADC也已开发出这种基于SN-38的连接子,包括IMMU-130(labetuzumab govitecan)[84–86]和IMMU-140,分别靶向CEACAM5和HLA-DR(表1)。Labetuzumab govitecan在I期(NCT01270698)中展现了可接受的毒性和活性,然而,II期评估在2020年因未公开原因终止(NCT01915472)。IMMU-140针对HLA-DR,在血液病和黑色素瘤中展现了有希望的临床前活性。SN-38载荷也在临床前评估中针对各种液体肿瘤(表1)。据我们所知,尽管临床前结果有希望,但这些ADC中没有一个进入临床试验,最近的相关出版物超过七年前。最近,为了治疗自身免疫疾病,绕过激素抵抗,开发了一种A7R-SN-38 ADC(表1)。
2.3.Belotecan衍生物
另一种拓扑异构酶1抑制剂KL610023,是FDA批准的分子belotecan的衍生物,正在作为ADC载荷进行研究。这种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被开发用于生成抗TROP2 ADC(SKB-264),目前正在进行I/II期临床试验(NCT04152499)治疗各种实体瘤的患者(表1,图2A)。
2.4.其他拓扑异构酶1抑制剂
作为ADC载荷的喜树碱衍生物的一个限制是分子内缺乏可连接的化学胺基团。为了在不改变其抗肿瘤性质的情况下在载荷内插入可连接的功能,已经合成了其他CPT衍生物(表1)。在这些衍生物中,cAC10的临床前研究,一种抗CD30抗体偶联到8个AMDCPT分子,显示出非常有希望的结果(图2B)。最近开发了几种非喜树碱衍生物,包括吲哚异喹啉、二苯萘吡啶酮和氟吲哚异喹啉(图2C)。这些分子显示出与CPT衍生物相比具有几个优点,包括更高的细胞毒性、改善的稳定性或延长的活性,并且目前正在作为小分子进行早期临床试验。LMP-517,与氟吲哚异喹啉偶联,正在被研究;然而,据我们所知,还没有数据被披露。
3.已经进入临床试验的载荷:承诺和失败
虽然拓扑异构酶1抑制剂深刻地改变了ADC载荷格局,但其他几个药物已经在临床试验中进行了评估。表2总结了在患者中评估的原始载荷。主要类别包括拓扑异构酶2抑制剂、RNA聚合酶抑制剂、Bcl-xL抑制剂和免疫刺激剂。此外,糖皮质激素现在作为超出肿瘤学适应症的ADC载荷出现了。
3.1.拓扑异构酶2抑制剂
拓扑异构酶2抑制剂在血液病恶性肿瘤和实体瘤的抗癌治疗中广泛使用。它们的机制复杂,可能不仅涉及直接抑制拓扑异构酶2活性,还包括DNA插入、ROS诱导和线粒体破坏。它们的毒性谱包括骨髓抑制、胃肠道毒性,在某些情况下还有高级别心脏毒性。多柔比星作为治疗乳腺癌、膀胱癌和甲状腺癌以及淋巴瘤和多发性骨髓瘤的一线治疗已经使用了几十年。多柔比星也是ADC开发中使用的第一批载荷之一,当时常规化疗小分子首次被偶联。第一个含有拓扑异构酶2抑制剂的ADC(SGN-15, BMS-182248)由多柔比星偶联到靶向Le-Y抗原的小鼠BR-96抗体(表2,图3)。SGN-15是在ADC发现的最初阶段与KS1/4-甲氨蝶呤(表2)一起在20世纪80年代开发的,用于治疗前列腺癌、乳腺癌和NSCLC。它的I期临床试验显示了可接受的耐受性,然而II期由于连接子不稳定和Le-Y靶标在正常组织中的表达导致了非靶向毒性。因此,ADC在可接受的剂量下缺乏效力。已经批准的化疗药物偶联观察到的令人失望的结果形成了共识,即ADC载荷应该比常规化疗药物更强效。这导致了第二代ADC的开发,它们被偶联到更强效的载荷上,如微管抑制剂和DNA损伤剂。
图3 展示了已经进入临床试验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的结构以及它们有效载荷(蓝色)的分类,这些有效载荷根据它们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类。图中注释:[ADC名称],抗体,有效载荷。
尽管早期开发不尽人意,多柔比星后来被偶联到靶向CD74的抗体milatuzumab(IMMU-110)用于治疗多发性骨髓瘤(表2,图3)。这种ADC被带到临床试验中,但显示出令人失望的效力,其开发在2013年被终止(NCT01101594)。此外,多柔比星还被用作ADC载荷在临床前连接子概念验证研究中(表3),它被偶联到一个新的可切割连接子(NEBI)或一个不可切割连接子(SMAC)。SMAC研究的结果表明,不可切割连接子对于基于多柔比星的ADC开发可能过于严格,因为没有观察到细胞毒性。
鉴于多柔比星作为ADC载荷的效力不足,另一种蒽环类药物PNU-159682,其细胞毒性是多柔比星的100倍,后来被探索。除了比其他拓扑异构酶2抑制剂更强效外,PNU-159682不是efux泵的底物。被发现是efux泵底物的载荷是ADC开发中的限制因素。2020年,一种基于PNU-159682的新型ADC,NBE-002(表2,图3),针对ROR1,进入I/II期临床试验(NCT04441099)。有趣的是,NBE-002诱导了长期免疫保护,这表明它可以成功地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结合。SOT102(前称SO-N102)是另一种有前景的基于PNU-159682的ADC,靶向CLDN18.2(表2,图3)。SOT102在低表达肿瘤中展示了大的治疗窗口,并已于2022年4月进入I期临床试验(EudraCT编号2021-005,873-25)。PNU-159682的许多临床前用途也被报道,结果证明了它能够绕过常用载荷如MMAE或DM1的抗性机制(表3)[110, 111, 114–118]。PNU-159682载荷还与MMAE一起偶联形成双药ADC(表3)。然而,尽管体外同时观察到了两种作用机制,但没有观察到协同作用。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临床前阶段也开发了柔红霉素和伊达比星的偶联物(表3,图4),但显示出降低的效力。一种抗HER2 afbody-idarubicin偶联物最近在体外进行了评估,具有特异性针对HER2阳性头颈鳞状细胞癌(HNSCC)细胞而不是HER2阳性BC细胞(表3)。
图4 非传统ADC有效载荷的化学结构图,这些有效载荷处于临床前阶段。
3.2.转录抑制剂
转录在细胞发展、活动和增殖中具有基本作用,因此可以构成ADC载荷的一个创新和原始靶标。转录由RNA聚合酶II(RNApolII)调节,它直接与DNA结合,并涉及转录因子,这些因子与RNApolII形成复合体以启动转录(如TFIIH)和共同调节因子(如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这些因子介导染色质结构和可及性。尽管一些HDAC抑制剂已经获得批准,但由于耐受性差,目前还没有批准的RNApolII抑制剂。
毒蝇伞素是从毒蝇伞蘑菇中提取的天然且高效的RNApolII抑制剂。α-毒蝇伞肽和β-毒蝇伞肽连同其他七种大环衍生物构成了毒蝇伞素家族。尽管它们作为实验室试剂广泛用于探索转录机制,但α-毒蝇伞肽被证明毒性太大,特别是对肝脏,以至于不能作为抗癌药物进一步开发。然而,这种分子作为潜在ADC载荷具有许多优点,包括其原始的细胞内靶标、其有利的物理化学性质(包括亲水性)、其对efux泵的不敏感性,以及其在静止癌细胞中产生细胞毒性的能力。相比之下,毒蝇伞肽的亲水性预计将阻止通过旁观者效应杀死邻近细胞,这可能限制其在均匀分布的靶标中的使用。即使在这些情况下,完全缺乏旁观者效应可能导致由于患者之间的靶标分布不同而导致效力不足。
毒蝇伞肽衍生物β-毒蝇伞肽最早在1973年与白蛋白偶联,这种ADC前体证明了选择性杀死巨噬细胞(表3)。后来,这个衍生物被偶联到抗MUC1和抗PSMA抗体上,在临床前模型中展示了强大的选择性细胞毒性(表3)。它的类似物α-毒蝇伞肽及其衍生物偶氮-毒蝇伞肽也很早就被用作ADC载荷(表3)。偶氮-毒蝇伞肽-ADC比未偶联的分子显示出大约500倍的细胞毒性。这可以通过分子的亲水性来解释,这种亲水性降低了细胞膜的渗透性,同时作为ADC结构被有效内化。截至2021年5月,第一个毒蝇伞肽-抗体偶联物(ATAC®)候选药物HDP-101已经进入早期临床试验(表2,图3)。HDP-101是一个针对BCMA的ADC,目前正在评估用于治疗多发性骨髓瘤和浆细胞疾病的患者(NCT04879043)。ATAC最近被描述为免疫激活药物。它们被发现可以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ICD),并与ICI表现出协同作用,这为临床环境中的组合可能性开辟了新的视野。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其他靶标的一些α-毒蝇伞肽ADC(EpCam、HER2、PSMA、CD19)在体外和体内都显示出强大的抗肿瘤活性(表3)。α-毒蝇伞肽还作为双弹头与MMAE偶联(表3)。这种DAR 1+1 ADC靶向FGFR1,在体外显示出强大的细胞毒性。其他高效的RNApolII抑制剂在20世纪90年代被偶联,如鬼笔环肽,以及霉菌毒素三烯醇、疣状菌素A和roridin A(表3,图4)。考虑到自90年代以来ADC设计的进步,以及这些化合物在各种细胞系中的纳摩尔细胞毒性,这些分子可能在未来几年成为进一步探索的对象。
另一种阻止DNA转录的策略是抑制转录因子(TFs)。TFs对RNApolII附着在DNA上的启动步骤至关重要。TF抑制剂(TFi)已经证明它们在临床试验中具有抗肿瘤活性,其中水溶性前药minnelide目前正在II期评估中(NCT04896073)。雷公藤内酯,一种来自被称为“雷公藤”的中草药的天然化合物,具有高度的细胞毒性,但也具有疏水性,具有较差的生物利用度和高毒性(图4)。因此,正在努力开发具有更好药物化学特性的类似物。另一种策略是将这种分子偶联到靶向实体上,从而绕过这些问题。雷公藤内酯最近首次被偶联到抗CD26抗体上,以靶向间皮瘤和淋巴瘤(表3)。这种不可切割的ADC在目标细胞中有效地停止了mRNA合成,并在体外和体内展示了有希望的抗肿瘤活性。还开发了一种针对EGFR阳性肺癌的cetuximab-triptolide ADC(表3)。这种ADC对EGFR过表达模型具有选择性,并比未偶联的雷公藤内酯具有更低的毒性。Cetuximab-triptolide有效地诱导了转录抑制,在体外和体内都具有强大的抗肿瘤活性。还评估了针对HER2的雷公藤内酯ADC,并取得了类似的结果。然而,对于每种基于雷公藤内酯的ADC,都需要高剂量才能在异种移植模型中观察到抗肿瘤活性,这些论文中没有报告最大耐受剂量,从而质疑了治疗指数的宽度。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s)影响转录因子,因此参与包括转录在内的各种细胞过程。它们被发现在癌细胞中过度表达或过度激活,并被认为参与增加增殖、迁移和侵袭。Vorinostat和dacinostat是FDA批准的两个HDAC抑制剂(HDACi)的例子。然而,这些分子呈现出强烈的系统性副作用风险,如血小板减少和胃肠道毒性,以及较差的药代动力学(PK)特性。自2018年以来,它们已经在ADC设计中进行了研究:ST74612AA1是第一个生物偶联的HDAC抑制剂(表3,图4)。这种相对无毒的分子是第二代泛HDACi。这种分子被偶联到cetuximab和trastuzumab上,两种ADC都比未偶联的HDACi具有更安全的特性,同时在细胞系衍生的异种移植(CDX)和患者衍生的异种移植(PDX)模型中都具有活性。然而,正如观察到的基于TFi的ADC一样,异种移植模型接受了30 mg/kg的高剂量治疗。2020年,vorinostat和dacinostat也被偶联到cetuximab和trastuzumab上,在体外具有有趣的抗增殖活性(表3,图4)。
3.3.Bcl-xL抑制剂
Bcl-2家族成员可能是促凋亡蛋白(Bad、Bim、PUMA、Bik、Bak等)或抗凋亡蛋白(Bcl-2、Bcl-xL、Bcl-w、Mcl-1等)。在癌细胞中,这些蛋白之间的平衡通常倾向于生存,使得抗凋亡蛋白成为创新ADC载荷的有趣和原始靶标。
根据它们的化学功能骨架,Bcl-xL和Bcl-2抑制剂被分类为4大家族:N-酰磺胺类(navitoclax、venetoclax)、吲哚类(obatoclax)、棉酚乙酸(AT-101、sabutoclax)和苯并噻唑腙类(如WEHI-539)。Bcl-xL的抑制与严重的血小板减少有关,这证明了寻找高度特异性Bcl-2抑制剂的合理性,如venetoclax。目前venetoclax已获批准用于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一个亚组患者和急性髓系白血病。
ABBV-155(mirzotamab clezutoclax)是一种抗B7-H3抗体,与Bcl-xL抑制剂clezutoclax偶联(表2,图3)。这种创新ADC于2018年进入正在进行的I/II期临床试验,作为单一药物用于晚期实体瘤的治疗,以及与紫杉醇联合用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乳腺癌患者(NCT03595059)。在单一药物I期队列中包含的前31名患者中没有报告剂量限制毒性,SAEs包括贫血、淋巴细胞计数下降、疲劳和腹泻。在紫杉醇组合臂中观察到21%的患者部分缓解。
3.4.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人类激酶组包含超过500个激酶,其中150多个与各种疾病相关,包括癌症。蛋白激酶是催化磷酸化的酶,分为3类:丝氨酸、苏氨酸或酪氨酸激酶。目前正在临床试验中研究的小分子中超过四分之一是蛋白激酶抑制剂,超过30个FDA批准的癌症治疗分子是激酶抑制剂。在癌症中,各种激酶家族参与细胞周期进展、细胞增殖、运动和血管生成。自2001年首个激酶抑制剂伊马替尼获批以来,激酶抑制剂被分为5类:I型和II型是ATP竞争性,分别针对激酶的活性或非活性形式;III型结合ATP的变构口袋;IV型结合激酶的变构口袋,V型结合多种结合模式。
虽然在癌症治疗中被广泛探索,但蛋白激酶抑制剂作为ADC载荷并未被广泛探索,可能是因为它们的效力较低。抗CD19抗体B43已与染料木素(一种含有大豆异黄酮的植物雌激素)偶联,发现它通过抑制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一种酪氨酸激酶受体,诱导凋亡和细胞增殖抑制(表2,图3)。体外和体内的临床前研究(小鼠、大鼠、非人灵长类:NHP)表明在100 mg/kg的累积剂量下没有毒性,并且在小鼠模型中比标准化疗具有更强的抗肿瘤效果。这些有希望的结果导致了它在1999年首次用于治疗ALL和NHL的人体研究。除了在人类中呈现有利的药代动力学特性外,没有报告毒性和有希望的抗肿瘤活性。不幸的是,这种化合物的状态此后没有进一步报告(NCT00004858)。另外两项研究调查了染料木素偶联到抗EGFR或17.1A mAb的抗肿瘤活性,后者针对上皮膜抗原(表3)。抗EGFR-染料木素ADC在高达140 mg/kg的剂量下显示出良好的耐受性,在临床前模型中1 mg/kg时显著的抗肿瘤活性。17.1A-染料木素被发现比未偶联的染料木素在结肠癌模型中更活跃。
最近,另外三种激酶抑制剂被评估为ADC载荷。这些分子包括neolymphostin(一种PIKK抑制剂),dasatinib和staurosporine,两种多激酶抑制剂(表3,图4)。Trastuzumab neolymphostin展示了选择性和体外细胞毒性,尽管比其他常用的基于trastuzumab的ADC效力较低。一种与dasatinib偶联的抗CXCR4 mAb选择性地将dasatinib输送到目标T细胞,并展示了强大的免疫抑制效果。最后,广泛使用的实验室试剂和多激酶抑制剂staurosporine被偶联到cetuximab,用于治疗KRAS/BRAS突变的结肠癌细胞。总的来说,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在ADC格式中的效力有限,这个家族可能不会在更高级的设置中成功。
3.5.免疫刺激抗体偶联物
免疫刺激抗体偶联物是一类新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目前有2个ADC正在进行临床试验(表2,图3)(NJH395,BDC-1001),另一个SBT6050,由于赞助商的战略决策,其临床评估已被终止(NCT05091528)。STING激动剂和TLR激动剂构成了两类主要的偶联免疫刺激剂。
针对适应性免疫系统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成功极大地增强了利用先天免疫系统刺激的努力。然而,最有力的剂如STING和TLR激动剂的系统性给药与严重的系统毒性相关,由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引起,从而将当前研究限制在肿瘤内注射。它们与蛋白质或mAbs的偶联因此是利用它们强大的抗肿瘤潜力同时改善耐受性配置文件的有希望的手段。
几种含有TLR激动剂的免疫刺激ADC目前正在临床环境中进行评估。NJH395,结合了一个小分子TLR7/8激动剂和抗HER2 mAb,是第一个达到临床评估的(表2,图3)。在18名非乳腺癌HER2+恶性肿瘤患者的I期临床试验(NCT03696771)中,发现严重的毒性,包括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和淋巴细胞耗竭,没有显著的抗肿瘤活性。同样,BDC-1001,一种由抗HER2抗体与TLR7/8激动剂偶联的免疫刺激偶联物,目前正在进行I/II期评估,作为单一药物或与nivolumab联合用于治疗实体HER2+肿瘤的患者(NCT04278144,表2,图3)。它的临床前评估显示了强大和持久的免疫介导的抗肿瘤效力,并且临床评估显示出有希望的结果,包括在测试剂量下没有毒性和临床活性的证据。上述TLR7/8类似物也被偶联到抗PD-L1抗体,旨在结合免疫检查点抑制、抗体依赖性细胞吞噬作用(ADCP)和肿瘤内髓系重编程。这种免疫刺激ADC在临床前模型中优于抗PD-L1的抗肿瘤活性。SBT6050是一种pertuzumab-TLR8激动剂偶联物,目前正在作为单一药物以及与抗PD1抑制剂(NCT04460456)和与trastuzumab deruxtecan联合用于治疗HER2阳性实体癌(NCT05091528)进行评估。Pertuzumab不与trastuzumab结合相同的HER2表位,研究表明trastuzumab和SBT6050之间存在协同潜力。
已经报告了其他免疫刺激ADC的有希望的临床前结果,它们分别与UC-1V150、CL264或T785 TLR 7/8激动剂偶联(表3,图4)。最近披露了一种与TLR7/8激动剂D18偶联的抗PD-L1,其中包括在B16黑色素瘤模型中具有强大的抗肿瘤活性,该模型对PD1有抗性(表3,图4)。最近,作为一种免疫刺激ADC载荷,研究了一种更具选择性的激动剂,即TLR7激动剂。另一类新兴的免疫刺激剂载荷是STING激动剂。TAK-500是第一个进入临床试验的STING激动剂免疫激活ADC,目前正在招募患者(NCT05070247)。这种针对CCR2的ADC(TAK-676)正在评估用于治疗实体瘤(表2,图3)。此外,还有三种STING偶联的ADC正在进行临床前阶段的开发:CDR-550、XMT-2056和最近一种针对FcγR的免疫刺激ADC,与STING激动剂XMT-1621偶联(表3)。最先进的XMT-2056(STING激动剂:XMT-1621,图4)在小鼠异种移植中以1 mg/kg剂量导致肿瘤完全缓解,并在非人灵长类中耐受,没有临床迹象或不良组织病理学发现,并且与ICI显示出协同活性。这种有希望的ADC应该在2022年进入首次人体研究的临床试验。
4.在临床前阶段的非传统载荷
由于肿瘤细胞具有增加的合成活性,几种载荷候选物已经针对蛋白质合成的各个步骤进行了靶向,包括转录、剪接和翻译抑制剂以及蛋白质分解。另一种方法是针对在肿瘤细胞中过度活跃的其他普遍存在的细胞过程。然而,只有经过精心设计的ADC才能支持这类载荷,因为即使肿瘤中的ADC浓度高于周围组织,大多数静脉注射的化合物并没有定位到肿瘤。
4.1.HSP90抑制剂
HSP90(热休克蛋白90)是一种主要的分子伴侣蛋白,已被证明在多种肿瘤中异常表达。已经开发并测试了几种源自格尔德霉素(GA,图4)骨架的HSP90抑制剂在临床环境中。抑制剂与HSP90结合后,阻止其保护其客户蛋白免受蛋白酶体降解的能力。迄今为止发现的主要限制是显著的剂量限制毒性和不良的药代动力学特性。在21世纪初,人们努力化学修饰GA,合成了一种适合生物偶联的马来酰亚胺可切割药物连接子(表3)。结果产生的trastuzumab-GA ADC与用trastuzumab治疗的小鼠相比,提高了荷瘤小鼠的整体生存率。Streptonigrin和17-aminogeldanamycin被用于在DAR4处产生抗CD70和抗CD30可切割ADC,并在临床前模型中被发现活性(表3)。GA在载荷领域中的最近复苏重新定位了这种分子,通过生成一种HER2 scFv HBD/GA ADC,在HER2阳性肺癌临床前模型中展示了抗肿瘤活性(表3)。
4.2.剪接抑制剂
转录后,前mRNA通过剪接体去除内含子,加工成成熟的mRNA。snRNPs(小核糖核蛋白)U1、2、4、5和6构成了剪接体的主要snRNPs。这些复合体对成熟mRNA的生成至关重要,并且在癌细胞中通常被调节异常。靶向U2的SF3B1亚基已被证明可以有效地抑制剪接。已经发现几种药物是有效的剪接抑制剂,包括pladienolides、spliceostatins和thailanstatins。然而,这些高度细胞毒性分子的IC50s在纳摩尔范围内,由于化学不稳定性而没有进一步开发。E7107,一种pladienolide类似物,在临床试验中进行了评估(NCT00499499),但由于安全问题,特别是严重的眼部毒性,已停止使用。Tailanstatin A-trastuzumab偶联物在临床前模型中显示出高度活性,某些体内模型中的效力大于T-DM1(表3,图4)。
4.3.翻译抑制剂
开发可耐受的翻译抑制剂已被证明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翻译在健康组织中的普遍重要性。Omacetaxine(之前指定为homo-harringtonine)是第一个获得FDA批准的翻译抑制剂,它干扰蛋白质合成的初始延伸步骤。已经开发了其他几种翻译抑制剂用于治疗各种癌症,靶向核糖体、EIFs(真核生物翻译启动因子)或mTOR。迄今为止,只有pymberin被用作潜在的ADC载荷(表3,图4)。Pymberin,也称为irciniastatin A,是一种从海绵中分离出的天然碳水化合物。它通过β-葡萄糖醛酸苷连接子与抗CD30和抗CD70抗体偶联,在体外展示了选择性和抗增殖活性,IC50s在亚纳摩尔范围内。
4.4.蛋白酶体抑制剂
蛋白酶体抑制剂是一种极其有效的抗癌剂。Bortezomib在2003年被批准用于治疗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从那时起显著改善了患者的预后。已经开发出几种其他抑制剂,具有减少神经毒性和/或允许口服给药的特点。环氧酮衍生物,如卡马霉素B类似物,强烈抑制20S蛋白酶体,已被结合到曲妥珠单抗上(表3,图4)。尽管未结合的有效载荷在体外细胞毒性方面令人满意,但相应的ADC(抗体药物偶联物)证明比基于MMAE的ADC效力要低。
4.5.PROTACS
靶向蛋白降解的嵌合分子(PROTACs)是双功能分子,它们将E3连接酶与目标蛋白结合在一起,从而允许其泛素化并通过蛋白酶体降解。PROTACs不是直接抑制其目标蛋白,而是触发其降解,具有几个潜在的临床优势,如延长效果、催化活性,因此具有非常强的细胞毒性。降解剂-抗体偶联物(DACs)构成了ADC领域中一个令人兴奋的新兴家族。在DAC设计中,PROTACs可以从被mAb(单克隆抗体)内部运输到细胞中获益,以克服它们有限的细胞渗透性。当前DACs的构建、生物活性和挑战已在最近的综述中报道。BRD4/BET降解剂GNE-987被结合到抗CLL1抗体上,导致恢复了药代动力学特性,并在小鼠异种移植中显示出强大的体内活性(表3,图4)。MZI类似物结合到曲妥珠单抗或抗STEAP1抗体也被评估了体外,证明了选择性BRD4降解和细胞毒性(表3,图4)。其他包含VHL或CRBN配体的BRD4降解剂-抗体偶联物最近也被生成了(表3,图4)。同样,雌激素受体(ER)、TGFbR2和BRM降解剂正在作为DAC有效载荷进行研究,通过结合到抗HER2、抗B7-H4和/或抗CD22抗体(表3,图4)。ORM-5029,最新披露的DAC或抗体新降解剂偶联物(AnDC™),旨在通过Pertuzumab将GSPT1降解剂(Smol006)输送到HER2表达细胞。这种AnDC™显示出比其他GSPT1降解剂更强的细胞毒性和与DS-8201a相当的抗肿瘤活性。ORM-5029的毒性目前正在研究中,结果将构成关于DACs治疗窗口的首次报告。
4.6.其他分子
有效载荷多样化的努力导致了最近非传统抗体-药物偶联物的临床前开发,这些偶联物提供具有独特作用机制的有效载荷。通过靶向烟酰胺磷酸核糖基转移酶抑制剂(NAMPTs)改变细胞代谢构成了一种新颖而原创的ADC技术。FK-866类似物被结合到抗CD30抗体上,随后的ADC在体外和体内选择性地耗尽了NAD(表3,图4)。CD30-NAMPTi在L540cy模型中以3 mg/kg剂量显示了有希望的体内抗肿瘤活性,实现了完全缓解。在大鼠中,以100 mg/kg以上的MTD(最大耐受剂量)勾勒出了有利的治疗指数。其他NAMPTis也被合成并结合到针对c-Kit的mAb。尽管在体外具有选择性和强大的细胞毒性(亚纳摩尔IC50s),这些不可切割的ADC在体内活性中等,仅在20 mg/kg剂量下实现了部分反应。
KSP(动力蛋白纺锤体蛋白)抑制剂,也称为Eg5抑制剂,构成了一个新兴的ADC有效载荷家族。Eg5是抗肿瘤治疗的一个有希望的靶点,因为它的表达仅限于增殖细胞,并且不在神经系统细胞中表达。因此,这些有效载荷不应该呈现与微管靶向剂相关的经典神经系统副作用。KSP抑制防止了细胞分裂期间的中心体分离,从而导致有丝分裂停滞。KSP抑制剂衍生物,具有亚纳摩尔效力,被结合到HER2和TWEAKR/Fn14靶向抗体(表3,图4)。TWEAKR-KSPi ADC在尿路上皮PDX中实现了完全缓解,而小分子KSP抑制剂ispinesib仅在这个模型中延缓了肿瘤生长。通过与flanesib结合,也生产了ADC,具有可接受的PK特性和良好的体内效力。
5.结论
抗体-药物偶联物已成为治疗日益增多的癌症指征的重要组分,并且正在进行数百项临床试验以探索新的靶点和指征。ADC领域取得的惊人进展主要得益于将它们的设计量身定制到特定靶点上。这得益于几项成就,包括(1)对越来越多靶点的探索和验证,(2)专为ADC设计而进行的mAbs(单克隆抗体)的适当筛选,重点关注交叉反应性、pH变化帮助下的优先肿瘤结合、降低到低纳摩尔范围的亲和力以避免粘性并促进内化和FcRn循环,(3)结合技术的进步,使药物-抗体比率更高,和/或恢复裸mAb样的药代动力学特性,以及(4)有效载荷的多样化(如图5所示),正如最近通过拓扑异构酶1抑制剂取得的突破所例证。
图5 展示了ADC有效载荷的靶标景观图,这些靶标超出了微管和DNA插入剂的范围。注释:FDA批准的ADCs,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ADCs。
在未来的发展中,具有原创作用机制的有效载荷的持续多样化预计将发挥关键作用。在晚期疾病中,通常通过结合具有互补作用机制的药剂来实现治愈,并且尽可能地结合非冗余的毒性。虽然目前批准的ADC拥有与传统化疗药剂相似的作用机制,但未来的有效载荷可能会针对迄今为止因毒性过大而难以处理的关键细胞现象。正如以前观察到的,与可切割链接物结合的auristatins和maytansinoids,topo-1 ADCs的旁观者效应已经证明了其对低或异质性肿瘤治疗的有效性,并且应该在后续开发中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些新型有效载荷的另一个主要优势可能在于它们能够针对静止的肿瘤细胞,这些细胞构成了患者肿瘤储备的大部分。此外,在新兴的有效载荷家族中,目前与严重副作用相关的几种激酶抑制剂将从更大的治疗指数中受益。就PROTACs而言,它们受益于亚化学计量活性,理论上可以降低细胞毒性的有效载荷阈值。
有效载荷的多样化也预示着ADC治疗武器库向尚未从靶向治疗中受益的其他癌症的开放。Sacituzumab govitecan导致TROP2在TNBC中的验证,而正在进行临床评估的基于SN-38的ADC突出了在ADC领域中代表性不足的癌症类型中的新靶点的潜力(HER3、CEACAM5、B7-H3和GPR20)。有趣的是,针对TNBC的临床试验展示了越来越多的包含原创有效载荷的抗体-药物偶联物,包括Dxd、PNU-159682和SN-38。
正如我们在这篇综述中所描述的,已经确定了几个潜在的有效载荷,并且许多已经显示出有希望的临床前结果。其中一些化合物已经进入临床试验,但由于毒性特征不满意而没有继续进行。在这方面,应该强调的是,主要的技术进步,特别是安全获取高药物-抗体比率的ADC的可能性,支持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在ADC生产和表征不够理想的时候探索的有效载荷应该用目前可用的技术重新考虑。
整合原创有效载荷的新ADC格式,如双重有效载荷(表3)、治疗诊断和非内化偶联物,在最近的临床前研究中显示出巨大潜力,可能构成ADC研究中不断增长的领域。非内化ADC将特别受益于具有强烈旁观者杀伤效应或针对细胞外或基质靶点的新型有效载荷,正如基于PNU-159682的ADC针对tenascin-C、基质金属蛋白酶细胞外蛋白的抑制或最近的碳酸酐酶抑制(表3)。有趣的是,ADC技术也在非肿瘤学指征中被探索。两种原创ADC(ABBV-3373和ABBV-154),含有糖皮质激素受体调节剂(GRM),正在临床评估用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克罗恩病(表2, NCT03823391, NCT04888585, NCT05068284和NCT04972968)。其他免疫学ADC有效载荷正在临床前环境中进行研究,并可能构成ADC设计中的新兴类别。此外,一种在临床前评估中显示出有希望结果的A-利福霉素衍生物,已经在患有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血症的患者中进行了1期临床试验(NCT03162250)。非细胞毒性有效载荷也进入了有效载荷领域,例如通过将肝X受体(LXR)激动剂结合到抗CD11b抗体来针对脂质代谢的细胞内靶向,用于治疗动脉粥样硬化(表3)。
尽管符合条件的疾病范围扩大了,但开发这些新型有效载荷的一个关键问题将是减轻它们的副作用。目前批准的ADC已经显示出它们与预期的(骨髓抑制、神经毒性)或意外的(如眼部或肺部)毒性相关。因此,获得令人满意的治疗指数将是未来创新ADC有效载荷发展的基本属性。
识别微信二维码,添加生物制品圈小编,符合条件者即可加入
生物制品微信群!
请注明:姓名+研究方向!
版
权
声
明
本公众号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且明确注明来源和作者,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cbplib@163.com),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所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抗体药物偶联物
分析
对领域进行一次全面的分析。
登录
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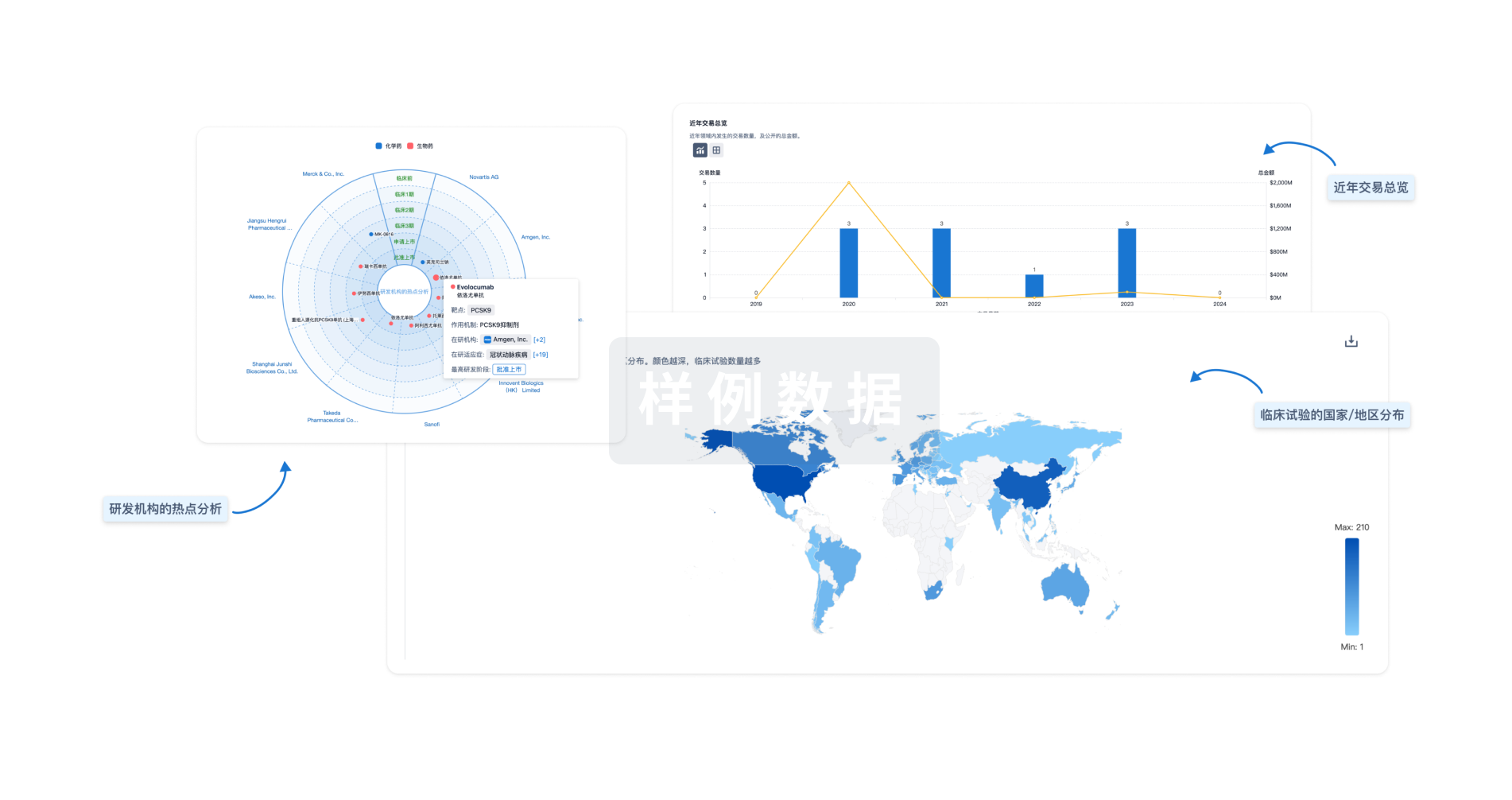
生物医药百科问答
全新生物医药AI Agent 覆盖科研全链路,让突破性发现快人一步
立即开始免费试用!
智慧芽新药情报库是智慧芽专为生命科学人士构建的基于AI的创新药情报平台,助您全方位提升您的研发与决策效率。
立即开始数据试用!
智慧芽新药库数据也通过智慧芽数据服务平台,以API或者数据包形式对外开放,助您更加充分利用智慧芽新药情报信息。
生物序列数据库
生物药研发创新
免费使用
化学结构数据库
小分子化药研发创新
免费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