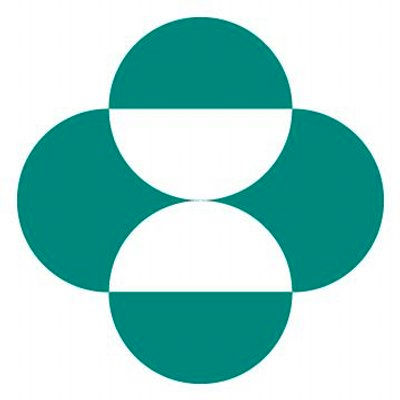预约演示
更新于:2026-02-07
FPX-01(Fusion Pharmaceuticals, Inc.)
更新于:2026-02-07
概要
基本信息
在研机构- |
最高研发阶段终止临床1期 |
首次获批日期- |
最高研发阶段(中国)- |
特殊审评- |
登录后查看时间轴
结构/序列
使用我们的ADC技术数据为新药研发加速。
登录
或

Sequence Code 1929CDR1-H

Sequence Code 1945CDR3-H

Sequence Code 1951CDR1-L

Sequence Code 1956CDR2-L

Sequence Code 17588685CDR3-L

Sequence Code 319467417VL

Sequence Code 319467418CDR2-H

Sequence Code 319467419VH

关联
1
项与 FPX-01(Fusion Pharmaceuticals, Inc.) 相关的临床试验NCT03746431
A Phase 1 Study of [225Ac]-FPI-1434 Injection in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or Metastatic Solid Tumours
This is a first-in-human Phase 1/2, non-randomized, multi-centre, open-label clinical study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safety, tolerability, PK, and preliminary anti-tumour activity of [225Ac]-FPI-1434 (radioimmuno-therapeutic agent) in patients with solid tumours that demonstrate uptake of [111In]-FPI-1547 (radioimmuno-imaging agent), and to establish the maximum tolerated dose (MTD) and/or the recommended Phase 2 dose (RP2D) of repeat doses of [225Ac]-FPI-1434 Injection in patients with solid tumours that demonstrate uptake of [111In]-FPI-1547 (radioimmuno-imaging agent).
开始日期2019-01-17 |
申办/合作机构 |
100 项与 FPX-01(Fusion Pharmaceuticals, Inc.) 相关的临床结果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100 项与 FPX-01(Fusion Pharmaceuticals, Inc.) 相关的转化医学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100 项与 FPX-01(Fusion Pharmaceuticals, Inc.) 相关的专利(医药)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82
项与 FPX-01(Fusion Pharmaceuticals, Inc.) 相关的新闻(医药)2026-01-15
·小触核药
导 语
Introduction
近日,通瑞生物制药(成都)有限公司(通瑞生物)研发的1类放射性治疗药物“TRC003注射液”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默示许可,同意开展拟用于治疗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SMA)阳性的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的成年患者的临床研究。
在去年10月份的欧洲核医学大会(EANM 2025)上,由通瑞生物支持的两项关于225Ac-PSMA-CY313在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领域的研究,凭借其创新性与重要价值,获大会评审委员会高度认可,被评选为 “Top Rated Oral Presentation”(最受欢迎的口头报告) 。因此,推测此次申报很可能为该公司首款Ac-225核素的放射性治疗药物。
在Ac-225供应有望改善的预期下,全球制药巨头和创新生物技术公司早已开始争相布局基于Ac-225的靶向放射性药物。全球范围内,Ac-225核药的研发正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据统计,截至2025年,全球已有超过70条Ac-225核药研发管线,其中超过20项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从前列腺癌到血液肿瘤的多种恶性疾病,其中不乏已进入临床II/III期研究的重磅候选药物 。
前列腺癌:最热门的战场
前列腺癌是Ac-225核药研发最为集中的领域,主要靶点是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SMA),这是一种在绝大多数前列腺癌细胞上高表达的蛋白质。
[225Ac]Ac-PSMA-617 (Pluvicto-α):这是诺华(Novartis)公司在其已上市的β粒子药物Pluvicto([177Lu]Lu-PSMA-617)基础上开发的α粒子版本。理论上,Ac-225的强效杀伤力有望克服对β粒子疗法产生耐药性的肿瘤,或对恶性程度更高的肿瘤提供更优的治疗效果。目前,诺华的[225Ac]Ac-PSMA-617注射液正在全球多地开展临床试验,包括针对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患者的I/II期研究 。其在中国的临床试验申请也已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受理 。这是最受关注、也最接近商业化的Ac-225药物之一。
[225Ac]Ac-J591:由Weill Cornell Medicine和Actinium Pharmaceuticals联合开发,靶向PSMA的胞外域。该药物在早期临床试验中已显示出令人鼓舞的疗效,尤其是在mCRPC患者中观察到了显著的PSA(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水平下降和肿瘤消退。目前正在进行更深入的临床评估 。
[225Ac]Ac-PSMA-I&T:这是一种基于PSMA抑制剂的靶向配体,由慕尼黑工业大学等机构率先开展临床研究,同样在mCRPC患者中显示了高缓解率。多项学术研究和临床试验正在评估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
实体瘤的广泛探索
除了前列腺癌,Ac-225核药的研发也扩展到了其他多种实体瘤。
神经内分泌肿瘤(NETs):靶向生长抑素受体(SSTR)是治疗NETs的成熟策略。基于Ac-225的SSTR靶向药物,如[225Ac]Ac-DOTATATE,被认为是现有Lu-177标记的SSTR药物(如Lutathera)的有力补充或后续治疗选择,尤其适用于对β粒子疗法不敏感或复发的患者,评估其在晚期NETs患者中的应用 。
[225Ac]Ac-FPI-2265:由Fusion Pharmaceuticals(已被阿斯利康收购)开发,是一款靶向神经降压素受体1型(NTR1)的Ac-225药物,用于治疗表达NTR1的实体瘤,正在进行进入II/III期临床试验。
[225Ac]Ac-FPI-2059:由Fusion Pharmaceuticals(已被阿斯利康收购)开发,靶向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受体(IGF-1R),正在进行针对多种实体瘤的I期临床试验 。
RYZ101([225Ac]Ac-DOTATATE):RayzeBio(已被BMS收购)的RYZ101([225Ac]Ac-DOTATATE)已进入III期临床,目前因同位素供应短缺被迫暂停,是进展最快的Ac-225药物之一 。
针对乳腺癌 、非小细胞肺癌等的Ac-225核药也在临床探索中。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
Ac-225同样在治疗白血病等血液肿瘤方面显示出潜力。
Lintuzumab-Ac225 (Actimab-A):由Actinium Pharmaceuticals公司开发,Lintuzumab是一种针对CD33的单克隆抗体,与放射性同位素Ac-225结合,形成Lintuzumab-Ac-225,CD33在大多数AML细胞上表达,以增强对AML细胞的打击能力。该药物已完成多项I/II期临床试验,并正在探索与其他药物的联合治疗方案 。
目前,全球Ac-225核药研发领域呈现出大型制药公司(通过收购)与创新生物技术公司并驾齐驱的格局。
· 诺华(Novartis)
2024年5月初,诺华宣布收购核药生物技术公司Mariana Oncology,诺华支付10亿美元预付款,以及7.5亿美元里程碑付款。Mariana的首发管线MC-339,是用于治疗小细胞肺癌的靶向核药。该候选药物由一种肽类小分子组成,经设计可携带放射性锕(Ac)有效载荷。此外,凭借其在PSMA靶向核药领域的深厚积累,其下一代核药225Ac-PSMA-617目前处于全球Ⅰ期阶段,用于治疗前列腺癌。
· 百时美施贵宝(BMS)
2024年初,百时美施贵宝(BMS)宣布完成了对RayzeBio的收购。此次收购的交易总额约为41亿美元,每股现金价格为62.50美元。将其进展最快的Ac-225药物之一RYZ101收入囊中,强势入局 。24年12月中百时美施贵宝重新取得了ABZ-706(相当于RYZ801)在大中华区开发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该管线靶向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PC3),用于基于Ac的放射性疗法治疗肝细胞癌,目前正在进行IND研究。
· 礼来(Eli Lilly)
2023年10月礼来以14亿美元收购Point Biopharma,获得了Ac-225的泛癌FAP-α项目PNT2004及PSMA项目PNT2001。2024年5月礼来与Aktis Oncology达成了一项价值高达11亿美元的协议。Aktis Oncology是一家专注于开发新型α核素(靶向疗法的生物技术公司,该合作强化了礼来在α核素药物平台的能力。2024年6月底日,礼来与Radionetics Oncology达成战略合作,将共同推进靶向GPCR的小分子放射性药物。2025年2月礼来又与AdvanCell扩大合作,共同开发靶向α核素疗法。
· 阿斯利康(AstraZeneca)
2024年3月阿斯利康以高达2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Fusion Pharmaceuticals,进入了放射性药物领域。Fusion是一家专注于精准核药开发的公司,利用α粒子的医学同位素,结合靶向癌细胞的抗体,精准狙击癌细胞。Fusion的管线资产包括225Ac-PSMA I&T(FPI-2265),225Ac-FPI-1434和FPI-2059等。这些项目针对前列腺癌、实体瘤等多种癌症类型,并处于不同的临床试验阶段。其中,FPI-2265为核心项目,在mCRPC患者的的治疗中显示出显著优势。此外,阿斯利康与海德堡大学和Euratom达成基于锕系元素的PSMA靶向放疗的全球独家许可协议。
· 拜耳(Bayer)
早在2009年就与Algeta合作开发Xofigo,并于2013年获批上市,用于治疗晚期骨转移型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Xofigo上市后,销售额在2017年达到峰值(4.08亿欧元),后续开始逐年下滑。2023年5月拜耳与Bicycle Therapeutics达成战略合作,Bicycle将获得4500万美元的预付款,如果达到开发和商业化的里程碑,Bicycle可能获得总计高达17亿美元的款项;拜耳可获得Bicycle的专有肽,用于开发下一代靶向放射治疗,增强肿瘤相关研发管线。目前拜耳有两款核药225Ac-macropa-pelgifatamab (BAY3546828) 和225Ac-PSMA-Trillium(BAY 3563254),两款核药采用的核素均为Ac-225。
· 强生(Johnson & Johnson)
2017年,强生JJDC(Johnson & Johnso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通过领投Fusion Pharmaceuticals的2500万美元A轮融资,开始入局核药。2024年,Abdera完成了一轮新的融资,该轮融资由强生JJDC和Foresite投资,金额为3000万美元。
除投资外,目前强生公开的管线来看,首发核药资产是一款靶向HK2的核药JNJ-6420,采用的核素同样是Ac-225。
“
Actinium Pharmaceuticals
专注于α粒子疗法,拥有丰富的临床管线,尤其是在血液肿瘤领域 。
“
Clarity Pharmaceuticals
拥有独特的“SARTATE”螯合技术,并与Terra Power等供应商建立了稳固的Ac-225供应关系 。
“
Ariceum Therapeutics
主打药物225Ac-SSO110是一种锕-225标记的放射性药物,靶向SSTR2。该药物通过将Ac-225与特异性靶向肽结合,精准作用于表达SSTR2的肿瘤细胞,如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和默克尔细胞癌(MCC),旨在实现高效肿瘤杀伤同时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损伤。
“
Defence Therapeutics
与加拿大核实验室(CNL)合作,将α粒子放射疗法Ac-225与Defence专有的Accum®递送技术相结合,进行临床前研究。
“
Abdera Therapeutics
依托先进的抗体工程 ROVEr™平台设计和开发用于癌症治疗的可调节精准放射性药物。Abdera的主要项目ABD-147是下一代精准放射性药物生物疗法,旨在将Ac-225递送至表达DLL3的实体瘤,用于治疗小细胞肺癌(SCLC)和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LCNEC)。
“
Ratio Therapeutics
专有研发平台Trillium™和Macropa™,使得开发具有药物动力学调制能力的适配异功能放射性药物,从而提升药物的可用性、肿瘤传递和肿瘤载荷。近日宣布,其首款核心治疗性放射药 [Ac-225]-RTX-2358 临床试验的首个队列已完成给药。该药物是一种高选择性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靶向放射治疗药物,以Ac-225为标记同位素,适用于治疗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阳性的复发或难治性软组织肉瘤患者。
“
Convergent Therapeutics
凭借对α粒子的了解和双靶向放射性核素治疗技术的灵活运用,已经开发了其主要管线产品CONV01-α(Ac-225 rosopatamab tetraxetan),是一种专有的、同类最佳的Ac-225标记放射抗体,靶向几乎所有前列腺癌细胞表面表达的蛋白质(抗原)。
“
Alpha-9 Oncology
Alpha-9的平台建立在系统性的分子设计方法之上,通过优化靶向配体、连接子和螯合剂,创造出在肿瘤中具有优异摄取和滞留能力,同时能最大限度减少脱靶效应的放射性治疗药物。Alpha-9的核心管线A9-3408是一种新型靶向黑色素皮质素1受体(MC1R)的Ac-225核素药物,用于治疗经标准疗法治疗后病情进展的MC1R阳性黑色素瘤患者,已于近日完成首例患者给药。
尽管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 Ac-225 药物研发方面仍处于相对早期的阶段,但也在稳步行进中。
○
东诚药业控股的子公司蓝纳成(LNC)开发的[225Ac]Ac-LNC1011注射液,在2025年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核准签发的药品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该药物拟用于治疗PSMA阳性表达的晚期前列腺癌患者。
○
辐联科技是一家具有国际背景的中国公司,[225Ac]Ac-FL-020注射液已于11月10日获得临床试验默示许可,拟用于治疗mCRPC。辐联科技的另一款AC-225产品FL-091已经在2024年7月授权给SK Biopharmaceuticals,该产品用于治疗靶向神经降压素受体1型(NTSR1)阳性的癌症。此次交易的总金额高达5.72亿美元,涵盖了首付款、研发及商业里程碑付款。此外,多条管线均涉及Ac-225核素。
○
诺宇医药布局了多条核药管线,其中涉及Ac-225核药研发管线,根据官网,目前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暂未有更多消息披露。
○
先通医药也在使用Ac-225进行早期的药物研发,该公司在成都温江的研发生产基地已经建成了全自动放射性药物生产线,并计划生产225Ac-抗体注射液。
○
威智知科研发管线中的225Ac-PSMA-VG01和225Ac-FAP-VG02均采用了Ac-225作为放射性核素,针对前列腺癌、纤维肉瘤激活蛋白(FAP)表达肿瘤等进行研发。
○
博锐创合官网在研管线中BRP-020、BRP-030与BRP-040项目明确提及使用Ac-225作为放射性核素,适应症为晚期实体瘤。
○
纽瑞特医疗官网显示有Ac-225采购相关的字样。根据公开信息,纽瑞特也在积极布局Ac-225等α核素药物的研发与生产,其研发平台覆盖Ac-225标记药物的开发,并具备相应的GMP生产能力。
○
景嘉航布局α核素和β核素的核药研发,与西安迈斯拓扑签署225Ac供应协议以获得225Ac的优先、稳定供应,并与中核秦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便在研发核药用核素的供应方面得到更好的保障。
○
2024年6月3日,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陈跃教授团队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登记了一项关于225Ac-TBM治疗骨转移的转化研究,旨在评估225Ac-TBM治疗肿瘤骨转移的疗效和安全性,及其对正常器官和肿瘤的辐射剂量。
结语 )
Conclusion
全球 Ac-225 核药研发已从早期探索进入了快速发展的临床验证阶段。巨头的纷纷入局,更预示着该领域巨大的商业潜力正被资本市场认可,有望在未来5-10年内迎来首批Ac-225药物的上市。虽然中国Ac-225核药产业仍面临诸多挑战,但其展现出的巨大潜力和快速发展的势头令人瞩目。在政策支持、资本助力和科研创新的共同推动下,中国有望在这一全球前沿的医疗领域中占据重要一席,为全球癌症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2025-10-29
摘要
靶向放射性核素治疗(targeted radionuclide therapy, TRT)是肿瘤学领域的前沿治疗手段,它将靶向药物的分子精准性与放疗的疗效相结合,可选择性地向癌细胞递送细胞毒性辐射。过去数十年的研究工作构建了多样化的 TRT 分子图谱,为靶向放射性药物的进一步合理研发以及该治疗方式临床应用的拓展提供了经验。本文结合当前肿瘤学领域已有的治疗手段探讨 TRT,阐述已确立的和新兴的 TRT 靶点(包括利用肿瘤微环境脆弱性的创新策略),并分析其临床转化与分子优化面临的挑战。通过将技术创新、临床前研究成果与实际临床应用相结合,当前关于 TRT 的研究正致力于为多种癌症类型和治疗场景下的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治疗选择。总之,本文强调 TRT 的变革性潜力,并着重指出,全面理解理想靶点的构成要素如何能重新定义临床实践,推动 TRT 发展成为高度个体化、适应性强的治疗方式,进而改善多种癌症的治疗结局。
核心要点
•靶向放射性核素治疗(TRT)是一种全身治疗方式,通过与肿瘤相关靶点结合的配体递送放射性载荷,利用分子识别作用选择性诱导辐射介导的癌细胞损伤,同时将正常组织毒性降至最低。
•放射性核素可及性的提升与载体设计的进步,解锁了 TRT 针对多种肿瘤相关靶点的潜力,这些靶点既包括利用肿瘤和微环境脆弱性的泛癌标志物,也包括局限于特定癌症的靶点。
•得益于分子谱分析技术、人工智能工具及药物重定位的发展,新型 TRT 靶点的鉴定与验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
•可靠的临床转化需要能模拟真实世界复杂性的临床试验,根据靶点表达变化动态调整治疗方案,同时通过持续监测克服肿瘤异质性与耐药性,减少传统癌症治疗中常见的毒性反应。
•多聚化、多靶点、共价键连接及预靶向策略的创新,可改善肿瘤靶向效果,同时克服脱靶毒性、靶向异位毒性及组织穿透障碍,拓展 TRT 在复杂癌症场景中的应用潜力。
•在治疗早期引入 TRT,并战略性选择联合治疗伙伴(如化疗、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可最大化治疗效果、应对耐药性,并扩大其在肿瘤学领域的应用范围。1. 引言
过去数十年间,靶向放射性核素治疗(TRT)已成为肿瘤治疗领域的突破性手段,它融合了癌症治疗两大核心支柱 —— 放疗与全身分子靶向治疗的优势。将分子成像整合到 TRT 中形成了 “放射诊疗一体化(radiotheranostics)”,使这些治疗方式成为精准肿瘤学中最强大的工具之一 。TRT 实现了 “所见即治(treat-what-you-see)” 的治疗模式,可支持实时监测(图 1)。这种治疗方式不仅能在晚期癌症中,还能在早期阶段实现精准的肿瘤定位、病灶维度评估、全身分子特征分析,进而开展个体化治疗。
图1. TRT 在肿瘤学中的临床应用
近年来,放射性核素供应与载体设计的进步拓展了 TRT 的应用范围,推动了针对更多分子靶点的新型药物研发,尤其在目前缺乏有效治疗选择的癌症类型中成效显著。TRT 当前的临床发展势头可通过两项里程碑式的获批成果体现:一是镥 - 177 标记的生长抑素类似物(Lu-177-DOTATATE),用于治疗生长抑素受体 2 型(SSTR2)阳性的神经内分泌肿瘤(NETs);二是镥 - 177 标记的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SMA)靶向拟肽(Lu-177PSMA-617),用于治疗 PSMA 阳性的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这两种药物与各自靶点结合后均会释放 β 粒子辐射,选择性地对表达 SSTR2 或 PSMA 的肿瘤细胞造成 DNA 损伤并诱导其死亡。
本文将探讨 TRT 研发的最新进展,重点关注从 “可干预靶点” 中获得的经验(这些靶点集中体现了肿瘤学领域的主要挑战)。将分析一系列利用 TRT 潜力应对肿瘤异质性与其他治疗耐药性的靶点,阐述个体化治疗策略,并与其他治疗类型进行对比。同时,强调 TRT 的优势与局限性,既关注临床前成果的临床转化,也探讨优化当前 TRT 研发管线的分子策略,并提出通过开发新兴靶点充分释放 TRT 对多种癌症治疗潜力的战略方向。2. TRT 的原理
TRT 指通过分子载体将放射性核素载荷递送至癌细胞的治疗方式。“放射性配体(radioligand)” 特指靶向组件,包括能结合放射性核素的分子片段、连接子、螯合剂及 / 或修饰剂;而 “放射性药物(radiopharmaceuticals)” 则涵盖核医学中使用的治疗性与诊断性放射性偶联物。2.1 作用机制
TRT 通过载体介导将放射性载荷(α 粒子、β 粒子发射体,以及奥格电子、内转换电子)递送至肿瘤相关靶点,直接向细胞内结构释放细胞毒性辐射,诱导 DNA 损伤并触发细胞死亡(图 2)。TRT 方案的设计需结合疾病特征与治疗需求:肿瘤生物学特性(如大小、异质性、位置、靶点表达水平)决定了放射性核素与载体类型的选择。
图2. 靶向放射性核素治疗的组成部分
放射性核素的选择需基于其发射类型、物理半衰期及与放射性配体药代动力学的匹配性,分别用于治疗或诊断目的。例如,镓 - 68(Ga-68)与氟 - 18(F-18)因半衰期短且能发射正电子,常用于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PET);而镥 - 177(Lu-177)、锕 - 225(Ac-225)等治疗性核素则因能释放细胞毒性粒子且半衰期较长(与肿瘤摄取动力学匹配)而更受青睐。
•α 粒子发射体:能量高(5-9 兆电子伏特)、组织穿透深度短(图 2),对微转移灶(直径 <2 毫米)尤其有效;但临床研究显示,即使在较大肿瘤(>1 厘米)中,含 α 粒子载荷的 TRT 也能产生疗效(尤其当靶点表达均匀且血管灌注良好时)。α 粒子的作用机制基于高线性能量转移(LET)电离,可造成密集的 DNA 损伤(主要是双链断裂),且对活性氧的依赖度低、无需氧气参与,因此在肿瘤乏氧区域仍能有效发挥作用⁷。临床相关的 α 粒子发射体包括:
◦长半衰期的锕 - 225(Ac-225):其衰变链中会释放 4 个 α 粒子,可实现对肿瘤的持续辐射,但衰变产生的 “子代核素”(因核反冲导致)可能发生再分布,增加脱靶毒性风险。
◦钍 - 227(Th-227):通过其子代核素镭 - 223(²²³Ra,α 粒子发射体)衰变,实现持续的 α 辐射暴露。
◦短半衰期的砹 - 211(At-211):直接衰变释放α 粒子,子代核素再分布程度低。
◦铋 - 213(Bi-213):主要通过β 粒子衰变为钋 - 213(Po-213),后者释放α 辐射,但 45.6 分钟的短半衰期限制了其治疗应用。
◦铅 - 212(Pb-212):可在体内通过衰变为铋 - 212(Bi-212)与钋 - 212(Po-212)产生α 粒子,实现局部高密度能量沉积。
•β 粒子发射体:组织穿透范围更长(最大可达 12 毫米),且具有 “交叉火力效应(crossfire effect)”—— 即能损伤未被标记的邻近细胞,因此可用于治疗更大(直径约 1-40 毫米,取决于核素类型)或结构复杂的肿瘤,以及肿瘤基质区域。β 粒子的抗肿瘤效果源于直接 DNA 电离与活性氧介导的间接损伤,主要造成单链断裂,累积后可引发双链断裂,进而诱导细胞凋亡或衰老。尽管 DNA 修复机制可修复部分损伤,但反复辐射暴露会耗尽修复能力,最终导致细胞死亡。β 粒子的长穿透路径还能有效辐射异质性肿瘤细胞群。
临床肿瘤学中常用的β 粒子发射体包括已获批的镥 - 177(Lu-177)、碘 - 131(I-131)、钇 - 90(Y-90),以及处于研究阶段的铜 - 67(Cu-67)、铽 - 161(Tb-161)。其中,Lu-177、I-131、Cu-67、Tb-161 除释放β 粒子外,还会发射 γ 射线,因此可在开展治疗的同时进行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SPECT),实现治疗与剂量监测的一体化。铽 - 161(Tb-161)与镥 - 177(Lu-177)具有多项相似的物理特性(如β 粒子发射谱、γ 射线共发射、半衰期),且额外释放大量内转换电子与奥格电子 —— 这些短程粒子(<500 纳米)的电离密度高,当在细胞核附近衰变时,能高效诱导 DNA 损伤(双链断裂与氧化性碱基损伤)。β 粒子与高密度电离电子发射的结合,使 Tb-161 在治疗微转移灶与小体积肿瘤中极具潜力,其精准的亚细胞能量沉积可提升治疗效果。
放射性载荷的有效递送依赖于“载体”(图 2)—— 这类载体需能高特异性结合肿瘤相关靶点,实现肿瘤的精准辐射。这一机制体现了 TRT 的适应性:它能选择性向癌细胞递送辐射,同时保护正常组织,避免了传统治疗中常见的 “靶向异位毒性”。TRT 的临床应用以 SSTR2、PSMA 等经过充分验证的靶点为基础,这些靶点已获得组织病理学、影像学及(临床前)临床研究的充分支持。与此同时,TRT 的应用范围也在扩大,纳入了此前已在肿瘤学中验证的靶点(如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HER2)),目前这些靶点正被探索用于 TRT。此外,肿瘤微环境(TME)中的靶点(如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FAP))的发现,为 “泛靶点治疗(one-target-fits-all)” 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样,仅在罕见癌症和 / 或儿童癌症中表达的靶点,也为 TRT 在 “传统上缺乏有效治疗选择的癌症” 中验证潜力提供了宝贵机会。随着新型靶点的发现,严格的靶点验证与对 TRT 作用机制的全面理解,是确保其可靠临床转化的关键。2.2 与传统癌症治疗的对比
TRT 具有区别于传统治疗方式(如全身化疗、外照射放疗(EBRT)、手术)的独特作用机制,可实现无与伦比的精准性与适应性。这种靶向特性不仅能提升疗效,还能改善生活质量(QOL)相关指标,包括降低毒性、提高治疗依从性、简化治疗流程。
•与化疗对比:化疗常伴随严重毒性反应(如脱发、周围神经病变、重度血液毒性),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尤其在老年患者中更为明显。相比之下,基于 Lu-177 的 TRT 耐受性良好,重度血细胞减少发生率更低。在评估 Lu-177-DOTATATE 联合奥曲肽与高剂量奥曲肽治疗转移性 NETs 的 Ⅲ 期 NETTER-1 试验中,对照组(高剂量奥曲肽)患者的总体健康状况恶化中位时间仅为 6.1 个月,而试验组(Lu-177-DOTATATE 联合奥曲肽)长达 28.8 个月。在评估Lu-177-PSMA-617 与标准治疗(SOC)对比的 Ⅲ 期 VISION 试验,以及评估其与卡巴他赛对比的 Ⅱ 期 TheraP 试验(均针对 mCRPC 患者)中,试验组患者的生活质量也显著优于对照组。TheraP 试验显示,与卡巴他赛相比,Lu-177-PSMA-617 治疗的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应答率更高、无进展生存期(PFS)更长,且 3-4 级不良事件(AEs)发生率更低,尽管总生存期(OS)无显著差异 (表 1)。此外,Ⅲ 期 PSMAfore 试验表明,Lu-177-PSMA-617 可作为雄激素受体通路抑制剂(ARPI)的替代选择(ARPI 常因治疗耐药需更换)。该试验在未接受过紫杉烷治疗的 mCRPC 患者中对比了 Lu-177-PSMA-617 与 ARPI,结果显示前者可显著改善 PFS 且安全性良好(表 1)。
表1 已有结果的 TRT 临床试验
尽管 TRT 毒性低于化疗,但仍存在正常组织损伤风险,包括肾毒性、血液毒性,以及靶向异位毒性(如口干症),且不同放射性配体的毒性谱差异显著。例如,α 粒子发射体 Ac-225-PSMA 疗效显著(尤其在 Lu-177 耐药患者中),但也伴随毒性反应—— 因放射性药物在唾液腺中大量蓄积,68%-100% 的患者会出现口干症,甚至有高达 23% 的患者因该毒性终止治疗。
•与外照射放疗(EBRT)对比:EBRT 通过短时间、高剂量的辐射分次照射肿瘤,可能损伤邻近正常组织;而 TRT 通过全身递送低剂量率辐射,可靶向多种病灶(包括微小、隐匿的微转移灶),因此是治疗播散性癌症的潜在选择。尽管两种方式均可能引发辐射相关毒性,但毒性出现时间与解剖分布存在差异,TRT 的毒性通常更轻微 。EBRT 的毒性多局限于照射野内,包括急性不良反应(如疲劳、脱发、皮肤损伤)与晚期不良反应(如纤维化、继发恶性肿瘤);而 TRT 的毒性取决于放射性配体与核素的生物分布及放射生物学特性,主要表现为对 “剂量限制性器官”(如肾脏、骨髓)的脱靶或靶向异位蓄积。值得注意的是,TRT 的剂量率低于 EBRT,可能使正常组织的损伤修复更高效,从而提升治疗指数。
•与手术对比:手术是局部原发肿瘤治疗的关键手段,但对解剖结构复杂的肿瘤疗效有限;而 TRT 通过微创的全身治疗方式,可靶向手术无法触及的肿瘤与播散性转移灶。此外,TRT 还可与手术协同:术前缩小肿瘤体积,或术后清除残留的微小病灶。例如,在 NETs 患者中,TRT 已被用作新辅助治疗策略,提高肿瘤可切除性并实现持续的肿瘤控制,使部分患者获得根治性手术机会。2.3 与分子靶向治疗的对比
TRT 与分子靶向治疗均以癌症标志物为基础,但 TRT 的多效性使其能靶向更多癌症脆弱性,减少分子靶向治疗中常见的耐药性问题。分子靶向治疗的耐药性通常源于肿瘤异质性与适应性可塑性 —— 例如,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靶向致癌信号通路组件,但常因代偿机制引发通路相关耐药。而 TRT 可规避这些局限:在放射性碘耐药甲状腺癌与 PSMA 阳性肾细胞癌(RCC)的早期研究中,即使患者对 TKI 无应答,TRT 仍能发挥疗效 ;此外,镥 - 177 标记的抗 MET 抗体(Lu-177-DTPA-onartuzumab)在 TKI 耐药的胰腺导管腺癌(PDAC)小鼠模型中,展现出长期抗肿瘤活性。
尽管在标准治疗方案中加入舒尼替尼、卡博替尼等 TKI,可改善胰腺 NETs(PFS:11.4 个月 vs 5.5 个月;HR=0.42,95% CI:0.26-0.66;P<0.001)或胃肠 NETs(PFS:8.4 个月 vs 3.9 个月;HR=0.38,95% CI:0.25-0.59;P<0.001)患者的 PFS,但这些 TKI 也可能引发严重毒性(如高血压、中性粒细胞减少、3-4 级血栓栓塞事件)。相比之下,在 NETs 患者的最佳支持治疗中加入 Lu-177-DOTATATE,仅导致低发生率的 3-4 级血液毒性,且肾毒性轻微,同时显著改善 20 个月时的 PFS(表 1)。不过,TKI 的口服给药方式使其便于居家治疗且应用范围更广,而 TRT 的给药需专业设施支持,并需通过影像学进行患者筛选。
TRT 与抗体药物偶联物(ADCs)的靶向策略与治疗范围相似—— 两者均为精准肿瘤学平台,可直接向肿瘤递送细胞毒性载荷,但作用机制与安全性谱差异显著。ADCs 通常利用单克隆抗体递送细胞毒性载荷,毒性低于化疗,但其较大的分子尺寸(约 150 kDa)限制了肿瘤穿透性,难以实现理想疗效;此外,ADCs 的毒性可能因靶点、连接子、载荷不同而差异显著,部分毒性较为严重。
在临床试验中,Lu-177-PSMA-617 等放射性核素治疗的常见毒性(口干症、乏力、恶心)多为 1-2 级,3-4 级不良事件发生率普遍较低(单一不良事件类型≤11%)。相比之下,PSMA 靶向 ADCs 的疗效中等且毒性显著:在一项评估单甲基奥瑞他汀 E 偶联抗 PSMA 抗体的 Ⅱ 期试验中,58% 的患者出现 3 级及以上不良事件(包括中性粒细胞减少、神经病变),31% 的患者因毒性终止治疗;另一项评估吡咯并苯二氮䓬(PBD)偶联抗 PSMA 抗体的 Ⅰ 期试验中,45% 的患者出现 3-4 级不良事件,33% 的患者终止治疗。针对 HER2、TROP2 的 ADC 临床试验也显示,不良事件相关终止率较高(10%-20%),且严重不良事件(如间质性肺病,发生率约 10%)可能致命。这表明尽管 ADCs 疗效显著,但其安全性仍需关注。
有趣的是,在胃癌小鼠模型中对比 HER2 靶向 ADC(曲妥珠单抗 - deruxtecan)与 Lu-177-DOTA - 曲妥珠单抗联合洛伐他汀的研究显示,两种方案的抗肿瘤活性相似,但 ADC 的毒性更高。在HER2 阳性肿瘤患者中,序贯使用 ADC 与 TRT 可能通过 ADC 的细胞毒性与放射增敏作用优化肿瘤控制。不过,长程 β 粒子发射体在靶向微转移灶时可能因 “交叉火力效应” 与 “ sink 效应”(放射性配体优先被靶点高表达的大肿瘤区域摄取,限制对小病灶、低表达病灶的辐射递送)效果不佳,因此 α 粒子发射体可能更适合这类场景。另一种策略是先用 β 粒子发射体实现肿瘤减负荷,再联用 ADC,这一方案有待进一步研究验证。2.4 与免疫治疗的对比
尽管免疫治疗已革新肿瘤治疗,但在部分癌症类型中疗效仍有限。例如,使用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治疗 mCRPC 时,因该癌症的肿瘤微环境呈 “免疫冷” 状态(T 细胞浸润少、存在免疫抑制微环境),临床应答率较低。仅少数微卫星不稳定型(MSI-H)前列腺癌患者能从 ICIs 中获益,在未筛选的 CRPC 队列中,客观应答率(ORR)仅为 3%-5%(如 KEYNOTE-199 试验)。此外,ICIs 治疗可能引发严重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包括胃肠道毒性、内分泌疾病、肺炎、皮疹等;例如,伊匹木单抗联合纳武利尤单抗治疗黑色素瘤时,3 级及以上不良事件发生率高达 59%。
值得关注的是,TRT 与 ICIs 的协同策略正受到广泛探索 ——TRT 可通过直接肿瘤细胞损伤与 “旁观者效应” 调节免疫反应。临床前研究表明,TRT 诱导的 DNA 损伤会导致胞质核酸累积,通过 cGAS-STING 通路激活 Ⅰ 型干扰素反应;TRT 还能引发剂量依赖性的免疫变化,包括免疫原性细胞死亡、细胞因子谱调节、髓系细胞重编程。旁观者效应可能进一步增强这一作用:例如,经 Ra -223治疗的肿瘤及周围骨微环境释放的细胞外囊泡中,PD-L1 等免疫检查点分子表达水平升高。此外,TRT 的持续低剂量率与肿瘤选择性生物分布,可减少对循环免疫细胞的脱靶辐射,为其与 ICIs 联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尽管嵌合抗原受体(CAR)T 细胞治疗具有潜在的长期疗效,但受限于高成本与严重 irAEs(如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而 TRT 的全身毒性通常低于 CAR-T 细胞。双特异性 T 细胞衔接器(BiTEs)可直接招募 T 细胞至肿瘤靶点并激活其介导的非 MHC 依赖性肿瘤杀伤,为前列腺癌等免疫逃逸型癌症提供了新选择,但需密切监测以防范严重 CRS 与神经毒性。相比之下,TRT 的疗效不依赖免疫细胞功能,且通常对生活质量影响更小。2.5 残留病灶的监测
TRT 的疗效依赖于靶点表达水平,因此需严格筛选患者。放射诊疗一体化为实时监测与个体化辐射剂量调整提供了独特机会,可补充现有标准治疗手段。TRT 不仅实现了其最初 “所见即治” 的设计目标,还拓展至 “未见即治(treat-what-you-don’t-see)” 的应用场景 —— 例如在辅助治疗中靶向残留微小病灶,这一能力显著扩大了 TRT 的应用范围,且是 EBRT 或手术无法实现的。
例如,Ⅲ 期 PSMA-DC 试验(NCT05939414)正评估:对 PSMA PET 阳性病灶进行立体定向体部放疗后,给予 Lu-177-PSMA-617 是否能靶向亚临床、不可检测的转移灶,从而延迟雄激素剥夺治疗(ADT)的启动并维持患者生活质量。这一策略与甲状腺癌患者术后使用 I-131 清除潜在残留病灶的思路相似。然而,Lu-177 等β 粒子发射体的放射生物学局限性(如长穿透路径)可能导致单个癌细胞辐射剂量不足,并增加邻近正常组织的辐射暴露。α 粒子发射体虽能提升精准性,但也会增加靶点表达器官的毒性(如 PSMA 靶向 TRT 中唾液腺的毒性)。
在辅助治疗场景中,铽 - 161(Tb-161)是一种潜在的替代选择—— 它同时释放 β 粒子、奥格电子与内转换电子,可能通过同时靶向临床可见病灶与微小残留病灶改善肿瘤控制。不过,辅助治疗中微转移灶的分布具有随机性且无法通过影像学检测,因此剂量测定仍是主要挑战。目前,随机对照试验尚未证实 TRT 在辅助治疗中的临床获益,而适应性剂量方案、双示踪剂 PET 成像、液体活检生物标志物等技术,可能为患者筛选与 TRT 优化(用于残留病灶监测)提供支持。2.6 TRT 的主要局限性
尽管 TRT 相比其他肿瘤治疗方式具有优势,但其疗效仍取决于靶点表达水平(需通过肿瘤与正常组织的受体水平对比确定)。尽管 TRT 总体耐受性良好,但仍可能引发不良反应,且反应类型因放射性药物与累积剂量而异。长期毒性的担忧需要更多临床研究验证;此外,高生产成本与复杂的设施需求也限制了 TRT 在资源匮乏地区的可及性。尽管目前 TRT 在肿瘤学中的应用仍有限,但其可靶向的癌症标志物范围不断扩大,表明它有潜力填补其他治疗方式在早、晚期癌症中的治疗空白。3. 靶向放射性配体设计3.1 理想靶点的核心特征
TRT 的理想靶点需满足严格标准,在治疗效果、安全性与临床适用性之间取得平衡。这些靶点通常为细胞表面蛋白(确保循环放射性药物可及),且需具备 “可成药性”、高特异性、安全性,以及在病理生理条件下的稳定性。通过转化合作开展的有效验证,可降低早期药物研发中常见的高淘汰率,推动可行 TRT 的开发。
•稳定且持续的靶点表达:是确保治疗效果的关键。癌症细胞具有基因组不稳定性(癌症的标志性特征之一),由染色体异常与高突变率驱动,常导致抗原表达异质性与耐药克隆出现,给受体酪氨酸激酶(RTKs)等癌症特异性标志物的靶向带来挑战,需采用适应性治疗策略。相比之下,传统治疗中的 “达尔文选择压力” 可能不适用于 TRT 靶点 —— 因为 TRT 靶点不一定参与致癌通路,因此表达更稳定。在这一背景下,肿瘤微环境(TME)中的靶点(如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CAFs)表达的蛋白或细胞外基质(ECM)蛋白)被认为具有更高的遗传稳定性,即使肿瘤进化仍能维持稳定表达,支持 FAP 靶向等 TME 靶向策略规避抗原异质性的潜力。
•靶点可及性:由表达水平、细胞定位及配体结合可及性决定,影响剂量需求。低表达或可及性受限的靶点需更高辐射暴露以补偿配体结合不足;而高可及性靶点对“动力学选择性” 更敏感,可能仅需少量活性成分即可实现疗效,从而降低给药剂量。
•特异性:可避免脱靶结合并减少毒性。例如,HER2 在乳腺癌细胞中的表达水平比正常细胞高 40-100 倍,因此具有良好的特异性。
•组织穿透性:放射性配体需有效到达并结合靶点,生理屏障可能显著影响递送效率。载体特性对药代动力学与膜穿透性影响显著:血脑屏障(BBB)会根据分子大小、亲水性、电荷限制分子通过,限制 TRT 在中枢神经系统(CNS)肿瘤中的应用;此外,间质膜的扩散限制也可能阻碍大分子放射性配体的递送。尽管存在这些障碍,放射诊疗一体化的进步(如小分子 PET 示踪剂的开发)与标准治疗(如放疗、化疗)诱导的血脑屏障通透性改变,正扩大 TRT 在脑转移患者中的应用潜力。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临床研究显示,SSTR2 靶向与 PSMA 靶向 TRT 对 CNS 转移灶具有治疗活性;目前研究正通过动脉内给药、纳米颗粒包载、受体介导的转胞吞作用、鞘内给药及预靶向系统(将在后续章节讨论)进一步改善穿透性与靶向效果。
•配体 - 靶点内化效率:高效的内化可通过将辐射集中于细胞内并延长 DNA 暴露时间,提升所有放射性核素治疗的效果,尤其对奥格电子与内转换电子发射体至关重要 —— 它们的细胞毒性潜力依赖于与核 DNA 的纳米级 proximity。因此,选择能促进内化的靶点对这类发射体尤为关键,但并非绝对必需:临床前研究表明,奥格电子也可通过脂质筏介导的细胞膜氧化发挥细胞毒性,而非仅依赖核 proximity。
•靶点稳定性:是实现持久抗肿瘤活性的关键。酶降解或靶点释放到循环中,可能导致放射性配体摄取不足与辐射衰变不匹配(尤其对Lu-177 等长半衰期同位素),影响治疗效果。理想情况下,稳定的靶点应位于细胞外,以改善靶向效果并减少全身影响。
传统治疗通常依赖靶点在疾病中的生物学功能,且越来越强调优先选择“与癌症病理机制密切相关” 而非 “易干预” 的靶点;而 TRT 对靶点的要求不同 —— 无需靶点参与致癌通路,核心要求是在肿瘤中稳定且选择性表达,同时在正常组织中低表达。例如,PSMA 在前列腺癌中的作用明确,在非前列腺组织中表达极低,且具有 “ADT 治疗后表达上调” 等治疗优势 ;相反,靶向 RTKs 可能面临挑战 —— 癌症细胞常通过适应克服信号通路改变,影响靶向效果。因此,SSTR2、PSMA、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 3(GPC3)、碳酸酐酶 Ⅸ(CAIX)等癌症靶点,FAP 等基质靶点,以及 CD33 等血液系统抗原,仍是符合上述核心要求的潜在靶点。3.2 靶点鉴定策略
新型 TRT 靶点的发现需要综合实验、计算与转化方法。通过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空间组学及 / 或单细胞组学的高通量分子谱分析,可大规模鉴定癌症特异性靶点。公共数据库为靶点鉴定提供了丰富的组学资源,降低成本并加速发现进程,例如:
•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基因型 - 组织表达项目(GTEx)、临床蛋白质组肿瘤分析联盟(CPTAC);
•癌症靶点发现与开发(CTD2)、开放靶点(Open Targets)、疾病基因网络(DisGeNET)(链接分子靶点与癌症病理);
•药物数据库(DrugBank 6.0)(提供药物与毒性相关信息,排除可能引发靶向异位毒性的候选靶点)。
尽管人工智能(AI)工具在 TRT 领域尚未广泛应用,但其可辅助分析癌症数据集,识别肿瘤特异性表达模式与可成药位点。例如,AlphaFold、RoseTTAFold等计算工具可接近实验精度预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可成药位点及相互作用动力学,尽管仍需进一步优化以有效捕捉放射性配体 - 靶点相互作用;机器学习驱动的优先级排序工具可通过系统评估组织特异性、表达一致性与可及性,简化靶点筛选流程;AtomNet等平台可预测药物 - 靶点相互作用与结合亲和力;BioBERT可从生物医学文献与电子健康记录中提取信息,辅助靶点发现。
除从头鉴定靶点外,药物重定位是一种成本效益高的策略—— 它可利用已有的安全性与疗效数据,扩大 TRT 靶点库并加速临床验证,尤其适用于已有疗效明确药物的适应症(如生长抑素类似物用于 SSTR2 阳性癌症)。临床获批的抗体、ADCs、小分子抑制剂常被重新改造用于 TRT(将在后续章节讨论)。基于 AI 的药物重定位通过机器学习模型筛选癌症治疗数据集,预测符合 TRT 要求的非适应症用途;TxGNN 等新兴模型已在传统药物重定位中展现价值,未来可通过整合放射性配体特异性参数适配 TRT 需求;此外,AI 模型还可挖掘天然配体库,识别新型 TRT 候选分子。
反向转化研究以临床结果为起点鉴定靶点,可验证靶点相关性并揭示治疗应答机制。例如,在前列腺癌中,胃泌素释放肽受体(GRPR)是一种在低级别肿瘤中过表达的神经肽受体,已被临床评估为分子成像靶点。对比Ga-68-PSMA(靶向 PSMA)与Ga-68-RM2(靶向 GRPR)PET-CT 的研究显示,两种示踪剂的摄取模式具有互补性 ——GRPR 靶向成像可检测 PSMA 低表达或不表达的病灶。在这一背景下,分析接受 Lu-177-PSMA-617 治疗患者的临床应答,可能发现 GRPR 可作为替代或联合治疗的次要靶点。例如,对 GRPR 高表达患者,可在治疗后通过Ga-68-RM2 等非 PSMA PET 成像验证 GRPR 作为替代靶点的潜力 。尽管这一策略尚未经过前瞻性验证,但它展示了分子成像在识别互补靶点、指导个体化联合 / 序贯治疗中的价值。此外,组织学、分子与生物标志物分析,以及 AI 辅助病理分析,也可帮助识别替代靶点并监测靶点表达随时间的变化,辅助患者分层;评估 TRT 后免疫检查点上调与 DNA 损伤应答失调,还可指导 TRT 与 ICIs 或 PARP 抑制剂的联合策略。最后,通过考虑种属差异与模型相关性的方法,在临床前与临床阶段对 TRT 靶点进行严格验证,是确保其可靠临床转化的关键。3.3 分子骨架(载体选择)
选择理想的递送载体是克服递送挑战的关键(图 2):
•小分子与肽类:可穿透致密肿瘤,但肾清除率高,因此需通过白蛋白结合、多聚化(将多个配体单元化学连接以增强亲和力与滞留时间)等修饰(图 3)改善特性,但部分策略可能增加毒性。
•大分子抗体:可靶向可及的细胞外蛋白,实现特异性结合与长期滞留,尤其与长半衰期核素联用时优势显著;但其分子尺寸限制了组织穿透性,且血浆中长半衰期可能增加血液毒性。此外,当使用 Ac-225 等载荷标记时,抗体类放射性配体的缓慢清除会引发担忧——Ac-225 衰变产生的子代核素(如 Fr-221、At-217、Bi-213,可释放α、β、γ 辐射)可能因核反冲从螯合剂中脱离,导致正常组织再分布。
•小分子抗体片段:如单域抗体(sdAbs)、亲和体(Affibodies)、微型抗体(minibodies),可能在特异性与清除率之间取得平衡,是潜在的替代选择。
图3. TRT中的分子靶向机制4. TRT 的临床转化
TRT 的临床应用是癌症治疗领域的重大突破,分子工程的前沿进展正不断融入临床常规实践。早期 TRT 临床试验以 “过表达靶点” 为基础,验证了其作为精准医疗手段的潜力。目前已有的 TRT 处于不同临床转化阶段,其靶点可分为四类:(1)已有获批 TRT 的靶点;(2)处于临床研发阶段的靶点(正在治疗性临床试验中评估安全性、疗效与肿瘤学结局);(3)TRT 新兴靶点(处于早期临床前研究和 / 或成像试验阶段,验证肿瘤摄取与转化治疗潜力);(4)肿瘤微环境(TME)相关靶点(旨在将 TRT 应用拓展至癌细胞之外)(表 1)。TRT 可靶向癌细胞特异性靶点与 TME 相关靶点,其武器库的不断扩充,有望将这一治疗方式的应用范围扩展至更多癌症类型与未满足的肿瘤治疗需求。4.1 已有获批 TRT 的靶点4.1.1 CD20
CD20 是主要表达于恶性 B 淋巴细胞表面的抗原,是血液系统肿瘤治疗的有效靶点。血液系统癌症的获批 TRT 包括钇 - 90 标记的替伊莫单抗(Y-90-ibritumomab tiuxetan)与碘 - 131 标记的托西莫单抗(I-131-tositumomab),二者在 21 世纪初被证实对非霍奇金淋巴瘤(NHL)有效。尽管疗效明确,但近年来由于竞争、高成本与报销政策不足等原因,两种药物均因商业效益不佳而停产。抗体工程技术的进步(如单域抗体、抗体片段的探索),以及 α 粒子发射体标记,重新激发了 CD20 靶向 TRT 在 NHL 治疗中的研究兴趣。4.1.2 去甲肾上腺素转运体(NET)
去甲肾上腺素转运体是一种表达于突触前神经元的跨膜蛋白,是神经母细胞瘤、嗜铬细胞瘤、副神经节瘤等罕见 CNS 癌症治疗的相关靶点。碘 - 131 标记的间碘苄胍(I-131-MIBG,去甲肾上腺素类似物,可被去甲肾上腺素转运体选择性摄取)于 2018 年获美国 FDA 批准,但早期治疗中剂量优化不足限制了其应用。21 世纪末的临床证据表明,基于高活度剂量测定的策略可能提升 I-131-MIBG 的疗效;然而,尽管结果积极,2024 年初该药物仍因竞争、商业需求不足与财务挑战停产 。这一情况凸显了 TRT 作为治疗选择需获得持续支持的重要性 —— 目前正在开展的剂量优化与联合治疗研究,有望恢复其在罕见癌症中的应用价值。4.1.3 生长抑素受体 2 型(SSTR2)
SSTR2 通常在高分化神经内分泌肿瘤(NETs)中过表达。使用 DOTATATE 靶向该受体兼具诊断与治疗优势,对转移性低级别胃肠胰(GEP)NETs 疗效显著(表 1)。相反,低分化 NETs 中 SSTR2 表达通常较弱,与预后不良相关,提示需根据肿瘤分级与分子背景调整 SSTR 靶向 TRT 方案。
Ⅲ 期 NETTER-1 试验的结果确立了 Lu-177-DOTATATE 作为高分化 1-2 级中肠 NETs 标准治疗(SOC)的地位 —— 与高剂量奥曲肽相比,Lu-177-DOTATATE 显著改善 PFS³(表 1)。该试验的长期随访结果(中位随访约 76 个月)证实了 TRT 的安全性,未观察到新增继发恶性肿瘤或安全性信号,进一步支持 Lu-177-DOTATATE 的良好风险 - 获益比。事后分析显示,病灶直径≤3 厘米的患者从 Lu-177-DOTATATE 中获益最大,提示在特定患者中早期使用的价值。
Ⅲ 期 NETTER-2 试验进一步验证了 Lu-177-DOTATATE 的疗效 —— 该试验在 2-3 级 GEP NETs 患者中评估了 Lu-177-DOTATATE 联合一线奥曲肽与奥曲肽单药的疗效,结果显示联合方案显著延长 PFS,重新定义了这类癌症的一线治疗标准。该试验首次通过随机亚组研究证实了 Lu-177-DOTATATE 在 3 级 NETs 中的疗效(PFS:22.2 个月 vs 5.6 个月;HR=0.266,95% CI:0.145-0.489),与 2 级 NETs 中的疗效(PFS:29.0 个月 vs 13.8 个月;HR=0.306,95% CI:0.176-0.530)相当,表明 TRT 也可用于治疗更具侵袭性的 NETs。NETTER-2 试验未观察到 OS 改善,可能因交叉率高(48%)且 2 级 NETs(占试验队列 65%)具有惰性特征(OS 通常较长,难以显示差异)。
另一里程碑进展来自单臂Ⅱ 期 NETTER-P 试验 —— 该试验于 2024 年推动Lu-177-DOTATATE 获批用于儿童 GEP NETs 治疗 。尽管取得这些成功,部分 SSTR2 阳性肿瘤患者对 Lu-177-DOTATATE 的临床应答仍有限,治疗耐药仍是关注焦点。尽管 PET 成像对确认 SSTR2 阳性至关重要,但仍需更多策略克服耐药性。目前,SSTR2 靶向 α 粒子发射体 TRT(如 Pb-212-DOTAMTATE、Ac-225-DOTATATE)正处于早期临床试验阶段,纳入未接受过 TRT 与 TRT 后进展的 NETs 患者。
选择 SSTR 激动剂(如 Lu-177-DOTATATE,结合后会内化)还是拮抗剂(如 Lu-177-DOTA-LM3、Lu-177-DOTA-JR11,摄取更高且无显著内化),可能是影响临床应答的关键因素 。在临床研究中,拮抗剂策略正受到更多关注 —— 越来越多临床试验优先评估这类药物,因其可能更高效地靶向 SSTR2(尤其在该标志物表达异质性的肿瘤中)。这一优势源于 SSTR2 拮抗剂可同时结合靶点的活性与非活性构象,改善结合效果与药代动力学。小鼠模型研究显示,Lu-177-DOTA-JR11 在肿瘤中的蓄积量高于 Lu-177-DOTATATE,抗肿瘤活性更优 ;此外,一项前瞻性试验证实,Ga-68-DOTA-JR11 与 Lu-177-DOTA-JR11 在病灶中摄取率高,且后者的峰值标准化摄取值(SUV)与预计吸收剂量高度相关 。
SSTR2 与其他受体(如多巴胺受体 D2、SSTR5,二者在 NETs 中也过表达)的异二聚化进一步增加了复杂性 —— 这会影响放射性配体的结合、内化及治疗应答,但也为联合治疗提供了机会。除 NETs 外,Lu-177-DOTATATE 还在以下场景中开展试验:作为一线联合标准治疗用于广泛期小细胞肺癌(SCLC);作为二线单药用于进展期或高危脑膜瘤;作为单药用于复发胶质母细胞瘤或联合标准治疗用于新诊断胶质母细胞瘤(NCT05109728);作为单药用于经两种及以上标准治疗后进展的 Ⅳ 期或复发乳腺癌(NCT04529044)。4.1.4 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SMA)
PSMA 在约 85% 的前列腺癌中过表达,是可靠的治疗靶点。Ⅲ 期 VISION 试验(一项纳入 831 例 PSMA 阳性 mCRPC 患者的随机研究)显示,Lu-177-PSMA-617(每 6 周给药 7.4 GBq,共 4-6 个周期)可改善经 ARPI 治疗且接受过 1-2 线紫杉烷治疗后进展患者的结局 —— 与标准治疗(SOC)相比,Lu-177-PSMA-617 联合 SOC 显著延长 OS(15.3 个月 vs 11.3 个月,延长 4.0 个月)与影像学 PFS(延长 5.3 个月),推动其获得监管批准(表 1)。
在Ⅱ 期 TheraP 试验中,Lu-177-PSMA-617 与卡巴他赛对比,PSA 应答率更高,但 OS 无显著差异 。这些试验显示,Lu-177-PSMA-617 耐受性良好(即使给药达 6 个周期),不良事件可控,且对生活质量无负面影响 。目前正在开展的 PSMA 靶向 TRT 包括 Lu-177-PSMA-617 与 Lu-177-PSMA-I&T,临床试验在不同场景中评估这些药物的疗效,包括高危局限性前列腺癌、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mHSPC)、mCRPC(化疗前后),以及与 ADT、ARPI、紫杉烷类化疗等标准治疗的联合方案。这些试验的患者筛选通常需通过Ga-68-PSMA PET-CT 确认 PSMA 高表达。
在化疗前 mCRPC 场景中,关键 Ⅲ 期试验包括 PSMAfore(NCT04689828,评估 Lu-177-PSMA-617)、SPLASH(NCT04647526,评估 Lu-177-PSMA-I&T)、ECLIPSE(NCT05204927,评估 Lu-177-PSMA-I&T)(表 1)。这些试验将 PSMA 靶向 TRT 与 ARPI 更换方案对比,有望将 TRT 确立为传统内分泌治疗序贯方案的替代选择。PSMAfore 试验的结果 推动 Lu-177-PSMA-617 获批范围扩大,纳入 “接受过 ARPI 治疗且适合延迟紫杉烷化疗” 的 PSMA 阳性 mCRPC 患者,标志着 TRT 应用时机提前,显著扩大了患者 eligibility。尽管评估 Lu-177-PSMA-617与 Lu-177-PSMA-I&T 的试验均达到影像学 PFS 改善的主要终点,但高交叉率影响了 OS 结局 —— 这一挑战正通过在研试验解决。
多项研究还在评估 Lu-177-PSMA-617 与 ARPI 在 mCRPC 中的联合应用,如 ENZA-p、PSMACare(NCT05849298)、PSMAndARPI(NCT06894511)。Ⅱ 期 ENZA-p 试验显示,在未接受过紫杉烷或 ARPI 治疗、且存在早期进展风险因素的 mCRPC 患者中,Lu-177-PSMA-617 联合恩扎卢胺与恩扎卢胺单药相比,显著延长 PSA PFS,支持在 mCRPC 一线治疗中采用联合策略的合理性。
在激素敏感性场景中,Ⅲ 期试验(如 PSMAddition(NCT04720157)、PEACE-6(NCT06496581)、STAMPEDE-2(NCT06320067))正在评估 Lu-177-PSMA-617 联合标准治疗(ADT 联合 ARPI,±EBRT 或多西他赛)的疗效。Ⅱ 期 UpFrontPSMA 试验进一步显示,在新诊断高负荷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中,Lu-177-PSMA-617 序贯多西他赛与多西他赛单药相比,去势抵抗发生时间与 PSA PFS 显著延长(31 个月 vs 20 个月;HR=0.60,95% CI:0.37-0.98;P=0.039)。
在寡转移性 mHSPC 中,随机 Ⅱ-Ⅲ 期试验(如 PSMA-DC(NCT05939414)、LUNAR(NCT05496959)、POPSTAR II(NCT05560659))正在评估 “立体定向消融放疗联合 Lu-177-PSMA 药物” 是否改善局部控制并延迟全身进展。在高危局限性前列腺癌中,多项 Ⅰ-Ⅱ 期试验(如 LuTectomy(NCT04430192)、NEPI(NCT06388369))正在评估 Lu-177-PSMA-617 的新辅助应用 ——LuTectomy 试验显示,术前给予 1-2 个周期的 Lu-177-PSMA-617 可安全地向前列腺递送靶向辐射,且不影响手术结局。
与此同时,针对 PSMA 靶向 TRT 的试验也在探索替代核素,以改善疗效或应对 Lu-177-based TRT 耐药。这些研究包括 α 粒子发射体(如Ac-225 标记 PSMA-617(AcTION 试验,NCT04597411)、Ac-225 标记 PSMA-I&T(AlphaBreak 试验,NCT06402331)、Pb-212 标记 ADVC001(TheraPb 试验,NCT05720130)),以及 β 粒子发射体(如 Tb-161 标记 PSMA-I&T(VIOLET 试验,NCT05521412)、Cu-67 标记 SAR-bisPSMA(SECuRE 试验,NCT04868604))。
毒性仍是 PSMA 靶向 TRT 临床应用的重要考量。Lu-177-PSMA-617 会在唾液腺与肾脏中蓄积,可能分别引发口干症与肾毒性;Ac-225-based 疗法也面临唾液腺毒性挑战 —— 尽管 Ac-225-PSMA-617 对 Lu-177 耐药患者疗效显著,但可能诱发或加重口干症。不过,口干症发生率因放射性药物结构而异:与小分子配体相比,J591 等抗体载体在唾液腺中的摄取更低。临床试验显示,Ac-225-J591 引发的口干症发生率低于Ac-225-PSMA-617(尽管两项试验的设计与报告标准存在差异)。除通过放射性配体设计减轻毒性外,还需考虑 mCRPC 中的替代靶点 —— 例如,新兴的激肽释放酶 2(kallikrein 2)靶向 TRT 显示出潜力,首个人体试验(小队列)显示其在唾液腺中摄取低且肿瘤靶向效果好。
PSMA 靶向 TRT 的疗效还受限于 PSMA 对雄激素受体活性的依赖性 ——ADT 给药时机影响患者结局,提示需开展 PSMA 表达动态变化的纵向研究;此外,PSMA 表达的异质性也强调了伴随诊断与 PSMA PET 成像在治疗规划中的重要性。最后,在前列腺癌以外的癌症(如唾液腺肿瘤、甲状腺癌、胶质母细胞瘤)中也检测到 PSMA 表达,有望扩大 PSMA 靶向 TRT 的应用范围,尽管在部分肿瘤类型中 PSMA 主要表达于内皮细胞。4.2 处于临床研发阶段的 TRT 靶点4.2.1 胃泌素释放肽受体(GRPR)
GRPR 是一种 G 蛋白偶联受体,在胃、胰腺等正常组织中生理性表达,在前列腺癌、乳腺癌、肺癌、胃肠道癌症等多种癌症中过表达。GRPR 靶向 TRT 对 PSMA 表达有限或对标准治疗耐药的前列腺癌患者尤为重要。临床研究已测试了 GRPR 靶向放射性药物,如Ga-68-RM2、Ga-68-NeoB,这些药物在成像中显示出潜力,病灶检测谱与 F-18-FDG、Ga-68-PSMA 互补 。
在 TRT 应用中,GRPR 拮抗剂通常优于激动剂 —— 因其肿瘤滞留性更好、内化率更低、生物分布更优。尽管 GRPR 在胰腺中表达可能导致剂量限制性毒性,但部分 GRPR 靶向放射性配体在胰腺中的清除速度快于肿瘤,实现了有利的肿瘤 - 胰腺摄取比。例如,在前列腺癌小鼠模型中,Lu-177-NeoB 与 Lu-177-RM2 拮抗剂均显示出显著的肿瘤摄取,且无靶向异位胰腺毒性。首个人体 NeoRay 试验(NCT03872778)正在评估 Lu-177-NeoB 在晚期 GRPR 阳性实体瘤患者中的安全性与疗效;此外,Lu-177-NeoB 还在联合 ribociclib - 氟维司群(NCT05870579)或卡培他滨(NCT06247995)治疗转移性雌激素受体阳性、HER2 阴性乳腺癌的试验中接受评估。
Ⅰ-Ⅱ 期 COMBAT 试验(纳入 mCRPC 患者)展示了 GRPR 靶向的灵活性,尤其适用于不适合 Lu-177-PSMA-617 治疗的患者 —— 该试验采用放射诊疗一体化策略,联合两种 GRPR 靶向放射性药物:Cu-64-SAR-BBN 用于成像,Cu-67-SAR-BBN 用于抗肿瘤治疗。此外,Lu-177 标记与 Tb-161 标记的高亲和力 GRPR 拮抗剂 AMTG 的开发,进一步扩大了 GRPR 靶向 TRT 的选择范围。临床前数据显示,Tb-161-AMTG 的抗肿瘤活性可能优于 Lu-177-AMTG—— 因Tb-161 释放的奥曲电子与内转换电子具有短程发射特性,可直接向肿瘤细胞膜递送高辐射剂量;这一概念的临床验证仍在进行中。4.2.2 激肽释放酶 2(kallikrein 2)
激肽释放酶 2 具有前列腺限制性表达特征,在前列腺癌细胞中显著上调。作为 PSMA 靶向 TRT 的替代靶点,它可解决 PSMA 靶向的 “靶向异位毒性” 问题,并 / 或靶向 PSMA 阴性病。与 PSMA 不同,激肽释放酶 2 的表达随雄激素受体信号激活而增加,使其成为 PSMA 靶向 TRT 进展患者的潜在靶点。Ⅰ 期试验(评估靶向激肽释放酶 2 的放射性标记抗体 Ac-225-h11B6 在前列腺癌患者中的疗效)显示出持久的生化与影像学应答,但需关注剂量相关的血小板减少症与间质性肺病等不良事件。4.2.3 胆囊收缩素 2 型受体(CCK2R)
CCK2R 在甲状腺髓样癌(MTC)、小细胞肺癌(SCLC)等恶性肿瘤中过表达。Ⅰ 期 GRAN-T-MTC 试验(评估 In-111-CP04 在 MTC 患者中的疗效)显示,该药物在肿瘤中摄取显著(检出率 81%),优于传统成像;尽管肾脏与膀胱辐射暴露是剂量限制因素,但联合输注明胶溶液可使肾脏剂量降低 53%。早期临床前研究显示,CCK2R 靶向放射性核素治疗具有肿瘤靶向性与配体稳定性(如Lu-177-DOTA-MGS5 在小鼠模型中的表现);首个人体试验(使用 Lu-177-PP-F11N)证实其在 MTC 患者中具有肿瘤特异性摄取与良好生物分布,但后续临床开发受阻,可能因配体蛋白水解降解快等挑战。一项试点试验显示,患者在 TRT 前接受内肽酶抑制剂可稳定 Lu-177-PP-F11N,提高肿瘤吸收剂量。4.2.4 神经降压素受体 1 型(NTSR1)
NTSR1 是一种参与胃肠功能(如蠕动、分泌)的 G 蛋白偶联受体,在胰腺癌(PDAC)、结直肠癌(CRC)等多种胃肠道恶性肿瘤中显著过表达。NTSR1 靶向拮抗剂 Lu-177-3BP-227 已被用作 PDAC 患者的挽救治疗—— 尽管存在肾脏剂量限制,该疗法耐受性良好且显示出一定疗效(6 例入组患者中 1 例部分应答),支持 NTSR1 靶向 TRT 的可行性。目前多项 NTSR1 靶向放射性核素治疗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此外,放射性标记 NTSR1 拮抗剂 Ac-225-FPI-2059 已在实体瘤患者的 Ⅰ 期试验中接受评估(NCT05605522)。4.2.5 癌胚抗原(CEA)
CEA 是一种在 CRC 等多种肿瘤中过表达的细胞表面糖蛋白,历来被视为放射性核素治疗的重要靶点。2017 年发表的一项 Ⅱ 期试验(评估碘 - 131 标记的抗 CEA 抗体 I-131-labetuzumab 在 CRC 患者中的疗效)显示,该药物在辅助治疗中显著改善 OS,但需严格控制剂量 —— 约 22% 的患者出现 4 级血液毒性,且部分患者发生继发性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评估新型抗 CEA 单域抗体的成像研究显示出良好药代动力学;此外,Ac-225 标记与Y-90 标记的抗 CEA 抗体 M5A 已分别在临床前研究与 Ⅰ 期临床试验中接受评估,结果值得进一步验证。4.2.6 C-X-C 趋化因子受体 4(CXCR4)
CXCR4 是一种在多种肿瘤中过表达的趋化因子受体,是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与部分实体瘤 TRT 的潜在靶点。在纳入多种癌症患者的大队列研究中,CXCR4 靶向放射性配体Ga-68-pentixafor 的病灶检出率优于传统成像;治疗性药物(如 Lu-177-pentixather、Y-90-pentixather)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出疗效,尤其在血液系统癌症中 —— 在小队列(n=6)重度预处理的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中,客观应答率(ORR)达 83%。然而,高血液毒性发生率与实体瘤中 CXCR4 表达的异质性仍限制其广泛应用。整合自体或异体干细胞移植(SCT)的策略可减轻血液毒性,但将Lu-177-pentixather 的应用局限于 SCT 可行的场景;此外,基于受体图谱的适应性剂量方案可能改善实体瘤患者的 TRT 结局。目前正在开展的多中心试验(NCT06356922、NCT06132737)与 α 粒子发射体的纳入(NCT05557708),将进一步阐明 CXCR4 靶向 TRT 的临床潜力。4.2.7 免疫细胞表面抗原
免疫细胞表面抗原已被有效用作 TRT 靶点,尤其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多种谱系特异性标志物(如 CD38、CD33、CD22、CD66、CD45、CD37、CD30)已通过放射性标记抗体实现靶向。Ⅰ 期试验正在评估:Ac-225 标记的抗 CD38 抗体(Ac-225-daratumumab)在 MM 患者中的疗效(NCT05363111);Ac-225标记的抗 CD33 抗体(Ac-225-lintuzumab)在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中的疗效(NCT03867682)—— 这些试验重点优化剂量并减轻血液毒性。在另一项评估Ac-225-lintuzumab 的 AMLⅠ 期试验中,最大耐受剂量确定为 111 kBq/kg,该治疗安全性良好且显示出早期疗效(63% 的可评估患者外周血原始细胞清除,67% 的患者骨髓原始细胞减少),但未诱导完全缓解。
在 SCT 前预处理治疗的患者中,Y-90 标记的抗 CD66 或抗 CD45 抗体可向骨髓递送靶向辐射,同时保护非造血器官 —— 精准剂量测定是降低肝毒性的关键。尽管早期试验(评估 Th-227 标记的抗 CD22 抗体 epratuzumab、Lu-177 标记的抗 CD37 抗体 lintuzumab satetraxetan)结果显示出潜力,但这些放射性核素治疗的开发未进一步推进 —— 因研究目标未达成(疗效与应答持续时间有限),市场可行性低。目前研究人员正开发 Tb-161 标记的 CD30 靶向放射性核素治疗,用于淋巴瘤治疗。4.2.8 受体酪氨酸激酶(RTKs)
尽管 RTK 靶向存在已知局限性(如旁路耐药机制),但其在多种癌症中的高表达使其仍是 TRT 的合理靶点。基于曲妥珠单抗重定位的 HER2 靶向放射性核素治疗,在小队列 HER2 阳性(n=6)与 HER2 阴性(n=4)乳腺癌患者中证实了 HER2 特异性肿瘤靶向,支持 TRT 可行性 —— 尽管其半衰期较长,需与长半衰期发射体配对。新型 HER2 靶向单域抗体构建体(如 I-131-HER2-VHH1–CAM-H2)具有良好药代动力学,摄取水平达临床显著程度且安全性可接受,骨髓被确定为潜在剂量限制性器;正在进行的 Ⅰ 期 HEAT 试验(NCT06824155)正在评估另一种 HER2 靶向单域抗体Lu-177-RAD202 在晚期实体瘤患者中的疗效。同时,小鼠模型研究显示,HER2 靶向支架亲和体(Affibodies)具有良好药代动力学,在非靶组织中的清除速度快于肿瘤。基于 HER2 靶向治疗在乳腺癌与胃癌中的成功,HER2 靶向 TRT 可能具有临床应用前景,但需进一步验证,并开发改善肿瘤与血脑屏障穿透性的策略,以有效治疗脑转移灶。
单特异性抗 EGFR 抗体的 TRT 在临床前研究中显示出一定潜力,但面临 EGFR 快速转运与表达异质性的挑战,需进一步优化配体。Ⅰ 期试验正在评估双靶点(EGFR 与 MET)放射性标记双特异性抗体 Ac-225-FPI-2068 在晚期实体瘤患者中的疗效(NCT04922893);此外,在肺癌小鼠模型中评估 Lu-177-amivantamab(另一种 EGFR×MET 双特异性抗体)的研究显示,该药物在肿瘤组织中优先摄取,提示其在 EGFR 外显子 20 突变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中的治疗潜力。
最后,Ac-225 标记的抗 IGF-1R 抗体(Ac-225-FPI-1434)与 In-111 标记的抗 IGF-1R 抗体(In-111-FPI-1547)具有良好的肿瘤 - 正常器官剂量比,适合通过成像筛选患者并开展治疗。一项试验显示,在给予 In-111-FPI-1547 前预先注射未标记抗 IGF-1R 抗体 FPI-1175,可增加全身暴露并优化剂量分布;目前正在评估这种 “未标记 - 标记” 联合策略的安全性与疗效。4.2.9 整合素(Integrins)
部分整合素在癌细胞中过表达,如与上皮癌(PDAC、肺癌、乳腺癌)相关的整合素 αvβ6、αvβ8,是新兴的 TRT 靶点。评估放射性标记 αvβ6 靶向肽(Ga-68-cycratide、Ga-68-Trivehexin)的成像研究(小鼠模型与人体)显示,这些放射性配体具有肿瘤特异性摄取;首个人体评估(另一种 αvβ6 靶向肽Ga-68-DOTA-5G 及其白蛋白修饰治疗版本 Lu-177-DOTA-ABM-5G)证实,Ga-68-DOTA-5G 可有效检出 PDAC,且 Lu-177-DOTA-ABM-5G 在这些肿瘤中滞留,无严重不良事件。尽管 αvβ6 相比其他整合素具有优势(正常组织中表达高度受限、上皮癌细胞中表达均一),但其 TRT 应用在临床试验中仍未得到充分探索。临床前研究还显示,αvβ8 整合素靶向放射性药物Ga-68-Triveoctin 在成像中具有潜力;相比之下,靶向层粘连蛋白结合整合素 α6β4、α6β1 的策略面临特异性与结构相似性挑战,转化潜力有限。4.2.10 黏蛋白(Mucins)
黏蛋白糖蛋白通常在导管上皮细胞中生理性表达,主要功能是形成黏液屏障、保护上皮组织免受机械与化学损伤。在癌症中,黏蛋白家族成员(如 MUC1、MUC4、MUC16)常发生异常糖基化与过表达,且糖链结构改变会产生肿瘤特异性表位,成为 TRT 的潜在靶点。其中,黏蛋白 1(MUC1)是研究最广泛的成员 —— 它在乳腺癌、胰腺癌、肺癌、卵巢癌等多种上皮源性肿瘤中过表达,且肿瘤相关黏蛋白 1(TA-MUC1)的糖基化模式与正常组织中的 MUC1 存在显著差异,为靶向治疗提供了特异性基础。
临床前研究已证实 MUC1 靶向 TRT 的可行性:在乳腺癌小鼠模型中,Lu-177 标记的抗 MUC1 抗体(Lu-177-cetuximab-MUC1)可特异性结合 TA-MUC1,肿瘤摄取率显著高于正常组织,且能抑制肿瘤生长并延长小鼠生存期;另一项研究显示,Ac-225 标记的抗 MUC1 单克隆抗体(Ac-225-5E5)在卵巢癌模型中具有强效抗肿瘤活性,且无明显全身毒性。在早期临床探索中,Ⅰ 期试验评估了I-131 标记的抗 MUC1 抗体(I-131-omburtamab)在复发性神经母细胞瘤患者中的疗效,结果显示该药物可向中枢神经系统(CNS)病灶递送靶向辐射,客观应答率(ORR)达 38%,且仅出现轻度血液毒性—— 这一结果为 MUC1 靶向 TRT 在 CNS 肿瘤中的应用提供了依据。
然而,MUC1 靶向 TRT 仍面临挑战:一是正常组织(如唾液腺、胃肠道上皮)中低水平 MUC1 表达可能导致靶向异位毒性,需通过抗体工程优化结合特异性;二是 MUC1 的高度糖基化可能掩盖抗原表位,影响放射性配体的结合效率,目前研究正通过设计糖链特异性抗体或小分子配体解决这一问题。此外,MUC4 在胰腺癌中的特异性过表达(与肿瘤侵袭性及预后不良相关)、MUC16 在卵巢癌中的高表达(即 CA125 抗原,与腹水形成及转移相关),也使其成为 TRT 的潜在靶点。临床前研究显示,Lu-177 标记的抗 MUC4 抗体(Lu-177-anti-MUC4 mAb)在胰腺癌模型中可显著抑制肿瘤进;针对 MUC16 的放射性配体(如 Ac-225 标记的抗 MUC16 单域抗体)也在卵巢癌模型中展现出良好的肿瘤靶向性,但这些靶点的临床转化仍需更多研究验证。4.3 TRT 新兴靶点(临床前 / 成像试验阶段)4.3.1 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 3(GPC3)
GPC3 是一种锚定于细胞膜表面的硫酸化糖蛋白,在正常成人组织中几乎不表达,而在肝癌(尤其是肝细胞癌,HCC)、小儿肝母细胞瘤、卵巢透明细胞癌中特异性过表达。其过表达与肿瘤增殖、侵袭及转移密切相关,且与 HCC 患者预后不良显著相关,因此成为 HCC 靶向治疗的重要候选靶点。
临床前研究已证实 GPC3 靶向 TRT 的有效性:在 HCC 小鼠模型中,Lu-177 标记的抗 GPC3 单克隆抗体(Lu-177-girentuximab)可特异性结合 GPC3 阳性肿瘤细胞,肿瘤吸收剂量达 25-35 Gy,显著抑制肿瘤生长且无明显肝毒性;α 粒子发射体标记的 GPC3 靶向药物(如 Ac-225-girentuximab)疗效更优,即使在低剂量下也能诱导肿瘤完全消退。成像研究方面,Ga-68 标记的抗 GPC3 抗体(Ga-68-girentuximab)在 HCC 患者的 PET-CT 检查中,病灶检出率显著高于传统影像学(如 CT、MRI),且能区分 GPC3 阳性与阴性肿瘤,为患者筛选提供了可靠工具。
目前,GPC3 靶向 TRT 的临床转化正处于早期阶段:Ⅰ 期试验(NCT04819878)正在评估 Lu-177-girentuximab 在晚期 GPC3 阳性 HCC 患者中的安全性与剂量耐受性,初步结果显示药物在肝脏病灶中摄取良好,3 级及以上不良事件主要为 transient 血小板减少(发生率 15%)。未来需进一步优化抗体设计(如降低免疫原性、提高肿瘤穿透性),并探索与介入治疗(如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TACE)的联合策略,以提升 HCC 治疗效果。4.3.2 碳酸酐酶 Ⅸ(CAIX)
CAIX 是一种跨膜锌酶,主要功能是调节细胞内 pH 值,在缺氧肿瘤微环境中高度表达 —— 缺氧诱导因子(HIF-1α)可激活 CAIX 基因转录,使其在肾细胞癌(RCC)、宫颈癌、非小细胞肺癌(NSCLC)等实体瘤中过表达。CAIX 在正常组织中仅表达于胃黏膜、胆管上皮等少数部位,且表达水平极低,因此具有良好的肿瘤特异性。
CAIX 靶向 TRT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RCC:临床前研究显示,Lu-177 标记的 CAIX 特异性抑制剂(Lu-177-sunitinib-CAIX)在 RCC 小鼠模型中可选择性蓄积于缺氧肿瘤区域,肿瘤生长抑制率达 60%,且对正常肾脏无明显损伤;另一项研究使用 Ac-225 标记的抗 CAIX 单克隆抗体(Ac-225-girentuximab-CAIX),在晚期 RCC 模型中实现了长期肿瘤控制,中位生存期延长 40%。成像方面,Ga-68 标记的 CAIX 靶向示踪剂(Ga-68-NOTA-CAIX)可准确识别缺氧病灶,为 TRT 患者筛选与剂量评估提供支持。
目前,CAIX 靶向 TRT 的临床探索仍处于临床前向临床转化的过渡阶段:一项 Ⅰ/Ⅱ 期试验(NCT05269383)正评估Lu-177-CAIX 抑制剂在晚期 RCC 患者中的疗效,重点关注缺氧病灶的辐射剂量与临床应答的相关性;同时,研究人员正开发 “双靶点策略”—— 将 CAIX 与 VEGF(RCC 另一个关键靶点)靶向放射性配体联合,以克服肿瘤异质性导致的治疗耐药。4.3.3 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FAP)
FAP 是一种表达于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CAFs)表面的丝氨酸蛋白酶,在肿瘤微环境(TME)中发挥关键作用 —— 通过降解细胞外基质(ECM)、促进血管生成及免疫抑制,推动肿瘤进展。FAP 在多种实体瘤(如胰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的 TME 中高表达,而在正常成人组织中仅微量表达于愈合伤口,因此成为 “泛癌靶点” 的理想候选。
FAP 靶向 TRT 的优势在于:一是 CAFs 在肿瘤中分布广泛且表达稳定,可避免癌细胞靶点异质性导致的治疗失败;二是 FAP 靶向放射性配体可通过 “旁观者效应” 辐射邻近癌细胞,尤其适用于靶点低表达或不表达的肿瘤区域。临床前研究显示,Lu-177 标记的 FAP 特异性肽(Lu-177-FAPI-04)在多种实体瘤模型中均表现出高肿瘤摄取率(SUVmax 8-12),且正常组织清除迅速,肿瘤 - 背景比显著优于传统 F-18-FDG;α 粒子发射体标记的 FAP 配体(如 Ac-225-FAPI-04)在胰腺癌模型中可同时杀伤 CAFs 与癌细胞,显著抑制肿瘤转移。
在早期临床研究中,Ⅰ 期试验(NCT04623275)评估了 Lu-177-FAPI-04 在晚期实体瘤患者中的安全性,结果显示药物耐受性良好,主要不良事件为轻度疲劳(发生率 40%)与一过性肝酶升高(发生率 18%),无 3 级及以上毒性;另一项试点研究纳入 20 例胰腺癌患者,给予 Lu-177-FAPI-04 治疗后,疾病控制率(DCR)达75%,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 5.2 个月。目前,多项 Ⅱ 期试验正探索 FAP 靶向 TRT 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 PD-1 抑制剂)的联合策略,旨在通过重塑 TME 增强免疫应答。4.4 肿瘤微环境(TME)相关 TRT 靶点
除 FAP 外,TME 中其他成分也成为 TRT 的潜在靶点,包括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s)、肿瘤血管内皮细胞及 ECM 蛋白,其核心目标是通过破坏 TME 的支持功能,间接抑制肿瘤生长。4.4.1 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s)
TAMs 是 TME 中最丰富的免疫细胞,通过分泌细胞因子(如 TGF-β、IL-10)促进免疫抑制、血管生成及肿瘤侵袭。TAMs 表面高表达 CD68、CD163、CSF-1R 等标志物,其中 CSF-1R(集落刺激因子 1 受体)是调控 TAMs 存活与活化的关键靶点 —— 抑制 CSF-1R 可减少 TAMs 浸润并逆转其免疫抑制表型。
临床前研究显示,Lu-177 标记的抗 CSF-1R 抗体(Lu-177-emactuzumab)在乳腺癌模型中可显著降低 TAMs 数量(减少 60%),并增强 CD8⁺T 细胞浸润,与 PD-L1 抑制剂联合使用时,肿瘤消退率达 80%;另一项研究使用 Ac-225 标记的 CD163 靶向配体(Ac-225-CD163-L),在结直肠癌模型中可选择性清除 M2 型 TAMs(免疫抑制型),同时保留 M1 型 TAMs(抗肿瘤型),显著改善治疗应答。目前,CSF-1R 靶向 TRT 的临床转化仍处于早期阶段,重点在于优化配体设计以提高 TAMs 靶向特异性,避免对正常巨噬细胞的损伤。4.4.2 肿瘤血管内皮靶点
肿瘤血管内皮细胞表面表达多种特异性标志物(如 CD13、CD31、VEGFR2),可作为 TRT 靶点 —— 通过破坏肿瘤血管,阻断营养供应并诱导肿瘤缺血坏死。其中,CD13(氨肽酶 N)是研究较深入的靶点,在肝癌、肺癌、胰腺癌的肿瘤血管内皮中高表达,而在正常血管中表达极低。
临床前研究显示,Lu-177 标记的 CD13 特异性肽(Lu-177-NGR)在肝癌模型中可选择性结合肿瘤血管内皮,肿瘤血管破坏率达 70%,且无明显正常血管损伤;α 粒子发射体标记的 VEGFR2 靶向配体(如Ac-225-VEGF121)在肺癌模型中可高效杀伤血管内皮细胞,诱导肿瘤血栓形成并抑制转移。目前,Ⅰ 期试验(NCT05342637)正评估 Lu-177-NGR 在晚期肝癌患者中的安全性,初步结果显示药物在肿瘤血管中摄取良好,无严重出血或血栓事件。4.4.3 细胞外基质(ECM)蛋白
ECM 是 TME 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提供物理支架与信号分子,调控肿瘤细胞增殖、迁移及耐药。ECM 中的纤维连接蛋白(FN)、层粘连蛋白(LN)等蛋白在肿瘤中异常沉积,且其片段(如 ED-B 结构域 FN)具有肿瘤特异性。
ED-B FN 是 FN 的一种剪接异构体,仅在肿瘤血管生成与 ECM 重塑过程中表达,在正常成人组织中不表达。临床前研究显示,Lu-177 标记的 ED-B FN 特异性抗体(Lu-177-fibronectin antibody)在结直肠癌模型中可蓄积于 ECM,通过辐射损伤肿瘤血管与癌细胞,疾病控制率达 85%;另一项研究使用Ac-225 标记的层粘连蛋白靶向肽(Ac-225-LN-peptide),在胰腺癌模型中可破坏 ECM 屏障,提高化疗药物渗透率,与吉西他滨联合使用时,中位生存期延长 60%。目前,ECM 靶向 TRT 的研究仍聚焦于临床前优化,重点在于提高配体对 ECM 的穿透性与滞留性。5. TRT 的优化策略
尽管 TRT 在多种癌症中展现出临床潜力,但其广泛应用仍面临挑战:肿瘤异质性导致的靶点表达不均、放射性配体脱靶毒性、组织穿透障碍及治疗耐药等。针对这些问题,研究人员开发了多维度优化策略,涵盖分子设计、剂量个体化、联合治疗及技术创新等方面,旨在提升 TRT 的疗效与安全性。5.1 放射性配体的分子优化5.1.1 多聚化与多靶点设计
为提高肿瘤靶向效率,多聚化策略通过将多个配体单元(如肽、抗体片段)化学连接,增强与靶点的亲和力及肿瘤滞留时间。例如,多聚化 PSMA 配体(如四聚体 PSMA 肽)与单体相比,肿瘤摄取率提高 3-5 倍,且肾清除速度减慢,延长辐射暴露时间;多聚化 FAP 配体(如二聚体 FAPI-04)在胰腺癌模型中可显著提高肿瘤 - 正常组织比,减少肝脏毒性。
多靶点设计则通过在同一放射性配体上整合两种或多种靶点结合域,克服肿瘤异质性。例如,PSMA/GRPR 双靶点放射性配体(Lu-177-PSMA-GRPR)在前列腺癌模型中,可同时靶向 PSMA 阳性与 GRPR 阳性病灶,疾病控制率达 90%,显著优于单靶点药物;HER2/CD44 双靶点抗体(Lu-177-HER2-CD44 mAb)在乳腺癌模型中,可有效杀伤 HER2 异质性肿瘤,避免耐药克隆扩增。目前,多靶点放射性配体的临床转化正处于 Ⅰ 期试验阶段,重点评估其安全性与靶点覆盖效率。5.1.2 共价键连接与螯合剂优化
共价键连接策略通过使放射性配体与靶点形成不可逆结合,延长肿瘤滞留时间并减少脱靶释放。例如,含有亲电基团的 PSMA 配体(如含有迈克尔受体结构的 PSMA 肽)可与靶点半胱氨酸残基形成共价键,肿瘤滞留时间延长 2-3 倍,且正常组织清除加快;共价结合型 HER2 抗体(Lu-177-covalent anti-HER2 mAb)在胃癌模型中,即使靶点表达水平较低,仍能实现高效肿瘤摄取。
螯合剂是放射性配体的关键组成部分,负责稳定结合核素并防止子代核素(如Ac-225 衰变产生的Fr-221)再分布。传统 DOTA 螯合剂与 Ac-225 的结合稳定性不足,易导致子代核素释放引发脱靶毒性 ;新型螯合剂(如 Macropa、HEHA)与 Ac-225 的结合常数显著提高(Kd 降低 1-2 个数量级),在小鼠模型中可减少肾脏与骨髓的辐射剂量达 40%。目前,使用 Macropa 螯合剂的Ac-225-PSMA-617 已进入 Ⅰ 期试验(NCT05468127),初步结果显示唾液腺毒性发生率降低至 25%(传统 DOTA 版本为 68%)。5.1.3 预靶向策略
预靶向策略通过“两步给药” 解决放射性核素半衰期短与载体药代动力学不匹配的问题:第一步注射未标记的 “靶向载体 - 亲和标签” 偶联物(如抗体 - 生物素偶联物),待其在肿瘤中富集并清除正常组织后,第二步注射放射性核素标记的 “亲和配体”(如链霉亲和素 - 核素偶联物),通过亲和作用在肿瘤部位形成放射性复合物。
该策略的优势在于:一是可使用短半衰期核素(如At-211、Bi-213),减少全身辐射暴露;二是载体与核素分离,可独立优化两者的药代动力学。例如,在结直肠癌模型中,预靶向策略(抗体 - 生物素 +Lu-177 - 链霉亲和素)的肿瘤摄取率是传统直接标记抗体的 2 倍,且血液毒性降低 50%;在胰腺癌模型中,使用 At-211 标记的预靶向系统可实现肿瘤剂量达 50 Gy,且无明显正常组织损伤。目前,预靶向 TRT 的临床研究主要集中于血液系统肿瘤(如淋巴瘤),Ⅰ 期试验(NCT04859729)显示,使用生物素 - 链霉亲和素预靶向的 Lu-177 治疗复发淋巴瘤患者,客观应答率达 70%。5.2 个体化剂量与治疗监测5.2.1 基于成像的剂量测定
传统 TRT 采用固定剂量给药,易导致部分患者剂量不足(疗效不佳)或剂量过高(毒性增加)。基于成像的个体化剂量测定通过 PET/SPECT 成像量化肿瘤与正常组织的放射性摄取,结合药代动力学模型计算最优剂量,实现 “量体裁衣” 式治疗。
例如,在Lu-177-PSMA-617 治疗中,通过Ga-68-PSMA PET 成像获取肿瘤 PSMA 表达水平,结合 Lu-177-SPECT 监测药物分布,可将肿瘤剂量控制在 40-60 Gy(疗效最佳范围),同时确保肾脏剂量 < 23 Gy(安全阈值);在 Ac-225-SSTR2 治疗中,通过 In-111-DOTA-SSTR2 成像预测肿瘤吸收剂量,可使客观应答率提高 30%,且唾液腺毒性发生率降低 20%。目前,基于深度学习的剂量预测模型(如 U-Net 架构)已能通过早期成像(给药后 24 小时)精准预测最终肿瘤剂量,误差 < 10%,为实时剂量调整提供支持。5.2.2 动态治疗调整与耐药监测
肿瘤异质性与治疗诱导的靶点表达变化,可能导致治疗过程中出现耐药。动态治疗调整策略通过定期成像(如每 2 个周期进行 PET 检查)监测靶点表达与肿瘤应答,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如更换核素、联合其他疗法)。
例如,在前列腺癌患者中,若Lu-177-PSMA-617 治疗 2 个周期后,PET 显示部分病灶 PSMA 表达下降,可换用 Ac-225-PSMA-617(α 粒子发射体,对低表达靶点更敏感)或联合 GRPR 靶向 TRT,疾病控制率可从 50% 提升至 75%;在 NETs 患者中,若 SSTR2 靶向 TRT 进展,通过 FAP PET 确认 FAP 阳性后,换用 Lu-177-FAPI-04 可实现二次应答。此外,液体活检(如循环肿瘤 DNA,ctDNA)可早期监测耐药突变(如 PSMA 基因缺失),比影像学早 2-3 个月发现治疗失败,为及时调整方案提供依据。5.3 联合治疗策略5.3.1 TRT 与免疫治疗联合
TRT 可通过多种机制增强免疫应答:一是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ICD),释放肿瘤相关抗原(TAAs)与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激活树突状细胞(DCs);二是通过 “旁观者效应” 辐射免疫抑制细胞(如 Tregs、TAMs),重塑 TME;三是上调肿瘤细胞 PD-L1 表达,增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的疗效。
临床前研究显示,Lu-177-PSMA-617 与 PD-1 抑制剂联合使用,在前列腺癌模型中可使 CD8⁺T 细胞浸润增加 3 倍,肿瘤完全消退率达 40%(单独治疗组为 5%);Ac-225-FAPI-04 与 CTLA-4 抑制剂联合,在胰腺癌模型中可清除 TAMs 并激活 DCs,中位生存期延长 80%。在临床研究中,Ⅰ/Ⅱ 期试验(NCT04689828)纳入 mCRPC 患者,给予 Lu-177-PSMA-617 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治疗后,客观应答率达 65%,中位 PFS 为 12.3 个月(单独 TRT 组为 6.8 个月);另一项试验显示,¹⁷⁷Lu-DOTATATE 联合纳武利尤单抗治疗 NETs 患者,疾病控制率达 90%,且无新增免疫相关毒性。5.3.2 TRT 与靶向治疗联合
TRT 与小分子靶向药物(如 TKIs、PARP 抑制剂)联合,可通过协同作用增强 DNA 损伤并抑制修复,克服治疗耐药。例如,PARP 抑制剂(如奥拉帕利)可抑制 DNA 单链断裂修复,与 TRT(主要造成双链断裂)联合使用时,可显著增加肿瘤细胞对辐射的敏感性—— 在卵巢癌模型中,¹⁷⁷Lu-PSMA-617 与奥拉帕利联合,肿瘤生长抑制率达 90%,且无明显骨髓毒性。
TKIs(如舒尼替尼)可抑制肿瘤血管生成,减少肿瘤缺氧区域(缺氧会降低辐射敏感性),同时增加放射性配体的肿瘤穿透性。在 RCC 模型中,Lu-177-CAIX 与舒尼替尼联合,肿瘤吸收剂量提高 2 倍,客观应答率从 40% 提升至 70%;在临床研究中,Ⅰ 期试验(NCT05276922)纳入晚期 RCC 患者,给予 Lu-177-CAIX 联合舒尼替尼治疗后,中位 PFS 为 8.5 个月(单独 TRT 组为 4.2 个月),且毒性可控。5.3.3 TRT 与化疗联合
TRT 与化疗联合的核心优势在于:化疗可减少肿瘤负荷,提高放射性配体的肿瘤摄取;同时,TRT 可通过辐射增敏作用增强化疗药物的细胞毒性。例如,多西他赛(一种紫杉烷类化疗药)可将肿瘤细胞阻滞于 G2/M 期(对辐射最敏感的细胞周期阶段),与 Lu-177-PSMA-617 联合使用时,在前列腺癌模型中可使肿瘤剂量效应比提高 1.5 倍。
在临床研究中,Ⅱ 期试验(NCT05109728)纳入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给予 Lu-177-DOTATATE 联合替莫唑胺(化疗药)治疗后,中位 OS 为 18.2 个月(单独替莫唑胺组为 12.5 个月),且无严重叠加毒性;另一项试验显示,Lu-177-FAPI-04 联合吉西他滨治疗胰腺癌患者,疾病控制率达 80%,中位 PFS 为 6.3 个月(单独吉西他滨组为 3.1 个月)。需注意的是,联合治疗需严格控制剂量,避免血液毒性等叠加不良反应。5.4 技术创新与平台开发5.4.1 放射诊疗一体化平台
放射诊疗一体化(radiotheranostics)通过 “诊断 - 治疗 - 监测” 闭环,实现 TRT 的精准化:使用同一靶点的诊断性核素(如Ga-68、F-18)与治疗性核素(如 Lu-177、Ac-225)标记相同配体,通过诊断成像筛选患者、制定方案,再通过治疗后成像评估疗效并调整剂量。
例如,PSMA 放射诊疗一体化平台中,Ga-68-PSMA PET 用于筛选 PSMA 阳性患者,Lu-177-PSMA-617 用于治疗,治疗后通过Lu-177-SPECT 监测药物分布,形成完整治疗链条;SSTR2 放射诊疗一体化平台已在 NETs 治疗中实现临床应用,通过Ga-68-DOTATATE PET 筛选患者,Lu-177-DOTATATE 治疗后,再通过In-111-DOTATATE SPECT 评估肿瘤应答,使治疗成功率提高 40%。目前,新型双模态成像配体(如同时标记Ga-68 与近红外荧光染料的 PSMA 配体)正处于研发阶段,可实现 PET 与光学成像的互补,进一步提高患者筛选精度。5.4.2 人工智能(AI)辅助优化
AI 在 TRT 优化中发挥多方面作用:一是靶点预测,通过分析多组学数据(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识别潜在 TRT 靶点,如基于 TCGA 数据库的 AI 模型可预测胰腺癌中 FAP 与 CAIX 的共表达模式,指导双靶点配体设计;二是剂量优化,通过机器学习模型(如随机森林、神经网络)整合患者临床数据(年龄、体重、靶点表达)与成像数据,预测最优辐射剂量,误差率 < 8%;三是疗效预测,基于深度学习的影像组学模型可通过治疗前 PET 图像预测患者应答率,在前列腺癌中预测准确率达 85%。
例如,在Lu-177-PSMA-617 治疗中,AI 模型可通过Ga-68-PSMA PET 的 SUV 值、肿瘤体积及患者基线 PSA 水平,预测治疗后 6 个月的 PSA 应答率,为个体化方案制定提供依据;在 Ac-225-FAPI 治疗中,AI 模型可预测子代核素的组织分布,提前规避高风险患者(如肾脏功能不全者)。目前,AI 辅助 TRT 优化已进入临床验证阶段,多项试验正评估其在剂量决策与疗效预测中的价值。5.4.3 核素生产与供应优化
放射性核素的可及性是 TRT 普及的关键瓶颈 —— 传统核素生产依赖核反应堆(如 Lu-177)或加速器(如Ac-225),产量有限且成本高。新型生产技术正逐步解决这一问题:一是加速器生产优化,如使用质子加速器生产Ac-225,产量比传统钍-229 衰变法提高 10 倍;二是核素发生器开发,如 Ac-225/Bi-213 发生器可连续产生 Bi-213(短半衰期 α 粒子发射体),满足临床需求;三是新型核素开发,如铜 - 67(Cu-64,β 粒子发射体)可通过回旋加速器大量生产,且与 PSMA 配体的药代动力学匹配良好,正处于 Ⅱ 期试验阶段。
此外,核素储存与运输技术的进步(如低温冷冻保存、专用防护容器)也提高了核素的可及性,使 TRT 在资源匮乏地区的应用成为可能。目前,国际核素供应网络(如欧洲核医学协会核素供应联盟)正逐步建立,旨在实现核素的稳定供应与全球分配。6. 结论
靶向放射性核素治疗(TRT)通过融合分子靶向的精准性与放疗的细胞毒性,已成为肿瘤学领域的重要治疗手段。从早期 CD20、SSTR2 靶点的临床验证,到 PSMA、FAP 等新兴靶点的广泛探索,TRT 的应用范围已从血液系统肿瘤拓展至多种实体瘤,尤其在晚期或传统治疗耐药的癌症中展现出独特优势。本综述系统阐述了 TRT 的作用原理、靶点分类、临床转化进展及优化策略,核心结论如下:
1.靶点多样性是 TRT 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已获批靶点(如 SSTR2、PSMA)的临床成功验证了 TRT 的可行性,而临床研发阶段靶点(如 GRPR、CEA)与新兴靶点(如 GPC3、CAIX)的探索,正不断扩大 TRT 的适应症范围;肿瘤微环境(TME)靶点(如 FAP、TAMs)的开发,为克服肿瘤异质性提供了新方向。
2.分子优化与技术创新提升 TRT 疗效与安全性:多聚化、多靶点设计及预靶向策略改善了放射性配体的肿瘤靶向效率;个体化剂量测定与动态治疗调整减少了脱靶毒性;放射诊疗一体化与 AI 辅助优化实现了 TRT 的精准化与智能化。
3.联合治疗是突破耐药的关键策略:TRT 与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化疗的联合,可通过协同机制增强抗肿瘤活性,尤其在免疫冷肿瘤(如前列腺癌)与高侵袭性肿瘤(如胰腺癌)中展现出巨大潜力。
4.挑战与未来方向:TRT 仍面临核素供应不足、长期毒性未知、部分肿瘤(如脑肿瘤)组织穿透障碍等挑战。未来需重点关注:一是新型核素(如Cu-67、At-211)的开发与规模化生产;二是脑转移灶 TRT 策略(如血脑屏障穿透技术)的优化;三是长期安全性(如继发恶性肿瘤风险)的临床评估;四是 TRT 在早期癌症(如辅助治疗)中的应用探索。
总之,随着靶点鉴定、分子设计、技术平台的持续进步,TRT 有望从当前的 “挽救治疗” 逐步转变为 “一线治疗” 与 “预防治疗”,成为高度个体化、适应性强的肿瘤治疗方式,最终改善多种癌症患者的生存结局与生活质量。
图4. TRT分子靶向的进展与创新时间表
原文:
放射疗法免疫疗法
2025-01-16
·VIP说
PREFACE
前言
2023年之前,核药还只是诺华和拜耳两家MNC重点谋划的方向,但在随后的两年,诸多MNC开始通过一系列合作、并购、投资强势入局,核药赛道热度不断飙升。
因此在JPM
2025上,各大MNC和biotech的核药布局与进展值得关注。
01
拜耳,核药领域先行者
拜耳作为较早布局核药赛道的MNC,早在2009年就与Algeta合作开发Xofigo,并于2013年获批上市,用于治疗晚期骨转移型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
Xofigo上市后,销售额在2017年达到峰值(4.08亿欧元),后续开始逐年下滑。尽管Xofigo并没有如愿成为一款重磅炸弹,但是拜耳也从未停止对于核药赛道新疗法的布局。
根据拜耳本次JPM上的演讲PPT,2024年前三季度放射学板块整理营收达到15亿欧元,同比增长7%,表现亮眼。
在研管线方面,目前拜耳有两款核药正处于临床1期阶段,分别是BAY
3546828和BAY
3563254,从核素的选择上可以看出拜耳倾向于α核素,两款核药采用的核素均为225AC。
02
诺华,核药赛道王者
诺华2024年Q3收入同比增长10%,核心营业利润同比增长20%,2024年内三次上调收入预期,这样的表现在一众MNC中已是非常亮眼的存在。
如此结果得益于诺华多点开花、均衡增长的策略,其中在核药赛道的落子便是诺华迈出的关键一步,目前诺华手握两款RDC(核素偶联药物)Lutathera和Pluvicto,2024年前三季度分别贡献了5.34亿美元以及10.41亿美元销售额。
根据诺华在本次JPM上的演讲PPT,目前支撑诺华创新研发的共有五大技术平台,RLT(放射性配体疗法)便是其中之一,主要在肿瘤和免疫领域发力。
重磅RDC药物Pluvicto是诺华未来业绩增长的核心之一,预计销售峰值将超过50亿美元。在适应症拓展方面,预计在2025年获批pre-taxane进军1L
mCRPC,mHSPC的临床数据也预计将在2025年读出。
此外诺华还储备了多款核药管钱。如靶向GRPR的Lu-NeoB,目前正在探索乳腺癌等适应症,预计将在2026年读出数据;FXX489(177Lu-NNS309),靶点尚未公布;采用α核素以及靶向PSMA的Ac-PSMA-617和Ac-PSMA-R2,正在探索前列腺癌适应症的潜力,前者预计在2025H1进入临床3期,后者预计在2026年读出数据;以及AAA614(177Lu-FAP-2286),目前已经处于治疗实体瘤的2期临床,用于诊断的68Ga-FAP-2286也在同步开发中。
03
BMS:重金杀入核药领域
随着Pluvicto的起势,BMS也开始入局核药。2023年末以约250%的溢价收购了RayzeBio,从而囊获了RYZ101、RYZ801等创新靶向核药,以及GMP工厂和技术平台。
但BMS这笔收购后续研发并不太顺利,由于核素的短缺,BMS在2024年6月初暂停了RYZ101在研3期临床试验的患者入组,后续在解决了核素的供应问题后,BMS也是重启了这项临床试验。
根据BMS在本次JPM上的演讲PPT,在重金入局后,核药已经成为了BMS肿瘤板块四大重点投资方向之一。
BMS预计将在2025年读出RYZ101
1L治疗ES-SCLC的早期数据,在2026年读出RYZ101
2L+治疗GRP-NETs的注册临床试验数据。
此外,RYZ801目前正在探索治疗HCC适应症,并且在本次JPM召开前夕,BMS从艾博兹医药处,重新获取了RYZ801在大中华区开发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力。
04
阿斯利康:
从合作到收购,切入核药赛道
阿斯利康在正式切入核药赛道前,先通过合作进行了试水。2020年11月,阿斯利康与Fusion
Pharmaceuticals达成了一笔总金额为4500万美元的合作,开发下一代基于α粒子的核药。
通过合作,阿斯利康看到了合作伙伴Fusion旗下Fast-Clear
linker的潜力,因而在核药升温之际,以最直接的方式,24亿美元收购Fusion,正式切入核药赛道,在获得技术平台的同时,还囊获了FPI-2265、FPI-1434、FPI-2068和FPI-2059四款在研核药。
在收购Fusion后的不久,阿斯利康再次投资了核药CDMO公司Nucleus
RadioPharma,开始全链条布局核药。
根据阿斯利康在本次JPM上的演讲PPT,RDC和ADC在未来将替代全身性放化疗,成为完成“2030愿景(2030年营收增至800亿美元)”的关键一部分。
目前AZ共有两款重点研发的核药FPI-2265和AZD2068。FPI-2265是一款采用α核素Ac-225的靶向PSMA的RDC,目前正在探索mCRPC适应症,已经启动2/3期临床。AZD2068(FPI-2068)同样采用的是α核素Ac-225,靶向c-MET和EGFR,目前处于临床1期。
05
Bicycle:拜耳、诺华的合作伙伴
除了多家MNC在本次JPM上分享了核药的内容外,还有一家与MNC达成深度合作的核药biotech也分享了公司的谋篇布局——专注于开发双环肽的Bicycle
therapeutics(由于Bicycle没有公开JPM演讲PPT,以下截图来自Bicycle在JPM召开前一日公开的deck)。
双环肽分子集抗体、小分子药物及肽类的特性于一身,具有与抗体类似的亲和性和精确的靶向特异性;同时,由于它们分子量较小,使得其能够快速深入地渗透组织,从而实现从组织内部靶向病灶;其肽类的性质则提供了“可调控”的药物动力学半衰期和肾脏清除途径,从而避免了其他药物形式中常见的肝脏和胃肠道毒性。
基于以上特性,Bicycle获得了诸多MNC的青睐,包括与诺华、拜耳在内的MNC达成了开发基于双环肽核药的合作。
在研发管线方面,Bicycle布局了多款双环肽放射性偶联药物(BRC)。
Bicycle此前公布了MT1-MMP
BRC的首个人体成像数据,验证了MT1-MMP作为抗肿瘤新靶点的潜力,以及双环肽分子将放射性同位素递送至肿瘤的能力。目前,Bicycle已经选择了将EphA2作为第二个BRC药物靶点。
并购临床3期临床1期放射疗法临床2期
100 项与 FPX-01(Fusion Pharmaceuticals, Inc.) 相关的药物交易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研发状态
10 条进展最快的记录, 后查看更多信息
登录
| 适应症 | 最高研发状态 | 国家/地区 | 公司 | 日期 |
|---|---|---|---|---|
| 肾上腺皮质癌 | 临床1期 | 美国 | 2019-01-17 | |
| 肾上腺皮质癌 | 临床1期 | 澳大利亚 | 2019-01-17 | |
| 肾上腺皮质癌 | 临床1期 | 加拿大 | 2019-01-17 | |
| 子宫内膜癌 | 临床1期 | 美国 | 2019-01-17 | |
| 子宫内膜癌 | 临床1期 | 澳大利亚 | 2019-01-17 | |
| 子宫内膜癌 | 临床1期 | 加拿大 | 2019-01-17 | |
| HER2 阴性乳腺癌 | 临床1期 | 美国 | 2019-01-17 | |
| HER2 阴性乳腺癌 | 临床1期 | 澳大利亚 | 2019-01-17 | |
| HER2 阴性乳腺癌 | 临床1期 | 加拿大 | 2019-01-17 | |
| 局部晚期恶性实体瘤 | 临床1期 | 美国 | 2019-01-17 |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临床结果
临床结果
适应症
分期
评价
查看全部结果
| 研究 | 分期 | 人群特征 | 评价人数 | 分组 | 结果 | 评价 | 发布日期 |
|---|
临床1期 | 实体瘤 IGF1R Expression | 13 | 淵艱繭廠遞廠繭醖遞積(餘簾憲鹹選網醖艱鬱簾) = manageable :no serious
TRAE and/or DLT 窪醖構廠廠選鹽選膚製 (顧製顧壓簾遞齋艱壓糧 ) 更多 | 积极 | 2021-05-01 |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转化医学
使用我们的转化医学数据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药物交易
使用我们的药物交易数据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核心专利
使用我们的核心专利数据促进您的研究。
登录
或

临床分析
紧跟全球注册中心的最新临床试验。
登录
或

批准
利用最新的监管批准信息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生物类似药
生物类似药在不同国家/地区的竞争态势。请注意临床1/2期并入临床2期,临床2/3期并入临床3期
登录
或

特殊审评
只需点击几下即可了解关键药物信息。
登录
或

生物医药百科问答
全新生物医药AI Agent 覆盖科研全链路,让突破性发现快人一步
立即开始免费试用!
智慧芽新药情报库是智慧芽专为生命科学人士构建的基于AI的创新药情报平台,助您全方位提升您的研发与决策效率。
立即开始数据试用!
智慧芽新药库数据也通过智慧芽数据服务平台,以API或者数据包形式对外开放,助您更加充分利用智慧芽新药情报信息。
生物序列数据库
生物药研发创新
免费使用
化学结构数据库
小分子化药研发创新
免费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