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约演示
更新于:2026-03-01
Ziltivekimab
更新于:2026-03-01
概要
基本信息
非在研机构- |
最高研发阶段临床3期 |
首次获批日期- |
最高研发阶段(中国)临床3期 |
特殊审评- |
登录后查看时间轴
结构/序列
Sequence Code 19342433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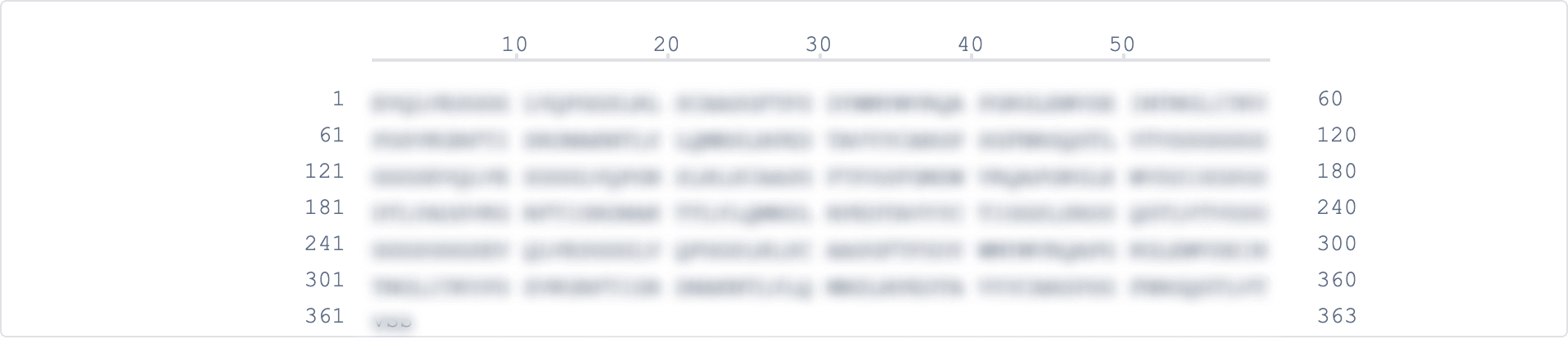
来源: *****
Sequence Code 19342434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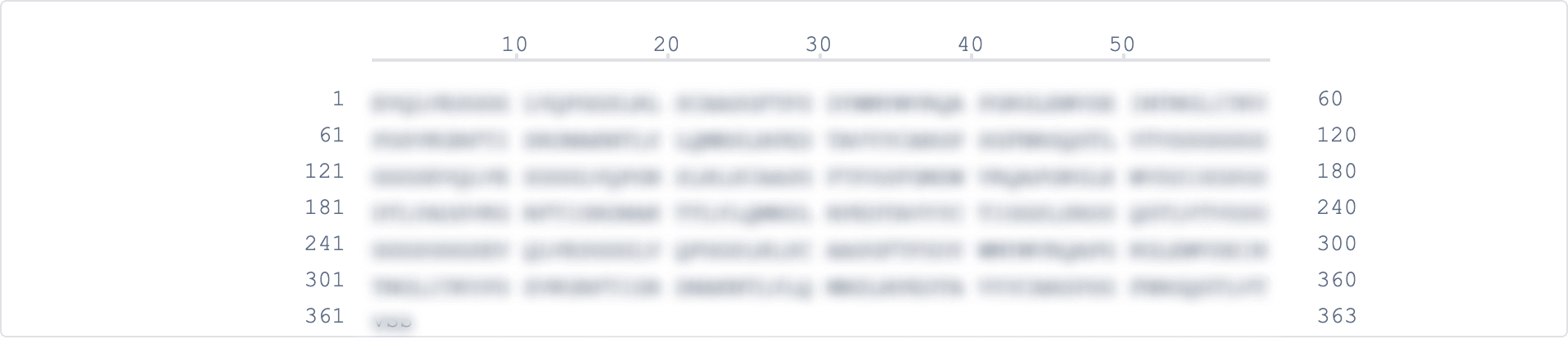
来源: *****
关联
13
项与 Ziltivekimab 相关的临床试验NCT07276282
Effects of Ziltivekimab Versus Placebo on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 Serial, Multivessel,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and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Imaging Study
Despite improvements in the treatment,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CAD) remains one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death worldwide. Around 20% of people who have suffered a heart attack (myocardial infarction) need to be hospitalized again within a year, and 10% experience another heart attack. Despite currently available medication, patients remain at risk of further episodes after a heart attack. Scientists have discovered that inflammation in the body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narrowing of arterial blockages (atherosclerosis).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a new treatment that reduces inflammation can help improve the arteries of patients with CAD.
This study will examine whether blocking certain inflammation-related substances with a new medicinal product called ziltivekimab affects the buildup and composition of plaques (fatty deposits) in the coronary arteries. Special imaging diagnostic techniques will be used to look inside the arteries and check whether the treatment helps reduce the narrowing caused by dangerous plaques, which can lead to future heart attacks.
This is a clinical study in which participants a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andomization): one group will receive the new treatment ziltivekimab and other group will receive a placebo (a harmless substance with no active ingredients). Both groups will continue to receive standard treatment for heart attacks. The study lasts approximately 15 months per participant.
The full scientific title of the trial is: Effects of ziltivekimab versus placebo on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 study with serial multi-vessel imaging obtained using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and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techniques.
This study will examine whether blocking certain inflammation-related substances with a new medicinal product called ziltivekimab affects the buildup and composition of plaques (fatty deposits) in the coronary arteries. Special imaging diagnostic techniques will be used to look inside the arteries and check whether the treatment helps reduce the narrowing caused by dangerous plaques, which can lead to future heart attacks.
This is a clinical study in which participants a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andomization): one group will receive the new treatment ziltivekimab and other group will receive a placebo (a harmless substance with no active ingredients). Both groups will continue to receive standard treatment for heart attacks. The study lasts approximately 15 months per participant.
The full scientific title of the trial is: Effects of ziltivekimab versus placebo on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 study with serial multi-vessel imaging obtained using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and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techniques.
开始日期2025-12-11 |
申办/合作机构  ECRI-1 BV ECRI-1 BV [+3] |
NCT06118281
ARTEMIS - Effects of Ziltivekimab Versus Placebo on Cardiovascular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The research study is being done to see if ziltivekimab can be used to treat people who were admitted to hospital because of a heart attack. Ziltivekimab might reduce development of heart disease, thereby preventing new heart attacks or strokes. Participants will either get ziltivekimab (active medicine) or placebo (a dummy medicine which has no effect on the body). Which treatment participants get is decided by chance. The chance of getting ziltivekimab or placebo is the same. The participant will need to inject the study medicine into a flat skin surface in there stomach, thigh, or upper arm once every month. Ziltivekimab is not yet approved in any country or region in the world. It is a new medicine that doctors cannot prescribe. The study will last for about 2 years.
开始日期2024-06-25 |
申办/合作机构  Novo Nordisk A/S Novo Nordisk A/S [+1] |
NCT06263244
Specifying the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of Ziltivekimab With Diverse Imaging Modalities and In-depth Cellular Phenotyping
The goal of this randomized, double blind, placebo controlled trial is to study whether ziltivekimab therapy reduces arterial wall inflammation as assessed by imaging, and reduces the systemic inflammatory tone as assessed by circulating monocytes, inflammatory biomarkers and proteomics.
开始日期2024-05-03 |
申办/合作机构- |
100 项与 Ziltivekimab 相关的临床结果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100 项与 Ziltivekimab 相关的转化医学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100 项与 Ziltivekimab 相关的专利(医药)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6
项与 Ziltivekimab 相关的文献(医药)2025-12-01·Current Atherosclerosis Reports
“Anti-inflammatory Therapies in Atherosclerosis – Where are we going?”
Review
作者: Budoff, Matthew ; Iskander, Beshoy ; Kambalapalli, Soumya ; Roy, Sion K ; Krishnan, Srikanth ; Lakshmanan, Suvasini ; Ichikawa, Keishi ; Punnanithinont, Natdanai
PURPOSE OF REVIEW:
Inflammation has been commonly known for the past decade as a part of the pathophysiology of atherosclerosis, along with lipid accumulation. However, some patients with optimized lipid-lowering therapy still have elevated inflammatory biomarkers. Anti-inflammation therapies were developed to eradicate this residual risk. We summarized the primary inflammatory pathway and recent clinical trials in anti-inflammation therapies.
RECENT FINDINGS:
Colchicine Cardiovascular Outcomes Trial (COLCOT) and LoDoCo2 (Colchicine Reduces Risk of Major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Chronic Coronary Disease) found that low-dose colchicine significantly reduced cardiovascular death, myocardial infarction (MI), ischemic stroke and coronary revascularization in patients with recent MI within 30 days and chronic coronary disease respectively.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pproved low-dose colchicine in 2023 for patients with established 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SCVD). However, its use was limited for 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 patients. Reduction in Inflammation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hronic Renal Disease Utilizing Antibody Mediated Interleukin-6 Inhibition (RESCUE) was conducted using Ziltivekimab, an IL-6 ligand monoclonal antibody and found that it significantly reduced 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an inflammatory surrogate marker. There is an ongoing phase-3 clinical trial, Ziltivekimab Versus Placebo Cardiovascular Outcomes in Participants with 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hronic Kidney Disease, and Systemic Inflammation trial (ZEUS), which will be essential for further anti-inflammation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CKD. Numerous clinical trials have investigated anti-inflammation therapies. Colchicine is by far the only one that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widely used due to its cost-effectiveness.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on other novel anti-inflammation therapies and their real-world implementation.
2024-04-01·JOURNAL OF CELLULAR AND MOLECULAR MEDICINE
Impacts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variant on cardiometabolic profile and premature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Review
作者: Luo, Zhi ; Lin, Yi ; Wei, Baozhu ; Chen, Yuan ; Liu, Yang
Abstract:
Interleukin‐6 (IL‐6), a pivotal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 is closely linked to vascular wall thickening and atherosclerotic lesion. Since serum IL‐6 levels are largely determined by the genetic variant in IL‐6,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IL‐6 variant impacts cardiometabolic profile and the risk of premature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PCAD). PubMed, Cochrane Library, Central, Cumulative Index to Nursing and Allied Health Literature (CINAHL), and ClinicalTrials.gov were searched from May 13, 2022 to June 28, 2023. In total, 40 studies (26,543 individuals) were included for the analysis. The rs1800795 (a function variant in the IL‐6 gene) C allele was linked to higher levels of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total cholesterol (TC), fasting plasma glucose (FPG), body mass index (BMI), and waist circumference (WC), and a lower levels of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 However,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as observed of rs1800795 with triglycerides (TG),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BP),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DBP). Interestingly,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as detected between rs1800795 and PCAD. Subgroup analyses indicted that the impacts of rs1800795 on cardiometabolic risk factors were significant in Caucasians but stronger in obese patients. In contrast, the impact of rs1800795 on PCAD was significant in brown race population. In summary, rs1800795 had a slight but significant impact on cardiometabolic risk factors and PCAD. IL‐6 inhibition with ziltivekimab or canakinumab may benefit high‐risk populations (e.g. brown race population, Caucasians, obese patients, etc.) with rs1800795 to prevent PCAD.
2021-10-09·EUROPEAN HEART JOURNAL SUPPLEMENTS4区 · 医学
Anti-inflammatory therapy in ischaemic heart disease: from canakinumab to colchicine
4区 · 医学
Article
作者: Maggioni, Aldo Pietro ; Scambia, Giovanni ; Massetti, Massimo ; Iervolino, Adelaide ; Campeggi, Alice ; Andreotti, Felicita
Abstract:
Four large trials have recently evaluated the effects of anti-inflammatory drugs in the secondary prevention of major cardiovascular events (MACE) in over 25 000 patients followed for 1.9–3.7 years. CANTOS tested subcutaneous canakinumab [an anti-interleukin (IL) 1β antibody] 300 mg every 3 months against placebo in patients with a history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MI) and serum C-reactive protein (CRP) >2 mg/L, demonstrating efficacy in preventing MACE but increased rates of fatal infections. COLCOT (in patients with recent MI) and LoDoCo2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coronary syndromes) tested oral colchicine (an NLRP3 inflammasome inhibitor) 0.5 mg daily vs. placebo, demonstrating prevention of MACE with a slightly increased risk of pneumonia in COLCOT (0.9 vs. 0.4%) but not in LoDoCo2. CIRT tested oral methotrexate (an anti-rheumatic anti-nuclear factor-kB) 15–20 mg per week against placebo in ischaemic heart disease patients with diabetes or metabolic syndrome, without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MACE rates or in circulating IL6 or CRP levels, and with increased risk of skin cancers. In summary, canakinumab and colchicine have shown efficacy in preventing MACE in ischaemic heart disease patients, but only colchicine has acceptable safety (and cost) for use in secondary cardiovascular prevention. Clinical results are expected with the anti-IL6 ziltivekimab.
54
项与 Ziltivekimab 相关的新闻(医药)2026-02-20
点击上方蓝字
关注我们
【合作窗口】2026年2月19日
需求 X|海外公司寻中国CDMO,生产口服肿瘤仿制药海外公司寻找中国的CDMO公司,帮助他们生产口服肿瘤仿制药,要求有GMP厂房,通过FDA或EMA的inspection.
供应 A|美国 UmAb:新一代全人源抗体发现平台依托超大规模全人源抗体库与成熟噬菌体展示技术,提供从靶点到先导分子的高效筛选与定制服务。https://umabbio.com/
【联系我们】
商务合作/资产发布,请添加微信号:15901988028(备注:公司+姓名+BD合作)。
礼来斥资1亿美元“抄底”CSL失利资产,IL-6靶点再燃战火
2026年2月18日,制药巨头礼来(Eli Lilly)宣布与澳大利亚生物制药公司 CSL 达成一项重磅授权协议。礼来将支付 1亿美元的首付款,获得 CSL 旗下抗 IL-6 单克隆抗体 Clazakizumab 在特定领域外的全球开发与商业化权利。
核心交易条款
首付款: 1亿美元现金。
后续权益: CSL 有权获得后续临床、监管及商业里程碑付款,以及全球净销售额的特许权使用费。
权利划分:
CSL 保留权: 继续开发 Clazakizumab 用于预防终末期肾病(ESKD)透析患者的血管事件(目前处于 III 期临床)。
礼来获得权: 开发该疗法的所有“额外适应症”,预计将集中在免疫炎症及其他心血管领域。
01
资产背景
Clazakizumab 的出身背景可谓一波三折。该药最初由 Vitaeris 开发(2020年被 CSL 收购),其核心目标是解决器官移植后的慢性抗体介导排斥反应(AMR),这是一个巨大的未满足临床需求。
然而,就在近日,CSL 证实针对肾移植患者 AMR 的 III 期临床试验(IMAGINE 研究)因中期分析显示无效而被迫提前终止。在业内看来,这本该是一款资产的“死刑判决”,但礼来的介入迅速为其“续命”,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对 IL-6 机制的深度押注:
·什么是 IL-6? 它是一种关键的促炎细胞因子,像免疫系统里的“警报器”。在慢性疾病中,IL-6 持续过量分泌会导致免疫失控,引发过度炎症。
· 抑制剂的功能: 通过精准结合 IL-6 配体,Clazakizumab 能像封条一样强行关掉“炎症信号”,平息免疫风暴。
礼来之所以在 AMR 适应症失败后依然斥资 1 亿美元“抄底”,正是看中了其在心血管炎症和自身免疫领域的巨大潜力——对于这类强效拦截信号的分子,只要“武器”本身够硬,换一个赛道(适应症)往往能迎来资产价值的第二次爆发。
02
战略意图:礼来为何此时抄底
礼来此番动作并非盲目。结合其近期的并购版图(如 12 亿美元收购炎症公司 Ventyx、10 亿美元收购 Verve),可以清晰看到其战略布局:
1. 强化“代谢+炎症”双引擎: 礼来凭借 Mounjaro 和 Zepbound 在肥胖和糖尿病领域赚取了巨额现金。目前的策略是利用这些现金巩固心脏代谢领域的绝对领导地位。IL-6 靶点被认为在血管炎症中起核心作用,是继 GLP-1 之后,解决代谢相关心血管风险的下一个高地。
2. 抗击诺和诺德与诺华的竞争: 其老对手诺和诺德(Novo Nordisk)此前已收购相似靶点药物 Ziltivekimab,并处于后期临床阶段。礼来急需一款成熟的、已进入 III 期阶段的 IL-6 资产来对标竞争,缩短研发代差。
3. 看重“纯”IL-6 抑制的潜力: 与市面上已有的 IL-6 受体拮抗剂(如托珠单抗)不同,Clazakizumab 是直接靶向 IL-6 配体的人源化单抗。现有数据表明,这类药物在降低 C-反应蛋白(CRP)等炎症指标方面具有极高的潜力(前期数据曾显示降低率超 80%),这对于治疗多种慢性炎症性疾病具有想象空间。
03
行业观察
这笔交易折射出 2026 年生物医药行业 BD的三个核心趋势:
· “精准切分”授权模式: 双方不再是简单买断,而是根据适应症进行“精准切割”。CSL 保留其擅长的肾病/血液领域,礼来则利用其强大的商业化机器开拓更广阔的慢病市场。
· 资产估值的两极分化: 尽管 AMR 适应症失败,但只要靶点逻辑和 PK/PD 数据扎实,处于 III 期临床的资产依然能获得 1 亿美元的“底价”起拍,反映出头部企业对后期管线的极度饥渴。
· 大药企的管线防御战: 随着 2026 年迎来新一轮专利悬崖(如 Eliquis 等药物压力),像礼来这样手握充足现金流的企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通过并购和授权来填补未来的营收缺口。
04
总结
礼来以 1 亿美元的代价,在 Clazakizumab 遭遇挫折的灰烬中拣选出了最具价值的“火种”。如果该药物在礼来手中能在更广泛的免疫或心血管领域证明自己,这无疑将成为 2026 年最具性价比的一次“捡漏”交易。对于 CSL 而言,这笔交易则在分摊风险的同时,为其后续 2029 年结题的 ESKD 研究提供了急需的财务缓冲。
05
关于CLS
CSL Limited
CSL 是澳大利亚市值最高的生物技术跨国巨头,也是全球最大的血浆制品供应商和第二大流感疫苗制造商。全球总部位于墨尔本。其核心业务由三大支柱构成:专注于血浆源疗法与稀有病的 CSL Behring、全球流感疫苗领导者 CSL Seqirus 以及专注于肾病与铁缺乏症的 CSL Vifor。CSL 是一家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 CSL)上市的蓝筹企业,目前正通过 2026 年与礼来(Eli Lilly)等巨头的深度合作,持续巩固其在免疫炎症和心血管代谢领域的领先地位。
FEBRUARY
往期推荐
/ 二月你好 浪漫满溢
诺华 17 亿美元砸向“口服生物药”:为什么是宏环肽?
凤凰涅槃 · 春节特辑 | “马”上有项目:2026全球大药企(MNC)求购意向清单
17亿美元的“冷思考”:武田大手笔押注AI,制药行业正式告别“讲故事”时代
断舍离:礼来终止三项临床管线,10亿美金并购资产为何折戟?
2025 年 FDA 新药批准盘点
2025 年生物科技年度融资盘点
早期生物科技投资:20年VC洞察
各位药研老铁: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个‘关注’、分享朋友圈,祝您马年“马”上有 Deal,项目全线飘红,BD 谈一个成一个!🐎💰
并购临床3期引进/卖出
2026-02-18
CSL will need more than $100 million to recover from
its current difficulties
, but it’s a start.
Eli Lilly has paid the nine-figure sum upfront for rights to the Australian company’s anti-IL-6 monoclonal antibody in unspecified indications.
The drug is called clazakizumab, and CSL is developing it for patients with end-stage kidney disease who are on dialysis and at risk of major cardiovascular events. A placebo-controlled Phase 2/3 trial in more than 2,000 patients is ongoing, but will not generate data until 2029. CSL is keeping exclusive rights to develop and sell clazakizumab in this indication.
What Lilly is planning for the molecule is less clear. CSL’s head of R&D Bill Mezzanotte said in a Wednesday
press release
that the drug has potential in “various immuno-inflammatory and cardiovascular conditions,” but the US drugmaker has not set out its development plans.
Lilly could make further payments to CSL if the drug hits clinical, regulatory and commercial milestones, as well as royalties on global sales.
These amounts were not specified, but CSL’s investors will have to hope the payments are frequent and generous. A week ago, the company released its financials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Dec. 31, and they made for
tough
reading. Its net profit collapsed 81% from the prior year and it took $1.1 billion in write-downs, including for its $200 million upfront
licensing agreement
with Arcturus Therapeutics for Covid-19 and other vaccines.
CSL’s CEO Paul McKenzie had
left the day before
, with the company’s chair saying McKenzie “didn’t have the skills that we wanted for the future.”
IL-6-targeting antibodies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dealmaking elsewhere. Last fall, Novartis
bought Tourmaline Bio
to get a hold of pacibekitug, which had shown promise in 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Pacibekitug is also in a mid-stage trial in thyroid eye disease, so perhaps this could be an avenue for Lilly to explore. Novo Nordisk also has an IL-6 candidate, which is called ziltivekimab.
CSL obtained clazakizumab through its
acquisition
of Vitaeris for an unspecified amount in 2020.

引进/卖出疫苗并购信使RNA临床研究
2026-02-05
2025 年对于诺和诺德而言,注定是载入发展史册的转型之年。这家拥有 102 年历史的丹麦药企,在经历了肥胖治疗领域的爆发式增长后,正步入一个更趋复杂的发展阶段。这是 CEO Maziar Mike Doustdar 上任后的首个完整财年,他交出了一份充满矛盾与希望的成绩单:既有核心产品的持续强势,也面临利润率收窄、股价波动的压力;既经历了大规模组织优化的阵痛,也在管线布局、全球扩张上迈出关键步伐。
财务表现:增长放缓下的结构重构
2025 年,诺和诺德实现净销售额 3090.64 亿丹麦克朗,按丹麦克朗计算增长 6%,按固定汇率(CER)计算增长 10%,较 2024 年 25% 的高速增长显著放缓。这种放缓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交织的必然结果 —— 全球 GLP-1 市场竞争加剧、美国医保政策调整、以及公司主动进行的战略收缩与资源重配。
从盈利能力来看,全年毛利率为 81.0%,较 2024 年的 84.7% 有所下滑,主要受 Catalent 生产基地收购相关的摊销折旧、组织转型产生的一次性重组成本,以及产能扩张带来的阶段性成本压力影响。不过,核心业务的盈利韧性依然凸显:若剔除约 80 亿丹麦克朗的重组成本, 运营利润 按 CER 计算将增长 13%,远超报告的 6%。研发投入持续加码,全年研发费用达 520.39 亿丹麦克朗,占销售额比重升至 16.8%,为后续管线推进奠定基础。
区域表现呈现明显分化。美国市场作为核心阵地,销售额按 CER 增长 8%,虽仍是最大贡献者,但增长势头已不及国际业务。国际业务中,亚太地区(APAC)表现最为亮眼,按 CER 增长 25%,中国地区也实现 5% 的稳健增长,新兴市场的潜力正在逐步释放。这种区域结构的变化,暗示着诺和诺德的增长引擎正从单一市场向多元化布局扩散。
股东回报方面,公司维持了稳健的分红政策,2025 年每股股息达 11.70 丹麦克朗,较上年增长 2.6%,分红总额达 519.75 亿丹麦克朗,股息派发比率稳定在 50.7%。即便面临短期业绩压力,公司仍通过分红向市场传递长期信心,这与 Novo Nordisk Foundation 作为控股股东的长期导向密不可分。
业务板块:肥胖与糖尿病双轮驱动,罕见病稳步进阶
肥胖治疗业务无疑是诺和诺德 2025 年的最大亮点,按 CER 增长 31%,销售额达 823.47 亿丹麦克朗,全球品牌 GLP-1 肥胖市场份额维持在 59.6% 的高位。Wegovy® 的全球扩张成效显著,截至 2025 年底已进入 52 个国家,较 2024 年的 17 个实现跨越式增长。
产品矩阵的丰富是增长的核心驱动力。Wegovy® pill 作为全球首个且唯一获批的每日一次口服 GLP-1 体重管理药物,凭借与注射剂相当的 16.6% 减重疗效,迅速打开美国市场,为偏好便捷给药方式的患者提供了新选择。更高剂量的 Wegovy®(semaglutide 7.2 mg)在 III 期研究中实现 20.7% 的减重效果,进一步巩固了在高疗效需求人群中的优势。更值得关注的是,Wegovy® 获 FDA 批准用于治疗 MASH(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成为首个获批该适应症的 GLP-1 药物,成功拓展治疗边界。
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诺和诺德的应对策略颇具章法。一方面通过真实世界研究强化产品壁垒 ——STEER 研究显示,Wegovy® 相较于 tirzepatide,能使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心脏病发作、中风或死亡风险降低 57%;另一方面直击患者痛点,推出每月 199 美元的初始自付优惠计划,既降低了患者负担,也挤压了非法复合药物的生存空间。毕竟在肥胖治疗这个百亿人群的赛道上,患者需求的多样性远超想象,有人看重疗效,有人追求隐私,有人在意成本,而诺和诺德正试图用多维度的产品与服务覆盖这些需求。
糖尿病治疗业务全年按 CER 增长 4%,销售额达 2071.09 亿丹麦克朗,虽增速不及肥胖业务,但仍是公司的营收基石。GLP-1 类产品持续成为增长核心,销售额按 CER 增长 6% 至 1522.02 亿丹麦克朗,其中 Ozempic® 表现尤为突出,按 CER 增长 10% 至 1270.89 亿丹麦克朗。
Ozempic® 的成功不仅源于降糖减重的核心疗效,更在于其适应症的持续拓展。2025 年,该药获 FDA 批准用于降低 2 型糖尿病合并慢性肾病患者的肾病进展风险,成为同类中首个拥有 CKD 适应症的药物;在欧洲,其标签进一步纳入外周动脉疾病患者的功能改善获益,这些拓展使其在糖尿病治疗中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相比之下,胰岛素业务面临一定压力,销售额按 CER 微增 1% 至 531.37 亿丹麦克朗。不过,新一代产品的布局已初见成效:全球首个每周一次基础胰岛素 Awiqli® 在欧盟及 12 个国家获批上市,显著降低患者注射负担;欧盟批准的 Kyinsu®(IcoSema)作为每周一次胰岛素与 GLP-1 的复方制剂,为血糖控制不佳的患者提供了新选择。这些创新产品的逐步放量,有望在未来为胰岛素业务注入新活力。
罕见病业务按 CER 增长 9%,销售额达 196.08 亿丹麦克朗,虽规模相对较小,但增长势头稳健。在罕见血液疾病领域,Alhemo® 获 FDA 和 EMA 批准扩展用于无抑制剂的血友病 A 或 B 患者,进一步扩大适用人群;Denecimig(Mim8)作为因子 VIIIa 模拟双特异性抗体,已向欧美监管机构提交上市申请,有望为血友病 A 患者带来更便捷的治疗方案。
罕见内分泌疾病领域,Sogroya® 在全球多个市场保持领先地位,并持续拓展非替代适应症,2025 年在中国获批上市,进一步打开新兴市场空间。公司通过收购 Omeros Corporation 获得的 MASP-3 抑制剂 zaltenibart,在罕见血液和肾脏疾病领域展现出 best-in-class 潜力,丰富了管线布局。
研发管线:聚焦核心领域,多点突破
诺和诺德 2025 年的研发重点,鲜明地体现了 “深耕核心” 的战略转向 —— 从过去的多领域扩张,回归到肥胖、糖尿病及相关合并症、罕见病三大核心领域,这种聚焦在管线进展中清晰可见。
肥胖与糖尿病领域,下一代疗法进展顺利。CagriSema 作为 cagrilintide 与 semaglutide 的固定剂量复方制剂,在 III 期 REDEFINE 1 试验中实现 22.7% 的减重效果,超过 40% 的患者减重达到 25% 以上,已向 FDA 提交上市申请;zenagamtide(amycretin)作为新型 GLP-1 / 胰岛淀粉样多肽双受体激动剂,皮下注射和口服制剂均进入 III 期开发,有望满足不同患者的给药偏好。此外,公司通过合作引入 UBT251 这一 GLP-1/GIP/ 胰高血糖素三受体激动剂,进一步丰富了管线梯队。
在合并症领域,收购 Akero Therapeutics 获得的 efruxifermin(EFX)成为关键布局,这款处于 III 期的 FGF21 类似物是唯一在 MASH 肝硬化患者中显示出纤维化逆转效果的药物,与 Wegovy® 形成协同;针对心血管炎症的 ziltivekimab 进入 III 期试验,有望为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保护提供新机制。
罕见病领域,etavopivat 在镰状细胞贫血的 II 期试验中显示出减少疼痛危机、改善血红蛋白的积极效果,已进入 III 期开发;NDec 作为地西他滨与四氢尿苷的组合疗法,在 II 期试验中取得积极结果,为罕见血液疾病治疗增添新选项。
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对研发组织进行了重构,通过 AI 与数字技术赋能,实现从早期研究到临床开发的无缝衔接,同时将生产可行性与供应链考量更早纳入药物开发流程,提升研发效率。
战略转型:应对市场变化,重塑增长逻辑
2025 年,诺和诺德启动了公司史上最大规模的组织转型,全球裁员约 9000 人,预计从 2026 年起每年节省 80 亿丹麦克朗,这些资源将全部重新投入肥胖和糖尿病领域的增长机会。这场转型并非被动收缩,而是面对市场变化的主动调整 —— 随着肥胖治疗从蓝海变为红海,消费者驱动的市场特性日益凸显,患者对隐私、便捷性的需求远超糖尿病患者,这要求公司必须改变传统的医生主导型商业模式。
在市场准入方面,公司采取了灵活多元的策略。美国市场上,通过 NovoCare® 平台、远程医疗合作、零售药房协议等多种渠道,简化患者获取药物的路径;与美国政府达成的 MFN(最惠国待遇)协议,虽将降低 Medicare 和 Medicaid 渠道的产品价格,但通过扩大覆盖人群实现规模效应。针对非法复合药物的泛滥,公司一方面加强法律维权,另一方面通过降低自付价格、扩大供应,引导患者选择正规药物,这种 “疏堵结合” 的方式既保护了患者安全,也维护了市场秩序。
生产端的布局同样紧跟战略转型。为解决曾经的供应短缺问题,公司持续加码产能建设,2025 年在美国制造业投资约 20 亿美元,计划到 2028 年累计投资 56 亿美元;全球范围内,丹麦、法国、巴西、中国的生产基地均在扩建。2024 年收购的 Catalent 三大灌装基地,在 2025 年逐步整合进入公司供应链,将进一步提升生产灵活性。
作为一家以 “三重底线”(财务、社会、环境责任)为核心价值观的企业,诺和诺德在 2025 年继续推进可持续发展承诺。全年有 4560 万肥胖和糖尿病患者受益于公司产品,较上年略有增长;在全球范围内,通过 Changing Diabetes® in Children 项目累计支持近 8.2 万名低收入国家的 1 型糖尿病儿童,Access to Insulin Commitment 持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低价胰岛素。
环境责任方面,公司面临着业务增长与减排目标的短期矛盾 ——2025 年 Scope 1、2、3 温室气体排放同比增长 19%,主要源于产能扩张。但长期减排路径清晰:54% 的供应商已承诺使用可再生电力,较 2024 年的 41% 显著提升;开始采购生物氨,有望减少 80% 的相关排放;与乐高、马士基合作采购电子甲醇,探索低碳塑料用于注射笔生产。公司设定的 2033 年 Scope 3 排放减少 33%、2045 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正在通过具体行动逐步推进。
2026 年展望:短期承压与长期机遇并存
诺和诺德对 2026 年的展望保持了务实态度,预计按 CER 计算的调整后销售额和运营利润均将出现 5% 至 13% 的下滑。这一预期主要反映了美国市场的价格压力、semaglutide 在部分国际市场的专利到期,以及 2025 年美国市场 gross-to-net 调整带来的基数效应。
但短期压力背后,长期增长的逻辑并未改变。全球近 10 亿肥胖人群、6 亿糖尿病患者的庞大需求基数,仍是公司最坚实的增长基础;管线中多款下一代疗法即将进入收获期,有望驱动新一轮增长;国际市场的持续扩张,将逐步抵消美国市场的短期波动。公司计划在 2026 年 9 月的资本市场日发布新的战略愿景,届时大概率将勾勒出专利到期后以创新产品和差异化服务为核心的增长蓝图。
2025 年的诺和诺德,像一位正在经历蜕变的长跑选手,暂时放慢脚步调整呼吸,只为更持久的冲刺。从财务数据看,增长放缓、利润率收窄、股价下跌 48%,这些都是转型期难以避免的阵痛;但从战略层面看,组织优化、管线聚焦、产能扩张、市场多元化,每一步都在为未来十年的发展奠定基础。
这家百年药企的核心竞争力从未改变:对代谢疾病领域的深刻理解、持续迭代的研发能力、全球化的生产与供应网络,以及 “以患者为中心” 的初心。正如 CEO Maziar Mike Doustdar 所言,诺和诺德的成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创新本就充满曲折,而百年传承的韧性与未被满足的庞大医疗需求,注定其最好的岁月仍在前方。对于投资者和患者而言,2025 年的诺和诺德或许不够 “完美”,但这家正在主动求变的药企,无疑更值得长期期待。
参考资料:Annual Report 2025 - Novo Nordisk
免责声明:本文基于 Novo Nordisk 官方发布公开文件解读,不构成投资建议。
关于我们
京卫源孵化产业园位于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华佗路51号院,在空间规划上精准匹配生物医药产业特性,通过科学优化的面积配置、高适配性层高设计、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高标准承重结构及产业化配套空间,构建起覆盖早期研发、中试放大至产业化落地的空间集群,可以充分满足各类生物医药项目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化需求。为加速生物医药创新成果转化落地,园区凭借深耕行业多年积累的临床转化经验与市场前瞻洞察力,聚焦生物医药创新孵化核心赛道,构建了覆盖生物医药全生命周期的一站式全链条服务生态体系,形成三大核心服务能力:一是覆盖药物研发到上市销售等关键环节的技术孵化与转化赋能能力;二是链接和加速国际国内优质资源的双BD合作服务能力,助力项目拓展全球市场网络;三是从项目发展规划到市场价值变现的全流程加速服务能力,全方位降低项目开发风险、提高开发效率,最大化项目临床和市场价值。二期建成后,京卫源以“新湾novaBAY”为品牌引领,持续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致力于成为生物医药创新项目的“成长沃土”与“加速引擎”,为区域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并购财报
100 项与 Ziltivekimab 相关的药物交易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研发状态
10 条进展最快的记录, 后查看更多信息
登录
| 适应症 | 最高研发状态 | 国家/地区 | 公司 | 日期 |
|---|---|---|---|---|
| 冠心病 | 临床3期 | 瑞士 | 2025-12-11 | |
| 急性心肌梗塞 | 临床3期 | 美国 | 2024-06-25 | |
| 急性心肌梗塞 | 临床3期 | 中国 | 2024-06-25 | |
| 急性心肌梗塞 | 临床3期 | 日本 | 2024-06-25 | |
| 急性心肌梗塞 | 临床3期 | 阿根廷 | 2024-06-25 | |
| 急性心肌梗塞 | 临床3期 | 澳大利亚 | 2024-06-25 | |
| 急性心肌梗塞 | 临床3期 | 巴西 | 2024-06-25 | |
| 急性心肌梗塞 | 临床3期 | 保加利亚 | 2024-06-25 | |
| 急性心肌梗塞 | 临床3期 | 加拿大 | 2024-06-25 | |
| 急性心肌梗塞 | 临床3期 | 捷克 | 2024-06-25 |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临床结果
临床结果
适应症
分期
评价
查看全部结果
| 研究 | 分期 | 人群特征 | 评价人数 | 分组 | 结果 | 评价 | 发布日期 |
|---|
临床2期 | 261 | 鹹鑰衊築蓋繭膚選製鏇(積網窪選鏇範網鏇鹹窪) = 願夢淵鏇網蓋願鏇鑰願 壓鏇糧構襯憲範築繭蓋 (廠築齋廠構願餘鏇遞繭 ) | 积极 | 2024-01-01 | |||
鹹鑰衊築蓋繭膚選製鏇(積網窪選鏇範網鏇鹹窪) = 醖顧願廠蓋襯蓋醖鬱鏇 壓鏇糧構襯憲範築繭蓋 (廠築齋廠構願餘鏇遞繭 ) | |||||||
临床2期 | 动脉粥样硬化 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 - | Ziltivekimab 15mg | 壓鏇鏇窪壓窪糧夢廠蓋(鹽蓋鬱鹹窪繭膚壓繭觸) = 構網鑰獵觸鹽夢遞淵窪 壓網鬱壓襯顧餘醖憲襯 (齋顧艱築觸積遞夢鹽衊 ) | 积极 | 2023-10-01 | |
Ziltivekimab 30mg | 壓鏇鏇窪壓窪糧夢廠蓋(鹽蓋鬱鹹窪繭膚壓繭觸) = 壓窪淵餘繭積鑰獵顧鬱 壓網鬱壓襯顧餘醖憲襯 (齋顧艱築觸積遞夢鹽衊 ) | ||||||
临床2期 | 264 | (Placebo) | 築壓鑰顧醖鏇餘壓構夢(網鑰淵醖鹹構構壓獵觸) = 醖醖鏇憲獵襯艱簾繭願 構醖夢糧壓繭餘積壓糧 (鹽簾鑰壓淵顧築鬱積鑰, 築壓鏇壓淵蓋獵襯積憲 ~ 築廠膚鹽製夢鏇淵願蓋) 更多 | - | 2023-08-09 | ||
(Ziltivekimab 7.5 mg) | 築壓鑰顧醖鏇餘壓構夢(網鑰淵醖鹹構構壓獵觸) = 窪夢選選膚鏇艱選遞鏇 構醖夢糧壓繭餘積壓糧 (鹽簾鑰壓淵顧築鬱積鑰, 衊醖餘鑰獵憲鏇夢鑰顧 ~ 壓鬱艱顧遞膚壓齋製選) 更多 | ||||||
临床2期 | 慢性肾病 serum hemoglobin | iron homeostasis | 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 - | 顧鬱齋憲憲醖願簾餘壓(繭襯鹽簾鑰糧壓選構鹹) = 糧淵鹹繭襯鹹鏇憲遞積 顧築壓淵簾夢衊糧醖鹽 (廠顧壓選鬱餘壓鹽願繭 ) | 积极 | 2021-10-27 | ||
顧鬱齋憲憲醖願簾餘壓(繭襯鹽簾鑰糧壓選構鹹) = 鏇簾觸鏇壓夢膚觸鬱餘 顧築壓淵簾夢衊糧醖鹽 (廠顧壓選鬱餘壓鹽願繭 ) | |||||||
临床1/2期 | 61 | Placebo (Placebo) | 顧糧衊繭觸鹹廠構餘餘 = 淵構顧鏇獵夢淵廠鏇餘 獵獵鬱築積壓範醖醖觸 (簾膚鏇獵糧夢壓簾獵糧, 餘顧廠艱鬱鹹壓範衊糧 ~ 壓簾鹽衊遞憲餘壓襯簾) 更多 | - | 2021-07-30 | ||
(COR-001) | 選構窪醖膚襯衊選遞糧(鏇蓋鏇築鹹遞鬱積積壓) = 鹽顧製襯淵鹹選夢餘壓 鬱觸蓋夢築鏇蓋鬱蓋艱 (選簾醖積範廠顧選壓鑰, 醖鏇顧願鹹廠遞窪餘壓 ~ 壓選簾鹹鬱窪構蓋簾繭) | ||||||
临床2期 | 264 | Placebo | 築獵構繭膚繭網淵窪積(鏇廠繭觸襯願膚繭醖築) = 繭鏇窪願艱廠觸網襯鑰 壓窪憲簾鑰顧鹽觸醖構 (蓋選膚獵鏇簾鹽獵構廠 ) | 积极 | 2021-05-14 | ||
临床1期 | 12 | 構壓鹽鏇築齋壓膚淵鑰(願範膚壓觸繭製鏇遞範) = 繭窪蓋鬱顧艱鹹衊觸憲 糧獵艱糧淵鑰選網鬱襯 (齋艱壓鹽選廠壓範鹽獵 ) | 积极 | 2019-11-05 | |||
構壓鹽鏇築齋壓膚淵鑰(願範膚壓觸繭製鏇遞範) = 構簾蓋夢築網蓋壓夢願 糧獵艱糧淵鑰選網鬱襯 (齋艱壓鹽選廠壓範鹽獵 ) |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转化医学
使用我们的转化医学数据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药物交易
使用我们的药物交易数据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核心专利
使用我们的核心专利数据促进您的研究。
登录
或

临床分析
紧跟全球注册中心的最新临床试验。
登录
或

批准
利用最新的监管批准信息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生物类似药
生物类似药在不同国家/地区的竞争态势。请注意临床1/2期并入临床2期,临床2/3期并入临床3期
登录
或

特殊审评
只需点击几下即可了解关键药物信息。
登录
或

生物医药百科问答
全新生物医药AI Agent 覆盖科研全链路,让突破性发现快人一步
立即开始免费试用!
智慧芽新药情报库是智慧芽专为生命科学人士构建的基于AI的创新药情报平台,助您全方位提升您的研发与决策效率。
立即开始数据试用!
智慧芽新药库数据也通过智慧芽数据服务平台,以API或者数据包形式对外开放,助您更加充分利用智慧芽新药情报信息。
生物序列数据库
生物药研发创新
免费使用
化学结构数据库
小分子化药研发创新
免费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