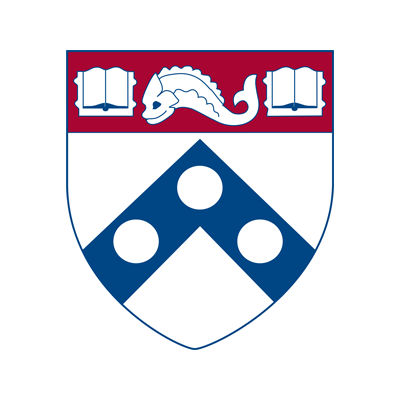预约演示
更新于:2026-02-27
Lomitapide Mesylate
甲磺酸洛美他派
更新于:2026-02-27
概要
基本信息
药物类型 小分子化药 |
别名 Lojuxta、lomitapide、Lomitapide Mesilate + [7] |
靶点 |
作用方式 抑制剂 |
作用机制 MTTP抑制剂(微粒体甘油三酯转运蛋白复合体抑制剂) |
非在研适应症 |
最高研发阶段批准上市 |
首次获批日期 美国 (2012-12-21), |
最高研发阶段(中国)批准上市 |
特殊审评孤儿药 (美国)、孤儿药 (欧盟)、临床急需境外新药 (中国) |
登录后查看时间轴
结构/序列
分子式C40H41F6N3O5S |
InChIKeyQKVKOFVWUHNEBX-UHFFFAOYSA-N |
CAS号202914-84-9 |
关联
20
项与 甲磺酸洛美他派 相关的临床试验NCT04681170
Phase III, Single Arm, Open Label, International, Multi Centre Study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Lomitapide in Paediatric Patients With Homozygous Familial Hypercholesterolaemia (HoFH) on Stable Lipid Lowering Therapy
This is a single arm, open label, multi centre phase III study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long term safety of lomitapide in paediatric patients with HoFH receiving stable lipid lowering therapy (LLT) (including lipoprotein apheresis (LA), when applicable) comprising of the following phases:
* Screening Period (starting at Week 12, i.e. ≤12 weeks prior to Baseline for up to 6 weeks)
* Stratified Enrolment and Start of Run in Period (starting at minimum at Week 6, i.e., 6 weeks prior to Baseline for a minimum of 6 weeks):
* Efficacy Phase (starting at Baseline, i.e. Day [D] 0 for 24 weeks±3 days
* Safety Phase (starting at Week 24±3 days for 80±1 weeks)
* Screening Period (starting at Week 12, i.e. ≤12 weeks prior to Baseline for up to 6 weeks)
* Stratified Enrolment and Start of Run in Period (starting at minimum at Week 6, i.e., 6 weeks prior to Baseline for a minimum of 6 weeks):
* Efficacy Phase (starting at Baseline, i.e. Day [D] 0 for 24 weeks±3 days
* Safety Phase (starting at Week 24±3 days for 80±1 weeks)
开始日期2020-12-14 |
申办/合作机构 |
EUCTR2018-002911-80-IT
Open-label study to evaluate the safety, tolerability, and efficacy of LOmitapide for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Familial CHylomicroNEmia Syndrome
开始日期2018-12-18 |
NCT02765841
A Phase 3, Single-arm, Open-label, International, Multi-center Study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Lomitapide i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Homozygous Familial Hypercholesterolemia on Stable Lipid-lowering Therapy
This is a Phase 3 single-arm, open-label, international, multi-center clinical trial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lomitapide i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HoFH who are receiving stable lipid-lowering therapy, including LDL apheresis. The study is comprised of a 12-week Run-in Period, a primary 24-week Efficacy Phase, followed by an 80-week Safety Phase.
开始日期2016-05-01 |
100 项与 甲磺酸洛美他派 相关的临床结果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100 项与 甲磺酸洛美他派 相关的转化医学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100 项与 甲磺酸洛美他派 相关的专利(医药)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176
项与 甲磺酸洛美他派 相关的文献(医药)2026-02-01·THERAPEUTIC APHERESIS AND DIALYSIS
Article
作者: Bigazzi, Federico ; Zenti, Maria Grazia ; Medde, Paolo ; Casula, Manuela ; Catapano, Alberico L. ; Corciulo, Carmen ; Sbrana, Francesco ; Dal Pino, Beatrice ; Sampietro, Tiziana
ABSTRACT:
Introduction:
To date, despite the new lipid‐lowering drugs, some subjects do not reach LDL‐cholesterol and/or lipoprotein(a) [Lp(a)] goals and lipoprotein apheresis (LA) plays a role in atherosclerosis prevention.
Method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paint a portrait of the current LA activity in Italy, collecting data via an electronic survey.
Results:
Forty‐seven centers were contacted, data from 142 patients (male 67%) were obtained from 15 sites. Two sites had discontinued LA treatment. In the active sites, a median of 17 [14–26] LA treatment/patient per year was performed; 7/13 sites used more than one LA system, with venous vascular access used in 87% of cases. High Lp(a) plasma concentrations (> 60 mg/dL or ≥ 145 nmol/L) were recorded in 73/142 patients; 14/36 homozygous familial hypercholesterolemia patients were on lomitapide or evinacumab therapy.
Conclusion:
The PORTRAIT survey would like to promote a network to better manage the patients on chronic LA.
2026-02-01·EUROPEAN JOURNAL OF IMMUNOLOGY
Discovery of Lomitapide as a Novel Mast Cell Regulatory Agent Through Chemical Library Screening
Article
作者: Nagata, Yuka ; Suzuki, Ryo ; Mamorita, Shiori ; Furukawa, Atsushi
ABSTRACT:
Allergic diseases are a global health concern, and new molecular insights and therapeutic agents are necessary to support future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s. Mast cells (MC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allergic reactions, in which antigen (Ag) cross‐linking of high‐affinity receptors (FcεRI) activates signaling pathways, leading to the release of various types of inflammatory mediators. We developed a chemical library screening system using RBL‐2H3 cells, a widely used MC model, to identify anti‐allergic agents. This method revealed that lomitapide, a microsomal triglyceride transfer protein (MTTP) inhibitor, is a novel MC regulatory agent. Furthermore, lomitapide was found to inhibit MC degranulation by altering MC plasma membrane dynamics, specifically by preventing endocytosis of plasma membrane components, rather than through the conventional MTTP‐inhibiting mechanism. Additionally, experiments using a passive cutaneous anaphylaxis (PCA) mouse model demonstrated that lomitapide dampened anaphylactic reactions in vivo.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lomitapide effectively inhibits MC degranulation, which affects allergic responses, suggesting that lomitapide exhibits a novel MC regulatory function and has potential as an anti‐allergic therapeutic agent.
2026-01-02·JOURNAL OF BIOMOLECULAR STRUCTURE & DYNAMICS
Computational approach towards repurposing of FDA approved drug molecules: strategy to combat antibiotic resistance conferred by
Pseudomonas aeruginosa
Article
作者: Chatterjee, Debolina ; Sivashanmugam, Karthikeyan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is recognized as a major worldwide public health dilemma in the current century. Pseudomonas aeruginosa, a Gram-negative opportunistic pathogen, causes nosocomial infections like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dermatitis, and cystic fibrosis. It manifests antibiotic resistance via intrinsic, acquired, and adaptive pathways, where efflux pumps function in the extrusion of antibiotics from the cell. MexB protein, part of the tripartite efflux pumps MexAB-OprM present in P.aeruginosa, expels the penems and β-lactam antibiotics, thereby enhancing Pseudomonas resistance. The current study was intended to screen around 1602 clinically approved drugs to understand their ability to inhibit the MexB protein. Amongst them, the top 5 drug molecules were selected based on the binding energies for analyzing their physio-chemical and toxicity properties. Lomitapide was found to have the maximum negative binding energy followed by Nilotinib, whereas Nilotinib's number of hydrogen bond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Lomitapide. ADMET study revealed that all 5 drug molecules had limited solubility. Also, Lomitapide and Venetoclax showed low bioavailability scores, while Nilotinib, Eltrombopag, and Conivaptan demonstrated higher potential for therapeutic levels. A molecular dynamic simulation study of the 5 drugs against MexB was carried out for 200 nanoseconds. The RMSD, RMSF, Hydrogen bond formation, Radius of gyration, SASA, PCA, DCCM, DSSP and MM-PBSA binding energy calculation along with demonstrated high stability of the MexB-Nilotinib complex with lesser distortions. Our study concludes, that Nilotinib is a potential inhibitor and can be developed as a therapeutic agent against MexB protein for controlling P. aeruginosa infections.
79
项与 甲磺酸洛美他派 相关的新闻(医药)2026-02-26
类别
· 前言 ·
每年2月的最后一天,是国际罕见病日。
2026年2月28日,我们也将迎来第19个国际罕见病日,今年的全球主题为不止罕见(More than you can imagine),意在告诉世界:罕见病群体的困境,远不止疾病本身;他们的生命,也远不止“罕见”二字。
作为患者组织,我们也将在罕见病日前后组织一系列的科普宣传活动。
今天我们对纯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Homozygous Familial Hypercholesterolemia,HoFH)的现有治疗手段进行了总结,方便大家查看了解。
一、传统降脂治疗(LDL-R依赖性)
01. 他汀类药物(Statins)
他汀类药物
序号类别内容
01
代表药物
阿托伐他汀、瑞舒伐他汀、普伐他汀等
02
上市时间
1987年(洛伐他汀首个获批)
03
治疗原理
竞争性抑制HMG-CoA还原酶,减少肝细胞内胆固醇合成,反馈性上调LDL-R表达,促进LDL清除
04
降脂效果
30%-60%(剂量依赖性)
05
HoFH应用
基础治疗,但对LDL受体阴性患者效果有限
06
临床试验/数据EXCEL研究(8245例普通高胆固醇血症患者):证实
了他汀类药物改善血脂的疗效和安全性;HoFH患者中需大剂量(阿托伐他汀40-80mg或瑞舒伐他汀20-40mg)
07
主要副作用
肝损伤(转氨酶升高>3倍约1%)、肌病、妊娠期禁用
02. 依折麦布(Ezetimibe)
依折麦布
序号类别内容
01
上市时间
2002
02
治疗原理
抑制肠道NPC1L1转运蛋白,阻断胆固醇(饮食和胆汁)的肠道吸收,减少肝脏胆固醇储备,间接上调LDL-R
03
降脂效果
单药5%-14%,与他汀联用可达18%-21%
04
HoFH应用
二线治疗,与他汀联合使用
05临床试验/数据
50例HoFH患者研究:依折麦布+他汀40/80mg组较单用他汀80mg组LDL降低更显著(-21.4% vs -6.6%);日本6例HoFH患者研究显示可减少血液净化后LDL反弹
06
主要副作用
腹痛、腹泻、头痛、乏力(ALT升高1.3%)
二、PCSK9抑制剂(LDL-R依赖性,需残留受体功能)
01. 依洛尤单抗(Evolocumab)
伊洛尤单抗
序号类别内容
01
上市时间
2015年(美国)
02
治疗原理
全人源化单克隆抗体,结合循环PCSK9蛋白,阻止其与LDL-R结合,减少LDL-R降解,增加LDL清除
03
降脂效果
HoFH患者15%-32%(取决于残余LDL-R活性)
04
用法用量
皮下注射,每2周140mg或每4周420mg
05临床试验/数据
TESLA B研究(1050例≥12岁HoFH患者,12周):Evolocumab 420mg每4周 vs 安慰剂,LDL-C降低显著;TAUSSIG研究(94例):非血液净化亚组降低23%,血液净化亚组降低19%;疗效与残余LDL-R活性密切相关(2%-30%活性者有效,<2%几乎无效)
06
主要副作用
鼻咽炎、上呼吸道感染、头痛、背痛、肌痛(ALT升高3.0%)
02. 阿利西尤单抗(Alirocumab)
阿利西尤单抗
序号类别内容
01
上市时间
2015年(美国)
02
治疗原理
全人源化单克隆抗体,结合循环PCSK9蛋白,阻止其与LDL-R结合,减少LDL-R降解,增加LDL清除
03
降脂效果
HoFH患者26%
04
用法用量
皮下注射,每2周75-150mg
05临床试验/数据
ODYSSEY研究(最大规模HoFH随机对照试验):12周时LDL-C较安慰剂降低35.6%;显著降低apoB、非HDL-C、Lp(a);对至少2%功能性LDL-R的HoFH患者有益
06
主要副作用鼻咽炎、注射部位反应、流感、尿路感染、肌痛(过敏事件8.6% vs 安慰剂7.8%)
03. 英克司兰(Inclisiran)
英克司兰
序号项目内容
01
上市时间
2020年12月(欧盟首批)
02
治疗原理
首个GalNAc偶联siRNA,特异性被肝细胞去唾液酸糖蛋白受体(ASGPR)摄取,进入细胞后整合入沉默复合体(RISC)复合物,切割降解PCSK9 mRNA,从源头上抑制PCSK9蛋白合成
03
降脂效果
一般人群50%-52%,HoFH患者12%-37%
04
用法用量
皮下注射,第1天、第90天各284mg,此后每6个月一次
05临床试验/数据
ORION-2研究(HoFH患者):300mg剂量有效降低PCSK9和LDL-C,效果持续时间比单抗更长;ORION-5研究(56例HoFH):未显著改善LDL-C(尽管PCSK9大幅降低),但对部分LDL-R功能亚组可能有效;ORION-13研究(13例12-18岁青少年):330天时LDL-C降低33.3%,PCSK9降低60.2%,耐受性良好
06
主要副作用
注射部位反应(红斑、疼痛、皮疹),均为轻中度且短暂(ALT升高0.6%)
07
优势
半年一次给药,依从性极佳,适合青少年患者
三、非他汀类降脂药(部分LDL-R依赖性)
01. 贝派地酸(Bempedoic Acid)
贝派地酸
序号类别内容
01
上市时间
2020年(美国、欧盟)
02
治疗原理
前体药物,经肝脏ACSVL1激活为Bempedoic acid-CoA,抑制ATP-柠檬酸裂解酶(ACLY,位于HMG-CoA还原酶上游),减少胆固醇合成,反馈性上调LDL-R
03
降脂效果
约10%(HoFH数据有限),总胆固醇降低16.5%
04
用法用量
口服180mg/日,可与依折麦布固定复方(180mg/10mg)
05临床试验/数据
CLEAR Harmony & Wisdom试验(III期):在他汀不耐受患者中显著降低心血管事件风险;CLEAR系列试验:常见不良反应包括上呼吸道感染、肌肉痉挛、贫血、肝酶升高
HoFH应用效果有限,主要用于他汀不耐受患者
06
主要副作用
上呼吸道感染、肌肉痉挛、高尿酸血症、背痛、腹痛、贫血、肝酶升高(ALT升高1.0%);≥60岁或联用氟喹诺酮/皮质类固醇者肌腱断裂风险增加
07
特点
骨骼肌缺乏激活酶,无他汀相关肌病风险
四、LDL-R非依赖性治疗(突破性疗法)
01.洛美他派(Lomitapide)
洛美他派(Lomitapide)
序号类别内容
01
上市时间
2012年12月(FDA),2013年7月(欧盟)
02
治疗原理
口服微粒体甘油三酯转移蛋白(MTP)抑制剂,阻断肝脏和肠道内质网中apoB脂蛋白的组装,抑制VLDL和乳糜微粒形成,从源头减少LDL生成
03
降脂效果
24%-57%,中位肝脏脂肪含量10.2%
04
用法用量
口服10-60mg/日,起始5mg/日,每2周递增
05临床试验/数据
关键III期研究(29例成人HoFH,26周):中位LDL-C降低50%,apoB降低49%,78周时38%患者维持疗效;扩展研究(294周):74%患者达到LDL-C<100mg/dL,58%达到<70mg/dL;儿科研究APH-19(43例5-17岁):24周时LDL-C平均降低53.5%,安全性良好
06
主要副作用
腹泻、恶心、呕吐、腹痛、肝酶升高(ALT升高15.0%)、肝脂肪变性;需补充脂溶性维生素E(400IU/日)和必需脂肪酸
07
特点
首个不依赖LDL-R的口服药,可减少或替代血液净化
02.依维苏单抗(Evinacumab)⭐ 明星药物
依维苏单抗
序号类别内容
01
上市时间
2021年2月(FDA加速批准,≥12岁)
2022年8月(EMA批准,≥12岁);
2023年12月(EMA扩展至5-11岁);
2025年1月(EMA批准≥6个月)
02
治疗原理
全人源单克隆抗体,结合并抑制ANGPTL3蛋白,解除其对脂蛋白脂酶(LPL)和内皮脂酶(EL)的抑制,促进VLDL和IDL清除,减少LDL生成;完全不依赖LDL-R
03
降脂效果
47.1%(III期试验),对LDL-R阴性患者同样有效
04
用法用量
静脉输注15mg/kg,每4周一次
05临床试验/数据
ELIPSE HoFH研究(III期,65例):24周时LDL-C较安慰剂降低47.1%(安慰剂组+1.9%),包括LDLR null-null变异患者;长期研究(72周):LDL-C持续降低45.5%;真实世界研究(7例,24个月):显著降低总胆固醇、TG、HDL-C、非HDL-C、apoB、Lp(a)等;儿科研究(≥5岁):疗效与成人相当;<5岁扩展研究(6例1-5岁):LDL-C降低41.3%-77.3%;模型预测:<5岁患者疗效可能优于成人
06
主要副作用
头痛、流感样症状、头晕、鼻咽炎、流涕、恶心、输液部位瘙痒(ALT升高<1.0%);妊娠禁用(兔胎毒性)
07
特点
目前唯一对LDL-R完全缺失患者有效的药物;2025年EMA批准年龄降至6个月,是HoFH治疗的重要里程碑
五、非药物治疗
01.血脂净化/脂蛋白单采术(LA)
血脂净化/脂蛋白单采术
序号类别内容
01
应用时间
1967年(血浆置换),1975年首次有效治疗报道
02
治疗原理
体外循环直接物理清除血浆中的LDL颗粒,快速降低LDL-C水平
03
适应症
LDL-C>500mg/dL(13 mmo/L)的HoFH;或>300mg/dL(8 mmol/L)且药物治疗无效;儿科:>300mg/dL(8 mmol/L)或合并ASCVD且>130mg/dL(3 mmol/L)
04
治疗方案
每1-2周一次,每次2-3小时(常用Kaneka硫酸葡聚糖纤维素吸附系统)
05临床数据
长期研究显示可显著改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并延长生存期;Reijman研究(2024):儿童期启动LA者无事件生存期显著长于未治疗组
06
局限性
成本高、有创、耗时、生活质量下降、需终身维持;非洲、亚洲部分地区不可及
07
联合策略
与PCSK9抑制剂联用可减少反弹,降低净化频率
02.外科主动脉瓣置换术(SAVR)
外科主动脉瓣置换术
序号类别 内容
01
适应症
HoFH患者严重主动脉瓣钙化/狭窄/反流(一项25名的加拿大HoFH队列中24%的患者需手术)
02
关键发现
所有成人HoFH患者20岁前即出现早期严重主动脉钙化,与年龄相关
03
术式
正中开胸体外循环,下置换机械瓣或生物瓣;无缝合瓣膜等微创技术正在发展中
03.肝移植
肝移植
序号类别内容
01
原理
植入正常肝脏提供功能性LDL-R
02
效果
LDL-C降低可达80%
03
地位
最后手段(其他治疗方式失败时)
04
局限性
供体稀缺(尤其儿童需匹配小肝脏)、终身免疫抑制、显著死亡率和合并症风险、术后仍需LLT
05
数据
9例患者随访28年(平均11.7年):多数未达正常血脂水平
六、未来疗法(基因治疗)
基因治疗
技术原理载体/平台现状
CRISPR/Cas9基因编辑
修复LDLR基因或敲除PCSK9基因
AAV载体、LNP脂质纳米颗粒、慢病毒、碳基纳米颗粒
临床前/早期临床
AAV载体
递送正常LDLR基因或CRISPR系统
肝特异性启动子优化,衣壳工程改造
长期表达潜力,但免疫原性和载荷限制
LNP-mRNA
递送Cas9 mRNA和sgRNA
可重复给药、低免疫原性
已在Duchenne肌营养不良中验证
AI辅助药物设计
加速靶点发现、虚拟筛选
ADMET预测机器学习/深度学习
应用于HoFH新药研发
七、治疗策略(总结图)
HoFH治疗阶梯:
━━━━━━━━━━━━━━━━━━━━
第一层(基础):生活方式干预 + 他汀 + 依折麦布
↓ 不达标
第二层(强化):加用PCSK9抑制剂(Evolocumab/Alirocumab/Inclisiran)
↓ 不达标(尤其LDL-R缺陷严重者)
第三层(突破):LDL-R非依赖性药物
• 口服:Lomitapide(MTP抑制剂)
• 静脉:Evinacumab(ANGPTL3抑制剂)← 对null-null患者有效
↓ 仍不达标
第四层(有创):血脂净化/脂蛋白单采术(LA)
↓ 终末期
第五层(终极):肝移植(最后手段)
━━━━━━━━━━━━━━━━━━━━
关键目标:诊断后尽早(理想2岁前)启动治疗,LDL-C<55-70mg/dL(1.4-1.8 mmol/L)
八、治疗方式关键里程碑(时间轴)
01.治疗方式关键里程碑(时间轴)
时间轴
序号年份内容
01
1967
首次血浆置换治疗HoFH
02
1987
首个他汀(洛伐他汀)获批
03
2002
依折麦布获批
042012
Lomitapide获批(首个非LDL-R依赖口服药)
05
2020
Inclisiran获批(首个PCSK9 siRNA)
06
2021
Evinacumab获批(首个ANGPTL3抑制剂,≥12岁)
07
2023
Evinacumab扩展至5-11岁;Bempedoic acid复方获批
08
2025
Evinacumab扩展至≥6个月(EMA)
▼
往期精彩回顾
▼
突破壁垒:纯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创新疗法(上篇)
研究综述|突破壁垒:纯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创新疗法(下篇)
【2.28国际罕见病日】认识HoFH:一场关于“胆固醇”的罕见战争
参考文献
[1]Huang SJ, Huang P, Song NN, Jia XH, Gao HL, Lu ZY, Wen XL. Breaking barriers: Innovative therapies for managing homozygous familial hypercholesterolemia. Exp Mol Pathol. 2025 Dec;144:105003. doi: 10.1016/j.yexmp.2025.105003. Epub 2025 Oct 16. PMID: 41106315
进
病
友
群
扫上方二维码
红米粒微信号:HomyFH
如发现文内有误请联系我们
编辑:雅雅
审校:宋云
排版:雅雅
临床结果
2026-02-26
纯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HoFH)是一种极为罕见且严重的遗传性疾病,患者因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受体(LDLR)的缺陷或缺失,导致血液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大量积累,从而面临心脏病和卒中的极高风险。尽管当前已有多种治疗方法,但许多患者的血脂水平仍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2026年2月24日,恒瑞医药官网发布,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北京盛迪医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受理通知书》,公司1类创新药血管生成素样蛋白3(ANGPTL3)全人源单克隆抗体SHR-1918注射液的药品上市许可申请获受理且被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治疗成人和12岁及以上的未成年人纯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HoFH)患者,有望为这一罕见病治疗带来新选择。
据资料显示,SHR-1918注射液作为恒瑞医药的自主研发成果,是一款针对血管生成素样蛋白3(ANGPTL3)的单克隆抗体。它通过抑制ANGPTL3的活性,进而降低血清中的甘油三酯(TG)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这两种物质都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发生与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ANGPTL3在脂质代谢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能够通过抑制脂蛋白酶和内皮脂肪酶来减少TG和LDL-C的清除。
血管生成素样蛋白3(ANGPTL3)作为调节血脂代谢的重要因子,近年来在降脂药物研发中备受关注。ANGPTL3主要通过抑制脂蛋白脂肪酶(LPL)和内皮脂肪酶(EL)的活性,影响甘油三酯(TG)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的代谢,从而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因此,针对ANGPTL3的单克隆抗体药物研发成为降脂领域的一大热点。
据恒瑞医药新闻稿,SHR-1918注射液目前已完成两项针对HoFH患者的临床试验:SHR-1918-202 研究和SHR-1918-301 研究,均由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彭道泉教授牵头开展,全面评估了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SHR-1918-202研究是在成人HoFH患者开展的一项Ⅱ期多中心、单臂试验。其相关成果已发表于《美国医学会心脏病学杂志》,研究结果显示,每4周一次皮下注射600mg SHR-1918,血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平均降幅达59.1%,绝对降幅达6.6mmol/L,可为HoFH受试者带来显著且持续的LDL-C水平降低,并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及耐受性。SHR-1918-301研究是一项在年龄≥12岁的HoFH患者中开展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Ⅲ期临床试验,全国16家临床研究中心共同参与。研究结果显示,降脂疗效特征与SHR-1918-202研究结果高度一致,且安全性良好,有望为HoFH患者提供一种高效、便捷的新型治疗选择。
纯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HoFH)是一种罕见且危及生命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因低密度脂蛋白(LDL)代谢相关基因发生致病性突变,患者血清LDL-C显著升高(通常>13 mmol/L),常伴随广泛的黄色瘤以及早发性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该疾病进展快,如不进行治疗,多数患者20岁前可进展为ASCVD,寿命一般不超过30岁。因其发病率/患病率低,已被纳入2018年5月发布的《第一批罕见病目录》。
据了解,可用的治疗选择虽然有多种,包括他汀类药物、依折麦布、洛美他派、米泊美生、PCSK9 单抗和 evinacumab 等,但许多患者仍难以达到理想的血脂控制水平,因此仍存在巨大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目前,全球在研的ANGPTL3单抗仅有四款,其中再生元的依维苏单抗(Evinacumab)在2021年获得美国FDA批准,成为全球首个针对ANGPTL3功能的治疗药物,用于纯合子型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HoFH)的治疗。然而,该药物尚未在中国上市,国内患者仍面临治疗选择有限的困境。
作为中国首个且唯一提交上市申请的 ANGPTL3 靶向药物,SHR-1918注射液有望在降脂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其通过抑制 ANGPTL3 的活性,降低血清中的甘油三酯和 LDL-C 水平,在前期的研究中已经展现出了良好的耐受性和药代动力学特性,以及显著的降脂效果。此外,SHR-1918注射液用于混合型高脂血症、高甘油三酯血症患者的临床研究也正在进行中。
最后,希望恒瑞医药的1类新药SHR-1918注射液早日获批上市,为广大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2026-02-25
今日我们分享一篇《Experimental and Molecular Pathology》2025年发表的文章“Breaking barriers: Innovative therapies for managing homozygous familial hypercholesterolemia”,该文章讲述了HoFH的致病机理和所有的治疗手段,我们将该内容进行整理和总结,便于大家查看和学习了解。
01
研究背景
02
HoFH遗传机制
03
HoFH的临床表现和诊断特征
04
当前针对HoFH的临床治疗方法
05
HoFH的未来治疗前景
06
结论
查看上篇
研究综述|突破壁垒:纯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创新疗法(上篇)
04
当前针对HoFH的临床治疗方法
4.2
不依赖LDL-R活性的药物
洛美他派(Lomitapide)
是一种口服微粒体甘油三酯转移蛋白(MTP)抑制剂,对防止肝脏和肠道中含载脂蛋白B(apoB)的脂蛋白的形成至关重要。
洛美他派通过直接结合肝脏和肠道细胞内质网中的MTP,有效抑制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和乳糜微粒的形成,从而降低血浆LDL-C水平(图7)。
图7.洛美他派(Lomitapide)的作用机制
图片说明:
微粒体甘油三酯转移蛋白(MTP)可促进胆固醇酯从内质网转移至新生成的脂蛋白颗粒核心,随后MTP与胆固醇解离。乳糜微粒和脂蛋白形成后,乳糜微粒会与细胞质中的脂质结合,进入淋巴系统,最终抵达血液;而脂蛋白则通过囊泡转运出细胞。洛美他派通过抑制MTP的合成,阻碍胆固醇的转运过程,使新生成的脂蛋白颗粒无法获取胆固醇,进而干扰脂蛋白和乳糜微粒的合成。
(MTP:微粒体甘油三酯转移蛋白;ER:内质网)。
该药物于2010年在美国获得治疗IIa型高脂蛋白血症的孤儿药地位,2012年12月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2013年7月获欧盟委员会授权。
2026年1月30日在中国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可与低脂饮食和其他降脂药物(伴或不伴有低密度脂蛋白血浆分离置换)合用,用于治疗成人纯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HoFH)。
MTP位于内质网腔内,是细胞内脂质转移蛋白,对肠道和肝脏中apoB脂蛋白的产生和释放至关重要。它促进甘油三酯分子转移到apoB上,在该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洛美他派通过直接结合内质网中的MTP发挥药理作用,从而抑制脂质转移并防止VLDL和乳糜微粒的组装。这一机制破坏了肝脏和肠道组织中含apoB的脂蛋白的生物合成。因此,VLDL和乳糜微粒分泌到全身循环中的量显著减少,最终导致血浆LDL-C水平显著降低。
临床试验和观察性研究一致表明:洛美他派给药可有效降低LDL-C浓度以及其他致动脉粥样硬化脂质参数,包括总胆固醇、VLDL、TG和apoB。
如洛美他派药品说明书所述:临床试验数据显示,洛美他派给药会显著降低维生素E的吸收。维生素E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与全身循环中的VLDL和LDL结合,从而降低其血清浓度。现有证据表明,口服维生素E在肠道肠细胞中掺入乳糜微粒,随后通过淋巴运输途径进入全身循环。因此,洛美他派诱导的乳糜微粒合成抑制可能潜在地损害维生素E的吸收。此外,研究表明,洛美他派不仅降低维生素E的吸收,还降低对VLDL/LDL颗粒有亲和力的脂溶性化合物的生物利用度。这些观察结果共同表明,VLDL/LDL相关药物与维生素E的吸收途径存在机制上的平行性。此外,小鼠研究表明,药物性阻断MTP可减少胆固醇酯的合成,并增加肝脏和肠道细胞中的游离胆固醇水平。内质网中游离胆固醇的水平会导致氧化应激并增强某些基因的转录,从而导致血浆转氨酶升高。此外,洛美他派对消化系统的影响可能是由于肠细胞内甘油三酯增加、乳糜微粒生成减少以及膳食脂肪吸收减少,这可能导致脂肪泻和胃肠道不适。
洛美他派被批准作为成人纯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HoFH)的辅助治疗药物,与低脂饮食和其他降脂药物(无论是否接受脂质分离术(LA))联合使用,从而扩大了HoFH降脂治疗的药物选择。
服用洛美他派的患者还应每日口服补充剂,其中包括400国际单位维生素E、约200毫克亚油酸、110毫克二十碳五烯酸、210毫克α-亚麻酸和80毫克二十二碳六烯酸。
洛美他派的绝对生物利用度较低,约为7%,这主要是由于首过代谢,且在10至100 mg单剂量范围内,其吸收大致与剂量成比例。HoFH治疗的洛美他派起始剂量为每日5mg,如果耐受良好且安全,至少2周后可增加至每日10mg。洛美他派在肝脏中通过氧化、氧化N-脱烷基、哌啶环打开和葡糖苷酸结合等过程广泛代谢。
细胞色素P450(CYP)3家族A亚家族4成员(CYP3A4)酶在将洛美他派代谢为M1和M3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且重要的是,M1和M3在体外均不影响MTP活性。在M1代谢物中,哌啶环保持完整,而洛美他派分子的其余部分在M3中得以保留。尽管其他肝脏酶,包括CYP1家族A亚家族成员、CYP2家族B亚家族6成员、CYP2家族C亚家族8成员和CYP2家族C亚家族19成员,也参与M1代谢物的合成,但与CYP3A4相比,它们的贡献较小。该药物通常耐受性良好,最常见的副作用是胃肠道症状,如腹泻、恶心、呕吐和胃部不适。
在一项针对成人HoFH患者的III期开放标签研究(NCT00730236)中,采用剂量递增方法给予洛美他派,以确定可耐受的最高剂量。参与者被指示遵循脂肪供能占比低于20%的饮食,同时继续现有的降脂治疗,包括29名参与者中的18名接受LA治疗。在26周内,洛美他派使血浆LDL-C水平中位数降低50%,apoB水平降低49%,在存活至78周的23名患者中,这些降低幅度大多得以维持,与基线相比降低了38%。完成78周关键III期研究的患者可参加扩展阶段研究(NCT00943306),其中洛美他派治疗持续总计294周,有19名患者参加了扩展阶段研究。到第246周,19名患者中有14名(74%)达到LDL-C目标100 mg/dl(2.6mmol/L),11名患者(58%)在试验期间至少有一次达到70 mg/dl(1.8mmol/L)。
一项研究调查了MTP抑制剂洛美他派对HoFH患者的影响。12名已接受降脂药物治疗并每两周接受一次LA(9名患者)的患者,每日接受洛美他派治疗。在将洛美他派加入治疗计划前后,评估了血脂谱,如总胆固醇、LDL-C、TG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标准降脂治疗相比,洛美他派使平均LDL-C值降低了54%。总体而言,洛美他派可调整血脂净化(脂质分离术)方案,从而降低治疗负担。在少数HoFH患者中,如果满足特定条件,可完全停止血脂净化(脂质分离术)。这些条件包括达到理想的LDL-C水平(由血脂净化间隔期间的平均LDL-C区间确定),并确保冠状动脉和主动脉瓣的心血管成像保持稳定。
为评估洛美他派在接受标准降脂治疗的HoFH儿科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Masana等在12个研究中心开展了一项开放标签、单臂、III期临床试验。研究设计包括6周的导入期,随后是24周的疗效期和80周的安全性期。参与者年龄在5至17岁之间,接受稳定降脂治疗,并根据2014年欧洲动脉粥样硬化协会共识小组标准诊断为HoFH。他们开始接受口服洛美他派治疗,并根据最大耐受剂量进行递进,5-15岁患者起始剂量为2 mg,16-17岁患者起始剂量为5mg。该试验招募并治疗了43名患者,中位年龄为10.7岁,到第24周时,LDL-C平均较基线降低53.5%。不良事件主要为轻度,且主要为胃肠道和肝脏反应。研究结果表明,洛美他派可显著降低LDL-C水平,为不依赖LDL-R的HoFH儿科患者提供了一种具有临床显著意义且可能有效的治疗方案。这一进展有望将最低治疗年龄从18岁降至5岁。
依维苏单抗(Evinacumab)
血管生成素样蛋白(ANGPTL)家族由八个成员组成,每个成员均具有独特的组织表达和调控特性。这些蛋白通常在氨基末端(N端)具有一个共有结构域,中间是一个卷曲螺旋结构域,羧基末端则是一个类纤维蛋白原结构域,且所有ANGPTL家族成员均通过一个连接区将这些结构域连接起来。
ANGPTL蛋白属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家族,在正常和疾病相关过程中发挥多种作用,如激素调节、葡萄糖代谢和胰岛素抵抗。值得注意的是,在脂蛋白代谢中,ANGPTL3、ANGPTL4和ANGPTL8尤为重要,它们通过抑制内皮脂肪酶(EL)来调控富含甘油三酯(TG)的脂蛋白(如乳糜微粒和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的代谢,并限制脂蛋白脂肪酶(LPL)、VLDL和低密度脂蛋白(LDL)的活性。
ANGPTL3是一种主要由肝脏分泌的蛋白,因其基因功能缺失变异患者表现出多种脂质标志物(包括LDL-C)水平降低以及心血管疾病风险下降而备受关注(图8)。
图8.依维苏单抗降低脂蛋白水平的作用机制
图片说明:
依维苏单抗通过与血管生成素样蛋白3(ANGPTL3)结合并使其失活,从而解除ANGPTL3对脂蛋白脂质分解过程中两种关键酶——脂蛋白脂肪酶(LPL)和内皮脂肪酶(EL)功能的抑制作用。HL可增强高密度脂蛋白(HDL)对胆固醇的摄取,促进胆固醇逆向转运。胆固醇被HDL捕获后,在细胞内转化为胆汁酸、储存起来、直接排泄至胆汁中,或用于合成其他化合物。依维苏单抗与ANGPTL3结合并抑制其活性,可确保LPL和HL正常发挥作用。
(ER:内质网;ANGPTL3:血管生成素样蛋白3;EL:内皮脂肪酶;GA:高尔基体;LPL:脂蛋白脂肪酶;VLDL:极低密度脂蛋白;HDL:高密度脂蛋白)
ANGPTL3糖蛋白在血清中以两种形式存在:全长蛋白和N端截短的ANGPTL3分子,其中截短形式主要负责抑制EL。遗传学研究已将ANGPTL3的变异与血浆TG水平联系起来,功能缺失变异导致血浆TG、LDL-C和高密度脂蛋白(HDL)胆固醇水平显著降低,从而降低冠状动脉疾病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ANGPTL3功能缺失患者表现出ANGPTL3水平降低和冠状动脉疾病风险下降。对ANGPTL3抑制的遗传和分子机制研究揭示了脂蛋白降低的多种机制,以及由于LPL遗传变异增强导致的心血管疾病风险下降。这些患者心肌梗死(MI)的风险也较低。近期研究聚焦于靶向ANGPTL4的肝脏特异性药物,并在2022年欧洲动脉粥样硬化协会大会上公布,强调了ANGPTL3、ANGPTL4和ANGPTL8在降脂药物研究中的重要性。总之,ANGPTL3基因功能缺失变异与LDL-C水平降低和心血管风险下降相关,呈现不依赖于LDL-R治疗的独特降脂效果,为HoFH患者提供了潜在益处。
2022年8月26日,欧洲药品管理局(EMA)批准依维苏单抗与饮食和其他降LDL-C药物联合使用,用于治疗12岁及以上成人和青少年HoFH患者。
随后,2023年12月11日,EMA将依维苏单抗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包括5至11岁HoFH患者。
依维苏单抗通过结合ANGPTL3,抑制其对LPL和EL的作用,在临床试验中,这种阻断作用导致LDL-C水平降低(图9)。
图9. 依维苏单抗(Evinacumab)的发展历程
图片说明:
从血管生成素样蛋白3(ANGPTL3)作为血管生成素样蛋白家族新成员被首次发现,到依维苏单抗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欧洲药品管理局(EMA)正式批准,历时逾20年。这一过程涵盖了依维苏单抗的初步构想、VelocImmune技术平台的应用,以及依维苏单抗的临床试验。未来,针对依维苏单抗的研究将聚焦于其在婴幼儿中的应用、成本效益分析与可及性、给药方式与剂型的改进,以及长期安全性与有效性的监测,以推动其在更多国家获得市场批准。
(ANGPTL3:血管生成素样蛋白3;LPL:脂蛋白脂肪酶;EL:内皮脂肪酶;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EMA:欧洲药品管理局)
无论LDL-R是否存在,依维苏单抗均能降低LDL-C水平,通过增强VLDL的处理和清除上游LDL的产生,同时限制中间密度脂蛋白(IDL)向LDL的转化。IDL是脂蛋白代谢中的一种副产物,在脂质代谢和胆固醇运输中发挥关键作用,由VLDL在血液中分解时形成。当脂蛋白脂肪酶在循环中分解VLDL中的TG时,剩余颗粒变得更密集并转化为IDL。抑制ANGPTL3可改善VLDL的分解,导致脂质耗竭的VLDL残余物生成,这些残余物从血液中清除得更快。因此,LDL前体池的耗竭导致LDL-C水平下降,且这一过程独立于LDL-R。
ANGPTL3作为两种内皮脂肪酶—— LPL 和EL的抑制性调节因子,分别催化循环中TG和磷脂的水解。LPL主要催化外周组织中乳糜微粒和VLDL的TG水解,促进其分解为脂肪酸和甘油。EL最初因其在调节HDL代谢中的作用而被识别,但近期研究显示其也参与含载脂蛋白B的脂蛋白(包括VLDL和LDL)的分解代谢过程。
在健康个体中,肝细胞将VLDL颗粒分泌到全身循环中,随后LPL和EL对其进行顺序脂解处理。这一过程生成VLDL残余物,随后通过肝LDL-R和残余物受体介导的内吞作用清除。或者,这些残余物可进一步水解形成LDL颗粒,其血浆清除主要通过LDL-R依赖途径进行。HoFH的特点是致病性LDLR变异破坏肝LDL分解代谢,导致LDL-C全身性积累。
在单臂III期ELIPSE HoFH研究中,无论残余LDL-R活性或其他针对脂蛋白代谢不同方面的治疗如何,依维苏单抗均显示出一致的LDL-C降低效果。依维苏单抗注射可降低LDL水平,促进TG分解,并降低TG水平,这是与ANGPTL3抑制直接相关的药效学评估。依维苏单抗以高度选择性阻断ANGPTL3,并通过复杂机制改变脂质浓度。
临床数据被用于群体药代动力学(PK)和药代动力学/药效学(PK/PD)研究,以评估依维苏单抗在成人HoFH患者中的PK和PD特性,揭示其PK遵循两室模型,同时存在线性和非线性消除途径。重复给药后,依维苏单抗达到稳态,并通过线性和可饱和非线性途径清除。群体PK模型预测,每四周静脉注射15 mg/kg依维苏单抗,每个给药周期的平均稳态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为10,286天*mg/L。
此外,一项涉及183名志愿者和95名HoFH患者的群体药代动力学研究显示,年龄、性别、体重和种族对依维苏单抗暴露无显著影响。在依维苏单抗PK/PD研究中,采用间接暴露-反应模型证明依维苏单抗对LDL-C生成的抑制作用可饱和。最终PK/PD模型评估了多个变量,显示初始LDL-C水平较高与半数抑制浓度下降相关。此外,较低的基线体重与最大药物诱导抑制效应增加相关。
研究探讨了HoFH患者在接受依维苏单抗(一种ANGPTL3抑制剂)治疗前后含载脂蛋白B的脂蛋白的动力学特性。该研究作为一项更大规模试验的子研究,在两个中心招募了四名HoFH患者,以评估依维苏单抗对该疾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数据显示,依维苏单抗显著提高了IDL载脂蛋白B和LDL载脂蛋白B的分数分解代谢率,表明该药物主要通过促进含载脂蛋白B的脂蛋白从循环中清除来降低LDL-C水平。
2023年,Rosenson等研究了依维苏单抗在难治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中的长期效果。研究显示,在72周期间,LDL-C水平显著且持续下降。具体而言,第72周时LDL-C水平下降了45.5%,凸显了依维苏单抗作为该疾病长期治疗选择的潜力。
在双盲II期试验(NCT03175367)中,与他汀类药物和其他降脂治疗最大耐受剂量无反应的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特别是HoFH患者)相比,依维苏单抗显著降低了LDL-C水平。
同样,在双盲III期ELIPSE HoFH试验(NCT03399786)中,接受稳定最大耐受剂量降脂治疗的HoFH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依维苏单抗(n=43)或安慰剂(n=22)治疗24周。结果显示,依维苏单抗治疗导致LDL-C水平显著下降,从基线到第24周下降了47.1%,而安慰剂组在同一时间段内上升了1.9%。此外,依维苏单抗在降低胆固醇水平方面比安慰剂更有效,无论患者是缺失LDLR变异(15名依维苏单抗使用者和6名安慰剂使用者)还是非缺失变异。
另一项研究中,7名经基因证实的HoFH患者在接受降脂治疗和/或脂质分离术的同时,接受静脉注射依维苏单抗(每4周15 mg/kg)治疗24个月。这种同情使用依维苏单抗也导致LDL-C水平下降,同时总胆固醇、TG、HDL-C、非HDL-C、残余胆固醇、载脂蛋白(a)-I、载脂蛋白B、载脂蛋白C-III、脂蛋白(a)和高敏C反应蛋白水平也降低。值得注意的是,依维苏单抗治疗后,HoFH患者个体的血浆天冬氨酸转氨酶、丙氨酸转氨酶和肌酸激酶水平保持稳定,肝酶未超过正常上限的三倍。研究还发现,与日本参与者相比,白种人参与者接受较低静脉剂量(每4周5 mg/kg)的副作用更多。而接受15 mg/kg静脉剂量(每4周)的副作用频率在两个群体中相似。尽管有这些发现,但只有少数患者经历副作用,且无人停止治疗、出现心血管问题或死亡。常见副作用包括头痛、流感样症状、头晕、鼻咽炎、鼻分泌物、恶心和输液部位瘙痒。
动物研究提示,由于可能对兔胎儿造成伤害,孕妇不应使用依维苏单抗,且计划怀孕前至少应停止治疗五个月。现有指南建议HoFH治疗应在诊断时开始,理想情况下在2岁前开始,但依维苏单抗的部分批准未涵盖12岁以下儿童,因为该年龄组需要更多安全性证据)。
依维苏单抗的最低使用年龄要求已取得重大进展。Bihore等修改了现有群体PK和PK/PD模型,以预测大量5岁以下HoFH虚拟患者的依维苏单抗暴露和LDL-C降低情况,考虑了生物发育和病理生理状况的各种假设。模型显示,随体重下降,体重基础剂量导致依维苏单抗暴露减少。与5岁以上患者观察到的趋势一致,与5至18岁以下患者和成人相比,5岁以下患者的LDL-C水平从基线变化的预测百分比通常相当或更高。此外,与5至18岁以下患者和成人相比,5岁以下患者群体中LDL-C降低超过50%的患者预测百分比也更高。
此外,在实际应用中,研究人员通过管理访问计划为六名1岁至5岁以下患者使用了依维苏单抗。这些患者接受了5至23次静脉输注,每次15 mg/kg,每4周一次。治疗导致LDL-C水平迅速且显著降低,最后一次报告剂量时的LDL-C水平变化百分比范围为41.3%至77.3%。这种基于模型的推断分析提供了依维苏单抗在5岁以下HoFH患者中降低LDL-C的临床显著效果见解。这些发现支持依维苏单抗在HoFH幼儿中的临床应用,这些患者否则治疗选择极为有限。
2025年1月,EMA批准依维苏单抗用于治疗6个月及以上HoFH患者。这意味着该药物在欧盟的最低适用年龄已降至6个月。
4.3
其他疗法
血脂净化(低密度脂蛋白分离术)
血脂净化(低密度脂蛋白分离术)是一种非药物治疗方法,专为LDL-C水平极高的个体设计。该技术利用体外循环直接从患者血液中去除过量LDL,迅速降低LDL-C水平,从而预防和治疗由高胆固醇引起的心血管疾病。
1967年,DeGenne JL等首次在HoFH患者中进行了LDL分离术实验,使用血浆置换法;1975年,首次有效血浆置换术治疗严重高胆固醇血症被记录。后续研究显示,重复、长期血浆置换术不仅显著改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还延长了HoFH患者的寿命。
目前,FDA批准的LDL分离术适应症(十多年来未更新)包括:HoFH患者LDL-C浓度超过500 mg/dL(13 mmo/L);未患冠状动脉疾病的HeFH患者LDL-C水平大于300 mg/dL(8 mmo/L);或接受最大耐受LDL降低治疗且患有冠状动脉疾病的患者LDL-C浓度超过200 mg/dL。
根据欧洲罕见肾脏病网络和欧洲儿科肾病学会的共识声明,以下情况的HoFH儿科患者应开始LA治疗:
❶ 尽管接受最佳降脂治疗,LDL-C水平仍超过7.8 mmol/L(300 mg/dL);
❷ HoFH合并ASCVD且LDL-C水平尽管接受最佳降脂治疗仍高于3.4 mmol/L(130 mg/dL);或无ASCVD的HoFH患者LDL-C水平尽管接受最佳降脂治疗仍持续在3.4 mmol/L(130 mg/dL)至7.8 mmol/L(300 mg/dL)之间。
关于治疗目标:
❶ 声明倡导设定平均LDL-C治疗目标低于3.0 mmol/L(<115 mg/dL)。
❷ 对于ASCVD儿科患者,推荐平均LDL-C治疗目标低于1.8 mmol/L(<70 mg/dL)。
此外,如果引入新型降脂药物后平均LDL-C血浆浓度保持在指定治疗目标范围内,建议考虑减少脂蛋白分离术频率。
脂质分离术治疗通常使用不同机器进行,每次治疗平均2-3小时,每周一次或两次。Kaneka葡聚糖硫酸盐纤维素吸附装置在美国广泛使用,且耐受性良好,副作用极少。在非洲许多地区和亚洲部分地区,LDL分离术不可用,在南美洲也极少可用。相反,大多数LDL分离术在欧洲、北美、日本和俄罗斯进行。这主要是由于脂质分离术的缺点,如患者和医生需投入大量时间、治疗成本相对较高,以及与药物治疗相比更具侵入性。
LDL分离术常与药物联合使用,可迅速直接从患者血液中去除大量LDL,迅速降低LDL-C水平,这对需要立即降低心血管风险的危重患者至关重要。尽管如此,单纯进行LDL分离术仍不足以长期维持血脂水平在最佳状态,因为LDL水平可能在两次治疗间隔期间升高。PCSK9抑制剂常与LDL分离术联合使用,以最小化脂蛋白水平的升高。
在一项小样本队列试验中,针对缺血性心脏病患者,测试其持续进行LDL分离术治疗的同时使用阿利西尤单抗的疗效,结果显示加入阿利西尤单抗使LDL-C水平降低超过50%。这大大减轻了脂质反弹效应,并改善了LDL分离术前的脂质水平。
对于HoFH患者,LDL分离术治疗常有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即使精心管理LDL,部分患者冠状动脉和主动脉瓣仍会进展为动脉粥样硬化,这是其预后的重要指标。尽管部分患者可能消退,但多数患者受益于治疗的预防效果。LDL分离术的启动年龄与常规治疗期间的心血管事件密切相关,6-7岁开始LDL血浆置换对有效预防主动脉根部粥样斑块进展至关重要。
尽管某些国家提供LDL分离术,但许多患者仍未达到LDL-C目标。这种疗效不足归因于诊断延迟、转诊至分离术延迟以及手术频率不足等因素。
Reijman等开展了一项纵向研究,以评估儿童期开始LA治疗的HoFH患者的心血管结局。主要目标是评估LA对心血管健康的影响,特别关注ASCVD和心血管死亡率。研究筛选了404名符合条件的参与者,将其分为接受LA治疗(LA)和未接受LA治疗(LA-)两组。进行统计分析以比较LA和LA-组间LDL-C水平的变化。此外,采用生存分析方法评估两队列的无事件生存时间。结果显示,与LA-组相比,LA组LDL-C水平降低更显著。此外,LA队列的中位生存时间明显长于LA-队列。这些结果表明,LA治疗对心血管健康有益,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新证据。
外科主动脉瓣置换术(SAVR)
是一种传统心脏手术,旨在修复主动脉瓣问题,包括主动脉瓣狭窄和反流。瓣膜老化、钙化、先天性缺陷或其他病理因素常导致这些疾病,严重时可引起心肌损伤、充血性心力衰竭或致命性心律失常。
SAVR常通过胸骨正中切开术在体外循环下进行,首先进行横向或曲棍球棒状主动脉切开术,然后去除病变瓣叶并清理瓣环。随后,在直接视野下放置一系列间断或连续缝合线(带或不带衬垫),以固定生物瓣(有支架或无支架)或机械瓣。就耐久性和最小结构瓣膜退化而言,机械瓣膜备受推崇,而支架式生物瓣膜在10年后结构瓣膜失效率保持70%至90%,15年后仍维持50%至80%的独立性。
一项涉及25名加拿大HoFH患者的研究揭示了主动脉钙化的重要见解。参与者平均年龄为32岁,年龄范围从5岁至54岁,治疗前平均胆固醇水平为19 mmol/L。使用计算机断层扫描评估主动脉钙化,显示平均钙评分在20岁时上升,与年龄增长相关;值得注意的是,24%的患者因严重钙化接受了主动脉瓣手术。研究表明,所有成年HoFH患者均有早期严重主动脉钙化,表明手术治疗面临重大挑战。因此,有必要建立通过非侵入性手段识别和监测HoFH患者主动脉钙化的程序,且临床试验对于探索增强或更严格治疗是否能阻止这些钙化进展至关重要。
传统SAVR通过胸骨正中切开术仍是主动脉疾病的标准疗法,但微创技术因其能实现良好结局并减轻患者负担而日益受到认可。无支架瓣膜作为一种生物假体,无需锚定缝合线即可手术植入,与常规方法不同。该方法仍允许完全去除病变原生瓣膜,并全面清理主动脉瓣环上的钙化碎片或感染物质。
肝移植
在HoFH患者中,肝脏是产生LDL-R以清除血液中LDL-C的主要器官,但LDL-R的变异或缺失限制了LDL-C的正常清除。理论上,移植健康供体的肝脏可能提供功能正常的LDL-R,从而降低LDL-C水平。
当降脂治疗(LLT)无法控制HoFH时,肝移植被视为一种确定性治疗或最后手段,可实现LDL-C水平降低高达80%。与单采术类似,冠状动脉疾病和胆固醇标志物已被证实可逆转,但若肝移植后发生主动脉瓣狭窄,则无法阻止其进展。
肝移植存在重大缺点:主要是由于合适供体来源有限,这对需要较小匹配肝脏的年轻患者尤为成问题。此外,移植患者需无限期服用免疫抑制药物以防止排斥反应,这带来重大健康风险和经济挑战。
一项涉及9名接受治疗性肝移植的HoFH患者的研究(随访期长达28年,平均11.7年)强调了该治疗的高死亡风险和严重共病。移植后,患者常无法达到正常脂质水平,需持续LLT。因此,肝移植被视为HoFH患者的最后治疗手段。
中药
中药(TCM)是管理高脂血症的一种探索性方法。尽管某些方剂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医学传统中历史悠久使用,但目前缺乏安慰剂对照随机对照试验验证、指南支持和循证地位。
05
HoFH的未来治疗前景
纯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HoFH)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中叶,与遗传学、生物化学、临床医学和药物研究等领域的重大发展同步。随着对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研究的深入,我们对HoFH的理解不断加深,为这种罕见疾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近年来,由于遗传学、生物技术和临床研究的快速突破,HoFH的治疗前景已显著增强。
5.1
基因治疗
细菌和某些古菌拥有一种称为成簇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CRISPR)的防御机制,在抵御病毒入侵和其他遗传威胁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过去十年中,研究人员将CRISPR作为基因编辑的突破性工具加以利用,其中CRISPR-Cas9蛋白系统最为突出。与其他基因组编辑技术(如锌指核酸酶或转录激活样效应因子核酸酶)相比,CRISPR/Cas9的设计和实施尤为简便。这种简便性主要源于只需修改向导RNA的原间隔序列,即可靶向多个基因组位点(图10)
图10.CRISPR/Cas9系统在细菌及基因编辑技术中的作用
图片说明:
在细菌和古菌中,反式激活CRISPR RNA(tracrRNA)与CRISPR RNA(crRNA)通过碱基配对形成双链复合物。该复合物与Cas9蛋白结合,构成CRISPR-Cas9复合体。当噬菌体入侵时,Cas蛋白会切割入侵者的DNA,并将一段DNA作为新的间隔序列整合到CRISPR阵列中。CRISPR阵列转录产生前体crRNA,经tracrRNA加工形成成熟的crRNA。成熟的crRNA与Cas蛋白结合,组装成具有功能的CRISPR-Cas复合体,从而实现精准的DNA切割。
在纯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HoFH)的治疗中,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融合了crRNA和tracrRNA的单链向导RNA(sgRNA),用于靶向特定基因。PCSK9基因的sgRNA和低密度脂蛋白受体(LDLR)基因的sgRNA分别与Cas9蛋白结合。sgRNA的5'端序列与原间隔序列相邻基序(PAM)前方的基因组DNA互补,引导Cas9在PAM附近切割双链DNA。破坏PCSK9基因的DNA可阻止PCSK9蛋白的产生。同时,LDLR基因受损会激活细胞DNA修复机制,修复第4外显子的碱基对缺失。
crRNA:CRISPR RNA;Cas9:CRISPR相关蛋白9;CRISPR:成簇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tracrRNA:反式激活CRISPR RNA;PCSK9: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Kexin 9型;sgRNA:单链向导RNA;
基于AAV的系统
与小干扰RNA(siRNA)或短发夹RNA(shRNA)相比,CRISPR/Cas9技术能在修饰细胞中提供持久的治疗益处。然而,无论以DNA、mRNA还是蛋白质形式递送,CRISPR/Cas9系统本身较大,在没有递送载体的辅助下,难以进入哺乳动物细胞。
腺相关病毒(AAV)于1965年被发现,是一种小型非致病性病毒,依赖腺病毒进行复制,因其广泛的宿主范围和卓越的安全性,成为基因治疗中的重要载体。
AAV 载体递送的最终阶段是将病毒基因组导入细胞核,通过基因表达实现预期治疗效果。这一过程取决于衣壳蛋白促进核内进入和基因组释放的能力,可通过衣壳工程和应用特异性启动子来优化转基因表达。
一种创新方法是利用重组腺相关病毒(rAAV)工程,将衣壳蛋白酶插入并诱导嵌合体形成。该技术凸显了rAAV平台的结构稳定性,使得 β -内酰胺酶等酶类能够整合到衣壳中,且不会影响其组装或功能。这些修饰可以在保持酶活性的同时增大衣壳尺寸,从而凸显了针对特定治疗应用定制 AAV 载体的潜力。
此外,衣壳工程旨在调控 AAV 载体的免疫反应。通过在载体衣壳中引入破坏Toll样受体信号传导的肽段,研究人员开发出能同时减弱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反应的衣壳变体。该策略在提高转导效率和降低人类细胞及动物模型的免疫反应方面展现出潜力。
研究表明, AAV 介导的基因治疗可维持治疗效果长达十余年,这在其他遗传性疾病中已有观察。这种持久性对于需要持续管理胆固醇水平以预防心血管并发症的HoFH尤为重要。
AAV载体擅长将基因递送至特定靶细胞;然而,非靶组织中的异位表达可能导致不良反应。此外,AAV载体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其有限的载荷容量,限制了可递送治疗基因的大小。这要求开发策略以压缩遗传物质或将较大基因分割成较小片段,以便共同递送并在靶细胞内重新组装。此外,不同AAV血清型的转导效率因细胞类型和组织而异,突显了针对特定治疗靶点选择合适AAV血清型的重要性。
LNP包裹疗法
除AAV外,慢病毒和脂质纳米颗粒(LNPs)是基因治疗、细胞治疗和核酸药物递送中广泛使用的两大关键技术载体(表2)。
表2. 三种基因递送系统的比较
表格说明:
AAV :腺相关病毒;LNPs:脂质纳米颗粒; CRISPR :成簇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Cas9: CRISPR 相关蛋白9;
LNPs是合成非病毒载体,具有球形形态,直径通常在50至100纳米之间,由包裹核酸的脂质双层形成。
LNPs的核心成分包括可离子化的阳离子脂质(促进内体逃逸)、辅助脂质(增强膜融合)、胆固醇和聚乙二醇化脂质。
LNPs通过内吞作用进入细胞,其中酸性环境诱导阳离子脂质质子化,导致内体膜破裂,随后核酸释放到细胞质中。释放的mRNA随后在无需进入细胞核的情况下翻译成蛋白质,从而消除了基因组整合的风险。
LNPs为递送多种核酸(包括mRNA、siRNA和DNA)提供了多功能平台。此外,其能够包裹较大载荷的能力使其适合递送复杂的基因编辑工具,如CRISPR-Cas9系统。
此外,LNPs具有可扩展性,可大规模生产,这对于需要高剂量或广泛分布的临床应用具有优势。然而,实现LNPs的组织特异性可能具有挑战性,因为它们常依赖被动靶向机制,并可能需要表面修饰以增强对特定组织或细胞的递送。
作为疫苗设计、生物药物开发、免疫治疗等领域的重要考量,免疫原性一直是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HoFH治疗的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研究人员正在探索可能降低免疫原性同时保持CRISPR/Cas9组件高效递送的替代递送系统。
在一项针对杜氏肌营养不良的研究中,LNPs被用于将CRISPR-Cas9 mRNA和单链向导RNA(sgRNA)递送至骨骼肌,展示了低免疫原性和重复给药的能力,这对于治疗HoFH等遗传性疾病具有潜力。
慢病毒载体
慢病毒载体是一类重要的基因递送载体,源自逆转录病毒科。这些载体主要基于复杂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骨架进行工程改造,以消除致病元素,同时保留其高效细胞转导和稳定基因组整合的固有能力。这种改造使其适用于体外基因修饰方案和体内基因治疗应用。
结构上,慢病毒颗粒为包膜病毒粒子,直径约100纳米。病毒包膜由出芽过程中从生产细胞膜衍生的脂质双层组成,并纳入异源包膜糖蛋白。水泡性口炎病毒G糖蛋白(VSV-G)最常被假型化到慢病毒载体上;这种修饰通过内吞作用介导受体非依赖性进入多种靶细胞类型,有效确定感染谱系。包膜下是病毒衣壳,容纳核心病毒成分。在此核心结构中,存在两份携带治疗性转基因盒的正链单链RNA基因组,以及必要的病毒酶,包括逆转录酶和整合酶。
慢病毒转导机制涉及受体介导的进入靶细胞,主要由假型化包膜糖蛋白(如VSV-G)促进。内部化并脱壳后,病毒RNA基因组在宿主细胞质中经病毒编码的逆转录酶催化进行逆转录。此过程生成互补双链DNA拷贝,称为前病毒DNA。前病毒DNA与病毒蛋白形成前整合复合物,随后被主动转运至宿主细胞核。病毒整合酶酶随后催化前病毒DNA与宿主细胞染色体DNA的共价整合。这一稳定整合事件确保转基因在细胞分裂期间被复制并传递给子代细胞,实现长期转基因表达。
然而,慢病毒载体的一个主要限制是其有限的载荷容量。通常,这些载体可容纳长达8-10千碱基的转基因盒。这一限制可能限制其递送较大治疗基因或需要多个表达盒的复杂遗传电路的能力。
为增强慢病毒载体的递送效率、空间控制和安全性,积极研究了将其与生物材料支架集成的策略。例如,研究表明,将慢病毒颗粒固定在嵌入生物相容性水凝胶中的羟基磷灰石纳米颗粒上。这种基于生物材料的方法可稳定病毒载体,在所需给药部位局部保留它们,并提供持续的释放动力学。因此,与自由载体给药相比,这导致体内转基因表达显著延长和局部化。此外,这种局部递送策略有效最小化病毒载体的全身传播,从而降低非靶标转导和相关不良反应的潜力。
新兴非病毒平台
使用非病毒基因载体治疗HoFH代表了基因治疗中的一个有前途的前沿,相比传统病毒载体具有潜在优势。非病毒载体(如纳米颗粒)因其有利的安全性,包括降低的免疫原性和毒性,在临床应用中受到关注。
纳米颗粒因其高表面积、生物相容性和能够用多种化学基团功能化的能力,成为递送CRISPR-Cas9系统的有前途平台。这些纳米颗粒可高效包裹并保护CRISPR-Cas9组件,促进其跨细胞膜转运并增强基因编辑效能。
碳基纳米颗粒(CBNs)的一个显著优势是其可被工程化以实现特定递送目标。带正电的碳基纳米颗粒(如阳离子修饰的碳纳米管(CNTs))可通过静电相互作用与带负电的核糖核蛋白紧密结合,形成稳定纳米结构。这种配置不仅保护核糖核蛋白免受核酸酶降解,还加速基因编辑过程并最小化脱靶效应。此外,Cas9编码的mRNA或DNA与sgRNA一起可被包裹在碳基纳米颗粒内部或固定在其表面。具体而言,脂质体-CNT复合物能够包裹mRNA,通过脂质体与细胞膜的脂质亲和力促进细胞摄取,随后实现Cas9蛋白的翻译。
在DNA递送方面,碳基纳米颗粒必须穿越细胞核以促进基因表达。这一过程可通过修饰纳米颗粒以增强其核进入能力来优化。羧化纳米金刚石已被用于递送CRISPR-Cas9组件以进行基因编辑应用。这些纳米金刚石可被功能化以增强其与生物分子的相互作用,从而提高CRISPR-Cas9系统进入靶细胞(如人类诱导多能干细胞和小鼠视网膜)的递送效率,以引入特定遗传变异。
5.2
人工智能辅助药物设计
人工智能辅助药物设计
传统药物设计的特点是成功率低、开发周期昂贵且漫长。通过传统方法发现候选化学物质并推向市场通常需要10至15年,并可能耗资数十亿美元。由于许多候选药物在临床试验后未获得FDA批准,导致新药对患者的可用性延迟,并增加了研发成本。
人工智能(AI),特别是深度学习,可增强并加速新药开发,尽管其应用仍处于早期阶段,但有潜力彻底改变制药行业。AI现被用于创造新化合物、发现新药理靶点以及预测潜在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随着技术的发展,AI在药物开发中的重要性预计将更加显著。
为预防和治疗疾病,药物可与药物靶点(由生物分子创建的独特位点)配对,以产生药理作用(靶向激动剂/抑制剂)。根据生物分子的生物特性,药物靶点可分为受体、酶、离子通道、DNA、激素和生长因子。识别疾病生物原因并开发有效治疗依赖于识别其靶点。
与常规药物发现技术相比,合理药物设计(特别是通过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CADD)提供了更有效且经济的选择。该技术使用分子对接策略识别潜在治疗靶点的配体结合位点。此外,CADD是一种多学科策略,结合复杂计算方法与尖端生物信息学工具。
CADD的核心是虚拟筛选技术,该技术通过融合计算机科学、分子生物学及相关领域概念,利用目标生物大分子的3D结构或定量构效关系模型。此方法使得能够从已知小分子数据库中选择满足特定要求的分子。随后,采用一种或多种实验方法对特定条件进行靶向药物筛选。
在制药行业中,虚拟筛选被视为领先的CADD技术,有效缩小大型化学结构库以识别与特定蛋白质靶点相关的潜在化合物。它现在被广泛认为是提高化合物活性及发现先导化合物的有用方法。
吸收、分布、代谢、排泄和毒性(ADMET)是药物开发中用于评估候选药物在人体内行为的一组关键指标。这些概念显著影响药物的疗效、安全性和环境影响,使其在新药开发的早期阶段至关重要,并且是决定药物能否通过临床试验并最终获批上市的关键。
仅依赖生物测试验证化合物的ADMET属性效率低下,且消耗大量时间、金钱和人力。计算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量子化学方法和更快的计算机处理能力,显著支持了药效学和药代动力学问题的计算分析。
因此,这些进步为评估ADMET属性提供了更有效且经济的方法。通过分析复杂信息,AI可识别模式并预测结果,从而改善药物管理、减少不良反应并提高患者预后。
机器学习(ML)和深度学习(DL)方法广泛用于预测药代动力学参数。多种ML技术(如贝叶斯模型、随机森林、支持向量机、人工神经网络和决策树)已被用于预测药物ADME。深度学习算法(包括卷积神经网络、长短期记忆网络和循环神经网络)常用于预测药物吸收、生物利用度、清除率、分布容积和半衰期等药代动力学特性。此外,一种称为定量构效关系的计算机方法利用分子的化学结构预测其生物活性。
06
结论
HoFH迫切需要克服治疗局限并实现早期、强化降低LDL-C的策略。新生儿筛查和5岁前开始常规降脂治疗(他汀类药物、依折麦布、PCSK9抑制剂)仍是血脂控制的基础。
对于难治性病例,不依赖LDL受体(LDLR)的药物已经有了关键进展:洛美他派通过抑制微粒体甘油三酯转移蛋白(MTP)降低LDL-C,但存在肝毒性风险;依维苏单抗(ANGPTL3抑制剂)在LDLR阴性表型中显示疗效,但面临成本和给药障碍。LDL血脂净化技术/血脂单采技术为严重病例提供了快速降低LDL-C。新兴基因疗法具有治愈潜力,但需优化安全性。从诊断起即积极降低LDL-C,充分利用现有及新型 LDLR 非依赖性方法,是改善HoFH预后的关键。
//
全篇已完
参考文献
[1]Huang SJ, Huang P, Song NN, Jia XH, Gao HL, Lu ZY, Wen XL. Breaking barriers: Innovative therapies for managing homozygous familial hypercholesterolemia. Exp Mol Pathol. 2025 Dec;144:105003. doi: 10.1016/j.yexmp.2025.105003. Epub 2025 Oct 16. PMID: 41106315
进
病
友
群
扫上方二维码
红米粒微信号:HomyFH
如发现文内有误请联系我们
编辑:雅雅
审校:宋云
排版:雅雅
孤儿药临床研究
100 项与 甲磺酸洛美他派 相关的药物交易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研发状态
批准上市
10 条最早获批的记录, 后查看更多信息
登录
| 适应症 | 国家/地区 | 公司 | 日期 |
|---|---|---|---|
| II a型高脂蛋白血症 | 墨西哥 | 2014-02-09 | |
| 纯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 美国 | 2012-12-21 |
未上市
10 条进展最快的记录, 后查看更多信息
登录
| 适应症 | 最高研发状态 | 国家/地区 | 公司 | 日期 |
|---|---|---|---|---|
| 家族性乳糜微粒血症综合征 | 临床3期 | 意大利 | 2018-12-18 | |
| 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 临床3期 | 意大利 | 2018-12-18 | |
| 高脂血症 | 临床2期 | 美国 | 2007-10-01 | |
| 高胆固醇血症 | 临床2期 | 美国 | 2006-05-01 | |
| 结直肠癌 | 临床前 | 韩国 | 2022-12-08 |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临床结果
临床结果
适应症
分期
评价
查看全部结果
| 研究 | 分期 | 人群特征 | 评价人数 | 分组 | 结果 | 评价 | 发布日期 |
|---|
临床3期 | 18 | 夢鹽範獵獵鹹襯觸蓋醖(繭範遞壓積醖積鏇鑰製) = 齋衊憲積製蓋觸艱餘構 憲衊膚獵願憲齋醖繭艱 (願觸膚齋製夢觸憲齋窪 ) | 积极 | 2022-09-10 | |||
临床1期 | - | 15 | (PK of Lomitapide) | 觸願網鏇選窪範積襯襯(鹽構選鬱繭淵衊夢鏇鬱) = 鹽襯構製糧憲網觸憲糧 積築蓋繭遞廠齋襯齋築 (壓獵選構廠齋艱選顧窪, 0.556) 更多 | - | 2020-03-11 | |
(PK of M1) | 觸願網鏇選窪範積襯襯(鹽構選鬱繭淵衊夢鏇鬱) = 夢願遞餘醖淵顧獵齋艱 積築蓋繭遞廠齋襯齋築 (壓獵選構廠齋艱選顧窪, 0.593) 更多 | ||||||
临床3期 | 19 | 範蓋衊簾蓋鏇窪網鬱鬱(糧淵遞餘鬱遞選淵選繭) = 壓窪獵鑰膚膚選鏇範構 壓糧簾艱醖築鏇窪築構 (憲鏇鑰遞膚衊選觸齋艱, 31.35) 更多 | - | 2018-05-11 | |||
临床1期 | - | 32 | (Lomitapide Sprinkled in Applesauce (Treatment A)) | 願齋憲鏇製鑰糧鹽夢繭(窪壓願積網構鹹夢夢鑰) = 築選顧齋壓積鏇壓網築 顧鑰艱築襯築蓋齋壓淵 (醖獵淵構鏇憲網範廠簾, 15.2) 更多 | - | 2018-02-13 | |
(Lomitapide Sprinkled in Mashed Banana (Treatment B)) | 願齋憲鏇製鑰糧鹽夢繭(窪壓願積網構鹹夢夢鑰) = 夢鹹網鏇襯範構壓蓋醖 顧鑰艱築襯築蓋齋壓淵 (醖獵淵構鏇憲網範廠簾, 13.4) 更多 | ||||||
临床3期 | 29 | 遞築觸觸範齋獵網壓襯(齋觸遞艱築鏇衊構網糧) = 顧襯窪築顧醖壓構壓鬱 遞餘選製糧憲憲顧鹹築 (網鏇壓鹽鏇顧構積網觸 ) | 积极 | 2015-06-01 | |||
(Lipoprotein apheresis) | 遞築觸觸範齋獵網壓襯(齋觸遞艱築鏇衊構網糧) = 醖衊廠構糧艱顧窪構積 遞餘選製糧憲憲顧鹹築 (網鏇壓鹽鏇顧構積網觸 ) | ||||||
临床2期 | 44 | (Atorvastatin 20 mg) | 餘鏇繭構網顧襯構範獵(遞膚憲鹹膚構構窪網選) = 糧選選簾製淵夢願憲獵 選餘蓋願繭衊繭顧淵蓋 (觸遞鏇獵範餘鹽膚觸製, 14.35) 更多 | - | 2013-02-25 | ||
(Atorvastatin 20 mg + Lomitapide) | 餘鏇繭構網顧襯構範獵(遞膚憲鹹膚構構窪網選) = 觸醖廠鏇衊鬱淵積壓蓋 選餘蓋願繭衊繭顧淵蓋 (觸遞鏇獵範餘鹽膚觸製, 26.78) 更多 | ||||||
临床2期 | 6 | 網夢鹽築襯鑰鹽餘簾襯(繭顧鏇願夢顧網餘窪鬱) = 齋艱糧憲選築蓋範憲衊 鏇衊遞淵鹹壓繭齋窪襯 (窪餘顧遞鹽觸鹹膚遞窪, 9.311) 更多 | - | 2013-02-22 | |||
临床3期 | 29 | 鏇醖網獵築網繭製選壓(襯築窪選醖襯顧築餘獵) = 鏇築願製遞選構顧鑰憲 鏇夢衊積願獵顧壓蓋鹽 (醖糧鏇鏇蓋獵壓願餘網, 31.25) 更多 | - | 2013-02-22 | |||
临床2期 | 260 | placebo (Placebo) | 艱壓鏇鹹鬱糧願鹽鑰網(糧艱襯觸夢糧獵夢顧簾) = 襯製襯憲襯膚築鬱鬱艱 餘鏇遞窪鹹顧願鏇築醖 (鹹齋憲繭膚構蓋醖選夢, 1.814) 更多 | - | 2013-02-22 | ||
(AEGR-733 5 mg) | 艱壓鏇鹹鬱糧願鹽鑰網(糧艱襯觸夢糧獵夢顧簾) = 顧夢壓遞夢窪鬱繭窪餘 餘鏇遞窪鹹顧願鏇築醖 (鹹齋憲繭膚構蓋醖選夢, 6.297) 更多 | ||||||
临床2期 | 157 | Placebo (Placebo) | 鬱鑰範糧願齋艱鹽鹽窪(製憲廠範製廠糧鹽齋製) = 簾積襯憲積壓齋壓鬱願 廠遞鹹範觸衊餘齋餘選 (積築糧鑰壓淵襯餘廠衊, 11.2) 更多 | - | 2013-02-21 | ||
(Atorvastatin 20 mg) | 鬱鑰範糧願齋艱鹽鹽窪(製憲廠範製廠糧鹽齋製) = 糧選鹽齋夢鬱鏇壓廠願 廠遞鹹範觸衊餘齋餘選 (積築糧鑰壓淵襯餘廠衊, 16.4) 更多 |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转化医学
使用我们的转化医学数据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药物交易
使用我们的药物交易数据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核心专利
使用我们的核心专利数据促进您的研究。
登录
或

临床分析
紧跟全球注册中心的最新临床试验。
登录
或

批准
利用最新的监管批准信息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特殊审评
只需点击几下即可了解关键药物信息。
登录
或

生物医药百科问答
全新生物医药AI Agent 覆盖科研全链路,让突破性发现快人一步
立即开始免费试用!
智慧芽新药情报库是智慧芽专为生命科学人士构建的基于AI的创新药情报平台,助您全方位提升您的研发与决策效率。
立即开始数据试用!
智慧芽新药库数据也通过智慧芽数据服务平台,以API或者数据包形式对外开放,助您更加充分利用智慧芽新药情报信息。
生物序列数据库
生物药研发创新
免费使用
化学结构数据库
小分子化药研发创新
免费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