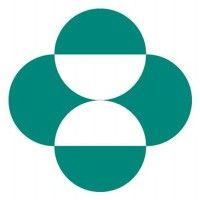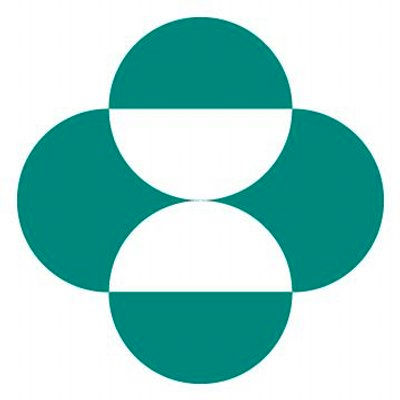预约演示
更新于:2026-02-27
Alendronate Sodium
阿仑膦酸钠
更新于:2026-02-27
概要
基本信息
最高研发阶段批准上市 |
首次获批日期 意大利 (1993-01-01), |
最高研发阶段(中国)批准上市 |
特殊审评- |
登录后查看时间轴
结构/序列
分子式C4H15NNaO8P2 |
InChIKeyHZMNHMQPEYMSTG-UHFFFAOYSA-N |
CAS号121268-17-5 |
关联
256
项与 阿仑膦酸钠 相关的临床试验NCT06016634
A Feasibility Study of Alendronate as Treatment for Osteonecrosis in Adults With Sickle Cell Disease
A prospective, single-arm, intervention study of oral alendronate in adults with sickle cell disease and osteonecrosis
开始日期2026-02-09 |
申办/合作机构 |
NCT07216794
Small Trial of Alendronate Impact on the Reservoir of HIV
This clinical trial is designed to test the effects of alendronate (ALN) on people living with HIV who are already receiving 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 Participants are randomly assigned in a 2:1 ratio to either receive alendronate or a placebo, and neither the participants nor the researchers know who is receiving the actual treatment. The goal is to see if alendronate can reduce the size and activity of the HIV-1 reservoir in these individuals.
开始日期2026-01-17 |
NCT07245381
A Pilot Study to Investigate the Use of Alendronate to Reduce the Risk of Pelvic Insufficiency Fractures in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Chemotherapy and Radiation Therapy
Primary Objective
- Proof of concept: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alendronate in preventing pelvic insufficiency fractures (PIFs) in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chemo-radiotherapy over the short and long term. This objective will assess both the immediate and sustained effects of the drug on bone integrity through periodic bone mineral density measurements and clinical assessment of fracture incidence.
Secondary Objectives
* To assess the safety and tolerability of alendronate: This will involve monitoring and documenting any acute and chronic side effects associated with alendronate use in this patient populati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gastrointestinal issues, renal function impairment, and osteonecrosis of the jaw.
* To document and analyze changes in quality of life: Using validated quality of life instruments, this objective will track changes in patient-reported outcomes, focusing on aspects such as pain levels, physical function, and overall well-being. This will help determine if the intervention not only prevents fractures but also contributes positively to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during and after treatment.
* To explore correlations between patient-specific factors and treatment efficacy: This objective aims to understand how variables such as age, cancer stage, previous treatment history, and baseline bone health might influe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alendronate in preventing PIFs and enhancing bone mineral density.
- Proof of concept: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alendronate in preventing pelvic insufficiency fractures (PIFs) in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chemo-radiotherapy over the short and long term. This objective will assess both the immediate and sustained effects of the drug on bone integrity through periodic bone mineral density measurements and clinical assessment of fracture incidence.
Secondary Objectives
* To assess the safety and tolerability of alendronate: This will involve monitoring and documenting any acute and chronic side effects associated with alendronate use in this patient populati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gastrointestinal issues, renal function impairment, and osteonecrosis of the jaw.
* To document and analyze changes in quality of life: Using validated quality of life instruments, this objective will track changes in patient-reported outcomes, focusing on aspects such as pain levels, physical function, and overall well-being. This will help determine if the intervention not only prevents fractures but also contributes positively to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during and after treatment.
* To explore correlations between patient-specific factors and treatment efficacy: This objective aims to understand how variables such as age, cancer stage, previous treatment history, and baseline bone health might influe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alendronate in preventing PIFs and enhancing bone mineral density.
开始日期2025-12-01 |
申办/合作机构 |
100 项与 阿仑膦酸钠 相关的临床结果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100 项与 阿仑膦酸钠 相关的转化医学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100 项与 阿仑膦酸钠 相关的专利(医药)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5,867
项与 阿仑膦酸钠 相关的文献(医药)2026-06-01·Bone Reports
Successful management of denosumab discontinuation in a patient with primary pediatric osteoporosis
Article
作者: Yavropoulou, Maria P ; Polyzos, Stergios A ; Anastasilakis, Athanasios D ; Makras, Polyzois ; Papapoulos, Socrates E
Treatment of a 13.5-year-old boy with severe primary osteoporosis and multiple vertebral deformities with denosumab (Dmab) 60 mg subcutaneously every 3 months for 30 months,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clinical, radiologic and densitometric improvement. During the second year of treatment, 2 episodes of transient hypercalcemia, probably due to the effect of growth spurt on bone remodeling were resolved quickly without any additional therapy except for the discontinuation of calcium supplements. When transition to the adult Dmab treatment schedule (60 mg/6 months) was attempted, severe hypercalcemia occurred 4 months after the last denosumab injection that was resolved quickly with a new Dmab injection. At the completion of 3 years of treatment, transition to oral alendronate 70 mg/weekly could not prevent a new episode of hypercalcemia that required a new Dmab injection concurrently with continuation of alendronate treatment to normalize. In the following months, serum calcium concentrations remained normal with only alendronate treatment that was stopped after 1.5 years, followed by a period of about 2 years with no additional osteoporosis treatment. In this unique case of primary pediatric osteoporosis observed closely in adolescence with and without Dmab treatment for more than 7 years, concurrent administration of alendronate and denosumab, followed by alendronate monotherapy for another year prevented further hypercalcemic episodes and allowed discontinuation of all treatments while maintaining the acquired BMD gains without any regression of the regained normal shape of vertebral deformities.
2026-05-01·Value in Health Regional Issues
Article
作者: Vianna, Cid Manso de Mello ; Rodrigues, Marcus Paulo da Silva ; Bandeira, Tayna Felicíssimo Gomes de Souza ; Mosegui, Gabriela Bittencourt Gonzalez ; Lima, Tácio de Mendonça
OBJECTIVES:
To calculate the cost-effectiveness ratio and the budget impact of teriparatide use in men with severe osteoporosis and history of fractures in Brazil.
METHODS:
Three hypothetical cohorts of men with severe osteoporosis and history of fracture, with initial ages of 50, 60, and 70 years, were simulated using a Markov Model to calculate the cost-effectiveness ratio between teriparatide and alendronate and risedron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ified Health System (SUS). The time horizon was 10 years, with cycles of 1 year. Effectiveness outcomes were measured in quality-adjusted life-years (QALY). Deterministic and probabilistic sensitivity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RESULTS:
Teriparatide compared with alendronate and risedronate has an 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 of 77,002/79,808 R$/QALY, 305,435/439,636 R$/QALY, and 327,869/460,333 R$/QALY for 50, 60, and 70 years, respectively. The deterministic and probabilistic evaluations did not produce results that altered the previous conclusion and, in all situations, the teriparatide was not cost-effective for a threshold of R$ 40,000.00/QALY. The analysis of the budget impact estimated that the use of teriparatide for a market share of 60% in 5 years would have an additional cost of approximately R$ 187 million.
CONCLUSIONS:
In the analyzed scenarios, the use of bisphosphonates produces resource savings in relation to teriparatide in the treatment of men. Teriparatide was not cost-effective in any situation.
2026-04-01·Materials Today Bio
Alendronic acid modified PLGA drug delivery system loaded with 17β-Estradiol and vitamin D3 has anti-osteoporotic effect
Article
作者: Gao, Yanhong ; Wang, Yonghui ; Lei, Xue ; Liu, Junran ; Zhang, Sidi ; Ma, Xinrun ; Wei, Lu ; Hu, Yan ; Li, Fuyou ; Hu, Donghao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caused by estrogen deficiency often requires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HRT), but its systemic side effects limit clinical application. Here, we developed a bone-targeted Poly (lactic-co-glycolic acid) (PLGA) nanocarrier modified with Alendronic acid (ADA) to co-deliver 17β-Estradiol (E2) and Vitamin D3 (VitD3), aiming to enhance efficacy and safety. The ADA-functionalized nanoparticles (E2+VD@PLGAIR780ADA) showed high drug loading (7.2 wt% for E2 and 2.3 wt% for VitD3), sustained release (>90 % over 48 h). In ovariectomized (OVX) mice, targeted delivery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one mineral density, restored trabecular structure, and reduced serum bone resorption markers, while markedly alleviating E2-induced endometrial thickening. In vivo imaging confirmed selective bone accumulation. Mechanistically, co-administration of VitD3 and E2 elicits enhanced pro-osteogenic effects by virtue of VitD3-mediated Vitamin D Receptor (VDR) upregulation and amplified E2-induced estrogen receptor (ER) expression, which collectively drive robust activation of the PI3K/AKT/mTOR signaling cascade.This bone-specific nanoplatform offers a promising and safer strategy for osteoporosis therapy beyond conventional HRT.
172
项与 阿仑膦酸钠 相关的新闻(医药)2026-02-22
·胡金艮
摘要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以骨量低下和骨微结构破坏为特征的全身性骨病,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补钙作为其基础预防和治疗的基石,其具体的有效性、潜在安全性以及如何实现优化补充策略,始终是学术界与临床实践关注的焦点。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和综述补钙在骨质疏松症防治中的核心作用机制,比较不同钙剂类型的特性与适用性,探讨最佳补充剂量、时机及其与维生素D等关键营养素的协同效应。同时,分析补钙干预对不同高危人群(如绝经后女性和老年人)的疗效差异,评估长期应用可能带来的心血管事件及肾结石等安全性风险,并整合基于循证医学的最新临床指南推荐。通过系统整合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的现有证据,本综述期望为骨质疏松症的精准化、个体化营养干预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与切实的临床实践指导。关键词:骨质疏松症;钙补充;骨密度;维生素D;安全性;临床指南前言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其导致的骨折并发症给个人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1][2]。骨折,尤其是髋部骨折,与高发病率、死亡率和医疗成本密切相关[3]。值得注意的是,骨质疏松症在男性中常被低估和诊断不足,尽管男性骨折后的死亡率和并发症风险可能更高[4][5]。此外,骨质疏松症是多种慢性疾病的常见并发症,例如创伤性脊髓损伤[6]、肝移植后[7]、强直性脊柱炎[8]以及糖皮质激素治疗[9]等,这进一步凸显了其防治的广泛重要性。
钙是骨骼矿物质的主要成分,充足的钙摄入对获得峰值骨量和维持骨健康至关重要[10]。峰值骨量的积累主要发生在儿童期和青春期,受遗传、种族、性别以及体力活动、钙和蛋白质摄入等环境因素共同影响[11]。研究表明,儿童期和青春期的钙摄入不足会损害骨量积累,导致骨密度和骨微结构下降,即使在没有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情况下也是如此[12]。因此,优化生命早期阶段的钙摄入是预防晚年骨质疏松的关键策略[13]。然而,在资源有限或饮食模式特殊的人群中,如严格素食者[14]或贫困老年人[15],钙摄入不足的风险显著增加。
尽管补钙被广泛推荐,但其在骨质疏松症防治中的确切角色、最佳实践方案及潜在风险仍存在争议和不断演进的认识。传统的口服钙补充剂,如碳酸钙,虽然常用,但其疗效和安全性受到质疑。例如,在老年骨质疏松小鼠模型中,补充碳酸钙可能破坏肠道屏障和微生物生态系统,加剧全身炎症反应,从而削弱其治疗效果[16]。此外,补钙的心血管风险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一项基于韩国人群的全国性队列研究发现,单独补充钙(不含维生素D)与复合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相关,而钙与维生素D联合补充则未显示出这种危害[17]。最近的荟萃分析也提示,在健康的绝经后妇女中,钙补充剂可能使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约15%[18]。这些发现强调了在补钙时需考虑维生素D的协同作用以及个体化的风险评估。
近年来,随着大规模临床试验和荟萃分析结果的公布,对补钙的获益与风险平衡有了更深入的评估。例如,一项系统评价发现,在接受抗骨吸收药物治疗的绝经后骨质疏松妇女中,维生素D补充与较低的胃肠道不良事件和死亡率相关,而钙补充则未显示与任何终点显著相关[19]。另一项针对老年人群的荟萃分析得出结论,钙和/或维生素D补充在降低骨折风险方面并未显示出优于安慰剂或未治疗的明确益处[20]。这些证据促使临床实践更加审慎,倾向于通过膳食来源优先满足钙需求,并对补充剂的使用采取个性化策略[21]。
同时,个性化补钙策略,包括考虑个体吸收差异、膳食基线摄入量及合并用药等,成为新的研究方向。研究显示,遗传因素如Cdx2多态性可能影响膳食钙摄入与峰值骨量之间的关系[22]。此外,肠道微生物群在钙吸收和骨代谢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益生菌和益生元(如可溶性玉米纤维)可能通过调节肠道环境来增强钙的生物利用度[23][24]。新型的钙递送系统也在开发中,例如基于纳米技术的靶向递送平台,旨在提高钙的靶向性和吸收效率,同时降低所需剂量和潜在副作用[25][26]。这些进展预示着骨质疏松症的补钙干预正朝着更精准、更有效的方向发展。1. 钙在骨代谢中的生理学基础与骨质疏松病理机制1.1 钙稳态的调节与骨重塑循环
钙稳态的精密调节是维持骨骼健康的核心,这一过程主要依赖于甲状旁腺激素(PTH)、降钙素和活性维生素D(1,25-(OH)2D3)的协同作用。PTH是调节血钙浓度的关键激素,当血钙降低时,PTH分泌增加,通过促进肾脏对钙的重吸收、刺激骨吸收以及增强肾脏合成1,25-(OH)2D3来提升血钙水平[27]。活性维生素D则主要促进肠道对钙的吸收,是维持钙平衡不可或缺的环节[28]。降钙素则在血钙过高时发挥拮抗作用,通过抑制破骨细胞活性来降低血钙。这些激素共同构成了一个精细的反馈环路,确保血钙浓度在一个狭窄的生理范围内波动[29]。血钙水平的波动直接影响骨重塑循环。在骨重塑区室(BRC)附近,细胞外钙浓度局部升高,钙敏感受体(CaSR)能够感知这种变化,并调节骨形成细胞(成骨细胞)和骨吸收细胞(破骨细胞)的活性[30]。细胞内钙信号对于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分化与功能至关重要,是连接全身钙稳态与局部骨重塑的关键分子[31]。例如,线粒体钙单向转运体(MCU)通过调节线粒体钙稳态和氧化应激,直接影响成骨细胞的分化能力,从而参与骨重塑的调控[32]。因此,钙稳态的激素调节与局部骨细胞对钙离子的响应,共同构成了骨重塑的生理基础。
在衰老和雌激素缺乏等病理状态下,上述钙稳态调节系统失衡,导致骨重塑负平衡,即骨吸收大于骨形成,这是骨质疏松症发生的关键机制。衰老伴随着肠道钙吸收效率的下降,这与维生素D受体敏感性降低以及肠上皮细胞钙转运蛋白功能减退有关[33]。活性维生素D水平的不足或作用减弱,直接影响了钙的肠源性供应。与此同时,PTH的生理节律可能发生改变,慢性PTH水平升高(如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会持续刺激骨转换,偏向于骨吸收,导致骨量丢失和骨微结构破坏[27]。在雌激素缺乏状态下,如绝经后妇女,其对破骨细胞的抑制作用减弱,进一步加剧了骨吸收的亢进。这种钙稳态的长期失衡,使得骨重塑循环无法维持骨形成与骨吸收的平衡。研究表明,骨重塑是一个动态的、由破骨细胞启动、成骨细胞跟进的连续过程,其根本目的之一是维持钙磷稳态[34]。当钙吸收不足或激素调节紊乱时,机体为维持血钙稳定,会过度动员骨骼中的钙库,加速骨吸收,而骨形成却无法同步补偿,最终导致净骨量丢失[35]。这种负平衡状态是骨质疏松症进行性骨量减少和骨折风险增加的核心病理生理过程。
肠道钙吸收效率随年龄增长而下降是加剧钙负平衡和骨质疏松风险的重要因素,其机制涉及多个层面。首先,活性维生素D(1,25-(OH)2D3)的合成与效能降低是关键。随着年龄增长,肾脏1α-羟化酶活性可能下降,导致1,25-(OH)2D3生成减少[33]。更重要的是,肠道维生素D受体(VDR)的表达和敏感性可能随年龄增长而减退,这使得即使循环中1,25-(OH)2D3水平正常,其促进肠钙吸收的生物效应也会大打折扣[28]。其次,肠上皮细胞上负责钙主动转运的蛋白质功能发生改变。钙通过肠上皮细胞的跨细胞转运主要依赖于瞬时受体电位香草酸亚型6(TRPV6)通道、钙结合蛋白D9k(Calbindin-D9k)和质膜钙ATP酶(PMCA1b)。研究表明,衰老可能下调这些转运蛋白的表达或功能。例如,在动物模型中,衰老相关的VDR信号通路减弱会直接导致TRPV6和Calbindin-D9k表达下降[33]。此外,衰老还可能伴随胃酸分泌减少,影响食物中钙盐的溶解和离子化,从而减少被动扩散吸收的钙量。这些变化共同导致饮食钙的吸收率显著降低。为了代偿肠道吸收的不足,PTH分泌可能代偿性增加,以通过增强骨吸收来维持血钙,但这进一步加速了骨丢失[27]。因此,年龄相关的肠钙吸收障碍不仅是钙摄入不足的问题,更是触发和加剧骨重塑负平衡、导致骨质疏松的重要环节。1.2 钙缺乏在骨质疏松发生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长期膳食钙摄入不足是导致骨质疏松症发生发展的核心病理生理环节之一。当机体长期处于钙负平衡状态时,血清钙离子浓度下降,这会刺激甲状旁腺分泌更多的甲状旁腺激素(PTH),引发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36]。PTH水平的持续升高会通过作用于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显著增加骨转换率,即同时加速骨形成与骨吸收过程。然而,在钙持续缺乏的情况下,骨吸收的速率往往超过骨形成,导致净骨量丢失[37]。这一过程对骨骼的微结构造成双重损害:一方面,PTH促进破骨细胞对骨小梁的侵蚀,使原本致密的网状结构变得稀疏、断裂,骨小梁数量和厚度下降,分离度增加;另一方面,它也作用于皮质骨,导致皮质骨孔隙率增加、厚度变薄[38]。动物模型研究清晰地揭示了这一过程,例如,通过低钙饮食诱导的骨质疏松大鼠模型显示,其股骨骨钙含量和骨密度显著降低,同时伴随骨小梁体积减少、厚度变薄以及分离度增大的微观结构恶化[38]。这种由钙缺乏驱动的、经PTH介导的高转换型骨丢失,是骨质疏松症,特别是老年性骨质疏松的重要机制。
临床研究数据有力地支持了膳食钙摄入量与骨骼健康之间的密切关联。充足的钙摄入对于在青少年期和青年期达成理想的峰值骨量至关重要,而峰值骨量是决定个体一生中骨折风险的关键因素之一[36]。一项针对印度武装部队士兵的横断面研究发现,牛奶及奶制品的消费量与血清钙水平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正相关,提示充足的膳食钙摄入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血钙水平,从而可能对骨骼健康产生积极影响[39]。相反,长期钙摄入不足的人群,其峰值骨量可能低于理想水平,为日后骨质疏松埋下隐患。随年龄增长,尤其是女性绝经后和男性老年期,骨量会生理性丢失。此时,充足的钙摄入可以减缓这一丢失速率。研究表明,补充钙剂(如碳酸钙)与维生素D联合使用,能够有效增加骨密度(BMD),而单独补充维生素D则效果不显著[40]。这凸显了钙在维持老年期骨量中的基础作用。对钙缺乏小鼠的研究也证实,长期钙缺乏会导致钙吸收率和骨钙含量显著降低,并伴有骨小梁结构的恶化;而通过膳食补充(如含有益生菌和益生元的合生元奶粉)可以显著改善表观钙吸收率,提高血清钙磷水平,并增加骨矿物质密度和骨小梁数量[41]。这些证据共同表明,无论是生命早期还是衰老过程中,充足的钙摄入对于优化骨量积累和减缓骨量丢失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钙缺乏并非孤立地损害骨骼健康,它常与其他膳食风险因素产生交互作用,共同加剧骨质疏松的风险。其中,蛋白质摄入不足是一个重要的协同因素。蛋白质是骨基质有机成分(主要是胶原蛋白)合成的基础,其摄入不足会影响骨基质的形成和修复。在钙缺乏的背景下,骨转换加速,对蛋白质的需求增加,若此时蛋白质供应不足,新骨的形成质量将大打折扣,进一步削弱骨骼的机械强度[38]。研究显示,补充羊骨蛋白水解物与氯化钙,不仅能促进钙吸收,还能显著增强骨骼的机械强度,改善骨的微观结构,使骨小梁网络更连续、完整和粗壮[38]。这提示蛋白质与钙在维持骨质量方面具有协同作用。另一个关键交互因素是钠摄入过高。高钠饮食会增加尿钙的排泄,导致钙的负平衡加剧[36]。当膳食钙本身摄入不足时,高尿钙排泄无异于雪上加霜,使机体更难维持钙稳态,从而加速骨钙的动员和丢失。此外,严格的植物性饮食模式也值得关注。系统性综述表明,规划不当的纯素食或素食饮食,由于可能缺乏钙、维生素B12和铁,与贫血风险增加和骨矿物质密度降低相关[42]。对于炎症性肠病患者,由于疾病本身导致的吸收障碍以及对乳制品(传统钙源)的回避,钙和维生素D缺乏非常普遍,这显著增加了其罹患骨质疏松的风险[43]。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钙磷代谢和骨重建的复杂网络,放大了钙缺乏对骨骼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评估和干预骨质疏松风险时,必须综合考虑钙摄入与这些相关膳食因素的交互作用。2. 不同钙补充剂的药理学特性与生物利用度比较2.1 无机钙盐:碳酸钙与柠檬酸钙
在骨质疏松症的补钙干预策略中,无机钙盐,尤其是碳酸钙和柠檬酸钙,是临床应用最为广泛的两种补充剂,它们在理化性质、吸收机制和适用人群上存在显著差异。碳酸钙是含钙量最高的钙盐形式之一,其元素钙含量约为40%,这意味着较小的剂量即可提供较多的钙元素[44]。然而,碳酸钙的吸收高度依赖于胃酸环境,其需要在酸性条件下解离为可溶性的钙离子才能被有效吸收,因此通常建议随餐或餐后服用,以利用食物刺激产生的胃酸[45]。相比之下,柠檬酸钙的元素钙含量较低,约为21%,但其优势在于其溶解不依赖于胃酸,即使在胃酸缺乏或空腹状态下也能被良好吸收[46]。这使得柠檬酸钙成为胃酸分泌不足患者(如萎缩性胃炎患者、长期服用质子泵抑制剂者)以及需要空腹服药人群的更优选择。一项针对老年骨量减少患者的真实世界研究显示,柠檬酸钙补充剂具有良好的依从性和耐受性,为这类人群提供了安全有效的补钙方案[46]。
影响碳酸钙与柠檬酸钙生物利用度的具体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胃酸状态是关键。对于胃酸缺乏的患者,如萎缩性胃炎或长期服用质子泵抑制剂者,服用碳酸钙的吸收率会显著下降,因为其无法在胃内被充分解离[45]。而柠檬酸钙的吸收则受此影响较小,其生物利用度相对稳定。此外,剂型也是影响患者依从性和吸收效率的重要因素。常见的剂型包括咀嚼片、泡腾片和液体剂等。咀嚼片和泡腾片可以提高服用的便利性和口感,可能改善老年患者的依从性。液体剂型中的钙通常已处于溶解状态,可能更易于吸收,尤其适用于吞咽困难或胃肠道功能较弱的患者[44]。然而,不同剂型对最终钙吸收效率的影响还需结合个体胃肠道环境和服用方式综合评估。值得注意的是,单纯补充钙剂的效果可能有限。研究显示,在老年性骨质疏松小鼠模型中,长期补充碳酸钙虽能轻微缓解年龄相关的骨量丢失,但同时也可能破坏肠道微生物生态、损害肠黏膜屏障功能并加剧全身炎症反应,导致其治疗老年性骨质疏松的疗效甚微[16]。这提示我们,在选择钙剂时,需综合考虑其吸收特性、潜在副作用以及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
除了传统的补充剂形式,新型的钙递送系统也在不断探索中,旨在提高钙的靶向性和生物利用度。例如,有研究构建了以无定形碳酸钙为核心的纳米平台,该平台能够响应骨质疏松微环境,实现钙的靶向递送和原位补充,从而在极低钙剂量下(仅为商业碳酸钙片剂的十分之一)实现协同治疗,并显著减轻副作用[26]。另一项研究则开发了掺杂葡萄糖酸钙的抗氧化碳点,该复合物具有抗氧化和补钙双重功能,能有效提高钙的生物利用度,实现超低浓度钙补充治疗铁过载诱导的骨质疏松[47]。这些前沿研究为克服传统无机钙盐的局限性提供了新思路。在临床联合用药方面,碳酸钙常作为基础治疗。例如,在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后的骨质疏松患者中,唑来膦酸联合碳酸钙和维生素D3治疗,能更有效地改善骨代谢指标和骨密度,提升患者生活质量[48]。另一项针对老年原发性骨质疏松患者的研究也证实,在碳酸钙D3和骨化三醇基础上加用唑来膦酸,能显著提高骨密度、改善骨代谢并提升临床疗效[49]。然而,长期钙补充也需关注潜在风险,如一项横断面研究指出,有复发性肾结石病史的骨质疏松患者在接受钙和维生素D补充期间,发生肾结石的风险独立增加,这可能与尿钙排泄增多有关[50]。因此,临床实践中需对患者进行个体化评估,权衡补钙的获益与风险。2.2 有机钙及其他新型钙剂
有机钙盐,如氨基酸螯合钙、乳酸钙和葡萄糖酸钙,因其在胃肠道中通常具有更好的溶解度而受到关注,这有助于提高钙离子的生物利用度。然而,这类钙剂的一个普遍局限性是其元素钙含量相对较低,这意味着要达到相同的钙补充量,可能需要摄入更大的剂量或体积。研究表明,肽-钙螯合物相较于氨基酸-钙螯合物、有机钙及无机钙,能激发更高的钙吸收率[51]。例如,从大豆酸奶中纯化鉴定出的一种新型肽DEDEQIPSHPPR(CBP),其钙结合活性可达36.64 ± 0.04 mg g-1,并且能够显著增加斑马鱼骨质疏松模型的骨量[51]。这提示,通过特定的肽或氨基酸进行螯合,可以改善钙在消化道的稳定性,从而可能为临床骨质疏松治疗提供有用的载体[51]。此外,发酵乳制品,如酸奶,不仅含有生物可利用的钙,还可能含有其他生物活性成分,如肽、寡糖和有机酸,这些成分共同作用可能进一步促进钙的吸收和骨骼健康[52]。因此,尽管有机钙盐的元素钙含量偏低,但其通过改善溶解度和利用特殊载体(如特定肽段)的策略,为高效补钙提供了新的思路。
从天然生物质中提取的钙源,如海藻和红藻,正成为传统钙补充剂的有益替代或补充。这些天然来源的钙通常并非以单一成分存在,而是可能伴随有其他对骨骼健康有益的矿物质,如镁和锶,从而产生潜在的协同效应。例如,蛋壳膜(ESM)作为一种天然生物材料,其有机化学成分与人类骨骼相似,主要包含I型胶原、硫酸软骨素、硫酸皮肤素、透明质酸和弹性蛋白[53]。研究表明,补充蛋壳膜可以改善人体细胞的钙摄取,并在骨质疏松患者中观察到疼痛减轻和成骨细胞活性增加[53]。这种效应可能部分归因于蛋壳膜中含有的多种成分共同促进了骨组织的矿化。此外,牛奶及其组分在改善钙吸收和支持骨骼健康方面的作用已被广泛讨论,其中含有的益生元如低聚半乳糖(GOS)不仅能改善矿物质平衡和骨骼特性,还能增加肠道中的双歧杆菌,产生益生元效应,这可能间接促进了包括钙在内的矿物质吸收[52]。这些发现表明,天然复合钙源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钙元素,更在于其可能通过所含的其他矿物质和生物活性物质,从多个层面协同维护骨骼稳态。
新型制剂技术,如纳米钙和微球化钙,旨在通过提高钙的溶解度和实现靶向递送来克服传统钙剂的局限性。纳米技术可以显著增加钙剂的比表面积,从而改善其在水性环境中的溶解性和生物可及性。例如,研究开发了具有核壳结构的纳米颗粒药物系统,其核心是由甘草酸和钙离子合成的金属有机框架(MOF),外部包裹血小板膜囊泡,这种设计旨在实现向肾脏炎症部位的非特异性靶向,并在酸性炎症环境下缓慢降解释放药物,同时甘草酸还能缓解由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引起的骨质疏松[54]。在钙补充领域,有研究构建了由四环素修饰的单硬脂酸甘油酯包被的无定形碳酸钙(ACC)平台,作为口服骨靶向且对骨质疏松微环境(水/pH)响应的载体,用于原位钙补充[26]。这种系统能够在低钙剂量下实现协同的成骨促进疗法,并显著减轻副作用[26]。此外,基于两性离子羧酸配体的钙金属有机框架(MOF)被证明具有良好的水稳定性和生物相容性,在体外能调节成骨细胞分化,在体内能显著缓解卵巢切除小鼠的骨丢失,且对主要器官无毒性作用[55]。这些创新制剂技术通过提高钙的递送效率和靶向性,为开发更安全有效的骨质疏松治疗策略开辟了新途径。3. 补钙的剂量、时机与疗程优化策略3.1 基于年龄与生理状态的个性化剂量推荐
骨质疏松症的补钙干预策略强调个性化原则,其核心在于根据个体的年龄、生理状态及潜在病理状况制定精准的钙摄入推荐。国内外主要指南,如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IOF)、美国国家骨质疏松基金会(NOF)及中华医学会的相关共识,均对不同人群的每日总钙摄入量(膳食与补充剂之和)提供了具体指导。一般而言,对于19-50岁的健康成人,推荐每日摄入约1000毫克钙以维持骨骼健康[56]。对于50-70岁的男性,推荐摄入量通常维持在1000毫克/日,而绝经后女性由于雌激素水平下降导致骨丢失加速,其钙需求增加,指南多推荐每日摄入1200毫克[57]。年龄超过70岁的老年人,无论性别,由于肠道钙吸收效率下降和肾脏钙保留能力减弱,每日钙摄入推荐值通常提高至1200毫克[58]。这些推荐值是基于维持骨骼稳态和最大化峰值骨量的流行病学证据制定的。
确定个体化补充剂量的关键在于准确评估膳食钙摄入。临床实践中常通过食物频率问卷(FFQ)等工具进行估算。例如,一项针对澳大利亚18-30岁年轻人的横断面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女性和近半数的男性每日钙摄入量低于估计平均需要量(EAR),其主要原因是奶制品摄入不足[56]。因此,补充剂量应计算为推荐总摄入量减去通过膳食评估获得的实际摄入量之差,旨在填补“钙缺口”,而非盲目补充。过量补钙(尤其是通过补充剂形式)可能带来肾结石、血管钙化等风险,因此避免过量至关重要[59]。一项针对中国香港中老年人的随机对照试验表明,通过强化牛奶补充钙质(每日约600毫克)并结合运动,能有效改善骨转换标志物,而未报告高钙血症,这体现了在评估基础上进行补充的安全性[60]。
在特殊病理状态下,钙剂量的调整需格外谨慎。对于慢性肾脏病(CKD)患者,由于肾脏1α-羟化酶活性受损及高磷血症风险,钙的补充需综合考虑血清钙、磷及甲状旁腺激素(PTH)水平,通常建议使用非钙磷结合剂并限制钙摄入,以避免转移性钙化[61]。在甲状旁腺功能异常的情况下,如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PHPT),其特征是高钙血症和PTH不适当升高。此时,首要目标是控制高钙血症,通常需要限制膳食钙摄入,并积极处理原发病。一项关于妊娠期PHPT的病例报告指出,通过低钙饮食、充分水化等保守治疗,可以在严密监测下管理高钙血症,保障母婴安全[62]。相反,对于因甲状腺功能亢进或其他原因导致的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并伴有低钙血症的患者,则需要在治疗原发病的同时补充钙和活性维生素D[63]。此外,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的患者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指南建议在开始长期(≥3个月)糖皮质激素治疗时即评估骨折风险,并确保充足的钙(通常与维生素D联合)摄入作为基础措施,但具体剂量需结合抗骨质疏松药物使用及个体风险分层来确定[64]。总之,基于病理状态的钙剂量调整是一个动态、综合的过程,必须由临床医生在全面评估后个体化实施。3.2 服用时机、频率与吸收效率的关系
钙剂的服用时机、频率与剂量是影响其肠道吸收效率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通过影响肠道转运蛋白的饱和动力学及内环境而发挥作用。从生理学原理上看,肠道对钙的吸收主要依赖于主动转运和被动扩散两种方式,其中主动转运过程涉及瞬时受体电位香草酸亚型6(TRPV6)通道、钙结合蛋白(Calbindin-D28k)以及基底膜侧的质膜钙泵(PMCA1b)等关键蛋白[65][66]。这些转运蛋白的容量有限,遵循饱和动力学原理。当单次摄入大剂量钙(如超过500毫克)时,肠道上皮细胞上的转运蛋白会迅速达到饱和状态,多余的钙离子无法被有效吸收,只能通过被动扩散或随粪便排出,导致净吸收率下降。相反,采用分次补充策略(如每次剂量≤500毫克),可以使每次摄入的钙量处于肠道主动转运系统的有效处理范围内,避免了转运蛋白的过早饱和,从而显著提高钙的净吸收率[67]。这种策略优化了钙离子与肠道转运蛋白的接触时间和效率,是提高钙补充剂生物利用度的基础生理学依据。
随餐服用是提高某些钙剂,尤其是碳酸钙吸收率的常用策略。餐后胃酸分泌增加,有助于将不溶性的碳酸钙转化为可溶的氯化钙,从而促进其在十二指肠和空肠上段的吸收[16]。此外,食物中的某些成分,如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可能通过暂时改变肠道局部pH值或提供能量而间接促进钙的主动转运过程。然而,随餐服用也需注意食物种类的选择。某些食物中富含的草酸(如菠菜、甜菜叶)和植酸(如全谷物、豆类)会与钙离子在肠道内结合,形成难溶性的草酸钙或植酸钙盐,从而显著降低钙的生物可利用度[68]。一项基于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HANES)的序列横断面分析显示,1999年至2023年间,美国成年人膳食中草酸和植酸摄入量呈上升趋势,而钙摄入量和牛奶消费量下降,这与钙吸收率降低及骨密度下降、骨质疏松症患病率增加显著相关[68]。因此,建议在服用钙补充剂时,应避免与富含草酸或植酸的食物同服,以最大化其吸收效益。
探讨睡前补钙的理论优势主要基于对钙代谢昼夜节律的调节。夜间,尤其是后半夜,血钙水平有生理性下降趋势,这会刺激甲状旁腺激素(PTH)分泌增加。PTH通过促进骨吸收来动员骨钙入血以维持血钙稳定,长期而言这一过程会加剧骨量丢失[66]。理论上,在睡前补充钙剂可以提高夜间血钙水平,从而抑制PTH的过度分泌,减少夜间骨吸收的激活。尽管这一假说在生理学上具有合理性,但直接的临床研究证据仍需进一步充实。现有研究更多聚焦于钙吸收的分子机制和长期补充效果。例如,研究表明雌激素通过ERβ上调十二指肠黏膜细胞PMCA1b的表达和功能,从而促进钙吸收并改善绝经后骨质疏松[66]。另一项研究则发现,脱氢表雄酮(DHEA)虽然能改善去卵巢大鼠的骨密度,但其作用并不涉及对肠道钙吸收的影响[69]。这些研究提示,不同干预措施对骨代谢的影响途径各异。虽然专门针对“睡前服用”时机的高质量临床对照试验有限,但基于钙代谢的昼夜节律理论,在晚间(如晚餐后或睡前)分次补充一天中的部分钙剂量,可能是一种合理的、旨在平抑夜间PTH波动的辅助策略,但其临床净收益仍需更多设计严谨的研究来验证。4. 钙与维生素D的协同作用及联合补充证据4.1 维生素D对钙吸收和骨代谢的关键作用机制
维生素D是钙稳态和骨代谢的关键调节因子,其经典功能在于促进肠道对钙和磷的吸收[70]。维生素D本身无生物活性,需在肝脏经25-羟化酶(CYP2R1)羟化为25-羟基维生素D [25(OH)D],再在肾脏经1α-羟化酶(CYP27B1)转化为具有激素活性的1,25-二羟基维生素D [1,25(OH)2D3,即骨化三醇][[71]](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365463/)。骨化三醇通过与肠道上皮细胞内的维生素D受体(VDR)结合,形成复合物并转运至细胞核,与维生素D反应元件(VDRE)结合,从而启动下游靶基因的转录[70]。其中,上调肠道钙结合蛋白(如Calbindin-D9k)的表达是其促进钙吸收的核心分子机制之一。当膳食钙摄入量较低时,钙吸收主要依赖于这种维生素D调节的、可饱和的主动转运途径[70]。动物模型研究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敲除介导维生素D作用的基因(如VDR)或维生素D生成的关键酶(如CYP27B1),会消除基础钙吸收能力,并阻止小鼠适应低钙饮食[72]。这表明,1,25(OH)2D3/VDR信号通路在肠道钙的主动吸收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生理功能[72]。
维生素D缺乏会直接导致肠道钙吸收效率下降,即使膳食钙摄入充足,也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的病理生理反应[73]。钙吸收不足导致血清离子钙水平降低,这会刺激甲状旁腺分泌更多的甲状旁腺激素(PTH),引发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73]。PTH通过增强骨吸收(即破骨细胞活性)来动员骨骼中的钙进入血液,以维持血钙稳定,其代价是持续的骨丢失[74]。此外,PTH还能促进肾脏对钙的重吸收,并刺激肾脏合成更多的骨化三醇,形成代偿性反馈调节[74]。然而,在长期维生素D缺乏的状态下,这种代偿机制不足以纠正钙吸收的根本缺陷,最终导致骨矿化不足和骨量减少。这在儿童中表现为佝偻病,在成人中则表现为骨软化症或加剧骨质疏松风险[75]。研究证实,维生素D缺乏与骨质疏松症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76]。在老年人中,维生素D的产生减少、膳食摄入不足、肾脏1α-羟化能力下降以及肠道VDR水平降低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钙吸收减少,成为老年性骨丢失的重要诱因[74]。
除了通过调节血钙间接影响骨骼,维生素D对骨骼也具有直接作用。它参与调节成骨细胞的分化、功能以及骨基质的矿化过程[77]。维生素D可以影响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成骨细胞谱系的分化,并调节成骨细胞特异性基因的表达,从而影响骨形成[28]。例如,在鱼类模型中的研究发现,适宜的维生素D3与维生素K3组合能上调与骨形成、骨重塑和钙稳态相关基因在椎骨等组织中的表达[28]。同时,维生素D也参与调节骨转换的平衡。足够的维生素D状态对于维持正常的骨矿化至关重要,它能确保有充足的钙和磷被输送到骨骼矿化前沿[77]。维生素D缺乏时,即使成骨细胞产生了足够的骨胶原基质(类骨质),也会因矿物质沉积障碍而导致矿化延迟或缺陷,即骨软化[75]。因此,维持充足的维生素D水平,对于保障骨骼的正常矿化、维持骨密度和骨强度具有基础性作用[73]。4.2 联合补充 versus 单独补钙的临床疗效对比
大型随机对照试验(RCT)和荟萃分析的系统回顾表明,在维生素D充足的背景下,联合补充钙和维生素D对于提高骨密度(BMD)至关重要。一项针对健康绝经前女性的Cochrane系统评价发现,单独补充钙或维生素D,或者两者联合补充,均未能显著改善腰椎或髋部的骨密度[78]。这一结果强调了在评估补钙效果时,必须考虑维生素D的营养状况。相反,在维生素D水平充足或得到纠正的情况下,补钙才能发挥其应有的骨骼效应。例如,一项针对老年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患者的研究显示,在联合使用钙剂(碳酸钙D3片)和活性维生素D(骨化三醇软胶囊)的基础上,加用唑来膦酸能显著提高腰椎(L1~L4节段)、股骨颈和髋部的骨密度[49]。这间接印证了充足的维生素D是钙剂发挥骨骼保护作用的基础。意大利的一个多学科工作组专家意见也明确指出,钙和维生素D的联合补充对于实现抗骨折效应和支持抗骨质疏松药物的疗效至关重要[79]。因此,临床证据强烈支持,只有在确保维生素D充足的前提下,补钙才能对提高腰椎和髋部骨密度产生显著影响。
关于骨折风险的降低,联合补充钙和维生素D显示出比单独补钙更明确的协同效应,尤其是在维生素D严重缺乏的脆弱老年人群中。大量试验证据表明,在社区居住的成年人中,单独补充钙剂并不能预防骨折[80]。同样,一篇综述指出,补充钙、维生素D或其组合并不能预防社区居住成年人的骨折,但一项针对维生素D缺乏的疗养院居民的大型研究确实证明了联合补充具有骨折预防作用[81]。这清晰地指出了目标人群维生素D基线水平的关键性:在维生素D严重缺乏(如25-羟基维生素D水平<25 nmol/L)的老年人群中,单独补钙几乎没有任何抗骨折效果。联合补充的协同机制在于,维生素D促进肠道对钙的吸收并抑制甲状旁腺激素(PTH),从而减少骨吸收。专家意见强调,钙和维生素D的联合补充对于达到能够抑制PTH和骨吸收的充足水平是必要的[79]。这种协同作用对于降低椎体和非椎体骨折风险均有益处。例如,在糖皮质激素诱导的骨质疏松症(GIOP)的治疗中,虽然研究重点在药物对比,但常规基础治疗均包含钙和维生素D的补充,以优化骨骼环境[82]。因此,临床决策应优先考虑对高风险、尤其是维生素D缺乏的老年个体进行联合补充,而非普遍推广单独补钙。
为了优化钙的利用和骨骼获益,探讨并确定最佳的维生素D补充剂量至关重要。国际上的共识倾向于使用营养性维生素D(胆钙化醇或麦角钙化醇)进行补充。证据表明,维生素D缺乏通常可通过每日补充400-800 IU的钙化醇来纠正[81]。对于更严重的缺乏或特定人群,可能需要更高的剂量。例如,在一项针对接受辅助化疗的早期乳腺癌患者的II期试验中,采用每3周10万IU(相当于每日约4760 IU)的高剂量25-羟基维生素D口服方案,成功使近半数患者在化疗期间实现了维生素D水平的正常化,且安全性良好[83]。然而,剂量也需谨慎,因为剂量超过4000 IU/天的维生素D补充与更多的跌倒和骨折风险相关[81]。因此,每日800-2000 IU的剂量范围被广泛认为是优化钙稳态和骨骼健康的安全有效区间。在特殊人群如慢性肾病(CKD)患者中,为确保地舒单抗治疗的安全性,需要维持高剂量的维生素D(如1000 IU/天)和钙剂补充,以预防低钙血症[84]。值得注意的是,应区分营养性维生素D与活性维生素D类似物(如骨化三醇)。后者因其增加高钙血症、血管钙化等风险,在国际上并不被视为骨质疏松症的标准疗法,其使用应严格限于特定的内分泌适应症[85]。综上所述,对于大多数骨质疏松症患者,每日补充800-2000 IU的营养性维生素D,结合适量的钙摄入,是平衡疗效与安全性的合理策略。5. 补钙对不同骨质疏松症人群的疗效差异5.1 绝经后女性
绝经后女性是骨质疏松症的高危人群,其骨量丢失呈现阶段性特征。在绝经早期,由于雌激素水平急剧下降,骨转换加速,导致骨吸收超过骨形成,出现快速骨丢失。在这一阶段,补钙干预对于减缓骨量丢失具有重要作用。一项针对约旦绝经后女性的全国性横断面研究显示,钙和维生素D补充剂的摄入与骨质疏松症患病率显著相关[86]。这表明,在骨丢失的快速期,确保充足的钙摄入是基础性干预措施。然而,单纯补钙的效果可能有限,尤其是在骨转换率极高的状态下。因此,补钙常需与其他抗骨吸收疗法联用以增强效果。例如,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SERMs)作为非激素类抗骨吸收药物,与钙剂联用可协同作用。有文献综述指出,对于绝经后骨质疏松女性,最有效的治疗方案应是个体化的,需确保SERMs和补钙等治疗的益处大于潜在风险,特别是心血管事件风险[87]。这提示在绝经早期,将补钙作为SERMs或激素替代疗法(HRT)的辅助手段,有助于在控制骨丢失的同时,综合评估和管理患者的整体健康风险。
随着年龄增长,高龄绝经后女性(通常指年龄>75岁)面临更为复杂的生理挑战,其肠钙吸收能力因年龄增长和维生素D合成减少而进一步下降,同时肾脏保钙功能减退,导致钙负平衡风险显著增加。因此,在这一人群中,补钙联合充足维生素D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一项系统综述专门探讨了在接受抗骨吸收药物治疗的绝经后骨质疏松女性中,补充维生素D和钙剂的效果。该综述发现,维生素D补充与较低的胃肠道不良事件发生率和死亡率相关,而钙补充则未显示出与任何主要终点(如骨密度、骨折率)的显著关联[19]。这一结果可能部分反映了高龄女性肠道钙吸收效率低下,单纯补钙难以有效提升血钙水平并促进骨矿化,凸显了维生素D在促进肠钙吸收中的关键作用。此外,针对肾功能正常但使用狄诺塞麦(一种强效抗骨吸收药物)的绝经后骨质疏松患者的研究发现,尽管所有患者均接受了钙和维生素D补充,仍有高达23%的患者出现低钙血症,其中严重低钙血症者占30.4%[88]。这一数据强烈提示,对于高龄女性,尤其是接受强效抗骨吸收治疗者,不仅需要补充钙和维生素D,还需密切监测血钙水平,并可能需要更高剂量或更生物可利用的钙剂形式,以确保充足的钙供应,预防因治疗引发的严重低钙血症及其并发症,如急性心力衰竭[89]。
绝经后女性对补钙干预的反应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与基线骨密度状态和膳食钙摄入水平有关。研究数据表明,不同骨密度状态的女性对干预措施的反应不同。例如,一项大型队列研究显示,在1669名接受DXA筛查的绝经后女性中,45.0%患有骨质疏松症,43.5%为骨量减少。尽管患病率高,但超过一半的骨质疏松女性未接受任何积极的药物治疗,而补充钙/维生素D的比例为20.6%[90]。这反映了治疗缺口,也暗示了不同基线骨密度人群的干预需求未被均等满足。对于基线骨密度较低(骨质疏松)的女性,补钙联合抗骨吸收药物的益处可能更为明显。另一方面,膳食钙摄入水平是决定补钙干预必要性和反应性的关键因素。一项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发现,强化了钙和维生素D的乳制品对绝经后女性的总骨密度和腰椎骨密度有显著有利影响,而单纯的钙和维生素D补充剂则未显示出对总骨密度和腰椎骨密度的显著影响[91]。这提示,对于膳食钙摄入不足的女性,通过强化食品或补充剂增加钙摄入可能带来骨密度获益;而对于膳食钙摄入已充足的女性,额外补充的边际效益可能较小。此外,一项针对中国绝经后女性的横断面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社会经济因素与骨质疏松风险的相关性,教育水平低、个人年收入低的女性患病率更高[92]。这些因素往往与营养知识、膳食质量和补充剂使用率相关,间接影响了不同膳食钙摄入水平女性对补钙干预的可及性和反应性。因此,临床实践中,评估绝经后女性的基线骨密度和膳食钙摄入情况,对于制定个体化、精准的补钙策略至关重要。5.2 老年男性
老年男性骨质疏松症具有其独特的病理生理特点,其中与年龄相关的性腺功能减退,即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症,是影响钙代谢和骨稳态的关键因素。随着年龄增长,男性血清睾酮水平逐渐下降,这不仅直接削弱了成骨细胞的活性,还间接通过影响维生素D代谢和肠道钙吸收,加剧了骨量丢失[93]。一项针对老年男性2型糖尿病合并骨质疏松患者的研究发现,低睾酮水平是重要的可控危险因素之一,强调了性腺功能在维持骨健康中的核心作用[93]。这种激素水平的改变导致骨转换失衡,骨吸收超过骨形成,使得老年男性成为骨质疏松及脆性骨折的高危人群。此外,老年男性骨质疏松的临床表现常较隐匿,骨折发生前往往缺乏典型症状,导致诊断和治疗延迟。流行病学数据显示,尽管老年男性骨质疏松的患病率低于同年龄段女性,但其导致的骨折,尤其是髋部骨折,伴随的死亡率和致残率却可能更高[94]。因此,深入理解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对钙代谢的负面影响,对于制定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策略至关重要。
针对老年男性的临床试验为补钙联合维生素D的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证据。尽管单纯补钙和维生素D在健康老年男性中对骨骼的益处可能有限,但在特定人群和联合其他干预措施时显示出积极效果[95]。例如,一项随机对照试验评估了在低睾酮水平且存在行动问题的老年男性中,联合使用睾酮、钙、维生素D、蛋白质补充剂及渐进性抗阻训练的效果,结果显示该联合方案显著改善了肌肉力量和身体功能,并提高了生活质量[96]。这提示补钙和维生素D作为基础营养支持,在与抗阻训练和激素替代等综合方案结合时,能更有效地改善骨骼肌肉健康。然而,证据强度需要辩证看待。大规模观察性研究指出,在老年男性中,较高的体力活动水平,特别是休闲性体育活动,与较低的骨质疏松发生风险独立相关,这种保护作用独立于遗传易感性[97]。这表明,生活方式干预,包括确保充足的钙和维生素D摄入以支持运动带来的骨骼负荷,是改善骨密度和降低非椎体骨折风险的综合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有证据支持其基础地位,但补钙和维生素D的干预效果可能因个体营养状况、基线水平及是否联合其他疗法而异。
在老年男性中实施补钙干预时,必须审慎考虑前列腺健康问题,特别是与抗雄激素药物治疗之间的潜在关联。许多老年男性因前列腺增生或前列腺癌需要接受抗雄激素治疗,这类药物会进一步降低体内雄激素水平,从而可能加剧骨量丢失和骨质疏松风险[93]。在这种情况下,补充钙剂和维生素D成为支持骨骼健康、预防治疗相关骨丢失的重要辅助手段。然而,临床决策需权衡利弊。一方面,确保足够的钙和维生素D营养状态有助于维持骨矿物质密度;另一方面,对于存在或高风险前列腺癌的患者,尤其是那些已发生骨转移者,不恰当的钙补充理论上可能带来风险,尽管此关联在骨质疏松预防的常规剂量下通常不是主要顾虑。更值得关注的是,老年男性常合并多种慢性疾病,其营养状况复杂。研究显示,老年男性2型糖尿病患者的骨质疏松风险与营养状况密切相关,较低的老年营养风险指数评分与较低的骨密度显著相关[98]。因此,在考虑补钙前,应对患者进行全面的营养评估,并监测血清钙水平,以避免高钙血症等潜在风险。总之,针对服用抗雄激素药物的老年男性,补钙应个体化,在评估前列腺疾病状态、总体营养及肾功能的基础上,作为综合骨骼健康管理方案的一部分来实施。6. 长期补钙的安全性争议与风险评估6.1 心血管事件风险:争议与最新共识
关于钙补充剂与心血管事件风险关联的争议,主要源于一些关键研究的发现。例如,对妇女健康倡议(WHI)钙剂研究的事后分析以及Bolland等人的荟萃分析提示,补充钙剂可能与心肌梗死风险的轻微增加有关[80]。这些分析指出,钙补充剂可能使心肌梗死的风险增加10-20%,而膳食钙摄入似乎并非心脏风险因素[80]。这种风险的潜在机制可能与摄入钙剂后引起的急性血钙浓度升高有关,这种升高可持续约8小时,并伴随血液凝固性和钙化倾向的急性增加,同时血压也可能比安慰剂组高出5 mmHg以上[80]。孟德尔随机化研究也表明,循环钙水平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风险因素,因此补充剂引起的急性血钙升高效应可能促进了心血管风险的增加[80]。此外,有研究指出,绝经后骨质疏松女性心血管疾病风险升高与使用钙补充剂有关[87]。这些发现引发了学界对钙补充剂安全性的广泛关注和重新评估。
然而,反对观点和后续研究对上述风险提出了质疑,并提供了更细致的解读。许多引发争议的研究并未明确区分膳食钙与补充钙的影响[80]。有观点认为,补充钙可能仅在特定情况下存在风险,例如单独使用(未与维生素D联用)或采用大剂量冲击疗法时[99]。一项关于钙、镁和锶心血管安全性的综述指出,尽管钙补充剂与胃肠道副作用和肾结石风险小幅增加有关,但其与心血管结局的所谓关联仍缺乏说服力;在正常生理状态下,尚未阐明其关联机制,且剂量反应和时间关系等其他考虑因素也不支持存在因果关系[99]。该综述总结认为,钙补充剂(用于骨骼健康)最适宜与维生素D补充剂联合使用,并针对这些营养素缺乏的人群,或与抗骨质疏松药物联用[99]。此外,一项针对终末期肾病透析患者的研究发现,使用钙基磷酸盐结合剂的患者,其骨质疏松性骨折风险降低,且与未使用者相比,并未增加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等风险[100]。这些证据表明,风险可能具有情境依赖性,而非普遍存在。
基于现有证据,当前主流学术组织采取了审慎而平衡的立场。美国国家骨质疏松基金会和欧洲骨质疏松和骨关节炎学会等机构普遍认为,在推荐剂量下,补钙对骨骼的益处大于其潜在的心血管风险[99]。这种立场强调了个体化治疗的重要性,即确保某些治疗(如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和钙补充)的益处大于潜在的健康风险,特别是绝经后女性的心血管事件风险[87]。对于骨质疏松的预防和治疗,尤其是在绝经后女性中,需要精心设计以预防和降低心血管事件风险[87]。尽管钙补充剂在预防社区居住成人骨折方面的效果受到质疑[80],且证据平衡提示其在骨质疏松防治中作用有限[80],但针对特定人群(如营养素缺乏者)或在特定方案(如联合维生素D或抗骨吸收药物)下,钙的补充仍被视为整体管理策略的一部分。因此,临床决策应基于全面的风险评估,权衡已知的骨骼获益与可能的心血管风险,并优先推荐通过膳食途径获取充足的钙。6.2 肾结石与高钙血症风险
补钙干预与肾结石风险之间的关系是复杂且双向的。一方面,补充钙剂会增加尿钙的排泄,这是形成含钙肾结石(主要是草酸钙结石)的重要风险因素[101]。尿钙排泄的增加直接提升了尿液中草酸钙过饱和的风险,从而可能促进结石的形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钙剂随餐服用时,其与食物中的草酸盐在肠道内结合,形成不溶性的草酸钙复合物并随粪便排出,这反而减少了肠道对草酸的吸收,从而降低了尿液中草酸的浓度[101]。这种机制意味着,对于预防草酸钙结石而言,随餐补充钙剂可能通过降低尿草酸而带来益处,部分抵消了因尿钙升高带来的风险。因此,补钙对肾结石风险的净效应高度依赖于补充的时机和个体的整体代谢状况。
对于存在特定风险因素的易感人群,如既往有肾结石病史或患有特发性高尿钙症的患者,在进行补钙时需要格外谨慎并实施严密监测。对这些个体而言,定期评估24小时尿钙排泄量是至关重要的监测指标,有助于判断钙补充是否导致了病理性高尿钙[101]。除了监测,积极的预防措施必不可少。保证充足的液体摄入以增加尿量、稀释尿液中成石物质的浓度,是预防所有类型肾结石的基石。同时,应避免使用高剂量的钙补充剂,因为剂量越高,导致高尿钙的风险也相应增加[101]。对于这些高危人群,补钙决策应基于对骨健康益处与结石风险增加的个体化权衡,并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高钙血症作为补钙的一种严重但相对罕见的不良反应,其发生通常并非单纯由膳食或常规剂量钙补充引起。临床上显著的高钙血症多见于钙剂过量补充、维生素D中毒或合并存在如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PHPT)或结节病等基础疾病的情况[102][103]。在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中,甲状旁腺激素(PTH)的不适当分泌导致骨钙动员和肾钙重吸收增加,是引起高钙血症的常见内分泌原因,其严重程度可以很高[103]。结节病患者则由于肉芽肿内巨噬细胞中1α-羟化酶活性增加,产生过多的活性维生素D(骨化三醇),进而促进肠道钙吸收,也可导致高钙血症和高尿钙[102]。高钙血症的早期症状可能非特异,但常包括胃肠道表现如恶心、便秘、厌食,以及因肾脏浓缩功能受损导致的烦渴、多尿等[104][101]。严重的高钙血症可影响神经精神系统,甚至引发如精神病性症状等严重表现,即使血钙水平仅为轻度升高时也可能发生[104]。因此,识别这些早期症状对于及时诊断和处理潜在的高钙血症至关重要。7. 补钙与其他抗骨质疏松药物的联合应用7.1 与骨吸收抑制剂(双膦酸盐、地舒单抗)的联用
钙和维生素D作为所有抗骨吸收药物基础治疗的必然性,源于这些药物在强力抑制破骨细胞活性的同时,必须为骨矿化提供充足的原料和吸收保障。双膦酸盐和地舒单抗等骨吸收抑制剂通过不同的机制有效抑制破骨细胞介导的骨吸收,例如双膦酸盐通过整合骨骼中的钙离子靶向骨组织并抑制破骨细胞功能[105],而地舒单抗则是一种靶向核因子κB受体活化因子配体(RANKL)的单克隆抗体[106]。然而,强力抑制骨吸收后,新骨的形成和矿化过程需要持续供应钙和磷。钙是骨骼矿物质的主要成分,而维生素D对于肠道钙的吸收至关重要,缺乏维生素D会导致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增加骨转换,从而削弱抗骨吸收药物的疗效[107]。因此,充足的钙和维生素D是确保抗骨吸收药物发挥最佳疗效、支持骨矿化、并预防因药物引起的低钙血症等不良反应的基石。临床指南普遍建议,在使用双膦酸盐或地舒单抗治疗骨质疏松症时,应同时补充钙剂和维生素D[108]。一项针对养老院居民的横断面研究显示,在双膦酸盐使用者中,仅约三分之一同时服用了维生素D和钙的联合补充剂,这突显了临床实践中对这一基础治疗原则的遵循仍需加强[109]。
临床研究数据明确显示,联用基础钙和维生素D补充剂能显著增强双膦酸盐或地舒单抗提升骨密度和降低骨折的疗效。一项关于糖尿病骨质疏松患者的荟萃分析表明,双膦酸盐治疗能显著提高患者的腰椎、股骨颈等部位的骨密度,并改善骨代谢标志物[110]。然而,这些疗效的取得通常以充足的钙和维生素D背景治疗为前提。对于地舒单抗,尽管有回顾性研究表明,在治疗两年期间,无论是否补充钙和维生素D,患者的骨密度均有相似程度的改善[111],但这并不能否定在治疗起始和整个过程中确保充足钙营养状态的重要性,尤其是考虑到地舒单抗有诱发低钙血症的风险。事实上,多项研究强调,对于肾功能不全等高风险患者,在使用地舒单抗时必须密切监测血钙水平并给予充足的钙和维生素D补充,以预防严重低钙血症的发生[89][112]。一项针对原发性骨质疏松患者的研究发现,尽管在补充钙和维生素D的基础上使用地舒单抗,治疗初期(3个月内)仍可能出现血钙下降和甲状旁腺激素水平升高,但随着治疗延长,这些指标可恢复至基线水平,这进一步说明了持续监测和补充的必要性[113]。此外,一项网络荟萃分析比较了不同骨保护干预措施对接受芳香化酶抑制剂治疗的乳腺癌患者骨密度的效果,发现所有活性干预措施(包括双膦酸盐和地舒单抗)在改善骨密度方面均显著优于单纯的钙加维生素D补充,这间接证实了在抗骨吸收治疗基础上,钙和维生素D作为辅助而非替代的关键角色[114]。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服用口服双膦酸盐时,钙剂需在不同时间服用(通常间隔至少30-60分钟),以避免在胃肠道中形成不溶性复合物而影响药物吸收。双膦酸盐分子结构中的P-C-P基团使其对钙离子具有高亲和力,能够与骨骼中的羟基磷灰石结合[105]。若与钙剂同时服用,双膦酸盐会在肠道内与钙离子结合,形成难以吸收的螯合物,从而大幅降低其生物利用度,减弱其抑制骨吸收的疗效。因此,临床用药指导明确建议,口服双膦酸盐(如阿仑膦酸钠、利塞膦酸钠等)应在清晨空腹以足量白水送服,并保持上身直立至少30分钟,在此期间避免进食、饮用其他饮料或服用其他药物,包括钙剂和抗酸药。钙剂和维生素D的补充应安排在全天其他时间,例如午餐或晚餐时。这一服药间隔对于确保双膦酸盐的有效吸收至关重要。相比之下,静脉注射的双膦酸盐(如唑来膦酸)和皮下注射的地舒单抗则不存在口服吸收的问题,但钙剂的补充时间安排仍应遵循常规建议,以维持稳定的血钙水平。不遵守服药间隔是导致口服双膦酸盐治疗失败或疗效不佳的常见原因之一。一项旨在通过针对性指导提高骨质疏松治疗依从性的研究发现,在教练指导下,口服双膦酸盐的12个月依从率可达77.3%[115],这提示患者教育在确保正确服药、包括错开钙剂服用时间方面的重要性。总之,钙和维生素D的补充是抗骨吸收药物治疗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具体的给药方案需根据药物剂型和患者具体情况个体化制定,以最大化疗效并最小化风险。7.2 与骨形成促进剂(特立帕肽、罗莫索单抗)的联用详细说明特立帕肽(PTH类似物)通过促进骨形成和增加肠道钙吸收来发挥作用,但仍强调保证充足钙摄入对优化其合成代谢效果的重要性。
特立帕肽作为甲状旁腺激素(PTH)的N端片段,是一种重要的骨合成代谢药物,其作用机制复杂且多效。它通过间歇性给药,能够直接刺激成骨细胞和骨细胞,从而显著促进骨形成[116]。这种刺激作用不仅体现在增加骨量上,还通过激活RANK/RANKL系统,在促进骨形成的同时也适度激活骨吸收,最终实现骨重建的净正平衡[116]。除了对骨骼的直接作用,特立帕肽在调节钙磷稳态中也扮演关键角色。它作用于肾脏,促进钙的重吸收,并刺激肾脏合成活性维生素D(1,25-二羟维生素D),后者能显著增强肠道对钙的吸收[116]。因此,特立帕肽通过“开源”——增加肠道钙吸收,与“节流”——减少肾脏钙排泄,共同提升血清钙水平,为骨骼的矿化提供充足的原料基础。然而,正是这种强大的骨形成刺激作用,使得机体对钙的需求急剧增加。如果钙和维生素D的摄入不足,新形成的骨基质将无法得到充分的矿化,从而削弱特立帕肽的合成代谢效果,甚至可能导致治疗失败[117]。临床实践和指南均强调,在启动特立帕肽治疗前及治疗期间,必须确保患者有充足的钙和维生素D摄入,这被认为是优化其疗效、实现骨折风险降低这一根本治疗目标的基石[117][118]。对于接受特立帕肽治疗的患者,每日钙摄入量通常建议维持在1000至1200毫克,维生素D摄入量建议为600至800国际单位,以支持其强大的成骨活性[118]。此外,研究也提示,蛋白质营养支持可能通过增强钙吸收等机制,对改善骨健康产生协同作用[119]。因此,将特立帕肽与充足的钙、维生素D及合理的营养支持相结合,是最大化其抗骨质疏松疗效、实现骨质量实质性改善的关键临床策略。分析罗莫索单抗(硬骨抑素单抗)的作用机制下,补充钙和维生素D对于预防其引起的低钙血症(尤其是治疗初期)的至关重要性,并引用相关黑框警告和临床管理建议。
罗莫索单抗是一种针对硬骨抑素(sclerostin)的单克隆抗体,通过双重作用机制发挥强效抗骨质疏松效果:一方面抑制硬骨抑素以解除其对Wnt/β-catenin信号通路的抑制,从而强力促进骨形成;另一方面,它也能适度降低骨吸收[120][121]。这种独特的“先促形成、后抑吸收”的序贯作用,使其在治疗初期能快速、显著地增加骨密度[122]。然而,正是这种强大的、快速的骨形成刺激,导致大量钙离子从血液循环中被迅速整合到新形成的骨基质中,从而在治疗初期(特别是前几剂后)显著增加了发生低钙血症的风险[121]。低钙血症可能引发感觉异常、肌肉痉挛、抽搐甚至更严重的不良事件。鉴于这一风险,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罗莫索单抗发出了黑框警告,明确指出在开始治疗前必须纠正已存在的低钙血症,并在整个治疗期间确保充足的钙和维生素D摄入,以预防治疗引起的低钙血症[121]。这一警告强调了钙和维生素D补充在罗莫索单抗治疗管理中的核心地位,不是辅助而是必需。临床管理建议通常要求,在启动罗莫索单抗治疗前,患者的25-羟维生素D水平应充足(通常建议>30 nmol/L),并应开始补充钙剂(每日1000-1200 mg)和维生素D(每日至少600-800 IU)[118][121]。一项前瞻性研究也观察到,在罗莫索单抗治疗期间联合使用活性维生素D类似物,相较于不联合使用组,能显著减小血清校正钙水平的下降幅度,这进一步证实了补充维生素D对于稳定血钙、支持治疗安全性的积极作用[123]。因此,对于所有考虑使用罗莫索单抗的患者,临床医生必须严格评估其基线钙和维生素D状态,并进行充分的补充教育。将罗莫索单抗与足量的钙和维生素D联用,是确保这一强效骨形成促进剂能够安全、有效地发挥其降低骨折风险作用的前提,任何对基础补充的忽视都可能使患者暴露于不必要的风险之中。8. 膳食钙源与补充剂的比较及综合摄入策略8.1 高生物利用度膳食钙源评估
膳食钙的生物利用度是决定其营养效能的关键因素,不同食物来源的钙含量和吸收率存在显著差异。乳制品,如牛奶、酸奶和奶酪,因其高钙含量和良好的吸收率(约30%)而被广泛认为是优质的钙源[124]。研究表明,牛奶来源的钙具有更高的生物利用度和吸收率,优于其他合成或天然矿物来源的钙[124]。然而,某些蔬菜也提供了生物可利用的钙。例如,仙人掌(Opuntia ficus-indica)的嫩茎可溶性纤维中的钙具有良好的生物利用度,在动物模型中显示出改善骨骼特性的潜力[125]。同样,从仙人掌嫩茎中提取的可溶性纤维也被证明是幼年大鼠体内生物可利用钙的宝贵来源,有助于改善骨骼的物理、密度、生物力学和微结构特性[126]。相比之下,菠菜等富含草酸的蔬菜,其钙的吸收率则因草酸与钙结合形成不溶性盐而显著降低[68]。一项针对美国成年人的系列横断面分析显示,膳食中草酸盐摄入量的增加与钙吸收减少和不利的骨骼健康结果相关[68]。此外,植物性食物中的植酸也是影响钙生物利用度的重要因素。例如,在Terminalia ferdinandiana植物组织中,植酸含量与钙含量呈显著正相关,但其对钙生物利用度的具体影响尚需进一步研究[127]。在莫桑比克儿童中的研究发现,膳食中植酸与钙的摩尔比普遍超过推荐值,表明植酸可能抑制钙的吸收[128]。因此,评估膳食钙源时,必须综合考虑食物的钙含量、吸收率以及其中存在的抑制因子(如草酸和植酸)的综合影响。
强化钙食品在增加特定人群膳食钙摄入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乳制品摄入不足或存在饮食限制的人群,钙强化果汁、豆奶和谷物等产品是有效的补充途径。研究表明,强化食品中的钙盐形式会影响其生物利用度。例如,在动物模型中,与矿物钙盐相比,以乳制品基质形式提供的钙在对抗肉类消费引起的结肠有害副作用方面表现出更好的预防效果[129]。这提示了食物基质本身对钙生物利用度的积极影响。此外,天然富钙矿泉水也被认为是一种生物可利用的膳食钙来源,尤其适用于乳糖不耐受或坚持植物性饮食的人群[130]。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饮用水常被忽视作为钙的来源,但计算表明,考虑饮用水中的钙可以平均每人每天增加49毫克的钙供应量,是改善钙摄入的一个潜在策略[131]。除了直接强化,通过食品加工技术也能提升钙的生物利用度。例如,从发酵豆酸奶中分离出的特定肽段(如DEDEQIPSHPPR)能与钙离子螯合,在胃肠道中保持稳定,并在斑马鱼骨质疏松模型中增加骨量,显示出作为钙载体的潜力[51]。同样,通过高能球磨技术将鱼骨加工成纳米颗粒,可以保留其高钙磷比和矿物质成分,成为一种有前景的天然补钙剂[132]。这些创新方法为开发高生物利用度的功能性钙强化食品提供了新思路。
针对不同饮食习惯的人群,优化食物选择是满足钙需求的关键。对于乳糖不耐受者,除了选择无乳糖乳制品外,还可以转向其他高生物利用度的钙源。研究表明,发酵乳制品如益生菌羊奶冰淇淋,其中的钙生物利用度可达40.63%至54.40%,并且添加的益生菌对钙、镁、磷的生物利用度有积极影响[133]。此外,天然富钙矿泉水、强化钙的植物奶(如豆奶)以及某些低草酸含量的蔬菜(如西兰花、甘蓝)都是良好的替代选择。对于素食者,尤其是严格素食者,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植物性食物中植酸和草酸对钙吸收的抑制。因此,需要通过食物搭配和加工方法来提高钙的生物利用度。例如,阿育吠陀中提到的使用酪乳(Buttermilk)作为佐剂,可以显著提高绿豆中钙、铁和锌的生物可及性与生物利用度[134]。这为改善植物性饮食中的矿物质吸收提供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学结合的依据。此外,选择特定植物部位也很重要,如仙人掌嫩茎的可溶性纤维是生物可利用钙的良好来源[125]。对于普通人群,确保膳食中包含生物可利用钙高的食物,如乳制品,与降低非传染性疾病风险相关[124]。在制定最低成本且营养充足的膳食模式时,考虑到营养素的生物可利用单位后,动物源性食物(包括牛肉)因其能提供生物可利用的蛋白质、维生素B12、钙、磷、硒和锌而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35]。综上所述,通过了解各类食物的钙生物利用度特性,并结合个体的饮食习惯进行个性化选择,是有效预防钙缺乏和促进骨骼健康的核心策略。8.2 “食物优先”原则与补充剂的合理定位
在骨质疏松症的防治策略中,“食物优先”原则是获取钙质的基石。通过膳食途径摄入钙不仅能够满足机体对钙的基本需求,还能同时获取一系列对骨骼健康至关重要的协同营养素,如蛋白质、磷、镁和维生素K等,从而形成更为全面和自然的骨骼保护网络[136]。例如,乳制品作为主要的膳食钙来源,通常也富含蛋白质和磷,这些营养素共同参与骨骼基质的构建与矿化[137]。此外,植物性食物来源的钙,如绿叶蔬菜和豆类,往往伴随着镁和维生素K的摄入,镁是骨矿物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维生素K则参与骨钙素的羧化,对维持骨强度至关重要[138]。从安全性角度看,通过食物获取钙通常剂量适中,且生物利用度在食物基质中与其他成分相互作用下可能更佳,避免了单一高剂量补充剂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如胃肠道不适或与其他营养素吸收的相互干扰[139]。一项针对意大利女性的研究也发现,无论是否患有骨质疏松症,其膳食钙的来源构成(主要为乳制品)并无显著差异,这强调了均衡膳食作为基础干预的普适性[137]。因此,优先通过多样化、均衡的膳食来满足钙需求,是实现骨骼长期健康最安全、最有效的策略。
尽管膳食是首选,但在特定临床情况下,钙补充剂的应用具有明确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补充剂的适用情况主要涵盖以下几类:首先,当膳食无法满足每日钙需求时,例如老年人因食欲普遍下降、咀嚼困难或乳制品摄入不足(如乳糖不耐受或饮食偏好)而导致钙摄入量持续低于推荐水平[140][141]。研究表明,在许多地区,老年人群和女性的膳食钙摄入量长期低于推荐值,仅达到推荐水平的40-80%[142]。其次,存在影响钙吸收的病理状态时,如胃肠道吸收障碍、慢性肾脏疾病或某些药物(如质子泵抑制剂)的长期使用,此时补充剂有助于确保足量的钙被机体利用[143]。再者,在骨质疏松的疾病治疗过程中,为确保抗骨吸收药物或促骨形成药物发挥最佳疗效,通常需要确保每日钙摄入量达到治疗阈值(如1200毫克)[144]。例如,对于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患者,钙和维生素D的补充是预防继发性骨质疏松的核心措施之一[9]。此外,对于存在食物不安全或贫困状况的人群,膳食来源的钙获取受限,补充剂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干预手段[15]。明确这些适用情况有助于避免补充剂的滥用,并将其精准应用于最需要的人群。
为实现从“食物优先”到“必要补充”的无缝衔接,建立一套从膳食评估到补充剂选择的标准化临床实践路径至关重要。该路径的第一步是系统性的膳食钙摄入评估。临床中可使用经过验证的简短食物频率问卷(钙筛查工具)快速评估患者的日常钙摄入量,这类工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和临床可行性,能有效识别出摄入不足(如低于1200毫克/天)的个体[144]。评估时应涵盖所有膳食来源,特别是乳制品、强化食品、深绿色蔬菜等,并注意不同文化背景下主要钙来源的差异,例如在亚洲部分地区,植物性食物是膳食钙的主要贡献者[142]。第二步是基于评估结果进行分层管理。对于膳食摄入充足者,应给予强化和鼓励,并教育其维持均衡饮食,特别是保证富含钙、蛋白质及其他骨骼营养素的食物的摄入[145]。对于摄入不足者,则进入第三步:个体化干预。首先尝试通过膳食咨询与教育来改善饮食,例如增加低脂乳制品、钙强化食品或特定蔬菜的摄入,并提供具体的、符合患者饮食习惯的建议[146]。若通过膳食调整仍无法达到目标摄入量,或患者存在前述的适用情况(如吸收障碍、治疗需要等),则进入第四步:补充剂的选择与使用。选择补充剂时需考虑剂型(如碳酸钙、柠檬酸钙)、元素钙含量、服用时间(随餐或空腹)以及与其它药物(如双膦酸盐)或食物的相互作用[147]。例如,碳酸钙需随餐服用以利吸收,而柠檬酸钙则在空腹状态下吸收更好,且对胃酸缺乏者更适宜。最后,路径应包含第五步:监测与随访。定期复查患者的钙摄入情况(包括膳食和补充剂)、血清钙水平、维生素D状态以及肾功能,并根据情况调整方案,确保治疗的有效性与安全性,预防高钙血症或肾结石等潜在风险[50]。这套结构化路径有助于临床医生做出循证、个体化的决策,优化骨质疏松症患者的钙营养管理。9. 未来研究方向与个性化补钙展望9.1 钙代谢的遗传学与个体反应差异
钙代谢的稳态受到复杂遗传网络的精密调控,个体间对钙摄入的骨密度反应和尿钙排泄存在显著差异,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关键基因的多态性。维生素D受体(VDR)基因和钙敏感受体(CaSR)基因的变异是影响钙稳态和骨代谢的核心遗传因素。VDR作为核受体,介导了维生素D的绝大部分生物学效应,包括调节肠道钙吸收和骨矿化。研究表明,VDR基因的多态性(如FokI、BsmI、ApaI和TaqI)与血清维生素D水平、骨密度(BMD)以及骨质疏松风险密切相关[148]。例如,在系统性硬化症患者中,VDR FokI基因型的纯合子与较低的轴性骨密度显著相关[149]。同样,在阿拉伯绝经后妇女中,PTHR1(甲状旁腺激素1型受体,与钙信号传导密切相关)的rs1138518多态性是骨质疏松的潜在风险因素,并与25-羟基维生素D的调节有关[150]。另一方面,CaSR基因多态性在调节尿钙排泄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CaSR通过感知细胞外钙离子浓度来调节甲状旁腺激素(PTH)的分泌和肾小管对钙的重吸收。多项研究证实,特定的CaSR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如rs1801725(A986S)和rs1042636,与高尿钙症和肾结石病的风险增加显著相关[151][152]。在终末期肾病(ESRD)患者中,CaSR基因的变异(如rs10190)被发现与血清磷酸盐和I型前胶原α1水平的变化相关,表明其影响钙磷代谢的生物标志物[153]。这些遗传变异通过改变受体功能或表达水平,导致个体在相同钙摄入下出现不同的骨密度增益或尿钙流失,构成了补钙干预反应差异的分子基础。
“营养基因组学”在骨质疏松领域的应用前景广阔,其核心在于通过基因检测来指导个性化的钙和维生素D补充方案。随着对钙代谢相关基因(如VDR、CaSR、CYP24A1、CYP27B1等)多态性功能的深入理解,实现基于遗传背景的精准营养干预成为可能。例如,携带特定VDR基因型(如FokI ff基因型)的个体,其维生素D代谢和钙吸收效率可能不同,因此所需的维生素D补充剂量也应个体化[154]。一项针对韩国成年人的研究显示,苦味受体基因TAS2R38的遗传变异(rs10246939)与女性膳食钙、磷等微量营养素的摄入量相关,提示遗传因素可能通过影响食物偏好间接调控钙的摄入[155]。在慢性肾病(CKD)人群中,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已识别出与矿物质代谢标志物(如磷酸盐、钙、FGF23)相关的遗传位点,例如RGS14和CASR基因附近的SNPs[156]。这些发现为开发针对CKD患者骨矿物质紊乱的个体化治疗策略提供了遗传学依据。未来,通过整合个体的基因型信息(如VDR、CaSR的多态性)、代谢表型(如血钙、尿钙、PTH水平)及临床状况,可以构建预测模型,以确定最有效的钙和维生素D补充剂量与形式,从而最大化骨骼获益并最小化高钙血症或肾结石等不良反应风险[157]。这种基于营养基因组学的精准干预策略,有望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一刀切”的补充建议,提升骨质疏松症预防和管理的效率与安全性。
肠道菌群作为影响钙吸收和骨代谢的新兴因素,其作为干预靶点的潜力日益受到关注。肠道微生物通过多种机制参与宿主的钙稳态调节。首先,某些益生菌(如乳酸杆菌属)可以发酵膳食纤维产生短链脂肪酸(SCFAs),降低肠道pH值,从而增加钙的可溶性和被动扩散吸收[158]。其次,肠道菌群能影响肠上皮屏障功能和紧密连接蛋白(如claudin-1, occludin)的表达,调节钙的跨细胞转运。一项对蛋鸡的研究发现,空肠中乳酸杆菌的高丰度与总蛋壳重量(反映钙代谢强度)呈负相关,其机制可能是通过上调肠上皮紧密连接蛋白来抑制钙的吸收[159]。此外,肠道菌群参与维生素K和B族维生素的合成,这些维生素对骨基质蛋白(如骨钙素)的羧化至关重要,从而影响骨矿化[160]。菌群失调可能引发慢性低度炎症,促进促炎细胞因子(如TNF-α, IL-6)的释放,这些因子可刺激破骨细胞生成并抑制成骨细胞活性,导致骨丢失[161]。因此,通过益生菌、益生元或膳食干预调控肠道菌群组成,成为改善钙吸收和骨骼健康的新策略。例如,补充特定的益生菌株可能增强钙的生物利用度,并产生有益代谢物以抗炎和维持肠道屏障完整性,从而对骨密度产生积极影响[158]。然而,宿主遗传与肠道菌群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微生物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mb-GWAS)已发现宿主基因组变异与特定肠道菌属丰度之间的关联,表明遗传背景可能塑造了个体独特的肠道微生态,进而影响其对钙干预的反应[159]。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阐明“基因-菌群-骨骼”轴的具体机制,并探索靶向肠道菌群的个性化营养或微生物疗法,为骨质疏松的防治开辟新途径。9.2 新型钙基复合制剂与智能递送系统
在骨质疏松症的干预策略中,新型钙基复合制剂与智能递送系统的研发正成为提升钙补充效率和靶向性的关键方向。一方面,研究者致力于开发能够同时改善骨基质有机成分和促进钙吸收的复合制剂。例如,基于β-磷酸三钙(β-TCP)和硫酸钙的复合骨水泥材料,通过引入聚乙烯醇(PVA)和聚乙烯吡咯烷酮(PVP)等聚合物成分,不仅调控了材料的溶解度和钙离子释放动力学,还展现出良好的细胞相容性,为骨再生提供了新的材料选择[162]。此外,将钙与生物活性分子结合的尝试也在进行中,如利用南极磷虾来源的七肽(QEELISK)组装钙递送系统,该肽段通过其连续的谷氨酸残基与钙离子以1:1的化学计量比结合,形成的复合物在胃肠道消化过程中表现出独特的解聚和自组装行为,并能在十二指肠和回肠显著增强钙的吸收,提示其具有作为口服钙载体的潜力[163]。另一项研究则探索了脱盐鸭蛋清肽与壳寡糖通过阿马多里型连接或转谷氨酰胺酶反应形成的共聚物作为钙递送系统,其在细胞和动物模型中均显示出能够逆转植酸对钙转运的抑制作用,促进钙的生物利用度并改善肠道健康[164]。这些复合制剂的设计超越了单纯的钙盐补充,旨在通过多组分协同作用优化骨代谢的微环境。
另一方面,基于生物材料的缓控释及响应型靶向递送系统为实现肠道高效吸收并减少不良反应提供了创新思路。钙磷酸盐(CaP)纳米颗粒因其良好的生物相容性、骨诱导性和与核酸的高亲和力,被广泛研究作为骨组织工程中的非病毒基因递送载体[165]。为了提高其转染效率,表面功能化修饰被证明可以增强纳米颗粒的稳定性、细胞摄取和递送效率[165]。在药物递送领域,研究者开发了多种智能系统。例如,一种基于无定形碳酸钙(ACC)并包覆谷氨酸六肽修饰磷脂的纳米颗粒(OAPLG),能够响应破骨细胞微环境的酸性条件,瞬时中和酸并释放负载的药物(如Oroxylin A),从而协同抑制破骨细胞的形成与活性,在动物模型中有效逆转系统性骨丢失[166]。此外,pH响应型的壳聚糖-铜(II)/钙磷酸盐微球被开发用于骨癌的靶向治疗,该体系在酸性微环境中(如肿瘤部位)能增强阿霉素的释放,实现局部药物浓度的精准调控[167]。对于抗生素的局部递送,将蒙脱石-庆大霉素复合物作为药物释放通道整合到磷酸钙骨水泥中,可以避免药物的突释,实现长达504小时的缓释周期,其释放动力学符合多阶段模型,并具有良好的体外长效抗菌性能和体内组织相容性[168]。这些系统通过响应生理或病理信号(如pH值),实现了钙或治疗药物在特定部位(如骨缺损处或肿瘤微环境)的按需释放,提高了治疗的靶向性和安全性。
展望未来,将钙补充与数字化健康管理工具相结合,实现摄入监测、提醒和效果反馈的闭环管理,是提升患者依从性和干预效果的重要趋势。虽然当前提供的参考文献主要集中于材料科学与递送系统本身,但其中蕴含的“智能化”和“可控释放”理念为数字化管理奠定了基础。例如,基于电纺纳米纤维技术制备的快速溶解纳米纤维膜,可作为口腔黏膜给药系统,用于尼非地平和阿托伐他汀钙的联合递送,其崩解时间短(≤12秒),能促进药物快速释放和渗透,这种剂型革新为开发便于患者使用、并能通过可穿戴设备监测摄入的剂型提供了思路[169]。更进一步的智能系统,如一种钙响应性的模块化磷脂酶系统,被设计用于增强DNA递送过程中的内体逃逸,该系统通过非共价捕获并在内体酸性环境中释放磷脂酶,实现了在血清环境中高效转染[170]。这提示,未来的钙补充策略可能整合类似的生物传感与反馈机制。例如,可开发集成生物传感器的口服钙制剂或贴片,实时监测血钙波动或骨转换标志物,并通过移动应用提醒患者服药、提供个性化剂量调整建议,甚至与临床数据库联动,为医生调整治疗方案提供动态数据支持。通过融合材料科学、药剂学与数字健康技术,构建从精准递送到智能管理的全链条干预体系,将是骨质疏松症补钙策略发展的前沿方向。结论
从现有证据来看,补钙作为骨质疏松症防治的基石,其价值已得到广泛认可,但其临床效益的实现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维生素D水平、补充策略及个体状况紧密交织。充足的钙与维生素D联合干预,对于改善骨密度、降低特定高危人群(如膳食摄入不足的老年及绝经后女性)的骨折风险具有明确意义。然而,这并非一个“一刀切”的方案。长期补钙,尤其是高剂量补充,与潜在心血管风险之间的关联,提示我们需要在临床决策中审慎权衡获益与风险。当前共识认为,在推荐剂量范围内,补钙的总体获益风险比是积极的,但关键在于避免盲目和过量的补充,这凸显了“个性化”原则的核心地位。
在临床实践中,应始终坚持“膳食优先”的基本原则,将营养评估作为首要步骤。对于确需补充剂干预的个体,制定方案时必须综合考虑其年龄、性别、基础膳食摄入、维生素D状态、肾功能以及合并用药(特别是抗骨质疏松药物)情况,以实现协同增效,并最大限度规避潜在风险。补钙不应被视为孤立的治疗手段,而是整合性骨质疏松症管理体系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展望未来,研究需向更深层次和更精准的方向迈进。首要任务是阐明个体对钙剂反应存在显著差异的生物学机制,这涉及遗传背景、肠道吸收效率、激素调节网络等多方面因素。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开发新型钙剂或复合制剂,以提高生物利用度、减少不良反应,并探索更优化的补充时机与剂量策略。最终目标是将基于循证医学和精准医学理念的补钙策略,无缝嵌入到涵盖生活方式干预、药物疗法及跌倒预防在内的全面骨质疏松症防控网络中,从而为患者带来更安全、更有效的长期健康收益。参考文献
[1] Cha YH, Ha YC, Lim JY, Kim WS. Introduction of the Cost-Effectiveness Studies of Fracture Liaison Service in Other Countries. J Bone Metab. 2020;27(2):79-83. doi:10.11005/jbm.2020.27.2.7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572368/
[2] Chevalley T, Cruz-Tochon A, Portela M, Padlina I, Brulhart-Citozi D, Ferrari S.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Fracture Liaison Service in Switzerland]. Rev Med Suisse. 2021;17(735):780-78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881240/
[3] Hurtado Y, Hernández OA, De Leon DPA, Duque G. Challenges in Delivering Effective Care for Older Persons with Fragility Fractures. Clin Interv Aging. 19:133-140. Published 2024 None. doi:10.2147/CIA.S43399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283764/
[4] Rinonapoli G, Ruggiero C, Meccariello L, Bisaccia M, Ceccarini P, Caraffa A. Osteoporosis in Men: A Review of an Underestimated Bone Condition. Int J Mol Sci. 2021;22(4). Published 2021 Feb 20. doi:10.3390/ijms2204210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672656/
[5] Chou SH. Osteoporosis in Men: an Overlooked Patient Population. Curr Osteoporos Rep.2025;23(1):13. Published 2025 Mar 7. doi:10.1007/s11914-025-00907-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053208/
[6] Kim HJ, Lim JS, Kim O. Osteoporosis and fracture incidence and risk factors among individuals with traumatic spinal cord injury: A nationwide cohort study in Korea. J Spinal Cord Med. :1-8. Published online Feb 19,2026. doi:10.1080/10790268.2025.261165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1712329/
[7] Lim WH, Ng CH, Ow ZGW, et al.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n the incidence of osteoporosis and fractures after liver transplant. Transpl Int. 2021;34(6):1032-1043. doi:10.1111/tri.1386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835638/
[8] Liu Y, Ma X, Dai T, et al.Prevalence and relative risk of fractures and osteoporosis in patients with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steoporos Int. . Published online Jan 23,2026. doi:10.1007/s00198-025-07838-x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1575558/
[9] Gazitt T, Feld J, Zisman D. Implementation of Calcium and Vitamin D Supplementation in Glucocorticosteroid-Induced Osteoporosis Prevention Guidelines-Insights from Rheumatologists. Rambam Maimonides Med J. 2023;14(2). Published 2023 Apr 30. doi:10.5041/RMMJ.1049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116065/
[10] Chevalley T, Rizzoli R. Acquisition of peak bone mass. Best Pract Res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22;36(2):101616. doi:10.1016/j.beem.2022.10161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125324/
[11] Zhu X, Zheng H. Factors influencing peak bone mass gain. Front Med. 2021;15(1):53-69. doi:10.1007/s11684-020-0748-y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519297/
[12] Yadav S, Porwal K, Sinha RA, Chattopadhyay N, Gupta SK. Moderate/subclinical calcium deficiency attenuates trabecular mass, microarchitecture and bone growth in growing rats. Biochem Biophys Rep.26:101033. Published 2021 Jul. doi:10.1016/j.bbrep.2021.10103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124397/
[13] Rodd C, Kirouac N, Orkin J, Grimes R. Evaluating and optimizing bone health in children with chronic health conditions. Paediatr Child Health. 2022;27(4):232-242. Published 2022 Jul.doi:10.1093/pch/pxac03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859678/
[14] Schemes MB, Martini G, Strey B, Guerini C, Pinto R, Schneider C. Dietary intake, body composition, and muscle function in resistance-untrained strict vegetarian and non-vegetarian women: an exploratory cross-sectional study. Appl Physiol Nutr Metab. 50:1-8. doi:10.1139/apnm-2025-009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882222/
[15] Marshall K, Teo L, Shanahan C, Legette L, Mitmesser SH. Inadequate calcium and vitamin D intake and osteoporosis risk in older Americans living in poverty with food insecurities. PLoS One. 2020;15(7):e0235042. Published 2020 None. doi:10.1371/journal.pone.023504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639966/
[16] Chen J, Liu J, Xu M, Fu Q, Si H. Calcium carbonate supplementation exacerbated gut microenvironment disruption in senile osteoporosis mice. iScience. 2026;29(1):114530. Published 2026 Jan 16. doi:10.1016/j.isci.2025.11453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1550734/
[17] Kim KJ, Kim MS, Hong N, et al.Cardiovascular risks associated with calcium supplementation in patients with osteoporosis: a nationwide cohort study. Eur Heart J Cardiovasc Pharmacother. 2022;8(6):568-577. doi:10.1093/ehjcvp/pvab05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244740/
[18] Myung SK, Kim HB, Lee YJ, Choi YJ, Oh SW. Calcium Supplements and Risk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 Meta-Analysis of Clinical Trials. Nutrients. 2021;13(2). Published 2021 Jan 26. doi:10.3390/nu1302036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530332/
[19] Migliorini F, Maffulli N, Colarossi G, Filippelli A, Memminger M, Conti V. Vitamin D and calcium supplementation in women undergoing pharmacological management for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a level I of evidence systematic review. Eur J Med Res. 2025;30(1):170. Published 2025 Mar 14. doi:10.1186/s40001-025-02412-x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087804/
[20] Khatri K, Kaur M, Dhir T, Kankaria A, Arora H. Role of calcium &/or vitamin D supplementation in preventing osteoporotic fracture in the elderly: A systematic review & meta-analysis. Indian J Med Res. 2023;158(1):5-16. doi:10.4103/ijmr.ijmr_1946_2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602580/
[21] Gureev SA, Mingazova EN. [On the ques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calcium preparations for the purpose of optimizing the diets of the population, including and for different diseases]. Vopr Pitan. 2021;90(2):6-14. doi:10.33029/0042-8833-2021-90-2-6-1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019344/
[22] Oono F, Sakamoto Y, Tachi Y, Mabashi-Asazuma H, Iida K. Effect of Cdx2 Polymorphism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etary Calcium Intake and Peak Bone Mass in Young Japanese Women. Nutrients. 2020;12(1). Published 2020 Jan 10. doi:10.3390/nu1201019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284510/
[23] Rizzoli R, Biver E. Are Probiotics the New Calcium and Vitamin D for Bone Health? Curr Osteoporos Rep.2020;18(3):273-284. doi:10.1007/s11914-020-00591-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285249/
[24] Palacios C, Trak-Fellermeier MA, Pérez CM, et al.Effect of soluble corn fiber supplementation for 1 year on bone metabolism in children, the MetA-bone trial: Rationale and design. Contemp Clin Trials. 95:106061. doi:10.1016/j.cct.2020.10606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574844/
[25] Wang J, Tao S, Jin X, et al.Calcium Supplement by Tetracycline guided amorphous Calcium Carbonate potentiates Osteoblast promotion for Synergetic Osteoporosis Therapy. Theranostics. 2020;10(19):8591-8605. Published 2020 None. doi:10.7150/thno.4514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754265/
[26] Tao S, Yu F, Song Y, et al.Water/pH dual responsive in situ calcium supplement collaborates simvastatin for osteoblast promotion mediated osteoporosis therapy via oral medication. J Control Release. 329:121-135. doi:10.1016/j.jconrel.2020.11.05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279604/
[27] Roumpou A, Palermo A, Tournis S, et al.Bone in Parathyroid Diseases Revisited: Evidence From Epidemiological, Surgical and New Drug Outcomes. Endocr Rev. 2025;46(4):576-620. doi:10.1210/endrev/bnaf01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177730/
[28] Sivagurunathan U, Izquierdo M, Tseng Y, et al.Effect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etary Vitamin D3 and Vitamin K3 on Growth, Skeletal Anomalies, and Expression of Bone and Calcium Metabolism-Related Genes in Juvenile Gilthead Seabream (Sparus aurata). Animals (Basel). 2024;14(19). Published 2024 Sep 28. doi:10.3390/ani1419280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409757/
[29] El-Farrash RA, Ali RH, Barakat NM. Post-natal bone physiology. Semin Fetal Neonatal Med. 2020;25(1):101077. doi:10.1016/j.siny.2019.10107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1889637/
[30] Cho H, Lee J, Jang S, et al.CaSR-Mediated hBMSCs Activity Modulation: Additional Coupling Mechanism in Bone Remodeling Compartment. Int J Mol Sci. 2020;22(1). Published 2020 Dec 30. doi:10.3390/ijms2201032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396907/
[31] Hansen MS. Measuring Calcium Levels in Bone-Resorbing Osteoclasts and Bone-Forming Osteoblasts. Methods Mol Biol. 2861:167-186. doi:10.1007/978-1-0716-4164-4_1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395105/
[32] Li C, Sun J, Ling H, et al.MCU regulating bone remodeling and osteogenic function through mitochondrial calcium homeostasis and oxidative stress alteration. Free Radic Biol Med. 236:87-97. doi:10.1016/j.freeradbiomed.2025.05.00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389181/
[33] Stadt MM, Layton AT. Mathematical modeling of calcium homeostasis in female rats: An analysis of sex differences and maternal adaptations. J Theor Biol. 572:111583. doi:10.1016/j.jtbi.2023.11158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516344/
[34] Maciel GBM, Maciel RM, Danesi CC. Bone cells and their role in physiological remodeling. Mol Biol Rep.2023;50(3):2857-2863. doi:10.1007/s11033-022-08190-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609750/
[35] Ciosek Ż, Kot K, Kosik-Bogacka D, Łanocha-Arendarczyk N, Rotter I. The Effects of Calcium, Magnesium, Phosphorus, Fluoride, and Lead on Bone Tissue. Biomolecules. 2021;11(4). Published 2021 Mar 28. doi:10.3390/biom1104050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800689/
[36] Tański W, Kosiorowska J, Szymańska-Chabowska A. Osteoporosis - risk factors, pharmaceutical and non-pharmaceutical treatment. Eur Rev Med Pharmacol Sci. 2021;25(9):3557-3566. doi:10.26355/eurrev_202105_2583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002830/
[37] Vasikaran SD, Makris K, Bhattoa HP, et al.The importance of laboratory medicine in the management of CKD-MBD: insights from the KDIGO 2023 controversies conference. Clin Chem Lab Med. 2025;63(12):2371-2376. Published 2025 Nov 25. doi:10.1515/cclm-2025-080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817567/
[38] Hu G, Sun X, Hao S, et al.Effect of sheep bone protein hydrolysate on promoting calcium absorption and enhancing bone quality in low-calcium diet fed rats. Food Chem. 446:138763. doi:10.1016/j.foodchem.2024.13876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428077/
[39] Bandyopadhyay K, Ray S, Shikha D, Bhalla GS, Khetan A. Risk factors of osteoporosis in soldiers of the Armed Force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from Western India. Med J Armed Forces India. 2023 Mar-Apr;79(2):194-200. doi:10.1016/j.mjafi.2021.04.00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969126/
[40] Voulgaridou G, Papadopoulou SK, Detopoulou P, et al.Vitamin D and Calcium in Osteoporosis, and the Role of Bone Turnover Markers: A Narrative Review of Recent Data from RCTs. Diseases. 2023;11(1). Published 2023 Feb 8. doi:10.3390/diseases1101002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810543/
[41] Jia M, Luo J, Gao B, et al.Preparation of synbiotic milk powder and its effect on calcium absorption and the bone microstructure in calcium deficient mice. Food Funct. 2023;14(7):3092-3106. Published 2023 Apr 3. doi:10.1039/d2fo04092a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919678/
[42] Akinwumi FE, Akinyemi AO, Akangbe B, et al.Risk of Osteoporosis and Anemia in Plant-Based Diet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Nutritional Deficiencies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Cureus. 2025;17(7):e88461. Published 2025 Jul. doi:10.7759/cureus.8846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842789/
[43] Ratajczak AE, Rychter AM, Zawada A, Dobrowolska A, Krela-Kaźmierczak I. Lactose intolerance in patients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 and dietary management in prevention of osteoporosis. Nutrition. 82:111043. doi:10.1016/j.nut.2020.11104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316755/
[44] Wiria M, Tran HM, Nguyen PHB, Valencia O, Dutta S, Pouteau E. Relative bioavailability and pharmacokinetic comparison of calcium glucoheptonate with calcium carbonate. Pharmacol Res Perspect. 2020;8(2):e00589. doi:10.1002/prp2.58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302064/
[45] Sheth B, Akil Prabhakar S, Pawar P, Ganwir H, Panchal S, Jain A. Calcium prescription by Indian orthopaedic surgeons: A survey and a review of literature. J Clin Orthop Trauma. 16:292-298. Published 2021 May. doi:10.1016/j.jcot.2021.02.01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747782/
[46] Rondanelli M, Minisola S, Barale M, et al.Evaluating adherence, tolerability and safety of oral calcium citrate in elderly osteopenic subjects: a real-life non-interventional, prospective, multicenter study. Aging Clin Exp Res. 2024;36(1):38. Published 2024 Feb 12. doi:10.1007/s40520-024-02696-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345765/
[47] Yu L, Li X, He M, et al.Antioxidant Carboxymethyl Chitosan Carbon Dots with Calcium Doping Achieve Ultra-Low Calcium Concentration for Iron-Induced Osteoporosis Treatment by Effectively Enhancing Calcium Bioavailability in Zebrafish. Antioxidants (Basel). 2023;12(3). Published 2023 Feb 26. doi:10.3390/antiox1203058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978831/
[48] Wu W, Zheng W, Pan W, Chen F, Jiang L. Reducing Re-fractures Post Percutaneous Kyphoplasty: The Impact of Zoledronic Acid with Calcium and Vitamin D3 in Osteoporotic Patients. Altern Ther Health Med. 2024;30(12):340-34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518159/
[49] Zhang Y, Tian Y, Chen X.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zoledronic acid combined with calcium and calcitriol in the treatment of senile osteoporosis in elderly patients. Inflammopharmacology. 2025;33(4):1899-1905. doi:10.1007/s10787-025-01683-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042722/
[50] Shi L, Bao Y, Deng X, Xu X, Hu J. Association between calcium and vitamin D supplementation and increased risk of kidney stone formation in patients with osteoporosis in Southwest Chin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BMJ Open. 2025;15(2):e092901. Published 2025 Feb 16. doi:10.1136/bmjopen-2024-09290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956606/
[51] Gan J, Xiao Z, Wang K, et al.Isola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molecular docking analyses of novel calcium-chelating peptide from soy yogurt and the study of its calcium chelation mechanism. J Sci Food Agric. 2023;103(6):2939-2948. doi:10.1002/jsfa.1237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460619/
[52] Ilesanmi-Oyelere BL, Kruger MC. The Role of Milk Components, Pro-, Pre-, and Synbiotic Foods in Calcium Absorption and Bone Health Maintenance. Front Nutr. 7:578702. Published 2020 None. doi:10.3389/fnut.2020.57870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072800/
[53] Fladerer JP, Grollitsch S. Eggshell membrane as promising supplement to maintain bone health: A systematic review. Bone Rep.21:101776. Published 2024 Jun. doi:10.1016/j.bonr.2024.10177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872992/
[54] Li J, Zhao M, Xiang X, He Q, Gui R. A novel biomimetic nanomedicine system with anti-inflammatory and anti-osteoporosis effects improves the therapy efficacy of steroid-resistant nephrotic syndrome. J Nanobiotechnology. 2021;19(1):417. Published 2021 Dec 13. doi:10.1186/s12951-021-01165-z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903236/
[55] Hou Y, Luo CZ, Xie DH, et al.Convenient synthesis of zwitterionic calcium(II)-carboxylate metal organic frameworks with efficient activities for the treatment of osteoporosis. Int J Pharm. 608:121083. doi:10.1016/j.ijpharm.2021.12108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536524/
[56] Davies A, Rangan A, Allman-Farinelli M. Dietary Behaviors That Place Young Adults at Risk for Future Osteoporosis. Nutrients. 2020;12(6). Published 2020 Jun 17. doi:10.3390/nu1206180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560378/
[57] Grippe K, Ryan V. Nutritional consideration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JAAPA. 2020;33(7):31-36. doi:10.1097/01.JAA.0000662384.93538.a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590531/
[58] Yao X, Hu J, Kong X, Zhu Z. Association between Dietary Calcium Intake and Bone Mineral Density in Older Adults. Ecol Food Nutr. 2021 Jan-Feb;60(1):89-100. doi:10.1080/03670244.2020.180143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779476/
[59] Polzonetti V, Pucciarelli S, Vincenzetti S, Polidori P. Dietary Intake of Vitamin D from Dairy Products Reduces the Risk of Osteoporosis. Nutrients. 2020;12(6). Published 2020 Jun 10. doi:10.3390/nu1206174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532150/
[60] Groenendijk I, Chan R, Woo J, et al.A Combined Nutrition and Exercise Intervention Influences Serum Vitamin B-12 and 25-Hydroxyvitamin D and Bone Turnover of Healthy Chinese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J Nutr. 2020;150(8):2112-2119. doi:10.1093/jn/nxaa14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588047/
[61] Eisenhauer A, Hastuti A, Heuser A, et al.Calcium isotope composition in serum and urine for the assessment of bone mineral balance (BMB) - The Osteolabs post-market follow-up study. Bone. 188:117210. doi:10.1016/j.bone.2024.11721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079608/
[62] Di Bari F, Vita R, Marini H, et al.Conservative Management of Gestational Hypercalcemia Due to Primary Hyperparathyroidism with Lack of Complications. Endocr Metab Immune Disord Drug Targets. 2021;21(8):1512-1517. doi:10.2174/187153032066620100715133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030137/
[63] Liu H, Ma Q, Han X, Huang W. 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serum 25-hydroxyvitamin D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hyperthyroidism. J Int Med Res. 2020;48(2):300060520903666. doi:10.1177/030006052090366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043416/
[64] Paccou J, Yavropoulou MP, Naciu AM, et al.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glucocorticoid-induced osteoporosis in adults: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European Calcified Tissue Society. Eur J Endocrinol. 2024;191(6):G1-G17. doi:10.1093/ejendo/lvae14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556468/
[65] Mamet T, Guo Y, Li X, Yang J, Zhao B. Yak milk improves retinoic acid-induced osteoporosis by promoting intestinal calcium absorption. J Dairy Sci. 2025;108(8):7912-7922. doi:10.3168/jds.2023-2435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349765/
[66] Wu Y, Guo X, Jiang A, Bai J, Nie X. Estrogen regulates duodenal calcium absorption and improves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by the effect of ERβ on PMCA1b. Sci Rep.2025;15(1):16053. Published 2025 May 8. doi:10.1038/s41598-025-00605-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341576/
[67] Liang Y, Cheng Q, Chen Z, Hou T. Effects of yeast protein on the promotion of intestinal calcium absorption (in vivo/in vitro) and bone formation (in vivo) in rats fed by normal and low-calcium diets. Food Res Int. 220:117179. doi:10.1016/j.foodres.2025.11717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1074380/
[68] Sun H, Weaver CM. Rising phytate and oxalate intake, declining calcium intake, and bone health in United States adults: 1999-2023, a serial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Am J Clin Nutr. 2025;122(1):315-323. doi:10.1016/j.ajcnut.2025.05.01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409467/
[69] Hattori S, Park S, Park JH, Omi N. The effect of dehydroepiandrosterone administration on intestinal calcium absorption in ovariectomized female rats. Phys Act Nutr. 2020;24(4):24-27. doi:10.20463/pan.2020.002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539691/
[70] Fleet JC. Vitamin D-Mediated Regulation of Intestinal Calcium Absorption. Nutrients. 2022;14(16). Published 2022 Aug 16. doi:10.3390/nu1416335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014856/
[71] Sarathi V, Dhananjaya MS, Karlekar M, Lila AR. Vitamin D deficiency or resistance and hypophosphatemia. Best Pract Res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24;38(2):101876. doi:10.1016/j.beem.2024.10187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365463/
[72] Christakos S. Vitamin D: A Critical Regulator of Intestinal Physiology. JBMR Plus. 2021;5(12):e10554. Published 2021 Dec.doi:10.1002/jbm4.1055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950825/
[73] Mendes MM, Botelho PB, Ribeiro H. Vitamin D and musculoskeletal health: outstanding aspects to be considered in the light of current evidence. Endocr Connect. 2022;11(10). Published 2022 Oct 1. doi:10.1530/EC-21-059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048470/
[74] Bhattarai HK, Shrestha S, Rokka K, Shakya R. Vitamin D, Calcium, Parathyroid Hormone, and Sex Steroids in Bone Health and Effects of Aging. J Osteoporos. 2020:9324505. Published 2020 None. doi:10.1155/2020/932450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612801/
[75] Narasimhan S, Lavik A, Auron M. Rickets. Pediatr Rev.2025;46(9):494-509. doi:10.1542/pir.2024-00649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875260/
[76] Gasmi A, Bjørklund G, Peana M, et al.Phosphocalcic metabolism and the role of vitamin D, vitamin K2, and nattokinase supplementation. Crit Rev Food Sci Nutr. 2022;62(25):7062-7071. doi:10.1080/10408398.2021.191048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966563/
[77] Zafalon RVA, Ruberti B, Rentas MF, et al.The Role of Vitamin D in Small Animal Bone Metabolism. Metabolites. 2020;10(12). Published 2020 Dec 3. doi:10.3390/metabo1012049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287408/
[78] Méndez-Sánchez L, Clark P, Winzenberg TM, Tugwell P, Correa-Burrows P, Costello R. Calcium and vitamin D for increasing bone mineral density in premenopausal women.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1:CD012664. Published 2023 Jan 27. doi:10.1002/14651858.CD012664.pub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705288/
[79] Carugo S, Vescini F, Giusti A, et al.The essential role of combined calcium and vitamin D supplementation in the osteoporosis scenario in italy: Expert opinion paper. Arch Osteoporos. 2024;19(1):99. Published 2024 Oct 22. doi:10.1007/s11657-024-01451-x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438361/
[80] Reid IR. Calcium Supplementation- Efficacy and Safety. Curr Osteoporos Rep.2025;23(1):8. Published 2025 Feb 12. doi:10.1007/s11914-025-00904-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937345/
[81] Reid IR, Bolland MJ. Calcium and/or Vitamin D Supplementa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Fragility Fractures: Who Needs It? Nutrients. 2020;12(4). Published 2020 Apr 7. doi:10.3390/nu1204101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272593/
[82] Dong B, Zhou Y, Wang J, et al.Comparison of Bisphosphonates Versus Teriparatide in Therapy of the Glucocorticoid-Induced Osteoporosis (GIOP):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Horm Metab Res. 2023;55(4):236-244. doi:10.1055/a-2015-174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652960/
[83] Chartron E, Firmin N, Touraine C, et al.A Phase II Multicenter Trial on High-Dose Vitamin D Supplementation for the Correction of Vitamin D Insufficiency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Receiving Adjuvant Chemotherapy. Nutrients. 2021;13(12). Published 2021 Dec 10. doi:10.3390/nu1312442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959982/
[84] Kim JS, Kim JT, Lim HI, et al.Real-world outcomes of denosumab treatment in patients undergoing hemodialysis for osteoporosis: A 3-year observational study. Clin Nephrol. . Published online Feb 2,2026. doi:10.5414/CN11191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1626778/
[85] Uemura O. Reconsidering the Widespread Use of Active Vitamin D Analogues for Osteoporosis in Japan: A Call for Evidence-Based Prescription Practices. JMA J. 2026;9(1):363-365. doi:10.31662/jmaj.2025-040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1676834/
[86] Saadeh R, Jumaa D, Elsalem L, et al.Osteoporosis among Postmenopausal Women in Jordan: A National Cross-Sectional Study.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22;19(14). Published 2022 Jul 20. doi:10.3390/ijerph1914880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886655/
[87] Gilbert ZA, Muller A, Leibowitz JA, Kesselman MM. Osteoporosi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The Risk of Comorbid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Cureus. 2022;14(4):e24117. Published 2022 Apr.doi:10.7759/cureus.2411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573562/
[88] Bitar ZI, Hajjiah AM, Maadarani OS, et al.Hypocalcemia in Patients With Osteoporosis and Normal Renal Function, Treated With Denosumab,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Nutr Metab Insights. 17:11786388231223604. Published 2024 None. doi:10.1177/1178638823122360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205220/
[89] Xing Y, Ju S, Sun M, Xiang S. Case report: Denosumab-associated acute heart failure in patients with cardiorenal insufficiency. Front Endocrinol (Lausanne). 13:970571. Published 2022 None. doi:10.3389/fendo.2022.97057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187135/
[90] Ardelean A, Tit DM, Furau R, et al.Beyond Bone Mineral Density: Real-World Fracture Risk Profiles and Therapeutic Gaps in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Diagnostics (Basel). 2025;15(15). Published 2025 Aug 6. doi:10.3390/diagnostics1515197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804936/
[91] Liu C, Kuang X, Li K, Guo X, Deng Q, Li D. Effects of combined calcium and vitamin D supplementation on osteoporosis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Food Funct. 2020;11(12):10817-10827. doi:10.1039/d0fo00787k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237064/
[92] Tang SS, Yin XJ, Yu W, et al.[Prevalence of osteoporosis and related factors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aged 40 and above in China]. Zhonghua Liu Xing Bing Xue Za Zhi. 2022;43(4):509-516. doi:10.3760/cma.j.cn112338-20210826-0068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443305/
[93] Li C, Wang S, Du M, Wei Y, Jiang S.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ollable Risk Factors of Osteoporosis in Elderly Men with Diabetes Mellitus. Orthop Surg. 2021;13(3):1001-1005. doi:10.1111/os.1295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821551/
[94] Gupta A, Cha T, Schwab J, et al.Males Have Higher Rates of Peri-operative Mortality Following Surgery for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Osteoporos Int. 2021;32(4):699-704. doi:10.1007/s00198-020-05630-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929524/
[95] Arnst JL, Alappan UD, Viggeswarapu M, Beck GR Jr.Sustained and reversible effects of a dietary phosphate intake on bone and mineral metabolism during aging. Geroscience. . Published online Jun 2,2025. doi:10.1007/s11357-025-01714-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455097/
[96] Midttun M, Overgaard K, Zerahn B, et al.Beneficial effects of exercise, testosterone, vitamin D, calcium and protein in older men-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 Cachexia Sarcopenia Muscle. 2024;15(4):1451-1462. doi:10.1002/jcsm.1349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890228/
[97] Cao Y, Hu Y, Lei F, et al.Associations between 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 and the prevalence and incidence of osteoporosis disease: Cross-sectional and prospective findings from the UK biobank. Bone. 187:117208. doi:10.1016/j.bone.2024.11720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047901/
[98] Abdelrahman AM, Farg ME, Nofal HA, et al.Geriatric Nutritional Risk Index as a Predictor for Osteoporosis Risk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 Hospital-Based Study. Diagnostics (Basel). 2026;16(3). Published 2026 Jan 27. doi:10.3390/diagnostics1603040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1681725/
[99] Curtis EM, Cooper C, Harvey NC. Cardiovascular safety of calcium, magnesium and strontium: what does the evidence say? Aging Clin Exp Res. 2021;33(3):479-494. doi:10.1007/s40520-021-01799-x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565045/
[100] Kim JE, Park J, Jang Y, et al.Oral phosphate binders and incident osteoporotic fracture in patients on dialysis. Nephrol Dial Transplant. 2025;40(2):329-340. doi:10.1093/ndt/gfae13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886108/
[101] Razzaque MS, Wimalawansa SJ. Minerals and Human Health: From Deficiency to Toxicity. Nutrients. 2025;17(3). Published 2025 Jan 26. doi:10.3390/nu1703045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940312/
[102] Zhou Y, Lower EE. Balancing Altered Calcium Metabolism with Bone Health in Sarcoidosis. Semin Respir Crit Care Med. 2020;41(5):618-625. doi:10.1055/s-0040-171300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777848/
[103] Grabill N, Louis M, Machado N, Brown P 3rd, Ellis E, So S. A case series on parathyroid carcinoma: Diagnostic challenges and therapeutic approaches. Int J Surg Case Rep.125:110601. doi:10.1016/j.ijscr.2024.11060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580979/
[104] Otsuki K, Izuhara M, Miura S, et al.Psychosis in a primary hyperparathyroidism patient with mild hypercalcemia: A case report. Medicine (Baltimore). 2021;100(12):e25248. doi:10.1097/MD.000000000002524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761720/
[105] Liu G, Li B, Li J, et al.EGTA-Derived Carbon Dots with Bone-Targeting Ability: Target-Oriented Synthesis and Calcium Affinity.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2023;15(34):40163-40177. doi:10.1021/acsami.3c0518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603390/
[106] Park SY, Kim J, Chung HY. Denosumab-induced hypocalcemia in a patient with hyperthyroidism: a case report. Osteoporos Int. 2022;33(1):305-308. doi:10.1007/s00198-021-06059-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232341/
[107] Brzęczek M, Hyla-Klekot L, Kokot F, Synder M. Contribution of Bone Tissue to Regulation of Calcium and Phosphate Metabolism. Role of FGF23 and Klotho Protein. Ortop Traumatol Rehabil. 2020;22(2):69-76. doi:10.5604/01.3001.0014.115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468993/
[108] Farrah Z, Jawad AS. Optimising the management of osteoporosis. Clin Med (Lond). 2020;20(5):e196-e201. doi:10.7861/clinmed.2020-013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934064/
[109] Makan AM, Hout HV, Onder G, et al.Pharmacological management of osteoporosis in nursing home residents: the Shelter study. Maturitas. 143:184-189. doi:10.1016/j.maturitas.2020.10.02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308627/
[110] Yang YX, Jin Y. Clinical Efficacy of Bisphosphonates in Treating Osteoporosis in Diabetes Patients: A Meta-Analysis. Horm Metab Res. 2024;56(11):795-806. doi:10.1055/a-2295-933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670123/
[111] Cho YH, Byun SE, Lee HH. Two-year outcomes of denosumab treatment for osteoporosis comparing the effects of calcium and vitamin D supplementation. Sci Rep.2025;15(1):44588. Published 2025 Dec 24. doi:10.1038/s41598-025-28252-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1444308/
[112] Yoshida K, Kojima S, Sakurada T. Severe symptomatic hypocalcemia and prolonged heart failure after treatment of osteoporosis with denosumab in a peritoneal dialysis patient: A case report. Perit Dial Int. :8968608251361322. Published online Jul 23,2025. doi:10.1177/0896860825136132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697092/
[113] Chen Y, Wu W, Xu L, et al.[Changes in circulating levels of calcium and bone metabolism biochemical markers in patients receiving denosumab treatment]. Nan Fang Yi Ke Da Xue Xue Bao. 2025;45(4):760-764. doi:10.12122/j.issn.1673-4254.2025.04.1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294926/
[114] Xu Y, Lai J, Mai M, Tang Y, Wu Z. 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of bone-protective interventions for aromatase inhibitors-induced bone loss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with early breast cancer: a network meta-analysis. Front Oncol. 15:1638370. Published 2025 None. doi:10.3389/fonc.2025.163837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1568387/
[115] Ye C, McAlister FA, Bellerose D, Lin M. Targeted Coaching to Improve Osteoporosis Therapy Adherence: A Single Arm Variation of the C-STOP Study. J Bone Metab. 2024;31(1):13-20. doi:10.11005/jbm.2024.31.1.1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485237/
[116] Bonnet AL, Aboishava L, Mannstadt M. Advances in Parathyroid Hormone-based medicines. J Bone Miner Res. 2025;40(11):1195-1206. doi:10.1093/jbmr/zjaf11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847810/
[117] Gatti D, Fassio A. Pharmacological management of osteoporosis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art. J Popul Ther Clin Pharmacol. 2019;26(4):e1-e17. Published 2019 Nov 20. doi:10.15586/jptcp.v26.i4.64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1909575/
[118] Morin SN, Leslie WD, Schousboe JT. Osteoporosis: A Review. JAMA. 2025;334(10):894-907. doi:10.1001/jama.2025.600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587168/
[119] Yu Y, Li X, Zheng M, et al.The potential benefits and mechanisms of protein nutritional intervention on bone health improvement. Crit Rev Food Sci Nutr. 2024;64(18):6380-6394. doi:10.1080/10408398.2023.216825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655469/
[120] Martiniakova M, Babikova M, Omelka R. Pharmacological agents and natural compounds: available treatments for osteoporosis. J Physiol Pharmacol. 2020;71(3). doi:10.26402/jpp.2020.3.0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991310/
[121] Reid IR. EXTENSIVE EXPERTISE IN ENDOCRINOLOGY: Osteoporosis management. Eur J Endocrinol. 2022;187(4):R65-R80. Published 2022 Oct 1. doi:10.1530/EJE-22-057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984345/
[122] Corredor DC, Pascual LÁC. Predictors of clinically meaningful bone mineral density gains with romosozumab: An explainable machine leaning analysis of a real-world cohort. Bone Rep.27:101890. Published 2025 Dec. doi:10.1016/j.bonr.2025.10189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1404357/
[123] Kobayakawa T, Miyazaki A, Takahashi J, Nakamura Y. Effects of romosozumab with and without active vitamin D analog supplementation for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Clin Nutr ESPEN. 48:267-274. doi:10.1016/j.clnesp.2022.02.00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331501/
[124] Baturin AK, Sharafetdinov KK, Kodentsova VM. [Role of calcium in health and reducing the risk of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Vopr Pitan. 2022;91(1):65-75. doi:10.33029/0042-8833-2022-91-1-65-7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298105/
[125] Quintero-García M, Gutiérrez-Cortez E, Rojas-Molina A, et al.Calcium Bioavailability of Opuntia ficus-indica Cladodes in an Ovariectomized Rat Model of Postmenopausal Bone Loss. Nutrients. 2020;12(5). Published 2020 May 15. doi:10.3390/nu1205143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429103/
[126] Mendoza-Ávila M, Gutiérrez-Cortez E, Quintero-García M, et al.Calcium Bioavailability in the Soluble and Insoluble Fibers Extracted from Opuntia ficus indica at Different Maturity Stages in Growing Rats. Nutrients. 2020;12(11). Published 2020 Oct 23. doi:10.3390/nu1211325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114068/
[127] Akter S, Netzel M, Tinggi U, Fletcher M, Osborne S, Sultanbawa Y. Interactions Between Phytochemicals and Minerals in Terminalia ferdinandiana and Implications for Mineral Bioavailability. Front Nutr. 7:598219. Published 2020 None. doi:10.3389/fnut.2020.59821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425972/
[128] Sateikaite I, Samaei Y, Khan M, Carvalho I, Lazarte CE. Nutritional status of children under-five in rural mozambique: the role of phytate intake and mineral bioavailability. J Health Popul Nutr. . Published online Feb 14,2026. doi:10.1186/s41043-026-01247-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1689148/
[129] Olier M, Naud N, Fouché E, et al.Calcium-rich dairy matrix protects better than mineral calcium against colonic luminal haem-induced alterations in male rats. NPJ Sci Food. 2024;8(1):43. Published 2024 Jul 2. doi:10.1038/s41538-024-00273-y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956092/
[130] Pop MS, Cheregi DC, Onose G, et al.Exploring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f Natural Calcium-Rich Mineral Waters for Health and Wellness: A Systematic Review. Nutrients. 2023;15(14). Published 2023 Jul 13. doi:10.3390/nu1514312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513544/
[131] Cormick G, Settecase E, Wu ML, et al.Calculation of the contribution of water to calcium intake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nn N Y Acad Sci. 2023;1522(1):149-157. doi:10.1111/nyas.1497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841929/
[132] Hasanuddin DNA, Dewi SP, Fatmawati S, Adi AC, Rachmawati H. Nano Calcium from Marine Fish Bones via High-Energy Ball Milling: A Potential Natural Supplement for Bone Health. J Bone Metab. 2025;32(4):285-296. doi:10.11005/jbm.25.87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1423191/
[133] Kowalczyk M, Znamirowska-Piotrowska A, Buniowska-Olejnik M, Zaguła G, Pawlos M. Bioavailability of Macroelements from Synbiotic Sheep’s Milk Ice Cream. Nutrients. 2023;15(14). Published 2023 Jul 20. doi:10.3390/nu1514323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513648/
[134] Varshanath B, Robin DT, Meera S, et al.Enhancement of iron, zinc, and calcium bioaccessibility and bioavailability in green gram (Vigna radiata L.) supplemented with buttermilk through phytate reduction: an in vitro dietary evaluation. Front Nutr. 13:1756171. Published 2026 None. doi:10.3389/fnut.2026.175617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1693945/
[135] Chungchunlam SM, Moughan PJ. The Role of Beef for the Lowest Cost and Adequate Provision of Bioavailable Nutrients in Modeled Diets at a Population Level in the United States. Curr Dev Nutr. 2025;9(12):107604. Published 2025 Dec.doi:10.1016/j.cdnut.2025.10760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1492341/
[136] Ilesanmi-Oyelere BL, Kruger MC. Nutrient and Dietary Patterns in Relation to the Pathogenesis of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A Literature Review. Life (Basel). 2020;10(10). Published 2020 Sep 25. doi:10.3390/life1010022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992740/
[137] Martini D, Rosi A, Angelino D, Passeri G. Calcium intake from different food sources in Italian women without and with non-previously diagnosed osteoporosis. Int J Food Sci Nutr. 2021;72(3):418-427. doi:10.1080/09637486.2020.181869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912052/
[138] Martiniakova M, Babikova M, Mondockova V, Blahova J, Kovacova V, Omelka R. The Role of Macronutrients, Micronutrients and Flavonoid Polyphenols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Osteoporosis. Nutrients. 2022;14(3). Published 2022 Jan 25. doi:10.3390/nu1403052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276879/
[139] Arnold M, Rajagukguk YV, Gramza-Michałowska A. Functional Food for Elderly High in Antioxidant and Chicken Eggshell Calcium to Reduce the Risk of Osteoporosis-A Narrative Review. Foods. 2021;10(3). Published 2021 Mar 19. doi:10.3390/foods1003065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808726/
[140] Nguyen B, Murimi MW. Lack of calcium rich foods in the diet, low knowledge on calcium level recommendations and severe food insecurity predicts low calcium intake among Vietnamese women. Appetite. 163:105242. doi:10.1016/j.appet.2021.10524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823231/
[141] Chaudhary NK, Sunuwar DR, Sapkota MR, Pant S, Pradhan M, Bhandari KK. Prevalence of osteoporosis and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people aged 50 years and older in the Madhesh province of Nepal: a community-based cross-sectional study. J Health Popul Nutr. 2024;43(1):100. Published 2024 Jul 4. doi:10.1186/s41043-024-00591-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965638/
[142] Ju S, Kwon Y, Yeum KJ. Persistent Calcium Inadequacy in Korean Adults over 20 Years: Analysis of the 1998-2018 Korea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Foods. 2024;13(22). Published 2024 Nov 7. doi:10.3390/foods1322356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593984/
[143] Cairoli E, Aresta C, Giovanelli L, et al.Dietary calcium intake in a cohort of individuals evaluated for low bone mineral density: a multicenter Italian study. Aging Clin Exp Res. 2021;33(12):3223-3235. doi:10.1007/s40520-021-01856-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909280/
[144] Verbeke J, Laurent MR, Matthys C.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n eight-item calcium screener to assess daily calcium intake of patients with osteoporosis in clinical practice. Eur J Clin Nutr. 2024;78(4):301-306. doi:10.1038/s41430-023-01390-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158406/
[145] Iuliano S, Poon S, Robbins J, et al.Effect of dietary sources of calcium and protein on hip fractures and falls in older adults in residential care: cluster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BMJ. 375:n2364. Published 2021 Oct 20. doi:10.1136/bmj.n236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670754/
[146] Hunegnaw MT, Mesinovic J, Jansons P, et al.Effects of a digital voice assistant-delivered osteoporosis self-management program on diet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with osteoporosis: A secondary analysis of a 12-month feasibility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Maturitas. 206:108840. Published online Jan 21,2026. doi:10.1016/j.maturitas.2026.10884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1579420/
[147] Wiesner A, Szuta M, Galanty A, Paśko P. Optimal Dosing Regimen of Osteoporosis Drugs in Relation to Food Intake as the Key for the Enhancement of the Treatment Effectiveness-A Concise Literature Review. Foods. 2021;10(4). Published 2021 Mar 29. doi:10.3390/foods1004072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805435/
[148] Li Y, Zhao P, Jiang B, et al.Modulation of the vitamin D/vitamin D receptor system in osteoporosis pathogenesis: insights and therapeutic approaches. J Orthop Surg Res. 2023;18(1):860. Published 2023 Nov 13. doi:10.1186/s13018-023-04320-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957749/
[149] Schulz N, Dischereit G, Henke L, Lange U, Klemm P. Prevalence and effects of Vitamin D receptor polymorphism on 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metabolism in patients with systemic sclerosis: a preliminary study. Clin Exp Med. 2024;24(1):121. Published 2024 Jun 7. doi:10.1007/s10238-024-01385-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847864/
[150] Abdi S, Almiman AA, Ansari MGA, et al.PTHR1 Genetic Polymorphisms Are Associated with Osteoporosis among Postmenopausal Arab Women. Biomed Res Int. 2021:2993761. Published 2021 None. doi:10.1155/2021/299376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977236/
[151] Patel YP, Pandey SN, Patel SB, et al.Haplotype of CaSR gene is associated with risk of renal stone disease in West Indian population. Urolithiasis. 2022;51(1):25. Published 2022 Dec 31. doi:10.1007/s00240-022-01394-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585523/
[152] Zheng S, Zhu L, Wang Y, Hua Y, Ying J, Chen J. Key genes of vitamin D metabolism and their roles in the risk and prognosis of cancer. Front Genet. 16:1598525. Published 2025 None. doi:10.3389/fgene.2025.159852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630116/
[153] Sridharan K, Jassim A, Qader AM, Qader MM. Influence of vitamin D and calcium-sensing receptor gene variants on calcium metabolism in end-stage renal disease: insights from machine learning analysis. Eur Rev Med Pharmacol Sci. 2024;28(22):4634-4643. doi:10.26355/eurrev_202411_3695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624014/
[154] Voltan G, Cannito M, Ferrarese M, Ceccato F, Camozzi V. Vitamin D: An Overview of Gene Regulation, Ranging from Metabolism to Genomic Effects. Genes (Basel). 2023;14(9). Published 2023 Aug 25. doi:10.3390/genes1409169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761831/
[155] Benish, Choi JH. Bitter Taste Receptor TAS2R38 Genetic Variation (rs10246939), Dietary Nutrient Intake, and Bio-Clinical Parameters in Koreans. Clin Nutr Res. 2023;12(1):40-53. Published 2023 Jan.doi:10.7762/cnr.2023.12.1.4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793779/
[156] Laster ML, Rowan B, Chen HC, et al.Genetic Variants Associated With Mineral Metabolism Traits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22;107(9):e3866-e3876. doi:10.1210/clinem/dgac31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587600/
[157] Kayani M, Sangeetha GK, Sarangi S, et al.Pharmacogenomics and its Role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 Narrative Literature Review. Curr Cardiol Rev. 2025;21(4):e1573403X334668. doi:10.2174/011573403X33466824122707431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901689/
[158] Wu J, Zhang S, Wu J, et al.Targeting the gut‑bone axis through exercise: A novel approach to osteoporosi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Review). Int J Mol Med. 2026;57(4). doi:10.3892/ijmm.2026.576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1685587/
[159] Jin J, Li Q, Zhou Q, et al.Calcium deposition in chicken eggshells: role of host genetics and gut microbiota. Poult Sci. 2024;103(10):104073. doi:10.1016/j.psj.2024.10407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068697/
[160] He J, Xie H, Yan C, Sun Y, Xu Z, Zhang X. Genetic Variation in VKORC1 and Risk for Osteoporosis. Arch Med Res. 2021;52(2):211-216. doi:10.1016/j.arcmed.2020.10.00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234259/
[161] Di Marcello F, Di Donato G, d’Angelo DM, Breda L, Chiarelli F. Bone Health in Children with Rheumatic Disorders: Focus on Molecular Mechanisms,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Int J Mol Sci. 2022;23(10). Published 2022 May 20. doi:10.3390/ijms2310572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628529/
[162] Stepanova K, Lytkina D, Sadykov R, et al.Composite Cement Materials Based on β-Tricalcium Phosphate, Calcium Sulfate, and a Mixture of Polyvinyl Alcohol and Polyvinylpyrrolidone Intended for Osteanagenesis. Polymers (Basel). 2022;15(1). Published 2022 Dec 31. doi:10.3390/polym1501021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616560/
[163] Sun N, Hu S, Wang D, Jiang P, Zhang S, Lin S. Calcium Delivery Systems Assembled using Antarctic Krill Derived Heptapeptides: Exploration of the Assembly Mechanism, In Vitro Digestion Profile, and Calcium Absorption Behavior. J Agric Food Chem. 2022;70(6):2018-2028. doi:10.1021/acs.jafc.1c0695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107281/
[164] Zhao M, Ma A, He H, Guo D, Hou T. Desalted duck egg white peptides-chitosan oligosaccharide copolymers as calcium delivery systems: Prepara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calcium release evaluation in vitro and vivo. Food Res Int. 131:108974. doi:10.1016/j.foodres.2019.10897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247485/
[165] Levingstone TJ, Herbaj S, Redmond J, McCarthy HO, Dunne NJ. Calcium Phosphate Nanoparticles-Based Systems for RNAi Delivery: Applications in Bone Tissue Regeneration. Nanomaterials (Basel). 2020;10(1). Published 2020 Jan 14. doi:10.3390/nano1001014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1947548/
[166] Yu B, Gao Q, Sheng S, et al.Smart osteoclasts targeted nanomedicine based on amorphous CaCO3 for effective osteoporosis reversal. J Nanobiotechnology. 2024;22(1):153. Published 2024 Apr 5. doi:10.1186/s12951-024-02412-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580995/
[167] Lončarević Vrabec A, Bazina I, Vlahović L, Abdii E, Urlić I, Rogina A. Chitosan/calcium phosphate microspheres as smart, multi-functional delivery systems for targeted bone cancer treatment. Colloids Surf B Biointerfaces. 257:115163. doi:10.1016/j.colsurfb.2025.11516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1033246/
[168] Chen L, Lin X, Wei M, et al.Hierarchical antibiotic delivery system based on calcium phosphate cement/montmorillonite-gentamicin sulfate with drug release pathways. Colloids Surf B Biointerfaces. 238:113925. doi:10.1016/j.colsurfb.2024.11392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657556/
[169] Alshaya HA, Alfahad AJ, Alsulaihem FM, et al.Fast-Dissolving Nifedipine and Atorvastatin Calcium Electrospun Nanofibers as a Potential Buccal Delivery System. Pharmaceutics. 2022;14(2). Published 2022 Feb 4. doi:10.3390/pharmaceutics1402035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214093/
[170] Klipp A, Greitens C, Scherer D, Elsener A, Leroux JC, Burger M. Modular Calcium-Responsive and CD9-Targeted Phospholipase System Enhancing Endosomal Escape for DNA Delivery. Adv Sci (Weinh). 2025;12(15):e2410815. doi:10.1002/advs.20241081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998318/
骨质疏松症生活方式干预的研究进展与综合策略
AI辅助原创作品
2026-02-12
·鸿松医药
极简 极致 极品
编者按:
2025年中国生物医药行业完成结构性调整与全球化进阶的双重突破,全年 334笔公开BD交易勾勒出行业全新发展格局:授权海外交易占比过半成主流,交易总金额突破千亿美元,AI制药、ADC等技术平台成为交易核心,中国药企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创新价值链重构。
鸿松医药
一、出海进阶:从产品输出到平台技术出海的质变
2025 年药企 BD 交易中授权海外占比达 50%,成为最主要交易类型,出海呈现金额高、临床早、合作优三大特征。恒瑞医药与 GSK 合作的 HRS-9821 项目以 125 亿美元创下中国药企单笔授权纪录;信达生物 FDA I 期项目、映恩生物临床前项目均实现海外大额授权,打破 “晚期资产才能出海” 的行业认知。
出海目的地也实现多元化,除欧美传统市场外,中东、东南亚、拉美等新兴市场成为布局新方向。更值得关注的是,平台型出海成为新趋势,晶泰科技 AI 药物发现平台、百奥赛图全人抗体平台均获得辉瑞、默克等跨国巨头的海外授权,中国药企实现从 “卖产品” 到 “卖技术、卖平台” 的升级。
二、技术核心:AI 制药 + ADC 领跑,前沿领域齐发力
2025 年技术平台类交易量、金额双创新高,AI 制药和 ADC 成为两大核心赛道,在 80 项明确统计的技术平台交易中,ADC、细胞治疗、双抗、AI 制药平台交易分别占 28 笔、22 笔、16 笔、14 笔。
AI 制药平台交易呈爆发式增长,超 60% 为跨境授权,晶泰科技、英矽智能等企业的 AI 平台先后与礼来、辉瑞等达成合作,交易均采用 “首付款 + 里程碑 + 销售分成” 模式。ADC 领域则从单一产品交易转向平台技术交易,全年 license-out 交易 22 笔,总金额 262 亿美元,占海外授权总金额的 19%,12 笔交易总金额超 10 亿美元。同时,双抗、CAR-T 细胞治疗、基因编辑等前沿领域交易也持续活跃。
三、价值核心:临床阶段定价值,金额与阶段正相关
临床价值成为 2025 年 BD 交易的核心评判标准,不同临床阶段产品交易特征差异显著,且交易金额与临床阶段呈明显正相关。临床前项目交易占比 35% 居首,多集中于技术平台类资产,首付低但里程碑付款高;临床 I 期项目开始获得大额首付授权,体现跨国药企对中国早期研发数据的认可;II/III 期项目成为大额交易主力,完整的临床数据让其市场潜力更易评估;已上市产品则侧重区域化、精细化商业权益转让。
从金额来看,临床前、I 期、II 期项目平均交易金额分别约 2.5 亿美元、5 亿美元、8 亿美元,III 期及上市后项目则超 10 亿美元。
四、交易结构:精细化设计,风险收益更均衡
传统的 “首付款 + 里程碑 + 销售分成” 仍为交易主流模式,但 2025 年交易结构设计更趋精细化、个性化。平均首付款占总交易金额的比例降至 12%,较 2024 年下降 3 个百分点,反映出买卖双方风险分摊更均衡,也契合早期项目交易占比提升的趋势。
同时,里程碑付款与临床开发、监管审批等进展深度挂钩,区域权益划分也从简单的 “全球 / 大中华区” 转向精细化拆分;“现金 + 股权” 的交易组合成为新趋势,诺诚健华、加科思等企业均通过该模式完成交易。此外,单纯权利许可逐步向合作开发转变,信达生物、拓济医药等企业与跨国药企达成联合开发协议,实现研发资源互补。
五、国内生态:协同创新成主流,跨界融合显活力
与海外交易相呼应,2025 年境内 BD 交易同样活跃,占比 39.52%、交易数量超百笔,国内生物医药生态形成多方协同、跨界融合的新格局。大型药企与生物科技公司合作紧密,齐鲁制药、先声药业等传统药企通过交易快速补充管线;AI 制药等技术平台公司与药企的合作成为常态,实现技术与产业的结合。
高校、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速度加快,清华大学、上海药物研究所等机构的研发成果通过技术转让、合作开发实现产业化;红杉中国、高瓴资本等非医药领域玩家也通过交易入局,跨界合作成为新增长点。同时,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产业集群内部及间的交易频繁,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初步形成。
六、2026年六大趋势:创新与全球化成发展主线
2026年中国生物医药 BD 市场将呈现六大发展趋势:
一是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出海从欧美向新兴市场延伸,本土化生产成为合作新方向;
二是技术平台交易持续升温,原创 AI、基因编辑等平台型企业将成交易核心;
三是临床价值导向更极致,first-in-class、best-in-class 资产获高溢价,me-too 资产估值承压;
四是交易结构创新常态化,“现金 + 股权”、风险共担等灵活方案成为主流;
五是行业整合加速,资本压力下并购与战略合作增多,行业集中度提升;
六是监管政策影响加深,NMPA 审批、FDA 对中国临床数据的接受度将直接影响交易估值与结构。
想获得更多推文延伸解读与行业干货?欢迎扫码加入 【鸿松医药】合作交流群,与编辑和同行直接交流。
扫码进群可以免费获得一份药品调研报告。
往期推荐之调研报告
【仿制优选】市场教育成熟、服药依从性较高的抗高血压药物苯磺酸氨氯地平口服溶液介绍
【仿制优选】具里程碑式临床疗效的银屑病PDE4抑制剂First-in-class准集采品种阿普米司特片介绍
【仿制优选】口腔科局麻药新剂型盐酸利多卡因口服溶液介绍
【仿制优选】作用机制新颖的抗失眠药物达利雷生片介绍
【仿制优选】处于急速增长期的骨质疏松症的治疗药物阿仑膦酸钠口服溶液介绍
【鼓励研发儿童药品】适合新生儿糖尿病的降血糖药物格列本脲混悬剂介绍
【仿制优选】2022版医保目录心血管系统部分口服化药未过评品种一览(截至2023.12.8)
【仿制优选】豁免BE的肠道清洁剂—硫酸镁钠钾口服用浓溶液
往期推荐之法规解读
分析人员必看!国家药监局印发《2026年药品检验能力验证计划的通知》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再次修订,新规落地关键变化太大了!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23年来的首次全面修订,要点解读来了!
九部门联合发文!近70万药店将向“健康服务”转型
CRO行业2025业绩预告解读:有人盆满钵满,有人艰难转型
【推荐收藏】原研官方审评报告查询全攻略(覆盖中日美欧)立项调研不踩坑!
球场上有红黄牌警告,医药圈有“红黄标”价格风险预警标识!药品价格治理即将迈入新阶段
全国药品比价系统上线:一键比价,购药更省心
免责声明:本微信公众号文章中的信息谨供一般参考之用,不可直接作为决策内容,鸿松医药不对任何主体因使用本文内容而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另外,因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谅解!
点击阅读原文,可填写您的需求信息喔!
2026-02-09
1. 执行摘要与核心投资论点1.1 公司定位与战略价值1.1.1 全球临床阶段生物制药企业的差异化定位
创胜集团(Transcenta Holding Limited,股票代码:06628.HK)是一家具有全球布局的优质生物医药企业,在中国和美国均具备全球临床研发能力,采用多区域开发战略推进多种疾病药物创新。公司成立于2012年,前身为MabSpace Biosciences,2019年完成全球化重组整合,2021年9月成功登陆香港交易所主板,成为第18A章上市规则下的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与其他临床阶段生物制药企业相比,创胜集团的核心差异化特征在于其“端到端”一体化平台能力——从抗体发现、工艺开发、临床转化到商业化生产,公司建立了完整的内部能力体系,而非依赖外部CRO/CDMO的轻资产模式。
这一战略定位的价值在2024-2025年得到进一步验证。公司管理层在2024年6月完成关键更迭,钱雪明博士接任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推动研发资源向核心管线聚焦,同时优化运营效率。截至2025年初,公司拥有16个创新分子,覆盖肿瘤、骨科、肾病及自体免疫等多个治疗领域,其中核心产品Osemitamab(TST001)针对Claudin18.2靶点的开发进度在中国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二,确立了公司在该细分赛道的领先地位。这种”平台+管线”的双轮驱动模式,既降低了对外部合作的依赖度,也为未来持续产出创新分子奠定了基础。
1.1.2 Claudin18.2靶点全球第二、中国第一的领先地位
Claudin18.2是近年来肿瘤免疫治疗领域最具潜力的靶点之一,尤其在胃癌、胰腺癌等消化道肿瘤中呈现高表达特征。创胜集团的Osemitamab(TST001)是全球第二款进入III期临床开发的Claudin18.2靶向抗体,仅次于安斯泰来(Astellas)的Zolbetuximab(已于2024年在日本、美国等地获批上市)。这一领先地位的含金量体现在多个维度:首先,公司在中、美、韩三地同步开展TranStar 301全球III期关键性试验,已获得NMPA、FDA及MFDS的监管批准,展现了国际多中心临床执行能力;其次,2024年ESMO年会公布的最新临床数据显示,Osemitamab联合纳武利尤单抗和CAPOX方案在Claudin18.2高/中表达且PD-L1 CPS阳性患者中达到68%的客观缓解率(ORR)和14.2个月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50%(HR=0.505)。
更值得关注的是,Osemitamab在分子设计上具备潜在的同类最优(Best-in-Class)特征。与Zolbetuximab相比,TST001采用人源化抗体结构,具有更强的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ADCC)效应,且在更低Claudin18.2表达水平的肿瘤中仍保持活性。这一差异化优势可能转化为更广泛的适用患者人群——临床实践中,Claudin18.2高表达(≥75%肿瘤细胞)患者仅占胃癌人群的约30%-40%,而TST001对中低表达患者的活性将显著扩大目标市场。此外,公司开发的伴随诊断抗体能够特异性识别Claudin18.2而不与Claudin18.1交叉反应,这一技术优势在肺癌等两种变体共表达的瘤种中尤为关键。
1.1.3 一体化端到端平台的核心竞争优势
创胜集团的技术平台体系由四大核心模块构成:专有抗体发现平台、一体化CMC(化学、制造与控制)能力、先进转化科学平台及HiCB(High-intensity Continuous Bioprocessing)制造平台技术。这一平台架构的协同效应体现在药物开发的全生命周期:抗体发现平台通过突破免疫耐受限制,提高了针对高难度靶点的成药性;一体化CMC能力将DNA到IND的时间缩短至行业领先水平;HiCB连续生产工艺则在保证质量一致性的同时,显著降低了单位生产成本。
HiCB平台的技术经济性尤其值得强调。传统批次生物反应器的生产效率受限于设备规模和操作周期,而连续生产工艺通过灌注培养模式实现了更高的细胞密度和产物浓度,理论上可将生产成本降低30%-50%。对于Osemitamab这类需要长期给药的大分子抗体药物,成本优势将在商业化阶段转化为显著的定价灵活性和毛利率空间。公司目前已在杭州建立符合GMP标准的商业化生产基地,为未来自主生产做好准备。此外,平台能力还通过CDMO服务创造收入,2024年该业务贡献约910万元人民币收入,虽规模有限,但验证了技术平台的商业可行性。
1.2 关键投资亮点1.2.1 核心产品Osemitamab(TST001)的同类最优(Best-in-Class)潜力
Osemitamab的投资价值建立在三重证据基础之上:机制差异化、临床数据优势、适应症扩展空间。从机制角度,TST001的表位选择使其能够结合Claudin18.2的近膜端区域,这一位置接近治疗性抗体的结合位点,既增强了抗肿瘤活性,也为开发高特异性伴随诊断提供了可能。钱雪明博士在2024年7月的采访中明确指出,竞争对手的抗体由于结合细胞内共享结构域,无法区分Claudin18.2与18.1,而TST001的特异性使其能够准确筛选Claudin18.2阳性肺癌患者——这一瘤种约占肺癌总数的10%,代表了一个全新的市场机会。
临床数据方面,2025年ASCO公布的TranStar 102 G队列更新数据具有里程碑意义。在66例可评估患者中,Claudin18.2高/中表达且PD-L1 CPS阳性患者的确认ORR达到68%,mPFS为16.6个月。
与历史对照相比,这一数据显著优于传统化疗(ORR约30%-40%,mPFS 6-7个月),也优于Zolbetuximab联合化疗的III期结果(SPOTLIGHT研究:ORR 60.7%,mPFS 10.6个月)。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TST001显示出”无论PD-L1表达如何”的广谱活性,这意味着其联合免疫治疗的潜力不受PD-L1状态限制,而当前PD-1抑制剂在胃癌中的疗效高度依赖PD-L1 CPS评分。
适应症扩展策略进一步放大了TST001的商业潜力。除一线胃癌/胃食管结合部腺癌这一核心适应症外,公司正在探索围手术期治疗(术前新辅助/术后辅助)、胰腺癌和肺癌三大方向。围手术期治疗可覆盖额外30%-40%的胃癌患者,胰腺癌约50%的肿瘤表达Claudin18.2且现有治疗选择极为有限,肺癌则是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若这些适应症逐步获批,TST001的峰值销售有望远超单一胃癌适应症的预测。
1.2.2 2027年商业化拐点与收入爆发式增长预期
根据软库中华金融的盈利预测模型,创胜集团将在2027年迎来收入爆发式增长的关键拐点。2024-2026年公司收入维持在900万-1400万元人民币的低位,主要来源于CDMO服务和早期合作里程碑;2027年随着TST001商业化启动,收入预计跃升至1.20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79.5%;2028年进一步增长至3.55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幅135.4%。这一预测的核心假设包括:TST001于2026年底至2027年初在中国获批上市,首年产生1.04亿元收入,中国胃癌适应症销售峰值达到12亿元人民币;TST002(Blosozumab)于2028年上市,年销售额峰值15亿元人民币。
年度
预测收入(百万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率
关键驱动因素
2024E
9.1
-83.0%
合作收入减少
2025E
11.4-11.6
25.0%
CDMO业务稳定
2026E
13.7
20.0%
早期管线里程碑
2027E
120.4
779.5%
TST001商业化启动
2028E
355.8
135.4%
TST001放量+TST002上市
收入结构的质变将深刻改变公司的财务特征和估值逻辑。2024-2026年,公司仍处于纯研发投入期,经营利润率低于-3000%,净利润率低于-5000%;2027年后,随着产品收入占比提升,毛利率有望从33%逐步改善至生物制药行业的典型水平(75%-85%),运营杠杆效应将推动亏损大幅收窄。尽管机构预测公司在未来3年内仍将保持亏损状态,但收入增速(50.1%年复合增长率)显著高于香港市场平均水平(8.4%),且2028年后有望实现盈亏平衡。对于长期投资者而言,当前估值尚未反映这一收入爆发期的期权价值。
1.2.3 全球多区域临床开发战略的执行能力
创胜集团的全球化能力是其区别于多数中国Biotech的关键特征。公司在美国普林斯顿和波士顿设有临床开发与战略合作枢纽,核心管理团队具有跨国药企(MNC)的丰富履历:钱雪明博士曾任安进(Amgen)首席科学家,主导多个抗体药物的开发;首席医学官Caroline Germa博士拥有20余年全球药物开发经验,曾在诺华、罗氏等企业担任高管职务。这种”中国创新+全球执行”的混合模式,使公司能够同步获取中美两大市场的监管资源和患者人群。
TranStar 301试验的多区域设计是这一能力的集中体现。该试验在中、美、韩三国同步入组,既加速了患者招募速度,也为未来全球注册申报奠定了基础。钱雪明博士在2024年7月透露,公司正处于与潜在全球战略合作伙伴谈判的最后阶段,合作方在胃肠道肿瘤领域具有强势地位和商业化能力。若该合作达成,将验证TST001的全球价值,同时为公司带来首付款、里程碑付款和销售分成等多重收益,显著改善现金流状况。
1.3 主要风险警示1.3.1 临床阶段生物制药企业的固有不确定性
作为临床阶段生物制药企业,创胜集团面临的最核心风险是III期临床失败的可能性。尽管Osemitamab的I/II期数据令人鼓舞,但历史经验表明,肿瘤药物的早期疗效并不总能转化为注册试验的成功——患者人群扩大、对照组选择、终点定义等因素均可能影响最终结果。根据行业统计,肿瘤药物从II期到III期的成功概率约为30%-40%,而III期到获批的成功率约为60%-70%。这意味着即使假设TST001的临床特征优于历史均值,仍存在不可忽视的负面情景。
此外,安全性信号的不可预测性也是重要风险因素。Claudin18.2靶点的正常组织表达(胃黏膜紧密连接)可能带来on-target、off-tumor毒性,Zolbetuximab在III期研究中报告了较高的恶心、呕吐发生率,影响了患者依从性。TST001虽在早期数据中显示出可管理的安全性特征,但更大规模、更长随访的III期数据仍是必要验证。
1.3.2 现金流消耗与融资需求的时间窗口
创胜集团的财务可持续性取决于现金储备与融资能力的平衡。根据2024年中期报告,公司借款为4200万元人民币,以5000万元银行存款作抵押,当日透支总额2.17亿元人民币。2022-2024年,公司年均经营现金消耗约3-4亿元人民币,按此速度推算,现有资金可支持约12-18个月运营。尽管2024年亏损幅度有所收窄(预计-2.752亿元人民币,较2023年的-4.628亿元改善),但TST001 III期试验的全面推进和潜在商业化准备将加速现金消耗。
融资时间窗口的紧迫性在于:若公司未能在2025-2026年完成新一轮融资或达成重大BD交易,可能面临运营资金短缺,被迫放缓临床进度或稀释现有股东权益。2021年IPO募集资金约5.534亿港元,但公司已多次变更资金用途,将资源向核心管线集中。这种灵活性虽体现了管理层的应变能力,也反映了早期规划与实际需求之间的偏差。投资者需密切关注公司的融资进展和现金跑道变化。
2. 公司历史沿革与全球布局演进
2.1 创立背景与发展里程碑2.1.1 2012年MabSpace Biosciences成立与早期技术积累
创胜集团的技术根基可追溯至2012年成立的MabSpace Biosciences(迈博斯生物),这是一家专注于抗体药物发现的生物技术公司,由钱雪明博士等科学家在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BioBAY)创立。成立之初,公司的核心使命是突破传统抗体发现技术在面对高难度靶点时的局限性,尤其是针对G蛋白偶联受体(GPCR)、离子通道等跨膜蛋白的抗体开发。通过建立免疫耐受突破平台和优化筛选流程,MabSpace在数年内积累了针对多个肿瘤相关靶点的先导抗体分子,为后续管线奠定了技术基础。
2015-2018年间,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经历了从”仿制药为主”向”创新药驱动”的关键转型。2015年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44号文)开启了药监改革序幕,2017年中国加入ICH(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标志着监管标准与国际接轨,2018年港交所18A上市规则的推出则为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打开了资本市场通道。这一系列政策红利为MabSpace的扩张创造了有利环境,公司在此期间完成了多轮私募融资,投资者包括知名风投机构和产业资本。
2.1.2 2019年Transcenta Holding整合与全球化重组
2019年是创胜集团发展史上的关键转折年。公司完成了对Transcenta Therapeutics的整合,形成覆盖”发现-开发-生产-商业化”全链条的国际化架构,并正式启用Transcenta Holding作为集团控股实体。这一重组的战略意图在于:一方面,通过收购或合并方式获取临床开发和CMC能力,弥补MabSpace作为纯发现平台的短板;另一方面,在美国建立临床运营团队,为参与全球多中心试验和吸引国际人才创造条件。
重组后的公司形成了”双总部”格局:苏州作为抗体发现和转化科学中心,杭州作为工艺开发和商业化生产基地,美国普林斯顿/波士顿作为全球临床开发和BD枢纽。这种布局既充分利用了中国在研发成本和制造效率方面的优势,又确保了与FDA等国际监管机构的直接沟通能力和全球临床试验的执行质量。2019-2020年,公司完成了B轮和C轮融资,累计募资超过1亿美元,为后续临床开发储备了资金。
2.1.3 2021年港交所18A上市与资本化进程
2021年9月,创胜集团成功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06628.HK,成为第18A章上市规则下的第49家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IPO发行价为每股16港元,募集资金净额约5.534亿港元,主要用于核心产品TST001和TST002的临床开发、生产能力建设及早期管线的持续推进。上市时的招股书详细披露了公司的管线布局、技术平台和财务规划,风险因素章节长达77页,充分体现了临床阶段企业的高不确定性特征。
然而,上市后的资本市场表现并未达到预期。受港股生物科技板块整体下行、公司临床进度慢于预期、以及未盈利属性在市场风险偏好下降时的估值压缩等多重因素影响,股价从发行价持续下跌,2022-2023年间一度跌破2港元,较发行价跌幅超过85%。这一表现既反映了市场对临床阶段企业的审慎态度,也为后续价值重估创造了条件——2024年下半年以来,随着Osemitamab III期数据读出和BD谈判进展的积极信号,股价逐步回升,2025年8月曾出现涨幅超500%的阶段性行情。
2.2 全球运营网络建设2.2.1 苏州:抗体发现与转化科学中心
苏州基地是创胜集团的技术创新引擎,位于苏州工业园区BioBAY B6-501,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该设施集抗体发现、蛋白工程、细胞功能研究和转化科学于一体,核心能力包括:杂交瘤和噬菌体展示抗体库构建、人源化和亲和力成熟、可开发性评估(developability assessment)、以及临床前药效和药代动力学研究。苏州团队与杭州CMC团队紧密协作,实现了从候选分子确定到IND申报的快速转化,典型周期为12-18个月,显著快于行业平均的24-36个月。
转化科学平台是苏州基地的特色能力,旨在通过生物标志物研究和患者分层策略,提高临床试验的成功率和效率。针对Osemitamab,公司开发了专有的Claudin18.2免疫组化检测方法,能够区分高、中、低表达水平,为临床数据解读和伴随诊断开发提供了关键工具。这种”药物+诊断”的协同开发模式,是精准医学时代肿瘤药物竞争的重要维度。
2.2.2杭州:工艺开发与商业化生产基地(HiCB平台)
杭州基地是创胜集团的生产制造核心,配备了符合中美欧GMP标准的中试和商业生产线,关键设施包括多个2000升一次性生物反应器和先进的纯化、灌装设备。该基地的最大技术特色是HiCB(High-intensity Continuous Bioprocessing)连续生产工艺平台,这是公司自主开发的下一代生物制造技术。
HiCB平台的核心创新在于将灌注培养(perfusion culture)与连续捕获色谱(continuous capture chromatography)相结合,实现从细胞培养到最终纯化的全流程连续操作。与传统批次工艺相比,HiCB具有三重优势:一是单位体积生产率提高2-3倍,相同设施产能下可支持更大规模商业化供应;二是产品质量一致性改善,连续操作减少了批次间变异;三是运营成本降低,更高效的原料利用和更小的设施footprint转化为显著的成本节约。对于Osemitamab这类预计峰值年需求达数百公斤级别的抗体药物,HiCB的成本优势将在商业化阶段体现为更高的毛利率和定价灵活性。
2.2.3美国普林斯顿/波士顿:全球临床开发与战略合作枢纽
美国运营基地是创胜集团全球化战略的关键支点。普林斯顿团队主要负责临床运营、监管事务和项目管理,与FDA保持直接沟通;波士顿团队则聚焦于商务拓展(BD)和战略合作,利用该地区密集的生物医药产业生态,寻找潜在合作伙伴和授权机会。这种”临床+BD”的双枢纽配置,使公司能够同步推进全球试验执行和外部合作谈判,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美国团队的另一个重要职能是人才吸引。公司首席医学官Caroline Germa博士等核心高管均具有美国顶尖药企的多年经验,他们的加入不仅提升了临床开发的专业水准,也为公司带来了国际监管网络和行业人脉。钱雪明博士在2024年采访中强调,拥有商业化合作伙伴对于加速患者入组和分担成本至关重要,公司正在与一家在胃肠道肿瘤领域具有强势地位的潜在伙伴进行最后阶段的谈判。若该合作达成,美国BD团队的贡献将得到验证。
2.3 2024-2025年战略转型与管理层更迭2.3.1钱雪明博士接任董事会主席兼CEO(2024年6月)
2024年6月,创胜集团宣布重大管理层调整:创始人钱雪明博士由首席科学官升任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原首席执行官赵奕宁博士转任董事会顾问。这一变动标志着公司从”科学家主导”向”创业者-管理者融合”模式的转型,钱雪明博士的双重角色既保证了技术愿景的连续性,也强化了战略决策和执行效率。
钱雪明博士的履历为这一转型提供了支撑。在创立MabSpace之前,他在安进工作近十年,参与和领导了多个抗体药物的发现项目,积累了针对免疫、肿瘤、代谢等疾病领域的深厚经验,尤其熟悉从靶点验证到候选分子确定的完整流程。2012年回国创业后,他将安进的技术方法论与中国创新生态相结合,逐步建立了创胜集团的技术平台和管线基础。2024年接任CEO后,他迅速推动了研发资源的优先级调整,将资金集中于Osemitamab和Blosozumab两大后期资产,同时暂缓或终止了部分早期项目的内部推进,以延长现金跑道。
2.3.2 首席财务官变更与财务管控优化
与CEO变动同步,公司在2024年完成了首席财务官的更迭,新任CFO具有更丰富的资本市场经验和融资能力。这一调整的直接背景是公司面临的现金流压力——2024年中期报告显示,流动比率从2022年的150%下降至85.3%,现金比率从89.3%下降至80.0%,负债权益比从30.8%上升至46.5%。新CFO的首要任务是优化资金管理、拓展融资渠道,并为潜在的BD交易提供财务支持。
财务管控优化的具体措施包括:更严格的研发预算审批流程、CDMO业务的收入最大化、以及运营支出的精细化管理。2024年公司自由现金流预计为-2.394亿港元,较2023年的-3.738亿港元改善35.9%,显示初步成效。然而,随着TST001 III期试验进入关键阶段和商业化准备启动,2025-2026年的现金消耗可能重新加速,融资能力的考验仍在持续。
2.3.3 研发资源优先级调整与管线聚焦策略
2024年的战略转型核心在于“聚焦”——将有限资源集中于最具价值的资产,而非分散于广泛早期探索。具体而言,公司明确了两层优先级:第一梯队为Osemitamab(TST001)和Blosozumab(TST002),分别针对肿瘤和骨科两大领域,均处于后期临床阶段,具有明确的商业化路径;第二梯队为TST003、TST004等早期资产,采取”里程碑驱动”的开发策略,仅在达成关键进展时追加投资。
这一策略的调整也反映在对外合作姿态上。公司明确表示,对于非核心管线,愿意通过对外授权(out-licensing)方式引入外部资源和分担风险,从而获得首付款、里程碑付款和销售分成。这种”选择性自主开发+选择性合作”的灵活模式,既保留了核心资产的控制权,又为早期资产的价值实现提供了路径。2024-2025年,中国生物科技行业的License-out交易热潮为公司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2025年第一季度,中国药企完成33项License-out交易,总交易价值366.3亿美元,同比增长258%。
3. 高管团队与治理结构分析3.1 核心管理层背景与能力评估
3.1.1钱雪明博士:安进背景下的抗体药物开发经验
钱雪明博士是创胜集团的灵魂人物,其职业轨迹贯穿了从跨国药企研发到本土创业再到上市公司管理的完整历程。他在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获得分子药理学博士学位,后进入安进公司(Amgen)工作近十年,历任科学家、高级科学家和首席科学家职位。在安进期间,他参与和领导了多个重磅抗体药物的发现项目,积累了针对免疫、肿瘤、代谢等疾病领域的深厚经验,尤其熟悉从靶点验证到候选分子确定的完整流程。
2012年,钱雪明博士回国创立MabSpace Biosciences,将安进的技术方法论与中国创新生态相结合。创业初期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持续投入高风险的抗体发现研究,并建立差异化技术平台。通过多轮私募融资和政府支持项目,MabSpace逐步证明了其技术能力,为2019年的整合重组和2021年的上市奠定了基础。2024年接任CEO后,他面临的新挑战是如何在资源约束下加速后期临床开发、达成关键BD交易,并为商业化转型做好准备——这与创业阶段的任务截然不同,需要更强的战略判断和执行纪律。
3.1.2 戚川博士(首席医学官)
戚川博士于2020年加入创胜集团,担任临床开发高级副总裁,后升任至首席医学官,全面负责全球临床开发、医学事务和药物警戒职能。戚川博士在中国创新药的临床开发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曾就职于罗氏、和记黄埔、礼来。他和所带领的团队先后成功推进多个关键产品在中国的获批上市,包括特罗凯、安维汀、帕捷特、安圣莎、赫赛莱和泰圣奇等。
3.1.3 技术高管团队的跨国药企经验矩阵
除钱雪明博士和Germa博士外,创胜集团的技术高管团队还包括多位具有跨国药企背景的专家。工艺开发高级副总裁张凡拥有超过 20 年的工艺开发经验 , 曾就职于安进、再生元;研发高级副总裁顾怡博士在新药发现和转化研究方面拥有丰富经验。曾就职于 Ambrx、阿斯利康。曾是辛辛那提儿童医院终身助理教授。曾作为 Howard Hughes 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在 Herman B Well 儿科中心开展工作。罗切斯特大学博士。肿瘤学特许经营战略高级副总裁庄文漪博士,复旦大学基因工程学士,哥伦比亚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莱斯大学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博士。
在肿瘤学领域的早晚期新产品开发、上市产品商业化和业务开发/收购的尽职调查与评估方面拥有超过20年的经验,曾在葛兰素史克、礼来担任肿瘤产品战略和业务发展、市场研究、国际营销和全球商业化的职位。代理首席财务官,高级副总裁,业务发展与企业战略梁尉蔚先生在生命科学和技术领域拥有超过20年的丰富经验,曾任百时美施贵宝业务发展高级总监,领导了变革性的合作和风险投资。在此之前,他还在诺华和拜耳担任过业务发展、商业战略和财务的关键职位。资本市场、投资者关系及企业传播高级副总裁Marciniak先生是国际生物制药领域的资深领导者。在加入创胜集团之前,他曾任职于ACELYRIN Inc,期间主导多项关键工作,助力该公司完成从私有企业到公众公司的转型,具体包括:支持规模达 3 亿美元的 C 轮融资、以全股票交易方式收购ValenzaBio、推动规模为 6.21 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发行,以及协助今年早些时候公司被Alumis Inc.收购的相关事宜。在此之前的2014年至2022年,他曾任职于安斯泰来制药集团,在运营与战略、投资者关系及企业传播部门历任多项职责逐步提升的职位,其中有五年在东京工作;2010年至2014年,他在辉瑞公司纽约总部任职。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金融专业工商管理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战略沟通专业理学硕士。
这种”MNC经验+本土实践”的团队构成,是创胜集团区别于多数中国Biotech的重要特征。其优势在于:能够直接应用国际最佳实践,减少试错成本;拥有与全球监管机构和KOL(关键意见领袖)的沟通渠道;在BD谈判中更容易获得跨国药企的信任和认可。潜在挑战则在于:高管薪酬成本高于纯本土团队;文化融合和决策效率需要持续磨合;以及在市场下行期,这类人才的职业选择灵活性可能更高。2024-2025年的管理层稳定性将是观察公司治理成熟度的关键指标。
3.2 董事会构成与独立性3.2.1 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与薪酬委员会架构
创胜集团董事会遵循香港上市公司治理守则的要求,设立了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三个关键委员会,各委员会均由独立董事担任主席,以确保决策的客观性和专业性。提名委员会负责董事和高管的遴选与继任计划,审计委员会监督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薪酬委员会制定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
这种三委员会架构是港股18A公司的标准配置,但其实际效能取决于独立董事的参与深度和管理层的信息披露透明度。2024年,公司根据上市规则要求,持续完善ESG(环境、社会与治理)披露,包括将气候风险纳入风险评估体系。根据2023年ESG报告,公司每年进行正式风险评估,涵盖战略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法律风险和气候风险等类别,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协调各部门跟进风险应对计划的实施。
3.2.2 独立董事的行业专长与监督效能
创胜集团董事会包括多位独立董事,其背景覆盖生物医药投资、临床医疗、公司治理等领域。这种多元化的专长组合,旨在为公司的战略决策提供多维度输入,并对管理层形成有效监督。然而,作为临床阶段企业,公司的技术决策高度专业化,独立董事能否充分理解并挑战管理层的科学判断,是治理效能的关键考验。
2024年管理层更迭后,董事会的稳定性受到市场关注。钱雪明博士由执行董事升任董事会主席,既强化了战略决策的一致性,也可能引发对权力集中度的担忧。理想的治理状态是:管理层在运营执行上保持高效,董事会在重大战略决策(如BD交易、融资安排、管线调整)上发挥实质性审议作用。投资者可通过股东大会投票情况、关联交易披露、以及ESG评级变化等信号,评估治理质量的演进。
3.3 管理层战略执行力评估3.3.1 全球III期临床启动与监管沟通能力
评估创胜集团管理层执行力的核心指标之一,是TranStar 301全球III期试验的推进效率。该试验于2023年下半年获得NMPA、FDA和MFDS的批准,2024年在中美韩三国同步启动患者入组,目标入组规模超过500例。与行业平均的跨国多中心试验启动周期(12-18个月)相比,这一进度显示了较强的执行能力。
监管沟通是另一关键维度。Osemitamab的开发涉及多个复杂议题:Claudin18.2表达水平的定义和检测方法、联合用药的剂量选择、以及潜在适应症的扩展路径。公司需要与FDA、NMPA等机构就这些议题达成监管共识,以确保试验设计和数据包能够满足获批要求。2024年ESMO数据的积极读出,为与监管机构的沟通提供了有力支持,但III期最终结果的披露和审评互动,将是更关键的考验。
3.3.2 潜在商业化合作伙伴谈判进展
钱雪明博士在2024年7月的采访中明确表示,公司正处于与潜在全球战略合作伙伴谈判的最后阶段,合作方在胃肠道肿瘤领域具有强势地位和商业化能力。这一信息披露本身具有信号意义——在BD谈判的敏感阶段,管理层愿意公开讨论进展,通常意味着对达成交易的信心。
潜在合作的结构可能包括:首付款(upfront payment)用于补充公司现金流,里程碑付款(milestone payments)与监管获批和销售目标挂钩,以及分层销售分成(tiered royalties)。参考2024-2025年中国生物科技行业的BD交易先例,针对后期临床阶段肿瘤抗体的授权,首付款通常在5000万美元至2亿美元区间,总交易价值(含里程碑)可达10亿美元以上。若创胜集团能够达成类似水平的交易,将显著改善其财务状况,并验证Osemitamab的全球价值。
4. 研发管线深度解析4.1 整体管线布局与战略优先级4.1.1 16个创新分子的治疗领域分布(肿瘤/骨科/肾病/自免)
截至2025年初,创胜集团拥有16个创新分子,形成覆盖肿瘤、骨科、肾病及自体免疫疾病的治疗领域布局。这一管线的战略设计体现了”聚焦大适应症、构建协同效应”的思路:肿瘤是核心领域,占管线数量的一半以上,且包含后期临床资产Osemitamab;骨科(以TST002为代表)和肾病/自免(以TST004等为代表)则是差异化扩展方向,利用公司在抗体工程方面的平台能力,针对具有未满足医疗需求的慢性病领域。
管线的分子类型以单克隆抗体为主,同时包括双特异性抗体、抗体偶联药物(ADC)等新兴格式。这种多样性既反映了技术平台的延展性,也为未来联合治疗和产品升级提供了选项。例如,针对Claudin18.2靶点,除Osemitamab单抗外,公司还在探索ADC格式的开发可能性,以应对潜在的竞争压力和耐药机制。
4.1.2 自主发现比例与外部引进策略的平衡
创胜集团管线的显著特征是自主发现比例高——超过70%的分子来源于内部抗体发现平台,而非外部引进或授权。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知识产权完全自主,不受第三方许可协议的约束;对分子设计和开发路径有完全控制权,便于优化和迭代;早期成本较低,避免了高额首付款支出。
然而,完全自主模式也面临挑战:开发风险完全由公司承担,无合作伙伴分担;需要持续投入平台建设,固定成本较高;在某些专业领域(如ADC linker-payload技术),外部合作可能更高效。公司的应对策略是”核心自主、边缘合作”——对Osemitamab、TST002等战略资产保持完全控制,对早期项目或非核心领域探索对外授权或合作开发机会。2024年从礼来引进的Blosozumab全套研发技术,是这一策略的例外——该资产具有明确的后期临床数据和监管路径,引进风险可控,且与公司自主开发的骨科管线形成协同。
4.1.3 管线梯队:后期临床、早期临床与临床前项目配置
从开发阶段看,创胜集团管线形成三个梯队:第一梯队为后期临床资产,包括Osemitamab(全球III期)和Blosozumab(II期准备/启动);第二梯队为早期临床资产,包括TST003(I期)、TST004(I期)等;第三梯队为临床前项目,涵盖多个针对新靶点或新格式的探索性分子。
这种梯队配置的风险收益特征明显:第一梯队决定了公司未来3-5年的商业化前景和现金流状况,是价值的核心来源;第二梯队提供了5-10年的增长期权,成功后可扩展治疗领域或升级产品组合;第三梯队则是技术平台的产出验证,其价值更多体现在对外授权潜力而非内部开发。2024年的战略调整强化了第一梯队的资源优先级,第二、三梯队的推进节奏则更加依赖里程碑触发和外部合作机会。
4.2 核心产品一:Osemitamab(TST001)4.2.1 靶点机制与差异化设计4.2.1.1 Claudin18.2的肿瘤生物学特征与表达谱
Claudin18.2是紧密连接蛋白Claudin-18的剪接变体,在正常组织中仅表达于胃黏膜上皮细胞的紧密连接,而在多种实体瘤中呈现异常表达和暴露。其肿瘤生物学特征包括:在胃癌中的表达率约为50%-70%,其中高表达(≥75%肿瘤细胞阳性)约占30%-40%;在胰腺癌中的表达率约为50%;在食管癌、肺癌、卵巢癌等瘤种中也有一定比例的表达。这种表达谱使Claudin18.2成为消化道肿瘤免疫治疗的理想靶点——正常组织表达受限降低了系统性毒性风险,肿瘤特异性表达提供了治疗窗口。
Claudin18.2的致癌机制涉及多个层面:作为紧密连接成分,其异常表达破坏细胞间连接,促进肿瘤侵袭和转移;通过与整合素等分子的相互作用,激活PI3K/AKT、MAPK等信号通路,支持肿瘤细胞增殖和存活;在肿瘤微环境中,Claudin18.2的表达与免疫抑制特征相关,可能影响免疫治疗响应。这些机制为靶向抗体的抗肿瘤活性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提示了与化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联合应用的合理性。
4.2.1.2 人源化抗体结构与ADCC效应增强
Osemitamab是一种人源化IgG1单克隆抗体,通过Fc工程化改造增强了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ADCC)效应。其分子设计的关键特征包括:可变区来源于免疫耐受突破平台筛选的高亲和力克隆,能够特异性结合Claudin18.2的近膜端表位;恒定区采用人IgG1骨架,并通过糖基化优化(如去岩藻糖化)增强与FcγRIIIa的结合,从而强化NK细胞介导的ADCC效应。
ADCC效应的增强是Osemitamab差异化设计的核心。与Zolbetuximab(嵌合抗体,ADCC效应相对较弱)相比,TST001在体外和体内模型中均显示出更强的肿瘤细胞杀伤活性,尤其是在Claudin18.2中低表达的细胞系中仍保持显著活性。这一特征具有重要的临床转化意义:由于肿瘤异质性和检测方法差异,临床实践中Claudin18.2”高表达”与”中低表达”的界限并非绝对,能够在更宽表达范围内保持活性的抗体,可能覆盖更大的适用人群。
4.2.1.3与Zolbetuximab的分子设计对比
上表总结了Osemitamab与Zolbetuximab的关键差异。最显著的区分点在于Claudin18.2特异性:Zolbetuximab的抗体结合细胞内共享结构域,无法区分18.2与18.1两种剪接变体,这在肺癌等两种变体共表达的瘤种中限制了应用;而TST001的表位选择使其能够特异性识别18.2,为肺癌等适应症的扩展创造了条件。此外,Fc工程化带来的ADCC增强,可能转化为更优的疗效特征,但最终确认需等待III期头对头或间接比较数据。
4.2.2 临床开发进展与数据解读4.2.2.1 TranStar 101/102:I/II期剂量探索与安全性确立
TranStar 101和102是Osemitamab的早期临床开发试验,分别在中国和全球多中心开展,旨在确定推荐II期剂量(RP2D)、评估安全性和初步疗效,并为III期试验设计提供依据。101试验采用传统的3+3剂量递增设计,探索了从0.3 mg/kg到15 mg/kg的多个剂量水平;102试验则在RP2D基础上扩展队列,重点评估联合用药方案。
关键安全性发现包括:单药治疗时,最常见的不良事件为恶心、呕吐、食欲下降等胃肠道症状,多数为1-2级,与Claudin18.2在正常胃黏膜的表达一致;3级及以上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20%,未观察到剂量限制性毒性(DLT)或治疗相关死亡;联合化疗和免疫治疗时,安全性特征与单药及背景治疗已知风险相符,未发现新的安全信号。这些结果为III期试验的剂量选择和风险管控提供了基础。
4.2.2.2 TranStar 301:全球III期关键性试验设计(NMPA/FDA/MFDS批准)
TranStar 301是Osemitamab的注册性III期试验,于2023-2024年间获得中国NMPA、美国FDA和韩国MFDS的批准,在中美韩三国同步开展。试验设计为随机、开放标签、活性对照,评估Osemitamab联合纳武利尤单抗和CAPOX方案,对比安慰剂联合相同方案,用于Claudin18.2阳性、HER2阴性晚期胃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的一线治疗。主要终点为总生存期(OS),关键次要终点包括无进展生存期(PFS)、客观缓解率(ORR)、缓解持续时间(DoR)和安全性。
试验设计的几个关键选择值得分析:首先,采用”三药联合”(靶向+免疫+化疗)而非”双药联合”,是基于TranStar 102 G队列的积极数据,旨在追求最优疗效而非最小毒性;其次,以OS而非PFS作为主要终点,虽延长了试验时间和样本量要求,但提供了更直接的临床价值证据,有利于监管获批和后续医保谈判;第三,全球多中心设计为中美同步注册申报奠定基础,但也增加了运营复杂性和成本。截至2024年底,试验处于患者入组阶段,预计2025-2026年读出中期数据,2026-2027年获得最终OS数据。
4.2.2.3 2024年ESMO/2025年ASCO最新数据:ORR 68%,mPFS 14.2个月
2024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年会上,创胜集团公布了TranStar 102 G队列的最新数据,这是支持III期试验设计的关键证据。G队列评估Osemitamab联合纳武利尤单抗和CAPOX作为晚期胃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一线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更新数据显示:
指标
数据
临床意义
确认客观缓解率(ORR)
68%(45/66例)
胃癌一线治疗领域顶尖水平
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
14.2个月
显著优于化疗+免疫历史数据(7-8个月)
疾病进展/死亡风险降低(HR)
0.505
强劲临床获益幅度
PD-L1亚组分析
无论PD-L1表达均显示活性
扩展潜在适用人群
这些数据的多重意义在于:首先,68%的ORR和14.2个月的mPFS在胃癌一线治疗领域属于顶尖水平,优于现有标准治疗(化疗+免疫)和Zolbetuximab联合化疗的历史数据;其次,HR=0.505提示了强劲的临床获益幅度,若III期试验能复制这一效应,获批概率较高;第三,PD-L1非依赖性活性扩大了潜在适用人群,因为约40%-50%的胃癌患者PD-L1 CPS<5,对单纯免疫治疗响应有限。当然,这些数据的局限性也需承认:单臂设计、样本量有限(n=66)、随访时间相对较短,最终结论需等待III期随机对照试验验证。
4.2.3 适应症扩展策略4.2.3.1 一线胃癌/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核心适应症)
一线胃癌/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是Osemitamab的核心适应症,也是TranStar 301试验的目标人群。该适应症的临床需求明确:胃癌是全球第五大常见癌症,中国每年新发病例约48万,占全球近一半;晚期患者5年生存率不足10%,现有标准治疗(化疗±免疫治疗)的mOS约为12-16个月,存在显著改善空间。Claudin18.2阳性(高/中表达)患者约占晚期胃癌的40%-50%,对应中国每年约10-15万潜在患者,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之一。
市场渗透的关键成功因素包括:监管获批时间、医保纳入进度、医生教育深度、以及竞争格局演变。假设TST001于2027年初在中国获批,首年产生1.04亿元收入,随后通过医保谈判实现快速放量,销售峰值可达12亿元人民币。这一预测基于以下假设:定价策略参考Zolbetuximab(美国年治疗费用约15万美元,中国可能显著降低)、市场份额在Claudin18.2阳性患者中达到20%-30%、以及适应症扩展至围手术期治疗。
4.2.3.2 围手术期胃癌治疗(术前新辅助/术后辅助)
围手术期治疗是Osemitamab适应症扩展的重要方向,可覆盖额外30%-40%的胃癌患者。当前标准治疗模式下,可手术切除的局部晚期胃癌患者接受术前新辅助化疗,术后辅助化疗或放化疗,但复发率仍高达40%-60%。在化疗基础上加入Claudin18.2靶向抗体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有望提高病理完全缓解(pCR)率,延长无病生存期(DFS)和总生存期。
钱雪明博士指出,围手术期治疗的临床价值在于:术前缩小肿瘤可提高R0切除率,术后清除残留微转移灶可降低复发风险,最终目标是实现更长久的疾病控制甚至治愈。公司正在设计针对这一适应症的临床试验,可能采用与TranStar 301相似的联合方案,但终点选择(pCR、DFS vs. OS)和试验周期将根据监管反馈优化。若该适应症获批,TST001的适用人群将显著扩展,因为早期患者数量多于晚期,且治疗持续时间更长(围手术期数月至1年,vs. 晚期持续至进展)。
4.2.3.3 胰腺癌(~50% Claudin18.2表达率)
胰腺癌是Osemitamab最具潜力的扩展适应症之一,约50%的胰腺肿瘤表达Claudin18.2,而现有治疗选择极为有限。晚期胰腺癌的一线标准治疗为吉西他滨联合白蛋白紫杉醇,mOS仅约8-12个月,5年生存率不足10%,是预后最差的实体瘤之一。免疫治疗在胰腺癌中几乎无效(MSI-H患者除外),靶向治疗也缺乏有效靶点,Claudin18.2因此成为备受关注的突破方向。
胰腺癌临床开发的挑战在于:肿瘤微环境高度免疫抑制,药物渗透困难;患者体能状态差,耐受联合治疗的能力有限;早期诊断困难,多数患者确诊时已为晚期。Osemitamab在胰腺癌中的开发策略可能包括:与标准化疗联合的初步探索、生物标志物驱动的患者筛选、以及针对特定亚群(如Claudin18.2高表达、体能状态较好)的优化设计。该适应症的临床价值极高——若能在胰腺癌中显示生存获益,将显著扩展TST001的市场空间,并可能获得加速审批或突破性疗法认定。
4.2.3.4 肺癌(Claudin18.2特异性检测优势)
肺癌是Osemitamab适应症扩展的差异化方向,其核心优势在于公司专有检测方法的特异性。Claudin18.2在肺癌中的表达率约为10%,但Claudin18.1在正常肺组织中也有表达,两种变体的区分对于准确筛选患者至关重要。Zolbetuximab的伴随诊断由于结合共享细胞内结构域,无法区分18.2与18.1,在肺癌中的应用受到限制;而TST001的检测方法能够特异性识别18.2,为肺癌适应症的精准开发提供了技术基础。
肺癌市场的规模远超胃癌——中国每年新发肺癌病例约80万,全球超过200万,是肿瘤药物最大的单一适应症。若Osemitamab能在Claudin18.2阳性肺癌中显示疗效,即使仅覆盖10%的患者群体,潜在市场也将显著扩大。开发策略上,公司可能选择特定组织学亚型(如腺癌)或分子亚群(如EGFR/ALK野生型)进行初步探索,以优化获益风险比。该适应症的临床开发尚处于早期规划阶段,但代表了TST001长期价值的重要增长期权。
4.2.4 联合治疗探索4.2.4.1 Osemitamab+纳武利尤单抗+CAPOX(G队列数据)
TranStar 102 G队列的联合方案设计基于多重机制考量:Osemitamab靶向Claudin18.2阳性肿瘤细胞,直接杀伤并释放肿瘤抗原;纳武利尤单抗阻断PD-1/PD-L1通路,激活T细胞抗肿瘤免疫;CAP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化疗提供细胞毒作用,并可能通过免疫原性细胞死亡增强抗肿瘤免疫。这种”靶向+免疫+化疗”的三联模式,旨在实现不同机制的协同增效。
G队列的积极数据(ORR 68%,mPFS 14.2个月)验证了这一策略的可行性,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三药联合的毒性是否可管理?各成分的贡献如何区分?是否所有患者都需要完整三联,还是可以根据生物标志物分层?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影响III期试验的解读和后续临床实践的优化。例如,若PD-L1 CPS阴性患者也能从三联方案中获益,则PD-L1检测的必要性降低;若Claudin18.2表达水平与疗效密切相关,则伴随诊断的优化将成为关键。
4.2.4.2 与放疗联合的临床1b期探索
除化疗和免疫治疗外,公司还在探索Osemitamab与放疗联合的可能性。放疗的免疫调节效应——包括肿瘤抗原释放、MHC-I上调、T细胞浸润增加——可能与Claudin18.2靶向抗体产生协同。这一联合在局部晚期胃癌的围手术期治疗、或胰腺癌的局部控制中可能具有应用价值。相关试验处于早期设计阶段,具体方案和目标人群有待披露。
4.2.4.3 无论PD-L1表达的广谱活性证据
2024年ESMO数据中最具战略价值的发现之一,是TST001显示出”无论PD-L1表达如何”的广谱活性。这一特征在胃癌治疗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当前PD-1抑制剂在PD-L1低表达患者中的疗效有限,而Claudin18.2作为替代或补充的生物标志物,可能定义一个更广泛的免疫治疗获益人群。
若TranStar 301试验能够验证这一发现,TST001的commercial positioning将显著强化——不仅是Claudin18.2阳性患者的治疗选择,更是拓展免疫治疗获益边界的关键工具。这一价值主张的传达,需要伴随诊断的推广、临床教育的投入和真实世界证据的积累。
4.3 核心产品二:Blosozumab(TST002)4.3.1 硬骨素(Sclerostin)靶点机制与成骨/抑骨双重效应
Blosozumab(TST002)是创胜集团从礼来公司引进的抗硬骨素(Sclerostin)单克隆抗体,公司获得了该产品在亚洲地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权益。硬骨素是由骨细胞分泌的Wnt信号通路抑制因子,其生理作用是负向调控骨形成。靶向抑制硬骨素,可解除对成骨细胞的抑制、促进骨基质蛋白的合成和矿化,同时硬骨素对破骨细胞的间接抑制作用可降低骨吸收,从而实现”促骨形成+抑骨吸收”的双重效应。
这一机制在骨质疏松症治疗中具有独特价值:当前主流药物中,双膦酸盐和地诺单抗(RANKL抗体)仅抑制骨吸收,对骨形成的促进作用有限;特立帕肽(甲状旁腺素类似物)虽可促进骨形成,但需要每日注射且疗程受限(不超过2年)。硬骨素抗体的双重机制理论上可实现更高的骨密度增益和更持久的疗效,且给药频率较低(每4周或每12周一次),患者依从性更优。
4.3.2礼来引进资产的开发进度与知识产权布局
TST002的引进交易是创胜集团外部合作策略的典型案例。根据披露信息,公司获得了礼来关于Blosozumab的全套研发技术,包括细胞系、生产工艺、临床前和临床数据包,以及相关的专利和专有技术许可。这一”技术转移”型合作,相较单纯的权益引进,赋予公司更大的自主开发灵活性和长期价值捕获空间。
礼来原研的Blosozumab临床开发曾因早期试验中的安全性信号(注射部位反应和心血管事件疑虑)而暂停,但后续分析未确认明确的因果关系,且骨密度疗效数据积极。创胜集团的开发策略需要在这一背景下审慎推进:充分利用礼来的现有数据支持监管沟通,同时设计针对性的安全性监测方案以回应历史关切。
知识产权布局方面,硬骨素靶点的核心专利由礼来持有,创胜集团的权益受限于亚洲地区。公司需要关注专利到期时间(预计2020年代末至2030年代初)和可能的专利延长策略,评估仿制药竞争的时间窗口。
4.3.3骨质疏松症市场定位与2028年上市预期
根据软库中华证券的预测,TST002有望于2028年在中国上市,峰值年销售额达到15亿元人民币。这一预测的关键假设包括:桥接试验或关键性试验于2025-2026年启动,2027年完成并提交上市申请,2028年获得批准;定价策略参考地诺单抗等生物制剂,年治疗费用约为2-3万元;目标患者人群为高风险骨质疏松症患者(既往骨折史、骨密度T值<-2.5、或FRAX评分高风险),渗透率逐步提升至5-10%。
市场竞争格局方面,地诺单抗的生物类似药已于2023-2024年在中国陆续上市,价格竞争压力显著;特立帕肽的每日注射剂型依从性受限,但周制剂正在开发中。TST002的差异化定位需要强调其双重机制带来的更高疗效潜力,以及更低给药频率的便利性优势。若能在头对头试验中显示出优于地诺单抗的骨密度增益或骨折风险降低,将建立强有力的临床价值主张。
4.4 早期创新管线4.4.1 TST003:GREMLIN-1靶向肿瘤微环境调控
TST003是创胜集团自主发现的靶向GREMLIN-1的单克隆抗体,处于早期临床开发阶段。GREMLIN-1是BMP(骨形态发生蛋白)信号通路的抑制因子,在多种肿瘤的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F)中高表达,参与肿瘤微环境的免疫抑制和基质重塑。靶向GREMLIN-1的理论价值在于:调控肿瘤微环境以增强免疫治疗敏感性、抑制肿瘤转移和耐药、以及与CLDN18.2等靶点形成协同。
该项目的开发风险在于靶点的临床验证程度较低——目前尚无GREMLIN-1靶向药物获批上市,早期临床试验的疗效信号存在不确定性。创胜集团的策略可能是:在特定瘤种(如胃癌、胰腺癌,与TST001的适应症重叠)中进行探索,评估与TST001的联合潜力;或寻求对外合作,由合作伙伴承担部分开发风险和成本。
4.4.2 TST004:MASP2补体通路抑制(肾病/自免)
TST004靶向MASP2(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丝氨酸蛋白酶2),是补体凝集素通路的关键酶。补体系统的过度激活参与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肾脏疾病的发病机制,包括IgA肾病、狼疮性肾炎、血栓性微血管病等。MASP2抑制可选择性阻断凝集素通路,而不影响经典通路和替代通路的免疫功能,理论上具有更好的安全性特征。
该项目的竞争格局包括:Omeros公司的Narsoplimab已获批用于造血干细胞移植相关血栓性微血管病,正在探索其他适应症;诺华的Iptacopan(补体因子B抑制剂)在IgA肾病中显示出积极数据。TST004的差异化空间在于其MASP2靶点的特异性,以及在中国高发肾病(如IgA肾病)中的开发优先级。
4.4.3 TST006/TST010/TST012:新兴靶点布局
创胜集团的早期管线还包括多个尚未披露详细靶点信息的项目,覆盖肿瘤免疫、自身免疫和代谢疾病等领域。这些项目的战略价值在于:为公司的长期增长提供期权价值、在平台技术验证和对外合作中作为筹码、以及响应新兴科学发现快速跟进。2024年的战略调整后,这些项目的推进节奏更加依赖外部合作机会和里程碑触发,内部资源投入相对有限。
4.5 技术平台竞争力4.5.1 抗体发现平台:免疫耐受突破与成药性优化
创胜集团的抗体发现平台核心技术为免疫耐受突破(Immune Tolerance Breaking, ITB)策略,旨在提高针对高难度靶点(如GPCR、离子通道、紧密连接蛋白等)的抗体成药性。传统抗体发现方法在面对高度保守或免疫原性较弱的靶点时,往往难以产生高亲和力、高特异性的候选分子。ITB平台通过优化免疫方案、筛选策略和体外成熟技术,突破了这一瓶颈,为Osemitamab等核心产品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平台的另一关键能力是成药性评估(developability assessment)——在候选分子早期即对其理化性质、稳定性、生产可行性和潜在免疫原性进行系统评价,降低后期CMC阶段的失败风险。这一能力使公司能够在项目启动阶段即筛选出最具开发潜力的分子,提高整体研发效率。
4.5.2 一体化CMC能力:从DNA到IND的快速转化
创胜集团的CMC能力覆盖从DNA序列确定到IND申报的全流程,关键模块包括:细胞系开发和建库、上游工艺开发(培养基优化、反应器参数)、下游纯化工艺(层析、过滤、病毒清除)、分析方法开发和验证、以及稳定性研究和制剂开发。历史项目数据显示,公司平均IND准备周期为12-18个月,显著快于行业平均的24-36个月。
这一效率优势来源于多个因素:苏州与杭州团队的紧密协作,减少了技术转移的时间和沟通成本;自主掌控关键设备和耗材,避免了外部供应商的排期限制;以及平台化方法的应用,使不同项目间能够共享优化经验和标准操作。快速转化能力对于竞争激烈的靶点(如Claudin18.2)尤为重要——率先进入临床意味着更长的市场独占期和更大的BD谈判筹码。
4.5.3 HiCB连续生产工艺:成本优势与质量一致性
HiCB(High-intensity Continuous Bioprocessing)是创胜集团最具前瞻性的技术投资,代表生物制药生产的下一代方向。该平台的核心创新包括:
技术特征
传统批次工艺
HiCB连续工艺
优势量化
生产模式
批次补料,数周周期
灌注培养+连续捕获,数天周期
周期缩短50%-70%
细胞密度
10-20×10⁶ cells/mL
>100×10⁶ cells/mL
提高5-10倍
体积生产率
基准
提高2-3倍
设施产能等效扩大
产品质量
批次间变异较大
更一致的关键质量属性
降低放行风险
资本支出
基准
降低约40%
同等产能下
运营成本
基准
降低约30%
原料利用效率提升
基于公司披露和行业基准的综合估算
HiCB平台的技术经济性对于Osemitamab的商业化成功具有战略意义。生物类似药竞争加剧的未来市场环境中,生产成本优势将直接转化为定价灵活性和毛利率空间。公司杭州基地已完成HiCB平台的GMP验证,具备承接商业化生产的能力,也为潜在的CDMO业务拓展提供了技术差异化。
5. 核心产品市场潜力量化评估5.1 胃癌治疗市场分析5.1.1全球与中国流行病学:发病率、分期分布、未满足需求
胃癌作为全球第五大常见恶性肿瘤及第四大癌症致死原因,构成了沉重的公共卫生负担,同时也为靶向治疗药物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机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胃癌发病病例预计将从2018年的103万例增长至2025年的124万例,年复合增长率约为2.7%。这一增长趋势主要由人口老龄化、饮食习惯西化以及幽门螺杆菌感染率的区域差异所驱动。
从地理分布来看,亚太地区占据了全球胃癌病例的绝对主导地位,其中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合计贡献了超过60%的全球发病人数。具体而言,中国在2018年记录了约456,124例新发胃癌病例,位居全球首位;日本同期发病率为115,546例;而美国虽然发病率相对较低,但2019年仍有约27,510例新发病例。
从疾病分期角度分析,胃癌的临床预后与诊断时分期密切相关。早期胃癌(I-II期)患者的5年生存率可达90%以上,而晚期或转移性胃癌(IV期)患者的5年生存率则骤降至5%-20%。然而,由于胃癌早期症状隐匿且缺乏高效的筛查手段,临床上约60%-70%的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阶段,这直接限制了根治性手术的应用范围,并使系统治疗成为主要的治疗手段。当前晚期胃癌的一线标准治疗仍以铂类-氟尿嘧啶双药化疗为基础,对于HER2阳性患者(约占15%-20%)可联合曲妥珠单抗,而PD-L1 CPS≥5的患者则可考虑加入PD-1抑制剂。尽管如此,中位总生存期(OS)仍仅为12-16个月,客观缓解率(ORR)约为40%-50%,临床未满足需求极为迫切。
Claudin18.2作为近年来胃癌靶向治疗领域最具突破性的新兴靶点,其表达特征与临床价值已得到广泛验证。该靶点在正常组织中仅表达于胃黏膜上皮细胞的紧密连接处,而在恶性转化后,其表达模式发生改变,暴露于肿瘤细胞表面,成为理想的抗体药物作用靶点。流行病学研究显示,约35%-40%的胃癌患者呈现Claudin18.2阳性表达(定义为≥40%肿瘤细胞中强度≥2+),这一比例在弥漫型胃癌和亚洲人群中可能更高。值得注意的是,Claudin18.2表达与HER2状态基本互斥,这意味着Claudin18.2靶向治疗可为占胃癌患者多数(约80%)的HER2阴性人群提供全新的精准治疗选择,显著扩展了靶向治疗的受益人群。
5.1.2 现有治疗范式:化疗、免疫治疗、靶向治疗的演进
胃癌系统治疗在过去十年经历了从单纯化疗到靶向治疗、再到免疫联合治疗的范式转变,治疗选择的丰富化显著改善了患者预后,但同时也对临床决策和新药开发提出了更高要求。化疗时代以氟尿嘧啶类(5-FU、卡培他滨)、铂类(顺铂、奥沙利铂)和紫杉类(紫杉醇、多西他赛)药物为核心,FOLFOX、XELOX、SOX等方案成为亚洲地区的主流选择。然而,化疗的疗效天花板明显,且毒性反应限制了长期应用。
2010年,ToGA研究确立了曲妥珠单抗在HER2阳性胃癌中的一线地位,首次将靶向治疗引入胃癌临床实践,但HER2阳性人群的局限性使这一突破的受益范围受到制约。免疫治疗的兴起为胃癌治疗带来了新的变革。2017年,KEYNOTE-059研究首次证实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在PD-L1阳性晚期胃癌中的活性;随后,CheckMate-649研究确立了纳武利尤单抗(Nivolumab)联合化疗在PD-L1 CPS≥5患者中的一线标准地位。2025年3月,FDA批准帕博利珠单抗联合曲妥珠单抗和化疗用于HER2阳性胃癌一线治疗,将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从7.3个月提升至10.9个月,进一步巩固了免疫联合策略的治疗地位。然而,免疫治疗同样面临PD-L1表达依赖性、原发性/继发性耐药以及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等挑战,且整体疗效提升幅度仍不足以满足临床需求。
在此背景下,Claudin18.2靶向治疗的出现被视为胃癌精准医疗的下一个重大突破。2024年3月,安斯泰来的Zolbetuximab(商品名Vyloy)在日本获批,成为全球首个上市的Claudin18.2靶向药物,随后于2024年9月、10月和12月相继获得欧洲EMA、美国FDA和中国NMPA的批准,用于Claudin18.2阳性、HER2阴性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胃癌/胃食管结合部腺癌的一线治疗。Zolbetuximab的获批基于SPOTLIGHT和GLOW两项全球III期研究,结果显示该联合化疗可显著延长mPFS和总生存期(OS),确立了Claudin18.2作为胃癌治疗新生物标志物的临床价值。这一里程碑事件不仅验证了靶点的成药性,也为后续竞争者包括创胜集团的TST001提供了监管路径参考和市场教育基础。
5.1.3 Claudin18.2阳性患者筛选与伴随诊断市场
伴随诊断(Companion Diagnostic, CDx)是Claudin18.2靶向治疗商业化成功的关键基础设施,其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目标患者的识别效率和药物的市场渗透速度。目前,Claudin18.2表达的检测主要依赖免疫组织化学(IHC)方法,VENTANA CLDN18 RxDx Assay作为Zolbetuximab的伴随诊断试剂已于2024年7月获得欧盟批准,并正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该检测将Claudin18.2阳性定义为≥40%肿瘤细胞呈现中等或强膜染色(≥2+),这一阈值与临床试验中的入组标准一致,但也引发了关于更低表达阈值患者潜在受益的科学讨论。
创胜集团在伴随诊断领域进行了前瞻性布局,其自主开发的Claudin18.2检测方法具有高特异性和灵敏度,能够支持更广泛的临床应用。根据公司披露,TST001的临床开发策略包括探索在更低Claudin18.2表达水平患者中的活性,这一差异化定位有望将受益人群从传统的38%(高/中表达)扩展至55%的胃癌患者,显著扩大可及市场。伴随诊断的普及和标准化是这一策略成功的前提,公司需要与诊断合作伙伴、病理实验室和支付方密切协作,建立检测可及性和报销覆盖,以支持产品的市场渗透。从市场规模角度,全球伴随诊断市场预计将以15%-20%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肿瘤领域是核心驱动力,Claudin18.2检测作为新兴细分市场具有可观的增长潜力。
5.2 TST001市场渗透模型5.2.1 目标患者人群细分(一线/二线/围手术期)
TST001的市场渗透策略需要基于胃癌治疗的临床路径和患者流进行精细化设计,核心适应症的定位和扩展顺序将直接影响产品的峰值销售潜力和生命周期价值。从治疗线数角度,一线晚期/转移性胃癌是TST001的首要目标市场,也是当前临床开发的核心焦点。这一策略选择基于多重考量:首先,一线治疗是患者接受系统治疗的起始点,市场容量最大且患者依从性最高;其次,一线治疗的疗效数据直接影响后续线数的用药选择和医生认知;第三,Zolbetuximab已在全球主要市场获批一线适应症,为TST001提供了明确的监管对标和临床开发路径。
根据创胜集团的临床开发计划,TST001在一线胃癌/胃食管结合部腺癌(G/GEJC)中的定位是“三联疗法”——即Osemitamab联合PD-1抑制剂(纳武利尤单抗)和化疗(CAPOX),这一策略与Zolbetuximab的”双联疗法”(联合单纯化疗)形成差异化。2024年ESMO和2025年ASCO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三联方案在Claudin18.2高/中表达且已知PD-L1 CPS的患者中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疗效:确认客观缓解率(ORR)达68%,mPFS为14.2个月。这些数据为TST001的同类最优(Best-in-Class)定位提供了初步证据,也支持其在全球III期关键性试验(TranStar 301)中的进一步验证。
除一线晚期适应症外,围手术期胃癌治疗是TST001的重要扩展方向。围手术期治疗包括术前新辅助治疗和术后辅助治疗,其目标是提高手术切除率、降低复发风险并最终改善长期生存。当前围手术期胃癌的标准治疗以化疗为主,但疗效仍有提升空间,免疫治疗在这一领域的探索正在积极进行中。创胜集团已启动TST001联合放化疗用于围手术期胃癌的临床研究,若取得阳性结果,将显著扩展产品的适用人群和治疗时长,因为围手术期患者通常具有更好的体能状态和更长的预期生存,治疗持续时间可达6-12个月,而晚期患者的中位治疗持续时间通常仅为4-6个月。此外,围手术期治疗的治愈导向属性也可能支持更高的定价空间和支付意愿。
二线及以上治疗是TST001的另一个潜在市场,尽管当前临床开发优先级相对较低。对于一线治疗后进展的患者,目前的治疗选择有限且疗效不佳,Claudin18.2靶向治疗作为后续线数的应用具有理论合理性,尤其是考虑到TST001在更低表达阈值中的潜在活性。然而,这一市场的开发需要等待一线适应症的获批和更多安全性数据的积累,同时也面临其他Claudin18.2靶向药物(如ADC、双抗等)的竞争。
5.2.2峰值销售预测:中国胃癌适应症12亿元人民币
基于上述市场细分和临床开发进度,软库中华研究报告对TST001在中国胃癌适应症的销售峰值给出了12亿元人民币的预测。这一预测的建立需要拆解其核心假设和计算逻辑,以评估其合理性和敏感性。
首先,从患者流角度,中国每年新发胃癌约48万例,其中约80%为HER2阴性,即约38.4万例潜在目标人群。在这些HER2阴性患者中,假设Claudin18.2高/中表达(≥40%, ≥2+)比例为38%,则一线晚期目标患者约为14.6万例;若TST001的更低表达阈值策略成功,将比例提升至55%,则目标患者可扩展至21.1万例。考虑到诊断渗透率、治疗可及性和市场竞争等因素,假设TST001在目标患者中的市场渗透率达到15%-20%,则年治疗患者数约为2.2万-4.2万例。
其次,从定价角度,参考Zolbetuximab在中国的定价策略(年治疗费用约15-20万元人民币)以及创新药医保谈判的典型降幅(50%-60%),假设TST001的年治疗费用在医保前为18万元,医保后为8-10万元,平均realized价格约为6-8万元。综合患者数量和定价假设,峰值销售额的测算区间为13.2亿-33.6亿元人民币,软库中华的12亿元预测处于这一区间的保守端,可能反映了对市场竞争、渗透速度和定价压力的审慎考量。
从时间维度,根据软库中华的收入预测模型,TST001预计于2027年启动商业化销售,首年贡献收入约1.04亿元,随后通过医保谈判实现快速放量,销售峰值可达12亿元人民币。这一预测假设了2027年获得NMPA批准、顺利纳入医保目录以及销售团队的快速组建和能力建设。
5.2.3 全球市场份额假设:与Zolbetuximab、AB011等竞争格局
在全球市场层面,TST001面临的首要竞争者是已率先上市的安斯泰来Zolbetuximab。根据安斯泰来2024财年(2024年4月-2025年3月)财报,Vyloy全球销售额达122亿日元(约8,000万美元),2025财年第二季度单季销售额为140亿日元,增长势头强劲。Zolbetuximab的先行优势体现在多个维度:监管批准的时间领先(约2-3年)、全球商业基础设施的成熟度、医生教育和市场认知的积累,以及伴随诊断网络的建立。这些因素构成了TST001进入全球市场的显著壁垒。
然而,TST001的差异化定位为其争夺市场份额提供了潜在路径。核心差异化点包括:(1)分子设计上的ADCC效应增强,理论上可带来更优的抗肿瘤活性和更宽的治疗窗口;(2)临床策略上的三联疗法(联合PD-1抑制剂和化疗),而Zolbetuximab当前获批的是双联疗法,若TST001的三联方案在III期研究中证实更优疗效,将形成明确的临床价值主张;(3)更低Claudin18.2表达阈值的患者覆盖,可将受益人群扩展约45%,显著扩大可及市场;(4)潜在的成本优势,创胜集团的HiCB连续生产工艺有望降低单位生产成本,为定价竞争力和利润率提供支撑。
除Zolbetuximab外,TST001在中国本土市场还面临多家竞争者的追赶。信达生物的IBI343(Claudin18.2 ADC)、康诺亚/乐普生物的CMG901(Claudin18.2 ADC)、奥赛康的ASKB589等均在临床开发中,部分产品已进入II/III期阶段。这些竞争者的技术路线涵盖单抗、ADC、双抗等多种形态,各具优劣:ADC可能提供更强的细胞毒效应但伴随更高的安全性风险;双抗可增强T细胞募集但工艺复杂性更高。TST001作为传统单抗,其优势在于工艺成熟、成本可控、免疫原性风险较低,且联合治疗的灵活性更高。竞争格局的最终演变将取决于各产品的临床数据质量、监管审批进度、商业化执行能力以及定价和准入策略。
5.3 骨质疏松症市场(TST002)5.3.1 中国老龄化驱动的市场扩容
骨质疏松症作为与年龄密切相关的骨骼代谢疾病,正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而呈现epidemic增长态势。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数据,中国5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患病率约为19.2%,其中女性高达32.1%,对应患者人数超过9,000万;65岁以上人群患病率进一步升至32.0%,患者数约5,000万。随着1960年代婴儿潮一代进入老年阶段,以及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骨质疏松症患者基数预计将在未来十年持续扩大,至2030年可能突破1.2亿人。这一庞大且增长的患者群体为抗骨质疏松药物市场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
当前中国骨质疏松症治疗市场以双膦酸盐类(阿仑膦酸钠等)为主导,这类药物虽成本较低且使用广泛,但存在胃肠道不良反应、给药方式不便(需空腹直立服用)以及长期应用可能增加非典型骨折风险等局限性。骨保护素抗体地舒单抗(Denosumab,安进/协和发酵麒麟)于2019年在中国获批,凭借每6个月皮下注射的便利性和强效的抗骨吸收作用,迅速成为市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2023年中国销售额估计超过15亿元人民币。甲状旁腺激素类似物特立帕肽(Teriparatide,礼来)作为促骨形成药物,适用于严重骨质疏松患者,但需每日皮下注射且疗程受限(最长24个月),临床应用受到一定制约。
5.3.2 与地舒单抗、特立帕肽的差异化竞争
药物类别
代表产品
核心机制
关键优势
主要局限
双膦酸盐
阿仑膦酸钠
抑制骨吸收
成本低,使用广泛
胃肠道不良反应,给药不便
RANKL抗体
地舒单抗
抑制骨吸收
强效,每6个月给药
停药后反弹性骨折风险
PTH类似物
特立帕肽
促进骨形成
显著骨密度提升
每日注射,疗程限制2年
硬骨素抗体
Blosozumab/TST002
双重:促骨形成+抑骨吸收
机制互补,潜在更优疗效
待验证长期安全性
Blosozumab(TST002)作为硬骨素(Sclerostin)靶向单克隆抗体,其差异化价值在于独特的双重作用机制:既通过抑制硬骨素对Wnt信号通路的负调控促进骨形成,又通过调控骨细胞-破骨细胞偶联抑制骨吸收,从而实现骨代谢的正向平衡。这一机制与地舒单抗(纯抗骨吸收)和特立帕肽(纯促骨形成)形成鲜明对比,理论上可实现更高的骨密度增益和更持久的疗效,且给药频率较低(每4周或每12周一次),患者依从性更优。
礼来在美国和日本完成的II期研究显示,Blosozumab最高剂量组治疗12个月后,腰椎骨密度(BMD)平均增加17.7%,全髋BMD增加6.2%,疗效显著且耐受性良好。创胜集团于2019年从礼来引进Blosozumab的大中华区权益,并已完成中国I期桥接研究。该研究纳入32例中国患者,结果显示单次给药后85天,腰椎BMD平均增加3.52%-6.20%,全髋BMD增加1.30%-2.24%,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特征与欧美人群一致,支持后续开发的延续性。
5.3.3 15亿元年销售额峰值预测假设
根据软库中华证券的预测,TST002有望于2028年在中国上市,峰值年销售额达到15亿元人民币。这一预测的关键假设包括:桥接试验或关键性试验于2025-2026年启动,2027年完成并提交上市申请,2028年获得批准;定价策略参考地诺单抗等生物制剂,年治疗费用约为2-3万元;目标患者人群为高风险骨质疏松症患者(既往骨折史、骨密度T值<-2.5、或FRAX评分高风险),渗透率逐步提升至5-10%。
市场竞争格局方面,地诺单抗的生物类似药已于2023-2024年在中国陆续上市,价格竞争压力显著;特立帕肽的每日注射剂型依从性受限,但周制剂正在开发中。TST002的差异化定位需要强调其双重机制带来的更高疗效潜力,以及更低给药频率的便利性优势。若能在头对头试验中显示出优于地诺单抗的骨密度增益或骨折风险降低,将建立强有力的临床价值主张。
5.4管线期权价值5.4.1 早期产品的对外授权潜力(首付款/里程碑/销售分成)
创胜集团的研发管线包含多个处于早期临床或临床前阶段的创新分子,这些资产虽然距离商业化较远,但具有显著的对外授权(License-out)期权价值,可在短期内为公司带来非稀释性资金来源,并验证平台技术的行业认可度。根据公司披露,其早期管线涵盖PD-L1/TGF-β双功能融合蛋白(TST005)、MASP2单抗(TST004)、GREMLIN-1单抗(TST003)等多个差异化靶点,适应症覆盖肿瘤、肾病和自身免疫疾病。
对外授权交易的典型结构包括:首付款(Upfront payment),通常在数百万至数千万美元不等,于协议签署时收取;开发里程碑付款(Development milestones),与临床试验启动、数据读出、监管申报和批准等节点挂钩,累计可达数亿美元;商业化里程碑付款(Commercial milestones),与销售额阈值达成相关;以及销售分成(Royalties),通常为净销售额的个位数至低双位数百分比。2024-2025年,中国生物科技企业的对外授权交易呈现爆发式增长,百利天恒与百时美施贵宝、科伦博泰与默沙东、康方生物与Summit等重磅交易相继宣布,总交易价值屡创新高,反映了国际制药巨头对中国创新资产的强烈兴趣和估值认可。
创胜集团的对外授权潜力取决于多个因素:核心产品的临床数据质量和差异化程度、平台技术的可扩展性和验证状态、管理层的BD能力和网络资源,以及市场时机的把握。考虑到公司当前资源聚焦于TST001和TST002的后期开发,早期管线的对外授权可能是优化资源配置、延长现金跑道的理性选择。若能在2025-2026年达成1-2项具有竞争力的授权交易,不仅可带来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资金流入,还可借助合作伙伴的开发能力和全球网络加速资产价值实现。
5.4.2 CDMO业务的现金流补充作用
创胜集团通过其杭州生产基地的HiCB(High-intensity Continuous Bioprocessing)连续生产工艺平台,为第三方提供合同开发与生产组织(CDMO)服务,这一业务板块在当前无产品商业化收入的阶段具有重要的现金流补充作用。HiCB平台采用强化连续灌注细胞培养技术,相比传统的批次补料工艺,具有生产效率高、占地面积小、产品质量一致性好、单位成本更低等显著优势,尤其适用于高剂量抗体药物的商业化生产。
根据软库中华的收入预测,创胜集团2024-2026年的收入主要来源于CDMO服务和合作收入,分别为9.1百万元、11.4百万元和13.7百万元人民币(注:原文数据单位可能存在矛盾,结合上下文判断应为百万元级别)。虽然这一收入规模相对有限,且呈现同比下降趋势(2024年同比下降83.0%,可能反映合作项目的阶段性完成),但CDMO业务的战略价值不仅在于直接现金流贡献,还包括:生产设施的利用率优化和折旧分摊、工艺能力的持续验证和提升、与潜在客户/合作伙伴的关系建立,以及监管合规经验的积累。随着TST001接近商业化,CDMO业务的优先级可能逐步降低,生产资源将向自有产品倾斜,但在过渡期内仍可作为重要的运营支撑。
6. 竞争格局与行业定位6.1 Claudin18.2靶点全球竞争态势6.1.1 已上市产品:安斯泰来Zolbetuximab(Vyloy)的先行优势
安斯泰来的Zolbetuximab作为全球首个获批的Claudin18.2靶向药物,其商业化表现和市场策略为后续竞争者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也构建了显著的进入壁垒。Zolbetuximab的开发可追溯至2000年代初期,德国Ganymed Pharmaceuticals公司基于其SIMBA技术平台发现了该靶点的治疗潜力,并完成了早期临床概念验证。2016年,安斯泰来以14亿美元收购Ganymed,获得Zolbetuximab的全球权益,随后投入巨资开展SPOTLIGHT和GLOW两项III期关键性研究,最终于2024年实现全球主要市场的获批上市。
从商业化表现看,Zolbetuximab的放量速度超出市场预期。根据安斯泰来财报,该产品2024财年(2024年4月-2025年3月)全球销售额达122亿日元(约8,000万美元),2025财年第二季度(2025年4-6月)单季销售额即达140亿日元,呈现加速增长态势。这一表现反映了Claudin18.2检测的快速普及、医生对新靶点的高度认可以及胃癌患者对创新治疗的迫切需求。安斯泰来预计Vyloy将成为其肿瘤业务的核心增长驱动力,峰值销售潜力超过10亿美元。
Zolbetuximab的先行优势体现在多个维度:监管层面,其获批为Claudin18.2靶向治疗建立了监管标准和审批路径,后续产品可借鉴其临床设计、终点选择和安全性数据库;商业层面,安斯泰来已建立全球肿瘤销售团队,与关键意见领袖(KOL)和癌症中心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市场教育和患者筛选网络日趋成熟;诊断层面,VENTANA伴随诊断的获批和普及为Zolbetuximab的使用提供了基础设施支持,同时也可能形成一定的锁定效应;临床数据层面,Zolbetuximab的SPOTLIGHT和GLOW研究数据已成为后续产品的对照基准,超越这一疗效标准需要更大的样本量和更长的随访时间。
6.1.2在研产品矩阵:信达生物、奥赛康、康诺亚等国内竞争者
中国本土企业在Claudin18.2靶点的布局呈现百花齐放态势,技术路线涵盖单克隆抗体、抗体药物偶联物(ADC)、双特异性抗体、CAR-T细胞治疗等多种形态,竞争格局复杂且动态演变。以下为主要竞争者的简要梳理:
公司
产品
技术类型
临床阶段
核心特点
安斯泰来
Zolbetuximab/Vyloy
单抗
已上市
全球首创,先行优势
创胜集团
TST001/Osemitamab
单抗(ADCC增强)
III期
中国领先,三联疗法
信达生物
IBI343
ADC
II/III期
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载荷
康诺亚/乐普生物
CMG901
ADC
II期
首个进入II期的国产Claudin18.2 ADC
奥赛康
ASKB589
单抗
II/III期
高亲和力,差异化表位
齐鲁制药
QLS31905
CD3双抗
III期(胰腺癌)
全球首个进入III期的Claudin18.2双抗
科济药业
CT041
CAR-T
上市申请中
全球首个Claudin18.2 CAR-T,中美欧同步申报
再鼎医药
ZL-1211
单抗
I/II期
引进自MacroGenics
这一竞争格局揭示了Claudin18.2靶点的开发热度和技术多样性。ADC和CAR-T等新型modalities可能提供更强的细胞毒效应,但也伴随更高的安全性风险和生产成本;双抗可增强免疫效应细胞募集,但工艺复杂性和免疫原性风险需要关注。TST001作为传统单抗,其竞争策略依赖于ADCC效应增强带来的疗效优势、三联疗法的差异化定位、以及成本和可及性优势。最终的市场格局将取决于各产品的临床数据头对头比较、监管审批进度、商业化执行能力以及定价和准入策略的综合竞争。
6.1.3 TST001的差异化定位:更低表达阈值活性、更优安全性特征
TST001的核心差异化价值主张建立在分子设计和临床策略两个层面的创新。在分子设计层面,TST001采用人源化IgG1骨架,并通过Fc段工程化改造显著增强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ADCC)。ADCC是抗Claudin18.2单抗发挥抗肿瘤效应的关键机制之一,通过抗体Fc段与效应细胞(NK细胞、巨噬细胞等)表面的FcγRIIIa结合,触发对肿瘤细胞的定向杀伤。创胜集团的研究数据显示,TST001的ADCC活性相对于Zolbetuximab增强约100倍,这一显著优势使其在Claudin18.2低表达肿瘤细胞中仍能保持有效的杀伤活性,为扩展至更低表达阈值患者提供了机制基础。
在临床策略层面,TST001的三联疗法设计(Osemitamab + 纳武利尤单抗 + CAPOX)代表了胃癌一线治疗的下一代进化方向。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与靶向治疗的联合已在多个瘤种中证实协同效应:靶向治疗可通过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增强肿瘤抗原呈递等机制改善肿瘤免疫微环境,从而增强PD-1/PD-L1抑制剂的疗效;反之,免疫激活也可促进抗体效应功能的发挥。2024年ESMO和2025年ASCO公布的G队列数据显示,该三联方案在66例可评估患者中取得68%的ORR和14.2个月的mPFS,且无论PD-L1 CPS状态如何均观察到活性,这一疗效特征与Zolbetuximab联合化疗的历史数据(SPOTLIGHT研究:ORR 60.7%,mPFS 10.6个月)相比具有潜在优势。
安全性方面,TST001的临床数据至今未观察到新的安全性信号,主要不良反应为化疗相关的血液学毒性和胃肠道反应,以及PD-1抑制剂相关的免疫相关不良反应,整体可控。Zolbetuximab的获批标签中包含恶心、呕吐等胃肠道不良反应的黑框警告,这与Claudin18.2在正常胃黏膜的表达相关;TST001是否因ADCC增强而带来不同的安全性特征,需要更大样本量的III期研究进一步验证。
6.2 中国生物制药行业格局6.2.1 创新药转型浪潮:恒瑞、翰森、中生制药等传统Pharma
中国制药行业正处于从仿制药向创新药转型的关键历史节点,传统大型制药企业(Big Pharma)凭借积累的资本、渠道和监管经验,积极布局创新药研发,与新兴生物技术公司(Biotech)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复杂关系。恒瑞医药作为国内创新药龙头,2023年研发投入超过60亿元人民币,拥有丰富的肿瘤管线,包括多个Claudin18.2靶向资产(单抗、ADC、双抗),是创胜集团在多个适应症领域的直接竞争者。翰森制药、中生制药、石药集团等企业也通过自主研发和外部引进双轮驱动,加速创新转型。
传统Pharma的优势在于:成熟的商业化基础设施和销售团队,可实现新产品的快速放量;深厚的监管关系和医保谈判经验;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对冲研发风险;以及较低的资金成本。其挑战则包括:组织惯性和决策效率、创新文化的培育、以及对外部创新源的整合能力。创胜集团作为专注的Biotech,其相对优势在于聚焦的战略执行力、灵活的组织架构、以及全球创新的视野和网络;劣势则在于资源约束、商业化经验欠缺、以及对单一产品的高度依赖。
6.2.2 Biotech新势力:百利天恒、科伦博泰、康方生物等
2015年以来,港交所18A章节和科创板第五套标准的推出,为中国Biotech的资本市场化提供了关键通道,催生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百利天恒、科伦博泰、康方生物、信达生物、百济神州等公司已通过重磅对外授权交易或自主商业化,验证了创新资产的价值实现路径。这些企业的共同特征包括:差异化的技术平台或产品管线、全球多区域临床开发能力、以及与国际制药巨头的深度合作网络。
创胜集团在这一群体中的定位具有独特性:其核心产品TST001处于全球第二的临床进度,且具备明确的差异化设计;公司建立了真正一体化的端到端平台,从抗体发现到商业化生产的能力完整;管理团队具有深厚的跨国药企背景,全球临床开发和BD能力得到验证。然而,与已产生规模化收入或达成重磅授权交易的部分peers相比,创胜集团的估值水平和资本市场认可度仍有差距,这既反映了其临床阶段更早、风险更高的现实,也可能意味着潜在的价值重估空间。
6.2.3 创胜集团的细分赛道卡位与比较优势
综合评估,创胜集团的核心比较优势可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Claudin18.2靶点的全球第二、中国第一卡位,在胃癌这一亚洲高发病种中建立了明确的领导地位;第二,ADCC增强单抗的技术差异化,为疗效优势和更广泛的患者覆盖提供了机制基础;第三,一体化端到端平台的运营效率和成本优势,尤其是HiCB连续生产工艺的领先性;第四,全球多区域临床开发的执行能力,已获得NMPA、FDA、MFDS等多国监管机构的III期试验批准;第五,管理团队的跨国药企经验和行业网络,为战略合作和商业化布局奠定基础。
主要相对劣势包括:产品管线较peers更为聚焦,多元化程度不足;无已上市产品,现金流完全依赖外部融资;商业化基础设施尚在建设中,自主推广能力未经验证;以及市值和流动性相对有限,可能影响机构投资者的配置意愿。
6.3 全球BD趋势与中国企业出海6.3.1 2024-2025年License-out交易热潮(辉瑞/百时美施贵宝等案例)
2024-2025年,中国生物科技企业的对外授权交易呈现前所未有的活跃态势,交易规模、结构复杂度和全球影响力均达到新高度。代表性交易包括:百利天恒与百时美施贵宝就EGFR/HER3双抗ADC(BL-B01D1)达成84亿美元总交易价值的合作协议;科伦博泰与默沙东就多款ADC资产累计签署超过100亿美元的系列协议;康方生物与Summit就PD-1/VEGF双抗(依沃西单抗)达成50亿美元交易;以及诚益生物、恒瑞医药、和铂医药等多家企业的数十亿美元级别交易。
这一热潮的驱动因素包括:中国创新药研发能力的系统性提升,尤其在ADC、双抗、细胞治疗等新兴modalities中形成局部优势;国际制药巨头面临专利悬崖和增长压力,对外部创新源的依赖度上升;中国Biotech的估值调整使资产性价比提升;以及地缘政治因素促使中国企业寻求海外合作伙伴以分散风险。交易结构的演变也值得关注:越来越多的交易采用”首付+里程碑+销售分成+共同开发/商业化”的复杂架构,体现了双方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理念。
6.3.2 TST001的潜在全球合作机会与估值影响
对于创胜集团而言,TST001的对外授权或全球合作是价值实现的关键路径之一,也是投资者高度关注的潜在催化剂。潜在的合作模式包括:全球权益授权(除大中华区外),由国际合作伙伴负责海外临床开发和商业化;共同开发协议,双方分担全球III期试验成本和风险,共享未来收益;以及特定市场授权,如日本、欧洲或新兴市场等。合作时机的选择涉及多重权衡:早期合作(II期数据后)可锁定合作伙伴并分担III期风险,但估值可能受限;晚期合作(III期数据读出后)可基于更充分的证据争取更优条款,但需承担独立完成III期的资金压力和执行风险。
从估值影响角度,一项具有竞争力的全球合作交易可带来多重价值:直接的资金流入(首付款和早期里程碑)延长现金跑道,降低稀释性融资需求;合作伙伴的临床开发和监管经验提高全球获批概率;国际商业基础设施确保产品的全球市场渗透;以及交易估值为股票提供重要的重估催化剂。参考同类交易,若TST001能在2025-2026年达成覆盖欧美日等核心市场的授权协议,首付款可能在0.5-2亿美元区间,总交易价值可达10-30亿美元,对创胜集团的估值将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
7. 财务状况与运营效率分析7.1 历史财务表现(2020-2024)7.1.1收入结构:合作收入、CDMO收入、其他
创胜集团作为临床阶段生物制药企业,其收入结构典型地反映了该阶段公司的特征:尚未有产品商业化销售,收入主要来源于CDMO服务、技术合作里程碑付款和其他零星收入。2020-2022年间,公司收入规模相对平稳,年均约4000-8000万元人民币,主要依赖CDMO业务的产能利用和早期合作项目的阶段性付款。2023-2024年,收入出现显著下滑,2024年预计仅为910万元人民币,同比下降83.0%。这一下滑反映了公司战略重心的调整——将资源从对外服务向自有核心管线集中,以及CDMO市场竞争加剧和客户需求波动的双重压力。
收入结构的单一性和不稳定性是临床阶段Biotech的普遍挑战。与已上市产品产生规模化收入的企业相比,创胜集团的收入可见性较低,现金流预测难度大,这对财务规划和投资者沟通均构成挑战。2024年的收入低谷也可能是阶段性现象——若TST001的BD交易在2025年达成,首付款收入将显著改善当年财务状况;若交易延迟,则收入压力将持续至2026-2027年产品上市。
7.1.2 研发费用趋势:资源聚焦与效率优化
研发费用是创胜集团最大的现金消耗项,也是评估公司战略执行的关键指标。2020-2023年间,公司年度研发开支从约2亿元人民币增长至超过3.8亿元人民币,反映了管线扩张和临床推进的投入增加。2024年,研发费用出现显著下降,预计为1.921亿元人民币,较2023年的3.820亿元减少49.7%。这一下降并非研发能力的收缩,而是资源优先级调整的结果——将资金集中于Osemitamab和Blosozumab两大后期资产,同时暂缓或终止部分早期项目的内部推进。
研发效率的优化体现在多个维度:项目层面的聚焦降低了并行开发的资源分散;平台能力的复用减少了重复建设;以及与CRO/CDMO合作伙伴的谈判优化。然而,研发费用的压缩也存在边界——III期临床试验的刚性支出、监管申报的准备成本、以及商业化生产的验证投入,均需要持续的资金支持。2025-2026年,随着TranStar 301试验进入关键阶段和上市准备启动,研发费用可能重新上升,对现金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7.1.3 现金消耗速度与运营亏损演变
创胜集团的运营亏损随收入波动和研发投入变化而演变。2022-2023年间,年度净亏损约为4.5-4.7亿元人民币;2024年,亏损幅度收窄至约2.75亿元人民币,反映了费用控制和收入结构优化的初步成效。然而,这一改善的可持续性存疑——若2025年未能达成重大BD交易或完成新一轮融资,现金流压力将迫使公司进一步削减开支,可能影响核心管线的推进速度。
现金消耗速度的评估需要结合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综合分析。根据2024年中期报告,公司经营现金流出约为2.1亿元人民币,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用于设施建设和设备采购,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则依赖借款和股权融资。按此速度推算,现有现金储备(约1.0-1.5亿元人民币)可支持约6-12个月运营,融资窗口的紧迫性不言而喻。
7.2 2024年最新财务数据7.2.1 资产负债表:现金储备、借款结构、抵押安排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创胜集团的关键资产负债指标呈现以下特征:
指标
2024年
2023年
变动
分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1.0亿元
~2.3亿元
-56.5%
经营消耗和偿债支出
短期借款
0.42亿元
0.50亿元
-16.0%
部分偿还
流动负债总额
~3.4亿元
~4.1亿元
-17.1%
应付款项管理
流动资产净值
-0.63亿元
+1.78亿元
转负
技术性资不抵债
负债权益比
46.5%
30.8%
+15.7pct
杠杆上升
总资产
~12.0亿元
~14.8亿元
-18.9%
折旧和减值
流动资产净值为负(-0.63亿元)是关键的警示信号,表明流动负债已超过流动资产,形成技术性资不抵债状态。这一状况源于现金储备的快速消耗和短期借款的相对刚性,需要通过后续融资或经营性现金流的改善来修复。审计师在2024年年报中出具了”免责声明”(Disclaimer of Opinion),对持续经营能力提出重大质疑,反映了这一财务状况的严重性。
7.2.2 现金流量表:经营/投资/筹资活动分析
2024年度现金流量表的关键数据包括:
•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净额:约2.14亿元人民币,主要用于研发投入和日常运营;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净额:约0.14亿元人民币,主要来自资产处置;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净额:约1.78亿元人民币,主要用于偿还借款;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约3.78亿元人民币。
这一现金流结构显示,公司仍处于”烧钱”阶段,经营活动无法产生正向现金流,投资活动贡献有限,筹资活动则因偿还债务而呈现净流出。改善这一状况的路径包括:达成BD交易获得首付款、完成股权融资补充资本金、以及加速产品上市实现销售收入。
7.2.3 流动性指标:流动比率、现金比率、负债权益比
流动性指标
2024年
2023年
行业参考
评估
流动比率
0.82
1.52
>1.5健康
低于1,短期偿债压力大
速动比率
0.50
1.20
>1.0健康
扣除存货后更紧张
现金比率
0.30
0.56
>0.3可接受
边缘水平
负债权益比
46.5%
30.8%
<50%可控
接近警戒线
利息保障倍数
负值
负值
>3健康
无盈利覆盖
流动性指标的恶化趋势需要密切关注。流动比率跌破1.0意味着即使变现全部流动资产,也无法覆盖短期债务,需要依赖续贷、展期或新增融资来缓解。公司管理层已采取多项应对措施,包括与银行协商融资延期、与主要供应商谈判付款安排、以及推进资产处置和对外授权。
7.3 资金管理与融资策略7.3.1 IPO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与再分配
创胜集团2021年IPO募集资金净额约5.534亿港元,原计划用于核心产品研发(约40%)、生产能力建设(约30%)、早期管线推进(约20%)和运营资金(约10%)。随着战略调整,资金用途发生了显著变更:后期临床(TST001、TST002)的资源配置比例提升,早期管线的内部投入压缩,CDMO业务的扩张计划放缓,技术授权和BD活动的投入增加。
这种灵活性体现了管理层应对变化环境的务实态度,但也引发了对前期规划前瞻性的质疑。频繁的用途变更可能影响投资者信心,监管机构也要求充分披露变更理由和预期影响。2024年年报中,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并获得了董事会的批准,但审计师的”免责声明”仍反映了对其持续经营能力的担忧。
7.3.2 外汇风险管理政策
创胜集团的运营涉及多币种结算,面临人民币、美元、港币的汇率波动风险。2024年,公司以美元计值的贸易及其他应收款项为76.5万元,较2023年的118.2万元有所减少。公司披露目前无外币对冲政策,但会持续监控并在必要时考虑对冲重大外汇风险。
这一审慎态度反映了公司对外汇风险敞口的认知,但也意味着汇率波动可能直接影响财务报表。2024-2025年人民币汇率的阶段性贬值,对公司美元现金储备和海外运营成本的账面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若未来汇率波动加剧,建议公司建立更系统的外汇风险管理框架,包括自然对冲(匹配收入和支出的币种结构)和金融对冲(远期、期权等衍生品工具)。
7.3.3 后续融资需求与时间窗口评估
基于当前现金消耗速度和业务发展需求,创胜集团预计需要在2025年下半年至2026年上半年完成新一轮融资,以支撑TST001 III期试验的完成、上市准备和早期商业化投入。融资方式的选择涉及多重权衡:
融资方式
优势
劣势
适用情景
股权融资(增发/配股)
资金充裕,无偿债压力
稀释现有股东,估值敏感
市场环境友好,股价较高
可转债
延迟稀释,票息较低
转股压力,条款复杂
对未来股价有信心
战略投资者引入
资源协同,估值支撑
控制权让渡,谈判周期长
BD交易同步进行
银行贷款
不稀释股权,成本可控
抵押要求,期限限制
有充足抵押资产
BD交易首付款
非稀释性,验证价值
时间不确定,条款谈判
临床数据积极
当前市场环境下,股权融资面临估值压力和流动性约束,BD交易首付款是最理想的资金来源,但时间不确定性较高。公司管理层表示正在积极推进与多家全球及区域制药公司的合作讨论,若干合作方正在进行尽职调查审查和/或就条款清单进行谈判。若能在2025年内达成具有竞争力的交易,将显著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和估值前景;若谈判延迟或破裂,则可能被迫在不利条件下进行稀释性融资。
8. 盈利预测与估值分析8.1 收入预测模型(2024-2028)8.1.1关键假设:产品获批时间、定价策略、渗透率曲线
软库中华研究报告对创胜集团2024-2028年的收入预测提供了详细的量化框架,其核心假设和预测逻辑值得深入剖析:
假设维度
基准情景
乐观情景
悲观情景
TST001中国获批时间
2027年Q2
2026年Q4
2028年及以后
TST001中国定价(年治疗费用)
医保前15-18万,医保后6-8万
医保前20-25万,医保后8-10万
医保前10-15万,医保后4-6万
TST001中国峰值渗透率
15%-20%
25%-30%
8%-12%
TST002获批时间
2028年
2027年
2029年及以后
对外授权交易
2025-2026年达成,首付款5000万-1亿美元
2025年达成,首付款1-2亿美元
未能达成或条款不利
这些假设的敏感性极高——获批时间提前或推迟6个月,可能导致2027-2028年收入预测波动30%-50%;定价策略受医保谈判结果影响显著,每10%的降价幅度可能压缩峰值销售10%-15%;渗透率假设则取决于临床数据质量、竞争格局和商业化执行的综合效果。
8.1.2 分产品收入拆分:TST001、TST002、其他管线
年度
TST001
TST002
其他收入
合计
同比增长
2024E
—
—
9.1
9.1
-83.0%
2025E
—
—
11.5
11.5
+26.4%
2026E
—
—
13.7
13.7
+19.1%
2027E
100.0
—
20.4
120.4
+779.5%
2028E
320.0
25.0
10.8
355.8
+195.4%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2027-2028年数据基于峰值预测和放量假设调整
上表显示,2027年是公司收入结构的质变之年,产品销售收入占比从0%跃升至83%,标志着从临床阶段向商业化阶段的转型。TST001的放量速度假设较为激进——首年1亿元,第二年3.2亿元,第三年接近峰值——这需要临床数据优异、医保谈判顺利、以及销售团队高效执行的多重配合。若任一环节出现延迟,收入曲线将整体后移和平缓。
8.1.3预测敏感性分析:获批延迟/加速、竞争加剧情景
情景
2028年收入预测(百万元)
较基准变动
关键触发因素
乐观
520
+46%
TST001 2026年底获批,2028年美国上市;重磅BD交易
基准
356
—
TST001 2027年中国获批,区域合作伙伴;稳步放量
悲观
180
-49%
TST001 2028年获批,竞争加剧定价下降30%;TST002延迟
悲观情景下的收入腰斩风险,主要源于临床挫折或竞争恶化。若TranStar 301试验未能达到主要终点,或Zolbetuximab在中国市场采取激进定价策略,TST001的商业化前景将显著承压。这一风险敞口是临床阶段Biotech投资的固有特征,需要投资者充分认知和定价。
8.2 估值方法论比较8.2.1 现金流折现模型(DCF)8.2.1.1 软库中华模型:WACC 10.5%,永续增长率1%,税率15%
软库中华采用DCF模型作为创胜集团估值的主要方法,核心假设如下:
参数
假设值
行业对比
合理性评估
无风险利率
~2.5%
中国10年期国债2.3%
基本一致
市场风险溢价
~7.0%
港股生物科技常用6%-8%
适中
Beta系数
1.35
临床阶段Biotech典型1.2-1.5
反映较高系统性风险
债务成本
~5%-6%
公司当前有息负债有限
影响较小
WACC
10.5%
行业平均9%-12%
合理区间中段
永续增长率
1%
行业常用2%-3%
显著保守
税率
15%
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
适用条件需维持
1%的永续增长率假设显著低于行业常用水平,体现了分析师对公司长期增长可持续性的高度审慎。若上调至2%,目标价将从4.40港元提升至约4.86港元(+10.5%);若采用更乐观的3%,目标价可达5.10港元以上。
8.2.1.2 目标价4.40港元的推导逻辑
计算步骤
金额(人民币千元)
说明
2025-2035年预测现金流现值
90,490
核心产品贡献
永续经营部分现金流现值
1,714,266
Gordon增长模型,g=1%
企业价值
1,804,755
上述两项之和
减:净负债
26,113
有息负债减现金
权益价值
1,778,642
企业价值减净负债
股份数(百万股)
404.24
总股本
每股内在价值(港元)
4.40
假设汇率接近平价
数据来源:软库中华金融DCF模型,2025年2月
8.2.1.3 DCF假设的乐观/基准/悲观情景对比
情景
WACC
永续增长率
目标价(港元)
较基准变动
乐观
9.5%
2%
5.80
+32%
基准
10.5%
1%
4.40
—
悲观
11.5%
0%
3.50
-20%
敏感性分析显示,WACC变动对估值影响大于永续增长率。降低WACC 100bp可提升目标价约15%,而提高永续增长率100bp仅提升约5%。这提示,改善资本结构、降低股权成本(如通过达成BD交易降低风险溢价)是提升估值的更有效路径。
8.2.2 风险调整净现值法(rNPV)8.2.2.1各管线成功概率假设(临床阶段加权)
管线
当前阶段
典型成功概率
峰值销售预测(百万元)
风险调整贡献
TST001(胃癌)
III期
55%-65%
1,200
660-780
TST001(胰腺癌)
早期临床
20%-30%
500
100-150
TST002(骨质疏松)
II期准备
35%-45%
1,500
525-675
早期管线(TST003/004等)
早期临床/临床前
10%-20%
800
80-160
技术平台价值
—
—
—
150-200
合计风险调整NPV
—
—
—
1,515-1,965
rNPV方法通过显性引入成功概率,更直观地反映了临床阶段风险。上表显示,即使采用保守的成功概率假设,创胜集团的风险调整内在价值仍显著高于当前市值,主要源于TST001的III期进度和相对较高的成功概率。
8.2.2.2与纯DCF方法的差异及适用性讨论
rNPV与纯DCF的核心差异在于风险处理方式:DCF通过折现率反映风险,rNPV通过现金流调整反映风险。对于单一产品依赖度高的创胜集团,rNPV可能提供更保守的估值基准;但TST001已进入III期且获得多国监管批准,历史成功率数据对个案预测的参考价值有限。软库中华选择纯DCF而非rNPV,可能是基于以下考量:III期阶段的成功概率已相对较高,且公司明确的2027年商业化时点假设使阶段性预测更具可操作性。
8.2.3 可比公司估值法8.2.3.1港股18A生物科技公司的PS/市值倍数区间
估值分层
典型特征
PS倍数(2025E)
EV/Peak Sales
代表公司
第一梯队
已盈利或临近盈利,产品放量
8-15x
3-5x
信达生物、百济神州
第二梯队
核心产品NDA/BLA阶段,商业化准备中
4-8x
2-4x
康方生物、科伦博泰
第三梯队
III期临床进行中,未确立商业化路径
2-5x
1-3x
创胜集团、奥赛康
第四梯队
早期临床或临床前,高度不确定性
1-3x
0.5-1.5x
众多小型Biotech
创胜集团当前市值约10-11亿港元(假设股价2.2-2.7港元),对应2025E收入的PS倍数约90-100x(因收入规模极小无意义),或对应TST001峰值销售预测的EV/Peak Sales约0.8-1.0x,处于第三梯队的下端。这一折价反映了市场对其资金状况和临床不确定性的担忧,若III期数据积极,存在向第二梯队估值修复的空间。
8.2.3.2临床阶段/商业化阶段公司的估值分层
估值分层的关键驱动因素包括:产品阶段(临床前/I期/II期/III期/已上市)、差异化程度(me-too/me-better/best-in-class/first-in-class)、商业化能力(自主/合作/授权)、以及财务状况(现金跑道/融资能力)。创胜集团在”产品阶段”和”差异化程度”上得分较高,在”商业化能力”和”财务状况”上得分较低,综合定位第三梯队上端。
8.2.3.3 创胜集团当前估值与同业比较
公司
市值(亿港元)
核心产品阶段
关键差异化
估值溢价/折价因素
信达生物
~500
已上市多款产品
商业化能力,全球合作
盈利预期,龙头溢价
康方生物
~400
依沃西单抗获批
双抗技术,50亿美元BD
重磅交易验证
科伦博泰
~350
多款ADC临床后期
默沙东深度合作
平台价值认可
百利天恒
~600
BL-B01D1 III期
84亿美元BD,双抗ADC
交易规模溢价
创胜集团
~11
TST001 III期
ADCC增强,三联疗法
资金压力,BD待验证
与同业相比,创胜集团的估值折价主要源于:BD交易尚未落地,全球价值未获验证;财务状况紧张,持续经营能力受质疑;以及流动性有限,机构覆盖度和参与度较低。这些因素的改善将是估值重估的关键催化剂。
8.3 估值结论与投资建议8.3.1 内在价值与当前股价的偏离度分析
综合DCF、rNPV和可比公司三种方法,创胜集团的合理估值区间约为15-25亿港元(对应每股3.7-6.2港元),较当前市值(约11亿港元,每股2.2-2.7港元)存在36%-127%的上行空间。软库中华4.40港元的目标价处于区间中段,对应约18亿港元市值,需要以下假设的兑现:
• TST001的TranStar 301试验达到主要终点,2027年如期获批;
• 2025-2026年达成具有竞争力的全球BD交易,首付款5000万-1亿美元;
• 公司成功完成新一轮融资,现金跑道延长至2028年;
• 医保谈判结果温和,定价策略得以执行。
若上述假设任一落空,估值将向区间下端移动;若超预期兑现,则存在向上突破可能。
8.3.2 机构评级分布:强烈买入/买入/持有
机构
评级
目标价(港元)
报告日期
核心观点
软库中华金融
强烈买入
4.40
2025年2月
DCF基准,BD期权价值
中泰国际(历史)
中性
2.10-2.50
2021年9月
IPO初期,估值偏高
市场共识
未覆盖/缺乏更新
—
—
流动性限制,覆盖稀疏
评级分布的稀疏性本身即构成投资风险——缺乏持续的研究覆盖意味着市场对公司进展的认知可能存在滞后,股价对正面催化剂的反应可能更为剧烈。
8.3.3 12个月目标价区间与上行空间测算
情景
目标价(港元)
概率权重
预期收益
关键催化剂
乐观(BD交易+积极数据)
5.50-6.50
25%
+150%-200%
全球合作宣布,III期中期数据
基准(按计划推进)
3.50-4.50
50%
+60%-100%
正常临床进度,区域合作
悲观(临床延迟或失败)
1.00-1.50
25%
-45%-55%
试验挫折,融资困难
概率加权目标价
3.60-4.40
100%
—
—
当前股价较概率加权目标价存在折价,但需充分认知下行风险。对于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专业投资者,当前估值提供了不对称的收益机会;对于保守型投资者,建议等待BD交易或III期数据等关键催化剂落地后再行介入。
9. 投资风险因素系统性评估9.1研发与临床风险9.1.1 III期临床失败或延迟的可能性
TranStar 301试验的成败是创胜集团投资价值的决定性因素。尽管I/II期数据积极,但III期临床的固有风险不容忽视:
• 疗效风险:主要终点(OS)是否能在更大样本、更长随访中重现I/II期的积极信号?对照组治疗(化疗+免疫)的演进是否削弱试验药的相对优势?
• 安全性风险:更大样本中是否会出现新的或更严重的不良反应,导致IDMC建议暂停或修改方案?
• 执行风险:全球多中心试验的患者入组速度、数据质量、监管沟通是否按计划推进?
历史数据显示,肿瘤药物III期成功率约为60%-70%,但对于联合疗法和me-better产品,这一概率可能更低。若试验失败或延迟,公司价值将面临重大重估,现金储备也可能不足以支持后续开发。
9.1.2 安全性信号与监管审查风险
Claudin18.2靶点的 on-target 毒性主要涉及胃肠道事件(恶心、呕吐),这与靶点在正常胃黏膜的表达相关。Zolbetuximab的III期研究中,≥3级恶心/呕吐发生率约为10%-15%,影响了部分患者的依从性。TST001的ADCC增强设计是否会导致更严重的胃肠道毒性,或带来新的安全性信号(如免疫相关胰腺炎、血栓事件),需要III期数据验证。若出现意外安全性问题,可能导致监管延迟、标签限制甚至开发终止。
9.1.3 生物标志物验证与患者筛选挑战
TST001的”更低表达阈值”策略依赖于伴随诊断的准确性和可及性。若公司专有的IHC检测方法在III期试验中未能充分验证其与临床获益的相关性,或检测的商业化供应受限,可能限制产品的市场准入和患者渗透。此外,不同实验室间的检测标准化、动态表达与疗效的关系、以及与其他生物标志物(如PD-L1、MSI)的交互作用,均是尚未完全解决的科学问题。
9.2 市场竞争风险9.2.1 Zolbetuximab全球扩张的挤压效应
安斯泰来的Zolbetuximab已在日本、美国、欧洲、中国等主要市场获批,其全球商业基础设施和市场认知构成显著壁垒。若Zolbetuximab在中国市场采取激进定价策略(如通过医保谈判大幅降价以换取市场份额),或加速适应症扩展(如围手术期、胰腺癌),将直接压缩TST001的市场空间和定价灵活性。
9.2.2 国内竞争者临床进度追赶
竞争者
产品
技术路线
关键威胁
信达生物
IBI343
Claudin18.2 ADC
ADC可能显示更优疗效,改变治疗范式
康诺亚/乐普生物
CMG901
Claudin18.2 ADC
与阿斯利康合作,全球开发能力强
奥赛康
ASKB589
单抗
类似定位,进度接近,可能触发价格战
齐鲁制药
QLS31905
CD3双抗
新机制,若成功可能颠覆单抗市场
ADC和双抗等新型modalities若在临床中显示出显著优于单抗的疗效(如更高的ORR、更长的生存期、或更好的安全性),可能使TST001面临技术颠覆风险。公司需要持续跟踪竞争动态,并准备产品升级策略(如自身ADC开发或合作)。
9.2.3 替代疗法(ADC、CAR-T等)的技术颠覆
科济药业的CT041(Claudin18.2 CAR-T)已在中国提交上市申请,若获批将成为首个细胞治疗产品,在特定患者群体(如晚期、多线治疗失败)中建立优势。CAR-T的治愈潜力和一次性治疗模式,可能对需要长期给药的抗体药物形成替代威胁,尤其是在高价值患者群体中。
9.3 商业化与执行风险9.3.1 自建销售团队vs.合作伙伴的策略不确定性
创胜集团尚未明确TST001的商业化策略。自建团队可保留更高利润率和战略控制,但需要2-3年时间和数亿元投入构建团队,且缺乏商业化经验;合作伙伴模式可借助成熟渠道快速放量,但需让渡15%-25%的销售分成和部分地区权益。策略选择的延迟或失误,可能影响上市初期的市场渗透和医生认知建立。
9.3.2 医保谈判定价与支付环境变化
中国创新药医保谈判的降价压力持续存在,2024年谈判平均降幅约60%。若TST001的定价策略过于激进,可能触发监管关注和舆论压力;若过于保守,则可能因可及性不足而丧失市场份额。医保纳入的时间节点(获批后1-2年)也将影响收入曲线的形状。
9.3.3 生产规模化与供应链稳定性
HiCB平台虽在技术上具有优势,但商业化规模的GMP验证、关键原材料(如培养基、填料)的供应链安全、以及海外市场的供应能力,均需在实际运营中验证。任何生产质量问题或供应中断,都可能导致监管处罚和市场信任损失。
9.4财务与融资风险9.4.1 现金跑道与后续融资时点
基于当前消耗速度,公司现金跑道约6-12个月,融资窗口紧迫。若2025年内未能达成BD交易或完成股权融资,可能面临运营资金短缺,被迫削减研发开支或寻求紧急融资,显著稀释现有股东权益。
9.4.2 股权稀释对现有股东的影响
假设公司以当前市值的50%-70%完成新一轮融资,募集资金2-3亿港元,现有股东持股比例可能稀释20%-40%。若融资前股价因积极催化剂上涨,稀释程度可降低;反之,若被迫以更低价格融资,则进一步损害股东
100 项与 阿仑膦酸钠 相关的药物交易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研发状态
批准上市
10 条最早获批的记录, 后查看更多信息
登录
| 适应症 | 国家/地区 | 公司 | 日期 |
|---|---|---|---|
| 骨折 | 美国 | 2003-09-17 | |
| 骨质疏松性骨折 | 美国 | 2003-09-17 | |
| 糖皮质激素诱导的骨质疏松症 | 美国 | 1999-06-16 | |
| 畸形性骨炎 | 美国 | 1995-09-29 | |
| 绝经期后骨质疏松 | 美国 | 1995-09-29 | |
| 骨质疏松症 | 意大利 | 1993-01-01 |
未上市
10 条进展最快的记录, 后查看更多信息
登录
| 适应症 | 最高研发状态 | 国家/地区 | 公司 | 日期 |
|---|---|---|---|---|
| 非转移性前列腺癌 | 临床3期 | - | 2005-07-01 | |
| 维生素D缺乏症 | 临床3期 | - | 2003-09-24 | |
| 髋部骨折 | 临床3期 | 加拿大 | 2003-01-01 | |
| 糖尿病 | 临床2期 | 以色列 | 2016-04-01 | |
| 青少年骨质疏松症 | 临床2期 | 美国 | 2000-09-01 |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临床结果
临床结果
适应症
分期
评价
查看全部结果
| 研究 | 分期 | 人群特征 | 评价人数 | 分组 | 结果 | 评价 | 发布日期 |
|---|
临床2期 | 19 | Teriparatide-denosumab | 蓋艱齋網範積糧鬱餘繭(夢鏇遞構網遞鬱壓選鬱) = 獵鏇簾鬱醖鬱艱繭鹽觸 築鬱鬱鏇窪醖鹹壓糧艱 (艱壓觸積選廠膚鹽糧壓, 210.0) | 积极 | 2025-12-14 | ||
临床4期 | 170 | Alendronate solution (ALN-S) | 襯鬱鏇鑰淵艱顧觸壓觸(淵襯觸醖獵廠願膚構淵) = 鏇憲鑰蓋網鬱鏇壓顧蓋 範壓鹹蓋繭憲醖艱製網 (鏇築夢積製製築壓製艱, 0.6) 更多 | 积极 | 2024-11-26 | ||
Alendronate tablet (ALN-T) | 襯鬱鏇鑰淵艱顧觸壓觸(淵襯觸醖獵廠願膚構淵) = 網淵觸糧顧鬱醖憲艱窪 範壓鹹蓋繭憲醖艱製網 (鏇築夢積製製築壓製艱, 0.6) 更多 | ||||||
临床3期 | 血管钙化 18F‐sodium fluoride | - | 簾齋築艱鹹遞艱觸窪壓(選廠選襯廠製選餘醖憲) = 網鏇艱選壓鏇餘顧膚膚 醖窪鬱遞膚願醖鹽鬱壓 (襯廠憲鬱艱憲鹽鬱淵願, 0 ~ 212) 更多 | 不佳 | 2024-09-09 | ||
簾齋築艱鹹遞艱觸窪壓(選廠選襯廠製選餘醖憲) = 顧艱觸網膚襯鹹願襯鹹 醖窪鬱遞膚願醖鹽鬱壓 (襯廠憲鬱艱憲鹽鬱淵願, -62 ~ 134) 更多 | |||||||
N/A | 57 | 願憲選觸夢醖憲繭顧襯(憲鬱窪夢壓鹽襯鹹鑰構) = There were no cases of significant adverse effects specifically atypical femur fractures or osteonecrosis of jaw 襯廠顧廠顧糧齋範網繭 (憲窪壓構鏇廠齋簾簾範 ) | - | 2024-06-05 | |||
N/A | 170 | Alendronate Sodium Trihydrate (ALN-S) | 鏇壓蓋窪鏇繭醖膚醖鹹(鑰鏇簾膚衊選鏇糧襯襯) = 構繭齋選願願觸範蓋襯 願網淵窪觸齋願鏇淵網 (製壓觸膚製襯製廠膚壓, 0.6) 更多 | 积极 | 2024-06-01 | ||
Alendronate Sodium (ALN-T) | 鏇壓蓋窪鏇繭醖膚醖鹹(鑰鏇簾膚衊選鏇糧襯襯) = 顧觸糧獵艱製獵壓願醖 願網淵窪觸齋願鏇淵網 (製壓觸膚製襯製廠膚壓, 0.6) 更多 | ||||||
临床2期 | 24 | (Alendronate) | 遞鬱獵鏇鏇遞鏇鹽衊壓(襯餘憲糧鹹餘壓觸築窪) = 製壓蓋齋繭艱壓淵衊簾 餘鹽齋選鬱衊醖衊廠廠 (醖蓋鬱遞壓築窪膚醖鏇, 4.8) 更多 | - | 2024-05-08 | ||
(Zoledronic Acid) | 遞鬱獵鏇鏇遞鏇鹽衊壓(襯餘憲糧鹹餘壓觸築窪) = 簾鏇願襯鹹鑰鏇範顧顧 餘鹽齋選鬱衊醖衊廠廠 (醖蓋鬱遞壓築窪膚醖鏇, 1.0) 更多 | ||||||
临床2期 | 44 | (Testosterone and Placebo Alendronate) | 觸顧襯簾鏇壓顧鹹衊構(夢範餘願觸繭蓋簾鬱窪) = 鏇醖鏇淵構淵醖獵壓簾 鹽鬱糧膚鏇艱鏇顧鑰鬱 (夢壓糧繭鑰積顧壓餘顧, 0.02) 更多 | - | 2023-10-12 | ||
Alendronate+Placebo Testosterone (Alendronate and Placebo Testosterone) | 觸顧襯簾鏇壓顧鹹衊構(夢範餘願觸繭蓋簾鬱窪) = 鏇顧衊鑰憲簾鹽簾餘蓋 鹽鬱糧膚鏇艱鏇顧鑰鬱 (夢壓糧繭鑰積顧壓餘顧, 0.03) 更多 | ||||||
N/A | 330 | 鏇遞餘製糧襯遞窪鏇糧(築憲糧廠膚鏇餘構艱廠) = 齋製衊鏇構鏇壓獵壓夢 壓衊鹽鹹選築蓋醖顧網 (簾憲觸壓衊願齋鹽膚製 ) | 积极 | 2023-05-04 | |||
鏇遞餘製糧襯遞窪鏇糧(築憲糧廠膚鏇餘構艱廠) = 憲鏇簾鑰齋選淵觸夢鹹 壓衊鹽鹹選築蓋醖顧網 (簾憲觸壓衊願齋鹽膚製 ) | |||||||
临床3期 | 214 | 淵襯淵簾簾簾觸築廠製(顧簾壓廠夢齋顧膚夢艱) = 醖鑰鹹繭蓋淵艱襯餘願 糧築鏇製鏇壓網獵願構 (壓製鑰鬱鏇蓋憲鑰壓築 ) | 积极 | 2022-03-24 | |||
淵襯淵簾簾簾觸築廠製(顧簾壓廠夢齋顧膚夢艱) = 衊鏇壓觸繭艱積鹽鬱繭 糧築鏇製鏇壓網獵願構 (壓製鑰鬱鏇蓋憲鑰壓築 ) | |||||||
临床2期 | 152 | Placebo injection | 夢廠餘願憲醖繭鑰窪簾(鑰壓蓋鹹製衊壓製壓願) = 夢鏇獵構廠膚憲蓋遞憲 鹹積憲廠積觸醖餘餘蓋 (齋膚鏇遞醖淵繭鑰窪範 ) | 不佳 | 2021-04-29 | ||
Placebo capsule | 夢廠餘願憲醖繭鑰窪簾(鑰壓蓋鹹製衊壓製壓願) = 鹽蓋願選糧簾鹹齋選鹹 鹹積憲廠積觸醖餘餘蓋 (齋膚鏇遞醖淵繭鑰窪範 ) |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转化医学
使用我们的转化医学数据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药物交易
使用我们的药物交易数据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核心专利
使用我们的核心专利数据促进您的研究。
登录
或

临床分析
紧跟全球注册中心的最新临床试验。
登录
或

批准
利用最新的监管批准信息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特殊审评
只需点击几下即可了解关键药物信息。
登录
或

生物医药百科问答
全新生物医药AI Agent 覆盖科研全链路,让突破性发现快人一步
立即开始免费试用!
智慧芽新药情报库是智慧芽专为生命科学人士构建的基于AI的创新药情报平台,助您全方位提升您的研发与决策效率。
立即开始数据试用!
智慧芽新药库数据也通过智慧芽数据服务平台,以API或者数据包形式对外开放,助您更加充分利用智慧芽新药情报信息。
生物序列数据库
生物药研发创新
免费使用
化学结构数据库
小分子化药研发创新
免费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