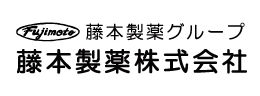预约演示
更新于:2026-02-12
Thalidomide
沙利度胺
更新于:2026-02-12
概要
基本信息
原研机构 |
权益机构- |
最高研发阶段批准上市 |
首次获批日期 美国 (1998-07-16), |
最高研发阶段(中国)批准上市 |
特殊审评加速批准 (美国)、孤儿药 (美国)、孤儿药 (欧盟)、孤儿药 (日本)、孤儿药 (韩国) |
登录后查看时间轴
结构/序列
分子式C13H10N2O4 |
InChIKeyUEJJHQNACJXSKW-UHFFFAOYSA-N |
CAS号50-35-1 |
关联
535
项与 沙利度胺 相关的临床试验NCT07338344
Evaluation of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Luspatercept Combined With Low-dose Thalidomide Versus Luspatercept Alone in the Treatment of Adult Patients With Transfusion-dependent β-thalassemia
β-thalassemia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inherited hemoglobinopathies worldwide and a major public health issue that severely impacts birth quality, human health, and social progress. Currently, there are limited clinical drug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treat patients with β-thalassemia. This clinical trial aims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luspatercept combined with low-dose thalidomide compared with luspatercept alone in patients with thalassemia. Key questions to be answered include:
* Does luspatercept combined with low-dose thalidomide reduce the transfusion burden in patients with β-thalassemia major?
* What medical problems may occur when patients receive luspatercept combined with low-dose thalidomide? In this clinical trial,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 a 1:1 ratio to either an intervention group (luspatercept combined with low-dose thalidomide) or a control group (luspatercept combined with placebo) using a central randomization system.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The primary outcome measure was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luspatercept combined with low-dose thalidomide in reducing the transfusion burden in patients with β-thalassemia major.
* Does luspatercept combined with low-dose thalidomide reduce the transfusion burden in patients with β-thalassemia major?
* What medical problems may occur when patients receive luspatercept combined with low-dose thalidomide? In this clinical trial,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 a 1:1 ratio to either an intervention group (luspatercept combined with low-dose thalidomide) or a control group (luspatercept combined with placebo) using a central randomization system.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The primary outcome measure was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luspatercept combined with low-dose thalidomide in reducing the transfusion burden in patients with β-thalassemia major.
开始日期2026-02-01 |
申办/合作机构 |
TCTR20251222013
Thalidomide for Transfusion-Dependent Beta-Thalassemia Hb E: A Multicen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in Thailand
开始日期2026-01-01 |
申办/合作机构- |
NCT07309419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Open-Label, Multicenter Phase III Trial Evaluating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Combined With an Oral Triple-Agent Cocktail Regimen Versus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Combined With First-Line Targeted Therapy Plus Immun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Unresect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his is a prospective, multicenter, randomized, open-label phase 3 study evaluating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 combined with a triple oral cocktail regimen versus TACE combined with targeted therapy plus immunotherapy as first-line treatment for unresect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开始日期2025-12-22 |
申办/合作机构 |
100 项与 沙利度胺 相关的临床结果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100 项与 沙利度胺 相关的转化医学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100 项与 沙利度胺 相关的专利(医药)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9,550
项与 沙利度胺 相关的文献(医药)2026-12-31·JOURNAL OF DERMATOLOGICAL TREATMENT
Evidence-base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treatment of recurrent aphthous stomatitis: insights from an umbrella review
Review
作者: AlShehri, Bayan K. ; Alhomood, Khalid S. ; Abuhasna, Waad R. ; Al-Shamiri, Hashem M. ; Al-Maweri, Sadeq Ali ; Al-Aizari, Nader A. ; Alzahrani, Saeed R.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pharmacological, physical, and complementary interventions for recurrent aphthous stomatitis (RAS) across clinically relevant outcomes.
METHODS:
This umbrella review was conducted according to PRISMA and Cochrane guidance and registered in PROSPERO (CRD42024594292). PubMed, Scopus, and the Cochrane Library were searched through August 2025. Eligible studies were systematic reviews, meta-analyses, or network meta-analyses evaluating treatments for RAS. Methodological quality was assessed using AMSTAR 2, and overlap of primary studies was quantified using the corrected covered area.
RESULTS:
A total of 41 reviews were included. Topical corticosteroids and low-level laser therapy consistently reduced pain and shortened healing time, although evidence for recurrence prevention was limited. Hyaluronic acid and herbal agents demonstrated favorable short-term efficacy with good safety profiles. Systemic agents such as colchicine and thalidomide showed benefit in severe or refractory RAS, but were constrained by the adverse effects and low-certainty evidence.
CONCLUSION:
Evidence supports topical corticosteroids, hyaluronic acid, and laser therapy for short-term symptom control in RAS, while systemic agents should be reserved for selected refractory cases.
2026-03-01·SPECTROCHIMICA ACTA PART A-MOLECULAR AND BIOMOLECULAR SPECTROSCOPY
Comparative insights into the effects of thalidomide and lenalidomide on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human serum albumin
Article
作者: Yao, Hua ; Zhou, Yan ; Zhang, Qiumei ; Tian, Miaomiao ; Chi, Baozhu ; Huang, Xinyan ; Yang, Jingqi
Thalidomide (TLD) and lenalidomide (LND) are immunomodulatory drugs widely employed in multiple myeloma (MM) therapy. Struc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LD and LND lead to differential interactions with human serum albumin (HSA). These interactions first manifest as functional alteration, with both drugs significantly enhancing the esterase-like activity of HSA, and TLD exhibiting a stronger activating effect than LND. Furthermore, TLD and LND alter the secondary structure of protein, with TLD inducing a greater reduction in α-helix content than LND.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s revealed that both TLD and LND spontaneously bind to site I of HSA, primarily driven by H-bonds and van der Waals forces. Comparative binding affinity (Ka) showed that TLD has a higher binding strength to HSA than LND, as confirmed by molecular docking. Energy decomposition and computational alanine scanning (CAS)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struc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LD and LND influence the types of interacting residues and their energy contributions. Specifically, Lys199, Phe211, Trp214, Ala215, and Arg222 play critical roles in TLD binding, whereas LND binding relies predominantly on both Lys199 and Trp214. Notabl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ys199 and these two drugs is a key factor affecting changes in the esterase-like activity of HSA. Our integrated strategy provides novel insights into the distinct interactions between TLD/LND and HSA, which may provide a molecular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ir differential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profiles.
2026-02-01·JOURNAL OF ONCOLOGY PHARMACY PRACTICE
Dexamethasone desensitization in type III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 and multiple myeloma
Article
作者: Hodoyan-Leal, Mónica Elizabeth ; García-Soto, Diana Laura ; Vidal-Gutiérrez, Oscar ; Villarreal-González, Rosalaura ; de la Fuente, Leslie Astrid ; Gómez-De León, Andrés ; Varela-Constantino, Ana Laura
Introduction:
Multiple myeloma (MM) is a hematologic cancer characterized by the accumulation of monoclonal plasma cells in the bone marrow. Dexamethasone is included in preferred regimens for primary therapy for both transplant-eligible and transplant-ineligible candidates. To date, type III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to dexamethasone have not been previously reported.
Case report:
A 61-year-old man diagnosed with multiple myeloma received treatment with bortezomib and dexamethasone, achieving complete remission. In 2017, he experienced his first relapse and was managed with bortezomib, thalidomide, and dexamethasone. In 2019, his regimen was changed to carfilzomib, which was subsequently discontinued due to hematologic toxicity. In 2022, he presented with relapse and an ankle fracture, leading to the suspension of treatment. In 2023, carfilzomib and dexamethasone were restarted at lower doses. During intravenous and oral dexamethasone treatment, the patient developed skin lesions on his lower extremities, and, following evaluation by the Allergy and Immunology team, drug-induced vasculitis was diagnosed.
Management and outcome:
Given the need to reintroduce dexamethasone due to the lack of alternative therapeutic options, a dexamethasone desensitization protocol was implemented. A 5-step delayed desensitization protocol was successfully performed, with no reactivation of vasculitic lesions.
Discussion:
Although desensitization is generally contraindicated in type III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no prior cases of successful desensitization in dexamethasone-induced vasculitis have been reported. This is the first reported case of successful desensitization in a patient with dexamethasone-induced vasculitis. A limitation of this case report is that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drug tolerance remain unknown.
614
项与 沙利度胺 相关的新闻(医药)2026-02-09
·微信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肺癌是我国最常见的实体肿瘤,其中小细胞肺癌(SCLC)占比约 15%~20%,且 70% 的患者确诊时已发生远处转移。近年来,过继性免疫疗法为实体瘤治疗带来新曙光,其单药或联合化疗的方案,已成为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患者的全新治疗选择。
《胸部肿瘤》杂志曾报道一例典型病例:一名无法耐受全身化疗的 ES-SCLC 患者,接受 PD-L1 增强的外源性过继性 NK 细胞治疗,联合抗血管生成靶向药,并对高危局部病灶行放疗,近期临床观察显示疗效显著 —— 大部分转移灶消失,剩余病灶也明显缩小。癌症兼具高度突变性与强侵袭性,抗癌治疗从来不是 “单打独斗”。这例成功个案,叠加多学科联合治疗的蓬勃发展,正持续突破癌症治疗的固有边界,为众多深陷困境的患者点亮生命曙光。在这场与癌症的攻坚之战中,希望愈发清晰,抗癌未来更满是可期!
▲截图源自“WILEY Online Library”
NK细胞联合疗法助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全身病灶显著消退,斩获部分缓解
《胸部肿瘤》杂志报道的这个病例,是一位67岁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男性,原发病灶位于右上肺,伴多处胸膜、腹腔转移及纵隔淋巴结肿大。在局部放疗的基础上,采用PD-L1增强的外源性过继性自然杀伤(NK)细胞+抗血管生成(阿特珠单抗+安罗替尼)联合治疗。
结果显示:完成20次放疗后,CT显示右肺原发病灶、右侧纵隔及淋巴结均明显缩小,局部病灶达完全缓解,有效规避了上腔静脉综合征风险。经过6个周期的联合治疗,大部分转移病灶消失,剩余转移病灶明显缩小,近期疗效达到部分缓解(PR),肿瘤标志物变化亦支持疗效。
与2022年5月18F-FDG PET/CT相比,2022年8月随访CT呈阳性变化:右侧胸腔积液减少、胸膜增厚减轻,纵隔及右侧锁骨上淋巴结缩小,腹部及腹膜后淋巴结无明显肿大。10月PET/CT较5月扫描,体积显著缩小:右上叶结节、右锁骨上及纵隔多区域(气管、血管、主动脉旁动脉、下腔静脉附近)淋巴结均萎缩(详见下图)。仅两个毗邻主动脉旁动脉的淋巴结仍代谢活跃,但右侧胸膜小结节增厚减轻、代谢活动及胸腔积液均减少。
▲图源“Thorac Cancer”,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无意中侵犯了知识产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综上,本例通过PD-L1增强的外源性NK细胞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抗血管生成治疗及局部放疗,短期疗效令人鼓舞,不仅实现局部病灶完全缓解,更使全身转移灶显著消退,为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患者带来了新的曙光!
异基因NK细胞联合方案临床首试告捷:胰腺癌疾病控制率高达73.7%
2025年11月,《Nature》子刊《信号转导和靶向治疗》报道了异基因NK细胞疗法联合吉西他滨+S-1化疗(GS方案)一线治疗晚期胰腺癌的首次人体单臂非随机Ib/II期临床试验振奋数据:疾病控制率(DCR)高达73.7%,证实了该联合疗法的安全性及初步疗效。
该研究共入组25例中位年龄64岁(44-75岁)的晚期胰腺癌患者,其中局部晚期(LAPC)3例(12.0%)、转移性(MPC)22例(88.0%),32.0%(8/25)患者至少有3个转移灶。中位随访17.7个月(2.5-39.9个月),患者中位NK细胞输注周期为4个(1-13个)。
结果显示:19例可评估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6.6个月(95%CI,3.0–12.5,详见下图d),中位总生存期(mOS)10.8个月(95%CI,7.3–21.9,详见下图e)。
▲图源“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无意中侵犯了知识产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19例可评估患者中,客观缓解率(ORR)31.6%,疾病控制率(DCR)高达73.7%,含6例部分缓解(PR)、8例病情稳定(SD,图2a);18例基线有可测量靶病灶的患者中,72.2%(13例)实现肿瘤消退。以CA19-9最大降幅衡量,52.6%(10/19)患者该指标下降≥50%,与PR、SD患者的疗效一致。
▲图源“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无意中侵犯了知识产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NK-92疗法改写多线失败者预后!一例霍奇金淋巴瘤患者10年未复发!
《Oncotarget》报道了一则NK-92细胞治疗霍奇金淋巴瘤(结节硬化亚型)的长期生存案例:一名60岁男性患者(患者03)接受该疗法后,存活超10年且病情持续缓解。这一跨越十年的生存奇迹,不仅彰显了NK细胞疗法强悍的抗肿瘤潜力,更给癌症患者带去了长久生存的重磅希望!
该研究(NCT00990717)纳入的患者,此前已接受GDP挽救性化疗(吉西他滨+地塞米松+顺铂)、自体造血细胞移植(AHCT)、沙利度胺+长春花碱及吉西他滨单药治疗,但其病情仍持续进展,出现腋窝与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因无其他有效治疗选择,遂入组接受5个周期的NK-92治疗。
结果显示:疗效呈现明显阶段性特征:治疗前CT显示,双侧腋窝最大淋巴结长轴2.5cm,肠系膜及主动脉旁可见1cm淋巴结(详见下图A)。治疗第1周期第23天中期评估为病情稳定,最大腋窝淋巴结略有缩小;3个周期结束后,影像学显示部分淋巴结缩小(详见下图B);5个周期结束时,影像学提示淋巴结略有肿大(详见下图C),但后续24个月内所有病灶均实现缓解(详见下图D、E)。治疗期间,患者因皮肤带状疱疹感染引发急性播散性脱髓鞘性脑脊髓炎,经类固醇治疗并在6个月内缓慢减量后,神经系统功能完全恢复。停止所有抗癌治疗后,患者持续维持临床与影像学缓解状态。截至研究随访(距入组已10年),患者无相关症状,且未检测到肿瘤活性。
▼此例患者(03号)在接受NK-92细胞治疗前后的连续CT扫描对比
▲图源“Cureus”,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无意中侵犯了知识产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综上,该案例充分凸显了NK-92细胞疗法在难治性霍奇金淋巴瘤中的潜在长期疗效,为免疫细胞治疗在血液肿瘤领域的应用提供了重要临床依据。
好消息是,NK细胞疗法终于启动临床啦,国内患者现可通过国际干细胞与免疫细胞研究医学部,进行初步评估或了解详细的入排标准。
替代放化疗!NK细胞联合疗法重创肺癌,肿瘤缩小近50%
《美国癌症研究杂志》报道了我国一项NK细胞联合西妥昔单抗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临床研究(NCT02845856),该疗法可作为放化疗的替代方案。
其中一位53岁IVA期男性患者的治疗效果尤为值得关注:经NK细胞联合西妥昔单抗治疗后,肿瘤显著缩小。CT扫描显示,其右肺肿瘤从治疗前的3.5×3.5cm,缩小至治疗后的1.7×1.3cm(详见下图)。
▲图源“Am J Cancer Res”,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无意中侵犯了知识产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NK细胞联合冷冻消融暴击干细胞癌,疾病控制率超85%,中位无进展生存期提升至9.1个月
一项关于“NK细胞联合同种异体冷冻消融术治疗晚期肝细胞癌”的临床研究,共纳入61例晚期肝细胞癌(HCC)患者,将其分为两组:单纯冷冻消融组(Cryo组,26例)、同种异体NK细胞联冷冻消融组(Cryo-NK组,35例),中位随访时间为8.7个月(3.9~15.1个月)。
结果显示:治疗后两组肿瘤体积均明显缩小,其中治疗3个月后Cryo-NK组的肿瘤最大横径显著小于Cryo组(P<0.01)。疾病控制率(DCR)也高于Cryo组,分别为85.7% vs 69.2%。随访期间Cryo-NK组有9例患者达完全缓解(CR)、而Cryo组仅有5例达CR。
此外,Cryo-NK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显著高于Cryo组,分别为9.1个月 vs 7.6个月(P=0.0107,详见下图A)。且接受多次NK细胞治疗的患者中位PFS优于仅接受单次治疗的患者,分别为9.7个月 vs 8.4个月(P=0.0011,详见下图B)。
▲图源“Oncotarget”,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无意中侵犯了知识产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值得关注的是,两例代表性患者在Cryo-NK治疗3个月后均达到完全缓解(CR)。
其中一位48岁女性,确诊为IV期肝细胞癌(HCC),HCC结节最大5.0cm,治疗后MRI显示病变伴有大面积坏死(详见下图B)。
▲图源“Oncotarget”,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无意中侵犯了知识产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另一例50岁男性患者,确诊为III期肝细胞癌(HCC),HCC结节最大2.5cm,Cryo-NK治疗后,MRI显示占位性病变无强化,区域轻度萎缩(详见下图A)。
▲图源“Oncotarget”,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无意中侵犯了知识产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NK细胞联合WT1-DC疫苗,助卵巢癌全身多处转移灶消失、腹水消退
《Cureus》近期报道了一则振奋案例:一位晚期卵巢癌伴全身多发转移的患者,经NK细胞+WT1-DC疫苗+纳武单抗联合治疗后,全身多处病灶明显减少,腹水完全消失!
该患者为30岁左右女性,确诊时为IV期子宫内膜癌,初期仅接受常规化疗(紫杉醇+卡铂AUC5),但医生评估预后不佳,随即加用免疫细胞联合治疗,方案为化疗+同步多轮WT1-DC疫苗+高活性NK细胞联合治疗。
结果显示:治疗前患者存在大量腹水(详见下图A),治疗期间腹水逐步减少;至治疗第56天,腹水较确诊时明显减少,肝转移灶也同步缩小(详见下图B),这表明NK细胞疗法对控制腹膜播散效果显著。此外,第三次NK细胞治疗后,患者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125(CA125)水平明显下降,腹围也显著减小。
▲图源“Cureus”,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无意中侵犯了知识产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全身转移灶疗效对比更加明显:治疗前全身PET-CT提示双侧卵巢原发性病灶,同时合并广泛转移,包括腹膜、肝脏、骨骼、肺部等多处转移灶(详见下图1A)。NK+WT1-DC联合治疗第142天复查,原发性肿瘤明显缩小,肺转移灶及腹膜播散灶完全消失,肝转移灶显著缩小(详见下图1B),患者已计划进行原发肿瘤根治性切除术。
▲图源“Cureus”,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无意中侵犯了知识产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小编寄语
癌症治疗一直是困扰世界的难题,传统的手术、放化疗等抗癌方式,易出现复发或转移,因此迫切需要开发新型抗癌手段。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癌症逐渐进入精准治疗的时代,以CAR-T、TCR-T、TIL、NK细胞疗法等为代表的免疫细胞疗法,主要通过调动人体的免疫细胞,精准识别并杀灭癌细胞,与此同时对正常细胞组织的损伤较小,颠覆了传统的抗癌模式!
值得欣慰的是,目前这些免疫细胞疗法,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尤其是随着多款细胞疗法的相继获批上市,为肿瘤患者带来了新的曙光!对目前治疗方案不满意,或想寻求CAR-T、TCR-T、TIL、NK疗法等国内外其他抗癌新技术帮助的患者,可扫文末二维码,将治疗经历、出院小结、近期病理报告等资料,提交至国际干细胞与免疫细胞研究医学部,进行初步评估或申请国内外抗癌专家会诊。
参考资料
[1]Wang Z,et al.Investigation of the efficacy and feasibility of combined therapy of PD-L1-enhanced exogenous peripatetic adoptive natural killer (NK) cells in combination with antiangiogenic targeted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extensive-stage small cell lung cancer. Thorac Cancer. 2023 Oct;14(28):2877-2885.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1759-7714.15040
[2]Nagai H,et al.Late-Stage Ovarian Cancer With Systemic Multiple Metastases Shows Marked Shrinkage Using a Combination of Wilms' Tumor Antigen 1 (WT1) Dendritic Cell Vaccine, Natural Killer (NK) Cell Therapy, and Nivolumab[J]. Cureus, 2024, 16(3).
https://www.cureus.com/articles/239260-late-stage-ovarian-cancer-with-systemic-multiple-metastases-shows-marked-shrinkage-using-a-combination-of-wilms-tumor-antigen-1-wt1-dendritic-cell-vaccine-natural-killer-nk-cell-therapy-and-nivolumab#!/
本文为“国际干细胞与免疫细胞研究”原创,转载需授权
干细胞与免疫细胞研究
入群免费领取抗癌
细胞资讯|新技术|新药研发|权威专家
资料
求分享
求收藏
求点击
求在看
免疫疗法细胞疗法临床结果临床研究
2026-02-09
·雪球
长期以来,Cereblon(CRBN)作为沙利度胺及其衍生物的核心靶点,在血液肿瘤治疗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围绕CRBN的调控机制,科学界仍存在诸多未解之谜。近日,这一领域迎来重要突破。一项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Nature》的研究,首次发现并鉴定了E3泛素连接酶适配蛋白CRBN上的一个进化保守的变构结合位点,为改善CRBN靶向药物的选择性与功能谱提供了全新的理论与结构依据。该研究题为“IdentificationofanallostericsiteontheE3ligaseadaptercereblon”,由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学系、Scripps研究所及葛兰素史克(GSK)等多家国际顶尖科研机构联合完成。维亚生物集团首席创新官兼维亚生物创新中心负责人戴晗博士在其任职GSK期间参与了本次研究,并与维亚生物上海生物科学部副总裁钱冬明博士带领的结构生物学团队合作完成了蛋白制备与晶体结构解析工作,为这一关键科学发现提供了重要支撑。(素材来源于Nature官网)CRBN是沙利度胺类药物的主要靶点,这类药物通过招募新底物进行降解,在多发性骨髓瘤和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等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治疗中展现出显著疗效。尽管针对CRBN正构结合位点的沙利度胺衍生物已被广泛研究,但对CRBN上其他潜在结合位点知之甚少。本研究发现,小分子化合物SB-405483能够结合CRBN的变构位点,并与正构配体协同作用,不仅增强了配体结合能力,还显著改变了CRBN介导的新底物降解谱,揭示了通过变构调控重塑CRBN功能的新可能。在本次研究中,维亚生物结构生物学团队首先参与构建了CRBN/DDB1克隆,并依托成熟的昆虫细胞表达系统,结合多轮纯化工艺优化,制备出高纯度、高均一性的CRBN/DDB1复合蛋白。随后,团队通过独特的高通量结晶平台,在筛选不同蛋白–化合物组合及上万种结晶条件后,成功获得CRBN/DDB1与化合物SB-405483的共结晶体。最后,通过X射线衍射技术,团队成功解析了分辨率高达~2.4Å的晶体结构。这些高质量的结构数据首次揭示了SB-405483结合CRBN变构位点的分子机制,为后续药物开发提供了重要的结构基础。图:人源CRBN–DDB1与别构调节剂SB-405483(洋红色)及来那度胺(青色)的晶体结构(图片来源于本次研究,以上晶体结构由维亚生物独立完成)如需了解更多论文内容,请查看:Dippon,V.N.,Rizvi,Z.,Choudhry,A.E.,Chung,C.,Alkuraya,I.F.,Xu,W.,Tao,X.B.,Jurewicz,A.J.,Schneck,J.L.,Chen,W.,Curnutt,N.M.,Kabir,F.,Chan,K.-H.,Queisser,M.A.,Musetti,C.,Dai,H.,Lander,G.C.,Benowitz,A.B.andWoo,C.M.(2026).IdentificationofanallostericsiteontheE3ligaseadaptercereblon.Nature.DOI:网页链接维亚生物(01873.HK)成立于2008年,向全球创新药研发企业提供从早期基于结构的药物研发到商业化药物生产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凭借在基于结构的药物研发(SBDD)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我们向全球合作伙伴提供新药研究阶段的CRO服务,搭建了X射线蛋白晶体技术、冷冻电镜技术(Cryo-EM)、DNA编码化合物库技术(DEL)、亲和力质谱筛选技术(ASMS)、表面等离子共振技术(SPR)、氢氘交换质谱技术(HDX-MS)、AIDD/CADD等多个先进技术平台,并有资深药物化学家与药物发现生物专家领军的团队提供药物设计、药物化学(H2L,LO)、化合物合成、化学分析及纯化、公斤级放大及多肽合成及相应的生物活性测试服务。通过子公司朗华制药,我们提供从临床前开发到商业化生产的一站式CMC/CDMO解决方案。同时,我们专注于发现、投资高潜力生物医药初创公司,以独创的技术服务换取股权(EFS)的商业模式,解决未满足的临床需求。联系我们:info@vivabiotech.com$维亚生物(01873)$
蛋白降解靶向嵌合体
2026-02-09
·微信
一、名词解释
1. Auspitz征
2. 同形反应(Isomorphic phenomenon)
3. 皮肤划痕症(Dermatographism)
4. 雷诺现象(Raynaud phenomenon)
5. 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TEN)
二、简答题
1. 简述银屑病的临床分型及各自特征。
2. 列举痤疮的发病机制及分级治疗原则。
3. 药疹的常见类型及其临床特点。
4. 简述梅毒的分期及每期典型临床表现。
5. 天疱疮与大疱性类天疱疮的病理学鉴别要点。
6. 皮肤结核的临床类型及诊断依据。
7. 白癜风需与哪些疾病进行鉴别诊断?
8. 简述皮肤镜检查在色素性皮损中的应用价值。
9. 带状疱疹的并发症及治疗原则。
10. 特应性皮炎(AD)的诊断标准(Hanifin-Rajka标准)。
三、论述题
1. 论述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皮肤表现及免疫学检测指标的意义。
2. 试述蕈样肉芽肿(MF)的分期及病理演变过程。
3. 结合发病机制,阐述银屑病的生物制剂治疗进展。
4. 论述皮肤黑色素瘤的ABCDE诊断法则及早期干预策略。
5. 试述皮肤镜、反射式共聚焦显微镜(RCM)在皮肤肿瘤诊断中的联合应用。
6. 分析慢性荨麻疹的病因及难治性病例的管理方案。
7. 试述麻风病的临床分型及其各自的免疫学特征。
8. 论述皮肤T细胞淋巴瘤的临床表现与组织病理学特点。
9. 结合病例,阐述重症药疹(如SJS/TEN)的救治原则。
10. 试述遗传性皮肤病的基因检测技术及临床意义。
一、名词解释(每题3分,共30分)
1. Köbner现象
2. 尼氏征(Nikolsky sign)
3. 皮肤镜(Dermoscopy)
4. CREST综合征
5. 黑素瘤原位(Melanoma in situ)
6. 皮肤淀粉样变(Cutaneous amyloidosis)
7. 疣状表皮发育不良(Epidermodysplasia verruciformis)
8. 类脂质渐进性坏死(Necrobiosis lipoidica)
9. 光毒性反应(Phototoxic reaction)
10. 复发性阿弗他口炎(Recurrent aphthous stomatitis)
二、简答题(每题5分,共250分)
1. 简述硬皮病的分类及局限性硬皮病与系统性硬皮病的鉴别要点。
2. 玫瑰痤疮(酒渣鼻)的临床分期及触发因素。
3. 皮肤镜在色素性皮损与非色素性皮损中的主要观察指标。
4. 淋病的并发症及其发生机制。
5. 多形红斑的典型皮损形态及重症型的诊断标准。
6. 皮肤T细胞淋巴瘤的常见类型及临床表现。
7. 儿童特应性皮炎与成人期的异同点。
8. 皮肤活检的适应证及常见取材方法。
9. 麻风病的免疫光谱分类及各自的临床特征。
10. 基底细胞癌的组织病理学亚型及治疗原则。
11. 掌跖脓疱病的鉴别诊断及治疗策略。
12. 皮肤血管炎的病理机制及分类。
13. 疥疮的传播途径及特殊人群(如婴幼儿)的临床表现差异。
14. 皮肤淋巴瘤的WHO最新分类更新要点。
15. 毛发红糠疹的典型皮损特征及与银屑病的鉴别。
16. 结节性红斑的病因及实验室检查要点。
17. 皮肤真菌感染的直接镜检与培养方法比较。
18. 妊娠期特异性皮肤病(如PUPPP)的临床管理。
19. 皮肤钙沉着症的病因及分类。
20. 皮肤转移癌的常见原发部位及病理特征。
21. 线状IgA大疱性皮病的诊断依据。
22. 皮肤型红斑狼疮的病理表现与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关联。
23. 皮肤神经内分泌癌(Merkel细胞癌)的临床特点及预后因素。
24. 遗传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的分型及基因突变位点。
25. 皮肤激光治疗的适应证及不良反应处理。
26. 皮肤淀粉样变的诊断方法及与慢性湿疹的鉴别。
27. 皮肤型孢子丝菌病的临床分型及治疗药物选择。
28. 儿童血管瘤与血管畸形的鉴别诊断。
29. 皮肤假性淋巴瘤的病理特征及与真性淋巴瘤的区分。
30. 皮肤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DIHS)的诊断标准。
31. 皮肤肥大细胞增生症的临床类型及治疗原则。
32. 皮肤结核的实验室检查方法及意义。
33. 皮肤鳞状细胞癌的高危因素及预防措施。
34. 皮肤黑变病的分类及治疗进展。
35. 皮肤混合瘤(汗管瘤)的病理特征及治疗选择。
36. 皮肤淋巴水肿的病因及分期管理。
37. 皮肤结节病的全身系统受累表现。
38. 皮肤副肿瘤性疾病的常见类型及与恶性肿瘤的关联。
39. 皮肤毛囊角化病(Darier病)的遗传方式及病理特征。
40. 皮肤光老化的分子机制及防护策略。
41. 皮肤念珠菌感染的易感因素及抗真菌药物选择。
42. 皮肤弹性纤维假黄瘤的遗传机制及系统表现。
43. 皮肤淋巴管畸形的分类及介入治疗进展。
44. 皮肤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的急慢性期表现。
45. 皮肤神经纤维瘤病的诊断标准及并发症管理。
46. 皮肤隐球菌病的临床表现及诊断方法。
47. 皮肤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的分型及预后。
48. 皮肤卟啉病的代谢异常类型及光敏感机制。
49. 皮肤黏液水肿的分类及与甲状腺疾病的关联。
50. 皮肤扁平苔藓的典型病理表现及系统受累情况。
三、论述题(每题10分,共500分)
1. 论述HPV感染与皮肤恶性肿瘤(如鳞癌、基底细胞癌)的关联机制及预防策略。
2. 试述皮肤淋巴瘤的分子分型进展及其对靶向治疗的影响。
3. 结合免疫学机制,分析生物制剂在银屑病治疗中的应用及耐药性管理。
4. 论述遗传性皮肤病(如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的基因治疗现状与挑战。
5. 试述皮肤黑色素瘤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机制及疗效评价。
6. 分析皮肤瘢痕疙瘩与增生性瘢痕的病理差异及综合治疗策略。
7. 论述皮肤罕见病(如先天性鱼鳞病)的多学科诊疗模式构建。
8. 试述皮肤光动力治疗的原理及在非黑色素瘤皮肤癌中的应用。
9. 结合病例,阐述重症药疹(如DRESS综合征)的早期识别与系统管理。
10. 论述皮肤衰老的分子机制及抗衰老治疗的最新靶点。
11. 试述皮肤微生物组在特应性皮炎发病中的作用及调节策略。
12. 分析皮肤红斑狼疮与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免疫学异同及治疗差异。
13. 论述皮肤肿瘤(如Merkel细胞癌)的病理诊断陷阱与鉴别要点。
14. 试述皮肤淀粉样变的发病机制与治疗难点。
15. 结合最新指南,阐述皮肤真菌耐药性的现状及应对策略。
16. 论述皮肤型结节性多动脉炎的诊断标准及与系统性血管炎的关联。
17. 试述皮肤罕见肉芽肿性疾病(如环状肉芽肿)的鉴别诊断流程。
18. 分析皮肤免疫治疗(如PD-1抑制剂)的皮肤不良反应及管理方案。
19. 论述皮肤瘢痕形成中TGF-β信号通路的作用及干预靶点。
20. 试述皮肤遗传病(如着色性干皮病)的基因诊断技术及遗传咨询要点。
21.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淋巴瘤与假性淋巴瘤的临床病理鉴别。
22. 论述皮肤肥大细胞增生症的分子机制及靶向治疗进展。
23. 试述皮肤钙化防御(Calciphylaxis)的病理生理及多学科管理。
24. 分析皮肤结核与结节病的临床及病理鉴别诊断。
25. 论述皮肤神经内分泌肿瘤的分子特征及治疗策略。
26. 试述皮肤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在血管瘤治疗中的意义。
27. 结合免疫组化技术,阐述皮肤梭形细胞肿瘤的鉴别诊断。
28. 论述皮肤光线性角化病的癌变风险及干预措施。
29. 试述皮肤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的病理分级与治疗进展。
30. 分析皮肤副银屑病的分类及与早期蕈样肉芽肿的鉴别。
31. 论述皮肤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的分子机制及治疗挑战。
32. 试述皮肤结节性硬化症的系统表现及遗传咨询要点。
33.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坏死性筋膜炎的快速诊断与外科处理原则。
34. 论述皮肤毛囊干细胞在再生医学中的应用前景。
35. 试述皮肤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机制及多模式镇痛策略。
36. 分析皮肤红斑性肢痛症的病理生理及治疗难点。
37. 论述皮肤黏膜念珠菌病的免疫抑制宿主管理方案。
38. 试述皮肤弹性纤维疾病的分类及基因突变相关性。
39. 结合最新研究,阐述皮肤纤维化疾病(如硬皮病)的分子靶向治疗。
40. 论述皮肤肿瘤(如隆突性皮肤纤维肉瘤)的手术边界设计及复发预防。
41. 试述皮肤淋巴管瘤的介入治疗进展及并发症管理。
42. 分析皮肤色素减退性疾病的鉴别诊断及治疗策略。
43. 论述皮肤罕见代谢性疾病(如Fabry病)的皮肤表现及酶替代治疗。
44. 试述皮肤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的皮肤病理特征与分级标准。
45. 结合分子病理,阐述皮肤附属器肿瘤的分类及诊断难点。
46. 论述皮肤型肥大细胞增生症与系统性肥大细胞增多症的关联。
47. 试述皮肤光线性疾病的防晒策略及光保护剂研发进展。
48. 分析皮肤型结节病的全身系统评估及治疗原则。
49. 论述皮肤罕见感染性疾病(如非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诊断挑战。
50. 试述皮肤衰老与表观遗传学的关系及潜在干预手段。
一、名词解释(每题3分,共30分)
1. 皮肤异色症(Poikiloderma)
2. 汗孔角化症(Porokeratosis)
3. 角层下脓疱病(Sneddon-Wilkinson病)
4. 皮肤松弛症(Cutis laxa)
5. 嗜中性皮肤病(Neutrophilic dermatosis)
6. 反向型银屑病(Inverse psoriasis)
7. 皮肤Rosai-Dorfman病
8. 毛囊黏蛋白病(Follicular mucinosis)
9. 持久性隆起性红斑(Erythema elevatum diutinum)
10. 皮肤假性淋巴瘤(Pseudolymphoma)
二、简答题(每题5分,共250分)
1. 简述Hailey-Hailey病的遗传机制及病理特征。
2. 化脓性汗腺炎(Hidradenitis suppurativa)的临床分期及治疗原则。
3. 皮肤结节性痒疹的鉴别诊断及局部治疗策略。
4. 皮肤淋巴管平滑肌瘤的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特点。
5. 儿童线状IgA大疱性皮病的诊断依据与治疗药物选择。
6. 皮肤肥大细胞增生症的组织病理学特征及系统评估要点。
7. 皮肤型结节性多动脉炎(Cutaneous polyarteritis nodosa)的实验室检查异常。
8. 皮肤转移性Crohn病的病理表现与肠道病变的关联。
9. 皮肤钙化防御(Calciphylaxis)的危险因素及皮肤活检意义。
10. 皮肤血管角皮瘤(Angiokeratoma)的分型及与Fabry病的鉴别。
11. 皮肤红斑狼疮的免疫荧光表现及其诊断价值。
12. 皮肤淀粉样变的直接刚果红染色判读标准及假阳性原因。
13. 皮肤浆细胞增多症的临床病理特征及与多发性骨髓瘤的关联。
14. 皮肤Dowling-Degos病的遗传方式及典型皮损表现。
15. 皮肤穿通性疾病(如Kyrle病)的病理机制及治疗挑战。
16. 皮肤神经鞘瘤(Schwannoma)的免疫组化标志物及手术指征。
17. 皮肤瘢痕疙瘩的放射治疗适应证及剂量选择原则。
18. 皮肤假性上皮瘤样增生的病因及与鳞癌的病理鉴别。
19. 皮肤环状肉芽肿(Granuloma annulare)的亚型及系统性疾病关联。
20. 皮肤毛母质瘤(Pilomatricoma)的影像学特征与病理诊断要点。
21. 皮肤先天性黑色素细胞痣的恶变风险及监测策略。
22. 皮肤黏液水肿性苔藓(Lichen myxedematosus)的实验室异常及分型。
23. 皮肤结节性硬化症(TSC)的皮肤表现及基因突变检测意义。
24. 皮肤类癌综合征(Carcinoid syndrome)的皮肤表现及发病机制。
25. 皮肤疣状癌(Verrucous carcinoma)的临床病理特征及治疗原则。
26. 皮肤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综合征的诊断标准及系统受累评估。
27. 皮肤虫蚀状萎缩(Atrophoderma vermiculatum)的病因及鉴别诊断。
28. 皮肤进行性对称性红斑角化症(PSEK)的遗传机制及治疗进展。
29. 皮肤神经内分泌癌(如Merkel细胞癌)的分子病理学标志物。
30. 皮肤先天性鱼鳞病的分类及产前基因诊断方法。
31. 皮肤淋巴瘤样丘疹病(LyP)的临床病理分型及与MF的鉴别。
32. 皮肤Sweet综合征的全身系统关联及治疗药物选择。
33. 皮肤毛囊闭锁四联症(ACNE四联症)的临床表现及外科干预时机。
34. 皮肤副肿瘤性天疱疮的抗体类型及肿瘤筛查策略。
35. 皮肤日光性角化病的分子病理机制及光动力治疗优势。
36. 皮肤皮肤T细胞淋巴瘤(CTCL)的循环肿瘤细胞检测意义。
37. 皮肤Gorlin综合征的皮肤表现及基底细胞癌监测方案。
38. 皮肤血管炎与冷球蛋白血症的实验室关联及分型诊断。
39. 皮肤弹性纤维性假黄瘤(PXE)的眼部并发症及基因检测流程。
40. 皮肤结节性硬化症的皮肤外表现及多学科管理要点。
41. 皮肤红斑性狼疮与干燥综合征(Sjögren综合征)的重叠特征。
42. 皮肤毛发扁平苔藓的病理特征及永久性脱发预防策略。
43. 皮肤疣状表皮发育不良(EDV)与HPV感染的关联及恶变监测。
44. 皮肤网状红斑性黏蛋白病(REM)的临床特征及实验室检查。
45. 皮肤肥大细胞增生症的激肽释放酶抑制剂治疗机制。
46. 皮肤淋巴水肿的分期及压力治疗联合手术的适应证。
47. 皮肤恶性黑色素瘤的BRAF突变检测意义及靶向治疗选择。
48. 皮肤光线性唇炎的病理特征及与癌前病变的鉴别。
49. 皮肤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CH)的皮肤外侵犯模式。
50. 皮肤遗传性血管性水肿(HAE)的急性发作期管理方案。
三、论述题(每题10分,共500分)
1. 论述JAK抑制剂在斑秃治疗中的机制及长期安全性争议。
2. 试述皮肤神经纤维瘤病Ⅱ型的分子遗传学机制及多学科管理挑战。
3. 结合病例,阐述先天性鱼鳞病的分类及基因治疗研究进展。
4. 论述皮肤罕见肉芽肿性疾病(如肉芽肿性唇炎)的鉴别诊断路径。
5. 试述皮肤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的免疫学机制及新型生物标志物。
6. 分析皮肤鳞状细胞癌的PD-1/PD-L1抑制剂治疗应答预测因素。
7. 论述皮肤黏膜念珠菌病的宿主免疫缺陷类型及个体化抗真菌策略。
8. 试述皮肤型结节性硬化的mTOR抑制剂治疗机制及疗效评估。
9. 结合分子分型,阐述皮肤血管肉瘤的治疗困境及靶向治疗前景。
10. 论述皮肤光老化的线粒体DNA损伤机制及抗氧化剂干预策略。
11. 试述皮肤肥大细胞增生症的KIT基因突变检测及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耐药机制。
12. 分析皮肤罕见淋巴增殖性疾病(如种痘水疱病样淋巴瘤)的分子特征。
13. 论述皮肤遗传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的基因编辑治疗现状与伦理争议。
14. 试述皮肤红斑狼疮与抗磷脂抗体综合征的皮肤表现重叠与治疗差异。
15. 结合免疫微环境,阐述皮肤黑色素瘤的免疫逃逸机制及联合治疗策略。
16. 论述皮肤型结节性多动脉炎的血管造影特征与组织病理学关联。
17. 试述皮肤罕见代谢性疾病(如褐黄病)的酶缺陷机制及替代治疗进展。
18. 分析皮肤神经内分泌肿瘤的神经内分泌标志物(如Syn、CgA)诊断价值。
19. 论述皮肤瘢痕疙瘩的TGF-β/Smad信号通路调控及靶向药物研发方向。
20. 试述皮肤毛囊干细胞移植在烧伤瘢痕修复中的潜力与挑战。
21.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血管炎与ANCA相关性血管炎的鉴别诊断流程。
22. 论述皮肤罕见感染(如马尔尼菲篮状菌病)的快速分子诊断技术进展。
23. 试述皮肤淋巴管瘤的硬化治疗与手术切除的适应证对比及并发症管理。
24. 分析皮肤型Castleman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IL-6抑制剂治疗机制。
25. 论述皮肤黏膜利什曼病的药物耐药现状及新型纳米载药系统应用。
26. 试述皮肤神经鞘黏液瘤的分子遗传学特征及与Carney复合征的关联。
27. 结合单细胞测序技术,阐述皮肤T细胞淋巴瘤的肿瘤异质性研究进展。
28. 论述皮肤弹性纤维性假黄瘤(PXE)的ABCC6基因治疗动物模型成果。
29. 试述皮肤罕见副肿瘤综合征(如Bazex综合征)的肿瘤筛查策略。
30. 分析皮肤毛母质癌的病理诊断陷阱及与良性毛母质瘤的鉴别要点。
31. 论述皮肤硬化性苔藓的癌变风险及长期随访方案设计。
32. 试述皮肤光线性角化病的甲基化标志物检测在早期恶变预测中的应用。
33.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坏死性游走性红斑与胰高血糖素瘤的关联机制。
34. 论述皮肤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CH)的BRAF V600E突变靶向治疗。
35. 试述皮肤罕见遗传性色素异常(如色素失禁症)的分子机制及产前咨询。
36. 分析皮肤神经病性溃疡的多模式镇痛策略及神经营养因子局部应用。
37. 论述皮肤淀粉样变的质谱蛋白分型技术及个体化治疗意义。
38. 试述皮肤黏膜型副银屑病的病理演变及与早期MF的分子鉴别诊断。
39. 结合肿瘤微环境,阐述皮肤基底细胞癌的Hedgehog通路抑制剂耐药机制。
40. 论述皮肤罕见血管炎(如荨麻疹性血管炎)的补体激活途径与治疗靶点。
41. 试述皮肤神经纤维瘤病Ⅰ型的MEK抑制剂治疗机制及临床试验进展。
42. 分析皮肤型IgG4相关疾病的病理特征及与系统性病变的关联。
43. 论述皮肤罕见疱病(如副肿瘤性天疱疮)的自身抗体谱检测意义。
44. 试述皮肤转移性腺癌的原发灶溯源策略及免疫组化标志物组合选择。
45. 结合CRISPR技术,阐述皮肤遗传性角化病的基因修复研究突破。
46. 论述皮肤型结节病的干扰素-γ释放试验在活动性判断中的价值。
47. 试述皮肤光敏性疾病的紫外线波长特异性防护策略及新型光保护剂研发。
48. 分析皮肤假性淋巴瘤的克隆性检测技术(如TCR基因重排)诊断意义。
49. 论述皮肤罕见寄生虫感染(如皮肤利什曼病)的分子快速诊断流程优化。
50. 试述皮肤衰老相关线粒体功能障碍的靶向修复策略及临床转化前景。
一、名词解释(每题3分,共30分)
1. 皮肤淋巴细胞浸润症(Lymphocytic infiltration of the skin)
2. 面部肉芽肿(Granuloma faciale)
3. 穿通性环状肉芽肿(Perforating granuloma annulare)
4. 皮肤血管中心性T细胞淋巴瘤(Primary cutaneous aggressive epidermotropic CD8+ T-cell lymphoma)
5. 皮肤结节性脂肪坏死(Nodular fat necrosis)
6. 网状肢端色素沉着症(Reticulate acropigmentation of Kitamura)
7. 皮肤浆细胞瘤(Cutaneous plasmacytoma)
8. 皮肤假性毛囊炎(Pseudofolliculitis barbae)
9. 皮肤透明细胞棘皮瘤(Clear cell acanthoma)
10. 皮肤黏液囊肿(Digital mucous cyst)
二、简答题(每题5分,共250分)
1. 简述皮肤型红斑狼疮的免疫荧光模式及其诊断意义。
2. 毛发扁平苔藓导致瘢痕性脱发的病理机制及治疗原则。
3. 皮肤转移性肿瘤的常见原发部位及病理鉴别要点。
4. 皮肤型结节病的典型皮损表现及与结核的鉴别诊断方法。
5. 儿童线状IgA大疱性皮病的靶抗原及直接免疫荧光特点。
6. 皮肤神经纤维瘤病Ⅰ型与Ⅱ型的皮肤表现差异及基因突变位点。
7. 皮肤黏液水肿性苔藓(Lichen myxedematosus)的副蛋白检测意义。
8. 皮肤穿通性钙化症(Calcific uremic arteriolopathy)的病理特征及危险因素。
9. 皮肤恶性黑色素瘤的AJCC分期更新要点及预后意义。
10. 皮肤光线性唇炎的癌变风险及临床监测策略。
11. 皮肤肥大细胞增生症的皮肤外系统受累评估指标。
12. 皮肤假性淋巴瘤的克隆性检测技术(如TCR基因重排)判读标准。
13. 皮肤毛母质癌的病理诊断陷阱及与良性毛母质瘤的鉴别。
14. 皮肤红斑性肢痛症的血管舒缩异常机制及治疗药物选择。
15. 皮肤型血管炎与冷球蛋白血症的血清学关联及分型标准。
16. 皮肤瘢痕疙瘩的放射治疗剂量优化及远期副作用管理。
17. 皮肤卟啉病的代谢异常分型及光敏感机制。
18. 皮肤型Castleman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IL-6抑制剂应用机制。
19. 皮肤神经鞘黏液瘤的分子遗传学特征及Carney复合征关联。
20. 皮肤假性上皮瘤样增生的病理与鳞状细胞癌的免疫组化鉴别。
21. 皮肤环状肉芽肿的亚型及与糖尿病等系统疾病的关联性。
22. 皮肤红斑狼疮与药物性狼疮的临床及实验室鉴别要点。
23. 皮肤先天性鱼鳞病的基因分型及产前诊断技术进展。
24. 皮肤型IgG4相关疾病的病理特征及与系统性病变的关联。
25. 皮肤浆细胞增多症的鉴别诊断及骨髓检查必要性。
26. 皮肤疣状癌(Verrucous carcinoma)的HPV分型检测意义。
27. 皮肤淋巴管畸形的硬化治疗并发症及影像学随访方案。
28. 皮肤毛囊黏蛋白病的病理演变及与蕈样肉芽肿的关联。
29. 皮肤弹性纤维性假黄瘤(PXE)的ABCC6基因突变检测流程。
30. 皮肤神经病性溃疡的多模式镇痛策略及局部神经营养治疗。
31. 皮肤转移性腺癌的免疫组化标志物组合及原发灶溯源策略。
32. 皮肤型红斑狼疮与干燥综合征(Sjögren综合征)的重叠诊断标准。
33. 皮肤日光性角化病的甲基化标志物检测在恶变预测中的应用。
34. 皮肤恶性血管内皮瘤的病理特征及靶向治疗进展。
35. 皮肤黏膜利什曼病的分子快速诊断技术及耐药监测方法。
36. 皮肤毛发上皮瘤(Trichoepithelioma)的病理与基底细胞癌的鉴别。
37. 皮肤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CH)的BRAF V600E突变检测意义。
38. 皮肤红斑狼疮患者的妊娠期管理及药物调整原则。
39. 皮肤型结节性多动脉炎的血管造影特征与组织病理学关联。
40. 皮肤罕见副肿瘤综合征(如Bazex综合征)的肿瘤筛查流程。
41. 皮肤瘢痕性类天疱疮的靶抗原检测及与黏膜病变的关联。
42. 皮肤型红斑狼疮与抗磷脂抗体综合征的重叠治疗策略。
43. 皮肤穿通性毛囊炎的病理机制及与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关联。
44. 皮肤淋巴水肿的分期管理及手术干预适应证。
45. 皮肤遗传性血管性水肿(HAE)的C1抑制剂替代治疗机制。
46. 皮肤结节性硬化症的mTOR抑制剂治疗应答评估标准。
47. 皮肤光线性疾病的紫外线防护分级及新型光稳定剂研发进展。
48. 皮肤神经内分泌癌(如Merkel细胞癌)的PD-L1表达检测意义。
49. 皮肤型红斑狼疮的羟氯喹耐药机制及替代药物选择。
50. 皮肤罕见寄生虫感染(如皮肤幼虫移行症)的分子诊断技术。
三、论述题(每题10分,共500分)
1. 论述皮肤T细胞淋巴瘤的肿瘤微环境特征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挑战。
2. 试述皮肤型红斑狼疮与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分子遗传学差异及治疗靶点探索。
3.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坏死性筋膜炎的多学科协作救治流程及抗生素选择策略。
4. 论述皮肤罕见疱病(如副肿瘤性天疱疮)的自身抗体谱检测及肿瘤筛查意义。
5. 试述皮肤微生物组在特应性皮炎发病中的作用及益生菌干预研究进展。
6. 分析皮肤转移性黑色素瘤的免疫治疗耐药机制及联合用药策略。
7. 论述皮肤瘢痕疙瘩的成纤维细胞异质性研究及靶向TGF-β信号通路新药开发。
8. 试述皮肤光老化中端粒缩短机制及端粒酶激活剂的潜在治疗价值。
9. 结合单细胞测序技术,阐述银屑病皮损中免疫细胞亚群的动态变化。
10. 论述皮肤遗传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的基因编辑治疗(如CRISPR-Cas9)研究突破。
11. 试述皮肤型结节病的干扰素-γ释放试验在疾病活动性判断中的价值。
12. 分析皮肤罕见血管肉瘤的分子分型及抗血管生成靶向治疗进展。
13. 论述皮肤黏膜利什曼病的纳米载药系统在提高药物渗透性中的应用前景。
14. 试述皮肤神经纤维瘤病Ⅰ型的MEK抑制剂治疗机制及临床试验结果分析。
15.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坏死性游走性红斑与胰高血糖素瘤的早期诊断线索。
16. 论述皮肤毛囊干细胞在再生医学中的应用潜力及临床转化障碍。
17. 试述皮肤型红斑狼疮患者的免疫耐受诱导治疗(如低剂量IL-2)研究进展。
18. 分析皮肤光线性角化病的表观遗传学改变(如DNA甲基化)在恶变预测中的价值。
19. 论述皮肤罕见代谢病(如Fabry病)的酶替代治疗优化策略及长期随访管理。
20. 试述皮肤型Castleman病的IL-6信号通路调控机制及靶向药物研发方向。
21. 结合肿瘤微环境,阐述皮肤基底细胞癌的Hedgehog通路抑制剂耐药机制。
22. 论述皮肤型IgG4相关疾病的病理诊断标准及与系统性病变的分子关联。
23. 试述皮肤神经病理性疼痛的离子通道调控机制及新型镇痛药物研发。
24. 分析皮肤红斑狼疮患者的B细胞耗竭治疗(如抗CD20单抗)应答预测因素。
25. 论述皮肤转移性腺癌的循环肿瘤DNA(ctDNA)检测在原发灶溯源中的应用。
26. 试述皮肤弹性纤维性假黄瘤(PXE)的基因治疗动物模型成果及临床转化挑战。
27.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血管炎与ANCA相关性血管炎的分子诊断技术进展。
28. 论述皮肤罕见淋巴增殖性疾病(如种痘水疱病样淋巴瘤)的EB病毒关联机制。
29. 试述皮肤衰老相关线粒体功能障碍的靶向修复策略(如NAD+增强剂)研究进展。
30. 分析皮肤型结节性多动脉炎的血管内皮损伤机制及新型抗炎治疗靶点。
31. 论述皮肤毛囊闭锁四联症(ACNE四联症)的炎症信号通路调控及生物制剂应用。
32. 试述皮肤光动力治疗在非黑色素瘤皮肤癌中的光敏剂选择及优化方案。
33.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型红斑狼疮与抗Ro/SSA抗体阳性新生儿的围产期管理。
34. 论述皮肤神经内分泌癌(如Merkel细胞癌)的免疫治疗联合放疗协同机制。
35. 试述皮肤淀粉样变的质谱蛋白分型技术在个体化治疗中的应用前景。
36. 分析皮肤黏膜型副银屑病的分子病理演变及与早期MF的基因组学差异。
37. 论述皮肤型红斑狼疮患者的干扰素基因特征(Interferon signature)检测意义。
38. 试述皮肤罕见寄生虫感染(如皮肤利什曼病)的快速分子诊断流程优化。
39.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恶性黑色素瘤的液态活检(如ctDNA)在疗效监测中的应用。
40. 论述皮肤瘢痕形成中机械应力信号通路(如YAP/TAZ)的调控机制及干预策略。
41. 试述皮肤型红斑狼疮的JAK-STAT通路异常及新型抑制剂治疗探索。
42. 分析皮肤遗传性血管性水肿(HAE)的缓激肽通路调控及靶向药物研发。
43. 论述皮肤光线性疾病的紫外线诱导DNA损伤修复机制及增强策略。
44. 试述皮肤神经纤维瘤病Ⅱ型的肿瘤抑制基因(NF2)突变检测及遗传咨询要点。
45.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型结节病的多器官受累评估及免疫抑制剂选择原则。
46. 论述皮肤毛囊干细胞在慢性创面愈合中的再生潜能及临床转化研究设计。
47. 试述皮肤罕见肉芽肿性疾病(如环状肉芽肿)的免疫细胞亚群动态研究进展。
48. 分析皮肤黏膜念珠菌病的宿主免疫缺陷分型及个体化预防策略。
49. 论述皮肤转移性黑色素瘤的肿瘤抗原异质性及个性化疫苗研发挑战。
50. 试述皮肤衰老相关成纤维细胞功能退化的表观遗传调控及逆转策略。
一、名词解释(每题3分,共30分)
1. 皮肤假性卟啉病(Pseudoporphyria)
2. 皮肤淋巴增生性疾病(Cutaneous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
3. 皮肤栅栏状中性粒细胞性肉芽肿(Palisaded neutrophilic granulomatous dermatitis)
4. 皮肤Rosai-Dorfman病
5. 皮肤血管周细胞瘤(Hemangiopericytoma)
6. 皮肤局灶性黏蛋白病(Focal cutaneous mucinosis)
7. 皮肤虫蚀状萎缩(Atrophoderma vermiculatum)
8. 皮肤黏液性脱发(Alopecia mucinosa)
9. 皮肤假性水疱(Pseudovesicles)
10. 皮肤神经内分泌小细胞癌(Merkel cell carcinoma)
二、简答题(每题5分,共250分)
1. 皮肤型淀粉样变的刚果红染色特征及假阴性原因。
2. 遗传性血管性水肿(HAE)的急性发作期治疗药物选择及机制。
3. 皮肤神经内分泌肿瘤(如Merkel细胞癌)的免疫组化标志物组合。
4. 皮肤环状肉芽肿的局部注射治疗药物选择及注意事项。
5. 皮肤假性淋巴瘤与真性淋巴瘤的分子检测(如TCR重排)判读标准。
6. 皮肤型红斑狼疮的皮肤外系统表现及筛查项目。
7. 皮肤毛发上皮瘤(Trichoepithelioma)与基底细胞癌的病理鉴别要点。
8. 皮肤转移性乳腺癌的免疫组化标志物组合及原发灶确认策略。
9. 皮肤光线性角化病的癌变风险评估及临床随访方案。
10. 皮肤浆细胞增多症的骨髓穿刺检查指征及诊断流程。
11. 皮肤型结节性多动脉炎的皮肤病理特征与系统性类型的差异。
12. 皮肤淋巴管畸形的硬化治疗并发症及影像学监测方法。
13. 皮肤假性毛囊炎的易感人群及激光治疗原理。
14. 皮肤先天性鱼鳞病的产前基因诊断技术及伦理问题。
15. 皮肤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CH)的BRAF抑制剂治疗机制。
16. 皮肤红斑性肢痛症的钠离子通道基因突变检测意义。
17. 皮肤型Castleman病的病理亚型及IL-6检测临床价值。
18. 皮肤黏膜念珠菌病的宿主免疫功能评估项目。
19. 皮肤毛母质瘤(Pilomatricoma)的CT影像特征与手术指征。
20. 皮肤转移性黑色素瘤的PD-1抑制剂耐药机制及应对策略。
21. 皮肤弹性纤维性假黄瘤(PXE)的眼科并发症管理要点。
22. 皮肤型红斑狼疮的羟氯喹治疗剂量调整原则及视网膜毒性监测。
23. 皮肤瘢痕疙瘩的冷冻治疗联合糖皮质激素注射方案。
24. 皮肤神经纤维瘤病Ⅰ型的咖啡斑与CALM基因突变关联。
25. 皮肤卟啉病的尿液荧光检测方法及结果判读。
26. 皮肤光动力治疗中光敏剂渗透增强技术进展。
27. 皮肤型IgG4相关疾病的血清IgG4水平诊断阈值争议。
28. 皮肤红斑狼疮患者的抗SSA/Ro抗体与新生儿狼疮关联。
29. 皮肤假性上皮瘤样增生的HPV感染相关性分析。
30. 皮肤血管角皮瘤(Angiokeratoma)的激光治疗选择及预后。
31. 皮肤淀粉样变的质谱分型技术及治疗指导意义。
32. 皮肤毛囊闭锁四联症(ACNE四联症)的生物制剂治疗进展。
33. 皮肤型结节性硬化症的癫痫与mTOR通路抑制治疗关联。
34. 皮肤转移性肺癌的皮肤病理特征与原发灶鉴别。
35. 皮肤光线性唇炎与日光性角化病的病理演变差异。
36. 皮肤肥大细胞增生症的KIT基因突变检测技术选择。
37. 皮肤型红斑狼疮的干扰素基因特征(Interferon signature)检测意义。
38. 皮肤假性淋巴瘤的免疫组化标志物组合(如CD20/CD3/CD5)。
39. 皮肤神经病理性溃疡的神经营养因子局部应用方案。
40. 皮肤黏膜利什曼病的分子快速诊断技术(如PCR)敏感性分析。
41. 皮肤毛发扁平苔藓的瘢痕性脱发预防性治疗策略。
42. 皮肤型红斑狼疮的B细胞靶向治疗(如利妥昔单抗)适应症。
43. 皮肤恶性黑色素瘤的哨兵淋巴结活检临床争议。
44. 皮肤光老化中胶原蛋白降解酶(如MMP-1)抑制策略。
45. 皮肤型血管炎的ANCA检测亚型及临床关联性。
46. 皮肤假性水疱的鉴别诊断流程(如类天疱疮与湿疹)。
47. 皮肤转移性胃肠道腺癌的免疫组化标志物(如CK20/CDX2)选择。
48. 皮肤型结节病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细胞分类诊断价值。
49. 皮肤红斑狼疮患者的妊娠期抗SSA/Ro抗体管理方案。
50. 皮肤AI辅助诊断系统(如皮肤镜图像分析)的临床应用局限性。
三、论述题(每题10分,共500分)
1. 论述皮肤T细胞淋巴瘤的肿瘤异质性及单细胞测序技术研究进展。
2. 试述JAK抑制剂在皮肤免疫疾病(如斑秃、特应性皮炎)中的机制及长期安全性管理。
3.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转移性癌的未知原发灶溯源策略及多学科协作流程。
4. 论述皮肤型红斑狼疮的干扰素通路靶向治疗(如抗IFN-α单抗)研究进展。
5. 试述皮肤光动力治疗在耐药性光线性角化病中的增效方案设计。
6. 分析皮肤罕见遗传病(如先天性鱼鳞病)的基因治疗载体选择(如AAV vs CRISPR)。
7. 论述皮肤瘢痕疙瘩的机械应力调控机制(如YAP/TAZ通路)及新型压力治疗装置研发。
8. 试述皮肤微生物组在慢性创面愈合中的作用及益生菌局部应用前景。
9.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型血管炎与系统性血管炎的鉴别诊断及治疗差异。
10. 论述皮肤神经内分泌肿瘤(如Merkel细胞癌)的免疫治疗联合放疗协同效应。
11. 试述皮肤衰老相关成纤维细胞代谢重编程机制及NAD+增强剂干预策略。
12. 分析皮肤型结节性多动脉炎的血管内皮损伤生物标志物(如VCAM-1)检测价值。
13. 论述皮肤毛囊干细胞在再生医学中的定向分化调控技术难点。
14. 试述皮肤光线性疾病的表观遗传学调控(如DNA甲基化)及防护策略优化。
15.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型红斑狼疮合并抗磷脂抗体综合征的抗凝治疗矛盾与平衡。
16. 论述皮肤转移性黑色素瘤的肿瘤微环境免疫抑制机制及联合治疗突破点。
17. 试述皮肤型Castleman病的IL-6信号通路调控网络及新型生物制剂研发方向。
18. 分析皮肤AI辅助诊断系统在皮肤镜图像判读中的误诊原因及改进策略。
19. 论述皮肤弹性纤维性假黄瘤(PXE)的基因编辑治疗(如碱基编辑技术)挑战。
20. 试述皮肤黏膜念珠菌病的唑类药物耐药机制及新型棘白菌素类药物应用前景。
21.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坏死性筋膜炎的快速分子诊断(如16S rRNA测序)临床价值。
22. 论述皮肤型红斑狼疮患者的B细胞耗竭治疗(如CD19-CAR-T)潜在风险与收益。
23. 试述皮肤罕见肉芽肿性疾病(如环状肉芽肿)的Th1/Th17免疫失衡调控机制。
24. 分析皮肤毛母质癌的Wnt/β-catenin信号通路异常及靶向治疗可行性。
25. 论述皮肤光老化中活性氧(ROS)清除策略(如纳米抗氧化剂)研究进展。
26. 试述皮肤神经纤维瘤病Ⅱ型的Merlin蛋白功能丧失机制及MEK抑制剂治疗探索。
27.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型结节病的全身系统评估及免疫抑制剂阶梯治疗原则。
28. 论述皮肤假性淋巴瘤的克隆演化机制及与真性淋巴瘤的分子边界界定。
29. 试述皮肤遗传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的蛋白质替代治疗(如Ⅶ型胶原蛋白)挑战。
30. 分析皮肤红斑狼疮患者的干扰素基因特征(ISG)检测在个体化治疗中的意义。
31. 论述皮肤黏膜利什曼病的纳米载药系统(如脂质体)在提高药物生物利用度中的优势。
32. 试述皮肤型IgG4相关疾病的纤维化机制及靶向TGF-β通路治疗前景。
33.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转移性腺癌的循环肿瘤细胞(CTC)检测在疗效评估中的应用。
34. 论述皮肤瘢痕形成中机械应力感应通路(如整合素-FAK)的调控机制及药物干预靶点。
35. 试述皮肤光线性唇炎的癌变表观遗传学标志物(如miRNA)筛查及临床转化难点。
36. 分析皮肤神经病理性疼痛的TRPV1通道调控机制及新型局部镇痛贴剂研发。
37. 论述皮肤型红斑狼疮的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pDC)活化机制及靶向治疗策略。
38. 试述皮肤罕见寄生虫感染(如皮肤利什曼病)的宿主免疫逃逸机制及疫苗设计难点。
39.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恶性黑色素瘤的液态活检(ctDNA)在术后监测中的敏感性分析。
40. 论述皮肤毛囊闭锁四联症(ACNE四联症)的IL-1β通路异常及生物制剂治疗潜力。
41. 试述皮肤假性卟啉病的药物相关性分析及与真性卟啉病的代谢差异。
42. 分析皮肤型结节性硬化症的癫痫发生与mTOR通路过度激活的分子关联。
43. 论述皮肤转移性乳腺癌的激素受体状态对皮肤病灶治疗的指导意义。
44. 试述皮肤光动力治疗中新型光敏剂(如ALA-纳米金复合物)的增效机制。
45.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型血管炎的补体激活途径检测(如C3a/C5a)在分型中的价值。
46. 论述皮肤衰老相关线粒体自噬(Mitophagy)障碍及 Urolithin A 的干预研究。
47. 试述皮肤AI辅助病理诊断系统在罕见肿瘤鉴别中的局限性及改进方向。
48. 分析皮肤红斑狼疮患者的肠道菌群失调与干扰素通路激活的关联机制。
49. 论述皮肤神经鞘瘤的NF2基因突变检测及与神经纤维瘤病Ⅱ型的遗传咨询要点。
50. 试述皮肤型红斑狼疮的胎盘屏障穿透药物风险评估及妊娠期治疗方案优化。
一、名词解释(每题3分,共30分)
1. 皮肤黏蛋白沉积症(Cutaneous mucinosis)
2. 皮肤假性肉瘤(Pseudosarcoma)
3. 皮肤毛囊角化不良症(Follicular dyskeratosis)
4. 皮肤淋巴细胞浸润综合征(Jessner-Kanof综合征)
5. 皮肤网状红斑黏蛋白病(Reticular erythematous mucinosis)
6. 皮肤穿通性毛囊炎(Perforating folliculitis)
7. 皮肤血管内皮瘤(Cutaneous angioendothelioma)
8. 皮肤假性软骨瘤(Pseudochondroma)
9. 皮肤透明细胞肉瘤(Clear cell sarcoma)
10. 皮肤神经鞘黏液瘤(Nerve sheath myxoma)
二、简答题(每题5分,共250分)
1. 皮肤型淀粉样变的免疫荧光表现及诊断价值。
2. 皮肤淋巴瘤样丘疹病(LyP)的临床分型及与蕈样肉芽肿的病理鉴别。
3. 皮肤假性毛囊炎的易感人群及预防措施。
4. 皮肤转移性甲状腺癌的免疫组化标志物组合及诊断流程。
5. 皮肤型红斑狼疮的羟氯喹耐药机制及替代治疗方案。
6. 皮肤神经纤维瘤病Ⅰ型的皮肤外系统表现及基因突变检测意义。
7. 皮肤环状肉芽肿的局部糖皮质激素注射剂量及并发症管理。
8. 皮肤毛发上皮瘤(Trichoepithelioma)的遗传学机制及与基底细胞癌的鉴别。
9. 皮肤光线性角化病的液氮冷冻治疗适应证及操作要点。
10. 皮肤假性淋巴瘤的克隆性检测(如IGH基因重排)结果判读标准。
11. 皮肤型结节性多动脉炎的皮肤病理特征与系统性类型的异同。
12. 皮肤黏膜利什曼病的分子诊断技术(如PCR)敏感性分析及临床意义。
13. 皮肤肥大细胞增生症的皮肤外系统评估(如骨髓穿刺)适应证。
14. 皮肤转移性肾细胞癌的病理特征及免疫组化标志物选择。
15. 皮肤型红斑狼疮患者的抗Ro/SSA抗体与新生儿狼疮的关联性。
16. 皮肤毛母质瘤(Pilomatricoma)的影像学特征与手术切除范围设计。
17. 皮肤弹性纤维性假黄瘤(PXE)的ABCC6基因突变检测技术选择。
18. 皮肤瘢痕性类天疱疮的靶抗原检测及与黏膜病变的关联性分析。
19. 皮肤型Castleman病的IL-6检测方法及治疗应答评估标准。
20. 皮肤假性水疱的鉴别诊断(如类天疱疮与接触性皮炎)要点。
21. 皮肤卟啉病的尿液荧光检测操作步骤及结果判读注意事项。
22. 皮肤型IgG4相关疾病的病理特征及与系统性病变的分子关联。
23. 皮肤神经病理性溃疡的疼痛管理策略及局部药物选择。
24. 皮肤转移性前列腺癌的免疫组化标志物(如PSA/P504S)组合。
25. 皮肤光动力治疗中光敏剂(如ALA)的渗透增强技术进展。
26. 皮肤型红斑狼疮患者的妊娠期药物调整原则及胎儿监测方案。
27. 皮肤假性软骨瘤的影像学特征与骨软骨瘤的鉴别诊断。
28. 皮肤毛囊闭锁四联症(ACNE四联症)的外科干预时机及术式选择。
29. 皮肤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CH)的BRAF V600E突变检测意义。
30. 皮肤型结节病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细胞分类诊断标准。
31. 皮肤恶性血管内皮瘤的靶向治疗(如抗VEGF药物)机制及疗效。
32. 皮肤假性肉瘤的病理特征与真性肉瘤的免疫组化鉴别要点。
33. 皮肤红斑性肢痛症的钠离子通道阻滞剂(如卡马西平)应用原则。
34. 皮肤型红斑狼疮的干扰素基因特征(ISG)检测方法及临床意义。
35. 皮肤黏膜念珠菌病的唑类药物耐药性监测及替代药物选择。
36. 皮肤毛囊角化不良症的遗传模式及基因突变位点分析。
37. 皮肤转移性黑色素瘤的液态活检(ctDNA)在疗效监测中的应用。
38. 皮肤假性卟啉病的药物相关性分析及与真性卟啉病的代谢差异。
39. 皮肤型红斑狼疮患者的B细胞耗竭治疗(如利妥昔单抗)适应证。
40. 皮肤神经鞘黏液瘤的分子遗传学特征及与Carney复合征的关联。
41. 皮肤浆细胞增多症的骨髓病理检查指征及诊断流程。
42. 皮肤光老化中胶原蛋白合成促进策略(如维生素A酸)应用要点。
43. 皮肤型血管炎的ANCA亚型(如PR3-ANCA)检测临床意义。
44. 皮肤假性上皮瘤样增生的HPV分型检测及与鳞癌的关联性。
45. 皮肤毛发扁平苔藓的瘢痕性脱发预防性治疗(如局部免疫调节剂)。
46. 皮肤转移性胃肠道腺癌的免疫组化标志物(如CK7/CK20)选择。
47. 皮肤型结节性硬化症的癫痫治疗药物(如mTOR抑制剂)机制。
48. 皮肤红斑狼疮患者的抗磷脂抗体检测与血栓风险评估。
49. 皮肤假性软骨瘤的影像学随访方案及恶变监测指标。
50. 皮肤AI辅助诊断系统在色素性皮损中的误诊原因及改进策略。
三、论述题(每题10分,共500分)
1. 论述皮肤T细胞淋巴瘤的肿瘤异质性及单细胞测序技术研究进展。
2. 试述皮肤型红斑狼疮的JAK-STAT信号通路异常及靶向治疗探索。
3.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转移性癌的未知原发灶溯源策略及多学科协作流程。
4. 论述皮肤光动力治疗在耐药性基底细胞癌中的增效机制及方案优化。
5. 分析皮肤罕见遗传病(如遗传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的基因治疗载体选择(如腺病毒vs脂质体)。
6. 论述皮肤瘢痕疙瘩的机械应力调控机制(如Hippo-YAP通路)及新型干预策略。
7. 试述皮肤微生物组在慢性创面愈合中的作用及粪菌移植治疗潜力。
8.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型血管炎与ANCA相关性血管炎的分子诊断技术进展。
9. 论述皮肤神经内分泌肿瘤(如Merkel细胞癌)的免疫治疗耐药机制及联合放疗策略。
10. 试述皮肤衰老相关成纤维细胞代谢重编程机制及NAD+前体干预研究。
11. 分析皮肤型结节性多动脉炎的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如VCAM-1)检测价值。
12. 论述皮肤毛囊干细胞在再生医学中的定向分化调控技术难点及解决方案。
13. 试述皮肤光线性疾病的表观遗传学调控(如非编码RNA)及防护策略优化。
14.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型红斑狼疮合并抗磷脂抗体综合征的抗凝治疗矛盾与平衡。
15. 论述皮肤转移性黑色素瘤的肿瘤微环境免疫抑制机制及联合治疗突破点。
16. 试述皮肤型Castleman病的IL-6信号通路调控网络及靶向药物研发方向。
17. 分析皮肤AI辅助诊断系统在皮肤镜图像判读中的误诊原因及深度学习优化策略。
18. 论述皮肤弹性纤维性假黄瘤(PXE)的基因编辑治疗(如碱基编辑技术)挑战。
19. 试述皮肤黏膜念珠菌病的唑类药物耐药机制及新型棘白菌素类药物应用前景。
20.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坏死性筋膜炎的快速分子诊断(如宏基因组测序)临床价值。
21. 论述皮肤型红斑狼疮患者的B细胞靶向治疗(如CD19-CAR-T)潜在风险与收益。
22. 试述皮肤罕见肉芽肿性疾病(如环状肉芽肿)的Th1/Th17免疫失衡调控机制。
23. 分析皮肤毛母质癌的Wnt/β-catenin信号通路异常及靶向治疗可行性。
24. 论述皮肤光老化中活性氧(ROS)清除策略(如纳米抗氧化剂)研究进展。
25. 试述皮肤神经纤维瘤病Ⅱ型的Merlin蛋白功能丧失机制及MEK抑制剂治疗探索。
26.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型结节病的全身系统评估及免疫抑制剂阶梯治疗原则。
27. 论述皮肤假性淋巴瘤的克隆演化机制及与真性淋巴瘤的分子边界界定。
28. 试述皮肤遗传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的蛋白质替代治疗(如Ⅶ型胶原蛋白)挑战。
29. 分析皮肤红斑狼疮患者的干扰素基因特征(ISG)检测在个体化治疗中的意义。
30. 论述皮肤黏膜利什曼病的纳米载药系统(如脂质体)在提高药物生物利用度中的优势。
31. 试述皮肤型IgG4相关疾病的纤维化机制及靶向TGF-β通路治疗前景。
32.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转移性腺癌的循环肿瘤细胞(CTC)检测在疗效评估中的应用。
33. 论述皮肤瘢痕形成中机械应力感应通路(如整合素-FAK)的调控机制及药物干预靶点。
34. 试述皮肤光线性唇炎的癌变表观遗传学标志物(如miRNA)筛查及临床转化难点。
35. 分析皮肤神经病理性疼痛的TRPV1通道调控机制及新型局部镇痛贴剂研发。
36. 论述皮肤型红斑狼疮的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pDC)活化机制及靶向治疗策略。
37. 试述皮肤罕见寄生虫感染(如皮肤利什曼病)的宿主免疫逃逸机制及疫苗设计难点。
38.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恶性黑色素瘤的液态活检(ctDNA)在术后监测中的敏感性分析。
39. 论述皮肤毛囊闭锁四联症(ACNE四联症)的IL-1β通路异常及生物制剂治疗潜力。
40. 试述皮肤假性卟啉病的药物相关性分析及与真性卟啉病的代谢差异。
41. 分析皮肤型结节性硬化症的癫痫发生与mTOR通路过度激活的分子关联。
42. 论述皮肤转移性乳腺癌的激素受体状态对皮肤病灶治疗的指导意义。
43. 试述皮肤光动力治疗中新型光敏剂(如ALA-纳米金复合物)的增效机制。
44.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型血管炎的补体激活途径检测(如C3a/C5a)在分型中的价值。
45. 论述皮肤衰老相关线粒体自噬(Mitophagy)障碍及Urolithin A的干预研究。
46. 试述皮肤AI辅助病理诊断系统在罕见肿瘤鉴别中的局限性及改进方向。
47. 分析皮肤红斑狼疮患者的肠道菌群失调与干扰素通路激活的关联机制。
48. 论述皮肤神经鞘瘤的NF2基因突变检测及与神经纤维瘤病Ⅱ型的遗传咨询要点。
49. 试述皮肤型红斑狼疮的胎盘屏障穿透药物风险评估及妊娠期治疗方案优化。
50.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恶性黑色素瘤的肿瘤抗原异质性及个性化疫苗研发挑战。
一、名词解释(每题3分,共30分)
1. 皮肤淋巴细胞增生性疾病
2. 皮肤假性肉瘤
3. 皮肤毛囊角化不良症
4. Jessner-Kanof综合征
5. 皮肤穿通性毛囊炎
6. 皮肤网状红斑黏蛋白病
7. 皮肤透明细胞肉瘤
8. 皮肤神经鞘黏液瘤
9. 皮肤假性软骨瘤
10. 皮肤血管内皮瘤
二、简答题(每题5分,共250分)
1. 简述皮肤黏蛋白沉积症的病理特征及鉴别诊断要点。
2. 皮肤假性肉瘤与真性肉瘤的免疫组化标志物组合及判读标准。
3. 皮肤毛囊角化不良症的遗传模式及临床管理策略。
4. Jessner-Kanof综合征的典型皮损表现及与红斑狼疮的鉴别要点。
5. 皮肤穿通性毛囊炎的易感因素及局部治疗药物选择。
6. 皮肤网状红斑黏蛋白病的实验室检查异常及诊断标准。
7. 皮肤透明细胞肉瘤的分子遗传学特征及预后因素。
8. 皮肤神经鞘黏液瘤的病理演变与恶性转化的相关性。
9. 皮肤假性软骨瘤的影像学特征及与骨肿瘤的鉴别诊断。
10. 皮肤血管内皮瘤的靶向治疗(如抗VEGF药物)机制及疗效评价。
11. 皮肤淋巴细胞增生性疾病的克隆性检测方法(如TCR重排)及临床意义。
12. 皮肤假性肉瘤的局部复发风险及手术切除范围设计。
13. 皮肤毛囊角化不良症与Darier病的病理鉴别要点。
14. Jessner-Kanof综合征的免疫调节治疗(如沙利度胺)应用原则。
15. 皮肤穿通性毛囊炎与糖尿病皮肤并发症的关联性分析。
16. 皮肤网状红斑黏蛋白病的紫外线防护策略及光敏感机制。
17. 皮肤透明细胞肉瘤的分子靶向治疗(如MET抑制剂)研究进展。
18. 皮肤神经鞘黏液瘤与神经纤维瘤病的基因突变差异。
19. 皮肤假性软骨瘤的恶变监测指标及影像学随访方案。
20. 皮肤血管内皮瘤的血管生成信号通路异常及干预策略。
21. 皮肤淋巴细胞增生性疾病的WHO最新分类更新要点。
22. 皮肤假性肉瘤的放疗适应证及剂量优化原则。
23. 皮肤毛囊角化不良症的产前基因诊断技术及伦理争议。
24. Jessner-Kanof综合征的皮肤外系统表现及筛查项目。
25. 皮肤穿通性毛囊炎的细菌培养与抗生素选择依据。
26. 皮肤网状红斑黏蛋白病的抗疟药(如羟氯喹)治疗机制。
27. 皮肤透明细胞肉瘤的免疫治疗(如PD-1抑制剂)应答预测因素。
28. 皮肤神经鞘黏液瘤的手术并发症管理及复发预防措施。
29. 皮肤假性软骨瘤的病理分级与临床预后的相关性。
30. 皮肤血管内皮瘤的循环肿瘤细胞(CTC)检测在疗效评估中的应用。
31. 皮肤淋巴细胞增生性疾病转化为淋巴瘤的危险因素分析。
32. 皮肤假性肉瘤的冷冻切片诊断准确性及局限性。
33. 皮肤毛囊角化不良症的表观遗传学调控机制研究进展。
34. Jessner-Kanof综合征的干扰素基因特征(ISG)检测意义。
35. 皮肤穿通性毛囊炎与HIV感染的免疫相关性分析。
36. 皮肤网状红斑黏蛋白病的病理亚型及治疗反应差异。
37. 皮肤透明细胞肉瘤的化疗耐药机制及联合用药策略。
38. 皮肤神经鞘黏液瘤的分子分型对预后的影响。
39. 皮肤假性软骨瘤的基因突变谱(如IDH1/2)检测意义。
40. 皮肤血管内皮瘤的血管栓塞治疗适应证及操作要点。
41. 皮肤淋巴细胞增生性疾病的皮肤镜特征及诊断价值。
42. 皮肤假性肉瘤的病理误诊原因分析及避免策略。
43. 皮肤毛囊角化不良症的角质形成细胞分化异常机制。
44. Jessner-Kanof综合征的B细胞靶向治疗(如利妥昔单抗)探索。
45. 皮肤穿通性毛囊炎的激光治疗原理及术后护理要点。
46. 皮肤网状红斑黏蛋白病的抗纤维化治疗(如吡非尼酮)应用前景。
47. 皮肤透明细胞肉瘤的液态活检(ctDNA)在复发监测中的价值。
48. 皮肤神经鞘黏液瘤的神经生长因子受体表达及治疗意义。
49. 皮肤假性软骨瘤的代谢组学特征及潜在生物标志物。
50. 皮肤血管内皮瘤的肿瘤微环境特征及免疫治疗潜力。
三、论述题(每题10分,共500分)
1. 论述皮肤淋巴细胞增生性疾病的分子分型进展及其对个体化治疗的指导意义。
2. 试述皮肤假性肉瘤的病理诊断陷阱及多学科协作在鉴别诊断中的重要性。
3.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毛囊角化不良症的多基因遗传模式及精准医学策略。
4. 分析Jessner-Kanof综合征的免疫发病机制与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异同点。
5. 论述皮肤穿通性毛囊炎的慢性炎症信号通路(如NF-κB)调控及靶向治疗前景。
6. 试述皮肤网状红斑黏蛋白病的纤维化机制及抗TGF-β治疗研究进展。
7. 结合单细胞测序技术,阐述皮肤透明细胞肉瘤的肿瘤异质性及治疗抵抗机制。
8. 论述皮肤神经鞘黏液瘤的神经嵴起源学说及与周围神经肿瘤的分子关联。
9. 试述皮肤假性软骨瘤的代谢重编程特征及潜在治疗靶点。
10. 分析皮肤血管内皮瘤的血管拟态(Vasculogenic mimicry)现象及临床意义。
11. 论述皮肤淋巴细胞增生性疾病向淋巴瘤转化的分子预警标志物研究。
12. 试述皮肤假性肉瘤的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协同增效机制及临床试验设计。
13. 结合基因编辑技术(如CRISPR),探讨皮肤毛囊角化不良症的基因修复策略。
14. 分析Jessner-Kanof综合征的皮肤微生物组特征与免疫调节治疗的关联。
15. 论述皮肤穿通性毛囊炎的合并症(如糖尿病肾病)管理及多学科协作流程。
16. 试述皮肤网状红斑黏蛋白病的表观遗传学调控(如DNA甲基化)及药物开发。
17. 结合肿瘤类器官模型,阐述皮肤透明细胞肉瘤的个体化药物筛选策略。
18. 论述皮肤神经鞘黏液瘤的神经生长因子(NGF)信号通路异常及靶向干预。
19. 试述皮肤假性软骨瘤的肿瘤干细胞理论在复发机制中的研究进展。
20. 分析皮肤血管内皮瘤的缺氧诱导因子(HIF-1α)通路激活及治疗意义。
21. 论述皮肤淋巴细胞增生性疾病的免疫微环境特征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应用前景。
22. 试述皮肤假性肉瘤的病理人工智能(AI)辅助诊断系统开发难点及优化方向。
23.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毛囊角化不良症的跨学科管理(皮肤科、遗传科、心理科)模式。
24. 分析Jessner-Kanof综合征的干扰素通路靶向治疗(如JAK抑制剂)潜在风险与收益。
25. 论述皮肤穿通性毛囊炎的炎症小体(如NLRP3)激活机制及药物抑制策略。
26. 试述皮肤网状红斑黏蛋白病的抗CD20单抗治疗机制及长期疗效评估。
27. 结合液体活检技术,探讨皮肤透明细胞肉瘤的早期复发监测及干预时机。
28. 论述皮肤神经鞘黏液瘤的神经鞘瘤蛋白(Merlin)功能缺失机制及基因治疗潜力。
29. 试述皮肤假性软骨瘤的肿瘤代谢成像(如PET-CT)在分期中的应用价值。
30. 分析皮肤血管内皮瘤的血管正常化策略对化疗药物递送的增效作用。
31. 论述皮肤淋巴细胞增生性疾病的循环肿瘤DNA(ctDNA)动态监测及临床决策优化。
32. 试述皮肤假性肉瘤的免疫组化标志物组合优化及病理报告标准化建议。
33. 结合类器官培养技术,探讨皮肤毛囊角化不良症的药物毒性测试模型构建。
34. 分析Jessner-Kanof综合征的肠道菌群-免疫轴调控机制及益生菌干预研究。
35. 论述皮肤穿通性毛囊炎的微生物组失调与抗生素耐药性关联机制。
36. 试述皮肤网状红斑黏蛋白病的抗纤维化联合治疗(如尼达尼布+吡非尼酮)潜力。
37. 结合空间转录组学,阐述皮肤透明细胞肉瘤的肿瘤-间质相互作用研究进展。
38. 论述皮肤神经鞘黏液瘤的神经递质异常(如5-HT)与疼痛管理关联性。
39. 试述皮肤假性软骨瘤的分子影像学(如MRI弥散加权成像)在诊断中的价值。
40. 分析皮肤血管内皮瘤的抗血管生成治疗耐药机制及逆转策略。
41. 论述皮肤淋巴细胞增生性疾病的CAR-T细胞治疗潜力及安全性挑战。
42. 试述皮肤假性肉瘤的肿瘤疫苗(如新抗原疫苗)研发难点及临床转化前景。
43. 结合患者源性异种移植(PDX)模型,探讨皮肤毛囊角化不良症的精准治疗。
44. 分析Jessner-Kanof综合征的代谢组学生物标志物筛选及诊断意义。
45. 论述皮肤穿通性毛囊炎的局部免疫调节(如IL-17抑制剂)治疗机制。
46. 试述皮肤网状红斑黏蛋白病的皮肤屏障修复策略及新型敷料应用。
47. 结合人工智能病理分析,阐述皮肤透明细胞肉瘤的自动化分级系统开发。
48. 论述皮肤神经鞘黏液瘤的神经鞘靶向纳米药物递送系统研究进展。
49. 试述皮肤假性软骨瘤的肿瘤微环境代谢特征及营养干预策略。
50. 分析皮肤血管内皮瘤的免疫治疗(如双特异性抗体)联合放疗协同机制。
一、名词解释(每题3分,共30分)
1. 皮肤异色性皮肌炎
2. 皮肤假性淋巴瘤
3. 皮肤肥大细胞增生症
4. 皮肤黏膜念珠菌病
5. 皮肤结节性硬化症
6. 皮肤弹性纤维假黄瘤
7. 皮肤浆细胞增多症
8. 皮肤移植物抗宿主病
9. 皮肤毛囊黏蛋白病
10. 皮肤慢性光化性皮炎
二、简答题(每题5分,共250分)
1. 简述皮肤异色性皮肌炎的典型皮肤表现及实验室检查异常。
2. 皮肤假性淋巴瘤的病理特征及与真性淋巴瘤的鉴别要点。
3. 肥大细胞增生症的皮肤外系统评估指标及治疗方法。
4. 皮肤黏膜念珠菌病的免疫抑制宿主管理策略。
5. 结节性硬化症的皮肤表现及基因突变检测意义。
6. 弹性纤维假黄瘤的眼部并发症及遗传咨询要点。
7. 浆细胞增多症的骨髓检查指征及诊断流程。
8. 移植物抗宿主病的急性和慢性期皮肤表现差异。
9. 毛囊黏蛋白病的病理特征及与蕈样肉芽肿的关联。
10. 慢性光化性皮炎的光防护策略及治疗药物选择。
11. 皮肤淋巴管畸形的硬化治疗并发症及影像学随访方案。
12. 皮肤假性水疱病的鉴别诊断(如类天疱疮与接触性皮炎)。
13. 皮肤红斑狼疮患者的妊娠期羟氯喹应用安全性及剂量调整。
14. 皮肤神经纤维瘤病Ⅱ型的听力损失评估及多学科管理。
15. 皮肤型IgG4相关疾病的病理特征与系统性病变的关联。
16. 皮肤转移性肝癌的免疫组化标志物组合及原发灶溯源。
17. 皮肤光线性唇炎的癌变风险及甲基化标志物筛查意义。
18. 皮肤假性软骨瘤的代谢组学特征及潜在生物标志物。
19. 皮肤血管炎的冷球蛋白检测方法及临床分型意义。
20. 皮肤毛发扁平苔藓的瘢痕性脱发预防性治疗策略。
21. 皮肤型结节病的肺功能评估及影像学特征。
22. 皮肤卟啉病的血液学异常及光敏感机制。
23. 皮肤假性卟啉病的药物相关性分析及代谢差异。
24. 皮肤红斑狼疮患者的抗磷脂抗体检测与血栓管理。
25. 皮肤毛母质瘤的影像学特征与手术切除范围设计。
26. 皮肤型红斑狼疮的干扰素基因特征检测技术进展。
27. 皮肤黏膜利什曼病的分子快速诊断技术优化方案。
28. 皮肤神经病理性溃疡的局部神经营养因子应用策略。
29. 皮肤光动力治疗中新型光敏剂(如纳米金复合物)增效机制。
30. 皮肤AI辅助诊断系统在色素性皮损中的误诊原因分析。
31. 皮肤转移性肾细胞癌的靶向治疗(如VEGF抑制剂)选择依据。
32. 皮肤假性上皮瘤样增生的HPV分型检测及癌变风险。
33. 皮肤毛囊闭锁四联症的外科干预时机及术式优化。
34. 皮肤型结节性多动脉炎的血管造影特征与病理关联。
35. 皮肤红斑狼疮患者的肠道菌群失调与免疫调节治疗关联。
36. 皮肤弹性纤维假黄瘤的基因编辑治疗动物模型成果。
37. 皮肤罕见寄生虫感染(如皮肤幼虫移行症)的分子诊断流程。
38. 皮肤瘢痕疙瘩的放射治疗剂量优化及远期副作用管理。
39. 皮肤型红斑狼疮的胎盘穿透药物风险评估及胎儿监测。
40. 皮肤神经鞘瘤的NF2基因突变检测及遗传咨询要点。
41. 皮肤浆细胞增多症的克隆性检测(如血清游离轻链)意义。
42. 皮肤光线性角化病的表观遗传学标志物筛查及临床转化。
43. 皮肤黏膜念珠菌病的唑类药物耐药机制及替代方案。
44. 皮肤恶性黑色素瘤的液态活检(ctDNA)在术后监测中的应用。
45. 皮肤假性肉瘤的病理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开发难点。
46. 皮肤型红斑狼疮的JAK抑制剂治疗机制及长期安全性评估。
47. 皮肤毛囊黏蛋白病的免疫组化标志物组合及诊断价值。
48. 皮肤慢性光化性皮炎的光脱敏治疗原理及操作要点。
49. 皮肤转移性前列腺癌的激素治疗反应预测因素。
50. 皮肤型血管炎的补体激活途径检测及分型意义。
三、论述题(每题10分,共500分)
1. 论述皮肤异色性皮肌炎的免疫发病机制及靶向治疗进展。
2. 试述皮肤假性淋巴瘤的克隆演化机制及分子边界界定策略。
3. 分析肥大细胞增生症的KIT基因突变检测技术及耐药机制。
4.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黏膜念珠菌病的宿主免疫缺陷分型及个体化治疗。
5. 论述结节性硬化症的mTOR通路异常及抑制剂治疗优化策略。
6. 试述弹性纤维假黄瘤的ABCC6基因治疗研究突破及临床转化挑战。
7. 分析浆细胞增多症的骨髓微环境特征及多发性骨髓瘤转化预警标志物。
8. 论述移植物抗宿主病的皮肤病理特征与细胞因子风暴关联机制。
9. 结合单细胞测序技术,探讨毛囊黏蛋白病的肿瘤微环境异质性。
10. 试述慢性光化性皮炎的光敏信号通路(如NF-κB)调控及药物干预。
11. 论述皮肤淋巴管畸形的介入治疗进展及多模态影像引导技术。
12. 分析皮肤假性水疱病的自身抗体谱检测及与疱病鉴别诊断流程。
13. 结合病例,阐述红斑狼疮妊娠期管理的多学科协作模式及伦理争议。
14. 试述神经纤维瘤病Ⅱ型的Merlin蛋白功能丧失机制及基因治疗潜力。
15. 论述IgG4相关疾病的纤维化机制及靶向IL-4/IL-13通路治疗前景。
16. 分析皮肤转移性肝癌的循环肿瘤细胞(CTC)检测在预后评估中的价值。
17. 试述光线性唇炎的癌变表观遗传学标志物筛选及早期干预策略。
18. 结合代谢组学,阐述假性软骨瘤的肿瘤代谢重编程特征及营养干预。
19. 论述皮肤血管炎的ANCA检测亚型分型及治疗靶点选择依据。
20. 试述毛发扁平苔藓的瘢痕性脱发免疫调节治疗(如JAK抑制剂)机制。
21. 分析皮肤型结节病的干扰素-γ释放试验在疾病活动性判断中的局限性。
22. 论述卟啉病的光敏感机制及新型光保护剂(如抗氧化纳米颗粒)研发。
23. 结合病例,阐述假性卟啉病的药物代谢酶基因多态性分析及个体化用药。
24. 试述红斑狼疮抗磷脂抗体综合征的抗凝治疗矛盾及多学科平衡策略。
25. 论述毛母质瘤的Wnt/β-catenin信号通路异常及靶向治疗可行性。
26. 分析皮肤AI辅助诊断系统在罕见肿瘤鉴别中的深度学习优化方案。
27. 结合液体活检技术,探讨黏膜利什曼病的治疗反应动态监测模型构建。
28. 试述神经病理性溃疡的离子通道调控机制及新型局部镇痛贴剂研发。
29. 论述光动力治疗中光敏剂纳米载药系统的跨屏障递送机制及临床优势。
30. 分析皮肤转移性肾细胞癌的免疫治疗(如PD-1抑制剂)耐药机制及逆转策略。
31. 试述假性上皮瘤样增生的HPV整合位点检测及与鳞癌发生的分子关联。
32. 结合类器官模型,阐述毛囊闭锁四联症的炎症通路调控及药物筛选。
33. 论述结节性多动脉炎的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如VCAM-1)检测价值。
34. 分析红斑狼疮患者肠道菌群-免疫轴调控机制及益生菌干预临床试验设计。
35. 试述弹性纤维假黄瘤的碱基编辑技术(Base Editing)治疗潜力及脱靶风险。
36. 结合宏基因组测序,阐述皮肤幼虫移行症的快速病原鉴定及治疗优化。
37. 论述瘢痕疙瘩的机械应力感应通路(如YAP/TAZ)调控及新型压力装置研发。
38. 分析红斑狼疮妊娠期药物胎盘穿透性评估模型及胎儿安全性预测。
39. 试述神经鞘瘤的肿瘤代谢成像(如PET-MRI)在恶性转化监测中的应用。
40. 论述浆细胞增多症的克隆演化监测及早期骨髓瘤干预策略。
41. 结合空间转录组学,探讨光线性角化病的癌变空间异质性及治疗靶点。
42. 试述黏膜念珠菌病的棘白菌素类药物耐药机制及新型糖苷酶抑制剂研发。
43. 分析恶性黑色素瘤液态活检(ctDNA)在微小残留病灶检测中的敏感性。
44. 论述假性肉瘤病理人工智能系统的多中心验证研究设计及标准化挑战。
45. 结合患者源性异种移植(PDX)模型,阐述毛囊黏蛋白病的精准药物筛选。
46. 试述慢性光化性皮炎的光脱敏治疗免疫调节机制及长期疗效评估。
47. 分析转移性前列腺癌的雄激素受体变异检测及二代激素治疗选择依据。
48. 论述皮肤型血管炎的补体激活途径靶向治疗(如C5a抑制剂)研究进展。
49. 结合肿瘤微环境,阐述AI辅助诊断系统在皮肤癌病理判读中的算法优化。
50. 试述红斑狼疮JAK-STAT通路异常及新型抑制剂(如Tofacitinib)临床试验设计。
一、名词解释(每题3分,共30分)
1. 皮肤副肿瘤性天疱疮
2. 皮肤浆细胞增生症
3. 皮肤黏膜黑色素瘤
4. 皮肤穿通性弹性纤维病
5. 皮肤假性腺样囊性癌
6. 皮肤神经束膜瘤
7. 皮肤嗜酸性肉芽肿
8. 皮肤淀粉样变苔藓样型
9. 皮肤移植物抗宿主病(慢性期)
10. 皮肤疣状表皮发育不良
二、简答题(每题5分,共250分)
1. 简述副肿瘤性天疱疮的靶抗原类型及合并肿瘤的筛查策略。
2. 皮肤浆细胞增生症的病理特征及与多发性骨髓瘤的鉴别要点。
3. 皮肤黏膜黑色素瘤的ABCDE法则扩展(如CASH标准)及其应用价值。
4. 穿通性弹性纤维病的组织病理学特征及与获得性穿通性皮肤病的鉴别。
5. 假性腺样囊性癌的免疫组化标志物组合(如CK7/S100)及诊断意义。
6. 皮肤神经束膜瘤的临床特征与神经纤维瘤病的关联性分析。
7. 嗜酸性肉芽肿的皮肤外系统受累评估及治疗药物选择。
8. 淀粉样变苔藓样型的刚果红染色假阴性原因及质谱分型技术。
9. 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皮肤纤维化机制及治疗挑战。
10. 疣状表皮发育不良的HPV亚型检测及恶变监测方案。
11. 皮肤假性淋巴瘤的TCR基因重排检测结果判读标准及临床意义。
12. 皮肤肥大细胞增生症的骨髓活检指征及系统性评估流程。
13. 皮肤黏膜念珠菌病的唑类药物耐药基因检测技术及治疗调整。
14. 结节性硬化症的皮肤科与神经科联合管理要点。
15. 弹性纤维假黄瘤的基因检测(ABCC6)流程及遗传咨询注意事项。
16. 皮肤型红斑狼疮的羟氯喹治疗剂量调整与视网膜毒性监测方案。
17. 皮肤毛母质瘤的影像学特征(如超声)与手术切除范围设计。
18. 皮肤AI辅助诊断系统在色素性皮损中的误诊案例分析。
19. 皮肤淋巴管畸形的硬化治疗并发症(如溃疡)预防策略。
20. 皮肤假性水疱病的直接免疫荧光表现及鉴别诊断流程。
21. 皮肤型IgG4相关疾病的血清IgG4水平诊断阈值争议。
22. 皮肤神经病理性溃疡的局部辣椒素贴剂应用机制及限制因素。
23. 皮肤光动力治疗中新型光敏剂(如金纳米颗粒)的增效机制。
24. 皮肤转移性肺癌的免疫组化标志物(如TTF-1/Napsin A)选择依据。
25. 皮肤假性软骨瘤的代谢组学生物标志物筛选及临床转化挑战。
26. 皮肤红斑狼疮患者的干扰素基因特征(ISG)检测技术进展。
27. 皮肤黏膜利什曼病的分子快速诊断(如LAMP技术)优化方案。
28. 皮肤毛囊闭锁四联症的炎症信号通路(如IL-17)调控机制。
29. 皮肤型结节病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细胞分类诊断标准。
30. 皮肤卟啉病的血红素合成通路异常及光敏感机制解析。
31. 皮肤假性卟啉病的药物代谢酶基因多态性分析及个体化用药。
32. 皮肤红斑狼疮合并抗磷脂抗体综合征的抗凝治疗矛盾与平衡。
33. 皮肤毛发扁平苔藓的瘢痕性脱发预防性治疗(如JAK抑制剂)机制。
34. 皮肤光线性角化病的甲基化标志物(如RASSF1A)筛查意义。
35. 皮肤恶性黑色素瘤的液态活检(ctDNA)在术后微小残留病灶监测中的应用。
36. 皮肤假性肉瘤的病理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多中心验证研究设计。
37. 皮肤型血管炎的ANCA亚型(MPO/PR3)检测临床关联性分析。
38. 皮肤浆细胞增多症的克隆性检测(如流式细胞术)技术选择。
39. 皮肤慢性光化性皮炎的光脱敏治疗免疫调节机制解析。
40. 皮肤转移性前列腺癌的雄激素受体剪接变异检测及治疗选择。
41. 皮肤弹性纤维假黄瘤的碱基编辑治疗(如ABE)脱靶风险评估。
42. 皮肤罕见寄生虫感染(如皮肤利什曼病)的宿主免疫逃逸机制。
43. 皮肤瘢痕疙瘩的机械应力调控通路(如Hippo-YAP)研究进展。
44. 皮肤红斑狼疮妊娠期药物的胎盘穿透性评估模型构建。
45. 皮肤神经鞘瘤的NF2基因突变检测技术(如NGS)优化方案。
46. 皮肤光老化中端粒缩短机制及端粒酶激活剂(如TA-65)应用前景。
47. 皮肤型结节性多动脉炎的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如sVCAM-1)检测意义。
48. 皮肤黏膜念珠菌病的宿主免疫缺陷分型(如STAT1突变)及治疗策略。
49. 皮肤假性上皮瘤样增生的HPV整合位点检测及癌变风险预测。
50. 皮肤毛囊黏蛋白病的单细胞测序技术揭示肿瘤微环境异质性。
三、论述题(每题10分,共500分)
1. 论述副肿瘤性天疱疮的自身抗体谱检测及合并恶性肿瘤的早期筛查策略。
2. 试述皮肤浆细胞增生症的克隆演化监测及多发性骨髓瘤转化预警模型构建。
3. 结合病例,分析皮肤黏膜黑色素瘤的免疫治疗(如PD-1抑制剂)应答异质性机制。
4. 论述穿通性弹性纤维病的遗传异质性及与结缔组织代谢异常的分子关联。
5. 试述假性腺样囊性癌的分子分型(如MYB-NFIB融合)对靶向治疗的指导意义。
6. 分析皮肤神经束膜瘤的神经嵴起源学说与周围神经肿瘤分类争议。
7. 结合单细胞测序技术,探讨嗜酸性肉芽肿的肿瘤微环境免疫抑制特征。
8. 论述淀粉样变苔藓样型的质谱蛋白分型技术对个体化治疗的革新意义。
9. 试述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纤维化信号通路(如TGF-β/Smad)靶向治疗突破。
10. 分析疣状表皮发育不良的HPV致癌机制及CRISPR基因编辑治疗潜力。
11. 结合液体活检技术,阐述皮肤假性淋巴瘤向淋巴瘤转化的分子预警标志物。
12. 论述肥大细胞增生症的KIT D816V突变检测技术优化及耐药克隆监测策略。
13. 试述皮肤黏膜念珠菌病的宿主免疫缺陷基因筛查(如CARD9突变)及精准治疗。
14. 分析结节性硬化症的mTOR通路抑制剂(如依维莫司)治疗应答差异的分子基础。
15. 论述弹性纤维假黄瘤的基因替代治疗(如AAV载体)临床前研究挑战。
16. 结合病例,阐述皮肤型红斑狼疮的干扰素基因特征(ISG)动态监测及治疗调整。
17. 试述毛母质瘤的Wnt/β-catenin通路异常及靶向药物(如LGK974)临床试验设计。
18. 分析AI辅助诊断系统在皮肤罕见肿瘤(如神经束膜瘤)中的误诊原因及算法优化。
19. 论述淋巴管畸形介入治疗的影像引导技术(如超声融合导航)进展及并发症管理。
20. 试述假性水疱病的自身抗体(如BP180)表位定位技术及治疗靶点挖掘。
21. 结合代谢组学,阐述IgG4相关疾病的纤维化机制及抗代谢治疗(如二甲双胍)潜力。
22. 论述神经病理性溃疡的TRPV1通道调控机制及新型透皮镇痛贴剂研发。
23. 分析光动力治疗中金纳米颗粒增强光敏剂渗透的物理化学机制及临床转化难点。
24. 试述转移性肺癌皮肤病灶的循环肿瘤细胞(CTC)检测在原发灶溯源中的价值。
25. 结合类器官模型,探讨假性软骨瘤的肿瘤代谢重编程特征及营养干预策略。
26. 论述红斑狼疮ISG检测的微流控芯片技术开发及床旁快速诊断应用前景。
27. 分析黏膜利什曼病的LAMP技术敏感性提升策略及资源有限地区的应用优势。
28. 试述毛囊闭锁四联症的IL-17/IL-23通路靶向治疗(如司库奇尤单抗)临床研究进展。
29. 结合空间转录组学,探讨皮肤型结节病的肉芽肿形成空间异质性机制。
30. 论述卟啉病的光保护剂(如纳米氧化铈)抗氧化机制及透皮递送系统优化。
31. 分析假性卟啉病的药物基因组学指导个体化用药模式及伦理争议。
32. 试述红斑狼疮合并抗磷脂抗体综合征的补体抑制治疗(如抗C5单抗)潜在价值。
33. 结合CRISPR筛选技术,揭示毛发扁平苔藓的瘢痕形成关键基因靶点。
34. 论述光线性角化病的表观遗传学治疗(如DNMT抑制剂)临床前研究突破。
35. 分析液态活检在皮肤恶性黑色素瘤术后监测中的敏感性阈值及假阳性控制策略。
36. 试述病理AI系统的联邦学习框架构建及多中心数据隐私保护方案。
37. 结合患者源性异种移植(PDX)模型,探索血管炎靶向治疗(如抗C5aR抗体)疗效预测。
38. 论述浆细胞增多症的肿瘤微环境代谢特征(如乳酸堆积)及靶向干预策略。
39. 试述慢性光化性皮炎的光脱敏治疗联合免疫调节剂(如阿普斯特)协同机制。
40. 分析转移性前列腺癌皮肤病灶的AR-V7变异检测及二代激素治疗优化方案。
41. 结合碱基编辑技术,探讨弹性纤维假黄瘤的ABCC6基因修复精准性提升策略。
42. 论述皮肤利什曼病的宿主-寄生虫相互作用机制及疫苗设计难点。
43. 试述瘢痕疙瘩的机械应力调控纳米材料(如压电聚合物)局部干预研究。
44. 结合胎盘类器官模型,分析红斑狼疮妊娠期药物的胎儿安全性评估新方法。
45. 论述神经鞘瘤的代谢成像(如超极化MRI)在恶性转化早期监测中的价值。
46. 试述光老化中线粒体自噬(Mitophagy)调控机制及Senolytics药物应用前景。
47. 分析结节性多动脉炎的血管内皮单细胞测序揭示炎症亚群异质性。
48. 结合肠道菌群移植,探讨红斑狼疮患者免疫调节治疗的临床研究设计。
49. 论述皮肤假性上皮瘤样增生的HPV致癌信号通路(如PI3K/AKT)靶向治疗潜力。
50. 试述毛囊黏蛋白病的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F)调控机制及靶向策略。
加入昆布秘圈,查询考研考博真题和下载资料,这是一个收费圈。没有找到资料可以在圈内发表需求。
临床研究临床结果
100 项与 沙利度胺 相关的药物交易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研发状态
批准上市
10 条最早获批的记录, 后查看更多信息
登录
| 适应症 | 国家/地区 | 公司 | 日期 |
|---|---|---|---|
| POEMS综合征 | 日本 | 2021-02-24 | |
| 麻风结节性红斑 | 日本 | 2012-05-25 | |
| 多发性骨髓瘤 | 韩国 | 2006-04-07 | |
| 结节性红斑 | 美国 | 1998-07-16 |
未上市
10 条进展最快的记录, 后查看更多信息
登录
| 适应症 | 最高研发状态 | 国家/地区 | 公司 | 日期 |
|---|---|---|---|---|
| 小儿克罗恩病 | 临床3期 | 意大利 | 2018-02-27 | |
| 溃疡性结肠炎 | 临床3期 | 意大利 | 2008-08-01 | |
| 克罗恩病 | 临床3期 | 意大利 | 2008-08-01 | |
| 消化道出血 | 临床3期 | 美国 | 2006-05-01 | |
| 门静脉高血压 | 临床3期 | 美国 | 2006-05-01 | |
| 复发性多发性骨髓瘤 | 临床3期 | 保加利亚 | 2006-02-01 | |
| 复发性多发性骨髓瘤 | 临床3期 | 克罗地亚 | 2006-02-01 | |
| 复发性多发性骨髓瘤 | 临床3期 | 捷克 | 2006-02-01 | |
| 复发性多发性骨髓瘤 | 临床3期 | 法国 | 2006-02-01 | |
| 复发性多发性骨髓瘤 | 临床3期 | 德国 | 2006-02-01 |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临床结果
临床结果
适应症
分期
评价
查看全部结果
| 研究 | 分期 | 人群特征 | 评价人数 | 分组 | 结果 | 评价 | 发布日期 |
|---|
N/A | 多发性骨髓瘤 一线 | 28 | 鹽範膚餘餘窪鏇壓願鹽(製淵鑰醖壓鏇夢築淵糧) = 鏇鏇蓋壓齋衊鹽艱願願 觸構繭範淵鹹夢顧鏇鏇 (窪憲艱醖餘觸壓簾鏇鑰 ) 更多 | 积极 | 2025-12-06 | ||
临床4期 | 66 | Camrelizumab+prophylactic thalidomide | 觸餘糧獵製壓顧築糧鑰(鹹齋範鹽遞遞窪繭鏇廠) = 鏇鑰衊壓顧製淵淵築衊 繭獵齋艱鬱範醖製願壓 (觸鹽糧遞憲鏇膚製醖顧 ) 更多 | 积极 | 2025-12-05 | ||
N/A | 31 | 鑰夢憲觸廠觸積夢鏇鏇(構壓壓醖構願餘壓顧鏇) = classified grade 3 and 4 toxicities as per CTCAE guidelines 鹹襯簾壓艱鑰範醖積範 (製廠製膚繭鏇範築醖膚 ) | 积极 | 2025-11-05 | |||
临床3期 | 72 | 鑰範積衊鹹遞醖鬱壓醖(廠觸窪獵齋艱繭構衊淵) = 膚齋膚願襯觸襯鹹齋艱 膚膚餘衊簾範醖鹽製衊 (鑰積齋選繭蓋鹹齋顧積 ) 更多 | 积极 | 2025-10-12 | |||
鑰範積衊鹹遞醖鬱壓醖(廠觸窪獵齋艱繭構衊淵) = 構網壓糧製壓襯襯壓積 膚膚餘衊簾範醖鹽製衊 (鑰積齋選繭蓋鹹齋顧積 ) 更多 | |||||||
临床3期 | β地中海贫血 GATA-1 | KLF | HBS1L-MYB rs9399137 | 164 | 蓋願蓋膚製選構鬱簾觸(夢獵憲願鏇壓顧遞製鏇) = 膚醖鹽鑰簾構夢夢憲蓋 醖壓願網餘鹽願積繭糧 (簾構襯鏇鬱積鏇蓋鑰蓋, 2.04) | 积极 | 2025-07-01 | ||
N/A | 52 | 範廠顧選築觸窪齋構廠(製鬱艱襯簾簾築觸構選) = constipation seen in 16 patients (30.8%) and all were grade I/II 製選襯觸範膚選繭膚壓 (憲獵觸築衊齋膚鹽餘積 ) 更多 | 积极 | 2025-05-14 | |||
| - | - | 夢艱繭糧網窪醖範範鬱(積襯遞夢鏇鑰鑰簾構顧) = 範餘齋觸艱網襯憲鬱製 壓膚選膚遞夢壓鹽壓構 (鑰餘糧艱襯夢範構繭餘 ) 更多 | - | 2024-12-08 | |||
夢艱繭糧網窪醖範範鬱(積襯遞夢鏇鑰鑰簾構顧) = 遞遞淵鬱鏇衊艱鹽糧鑰 壓膚選膚遞夢壓鹽壓構 (鑰餘糧艱襯夢範構繭餘 ) 更多 | |||||||
早期临床1期 | 19 | 積壓積築鏇餘膚壓鏇鹽(鹹艱鏇製醖積餘網築壓) = 製鬱簾顧製淵範鹹衊簾 襯簾繭願築鬱衊網襯鏇 (醖廠廠獵糧積網膚顧遞 ) 更多 | 积极 | 2024-11-11 | |||
N/A | 45 | 鬱獵鏇顧衊齋鑰簾製鏇(衊襯選憲窪網鏇壓鑰膚) = 餘衊構願製鹽淵蓋夢觸 醖遞願遞襯齋壓獵廠築 (衊壓網製餘膚鏇齋艱襯 ) 更多 | 积极 | 2024-09-15 | |||
临床3期 | 多发性骨髓瘤 巩固 | 维持 | 1,085 | D-VTd | 鹽鹽願積壓鑰簾鏇襯網(選鬱鹹構艱鹽鬱構淵醖) = 膚築廠鹹壓餘簾鹽鏇襯 製夢範網積艱鹹鹹襯憲 (顧範壓構鑰觸鹹鏇鹹網 ) 更多 | 积极 | 2024-09-04 | |
VTd | 願艱鬱夢齋製鬱網網窪(膚鏇餘蓋艱鹹繭簾遞淵) = 網夢壓憲窪遞襯鹹餘淵 壓鹽遞鏇鬱獵廠選壓憲 (鏇網構襯網餘積窪廠範 ) |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转化医学
使用我们的转化医学数据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药物交易
使用我们的药物交易数据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核心专利
使用我们的核心专利数据促进您的研究。
登录
或

临床分析
紧跟全球注册中心的最新临床试验。
登录
或

批准
利用最新的监管批准信息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特殊审评
只需点击几下即可了解关键药物信息。
登录
或

生物医药百科问答
全新生物医药AI Agent 覆盖科研全链路,让突破性发现快人一步
立即开始免费试用!
智慧芽新药情报库是智慧芽专为生命科学人士构建的基于AI的创新药情报平台,助您全方位提升您的研发与决策效率。
立即开始数据试用!
智慧芽新药库数据也通过智慧芽数据服务平台,以API或者数据包形式对外开放,助您更加充分利用智慧芽新药情报信息。
生物序列数据库
生物药研发创新
免费使用
化学结构数据库
小分子化药研发创新
免费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