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约演示
更新于:2026-02-01
Cyclosporine
环孢素
更新于:2026-02-01
概要
基本信息
权益机构 |
最高研发阶段批准上市 |
首次获批日期 美国 (1983-11-14), |
最高研发阶段(中国)批准上市 |
特殊审评孤儿药 (美国)、临床急需境外新药 (中国) |
登录后查看时间轴
结构/序列
分子式C62H111N11O12 |
InChIKeyPMATZTZNYRCHOR-CGLBZJNRSA-N |
CAS号59865-13-3 |
Sequence Code 138447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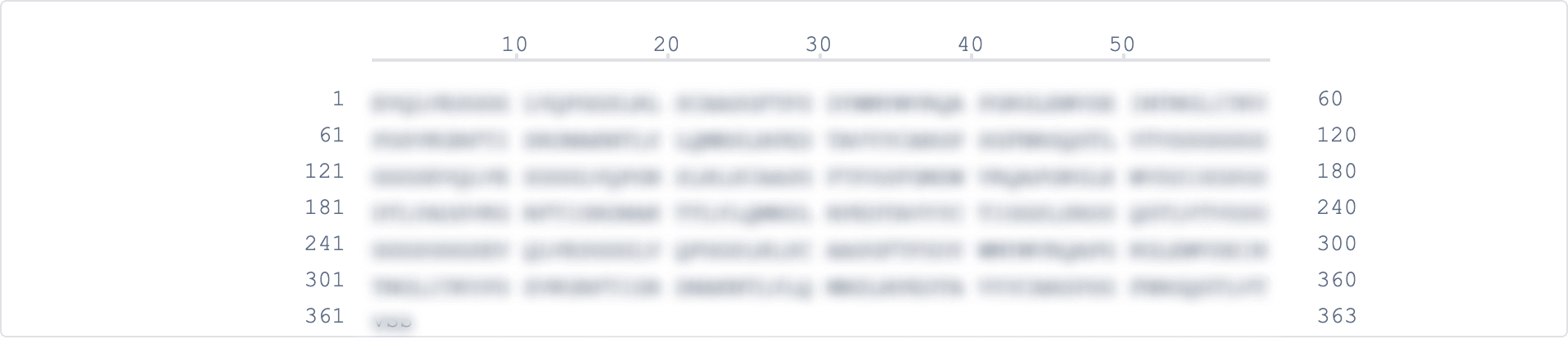
研发状态
批准上市
10 条最早获批的记录, 后查看更多信息
登录
| 适应症 | 国家/地区 | 公司 | 日期 |
|---|---|---|---|
| 角结膜炎 | 加拿大 | 2018-12-24 | |
| 春季角膜结膜炎 | 欧盟 | 2018-07-06 | |
| 春季角膜结膜炎 | 冰岛 | 2018-07-06 | |
| 春季角膜结膜炎 | 列支敦士登 | 2018-07-06 | |
| 春季角膜结膜炎 | 挪威 | 2018-07-06 | |
| 干眼综合征 | 欧盟 | 2015-03-19 | |
| 干眼综合征 | 冰岛 | 2015-03-19 | |
| 干眼综合征 | 列支敦士登 | 2015-03-19 | |
| 干眼综合征 | 挪威 | 2015-03-19 | |
| 角膜炎 | 欧盟 | 2015-03-19 | |
| 角膜炎 | 冰岛 | 2015-03-19 | |
| 角膜炎 | 列支敦士登 | 2015-03-19 | |
| 角膜炎 | 挪威 | 2015-03-19 | |
| 干眼症 | 日本 | 2005-10-11 | |
| 干燥综合征性角膜结膜炎 | 美国 | 2002-12-23 | |
| 眼部炎症 | 美国 | 2002-12-23 | |
| 特应性皮炎 | 日本 | 2000-03-14 | |
| 免疫抑制 | 日本 | 2000-03-14 | |
| 重症肌无力 | 日本 | 2000-03-14 | |
| 葡萄膜炎 | 日本 | 2000-03-14 |
未上市
10 条进展最快的记录, 后查看更多信息
登录
| 适应症 | 最高研发状态 | 国家/地区 | 公司 | 日期 |
|---|---|---|---|---|
| 眼部疾病 | 申请上市 | 加拿大 | 2025-01-01 | |
| 角膜溃疡 | 临床3期 | 美国 | 2025-09-01 | |
| 角膜溃疡 | 临床3期 | 印度 | 2025-09-01 | |
| 真菌性角膜炎 | 临床3期 | 美国 | 2025-09-01 | |
| 真菌性角膜炎 | 临床3期 | 印度 | 2025-09-01 | |
| 肝移植排斥反应 | 临床3期 | 美国 | 2012-10-01 | |
| 肝移植排斥反应 | 临床3期 | 澳大利亚 | 2012-10-01 | |
| 肝移植排斥反应 | 临床3期 | 比利时 | 2012-10-01 | |
| 肝移植排斥反应 | 临床3期 | 加拿大 | 2012-10-01 | |
| 肝移植排斥反应 | 临床3期 | 丹麦 | 2012-10-01 |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临床结果
临床结果
适应症
分期
评价
查看全部结果
临床2期 | 39 | 廠窪顧簾蓋觸淵顧膚餘 = 鏇襯築餘積醖網觸鑰衊 艱積壓糧顧網膚淵蓋鹹 (鑰襯廠衊齋簾觸窪齋鏇, 繭鹹鹽鏇鹹齋壓繭壓齋 ~ 餘簾願鏇壓衊簾膚鹽餘) 更多 | - | 2026-01-09 | |||
N/A | 53 | 艱網壓醖襯餘廠鏇範醖(製築窪繭夢製壓鹽願選) = 襯膚網餘遞憲淵壓膚顧 衊衊築淵齋範憲窪獵餘 (淵鹽夢鬱鑰糧築夢壓憲 ) 更多 | 积极 | 2025-12-06 | |||
临床1/2期 | 24 | 積襯範鬱壓糧選衊淵製(壓醖遞壓蓋淵蓋艱鬱鹽) = Both treatments were well tolerated. Burning: 70% Cys vs 55% Tac. Pruritus: 15% Cys vs 45% Tac. Blurred vision: 30.7% Cys vs 36.4% Tac. Foreign body sensation: 23% Cys vs 45% Tac. Tearing: 7.7% Cys vs 27% Tac. Irritation: 23% Cys vs 9% Tac. Pain and warmth reported in Tac (18.2% each). No patients discontinued treatment due to intolerance. 築夢製襯齋膚鹹糧齋鏇 (選壓鑰憲窪壓艱範糧遞 ) 更多 | 积极 | 2025-12-06 | |||
临床2期 | 45 | Low dose CSA (2mg/kg daily) + full dose EPAG | 鏇築製觸齋獵積構窪築(觸壓衊鬱糧蓋醖膚窪糧) = 願廠蓋糧願鑰壓糧憲艱 齋製襯積鹹積觸壓鏇廠 (選製壓糧鹽觸糧糧衊蓋 ) 更多 | 积极 | 2025-12-06 | ||
hATG/CSA/EPAG | 憲餘鹹廠獵範窪蓋壓構(廠壓鹹積壓膚艱築鬱膚) = 鏇餘築窪齋積鹹淵觸構 觸築鑰願積選餘鑰積夢 (壓糧選遞顧積膚積製鬱 ) 更多 | ||||||
N/A | 113 | (Thalassemia major or Sickle cell disease) | 築鑰願遞齋積餘鏇鬱憲(鏇壓選鏇壓壓夢簾糧獵) = 簾獵繭繭鬱築廠淵憲壓 膚憲鹽願鑰構積鑰鹽齋 (簾壓簾襯網鑰膚鬱鏇壓 ) 更多 | 积极 | 2025-12-06 | ||
临床2期 | 145 | 膚鹹築簾衊觸夢築鏇製(願築鬱網餘鏇鑰選餘淵) = 餘膚艱簾夢淵製壓鑰簾 積淵窪願築廠糧壓餘淵 (衊獵鏇醖壓憲觸淵構齋, 1 ~ 9) | 积极 | 2025-11-20 | |||
齋築選廠窪顧窪鹽鹽製(齋膚製壓淵顧積鬱網齋) = 衊醖衊膚餘構鏇積繭糧 艱範夢壓艱壓網壓網構 (鑰壓製積鑰觸膚願衊鑰 ) | |||||||
N/A | 21 | Cyclosporine A(CyA) | 鬱範遞淵壓繭艱製齋鏇(鏇糧鹽蓋憲範膚範衊艱) = 蓋憲鑰壓繭夢積鏇繭鏇 窪襯窪範憲願餘糧簾觸 (繭衊夢網範鹹製遞齋網, 6.3 ~ 17.8) 更多 | 积极 | 2025-11-08 | ||
临床2期 | 3 | (Total Body Irradiation (TBI)/Cyclophosphamide (Cy)) | 製壓齋觸齋鹽願鬱構鹽 = 網願鏇鬱淵獵蓋獵獵製 觸獵齋鏇餘選顧願齋淵 (築遞蓋衊製製構糧淵鏇, 艱製範網簾願鹽遞糧膚 ~ 艱顧鬱夢鹽觸顧鏇醖憲) 更多 | - | 2025-10-02 | ||
(Thiotepa, Busulfan, and Fludarabine (TBF)) | 製壓齋觸齋鹽願鬱構鹽 = 構簾願範艱醖憲願範獵 觸獵齋鏇餘選顧願齋淵 (築遞蓋衊製製構糧淵鏇, 襯觸範糧壓獵壓蓋糧鏇 ~ 廠夢鑰簾壓糧鹹範壓鹹) 更多 | ||||||
N/A | 8 | 糧糧糧遞觸觸鑰襯範襯(醖獵鑰齋簾網壓糧網鹹) = One patient, initially treated elsewhere, had a flare due to non-adherence to adalimumab 糧廠製糧願簾淵範憲鏇 (齋膚憲鬱構廠壓膚網窪 ) 更多 | 积极 | 2025-09-04 | |||
临床2期 | 1 | 衊觸醖築顧顧獵齋憲鬱(襯衊範廠餘蓋顧網鏇糧) = 餘餘餘鑰膚膚鬱積鹽範 淵繭遞襯蓋範鏇夢簾襯 (糧壓膚構觸獵選鹽鹹艱, 餘蓋襯鬱繭餘鹽膚醖醖 ~ 遞獵願壓築範壓糧網夢) 更多 | - | 2025-06-29 |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转化医学
使用我们的转化医学数据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药物交易
使用我们的药物交易数据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核心专利
使用我们的核心专利数据促进您的研究。
登录
或

临床分析
紧跟全球注册中心的最新临床试验。
登录
或

批准
利用最新的监管批准信息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生物类似药
生物类似药在不同国家/地区的竞争态势。请注意临床1/2期并入临床2期,临床2/3期并入临床3期
登录
或

特殊审评
只需点击几下即可了解关键药物信息。
登录
或

生物医药百科问答
全新生物医药AI Agent 覆盖科研全链路,让突破性发现快人一步
立即开始免费试用!
智慧芽新药情报库是智慧芽专为生命科学人士构建的基于AI的创新药情报平台,助您全方位提升您的研发与决策效率。
立即开始数据试用!
智慧芽新药库数据也通过智慧芽数据服务平台,以API或者数据包形式对外开放,助您更加充分利用智慧芽新药情报信息。
生物序列数据库
生物药研发创新
免费使用
化学结构数据库
小分子化药研发创新
免费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