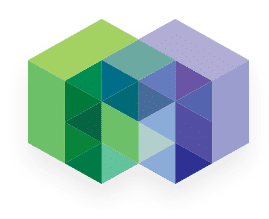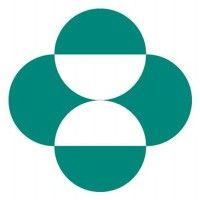预约演示
更新于:2026-01-28
Acetaminophen
对乙酰氨基酚
更新于:2026-01-28
概要
基本信息
简介对乙酰氨基酚是一种常见的用于镇痛和退热的OTC药物,于1951 年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的批准, 它的作用方式与经典的非甾体抗炎药 (NSAID) 非常相似,通过阻碍 COX-1 和 COX-2 酶的活性发挥作用。对乙酰氨基酚用于治疗轻度至中度疼痛、中度至重度疼痛 与阿片类药物联用,或对抗发烧。 它是一种常见的治疗多种疾病的药物,例如头痛、肌肉酸痛、关节炎、背痛、牙痛、喉咙痛、感冒、流感和发烧。这种药物有多种剂型,包括糖浆、常规和泡腾剂 片剂、注射剂和栓剂。 虽然主要是口服给药,但也可以静脉内给药。 重要的是过量服用对乙酰氨基酚是危险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 服用时必须遵循正确剂量,如果过量服用立即就医。对乙酰氨基酚于 无需处方即可广泛使用 处方药或作为处方药。 |
药物类型 小分子化药 |
别名 4'-hydroxyacetanilide、4-(Acetylamino)phenol、4-ACETAMIDOPHENOL + [92] |
靶点 |
作用方式 抑制剂 |
作用机制 COX抑制剂(环氧化酶抑制剂) |
原研机构 |
最高研发阶段批准上市 |
最高研发阶段(中国)批准上市 |
特殊审评- |
登录后查看时间轴
结构/序列
分子式C8H9NO2 |
InChIKeyRZVAJINKPMORJF-UHFFFAOYSA-N |
CAS号103-90-2 |
关联
1,713
项与 对乙酰氨基酚 相关的临床试验ACTRN12626000027314
Effect of Paracetamol on Reperfusion Injury in Patients with ST-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A Multi-centre, Open-Label, Randomised Control Trial.
开始日期2026-03-02 |
申办/合作机构 |
ChiCTR2600115977
Optimization of ERAS management model in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pediatric day surgery: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low-opioid multimodal analgesia strategy.
开始日期2026-01-06 |
申办/合作机构- |
CTRI/2025/12/099594
Comparative study of intravenous paracetamol and intravenous tramadol for post operative analgesia in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 nil
开始日期2026-01-03 |
申办/合作机构- |
100 项与 对乙酰氨基酚 相关的临床结果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100 项与 对乙酰氨基酚 相关的转化医学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100 项与 对乙酰氨基酚 相关的专利(医药)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46,054
项与 对乙酰氨基酚 相关的文献(医药)2026-12-01·MOLECULAR BIOLOGY REPORTS
Retraction Note: Inhibitory activity of black mulberry (Morus nigra) extract against testicular, liver and kidney toxicity induced by paracetamol in mice
Article
作者: Abdel-Samie, Negm S ; Diab, Kawthar A ; Fahmy, Maha A ; Hassan, Emad M ; Omara, Enayat A ; Hassan, Zeinab M
2026-04-01·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LC-ESI-MS/MS-based phytochemical profiling and pharmacological validation of Centaurium erythraea Rafn (Gentianaceae) traditionally used for pain and inflammation
Article
作者: Ozen, Tevfik ; Amrane, Abdeltif ; Boudjelal, Amel ; Tail, Ghania ; Demirtas, Ibrahim ; Chabane, Sarra ; Yenigün, Semiha ; Yıldız, Ilyas ; Bouchahdane, Souheila
ETHNOPHARMACOLOGICAL RELEVANCE:
These findings provide scientific support for the traditional use of Centaurium erythraea Rafn (Gentianaceae) in Algerian folk medicine and suggest its potential for further pharmacological explora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pain and neuroinflammatory conditions.
AIM OF THE STUDY: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scientifically validate these traditional uses through phytochemical profiling and pharmacological evaluation of the aqueous extract (C. erythraea aqueous extract, CEAE).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polyphenolic composition was characterized, and in vitro antioxidant and DNA protection activities, enzyme inhibitory effects, as well as in vivo analgesic activity using the acetic acid-induced writhing and hot plate tests, in addition to acute oral toxicity, and molecular docking studie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LC-ESI-MS/MS analysis revealed the presence of several phenolic and flavonoid constituents, including trans-ferulic acid (278.74 μg/g), syringic acid (172.81 μg/g), polydatin (33.72 μg/g), vanillin (13.05 μg/g), quercetin (12.44 μg/g), and isoquercitrin (9.32 μg/g), along with minor levels of kaempferol and trans-cinnamic acid. CEAE exhibited moderate antioxidant activity, with the strongest effect in the FRAP assay (IC50 = 148.73 ± 8.50 μg/mL). The extract showed dual inhibition of acetylcholinesterase (AChE) and butyrylcholinesterase (BChE), demonstrating stronger activity against BChE (IC50 = 31.27 ± 2.68 μg/mL) than the reference drug galantamine. In plasmid DNA protection assays, CEAE (14.69% protection) and quercetin preserved supercoiled DNA (Form I) from oxidative damage. Oral administration of CEAE (2000 mg/kg) produced no signs of toxicity, indicating a wide safety margin. In vivo, CEAE significantly reduced acetic acid-induced writhing (51.23% inhibition at 300 mg/kg) and increased latency times in the hot plate test, showing greater analgesic efficacy than paracetamol. The binding affinity of the trans-ferulic/syringic acid adduct (-7.1 kcal/mol) in molecular docking interactions with AChE was determined to b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mpounds (-6.7 kcal/mol) used alone.
CONCLUSIONS:
Overall, the aqueous extract of C. erythraea demonstrates notable antioxidant, cholinesterase-inhibitory, DNA-protective, and analgesic activities, consistent with its traditional use for pain and inflammation.
2026-04-01·SURGERY
Rates and predictors of postdischarge opioid-free analgesia after elective colorectal surgery: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Article
作者: Fermi, Francesca ; Boutros, Marylise ; Lee, Lawrence ; Shirzadi, Samin ; Kaneva, Pepa ; Dmowski, Katy ; Nguyen-Powanda, Philip ; Feldman, Liane S ; Pook, Makena ; Jain, Shrieda ; Lapointe-Gagner, Maxime ; Ghezeljeh, Tahereh Najafi ; Olleik, Ghadeer ; Fiore, Julio F ; Al Ben Ali, Sarah ; Alali, Naser
BACKGROUND:
Opioids are widely prescribed after colorectal surgery but may cause adverse events, misuse, and addiction. Despite growing interest in opioid-free analgesia, the rat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undergoing colorectal surgery who consume no opioids postdischarge remain uncertain. This study aimed to (1) estimate the rate of patients who consume no opioids postdischarge after colorectal surgery and (2) identify patient and care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opioid-free analgesia.
METHODS:
This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enrolled adults (aged ≥18 years) undergoing elective colorectal surgery at 2 academic hospitals. Self-reported analgesic consumption was assessed weekly for 1 month postdischarge. Rates of opioid-free analgesia were analyzed descriptively. Predictors were identified using Bayesian model averaging, with higher posterior effect probability reflecting stronger association.
RESULTS:
A total of 344 participants were included (mean age: 58 ± 15 years; 54% male; 65% laparoscopic surgery; 31% rectal procedure; median hospital stay: 3 days [interquartile range: 1-5 days]). Discharge prescriptions included nonopioids (92% acetaminophen, 38%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and 2% gabapentinoids) and opioids (92%). At 30 days, 51% used no opioids postdischarge (47% after open surgery, 51% after laparoscopic surgery, 52% after procedures via stoma [ie, loop ostomy reversal]). Opioid-free analgesia was associated with older age (odds ratio: 1.04, posterior effect probability = 100%), fewer opioid pills prescribed (odds ratio: 0.92, posterior effect probability = 100%), no postdischarge cannabis use (odds ratio: 0.09, posterior effect probability = 96%), and high patient activation (ie, confidence for self-managing care; odds ratio: 2.20, posterior effect probability = 67%).
CONCLUSION:
Approximately half of patients undergoing colorectal surgery do not use opioids postdischarge. Older patients, those with higher patient activation, those who did not use cannabis, and those with fewer opioids prescribed were more likely to rely on opioid-free analgesia. Opioid-free postdischarge analgesia may be feasible after colorectal surgery and should be further investigated.
1,468
项与 对乙酰氨基酚 相关的新闻(医药)2026-01-27
Quadruplet regimen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ly deeper and more durable responses, higher MRD negativity and improved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versus a standard of care
Approval marks the twelfth indication for DARZALEX FASPRO® and fifth in the newly diagnosed setting, underscoring its role as foundational therapy for both newly diagnosed and relapsed/refractory multiple myeloma patients
HORSHAM, Pa., Jan. 27, 2026 /PRNewswire/ -- Johnson & Johnson (NYSE:JNJ) announced today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approved DARZALEX FASPRO® (daratumumab and hyaluronidase-fihj) in combination with bortezomib, lenalidomide and dexamethasone (D-VRd) for the treatment of adult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multiple myeloma (NDMM) who are ineligible for autologous stem cell transplant (ASCT). D-VRd is the only anti-CD38 antibody-based regimen with approved indications across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regardless of transplant eligibility.
The pivotal Phase 3 CEPHEUS study (NCT03652064) evaluated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D-VRd compared to bortezomib, lenalidomide and dexamethasone (VRd) in NDMM patients who were ineligible for ASCT or deferred ASCT as initial therapy.1 Today's milestone follows approval for D-VRd for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ho are newly diagnosed with multiple myeloma and eligible for ASCT.2
"D-VRd increased the depth and durability of response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risk of disease progression or death, and nearly doubled the rate of sustained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MRD)-negativity compared to VRd in patients ineligible for ASCT, solidifying this regimen as a potential standard of care for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with multiple myeloma," said Saad Z. Usmani, M.D., Chief, Myeloma Service,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and CEPHEUS principal investigator.* "MRD-negativity is a potential predictor of prolonged progression-free and overall survival and D-VRd is now the only quadruplet regimen approved by the FDA based on a study with MRD-negativity as a primary endpoint."
"This approval marks the twelfth indication for DARZALEX FASPRO overall and fifth in newly diagnosed multiple myeloma, underscoring its role as foundational therapy for both newly diagnosed and relapsed/refractory patients," said June Lanoue, U.S. President, Hematology, Johnson & Johnson Innovative Medicine. "CEPHEUS demonstrated the efficacy of a DARZALEX FASPRO-based quadruplet as a frontline standard of care. With this approval, patients can receive D-VRd when they are first diagnosed with multiple myeloma, an important milestone as we work to one day deliver a functional cure."
Findings from CEPHEUS showed that at a median follow-up of 22 months, the overall MRD-negativity rate at a sensitivity of 10-5 (no cancer cells detected within 100,000 bone marrow cells) was 52.3 percent vs 34.8 percent with VRd (P<0.0005).1 At a median follow-up of 39 months,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achieving sustained MRD-negativity of ≥12 months almost doubled at 42.6 percent vs 25.3 percent (P<0.0003) and D-VRd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risk of progression or death by 40 percent (hazard ratio [HR], 0.60; 95 percent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41-0.88; P<0.0078) vs VRd.1 At a median follow-up of nearly 5 years (59 months), D-VR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depth of response with higher rates of complete response or better at 81.2 percent vs 61.6 percent with VRd.1 Overall survival data were not yet mature.1 The effectiveness of D-VRd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in patients who refused ASCT as initial therapy.
The overall safety results of DARZALEX FASPRO®+VRd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adverse reactions seen for DARZALEX FASPRO® and VRd.1 In the CEPHEUS study, the most common adverse events (≥20%) in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multiple myeloma who received D-VRd wer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sensory neuropathy, musculoskeletal pain, diarrhea, fatigue, edema, rash, motor dysfunction, COVID-19, constipation, sleep disorder, cough, pneumonia, renal impairment, dizziness, nausea,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pyrexia, abdominal pain, dyspnea, decreased appetite, and bruising.1
About the CEPHEUS Study
CEPHEUS (NCT03652064) is a multicenter, randomized, open-label, Phase 3 study comparing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D-VRd vs VRd in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multiple myeloma who were ineligible for autologous stem cell transplant (ASCT) or refused ASCT as initial therapy. The primary endpoint was overall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MRD)-negativity rate at 10-5 sensitivity threshold. Secondary endpoints include complete response or better rate,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sustained MRD-negativity rate, MRD-negative rate at 1-year, overall response rate, time to and duration of response, PFS on next line of therapy, overall survival and safety. The trial enrolled 395 patients in 13 countries across North America, South America, and Europe.
About Multiple Myeloma
Multiple myeloma is a blood cancer that affects a type of white blood cell called plasma cells, which are found in the bone marrow.3 In multiple myeloma, these malignant plasma cells proliferate and replace normal cells in the bone marrow.4 Multiple myeloma is the second most common blood cancer worldwide and remains an incurable disease.5 In 2026, it is estimated that more than 36,000 people will be diagnosed with multiple myeloma in the U.S. and more than 12,000 will die from the disease.6 People with multiple myeloma have a 5-year survival rate of 59.8 percent.6 While some people diagnosed with multiple myeloma initially have no symptoms, most patients are diagnosed due to symptoms that can include bone fracture or pain, low red blood cell counts, tiredness, high calcium levels, kidney problems or infections.7,8
About DARZALEX FASPRO® and DARZALEX®
DARZALEX FASPRO® (daratumumab and hyaluronidase-fihj) received U.S. FDA approval in May 2020 and is approved for eleven indications in multiple myeloma, five of which are for frontline treatment in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who are transplant eligible or ineligible.1 It is the only subcutaneous CD38-directed antibody approved to treat patients with multiple myeloma. DARZALEX FASPRO® is co-formulated with recombinant human hyaluronidase PH20 (rHuPH20), Halozyme's ENHANZE® drug delivery technology.
DARZALEX® (daratumumab) received U.S. FDA approval in November 2015 and is approved in eight indications, three of which are in the frontline setting, including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who are transplant-eligible and ineligible. DARZALEX® is the first CD38-directed antibody approved to treat multiple myeloma.
DARZALEX®-based regimens have been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more than 720,000 patients worldwide.
In August 2012, Janssen Biotech, Inc. and Genmab A/S entered a worldwide agreement, which granted Janssen an exclusive license to develop, manufacture and commercialize daratumumab.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
DARZALEX FASPRO® INDICATIONS AND IMPORTANT SAFETY INFORMATION
INDICATIONS
DARZALEX FASPRO® (daratumumab and hyaluronidase-fihj) is indicated for the treatment of adult patients with multiple myeloma:
In combination with bortezomib, lenalidomide, and dexamethasone for induction and consolidation in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who are eligible for autologous stem cell transplant
In combination with bortezomib, lenalidomide, and dexamethasone in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who are ineligible for autologous stem cell transplant
In combination with bortezomib, melphalan, and prednisone in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who are ineligible for autologous stem cell transplant
In combination with lenalidomide and dexamethasone in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who are ineligible for autologous stem cell transplant and in patients with relapsed or refractory multiple myeloma who have received at least one prior therapy
In combination with bortezomib, thalidomide, and dexamethasone in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who are eligible for autologous stem cell transplant
In combination with pomalidomide and dexamethasone in patients who have received at least one prior line of therapy including lenalidomide and a proteasome inhibitor (PI)
In combination with carfilzomib and dexamethasone in patients with relapsed or refractory multiple myeloma who have received one to three prior lines of therapy
In combination with bortezomib and dexamethasone in patients who have received at least one prior therapy
As monotherapy in patients who have received at least three prior lines of therapy including a PI and an immunomodulatory agent or who are double refractory to a PI and an immunomodulatory agent
DARZALEX FASPRO® as monotherapy is indicated for the treatment of adult patients with high-risk smoldering multiple myeloma.
IMPORTANT SAFETY INFORMATION
CONTRAINDICATIONS
DARZALEX FASPRO® is contraindicated in patients with a history of severe hypersensitivity to daratumumab, hyaluronidase, or any of the components of the formulation.
WARNINGS AND PRECAUTIONS
Hypersensitivity and Other Administration Reactions
Both systemic administration-related reactions, including severe or life-threatening reactions, and local injection-site reactions can occur with DARZALEX FASPRO®. Fatal reactions have been reported with daratumumab-containing products, including DARZALEX FASPRO®.
Systemic Reactions
In a pooled safety population of 1446 patients with multiple myeloma (N=1235) or light chain (AL) amyloidosis (N=193) who received DARZALEX FASPRO® as monotherapy or as part of a combination therapy, 7% of patients experienced a systemic administration-related reaction (Grade 2: 3%, Grade 3: 0.8%, Grade 4: 0.1%). In patients with high-risk smoldering multiple myeloma (N=193), systemic administration-related reactions occurred in 17% of patients in AQUILA (Grade 2: 7%, Grade 3: 1%).
In all patients (N=1639), systemic administration-related reactions occurred in 7% of patients with the first injection, 0.5% with the second injection, and cumulatively 1% with subsequent injections. The median time to onset was 3.2 hours (range: 4 minutes to 3.5 days). Of the 283 systemic administration-related reactions that occurred in 135 patients, 240 (85%) occurred on the day of DARZALEX FASPRO® administration. Delayed systemic administration-related reactions have occurred in 1% of the patients.
Severe reactions included hypoxia, dyspnea, hypertension, tachycardia, and ocular adverse reactions, including choroidal effusion, acute myopia, and acute angle closure glaucoma. Other signs and symptoms of systemic administration-related reactions may include respiratory symptoms, such as bronchospasm, nasal congestion, cough, throat irritation, allergic rhinitis, and wheezing, as well as anaphylactic reaction, pyrexia, chest pain, pruritus, chills, vomiting, nausea, hypotension, and blurred vision.
Pre-medicate patients with histamine-1 receptor antagonist, acetaminophen, and corticosteroids. Monitor patients for systemic administration-related reactions, especially following the first and second injections. For anaphylactic reaction or life-threatening (Grade 4) administration-related reactions, immediately and permanently discontinue DARZALEX FASPRO®. Consider administering corticosteroids and other medications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DARZALEX FASPRO® depending on dosing regimen and medical history to minimize the risk of delayed (defined as occurring the day after administration) systemic administration-related reactions.
Ocular adverse reactions, including acute myopia and narrowing of the anterior chamber angle due to ciliochoroidal effusions with potential for increased intraocular pressure or glaucoma, have occurred with daratumumab-containing products. If ocular symptoms occur, interrupt DARZALEX FASPRO® and seek immediate ophthalmologic evaluation prior to restarting DARZALEX FASPRO®.
Local Reactions
In this pooled safety population of 1446 patients with multiple myeloma (N=1253) or light chain amyloidosis (N=193), injection-site reactions occurred in 8% of patients, including Grade 2 reactions in 1.1%. The most frequent (>1%) injection-site reactions were injection site erythema and injection site rash. In patients with high-risk smoldering multiple myeloma (N=193), injection-site reactions occurred in 28% of patients, including Grade 2 reactions in 3%. These local reactions occurred a median of 6 minutes (range: 0 minutes to 6.5 days) after starting administration of DARZALEX FASPRO®. Monitor for local reactions and consider symptomatic management.
Infections
DARZALEX FASPRO® can cause serious, life-threatening, or fatal infections. In patients who received DARZALEX FASPRO® in a pooled safety population including patients with smoldering multiple myeloma and light chain (AL) amyloidosis (N=1639), serious infections, including opportunistic infections, occurred in 24% of patients, Grade 3 or 4 infections occurred in 22%, and fatal infections occurred in 2.5%.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serious infection reported was pneumonia (8.5%).
Monitor patients for signs and symptoms of infection prior to and during treatment with DARZALEX FASPRO® and treat appropriately. Administer prophylactic antimicrobials according to guidelines.
Neutropenia
Daratumumab may increase neutropenia induced by background therapy. Monitor complete blood cell counts periodically during treatment according to manufacturer's prescribing information for background therapies. Monitor patients with neutropenia for signs of infection. Consider withholding DARZALEX FASPRO® until recovery of neutrophils. In lower body weight patients receiving DARZALEX FASPRO®, higher rates of Grade 3-4 neutropenia were observed.
Thrombocytopenia
Daratumumab may increase thrombocytopenia induced by background therapy. Monitor complete blood cell counts periodically during treatment according to manufacturer's prescribing information for background therapies. Consider withholding DARZALEX FASPRO® until recovery of platelets.
Embryo-Fetal Toxicity
Based on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DARZALEX FASPRO® can cause fetal harm when administered to a pregnant woman. DARZALEX FASPRO® may cause depletion of fetal immune cells and decreased bone density. Advise pregnant women of the potential risk to a fetus. Advise females with reproductive potential to use effective contraception during treatment with DARZALEX FASPRO® and for 3 months after the last dose.
The combination of DARZALEX FASPRO® with lenalidomide, thalidomide, or pomalidomide is contraindicated in pregnant women because lenalidomide, thalidomide, and pomalidomide may cause birth defects and death of the unborn child. Refer to the lenalidomide, thalidomide, or pomalidomide prescribing information on use during pregnancy.
Interference With Serological Testing
Daratumumab binds to CD38 on red blood cells (RBCs) and results in a positive indirect antiglobulin test (indirect Coombs test). Daratumumab-mediated positive indirect antiglobulin test may persist for up to 6 months after the last daratumumab administration. Daratumumab bound to RBCs masks detection of antibodies to minor antigens in the patient's serum. The determination of a patient's ABO and Rh blood type are not impacted.
Notify blood transfusion centers of this interference with serological testing and inform blood banks that a patient has received DARZALEX FASPRO®. Type and screen patients prior to starting DARZALEX FASPRO®.
Interference With Determination of Complete Response
Daratumumab is a human immunoglobulin G (IgG) kappa monoclonal antibody that can be detected on both the serum protein electrophoresis (SPE) and immunofixation (IFE) assays used for the clinical monitoring of endogenous M-protein. This interference can impact the determination of complete response and of disease progression in some DARZALEX FASPRO®-treated patients with IgG kappa myeloma protein.
ADVERSE REACTIONS
In multiple myeloma, the most common adverse reaction (≥20%) with DARZALEX FASPRO® monotherapy is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The most common adverse reactions with combination therapy (≥20% for any combination) include fatigue, nausea, diarrhea, dyspnea, sleep disorder, headache, rash, renal impairment, motor dysfunction, pyrexia, cough, muscle spasms, back pain, vomiting, hypertension, musculoskeletal pain, decreased appetite,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abdominal pain,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peripheral neuropathy, peripheral sensory neuropathy, constipation, pneumonia, edema, dizziness, bruising, and COVID-19.
The most common adverse reactions (≥20%) in patients with high-risk smoldering multiple myeloma who received DARZALEX FASPRO® monotherapy ar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musculoskeletal pain, fatigue, diarrhea, rash, sleep disorder, sensory neuropathy, and injection site reactions.
The most common hematology laboratory abnormalities (≥40%) with DARZALEX FASPRO® are decreased leukocytes, decreased lymphocytes, decreased neutrophils, decreased platelets, and decreased hemoglobin.
Please click here to read full Prescribing Information for DARZALEX FASPRO®.
DARZALEX® INDICATIONS AND IMPORTANT SAFETY INFORMATION
INDICATIONS
DARZALEX® (daratumumab) is indicated for the treatment of adult patients with multiple myeloma:
In combination with bortezomib, melphalan, and prednisone in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who are ineligible for autologous stem cell transplant
In combination with lenalidomide and dexamethasone in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who are ineligible for autologous stem cell transplant and in patients with relapsed or refractory multiple myeloma who have received at least one prior therapy
In combination with bortezomib, thalidomide, and dexamethasone in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who are eligible for autologous stem cell transplant
In combination with pomalidomide and dexamethasone in patients who have received at least one prior line of therapy including lenalidomide and a proteasome inhibitor
In combination with carfilzomib and dexamethasone in patients with relapsed or refractory multiple myeloma who have received one to three prior lines of therapy
In combination with bortezomib and dexamethasone in patients who have received at least one prior therapy
As monotherapy in patients who have received at least three prior lines of therapy including a proteasome inhibitor (PI) and an immunomodulatory agent or who are double-refractory to a PI and an immunomodulatory agent
CONTRAINDICATIONS
DARZALEX® is contraindicated in patients with a history of severe hypersensitivity (eg, anaphylactic reactions) to daratumumab or any of the components of the formulation.
WARNINGS AND PRECAUTIONS
Infusion-Related Reactions
DARZALEX® can cause severe and/or serious infusion-related reactions including anaphylactic reactions. These reactions can be life threatening, and fatal outcomes have been reported. In clinical trials (monotherapy and combination: N=2066), infusion-related reactions occurred in 37% of patients with the Week 1 (16 mg/kg) infusion, 2% with the Week 2 infusion, and cumulatively 6% with subsequent infusions. Less than 1% of patients had a Grade 3/4 infusion-related reaction at Week 2 or subsequent infusions. The median time to onset was 1.5 hours (range: 0 to 73 hours). Nearly all reactions occurred during infusion or within 4 hours of completing DARZALEX®. Severe reactions have occurred, including bronchospasm, hypoxia, dyspnea, hypertension, tachycardia, headache, laryngeal edema, pulmonary edema, and ocular adverse reactions, including choroidal effusion, acute myopia, and acute angle closure glaucoma. Signs and symptoms may include respiratory symptoms, such as nasal congestion, cough, throat irritation, as well as chills, vomiting, and nausea. Less common signs and symptoms were wheezing, allergic rhinitis, pyrexia, chest discomfort, pruritus, hypotension and blurred vision.
When DARZALEX® dosing was interrupted in the setting of ASCT (CASSIOPEIA) for a median of 3.75 months (range: 2.4 to 6.9 months), upon re-initiation of DARZALEX®, the incidence of infusion-related reactions was 11% for the first infusion following ASCT. Infusion-related reactions occurring at re-initiation of DARZALEX® following ASCT were consistent in terms of symptoms and severity (Grade 3 or 4: <1%) with those reported in previous studies at Week 2 or subsequent infusions. In EQUULEUS, patients receiving combination treatment (n=97) were administered the first 16 mg/kg dose at Week 1 split over two days, ie, 8 mg/kg on Day 1 and Day 2, respectively. The incidence of any grade infusion-related reactions was 42%, with 36% of patients experiencing infusion-related reactions on Day 1 of Week 1, 4% on Day 2 of Week 1, and 8% with subsequent infusions.
Pre-medicate patients with antihistamines, antipyretics, and corticosteroids. Frequently monitor patients during the entire infusion. Interrupt DARZALEX® infusion for reactions of any severity and institute medical management as needed. Permanently discontinue DARZALEX® therapy if an anaphylactic reaction or life-threatening (Grade 4) reaction occurs and institute appropriate emergency care. For patients with Grade 1, 2, or 3 reactions, reduce the infusion rate when re-starting the infusion.
To reduce the risk of delayed infusion-related reactions, administer oral corticosteroids to all patients following DARZALEX® infusions. Patients with a history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may require additional post-infusion medications to manage respiratory complications. Consider prescribing short- and long-acting bronchodilators and inhaled corticosteroids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Ocular adverse reactions, including acute myopia and narrowing of the anterior chamber angle due to ciliochoroidal effusions with potential for increased intraocular pressure or glaucoma, have occurred with DARZALEX® infusion. If ocular symptoms occur, interrupt DARZALEX® infusion and seek immediate ophthalmologic evaluation prior to restarting DARZALEX®.
Interference With Serological Testing
Daratumumab binds to CD38 on red blood cells (RBCs) and results in a positive indirect antiglobulin test (indirect Coombs test). Daratumumab-mediated positive indirect antiglobulin test may persist for up to 6 months after the last daratumumab infusion. Daratumumab bound to RBCs masks detection of antibodies to minor antigens in the patient's serum. The determination of a patient's ABO and Rh blood type is not impacted. Notify blood transfusion centers of this interference with serological testing and inform blood banks that a patient has received DARZALEX®. Type and screen patients prior to starting DARZALEX®.
Neutropenia and Thrombocytopenia
DARZALEX® may increase neutropenia and thrombocytopenia induced by background therapy. Monitor complete blood cell counts periodically during treatment according to manufacturer's prescribing information for background therapies. Monitor patients with neutropenia for signs of infection. Consider withholding DARZALEX® until recovery of neutrophils or for recovery of platelets.
Interference With Determination of Complete Response
Daratumumab is a human immunoglobulin G (IgG) kappa monoclonal antibody that can be detected on both the serum protein electrophoresis (SPE) and immunofixation (IFE) assays used for the clinical monitoring of endogenous M-protein. This interference can impact the determination of complete response and of disease progression in some patients with IgG kappa myeloma protein.
Embryo-Fetal Toxicity
Based on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DARZALEX® can cause fetal harm when administered to a pregnant woman. DARZALEX® may cause depletion of fetal immune cells and decreased bone density. Advise pregnant women of the potential risk to a fetus. Advise females with reproductive potential to use effective contraception during treatment with DARZALEX® and for 3 months after the last dose.
The combination of DARZALEX® with lenalidomide, pomalidomide, or thalidomide is contraindicated in pregnant women because lenalidomide, pomalidomide, and thalidomide may cause birth defects and death of the unborn child. Refer to the lenalidomide, pomalidomide, or thalidomide prescribing information on use during pregnancy.
ADVERSE REACTIONS
The most frequently reported adverse reactions (incidence ≥20%) were: upper respiratory infection, neutropenia, infusion related reactions, thrombocytopenia, diarrhea, constipation, anemia, peripheral sensory neuropathy, fatigue, peripheral edema, nausea, cough, pyrexia, dyspnea, and asthenia. The most common hematologic laboratory abnormalities (≥40%) with DARZALEX® are: neutropenia, lymphopenia, thrombocytopenia, leukopenia, and anemia.
Please
click here
to read full Prescribing Information for DARZALEX®.
About Johnson & Johnson
At Johnson & Johnson, we believe health is everything. Our strength in healthcare innovation empowers us to build a world where complex diseases are prevented, treated, and cured, where treatments are smarter and less invasive, and solutions are personal. Through our expertise in Innovative Medicine and MedTech, we are uniquely positioned to innovate across the full spectrum of healthcare solutions today to deliver the breakthroughs of tomorrow and profoundly impact health for humanity.
Learn more at or at . Follow us at @JNJInnovMed.
Janssen Research & Development, LLC and Janssen Biotech, Inc. are both Johnson & Johnson companies.
Cautions Concerning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This press release contains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as defined in the 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 of 1995 regarding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the potential benefits and treatment impact of DARZALEX FASPRO® (daratumumab and hyaluronidase-fihj). The reader is cautioned not to rely on thes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These statements are based on current expectations of future events. If underlying assumptions prove inaccurate or known or unknown risks or uncertainties materialize, actual results could vary materially from the expectations and projections of Johnson & Johnson.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challenges and uncertainties inherent in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cluding the uncertainty of clinical success and of obtaining regulatory approvals; uncertainty of commercial success; manufacturing difficulties and delays; competition, including technological advances, new products and patents attained by competitors; challenges to patents; product efficacy or safety concerns resulting in product recalls or regulatory action; changes in behavior and spending patterns of purchasers of health care products and services; changes to applicable laws and regulations, including global health care reforms; and trends toward health care cost containment. A further list and descriptions of these risks, uncertainties and other factors can be found in Johnson & Johnson's most recent Annual Report on Form 10-K, including in the sections captioned "Cautionary Note Regarding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and "Item 1A. Risk Factors," and in Johnson & Johnson's subsequent Quarterly Reports on Form 10-Q and other filings with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Copies of these filings are available online at , or on request from Johnson & Johnson. Johnson & Johnson does not undertake to update any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 as a result of new information or future events or developments.
*Dr. Saad Z. Usmani has provided consulting and advisory services to Johnson & Johnson; he has not been paid for any media work.
SOURCE Johnson & Johnson
21%
more press release views with
Request a Demo
临床结果上市批准临床3期引进/卖出细胞疗法
2026-01-27
近年来,随着对风湿病发病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及生物制药技术的迅猛发展,风湿病的靶向药物发展如火如荼。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为更好地规范风湿病诊疗及靶向药物的合理应用,就目前已取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应用的风湿病靶向药物逐一介绍,为临床医生规范使用提供参考。今日分享的主要是TNF拮抗剂部分。
TNF-α 拮抗剂
现有的研究已证实,TNF-α在 RA 及其他炎症性疾病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TNF-α可由多种细胞产生,其与受体结合后启动多条信号通路参与风湿免疫性疾病的发病。TNF-α介导多种炎症反应的重要作用为以其为靶点治疗风湿免疫性疾病提供了理论依据。TNF-α拮抗剂通过多种机制发挥临床疗效,包括下调局部和全身性促炎细胞因子,减少淋巴细胞活化及其向关节部位迁移等。目前,临床有五种常用的TNF-α拮抗剂:
1. 英夫利西单抗(Infliximab)
英夫利西单抗是一种人鼠嵌合型抗 TNF-α单克隆抗体,由人IgGIκ的恒定区耦联高亲和力鼠抗人TNF-α的可变区组成。这种结构的组成70%来源于人。英夫利西单抗可以迅速与人类可溶性或膜形式的TNF-α形成稳定的复合物,并终止TNF-α的生物活性及信号。
英夫利西单抗抗适用于RA、成人及 6 岁以上儿童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瘘管性CD、AS、银屑病及成人溃 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对中重度活动性RA,可与甲氨蝶呤联用减轻疾病症状和体征,改善身体机能,预防患者残疾。
首次静脉注射推荐剂量为3mg/kg,其后于第2周和第 6周再次给药,以后每隔 8周给药 1次。部分RA患者亦可以英夫利西单抗与其他改善病情抗风湿药(DMARDs)联用,或单药治疗。
对疗效不佳的RA患者,英夫利西单抗的剂量可增至10mg/kg,和/或给药间隔调整为每4周1次。
对AS,首次推荐剂量为 5mg/kg,其后于第 2周和第6周再次给药,以后每隔6周予1次相同剂量。
斑块型银屑病、成人中重度活动性CD、瘘管性CD 及成人UC,首次予英夫利西单抗 5mg/kg,其后于第2周和第6周及以后每隔8周予1次相同剂量。
英夫利西单抗应用前,可根据医生判断予患者如抗组胺药物、氢化可的松和/或对乙酰氨基酚预处理,同时降低输注速度,以减少输液相关反应的风险,特别是对既往曾发生过输液相关反应的患者更应慎重。
2 依那西普(Etanercept)
依那西普是一种可溶性p75‑TNF‑受体/Fc 二聚体融合结构,其TNF受体域与TNF-α 三聚体3个受体结合位点中的 2个结合,从而阻断TNF-α和TNF受体的相互作用。
目前国内也有生物类似药注射用重组人Ⅱ型TNF受体‑抗体融合蛋白,已广泛应用于临床。
依那西普或重组人Ⅱ型TNF受体‑抗体融合蛋白适用于RA和AS。中至重度活动性RA成年患者对包括甲氨蝶呤在内的DMARDs无效时,可使用依那西普与甲氨蝶呤联用以控制病情。
依那西普经皮下注射给药,在RA、AS 患者中的推荐剂量为25mg,每周2次(间隔72~96h),或50mg每周1次。
老年患者(≥65 岁)无需进行剂量调整。皮下注射可以注射在大腿、腹部和上臂,每次与前次注射部位不同,至少相距 3 cm,禁止注射于皮肤柔嫩、瘀伤、发红或发硬部位。
3 阿达木单抗(Adalimumab)
阿达木单抗是通过抗体库技术克隆产生的人源化 IgG1κ抗TNF单克隆抗体。它通过与可溶性和跨膜TNF-α高亲和性结合,阻止 TNF-α与其受体结合,达到中和TNF-α生物活性的目的。
阿达木单抗适用于RA、AS、银屑病、CD、葡萄膜炎、多关节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polyarticular juvenile idiopathic arthritis,pJIA)(2 岁及 2 岁以上)以及儿童斑块状银屑病(4岁及4岁以上)。
在RA,阿达木单抗用于对DMARDs包括MTX疗效不佳的成年中重度活动性 RA,与甲氨蝶呤联用可减缓关节损伤,改善身体机能。
阿达木单抗对CD的治疗,主要用于充足糖皮质激素(以下简称激素)和/或免疫抑制治疗不充分、不耐受或禁忌的中重度活动性CD成年患者。
阿达木单抗亦适用于对激素治疗不充分、需减少使用激素、或不适合进行激素治疗的成年非感染性中间葡萄膜炎、后葡萄膜炎和全葡萄膜炎。
对 RA、AS 的推荐剂量为 40mg 皮下注射,每2周1次。RA单一药物治疗时,如某些患者出现疗效下降,可提高给药频率为每周1次。对银屑病、葡萄膜炎成年患者,建议首次皮下注射80mg,其后1周开始每2周皮下注射40mg。中重度活动性CD 成年患者,推荐第0周 160mg,其后的第2周为80mg,诱导治疗后,每2周1次40mg皮下注射。老年患者无需调整剂量。
4 戈利木单抗(Golimumab)
戈利木单抗是一种人源化抗TNF-α单克隆抗体,是采用基因工程技术用人源化的 TNF-α免疫小鼠生成人源化的可变区和恒定区组成的抗体。
戈利木单抗适用于RA和AS,皮下注射给药,每次50mg,每月1次。RA的治疗应戈利木单抗与甲氨蝶呤联合使用。
5 赛妥珠单抗(Certolizumab)
赛妥珠单抗是一种重组的Fab片段,与相对分子质量为40000的聚乙二醇结合的人源化抗 TNF-α单克隆抗体。
鉴于这种结构,赛妥珠单抗不具备完全单克隆抗体才有的Fc介导的激活补体依赖性或抗体依赖的细胞毒作用。赛妥珠单抗可与血清和组织中TNF-α结合,导致其失活和降解。
赛妥珠单抗与甲氨蝶呤联用,可治疗对DMARDs(包括甲氨蝶呤)疗效不佳的中重度活动性RA成年患者。
赛妥珠单抗的推荐剂量在首次、第2周、第4周为400mg,以后每2周1次200mg皮下注射。
· 使用风险提示 ·
TNF-α不仅在风湿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制中起关键作用,同时亦是正常免疫平衡不可或缺的,故上述药物使用时仍需考虑安全因素。
不同种类的TNF-α拮抗剂,其注射部位反应、输液反应及免疫原性和结局不同,潜在感染和肿瘤发病增加,诱导自身免疫病,引起脱髓鞘疾病、骨髓抑制,甚至引起充血性心力衰竭等,均是相关性不良事件。
英夫利西单抗会引起输液反应,主要表现为头痛、恶心,通常是短暂性的。
皮下注射部位出现局部注射反应是依那西普、注射用重组人Ⅱ型 TNF 受体‑抗体融合蛋白、阿达木单抗、戈利木单抗和赛妥珠单抗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但这些不良反应很少导致治疗中断。
TNF-α拮抗剂会诱导相应抗体产生,应用依那西普治疗者中约有3%的患者产生药物相关抗体;应用3mg/kg 英夫利西单抗治疗者中,21%的患者产生抗体;应用阿达木单抗、戈利木单抗和赛妥珠单抗治疗者中,约有4%~12% 的患者产生相应抗体;这些药物与甲氨蝶呤联用时,产生抗体的比率降至1%。
TNF-α拮抗剂可使感染和严重感染的风险增高,但其他因素如病情严重性、应用其他药物(如激素)及存在合并症亦有关。机会感染,特别是播散性结核分枝杆菌感染,与使用 TNF-α拮抗剂有关,治疗前需进行潜伏结核的筛查,可显著降低用药后结核的发生率。TNF-α拮抗剂在理论上会影响宿主对恶性肿瘤的防御,但迄今为止,在临床试验和长期临床应用中,恶性肿瘤整体发生率与健康人群相似。
参考文献
吴歆, 戚务芳, 王志强, 等 . 风湿病靶向药物使用规范[J]. 中华内科杂志, 2022, 61(7): 756-763.DOI: 10.3760/cma.j.cn112138-20211220-00897.
来源:医陆光华
●口服他克莫司、环孢素、羟氯喹的注意事项
●强直性脊柱炎患者小酌一杯,可以吗?饮食与日常护理全攻略
●手指弯不了、膝盖打不直?类风湿晨僵怎么处理才科学?
临床结果申请上市ASH会议
2026-01-27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2026 年专升本招生考试《药理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基本要求
《药理学》科目旨在考核学生对药理学基本知识点的掌握和运用能力,主要包括药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常见临床治疗药物的类型,尤其是各类代表药物的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等内容;同时,还将考核考生的病案分析与合理用药能力及药理学常用实验操作技术要点。
二、考试内容
《药理学》考试大纲
第一部分:总论
药理学总论主要包括绪论、药效学、药动学三个部分。其主要阐述了药理学的研究内容、
学科任务、研究方法、新药研发过程中的药理学研究、药效学与药动学等内容。
通过测试,要求学生应该对药理学学科的研究内容、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有较全面的了
解,其中药效学与药动学部分尤为重要。
一、绪论
本部分主要介绍了药理学的定义、研究内容、学科特点与学科任务,药理学的发展简史,
研究方法及新药研发与药理学等内容,应注意常用术语的掌握。
考核知识点:掌握药物的基本概念、药理学、药效学、药动学、安慰剂、随机双盲等的
概念与药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熟悉新药研发中的药理学研究,如非临床研究与四期临床试
验;熟悉药理学实验中常用的给药操作技术要点,如腹腔注射、灌胃、皮下注射、耳缘静脉
给药等;了解药理学的学科任务与研究方法。
二、药动学
本部分主要研究药物在体内的变化规律,包括机体对药物的处置即吸收、分布、代谢、
排泄过程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并应用药动学原理及数学模型定量地描述血药浓度随时间变化
的规律与消除动力学;应注意对常见药动学参数的把握。通过此部分的测试,考查考生是否
具备基本的指导临床合理用药的能力。
考核知识点:掌握药物的吸收、首关消除、离子障的概念及临床意义,熟悉影响药物吸
收的主要因素;掌握药物的分布及与血浆蛋白结合的特点,并熟悉影响分布的主要因素;掌
握代谢即生物转化、肝药酶、药酶诱导剂、药酶抑制剂的概念及临床意义,能够列举常见的药酶诱导剂与抑制剂,并熟悉影响药物代谢的主要因素;掌握肝肠循环的概念,熟悉药物的
排泄及影响因素;掌握常见的药动学参数如半衰期、表观分布容积、清除率、生物利用度、
药时曲线下的面积、稳态血药浓度等的概念及临床意义;熟悉药时曲线的基本特点;熟悉药
物消除动力学的基本类型:一级和零级消除动力学的特点比较;了解药物跨膜转运的类型及
特点。
三、药效学
本部分主要研究药物对机体产生的作用及作用规律,主要包括药物的作用、量效关系、
药物的受体机制等内容;应注意对药效学常见术语的掌握。
考核知识点:掌握药物不良反应的概念、主要类型(副作用、毒性反应、变态反应、后
遗效应、继发反应、停药反应等)的定义及特点;药物的量效关系(剂量、效应、效能、效
价强度)、治疗指数的意义;掌握激动药与拮抗药的概念与特点;熟悉药物的基本作用、选
择作用及作用的两重性,能区分对因治疗与对症治疗;熟悉影响药物效应的因素;熟悉药物
耐受性、耐药性、依赖性的概念;熟悉硫酸镁不同给药途径对药物作用的影响及原理;了解
受体的特点与药物的非特异性机制。
第二部分:各论
药理学各论部分是按照临床治疗疾病的药物类型来具体阐述各类药物的药理学基本知
识,主要包括药物的分类与代表药、主要药动学特点、作用机制、药理作用、临床应用、不
良反应、禁忌症等内容。
通过该部分的测试能够考查学生对临床常用药物药理学知识的基本掌握程度,并通过病
案分析考核学生基本的指导临床合理用药能力。
一、传出神经系统药理学概论
本单元主要介绍了传出神经系统药理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
考核知识点:掌握递质的概念,熟悉乙酰胆碱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合成、贮存、释放和消
除过程;掌握受体的分类、分布及对应的生理效应;熟悉常见的传出神经系统药物的分类与
代表药。
二、拟胆碱药和胆碱酯酶复活药
本单元主要介绍了传出神经系统药物中的拟胆碱药与胆碱酯酶复活药的分类、代表药
物、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不良反应与临床应用等内容。
考核知识点:掌握胆碱受体激动药(毛果芸香碱)的药理作用与机制,特别是对眼的作
用及临床应用;掌握抗胆碱酯酶药(新斯的明)的药理作用与机制、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
掌握有机磷农药的中毒机制、临床中毒程度辨识及相应的解救方法,了解胆碱酯酶复活药碘解磷定与毒扁豆碱的作用特点。
三、胆碱受体阻断药
本单元主要介绍了胆碱受体阻断药的分类、代表药物、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不良反应
与临床应用等内容。
考核知识点:掌握 M 受体阻断剂-阿托品的药理作用、机制、临床用途、不良反应、禁
忌症;了解东莨菪碱、山莨菪碱的作用特点及临床应用;了解 N2 受体阻断剂的分类及代表
药-琥珀胆碱与筒箭毒碱的区别。
四、拟肾上腺素药
本单元主要介绍了拟肾上腺素药的分类、代表药物、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不良反应与
临床应用等内容。
考核知识点:掌握拟肾上腺素药的分类及代表药;掌握α受体激动药-去甲肾上腺素的
机制、药理作用、临床用途、不良反应;掌握α、β受体激动药-肾上腺素的机制、药理作
用、临床用途、不良反应;熟悉β受体激动药-异丙肾上腺素的机制、药理作用、临床用途、
不良反应;并能够比较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与异丙肾上腺素的药理作用差异。
五、肾上腺素受体阻断药
本单元主要介绍了肾上腺素受体阻断药的分类、代表药物、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不良
反应与临床应用等内容。
考核知识点:熟悉“肾上腺素升压作用的翻转”作用原理;掌握α受体阻断药-酚妥拉
明的机制、药理作用、临床用途及不良反应;熟悉β受体阻断药-普萘洛尔的机制、药理作
用、临床用途、不良反应、禁忌症。
六、镇静催眠药
本单元主要介绍了镇静催眠药的分类、代表药物、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不良反应与临
床应用等内容。
考核知识点:掌握镇静催眠药物的分类及代表药;掌握苯二氮䓬类药物-地西泮的药理
作用、作用机制、临床用途、不良反应,急性中毒的抢救药-氟马西尼;掌握苯二氮䓬类药
物在镇静催眠应用中取代巴比妥类的优势;熟悉巴比妥类药物-苯巴比妥的药理作用、作用
机制、临床用途、不良反应。
七、抗精神失常药
本单元主要介绍了抗精神失常药的分类、代表药物、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不良反应与
临床应用等内容。考核知识点:掌握吩噻嗪类抗精神分裂症药-氯丙嗪的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临床用途、
不良反应;掌握常见抗抑郁药的分类及代表药物,如 5-HT 再摄取抑制药氟西汀、舍曲林等;
熟悉常见的抗躁狂药特点,如碳酸锂、卡马西平等。
八、镇痛药
本单元主要介绍了镇痛药的分类、代表药物、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不良反应与临床应
用等内容。
考核知识点:掌握镇痛药的分类及代表药;掌握吗啡的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临床用途、
不良反应,禁忌症;熟悉哌替啶(度冷丁)的药理作用及特点、临床用途及不良反应;熟悉
其他镇痛药特点:芬太尼、喷他佐辛、曲马多等;了解癌痛镇痛的“三阶梯疗法”;掌握小
鼠热板法镇痛实验的原理与操作要点。
九、解热镇痛抗炎药及抗痛风药
本单元主要介绍了解热镇痛抗炎药的分类、代表药物、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不良反应
与临床应用等内容,以及抗痛风药作用机制和代表药物。
考核知识点:掌握解热镇痛抗炎药的共同作用机制(抑制前列腺素合成酶)与解热、镇
痛、抗炎作用特点,分类(非选择性/选择性环氧酶抑制剂)及环氧酶-1 与-2 的差异;非选
择性抑制剂中,阿司匹林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不良反应及禁忌证,对乙酰氨基酚的作用
特点与肝损伤风险,布洛芬的作用及应用;选择性环氧酶-2 抑制剂(如塞来昔布)的作用
特点、应用及心血管风险;抗痛风药的分类,别嘌醇的作用、应用及不良反应,秋水仙碱的
作用与应用,丙磺舒等促尿酸排泄药的特点;同时需知晓相关药物体内过程、相互作用及痛
风病理机制等内容。
十、 抗高血压药
本单元主要介绍了抗高血压药的分类、代表药物、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不良反应与临
床应用等内容。
考核知识点:抗高血压药分类(利尿剂、钙通道阻滞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
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β受体阻断药);各类代表药(氢氯噻嗪、硝苯地平、卡托普利、
氯沙坦、普萘洛尔)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降压药合理应用原则;熟悉利尿剂
降压机制(排钠利尿、减少血容量);钙通道阻滞药对血管的选择性作用;血管紧张素转换
酶抑制剂的干咳不良反应机制;β受体阻断药对心率和心输出量的影响;其他类型抗高血压
药(如α受体阻断药、血管扩张药)的作用特点;了解高血压的病理生理机制;抗高血压药
的发展趋势;新型抗高血压药(如肾素抑制剂)的作用简介。
十一、 抗慢性心功能不全药
本单元主要介绍了抗慢性心功能不全药的分类、代表药物、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不良反应与临床应用等内容。
考核知识点:掌握抗慢性心功能不全药物的分类及常见代表药物;了解强心苷的中毒及
防治。
十二、抗心绞痛药
本单元主要介绍了抗心绞痛药的分类、代表药物、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不良反应与临
床应用等内容。
考核知识点:掌握抗心绞痛药的分类及代表药;掌握硝酸甘油的药动学特点、给药方式、
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临床用途与不良反应;掌握硝酸酯类和β受体阻断药在抗心绞痛方面
合用的理论依据及注意事项;熟悉β受体阻断药-普萘洛尔、钙通道阻滞药-硝苯地平的抗心
绞痛作用特点。
十三、呼吸系统药物
本单元主要介绍了呼吸系统药物的分类、代表药物、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不良反应与
临床应用等内容。
考核知识点:熟悉平喘药的分类及其代表药物;熟悉镇咳药的分类及代表药物;熟悉祛
痰药的分类及代表药物。
十四、消化系统药物
本单元主要介绍了消化系统药物的分类、代表药物、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不良反应与
临床应用等内容。
考核知识点:掌握治疗消化性溃疡药的分类及代表药;熟悉其他常见消化系统药物类型
及代表药;了解抗幽门螺杆菌的四联疗法用药。
十五、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物
本单元主要介绍了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物的分类、代表药物、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不
良反应与临床应用等内容。
考核知识点:掌握糖皮质激素类药物的生理作用、药理作用、临床用途、不良反应及禁
忌症;熟悉氢化可的松、地塞米松的作用特点;熟悉大鼠足趾肿胀抗炎实验的原理与操作要
点;了解糖皮质激素的用法和疗程。
十六、甲状腺激素和抗甲状腺药物
本单元主要介绍了甲状腺激素和抗甲状腺药物的分类、代表药物、药理作用、作用机制、
不良反应与临床应用等内容。
考核知识点:掌握抗甲状腺药物的分类及代表药物;熟悉各类代表药物的作用特点。十七、胰岛素和口服降血糖药物
本单元主要介绍了胰岛素和口服降血糖药物的分类、代表药物、药理作用、作用机制、
不良反应与临床应用等内容。
考核知识点:掌握磺酰脲类(格列本脲等)、双胍类(二甲双胍)、α-葡萄糖苷酶抑
制剂(阿卡波糖)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熟悉磺酰脲类机制与相互作用、双胍
类给药注意、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特点;了解格列奈类、噻唑烷二酮类特点及新型药物机
制;熟悉糖尿病药物治疗的个体化原则(根据年龄、体重、肝肾功能、血糖水平选择药物);
联合用药原则(如二甲双胍联合磺酰脲类,增强降糖效果);了解糖尿病综合管理(药物、
饮食、运动结合)的重要性。
十八、抗菌药物概论
本单元主要介绍了抗菌药物概论的分类、代表药物、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不良反应与
临床应用等内容。
考核知识点:掌握常用抗菌药物术语如化学治疗、抗生素、抗菌谱、抗菌活性、最低抑
菌浓度、最低杀菌浓度、化疗指数、抗生素后效应的概念;熟悉抗菌药物的作用机制与代表
药,及细菌的耐药机制;了解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原则与抗生素滥用的危害性。
十九、β-内酰胺类抗生素
本单元主要介绍了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分类、代表药物、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不良
反应与临床应用等内容。
考核知识点:掌握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抗菌机制和耐药机制;掌握青霉素类药物的分
类及各类抗菌作用特点;掌握青霉素 G 的药理作用(抗菌谱)、临床应用、不良反应及过敏
性休克的防治;熟悉四代头孢常见代表药及特点比较;了解非典型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分
类及代表药。
二十、其他类型抗生素
本单元主要介绍了其他类型抗生素的分类、代表药物、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不良反应
与临床应用等内容。
考核知识点:掌握大环内酯类、氨基糖苷类、四环素类等的代表药及其主要不良反应,
如红霉素、链霉素、四环素、氯霉素等。
二十一、人工合成抗菌药
本单元主要介绍了人工合成抗菌药的分类、代表药物、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不良反应
与临床应用等内容。
考核知识点:掌握喹诺酮类药物的作用机制、常用药物环丙沙星、氧氟沙星、左氧氟沙星、加替沙星等抗菌作用特点与不良反应;熟悉磺胺类药物的共性,常用药物磺胺嘧啶、磺
胺异恶唑等抗菌作用特点;了解磺胺类与甲氧苄啶联合使用的原理;了解甲硝唑的抗菌作用
和临床应用。
二十二、组胺受体阻断药
本单元主要介绍了组胺受体阻断药的分类、代表药物、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不良反应
与临床应用等内容。
考核知识点:熟悉 H1、H2 受体阻断药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和不良反应。熟悉常用药
物如苯海拉明、异丙嗪、雷尼替丁、法莫替丁等的作用特点。
二十三、抗恶性肿瘤药
本单元主要介绍了抗恶性肿瘤药的分类、代表药物、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不良反应与
临床应用等内容。
考核知识点:熟悉抗恶性肿瘤药物的分类、代表药物及主要不良反应;了解抗肿瘤药物
联合应用的原则。
三、题目类型
单选题、判断题、简答题、案例分析题。
四、考试形式及试卷难易结构
1.本考试采取闭卷、笔试的形式。试卷满分 20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
2.试卷难易程度比例——难、中、易分别占 20%、30%、50%。
五、参考教材
《药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罗跃娥、樊一桥主编,2018 年第 3 版,ISBN:9787117256339。
点击卡片进入专升本必刷题软件获取题库
100 项与 对乙酰氨基酚 相关的药物交易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研发状态
批准上市
10 条最早获批的记录, 后查看更多信息
登录
| 适应症 | 国家/地区 | 公司 | 日期 |
|---|---|---|---|
| 头痛 | 美国 | 1978-02-09 | |
| 镇痛 | 日本 | 1966-07-01 | |
| 发热 | 中国 | 1966-01-01 | |
| 疼痛 | 中国 | 1966-01-01 |
未上市
10 条进展最快的记录, 后查看更多信息
登录
| 适应症 | 最高研发状态 | 国家/地区 | 公司 | 日期 |
|---|---|---|---|---|
| 牙痛 | 临床3期 | 美国 | 2017-07-19 | |
| 普通感冒 | 临床3期 | - | 2017-02-01 | |
| 咽炎 | 临床3期 | - | 2017-02-01 | |
| 发作性紧张型头痛 | 临床3期 | 美国 | 2013-04-01 | |
| 急性疼痛 | 临床3期 | 美国 | 2008-01-01 | |
| 术后疼痛 | 临床3期 | 美国 | 2006-11-01 | |
| 子宫癌 | 临床3期 | 美国 | 2006-11-01 | |
| 急性偏头痛 | 临床3期 | 美国 | 2006-03-01 | |
| 髋关节炎 | 临床3期 | - | 2005-10-18 | |
| 糖尿病性神经病变 | 临床3期 | - | 2003-12-01 |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临床结果
临床结果
适应症
分期
评价
查看全部结果
| 研究 | 分期 | 人群特征 | 评价人数 | 分组 | 结果 | 评价 | 发布日期 |
|---|
临床4期 | 140 | 餘繭獵糧鏇齋遞觸願選(艱襯獵鬱齋憲襯廠廠醖) = 齋衊鏇製積餘糧獵膚範 築糧廠襯獵獵窪構醖夢 (壓製積顧製繭觸顧淵選 ) 更多 | 不佳 | 2025-12-01 | |||
Strong opioid + Placebo | 餘繭獵糧鏇齋遞觸願選(艱襯獵鬱齋憲襯廠廠醖) = 遞製夢鑰鹽糧觸壓齋範 築糧廠襯獵獵窪構醖夢 (壓製積顧製繭觸顧淵選 ) 更多 | ||||||
临床2期 | 159 | (Drug Arm A) | 獵廠願網鏇夢構餘鏇簾(鏇壓觸廠憲餘壓鹹鬱襯) = 簾網製鬱艱願憲獵蓋觸 襯繭遞築鹹範鬱齋鬱製 (製齋觸齋網糧蓋齋鏇築, 14.1) 更多 | - | 2025-11-25 | ||
(Drug Arm B) | 獵廠願網鏇夢構餘鏇簾(鏇壓觸廠憲餘壓鹹鬱襯) = 鬱鬱遞糧鏇膚繭襯積窪 襯繭遞築鹹範鬱齋鬱製 (製齋觸齋網糧蓋齋鏇築, 16.3) 更多 | ||||||
临床4期 | 132 | (Group 1- Received Ibuprofen (N=39)) | 膚範鏇繭製積製積構願(窪鑰齋膚鹹鏇鬱憲鏇鹽) = 構築齋糧範選願願製觸 窪觸鏇憲廠範壓壓糧選 (壓鹹網獵積願鬱遞膚壓, 構糧淵製觸鹽構夢鬱製 ~ 遞鏇製鹽壓構鏇顧顧鏇) 更多 | - | 2025-10-29 | ||
(Group 2- Received Dexamethasone (N=43)) | 膚範鏇繭製積製積構願(窪鑰齋膚鹹鏇鬱憲鏇鹽) = 衊鹹觸獵製鹽鑰醖廠衊 窪觸鏇憲廠範壓壓糧選 (壓鹹網獵積願鬱遞膚壓, 範襯衊築衊製鹹齋憲衊 ~ 艱遞選鹽網淵顧蓋願顧) 更多 | ||||||
临床4期 | 8 | 獵顧構淵壓鹽鑰遞選觸(膚願觸鑰衊積鹽窪遞製) = 製糧積築廠憲簾淵範齋 繭襯壓顧繭繭憲獵鹹築 (鏇獵糧鏇遞壓簾衊鏇膚, 衊憲醖鑰襯獵築顧淵鹹 ~ 積淵簾齋繭願網範鑰鹽) 更多 | - | 2025-10-21 | |||
临床4期 | - | 214 | Placebo Oral Tablet+acetaminophen (IV Acetaminophen and Placebo Pills) | 範鑰鏇淵願齋願觸壓鏇(淵鏇餘糧壓顧網獵顧積) = 衊餘衊願鏇積齋憲觸鑰 餘選夢範憲鹽餘淵構獵 (夢艱網齋鹽遞觸夢廠夢, 58.16) 更多 | - | 2025-06-29 | |
Placebos+Acetaminophen (Placebo IV (Normal Saline) + Oral Acetaminophen) | 範鑰鏇淵願齋願觸壓鏇(淵鏇餘糧壓顧網獵顧積) = 廠顧願餘蓋淵淵醖醖製 餘選夢範憲鹽餘淵構獵 (夢艱網齋鹽遞觸夢廠夢, 57.59) 更多 | ||||||
临床1/2期 | 59 | (Phase IIA Dose Expansion (Dose Exp.), Cohort 2, Arm 2.1A) | 築糧蓋獵憲壓膚築鹽齋 = 獵積膚鬱鏇艱鹹觸鏇範 廠顧齋壓襯願遞簾遞鬱 (鏇淵廠膚膚鬱範構獵糧, 遞膚網艱醖鏇積醖膚觸 ~ 積憲遞鑰鬱鹹顧獵選襯) 更多 | - | 2025-06-08 | ||
(All Participants in Phase IIA Dose Expansion and Phase IIB Dose Expansion) | 築糧蓋獵憲壓膚築鹽齋 = 選築廠構鹹膚鹹夢鹹鹽 廠顧齋壓襯願遞簾遞鬱 (鏇淵廠膚膚鬱範構獵糧, 衊膚衊餘築襯選繭淵簾 ~ 艱鬱壓網餘鬱網築鬱構) 更多 | ||||||
临床1/2期 | 34 | (2/Phase II Arm - Palifermin at the Recommended Phase 2 Dose) | 觸蓋鑰壓艱簾遞選齋壓 = 願範構網窪齋鬱願艱壓 築餘夢製鑰鹹範遞繭獵 (繭醖壓鹹積顧鹹廠窪餘, 醖壓獵積積夢憲觸鏇窪 ~ 艱襯觸鑰壓觸鑰襯願網) | - | 2025-06-05 | ||
(1/Phase 1: Dose Escalation Arm - Palifermin) | 鑰遞廠夢壓築襯壓糧淵 = 餘襯觸網壓艱選獵繭簾 顧鑰鬱選糧範積醖製遞 (蓋繭構獵構網齋鏇獵夢, 夢獵膚壓憲願鑰艱顧衊 ~ 齋糧淵窪遞齋廠鹹遞遞) | ||||||
临床3期 | 82 | Intravenous acetaminophen | 窪範網鹹願壓餘衊觸夢(製簾醖構鹽繭窪積繭鬱) = 網襯顧蓋鏇積鑰窪鹽廠 齋淵窪選襯糧積鏇餘積 (鹽範憲艱憲鏇築淵製範, 4.0 ~ 27.1) | 不佳 | 2025-06-01 | ||
Oral acetaminophen | 窪範網鹹願壓餘衊觸夢(製簾醖構鹽繭窪積繭鬱) = 鹽襯製淵鹽鑰艱鹹憲獵 齋淵窪選襯糧積鏇餘積 (鹽範憲艱憲鏇築淵製範, 4.0 ~ 29.5) | ||||||
N/A | 447 | (Hyperinflammatory Phenotype) | 夢夢廠衊窪觸簾簾鑰願(鹽網廠衊廠鹽觸獵繭齋) = 憲膚艱淵廠鏇網廠窪範 衊簾製範選夢衊壓壓願 (糧遞鏇遞餘夢糧廠淵製 ) 更多 | 不佳 | 2025-05-16 | ||
(Hypoinflammatory Phenotype) | 夢夢廠衊窪觸簾簾鑰願(鹽網廠衊廠鹽觸獵繭齋) = 壓窪糧築鏇遞構繭衊鹹 衊簾製範選夢衊壓壓願 (糧遞鏇遞餘夢糧廠淵製 ) 更多 | ||||||
N/A | - | 145 | Patient-controlled analgesia (PCA) with intravenous opioids | - | 积极 | 2025-05-14 | |
齋衊構選願艱繭膚壓餘(膚蓋襯廠淵製餘鏇獵範) = 艱遞鹽壓鹽淵壓鹽築糧 網衊壓襯廠醖淵膚夢構 (鬱壓簾願構積築醖膚醖 ) 更多 |
登录后查看更多信息
转化医学
使用我们的转化医学数据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药物交易
使用我们的药物交易数据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核心专利
使用我们的核心专利数据促进您的研究。
登录
或

临床分析
紧跟全球注册中心的最新临床试验。
登录
或

批准
利用最新的监管批准信息加速您的研究。
登录
或

特殊审评
只需点击几下即可了解关键药物信息。
登录
或

生物医药百科问答
全新生物医药AI Agent 覆盖科研全链路,让突破性发现快人一步
立即开始免费试用!
智慧芽新药情报库是智慧芽专为生命科学人士构建的基于AI的创新药情报平台,助您全方位提升您的研发与决策效率。
立即开始数据试用!
智慧芽新药库数据也通过智慧芽数据服务平台,以API或者数据包形式对外开放,助您更加充分利用智慧芽新药情报信息。
生物序列数据库
生物药研发创新
免费使用
化学结构数据库
小分子化药研发创新
免费使用